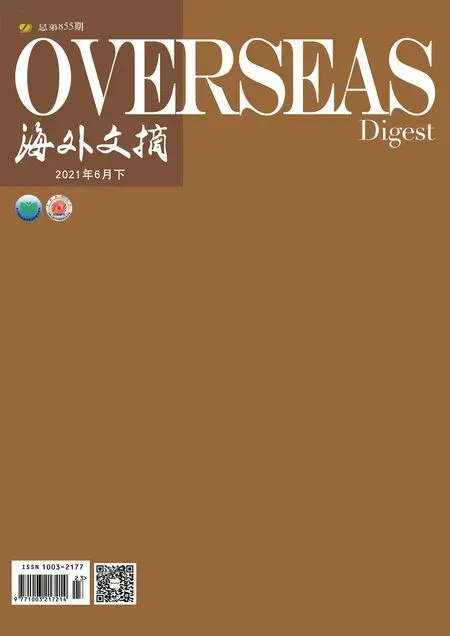對于標注漢語的字母體系的初探
寧秀野 (俄)尤利婭·茲羅賓娜
(圣彼得堡國立大學,俄羅斯圣彼得堡 301800)
1 古音與音變
本文提及的漢語古音主要包括,中古漢語發音和近古漢語發音。中古漢語經過了唐末及五代十國的戰亂,開始出現清唇音。再經歷蒙古帝國的擴張后,近古漢語出現。明末清初漢語出現團字,漸漸地奠定了現代漢語的發音。
1.1 古無輕唇音
該規律首次由清代語言學者錢大昕(1728-1804)提出,古無唇音說的是晚唐之前沒有輔音/f/、/f?/、/v/、/?/的讀法,只有/p/、/p?/、/b/、/m/的讀法,如“無”輔音為/m/,不是/?/。“佛”輔音部分不讀/v/,只讀/b/。這也與梵語中的Buddha相對。
1.2 團字的出現
由于1644 年滿清入關,漢語受到了北方語言的影響,漢語開始發生了腭化。原中古漢語中的/g/,/k/,/h/在近古漢語中變為了/j/,/q/,/x/。所以“江”在中古漢語中聲母為/g/,而在近古漢語中則變為了j的發音。“下”在中古音中聲母為/h/,而近古音中變為了/x/音。
2 字母標注漢字的歷史
字母標注漢字的歷史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1)藏語字母標注漢字。(2)波斯字母標注漢字。(3)拉丁及西里爾標注漢字。第一個時期(約7 世紀至9 世紀)是漢語中古音保存較為完整的一個時期,其中只有部分字出現了輕唇化的趨勢,而團字完全沒有出現。第二個時期(13 世紀之后)較為復雜,歷史跨度也很大,理論上在13 世紀其實就已經出現波斯字母標注漢字的情況,但現在掌握的資料大約是17 世紀,也就意味著此時漢語里已經存在了輕唇音和團字。這個時期也是理論與實際歷史讀音偏差較大的一個階段。第三個時期(16 世紀中葉至現在)經歷明清音韻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了團字的出現,這個時期資料豐富,而且標注更加體系化。
2.1 藏語字母標注漢字
怛羅斯戰役后,大唐在西域的勢力減弱。導致了吐蕃勢力的擴張,之后河西走廊也被吐蕃占領了。如日本漢學家高田時雄所說,當時吐蕃攻占了敦煌,統治者讓當地的百姓用藏文字母表示漢語,即使在歸義軍收復敦煌后,當地百姓仍然沿用藏文字母表示漢字,一些敦煌文獻足以佐證此段歷史。
本文將會以敦煌Pelliot tib.1259 殘片為例(如圖1 所示),去解釋中古漢語的特點,基于中古漢語和中古藏語發音的相似性,對于此階段不做兩種語言的發音對比。Pelliot tib.1259 的正面是由漢語所寫的《大般若波羅密多經》,而后面則是以藏文字母所寫的一首詩,該詩名為《游江樂·泛龍舟》。對照漢字后詩中出現了“風”“飛”“泛”“無”這樣的字眼,而它們讀音分別是/phung//pyi//bam//bu/。這里說明了中古無輕唇音,但/phung/這樣讀音的出現可以說明該殘片屬于唐代末期,也就是出現了輕唇音的趨勢。詩中同樣出現了“溪”“西”“江”這樣的字樣,他們的表音分別是/si/“/si/“gang/,這里可以佐證在唐代末期并未出現團字。

圖1 法藏敦煌文獻編號:Pelliot tib. 1259(背面)(1)
游江樂·泛龍舟
春風細雨霑衣濕, 何時恍惚憶揚州(春)。
南至柳城新造口,北對蘭陵孤驛樓。
回望東西二湖水, 復見長江萬里流。
白鶴(鷺)雙飛出溪壑, 無數江鷗水上游。
2.2 波斯-阿拉伯字母標注漢字
13 世紀隨著蒙古帝國的擴張,歐亞大陸大部分地區國與國之間的關口被打開。由于蒙古帝國對商業的重視,所以很快商業就在亞歐之間繁榮了起來。這時內地吸引了西邊很多的商人涌入,而進入內地的大部分商人的母語是波斯語,他們不會說漢語,所以他們只好用波斯字母標注漢語,以便學習漢語。
本階段將以《小兒錦》為例來說明近古漢語的特點,《小兒錦》的標注系統可以說是明清音韻的產物。其中輕唇音已經出現比如“廢”輔音已經用“?”(f)來表示,而“無” 輔音被標為了“?”(w)來表示。同時團字也出現在了標音系統中,為此更好的標音,波斯-阿拉伯字母發生了音變。比如:波斯-阿拉伯字母中 “?”在波斯語中只有“s”的音,但在漢語中卻出現了“q”和“x”的音,波斯字母中“?”只有“d”的音,而在漢語中發生音變,出現了“j”的音。除此之外還出現了其他波斯字母的音變現象,波斯字母中“?”只有/d?/的音,而在漢語中則變為了“zh”的音。波斯-阿拉伯字母中“?”只有“t”的音,而在漢語中發生音變,變為了“z”的音。由于漢語有些發音在波斯語中沒有,所以就出現了新的字母,比如“?”讀作“q”,專門用來拼寫漢語中的團字“q”。相比波斯語,在拼寫漢語時需要將所有的元音標出,要不在閱讀時會出現元音不明的情況,導致理解錯誤。《小兒錦》中并沒有標出聲調,但在使用時也沒有出現聲調不準的情況,可能是語境導致的。
2.3 拉丁及西里爾字母標注漢字
由于13 世紀的商業活動繁榮,所以各國的商人留下很多的游記,他們的游記吸引更多歐洲人去往亞洲。一開始是耶穌會進入大明傳教,而后來進入大清的商人和各種文人墨客越來越多。這個時期大致是從明末到清末,明清官話就在這個時期誕生。而明清官話本書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南京官話,明朝初期為了校正中原雅音,所以參考江淮官話,以南京話為基礎,奠定南京官話。第二部分是北京官話,清朝中葉,由于清朝的統治中心在北方,首都在北京,所以形成了以北方方言為參考,北京話為基礎的北京官話。
2.3.1 拉丁字母標注漢字
這個階段是明代中末期,意大利人利瑪竇來到了大明,編寫了《西字奇跡》一書。本書以拉丁字母標注漢字,成為了漢語拼音的先驅,當時讀音還是以南京官話為主。理論上南京官話區分入聲、尖團及平翹舌音。但其實《西字奇跡》會與理論上的南京官話有出入。
輕唇音在《西字奇跡》里已經出現,尤其體現在了“f”音上,比如:中古漢語中“復”和“緋”的聲母是“b”的音,但在《西字奇跡》中都變為了“f”的音。不過“我”的聲母依然是“ng”沒有出現“w”這樣的輕唇音,原因可能是正音的結果,要不就是只有部分字母完成了唇音化。
團字并沒有在《西字奇跡》中出現,雖然利瑪竇也將“j”“q”“x”用在了標注體系中,但發音與現代漢語中的團字完全不同。由于利瑪竇的注音更偏向意大利語和拉丁語讀音,所以“j”與“i”的發音是相近的,“j”本身也是“i”的變體,如在中世紀Iesus(耶穌)可能被寫成Jesus,那么在標注漢語時也會沿用這樣的讀音。比如:“弱”“如”的聲母就被注為“j”,但發音與團字的“j”毫無關系。“q”的發音為/k?u?/通常與后面的讀音“u”連用,如Kuran(古蘭經)這樣的注音是與阿拉伯語有出入的,所以要標成Quran。同樣在標注漢語時,“觀”和“廣”的韻母被注成“qu”,同樣與團字的“q”沒有關系。“x”的發音是/eks/,放在單詞中是發/ks/和/gs/的音,如“Xerxes”(薛西斯)中的“x”就會讀成/ks/。而在標注漢字時“x”的發音是/?/,所以這里發生了音變,如:“上”與“世”的聲母就是/?/,而與團音“x”無關。本文對照了在普通話中是團字讀音的字,相比之下在《西字奇跡》中,普通話的“j”“q”“x”被標為了“k”“c”“k”“sh”“s”“h”。如“堅”在普通話中聲母是“j”,而在《西字奇跡》中被標成了“kien”。而“降”和“蹶”的聲母也是如此。“漸”在普通話中也是同樣的情況,但在本書中被標為了“cien”。普通話中聲母“q”,在本書中被標成“k”,如“其”被注為“ki”。普通話中的“x”在本書中標為了三個聲母,分別是“? ”“s”“h”,如:“性”被標為“?im”,“信”被標為“sin”,“行”則標成“him”。由此可以說明團字的出現應該要比《西字奇跡》(1605 年)要晚。還需要注意的是,該標注體系有聲調系統,其中標出了五個調“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這為以后還原南京官話提供了便利。
2.3.2 西里爾字母標注漢字
本階段是上個階段的后續,由于更多的商人及文人墨客來到大清,帶回了更多關于中國的見聞,之后更多世界各國的人來到了中國。為了回應上面的趨勢,于1862 年清政府創辦了京師同文館。為此前任北京俄羅斯正教駐北京傳道團領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Палладiй)和(俄羅斯)帝國駐北京總領事巴·斯·波波夫(П.С. Поповъ)于1888 年編寫《漢俄合璧韻編》。
1728 年大清朝廷開設“正音書館”開始推廣北京官話,北京官話以北京話為參考,通常運用于官場。北京官話中已經出現了輕唇音和團字,所以可以說北京官話奠定了現代漢語發音的基礎。
本文將以大司祭巴拉第的《漢俄合璧韻編》為例,說明清代晚期的北京官話的讀音。該時期已經出現了輕唇音“f”和“w”,分別用西里爾字母“ф”和“у”來表示,如:“發”會標成“фа”,“風”會注成“фэнъ”,“無”會注成“у”。同樣這個時期也出現了團字“j”“q”“x”分別用“цз”“ц”“с”來表示,如:“嘉”會拼成“цзя”,“妻”會拼成“цы”,“薩”會拼成“са”。但“цз”“ц”“с”也同時表示尖字“z”“c”“s”,所以受標音的影響會出現混淆現象。在俄語中/i/類元音前的輔音要發生顎化,如:第ди、定динъ、丟дю,體ти、聽тинъ 等,這樣的地域發音可能會發生誤讀。
3 結論
本文力圖對比漢字以及字母的區別,但原則上語義與音素是無法對比的,所以本文將語義的讀音轉化成音素,這樣可以于同等條件下進行對比。但這樣的對比是存疑的,因為我們很難說用其他語言的字母體系能夠準確的表達漢語象形文字的發音。所以我們只好引用更多的字母體系進行對比。但這又引發了漢語本身的歷史發音和其他語言的地域發音的問題,以及這兩種發音相遇會產生什么結果。
在這里主要列舉了四個時期,他們分別是:唐代中末期(公元7 世紀至9 世紀)、蒙元時期(公元13 世紀左右)、明代末期(1563-1644)、清代末期(1840-1912)。漢語經過11 個世紀的演變,聲母出現了輕唇音和團字。其中有四套字母體系作為見證,先開始是唐代中末期藏文字母標注漢字,該字母體系幾乎完整的保留了中古音中的重唇音和團字出現之前相應讀音,其中僅僅出現了唇音的趨勢,可以說佐證了古無輕唇音和團字發音,并關聯其以后的讀音發展,也為后面的對比留下了很好的范本。此時中古藏語的讀音與中古漢語的讀音相近,所以幾乎沒有音變現象,相應的絕大多數中古藏語字母可以對應中古漢語發音,以至于如今敦煌文獻中的藏語字母標注殘片成為了校對中古音的證據之一。當然之前大約4 世紀也有用粟特字母表示漢語的情況,但因為表示的范圍基本只限于地名,所以在這里不予考慮。由于蒙元時期從中國的西部涌入了很多商人,所以出現了波斯字母表示漢字的情況。可以確定的是這個時期已經出現輕唇音,但由于掌握的資料是清代的(可能后來波斯字母表示體系又按著清代的官話重修了),所以已經出現團字。但明代末期的《小兒錦》中是否有團字,就要指望發現新的資料了。相比之下波斯字母為表示漢字也發生了音變并創造了新的字母去表示“j”“q”“x”,但在明朝末期的《西字奇跡》中,拉丁字母標注漢字的方案卻佐證了明代末期沒有團音的出現,而此時輕唇音已經確定出現。相比之下拉丁字母在表示“x”的時候發生音變變成/?/的發音。在晚清的《漢俄合璧韻編》中,輕唇音與團字已經完全出現,由于后期新出現的團字也給字母標注漢字增加了“新的挑戰”,所以只能取西里爾字母中相近的讀音來標注,所以為了標注“j”“q”“x”相應的字母“цз”“ц”“с”也發生了音變,除此之外俄語中/i/類元音前的輔音會發生顎化也會在標注漢字時消失。
所以由此可以對比出漢字(以發音的角度)的特點與字母讀音的特點及性質。漢字的讀音在不同的時期,由于發生音變會導致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發音,在性質上具有歷時性。由于發音也會受到歷史事件的影響,如,滿清入關等。所以漢字讀音也有其歷史性。相比之下無論在什么時期,字母都可以將漢字的讀音拆成聲母和韻母,到后期用于今人對于漢字古音的考證,所以說字母本身有分析性的。但字母的發音也受到地域發音的影響,由于其他語言的發音也是受到地域影響,導致對漢字的標音不準,所以字母也有其地域性(見表1)。字母本身已經是對字符進行了最大的縮減,相比《唐韻》《廣韻》的反切體系,藏文字母30 個、波斯字母32 個、拉丁字母26 個、西里爾字母37 個字母(十月革命之前)所編成的注音體系,更容易幫助來自各國的人學習漢語。通過以上的對比,我們發現對于漢字標音和字母讀音的研究,不止是語言學問題,還與背后的歷史和地域特點息息相關。

表1 以歷史語音音變,地域發音和字母音變角度的標注漢語對應表
注釋
(1)http://idp.bl.uk/database/oo_cat.a4d?shortref=Pelliot Tibetain_II;random=14857.a.對譯采用拉丁字母標注(也借鑒了其他的對譯).b.點為藏語中音節的劃分.c.漢語詩歌與藏語字母在讀音上一一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