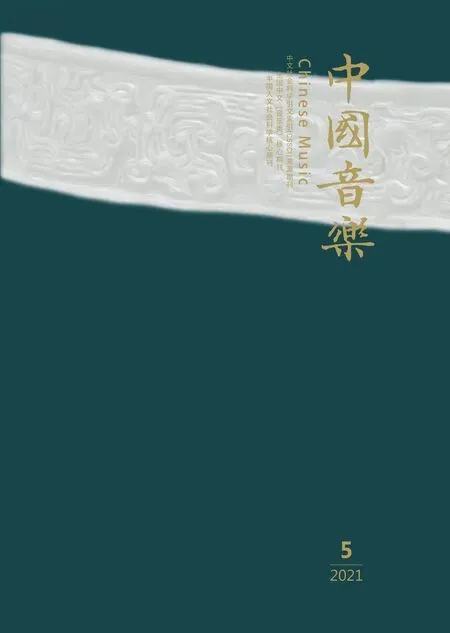彝族諾蘇火把節(jié)和祭祖送靈儀式體系的衍變關(guān)系
○ 路菊芳
一、兩類儀式在諾蘇文化系統(tǒng)中的分層格局
(一)從節(jié)日體系看兩類儀式的對立與協(xié)調(diào)關(guān)系
根據(jù)民俗學(xué)界研究,中國現(xiàn)代節(jié)日體系呈現(xiàn)明顯的官方與民間二元對立的特征。其實這種二元結(jié)構(gòu)自古就有萌芽,只是古代中國官方節(jié)日大多依據(jù)民間傳統(tǒng)習(xí)俗而擬定,傳統(tǒng)節(jié)日就是官方假日,如“唐代以前主要還是以民間傳統(tǒng)節(jié)日這一單一結(jié)構(gòu)為主,官府將一些傳統(tǒng)節(jié)日予以確定,供職于官府的大小官吏們也參與對那些節(jié)日的慶賀”①魏華仙:《官方節(jié)日:唐宋節(jié)日文化的新特點》,《四川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2009年,第2期,第108頁。等。但從節(jié)日的體系而言,官與民又統(tǒng)一于一個節(jié)日結(jié)構(gòu)中,即使唐代新興的很多節(jié)日,如唐朝統(tǒng)治者有意建構(gòu)的中和節(jié)、誕節(jié)、降圣節(jié),以及唐人民間發(fā)明的清明、八月十五等,②參見張宏梅:《唐代的節(jié)日與風(fēng)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頁。學(xué)者們認(rèn)為仍不能以官方和民間來劃分,因為唐朝節(jié)日民俗的流變發(fā)展是官方和民間共同在發(fā)揮作用。③同注②,第8頁。由此說明,在中國古代節(jié)日系統(tǒng)中,官方與民間一直在共同建構(gòu)節(jié)日,協(xié)調(diào)二元結(jié)構(gòu)的關(guān)系;同時也佐證了節(jié)日建構(gòu)并非今日之新題。而官方節(jié)日(官定節(jié)日、官辦節(jié)日)與傳統(tǒng)節(jié)日真正出現(xiàn)分野,源自20世紀(jì)20年代官方推行公歷(西歷),要求所有節(jié)假日根據(jù)公歷擬定,廢除夏歷(舊歷、老百姓用的農(nóng)歷)。但公歷節(jié)日對于老百姓生活造成諸多不便,官方用公歷假期,老百姓依然用舊歷祭祀過節(jié),無奈之下,官方只能取消對舊歷的限制,而采用公歷(官方)和夏歷(民間)并行的兩套歷法格局。④參見高丙中:《民族國家的時間管理—中國節(jié)假日制度的問題及其解決之道》,《開放時代》,2005年,第1期,第76頁。由此,也形成了現(xiàn)在節(jié)日體系中官方與民間的二元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
彝族文化中,節(jié)日往往體現(xiàn)為宗教儀式活動,火把節(jié)就是民間祭祀火神和祖先、慶祝豐收的傳統(tǒng)節(jié)日。現(xiàn)代官方將火把節(jié)作為法定節(jié)假日,是遵循了傳統(tǒng)節(jié)日的時間結(jié)構(gòu)和祭祀主題。雖然官方火把節(jié)中包含了諸多現(xiàn)代音樂文化信息,官方參與是其主要標(biāo)志行為,但在節(jié)日的時間框架內(nèi)依然體現(xiàn)著官與民的和諧統(tǒng)一。如阿都地區(qū)官方火把節(jié),無論儀式時間安排,還是儀式內(nèi)容主體,均具有明顯的傳統(tǒng)節(jié)日特征。而祭祖送靈自古即為古代彝族統(tǒng)治者為祭祀祖先創(chuàng)制的儀式結(jié)構(gòu),傳承至今體現(xiàn)的仍是民間傳統(tǒng),是屬于家支范圍內(nèi)人群的節(jié)日。那么,再從節(jié)日儀式的音樂文化內(nèi)容看,官方火把節(jié)是在民間火把節(jié)祭祀娛樂音樂活動基礎(chǔ)上的再造或建構(gòu)。因為傳統(tǒng)音樂文化仍是其固定內(nèi)容,加之畢摩誦唱的納入,又增添了官方火把節(jié)與諾蘇傳統(tǒng)宗教信仰的親緣關(guān)系。當(dāng)然官方火把節(jié)也吸收了現(xiàn)代通俗音樂文化,只是這些都是不穩(wěn)定的流動性因素。所以官方火把節(jié)在儀式內(nèi)容上體現(xiàn)了繼承傳統(tǒng)信仰,容納族性音樂,又展現(xiàn)當(dāng)代節(jié)慶儀式文化認(rèn)同的復(fù)合性特征。但祭祖送靈儀式是以畢摩誦唱為主要音聲,特定場合應(yīng)用世俗音樂的民間傳統(tǒng)節(jié)日。
由此,兩類儀式均歸屬為彝族諾蘇現(xiàn)代節(jié)日體系,體現(xiàn)著官方與民間、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民族與族群文化的二元特征。
(二)從民族和族群層看兩類儀式的主文化、亞文化關(guān)系
“亞文化、交互文化、主文化”是1992年美國馬克·斯洛賓針對音樂文化空間提出的基本描寫方式及詞匯組。⑤馬克·斯洛賓在其《西方微觀音樂文化的比較研究》(1992年)一文中認(rèn)為,主文化有區(qū)域、跨區(qū)域、單一民族國家的特征;具有主宰性,也可看成一種支配性的主流意識,兼具有形性和無形性,且無所不在的特征;是復(fù)合、矛盾的結(jié)合物。亞文化具有地域性特征,主要涉及文化層面有家庭、鄰里、組織委員會、族群、性別和階層。轉(zhuǎn)引自楊民康:《音樂民族志方法導(dǎo)論—以中國傳統(tǒng)音樂為實例》,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20年,第203頁。若從民族層和族群層⑥關(guān)于國族、民族和族群的內(nèi)涵和關(guān)系,參看筆者論文《彝族諾蘇人的現(xiàn)代火把節(jié)儀式音樂與國族文化認(rèn)同》,《中國音樂》,2020年,第6期。看兩類儀式,同樣存在著主文化和亞文化的交錯關(guān)系。
1.從民族層看兩類儀式的主、亞文化關(guān)系
自1987年涼山州政府將火把節(jié)做為法定節(jié)日,到1994年第一屆國際火把節(jié)舉行,火把節(jié)逐漸從地域性亞文化向區(qū)域性主文化發(fā)展。2016年義諾區(qū)馬邊政府突破傳統(tǒng),舉辦官方火把節(jié),火把節(jié)自此成為了涼山彝族諾蘇人各土語區(qū)共有的節(jié)日⑦涼山除了義諾土語區(qū)沒有民間火把節(jié)祭祀,其他土語區(qū)大多有此傳統(tǒng),至于何因也是眾說紛紜,所以義諾土區(qū)的馬邊官方才建構(gòu)火把節(jié)。,并且在不同地區(qū)呈現(xiàn)以官方為主導(dǎo)的主文化特色,代表的是民族文化認(rèn)同。如火把節(jié)開幕式中領(lǐng)導(dǎo)致辭、參與點火等官方行為,昭示了火把節(jié)儀式隱含的政治性色彩,也由此注定了火把節(jié)與祭祖送靈儀式不同文化風(fēng)格和儀式屬性的特征。
相對而言,祭祖送靈儀式尼姆撮畢是彝族遠(yuǎn)古時期已存在,備受當(dāng)時統(tǒng)治階層重視的傳統(tǒng)儀式活動。傳承至今,儀式規(guī)模和時長雖然有所縮減,但鑒于此儀式是彝族人死后靈魂歸祖的重要通道,儀式內(nèi)容涉及彝族天文歷法、自然地理、歷史文化和教育生產(chǎn)等各方面經(jīng)典文獻(xiàn),故其在諾蘇族群文化觀念中仍占據(jù)至高位置。彝族諺語“父養(yǎng)子娶妻生子,子養(yǎng)父送祖歸靈”就是對前述言論的重要論證。而至當(dāng)下社會,祭祖送靈儀式已無任何政治色彩,更多作為諾蘇族群一項古老宗教習(xí)俗自然傳承。因此,從民族層次分析祭祖送靈儀式,即處在與火把節(jié)并峙的亞文化層,代表的是族群文化認(rèn)同。
2.從族群層次看兩類儀式的主、亞文化關(guān)系
鑒于現(xiàn)代涼山的義諾土語區(qū)民間無火把節(jié)傳統(tǒng)習(xí)慣,所以從族群層看火把節(jié),它只是處于亞文化層。當(dāng)然義諾土語區(qū)民間傳說中曾有過此類習(xí)俗,只是未找到確切的文獻(xiàn)記載。而祭祖送靈儀式卻是既有地域性傳承因素,又有跨地域性傳播的區(qū)域文化特征;它不僅流傳在諾蘇族群中,在云南、貴州的彝族支系中同樣存在。因此,相對火把節(jié)而言,祭祖送靈儀式又是非常復(fù)雜和龐大的祭祀體系。由此看,祭祖送靈儀式又占據(jù)主文化層位置。
3.從儀式音樂文化看兩類儀式的對比和模仿關(guān)系
根據(jù)近幾年考察可知,火把節(jié)中主要存在四種音樂文化元素:當(dāng)代政治音樂文化、宗教音樂文化、民間音樂文化、通俗音樂文化。其中政治音樂文化并非直接呈現(xiàn),而是通過隱喻的手段和途徑,借用其他音樂表現(xiàn)形式來展示。由此,單獨從音樂類型看各地火把節(jié)儀式音樂,主要包含三種基本元素:畢摩儀式音樂、民間音樂和通俗音樂。民間音樂如民間歌曲朵樂嗬、丫,器樂音樂如馬布、口弦等。其中朵樂嗬是傳統(tǒng)火把節(jié)中固有音樂形式,現(xiàn)全部被移入官方火把節(jié),而丫作為諾蘇人山歌,在阿都火把節(jié)中也是固定出現(xiàn)。最有意思的是宗教儀式中的畢摩誦唱,尤以改編祭祖送靈儀式中《指路經(jīng)》(見譜例1)的模式性音調(diào)為盛,在不同地區(qū)火把節(jié)中廣為傳播(見譜例2)。兩首譜例中標(biāo)記Ⅰ、Ⅱ型旋律及其變化形式,可知兩類儀式音樂形態(tài)之間的模式與變體關(guān)系。需要指出的是火把節(jié)中畢摩誦唱不再是單純傳統(tǒng)祭祖儀式中誦唱,而是表演誦唱;專設(shè)的畢摩點圣火儀式也成為近幾年各地官方火把節(jié)中的共性特征。
譜例1 祭祖送靈儀式中的畢摩誦唱《指路經(jīng)》片段;采錄時間、地點:2017年10月、西昌太和農(nóng)村;誦者:曲比拉伙(美姑畢摩);采錄、記譜:阿余鐵日、路菊芳

譜例2 火把節(jié)中改編的畢摩誦唱片段;采錄時間、地點:2017年7月20日、布拖火把場;采錄、記譜:路菊芳

由此,舞臺上的畢摩表演唱具有了藝術(shù)性和舞臺效果,并改變了最初的儀式功能,更多作為一種傳統(tǒng)宗教文化符號象征而存在,同時隱喻著火把節(jié)與諾蘇傳統(tǒng)宗教信仰的一脈相承。
而祭祖送靈儀式在過去時期,也是神圣與世俗結(jié)合的狂歡。《西南夷族考察記》載“是日親友畢至,男女老幼,各穿新服……惟賽馬必賭輸贏,大哭不下淚。音樂、口琴、大號、槍聲,震動一時。以紅黃黑白布千條萬縷懸于竹頂,隨風(fēng)飄舞,此時雖為喪禮,但一般青年男女,借此男女錯綜的大好機會,實行初步的戀愛工作,真是悲喜之劇合演,可謂盛極一時。”⑧曲目藏堯:《西南夷族考察記》,轉(zhuǎn)引自馬玉華主編:《西南邊疆卷三—云南全省邊民分布冊(五種)》,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03頁。說明早期的祭祖送靈儀式也發(fā)揮著民間音樂傳播的功能,神圣祭奠的外圍包裹著世俗的娛樂。現(xiàn)代祭祖送靈儀式同樣如此,如“火角”儀式中,人們?yōu)楹嫱袩狒[的儀式氣氛或為凸顯本家族勢力,用各種混響造勢,鞭炮聲、煙火聲混雜著人們的喊叫聲,年輕人手提音箱播放很大聲響的通俗歌曲,或者敲鑼打鼓助威入場,也有人彈奏月琴或吹奏克西覺爾等民間樂器,場面壯觀,沸沸揚揚。但是,祭祀送靈儀式的核心—畢摩誦經(jīng)場域一直以來都是相對嚴(yán)肅和神圣的空間。
由此兩類儀式的音樂來源、音樂側(cè)重可證,在諾蘇族群文化發(fā)展的不同時期,兩類儀式曾發(fā)揮過相同的作用。發(fā)展至當(dāng)下,現(xiàn)代火把節(jié)偏重于世俗,祭祖送靈儀式著重神圣。故而可認(rèn)為,當(dāng)下火把節(jié)是對過去祭祖送靈儀式在某種程度上的模仿。
(三)兩類儀式在諾蘇文化中的分層一體格局關(guān)系
筆者根據(jù)對祭祖送靈儀式多年的考察,結(jié)合火把節(jié)發(fā)展現(xiàn)狀得出:在涼山地區(qū),祭祖送靈儀式流傳范圍和儀式規(guī)模由東北向西南逐漸縮小;反之,火把節(jié)卻從東北向西南逐漸擴大。在祭祖送靈儀式廣泛傳播的義諾土語區(qū),火把節(jié)雖是官方主辦節(jié)日,但該地區(qū)凸顯的族群文化是祭祖送靈儀式,火把節(jié)處于次要地位。其他有火把節(jié)傳統(tǒng)的土語區(qū),火把節(jié)是最隆重和流行的節(jié)慶儀式,占據(jù)主文化位置,而祭祖送靈儀式卻日漸式微。所以,從當(dāng)下彝族區(qū)域文化視角分析,火把節(jié)作為涼山彝族法定節(jié)日,被各地官方廣為傳播,具有強烈的主文化意識特征。
那么綜合上述論證,將諾蘇文化系統(tǒng)作為縱軸,地域和區(qū)域性地點作為橫軸,中間向右延伸的斜線為時間軸,兩類儀式體系的文化關(guān)系圖(見圖1)為:左縱欄為族群文化層,右縱欄為民族文化層。立于左欄族群文化層的祭祖送靈儀式即為主文化,具有地域性和跨區(qū)域性雙重屬性;當(dāng)時的火把節(jié)僅是地域性傳承的民間祭祀。而隨著“彝族”概念的出現(xiàn),民間火把節(jié)逐漸升級為官方火把節(jié)進入民族文化層,并從地域性到跨區(qū)域傳播,占據(jù)彝族民族區(qū)域主導(dǎo)文化的地位;而與之并列,承襲古代彝族的祭祖送靈儀式依然存在,且代表著諾蘇族群傳統(tǒng)文化特征,只是已經(jīng)處于亞文化層中。

圖1 火把節(jié)與祭祖送靈儀式的文化關(guān)系圖
由此,火把節(jié)以開放性的儀式特征既吸納民間音樂、畢摩文化,又展現(xiàn)當(dāng)下通俗音樂風(fēng)格,成為現(xiàn)代彝族諾蘇音樂傳承發(fā)展的重要載體。祭祖送靈儀式作為族群文化的典型代表,與火把節(jié)互有對比,又有聯(lián)系地共存于諾蘇信仰文化系統(tǒng)內(nèi)。
二、兩類儀式體系結(jié)構(gòu)要素的比較
(一)兩類儀式屬性的對比關(guān)系
1.儀式類型—復(fù)合型和聚合型
火把節(jié)原為彝族民間一種較零散的儀式活動,即以地域性的家庭祭祀祖先為主,結(jié)合部落或村寨為單位自愿組織而成的歡聚活動。現(xiàn)由官方出面,在民間祭祀儀式基礎(chǔ)上進行了規(guī)范、加工和改造,朔造出一種新型的彝族節(jié)日。即使無火把節(jié)傳統(tǒng)的土語區(qū),也從傳統(tǒng)中吸取經(jīng)驗“發(fā)明新的傳統(tǒng)”,形成定時定點的聚合型儀式。故可認(rèn)為現(xiàn)代火把節(jié)是一種復(fù)合型節(jié)日體系,以官方為顯性特征。而祭祖送靈尼姆撮畢從遠(yuǎn)古時代起就是彝族先祖統(tǒng)治、聯(lián)絡(luò)各種勢力的重大宗教活動,傳承至今流傳區(qū)域雖日漸縮小,但在諾蘇的不同土語區(qū),依然是其普遍信仰,代表諾蘇人的族群文化認(rèn)同。
由此,火把節(jié)從地域性到區(qū)域性的傳播發(fā)展,也使其儀式屬性從離散型發(fā)展到聚合型。但祭祖送靈儀式一直是定時定點的聚合型儀式,以地域性傳承和跨區(qū)域性傳播相互結(jié)合的方式存在。所以,兩類儀式在彝族宗教信仰文化中的地位,以及火把節(jié)儀式屬性的變遷,正是族群文化和民族文化相互影響的結(jié)果,也是本文將兩類大型儀式進行對比研究的初衷。
2.儀式功能屬性—官方與民間
火把節(jié)也是祭祖,只是相對于祭祖送靈儀式,為小型的家庭祭祖。官方介入后,儀式屬性開始轉(zhuǎn)變,其原初的儀式功能被擴大化,出現(xiàn)顯性和隱性兩種。顯性的儀式功能是祭祀火神,圍繞火展開祛除污穢的象征行為;隱性的儀式功能即為發(fā)展區(qū)域經(jīng)濟文化。⑨該部分筆者另文討論,此不贅述。但是祭祖送靈儀式不同于火把節(jié),它不會為了適應(yīng)社會時代發(fā)展而改變其送靈魂歸祖先的儀式功能,只是其送靈歸祖的表面隱含著微妙的家支間禮尚往來、相互炫耀家族勢力的意義。由此,整體觀察兩類儀式,火把節(jié)擔(dān)負(fù)著既要體現(xiàn)傳統(tǒng)儀式功能,又不能失去當(dāng)下政治意識形態(tài)賦予的功能意義,否則火把節(jié)就失去了官方扶持的根本價值。那么進一步推論,火把節(jié)本身攜帶的政治性特征,也使其從族群文化特征脫穎而出,升入民族文化層,代表民族文化認(rèn)同。與祭祖送靈儀式的族群性特征正好形成對比:一個政治層面(官方),一個文化層面(民間);一個是現(xiàn)代節(jié)慶儀式,一個為傳統(tǒng)節(jié)慶儀式。同時,火把節(jié)中納入畢摩誦唱元素,又從音樂和宗教信仰上將兩類儀式連接一起。
3.社會認(rèn)同屬性—民族性和族群性
從儀式參與群體分析,早期的火把節(jié)是家庭式小型祭祖,結(jié)合村寨規(guī)模的聚集活動;現(xiàn)轉(zhuǎn)型為以縣、區(qū)為單位的大型節(jié)慶活動,儀式參與群體已超越以往族群范疇。而祭祖送靈儀式的參與者僅限于族群范圍內(nèi)家族之間,不具備當(dāng)下政治性特征,但涉及不同家族間利益和權(quán)勢往來,是當(dāng)下諾蘇家族團結(jié)互助的儀式實踐活動。
從社會認(rèn)同角度分析,儀式參與群體范疇限定了其社會認(rèn)同度的大小。火把節(jié)從村寨規(guī)模的聚集,發(fā)展為人人都可參與的當(dāng)代節(jié)慶儀式活動,使其得到民族層,甚或超越民族層更廣范圍的社會認(rèn)同度。而祭祖送靈儀式本身屬性和參與人群的限定,使其只能在族群文化層傳承。甚至某些傳統(tǒng)地區(qū)的儀式程序禁止外族,尤其女性觀看,所以在社會認(rèn)同度上祭祖送靈儀式很難進入民族文化層。筆者認(rèn)為這也是官方之所以選擇火把節(jié)作為法定節(jié)日,象征彝族文化認(rèn)同的根本。
總之,火把節(jié)以開放性、較強的社會屬性和人為建構(gòu)的政治性特征得到民族內(nèi)外認(rèn)同,并以民間和官方兩種形式相互協(xié)調(diào),并處于同一節(jié)日體系代表著民族文化。而祭祖送靈儀式以半封閉型、較強的族群性認(rèn)同和宗教性特征只能處于族群認(rèn)同層面。隨著火把節(jié)中畢摩誦唱符號的納入,使原來火把節(jié)家庭式的小型祭祖,成為更廣泛意義上具有象征意義的表演祭祖—祭火。諾蘇人在無意中完成了傳統(tǒng)文化到現(xiàn)代認(rèn)同的交接,并通過族性音樂的衍變、發(fā)展,建構(gòu)著當(dāng)下的音樂文化認(rèn)同。
(二)兩類儀式構(gòu)成要素的模式與變體
根據(jù)官方、民間火把節(jié)儀式的區(qū)分,其儀式場域也分兩種:民間家庭祭祀的儀式場域和火把節(jié)舞臺上人為創(chuàng)造的儀式場域。另外,從儀式屬性的比較可知,祭祖送靈儀式對儀式場域和儀式結(jié)構(gòu)都有嚴(yán)格限制。火把節(jié)在官方介入后也成為定時定地點的聚合型儀式。下表(見表1)是針對兩類儀式要素的述略和比較。若將民間火把祭祀和官方火把節(jié)合在一起與祭祖送靈儀式對比,可觀之兩類體系在儀式時間、儀式場域上的相互對應(yīng),以及儀式主題、儀式表演對象等方面殊途同歸的相似之處。如儀式主題中,祭祖送靈儀式圍繞祭祖、送祖,同時也有祈禱后代子孫興旺和吉祥的意涵。而民間火把節(jié)家庭儀式主題為祭祀祖先和祈禱豐收、家人平安;但官方火把節(jié)儀式主題較復(fù)雜,除了祭火,展示傳統(tǒng)文化,也隱含著發(fā)展旅游,為地方帶來經(jīng)濟利潤的驅(qū)動力。尤其《指路經(jīng)》的改編誦唱、畢摩點圣火儀式的納入,使兩類儀式體系在宗教文化發(fā)展上存在必然關(guān)聯(lián)。

表1 火把節(jié)和祭祖送靈儀式構(gòu)成要素比較表
其次,兩類儀式的差異主要體現(xiàn)在儀式類型、社會屬性和儀式范疇方面。政府介入后使火把節(jié)具有了不同于祭祖儀式的政治性色彩,從原來零散的聚集儀式發(fā)展為大型的開放性儀式活動;從祈禱家庭平安到民族文化層,為民族區(qū)域帶來更大經(jīng)濟利潤的節(jié)日。而祭祖儀式停留于族群文化層面,其半封閉型儀式很難超越族群文化層。由此,兩類儀式的儀式類型和社會屬性,使火把節(jié)和祭祖送靈儀式一個處于民族文化層,一個處于族群文化層,兩者互相呼應(yīng),又各自平行發(fā)展。
總之,無論從何種角度看待,火把節(jié)和祭祖送靈儀式都是彝族諾蘇文化在不同時期,展現(xiàn)不同風(fēng)格特色的儀式實踐活動。而火把節(jié)是當(dāng)下社會認(rèn)同語境中,彝族諾蘇文化與當(dāng)代社會政治接合的最佳產(chǎn)物。
(三)兩類儀式結(jié)構(gòu)和音樂布局的擴大或縮減
祭祖送靈儀式雖普遍承襲于彝族不同地區(qū),但其儀式程序、儀式風(fēng)格等都有差異。這種差異除了土語間的不同,也有“視家族祭祀先人身份、亡故原因、瑪都(亡魂)多寡和財力決定儀式內(nèi)容和規(guī)模”⑩路菊芳:《馬邊彝族尼姆撮畢儀式音樂的多聲形態(tài)》,《中央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2016年,第4期,第75頁。的區(qū)分。因此,根據(jù)涼山彝族不同土語區(qū)火把節(jié)儀式結(jié)構(gòu)和音樂布局的共性因素,結(jié)合義諾土語區(qū)多個祭祖儀式個案中儀式結(jié)構(gòu)的固定因素和音聲布局進行對比(見表2和表3),可知畢摩誦唱是兩類儀式中共有音樂元素;其實民間器樂和《達(dá)體舞》也會在祭祖送靈儀式必要場合出現(xiàn),如火角儀式,但非固定因素;而火把節(jié)中廣泛改編的畢摩誦唱和祭火儀式,成為彝族各地火把節(jié)連接為一個宗教系統(tǒng)的紐帶;此外,儀式結(jié)構(gòu)中還有一個最關(guān)鍵的因素,即祭祖送靈儀式中頻繁出現(xiàn)的“木古此”[mu33ku33tsh?55]?“木古此”指點火,通知天神或曰祭祀天神;諾蘇的祭祖送靈儀式匯集了所有大小型儀式程序,日常儀式的很多經(jīng)文誦唱均可在祭祖送靈儀式中找到原型。而木古此在這里也頻繁出現(xiàn)。(該儀式規(guī)模小表格中并未顯示,但其重要性高于其他任何程序),它與“爾察蘇”[l?33tsha33su33]?“爾察蘇”指凈化儀式。是諾蘇畢摩做任何儀式的前奏曲,筆者推測官方火把節(jié)中的點圣火儀式,很大程度就是在祭祖送靈儀式“木古此”基礎(chǔ)上的模仿或者擴大化。

表2 火把節(jié)的儀式結(jié)構(gòu)和音樂布局

表3 祭祖儀式結(jié)構(gòu)和音樂布局的固定性因素
三、兩類儀式表演情景化的比較
“所有的表演,像所有的交流一樣,都是情景性的、被展演的(enacted),并在由社會所界定的情景性語境中呈現(xiàn)為有意義的。”?〔美〕理查德·鮑曼(Richard Bauman):《作為表演的口頭藝術(shù)》,楊利慧、安德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第71頁。那么,通過上文的論證,火把節(jié)和祭祖送靈儀式都可界定為一場具有情景化的文化表演,都在彝族傳統(tǒng)文化系統(tǒng)中發(fā)揮著一定的意義,闡述著共同的族群信仰。由于兩者產(chǎn)生于不同時空,應(yīng)用于不同表演場域,運用不同的表述語辭和文本,所以在表演形式上塑造了不同風(fēng)格的諾蘇文化。“自反性”?貝克認(rèn)為“自反性”“這個概念并不是(如其形容詞‘reflexive’所暗示的那樣)指反思(reflection),而是(首先)指自我對抗(self-confrontation)。”轉(zhuǎn)引自〔德〕烏爾里希·貝克、〔英〕安東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現(xiàn)代化 現(xiàn)代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傳統(tǒng)與美學(xué)》,趙文書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4年版,第9頁。吉登斯認(rèn)為“自反性這個概念并不是指反思(reflection),而是首先指自我對抗(selfconfrontation)。拉什則認(rèn)為自反性主要指“首先是結(jié)構(gòu)性自反性(structural reflexivity),在這種自反性中,從社會結(jié)構(gòu)中解放出來的能動作用反作用于這種社會結(jié)構(gòu)的‘規(guī)則’和‘資源’,反作用于能動作用的社會存在條件。其次是自我自反性(self-reflexivity),在這種自反性中,能動作用反作用于其自身。”轉(zhuǎn)引自李銀兵、李丹:《自反性、主體間性與現(xiàn)代性:民族志書寫特征探析》,《云南社會科學(xué)》,2017年,第5期,第121–129頁。概念主要以德國社會學(xué)家烏爾里希·貝克、英國人安東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為代表,美國學(xué)者芭芭拉·巴伯考克將其同表演民族志結(jié)合,談道“‘自反性’一詞表明了表演具有的兩種相關(guān)的能力,它們都植根于任何意義系統(tǒng)所具有的成為其自身的對象以及指涉自身(to refer to itself)的能力”?轉(zhuǎn)引自〔美〕理查德·鮑曼(Richard Bauman):《作為表演的口頭藝術(shù)》,楊利慧、安德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第72頁。,同理,火把節(jié)和祭祖送靈儀式作為文化表演,分別擁有對不同時期社會的自反性特征。
(一)兩類儀式表演語境的自反性
自反性主要指表演本身對于其源出文化的反映,也可理解為文化意義的意義,即情景的再情景化。火把節(jié)和祭祖送靈儀式具有不同的儀式屬性,代表不同的文化認(rèn)同,由此也限定了兩類儀式音樂不同的表演語境。首先,火把節(jié)屬于開放性儀式,其表演語境就必須以多元化形式呈現(xiàn)。如畢摩在舞臺上揮舞法扇祭祀天地或舞蹈,均是對傳統(tǒng)儀式情景的模仿和擴大化。再如丫的比賽,每個選手都是走上舞臺手拿話筒歌唱,與其原本山野之外個人感情抒發(fā)的歌唱完全不同;這時的丫更多是為了表演,獲得獎項心理的驅(qū)動。另外,祭祖送靈儀式屬于半封閉傳統(tǒng)儀式,音樂表演語境相對單一;但每一個儀式語境又都是對古代彝族遷徙歷史、自然萬物之源的情景追溯。其次,火把節(jié)處于民族文化層,為官方組織參與,由此火把節(jié)中就有體現(xiàn)政治色彩的語境,如領(lǐng)導(dǎo)開幕式致辭,以及丫歌手對當(dāng)下政府精準(zhǔn)扶貧政策的歌頌等,都是火把節(jié)政治最好的反射。?筆者博士論文實錄中有歌詞翻譯,此不贅述。而祭祖送靈儀式處于族群文化層,是各家族的相聚,無任何當(dāng)下政治痕跡,只是暗含著不同家族勢力、財力展示的競爭,當(dāng)然這也是備受諾蘇人看重之處。
總之,火把節(jié)以多元共生的表演語境,既能容納族群宗教文化,又能自反當(dāng)下政策變化,而成為各區(qū)域竭力扶持建構(gòu)的節(jié)慶儀式活動。
(二)兩類儀式表演形式的自反性
火把節(jié)處于民族文化層,其開放的儀式特征致使音樂表演者與觀眾分離。如朵樂嗬原本是女孩子們圍著篝火自由歌舞,觀眾、演員兼于一身;現(xiàn)在轉(zhuǎn)換為演員表演和觀眾欣賞分離。再如火把節(jié)家庭祭祀中,畢摩蹲在門口面對牲品為祖先誦唱;現(xiàn)轉(zhuǎn)換為火把節(jié)舞臺上畢摩手持經(jīng)書、舞動法扇,跟隨音樂聲音模仿或僅是營造神圣氣氛,唱、演分離的誦唱,等等均是對原來儀式表演形式的再創(chuàng)造。
此外,祭祖送靈儀式歸屬族群文化,其所有表演形式均停留在族群原初文化層面。如畢摩誦唱姿勢的傳統(tǒng)性,畢摩誦唱、表演、聲音和情感的融為一體等等。正如涂爾干所言,“宗教是一種既與眾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關(guān)的信仰與儀軌所組成的統(tǒng)一體系,這些信仰與儀軌將所有信奉它們的人結(jié)合在一個被稱之為‘教會’的道德共同體之內(nèi)。”?〔法〕愛彌爾·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東汲喆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4頁。
由此,在表演形式上傳統(tǒng)宗教和當(dāng)下節(jié)慶儀式表演尚存在很大差異。火把節(jié)中畢摩誦唱和表演,既是對諾蘇宗教傳統(tǒng)文化的建構(gòu),又是對當(dāng)下社會信息的自反。因為儀式主持者、參與者和觀眾不再是宗教信仰的踐行者,畢摩誦唱和表演行為只是在為不同族群身份的觀眾塑造宗教信仰的氛圍,是對火把節(jié)源自傳統(tǒng)宗教而建構(gòu)的符號象征。而祭祖送靈儀式是對諾蘇宗教信仰的自反,儀式主持者、參與者和觀眾就是諾蘇宗教儀式的實踐者,無需任何外力干涉就完成了諾蘇宗教的傳承。
(三)兩類儀式社會—心理上的自反性
表演的自反性除了體現(xiàn)在表演語境和表演形式上,也體現(xiàn)在社會和人們的心理認(rèn)同上。美國社會哲學(xué)家和社會心理學(xué)家喬治·赫伯特·米德認(rèn)為,“‘自我建構(gòu)’的過程中,表演的展示方式將表演中的自我(舞臺上的演員、火爐前的故事講述人、鄉(xiāng)村廣場上的節(jié)日舞蹈者)建構(gòu)為自我的對象和他人的對象,在扮演成他者的角色并從該視角反觀自身方面。表演是一個尤其有效的、升華的方式”。?同注?,第74–75頁。因此,自反性在兩類儀式中表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自我心理上的自反性。火把節(jié)作為彝族對外展示民族文化,增強民族自信心的儀式實踐活動,對于每一位彝族人都是一種自豪。作為舞臺演員為能夠展示自我,同時又歌唱自己民族歌曲而感到自豪;而作為臺下觀眾,當(dāng)看到舞臺上歌者或選美比賽獲獎?wù)呔秃妥约撼鲎酝患易寤騺碜酝坏貐^(qū)時,那種興奮和自豪感油然而生。這是通過他者表現(xiàn)激發(fā)對自我民族文化的自反性表現(xiàn),是觀眾與表演者一起完成自我身份認(rèn)同的建構(gòu),從心理認(rèn)識上強化本族群音樂文化的認(rèn)知。所以,火把節(jié)中以比賽的形式展示傳統(tǒng)音樂,倒也有一種激發(fā)本族群人們主動傳承自己民族文化的動力。而祭祖送靈,只有儀式現(xiàn)場傾聽畢摩誦唱的人們,才能感受到彝族歷史文化的精深和祖先的智慧。因此,兩類儀式,一個是對自我當(dāng)下身份的自反性確證,一個是對過去族群歷史文化的自反性認(rèn)同。
其二、社會認(rèn)同的自反性。前文已述火把節(jié)包含了當(dāng)下政治、宗教文化、民間音樂和通俗音樂四種音樂文化元素。相比祭祖送靈,火把節(jié)更多是面對當(dāng)下社會,瞻仰未來,加之其開放性儀式特征,有著比祭祖送靈儀式更廣的社會認(rèn)同度。而祭祖送靈儀式是對古代彝族宇宙觀、自然觀、歷史文化、生產(chǎn)教育等知識的集體回顧,每參加一次祭祖儀式就是對自我族群身份的一次強化和建構(gòu),這種根深蒂固的族群認(rèn)同在當(dāng)下社會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所以畢摩文化符號才會成為各地火把節(jié)中的共性特征,因為這是火把節(jié)得到族群宗教文化認(rèn)同的最大自反性行為。
總之,無論民族文化層的火把節(jié),還是族群文化層的祭祖送靈儀式,表演者同觀眾的互動產(chǎn)生共鳴,是作為一場儀式或者文化表演最成功的展示。火把節(jié)作為代表民族文化認(rèn)同的表演語境,既要與傳統(tǒng)信仰保持聯(lián)系,具有一定神圣感,又要與時代接軌,體現(xiàn)當(dāng)下社會時代的自反性特征。故,火把節(jié)在對參與者身份認(rèn)同建構(gòu)上具有較大的復(fù)雜性和難度,也是其音樂文化之所以多元共存的一個重要原因。而祭祖送靈儀式是諾蘇宗教信仰的核心,其以不斷的儀式重復(fù)強化族群身份認(rèn)同,鞏固宗教信仰。
結(jié) 語
綜上所述,從現(xiàn)代節(jié)日體系呈現(xiàn)的二元特征、人類學(xué)主文化和亞文化的關(guān)系得出:在諾蘇文化系統(tǒng)生成的時空維度中,火把節(jié)和祭祖送靈儀式共處同一節(jié)日體系。只是所處不同文化地位,擁有不同的音樂文化側(cè)重點,代表著不同的文化認(rèn)同建構(gòu),具有著官方與民間的二元對立關(guān)系。
那么,從彝族傳統(tǒng)宗教文化發(fā)展歷程視之,火把節(jié)和祭祖送靈儀式是諾蘇傳統(tǒng)文化不同歷史時期與不同社會制度接合的產(chǎn)物,兩者具有前后承遞的關(guān)系。從儀式音樂形態(tài)特征、音樂類型和儀式表演情景觀察,火把節(jié)和祭祖送靈儀式分別是其產(chǎn)生于不同時期文化語境的自反性體現(xiàn),同時火把節(jié)又是祭祖送靈儀式在古代彝族社會中的自反性表現(xiàn)。最后,再從兩類儀式此消彼長的傳承現(xiàn)狀分析,火把節(jié)本身具有的,不同于祭祖送靈儀式的開放性儀式特征,為其帶來先天的便利條件,使其能夠立足于當(dāng)下彝族社會作為諾蘇文化代言人,以及諾蘇本土文化對外展示的窗口。而祭祖送靈儀式在古代彝族社會作為主文化的時代已不復(fù)存在,只能與火把節(jié)并峙對望:一個外在,一個內(nèi)化;一個位居民族認(rèn)同,一個位居族群認(rèn)同。
“梅爾耶夫(Myerhoff)寫道:‘儀式借助永恒不變的和潛藏著的形式,把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聯(lián)系在一起,從而消除了歷史和時間。……即使人們發(fā)明了新的儀式,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材于已有的象征素材庫,新儀式的出現(xiàn)并不依憑于發(fā)明者的心血來潮,而是取決于那些參與在新儀式之中的人們所存在的社會環(huán)境。”?〔美〕大衛(wèi)·科澤:《儀式、政治與權(quán)力》,王海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頁。因此,這種并峙非偶然的相遇,偶然的接合,而是同儀式相關(guān)的社會物質(zhì)資源、政治文化環(huán)境密切相關(guān)。所以,諾蘇的音樂文化認(rèn)同建構(gòu)必須以族群信仰系統(tǒng)為基礎(chǔ),否則為無根之莖,生命持續(xù)力缺失,終有一天被另一種新的形式取代。而真正實現(xiàn)這種傳統(tǒng)文化延續(xù)的方式就是族性音樂文化在當(dāng)下節(jié)日中的承傳。
附言:文章內(nèi)容源自本人博士論文,撰寫過程中得到導(dǎo)師楊民康老師的辛勤指導(dǎo),特此深表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