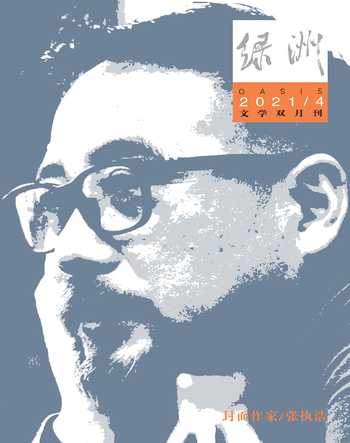人間花事
卜珊珊
桃花運(yùn)
春天點(diǎn)名時,無論叫到了誰,我們都要讓桃花先答應(yīng)一聲。因?yàn)橹挥刑一ㄔ诖汗饫锍ㄩ_心扉,大地上的春運(yùn)才算正式吹響號角。
我所理解的春運(yùn),意思是說,只有春天才有力量把你運(yùn)往詩意的遠(yuǎn)方。這個看似異于常理的概念,其實(shí)是被春天所認(rèn)同的,它早已為花所知,卻鮮為人類所知。
春運(yùn)的號角吹響之后,大自然就迎來了轟轟烈烈的客運(yùn)高峰。熙熙攘攘,你推我搡,那么多的桃花是從哪里來的?我猜是冒失的春天在黃昏失手打碎了一瓶粉色的墨,把漫天的云染成了粉紅色,三月的春風(fēng)就派上了大用場,春風(fēng)原本就是一把剪刀,把粉色的云當(dāng)成粉色的布,我們聽不見剪刀與布的摩擦聲,但一朵朵小小的五瓣花被它悄悄裁好了,就是桃花。
桃花美則美矣,卻倔強(qiáng),非要趕在新葉萌發(fā)之前綻放。不過在這趟春運(yùn)的過程中,并不曾有一片花瓣因擁擠而受傷。一車又一車的花瓣,浩浩蕩蕩,從南向北,直至占領(lǐng)一樹樹枝干,桃花才笑了起來。
桃花一笑,春天就不走了。桃花是世界上最熱情的花,婀娜多姿的花瓣將枝條壓得低低墜墜,密密匝匝,連風(fēng)都不能吹透,每一朵花,都散發(fā)著甜蜜的味道。桃花的味道,就是桃樹的體香,就是大地的乳香,是讓人喜歡并記憶的味道。一種我們喜歡的花朵的味道,就像我們喜歡的人的味道一樣,走出多遠(yuǎn),味蕾都銘記著它。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灼灼桃花是綿綿春雨在一夜之間點(diǎn)燃的。這般柔潤的好時節(jié),花隨風(fēng)潛入了夜,也說不上是哪個清晨,我睜開眼就發(fā)現(xiàn)遠(yuǎn)處灰蒙蒙的山被一樹樹粉侵占。
在春天,我只想和桃花一起虛度時光。山坡上的那些桃樹,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哨兵似的守在這里,仿佛怕外面的喧鬧傳進(jìn)來,怕這里的寧靜逃出去。所以我去看桃花,也得躡手躡腳。桃花開在山坡上,一蓬一蓬,一坡一坡,遠(yuǎn)看它連綴成粉色的云,近看它又破碎成粉色的心。我盡可以一株一株地看,一朵一朵地愛,沒有人會責(zé)怪我花心,而我堅(jiān)信一朵桃花的確是有心的。她們變了法子地使你出乎意料,使你看過一重,轉(zhuǎn)個彎,又看到不同的一面,眼睛永遠(yuǎn)不累,心也不會發(fā)膩。這樣好的桃花,也被人說過俗氣,如果這也叫俗氣,那她就是要俗氣,你管得著嗎?這樣的隨性勁兒,讓人歡喜,又讓人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慚愧,仿佛不能用文字替她洗刷這無妄之評是我的過錯。
一見桃花,我就不想走了。我最愛在桃林里發(fā)呆,就單單是發(fā)呆,也是件最美好的事情,在桃林里,空氣永遠(yuǎn)干凈、芬芳,每一縷都清新如泉,每一縷都溫馨如光,每一縷都甜蜜如糖,沒有一點(diǎn)暮氣,是柔軟的、年輕的好時光。
在這樣的時光里,我常常忘了自己,我的腦子里只有“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的詩句,一個女孩,要出嫁了,多像一瓣桃花,收斂了飛翔的羽翼,靜靜等待桃子的萌發(fā)。詩經(jīng)里的這瓣桃花,被采詩人做成了標(biāo)本,夾在泛黃的書頁里,保存完好,只要后來人一翻書,它就飄落人間。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fēng)。”崔護(hù)也有一朵情懷悵惘的桃花,開在他的期待里。初識時,人面和桃花一樣驚艷,只是后來,故地重游,伊人杳然,再浩繁美麗的春天,對于崔護(hù),都黯然失色了吧。
人間事,盡悠悠,有多少人一經(jīng)相遇便成了刻骨的思念,又有多少人一經(jīng)相識卻成了無奈的永別。開在城南的這枝桃花,是開在盛唐最美的相思。而今,在岸邊,在田野,在煙雨迷蒙的三月,灑脫的桃花依舊笑對春風(fēng),把千年的往事融進(jìn)生命的嫣紅。不知城南小路之上,是否還有一個桃花樣美麗的姑娘倚門回望。
桃花曾是相思,曾是愛情。我身邊也有一樹桃花,讓我可以湊近了看。一朵,兩朵,花兒粉唇微張,似乎在傾訴,那脫口而出的詩句,全都泊在春的枝頭。“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意近了,芳心醉了,多少年桃花倚著春風(fēng)笑得花枝亂顫,抖落一身花瓣又隨流水悄然遠(yuǎn)逝了。人面桃花都杳無蹤跡了,變成“落花人獨(dú)立,微雨燕雙飛”。我想起電影《山楂樹之戀》里靜秋和老三的相識相戀,開始也是這般甜蜜,結(jié)局也是這般讓人惆悵。
春來不是讀書天,兩個少年飛快地騎著山地車從我身邊呼嘯而過,打斷了我的思緒。春天多風(fēng),可那風(fēng)早已經(jīng)是吹面不寒的楊柳風(fēng)了,自然困不住少年的腳步。他們手里拿著風(fēng)箏,是在尋找合適的空地準(zhǔn)備大展宏圖。小時候我也愛放風(fēng)箏,風(fēng)箏得求著舅舅做。舅舅鋪開篾條兒,撐個四角兒,糊上報(bào)紙,再墜上兩條帶子,就告訴我這是“蝴蝶”。舅舅的“蝴蝶”怎么也飛不高,眼看著飛起來了,翻幾個筋斗,就栽下來了。我怪過風(fēng),怪過自己細(xì)細(xì)的胳膊和腿,可從來都沒質(zhì)疑過舅舅的手藝。
少年們把車子停在遠(yuǎn)處,很快一只“大蝴蝶”就自由地飛上了天空。過了一會兒,“大蝴蝶”漸漸低落下來,少年趕忙拉著線小跑起來,風(fēng)箏飛過桃林,高高地飛上天空,我的目光也隨著風(fēng)箏的起伏延伸到高處。
我羨慕那飛向云端的“蝴蝶”,人生在世,誰也無法做一只自由自在的風(fēng)箏,不知桃花羨不羨慕高揚(yáng)在桃林上空的“蝴蝶”。假如桃花羽化成蝶,那她要帶我們?nèi)ツ睦铮繒x太元中,武陵漁人誤打誤撞進(jìn)入的桃花源,成就了千古文人的桃花夢。桃花從此成了一扇門,一面是塵世喧囂,另一面是出世隱逸,我不能參破它的哲學(xué)況味。
胡蘭成說:桃花難畫,因要畫得它靜。在我身邊,此刻,山野桃花確實(shí)是靜的,開多少花,結(jié)多少果,她不知道撒謊。我甚至能聽見,風(fēng)吹過來,它們優(yōu)雅落下的聲音,像大地上又多了一層厚厚的詩行;山野里的風(fēng)是靜的,它在外面虛張聲勢可到了山里也得收斂起橫沖直撞的脾氣;日光是靜的,我看見它把我的影子和花的影子輕輕排放整齊;石頭是靜的,盡管它是山村里最耐勞的工匠,一點(diǎn)點(diǎn)把自己鑲嵌進(jìn)大山的腹地;在地里為桃花授粉的人也是靜的,她端著小小的藥瓶,用自己的一寸寸光陰點(diǎn)綴這十里桃林;桃樹的枝干是靜的,甚至干枯、灰暗,像二胡的弦,上面正流瀉著《二泉映月》,帶著哀而不傷的調(diào)子;我在這里的時光也是靜的,因?yàn)樾模谶@里也沉淀了下來,聲音都被那些土那些石那些花收納了,只有一群鳥,聚在一起飛,遺落在桃林里的鳥鳴變成跌宕起伏的樂音。在樂音聲中,我一次次學(xué)著反芻人生的浮與沉,反芻人生的高峰與低谷,反芻人生的明與暗,反芻人生的苦與甜。
不管怎么說,在春天,總要和桃花見上一面的。一個人,想把春天永遠(yuǎn)留在身邊是不可能的,可一個人卻可以把自己暫時地隱在桃林里,看桃花的花瓣一層一層落在自己的肩膀上。桃花若是愛你,這份運(yùn)氣就叫桃花運(yùn),桃花若是不接受你的表白,也會一路繁花相送,和桃花打交道的我們,從來就沒有吃過虧。
祖母蘭
祖母愛侍弄蘭花,家中最精致的花盆就都給了它。蘭很少開花,像小腳的祖母,行動緩慢,讓人等得著急。祖母不急,她常說,一朵花哪能急著開呢。
一年到頭,祖母的蘭似乎只在春節(jié)那幾日綻放。農(nóng)村多的是月季,月季如農(nóng)家飯桌上的白菜蘿卜般通俗,它好養(yǎng),栽在門口,一瓢水就能長成很大一株,月月開花,朵朵艷麗。明明月季更適合農(nóng)家,或者格桑、蜀葵、雞冠花也是皮實(shí)的,我不懂祖母為什么要養(yǎng)蘭。
祖母的冬天離不開火爐,她的爐子上永遠(yuǎn)煨著熱水。她在屋里用瓷盆搓完衣服,才邁著顫巍巍的腳步,把灰白色的洗衣水潑到院墻角,渾濁的泡沫邊淌邊破。洗完衣服,祖母守著她的火爐給我講故事啊。祖母對待孩子是最有耐心的,童年時我聽過多少關(guān)于大山的故事。在祖母口中,不聽話獨(dú)自上山玩耍的女娃被山神變成了山鳥,日日飛在山中卻不能回家。蘭花世外人一般兀自開著,花香里沾著肥皂的香,伴著咕咕咚咚的開水聲,我昏昏欲睡。
我趴在椅子上要打盹了,祖母還在絮叨她的回憶。她說她小時候也念過三年書,她的小姑姑每天給她梳最整齊的辮子,在門口的土堆上培燕子窩(一種游戲)的時候,也跟她父親學(xué)習(xí)過“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樣的詩句,只是那些像絲巾一樣柔軟的日子,出嫁之后就一去不復(fù)返了。
祖父家的日子真難熬,白天是永遠(yuǎn)沒有終止的農(nóng)活,她就夜里給孩子們做衣做鞋,鄉(xiāng)村寂然無聲,陪伴她的只有一盞煤油燈和蘭,蘭花已開過了,葉子趁著夜色往厚處堆。時間長了,她眼睛見光流淚,頭也開始疼。哪有錢去醫(yī),疼極了就去東村土郎中那里要點(diǎn)草藥煎服。她家徒四壁,卻有六個孩子,兩個小姑子,婆婆一直癱瘓?jiān)诖玻患胰撕谠絹碓绞菃栴}。
三十八歲那年,她頭疼發(fā)作的次數(shù)越來越多了,有一次實(shí)在是太疼了,她覺得自己頭要炸了,她顧不得這個家,顧不得孩子了,她把頭撞向墻壁,她想她的生命或許就要終結(jié)在此了。她撞暈了,血流在臉上還是熱的,后面發(fā)生的事情她就不知道了。
等她醒來,她第一次睡在了醫(yī)院里,她在輸液,她睡了一天一夜。穿白大褂的醫(yī)生走過來說,她不能再熬夜了,她太累了,她得了腦血管痙攣。她留下了感激的淚水,對醫(yī)生,也是對老天爺,她一直以為自己就要死了,沒想到只是這么輕的毛病,腦血管痙攣!她控制住自己,不讓自己笑出聲來。她為自己的想法羞愧,她這個年紀(jì)怎么有資格在看病上花錢呢。快走吧,她撞墻的時候還想她的幼兒只有三歲,隔了一天,她又可以回家給他洗衣做飯當(dāng)娘了。她讓醫(yī)生開了藥,就和祖父一起回家了。她握著手里小小的藥丸,就像握著自己的命不敢撒手。
后來她又吃過多少藥,她也記不得了。總之,她忍著藥的苦,忍著生活的苦,把孩子們個個喂養(yǎng)成人。
蘭之猗猗,與善人居,在時間的幽微淺淡處鐫刻了我的童年時光。
長大了,我繼續(xù)愛著大朵的月季,也學(xué)會了欣賞蘭。這世上有萬千詞語可以形容一朵花的美,要準(zhǔn)確匹配并不容易。花朵有出身,詞語也有,有的出身寒門,有的生而高貴,有的叫大家閨秀,有的叫小家碧玉,要相得益彰,要門當(dāng)戶對。為蘭,我也找到了一個詞語:蘭心蕙質(zhì)。
“芝蘭生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jié)。”君子的心叫過丹心、冰心,那一顆在歲月里守望的初心呢?
大抵應(yīng)該叫蘭心。
一種植物,一旦有了執(zhí)著,就有了性情。蘭,翠綠叢中,花苞初綻,宛如飽讀詩書的大家閨秀,身著長袍,輕挽發(fā)髻,整裝待發(fā)。正因她并不刻意去出風(fēng)頭,所以總能保持優(yōu)雅穩(wěn)重……蘭,就在那么一種謙和、簡約、隨意的氛圍中,詮釋著“四時有明法而不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道理。或孑然一身,或形影相隨,它總在大開大闔的游刃之間,一點(diǎn)一點(diǎn)散發(fā)自己的蘭心蕙質(zhì)。無花時節(jié),蘭更為低沉,把自己沒入草叢,深沉積淀,為的是固守年年歲歲的承諾。
誰能洞悉蘭草經(jīng)年的負(fù)重,誰能洞悉祖母經(jīng)年的負(fù)重?祖母從來不為自己叫苦,在歲月里,用耐心一點(diǎn)點(diǎn)等待花開,等待美好生活的到來。只是啜飲過生活風(fēng)霜的我自己開始領(lǐng)悟,在沉重的日子面前,農(nóng)人如何能輕盈得起來?祖母養(yǎng)蘭,或許就是為了讓日常生活的目光有所停頓。
我也常常在書里為蘭停頓。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離騷》里回環(huán)往復(fù)的蘭,一瓣就是一句結(jié)構(gòu)精巧的詩。“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fēng)。清風(fēng)脫然至,見別蕭艾叢。”陶翁的茅屋草舍前,幽蘭滿階,而不知其為蘭,只當(dāng)是閑庭野草,但只需要一縷風(fēng),蘭就不再遁藏,內(nèi)斂的風(fēng)華悉數(shù)展露。
這些綿綿不斷的情思,正是蘭花與生俱來的詩人氣質(zhì)。作為花,蘭花和別的花太不一樣了——它懂得要成為一朵真正的花,高貴的應(yīng)該是追求,雋秀的外表只是一層華衣。
蘭生幽谷,如影隨形的暗香,蕩漾著它的風(fēng)采盡顯著它的意境。詩人羅伯特·勃萊有一句詩:“貧窮而能聽見風(fēng)聲也是好的。”或許蘭香正是貧窮的日子里,生活向我們走漏的甜蜜風(fēng)聲。蘭香,原本是煙火人間呈現(xiàn)的平凡詩意。她悄悄把日子描摹成一段段有形有色的格調(diào),像戲曲、書法、詩歌一樣,表達(dá)和升華,又重新滲透到質(zhì)樸的農(nóng)家生活中。因?yàn)楹吞m花相識,我對大地上和祖母一般的農(nóng)人又多了一層認(rèn)識。
長大以后,我愛在植物園里尋蘭,愛在蘭展上賞蘭,愛在書里讀蘭。不管在哪里見到蘭,都能讓我放棄所有雜念,以便從一縷蘭香里,讓心更貼近從前的草木時光。或許,從偏僻鄉(xiāng)村走出來的人們,不管走得多遠(yuǎn),心中都有一條通往故鄉(xiāng)的路,蜿蜒崎嶇,芳草萋萋,而我的那條路上,永不會缺席的就是祖母的蘭。
今年過年回家,祖母養(yǎng)的蘭有兩株開花了。一株是寒蘭,養(yǎng)在家里五六年第一次開花,暗綠色的葉,前部邊緣有細(xì)細(xì)的齒,花為狹卵形,蕊柱稍向前彎曲,兩側(cè)有狹翅,淡黃色的唇瓣并不艷麗,但香氣濃烈。另一株是墨蘭,葉呈帶狀,全緣,近革質(zhì),暗綠色,有光澤,花瓣比萼片短而寬,向前伸展,覆于蕊柱之上,眼看那花瓣上墜著閃閃熒光,起初我以為是露水,湊近拿手捻了一點(diǎn)兒,放在嘴里,甜,才知道是蜜。
祖母呵,我和弟弟一直喚你奶奶,父親母親一直喚你娘,祖父一直喚你孩子奶奶。我一直以為你沒有名字,直到祖父去世了要帶戶口本去火化,我翻開戶口本才知道你叫薛瑞蘭。
多好聽的名字,蘭。
桂花落
桂花在這座園子里開放的時候,香味是紙包不住的,是窗戶擋不住的,撲簌簌的桂花香,茫茫然,卻直往鼻子里鉆。這個時候,平淡的日子被桂香托舉,陡然間疏闊起來。我的心情和畫家黃永玉一樣——他對表叔沈從文說:“三月間桃花開了,下點(diǎn)毛毛雨,白天晚上,遠(yuǎn)近都有杜鵑叫,哪兒也不想去了……我總想邀一些朋友遠(yuǎn)遠(yuǎn)地來看桃花,聽杜鵑叫……”
春天且去看桃花,聽杜鵑叫,秋天就聞聞桂香,一樣是人間樂事。
縱然有四季桂,可桂是屬于我心目中的秋天的。若是秋天沒有桂,便要單調(diào)許多。秋分前后,空氣里漸漸多的那層味道,那層淺甜的,飄浮的,幽微的暗香,雖然霧氣一樣縹緲,可我知道那就是桂。
陽光映照青石蒼苔,盛夏的喧鬧漸漸走遠(yuǎn)了。桂是秋天到來最明顯的線索,桂花疏疏落落的花瓣,抱在一起,一朵,便可比擬一闋清詞,使得一整株桂簡直可以稱得上是一本精妙的選本了。
桂,葉子還沒有老,還油汪汪的,花就開了。桂花不突出自己,它太小了。桃花、梨花、杏花、梅花縱然也小,但附著在老舊的枝干上依然是耀眼的,它們的花謝了才長出葉子。桂就藏在葉子里,與葉子和諧共生。
桂花是啥時候開的,香味是啥時候在這個園子里漫漶起來的,我說不清楚。我想,成熟的秋天應(yīng)該還葆有一絲童真,是她伸出調(diào)皮的手,撓了撓桂樹的胳肢窩,桂就繃不住臉了,滿樹花就集體笑了,那么多的小姊妹們一起笑,手挽著手,肩并著肩,哪能沒有聲音呢,只是我們不曾留神罷了。
白日喧囂,桂香如同游絲若隱若現(xiàn),只能聞其香而不見其樹,像我這般大意的人自是分不清桂和其他喬木的,但循著桂香這條線索,步入那些高樓背后的幽靜,那些平日里我似乎總沒有空停留半分鐘的鵝卵石小道,我就一定能找到它們。一株桂,見到我就不笑了,她只對王維笑。王維寫“人閑桂花落”,意思是王維有空陪她開放,也有空陪她凋謝,桂花感念詩人的陪伴,就一直在詩句里流芳。誰不渴望這種陪伴呢,這不正是愛爾蘭詩人葉芝那首久負(fù)盛名的《當(dāng)你老了》——
多少人愛你青春歡暢的時辰/愛慕你的美麗,假意或真心/只有一個人愛你那朝圣者的靈魂/愛你衰老了的臉上痛苦的皺紋
桂綻放得別有情懷,一點(diǎn)點(diǎn)地私語,不驚動別人,然后,悄悄落下,仍然不驚動別人,其香又那么醇厚綿長,這種情懷抓不著,說不出,也畫不出,卻一直在心頭縈繞。被一樹樹桂香圍繞,人特別容易發(fā)癡,有時候連眼神都是游離的,仿佛有心事一般。其實(shí),那根本不是在想心事,只是桂花的香味有一種輕微的迷幻作用,人在其中久了,就會陷入回憶的風(fēng)暴。
我想起外祖父便是桂花開的時節(jié)去世的,當(dāng)生命走到盡頭,杜冷丁也無法為他止痛了,他就搬個馬扎坐在院子的桂花樹旁。粗瓷壺泡出來的粗茶,陪伴著他,琥珀色的液體誠心實(shí)意地倒映著他微霜的鬢。就這樣,一上午過去了,一下午過去了,仿佛那只是日子最普通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陽光穿過枝丫,亮堂堂的,是秋天所特有的天光余韻,給他塵世最后一抹溫暖。他的頭發(fā)、衣領(lǐng)、褲腳、不離手的煙袋上,都悄悄附著了花瓣,與陽光融為一色,貫穿我整個秋天的回憶。
一晃十五年過去了。外祖父是我第一個去世的親人,我覺得他去世時還年輕,那時候我怎么懂什么是永別呢,不過覺得他走得倉促,沒有來得及和他見最后一面。而他的遺愿,是養(yǎng)一群羊,繼續(xù)支持兒女們單薄的家業(yè),支持孫輩們未竟的學(xué)業(yè)。有時我想,外祖父的一生不也正如一朵藏在葉子里的桂花,在蕓蕓眾生里不起眼又默默散發(fā)著香氣。
他十六歲便沒了父親,在舅舅家的屋檐下生活,要供養(yǎng)小腳的母親,撫養(yǎng)兩個年幼的妹妹。待成家后又相繼養(yǎng)大六個孩子,生活的重?fù)?dān)讓他沒有半點(diǎn)喘歇的機(jī)會。他耳朵聾得早,跟他說話要喊,母親說他年輕時很嚴(yán)厲,但對待孫輩卻和藹得很。他講過很多往事給我們聽,有些如木心的《從前慢》一樣美好,但我印象最深的一個卻很傷感——
他曾陪他的岳父去市里看病,回來晚了,沒有了公交車,卻又沒錢住旅店了。他就攙著病中的岳父深一腳淺一腳,從市里一步一步走回家。開車從市里回家要一個半小時,攙著病人步行得多長時間呢?我想過又不敢往深里想,只是如今每次從市里回家我都忍不住東張西望——多希望真的有時空穿梭,我們在另一個平行世界里重逢了,我可以捎他們一程,讓他們勞累的雙腿歇上一歇。有時候,這般想著想著就落下淚來,也無法和身旁人解釋這情緒的源頭。
死去元知萬事空。桂花樹下,花瓣無聲墜落,時如驟雨,時如輕露。無需多時,桂樹下大地裸露的肌膚就被涂抹上一層淡黃,細(xì)小的落花,安然地睡在微涼的大地上,讓人生憐。它們身后的背景里恰好生長著一株肥碩的芭蕉,秋桂的金黃,芭蕉的碧綠,濃墨重彩地洇在大地的宣紙上,有寫意的恬靜淡然。即便沒有風(fēng)雨侵?jǐn)_,桂花也會這么快就離開了母體,這世間的別離大多如此輕飄飄,讓人猝不及防。
也是這個秋天,讀到郁達(dá)夫《遲桂花》里的名句:桂花開得愈遲愈好,因?yàn)殚_得遲,日子才經(jīng)得久。從前,未曾好好看看身邊的親人,也未留意過桂花與別的花木不同,但愿往后年年,與花香樹木,人間親人,好好相伴。
在梅邊
在冬天,走進(jìn)魯南這個小小的村莊,邂逅湖就像在夜晚一抬頭和漫天繁星撞個滿懷,是一種孩提式的敞露,一抹深邃的意境,一個擁抱的溫柔,這份意外的驚喜讓我不禁放慢了腳步。
湖叫燕柳湖。燕柳湖,想必春來湖水綠如藍(lán),它的鶯歌燕舞、柳浪聞鶯肯定能讓游人流連忘返。然而我的到來卻是在冷寂的冬天,沒法確認(rèn)它的熱鬧之美。湖在冬天是寂寞的,我環(huán)顧四周,離湖最近的是蘆葦。只是我該如何描述冬天的蘆葦叢呢?它們太安靜了,仿佛只是一折星霜月痕,亦或者一個安然卻淺淺的夢境。我望向蘆葦,但它們低下了頭。
我可以想象一叢叢蘆葦盛長時的景象,水鳥飛翔,綠浪起伏。只是曾經(jīng)的蕩蕩蘆葦,如今都?xì)垟×耍陋?dú)清冷。畫家吳冠中畫過不少殘荷,他著筆于線之曲折,倒影蕩漾,藉此呈現(xiàn)花葉的迷宮。殘荷可入畫,冬天的蘆葦亦能打動人心。在冬天,反季節(jié)蔬菜可以在大棚里旺盛生長,但大地上自然存在的一切,比如眼前這一株株沉寂下來的蘆葦,仍然會喚醒人們對生命的敬重。蘆葦樣貌羸弱,但每一株蘆葦應(yīng)該都有一件終身信守的信條,否則它們何以做到可以在方寸之地扎根,并且一待就是一輩子。蘆葦在湖畔度過春夏秋冬,到了冬天,它低下了頭,守望著湖底這泓養(yǎng)育它的水。水一遍一遍在風(fēng)里蕩漾,安然地聽蘆葦敘述往事,眷眷不散。
把目光從蘆葦身上移開,仔細(xì)觀察還能發(fā)現(xiàn),草木的命運(yùn)到了冬天并不盡是凋零,燕柳湖畔隱隱還有梅香。仿佛在這寒冬里,依舊要讓人體會那藏在林木深處的春天氣息,它們的力量常常讓我熱淚盈眶。
從青少年開始,早就已經(jīng)背下了太多關(guān)于梅的詩,“墻角數(shù)枝梅,凌寒獨(dú)自開”“平時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朔風(fēng)如解意,容易莫摧殘”。我想起電視劇《甄嬛傳》中,甄嬛初進(jìn)宮時,性情簡純,在除夕之夜,獨(dú)自跑到倚梅園掛小像,所許的愿望便是“逆風(fēng)如解意,容易莫摧殘”。一個女子,背后有一座倚梅園做底子,真像水墨畫里的那朵色彩淺淺的梅,骨子里都透著清涼的芬芳。
我走近梅,梅就開在湖畔不遠(yuǎn)處。梅出生在低處、在偏僻、在旮旯。風(fēng)吹來,有花瓣落下,使她有一種遺世獨(dú)立的美。她絕不討好誰,因?yàn)樵蟮鼐湍芑畹煤芎玫木壒省KS意站在雪地里,幽幽地吐著香,婉轉(zhuǎn),樸素,卻意態(tài)悠遠(yuǎn)。她開得很好,沒有人舍得把她折下來。幽幽的清香不動聲色、不卑不亢、不絕如縷。她那樣驕傲,沒有人敢把她折下來。生命的風(fēng)骨之美,真的是穿越風(fēng)霜之后才有那份昂揚(yáng)自信。
有時,我會賴在梅旁不肯離去。看著這些樹,這些沒有言語的樹,分明在逆生長,老舊的枝干到了冬天才著上花朵,人不能越活越年輕,但是梅可以,在梅邊,才讓人懂得什么是韜光養(yǎng)晦,什么是厚積薄發(fā)。偶爾會下雪,雪裹挾著風(fēng),翻過一朵朵梅。我忍不住打了個寒顫,那些開在枝頭的梅,似乎早就得到了冷熱的訊息,不曾流露一點(diǎn)訝異。漫天的雪花飄落,落在梅花上,也落在燕柳湖里,我看到雪花落到梅花上點(diǎn)綴的花心晶瑩剔透,雪花落到湖面甚至激不起一點(diǎn)漣漪就融化了。
劉亮程在《一個人的村莊》里寫道:落在一個人一生中的雪,我們不能全部看見。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獨(dú)地過冬,我們誰也幫不了誰。此刻,雖然在梅邊,但我無法替一朵梅抖掉它身上的雪。
我想起那些回蕩著自己濃重嘆息聲的夜晚,孤獨(dú)與無助如洶涌的潮水將我吞噬。因?yàn)槟且彩俏乙粋€人的冬天,那是我才能感受到的冷。或許我們有很多理由和機(jī)會去跟別人痛斥自己正遭受著的冷與痛,但更多時候,我們都是一個人,縱然歲月一步步往深處走,將漸漸成落光了葉子的枝干,不甚明媚,有一點(diǎn)灰褐的暗淡,但熬過來的心會是那傲寒的一朵梅,梅從來沒有怕過生命里的冷。
就該學(xué)學(xué)梅,它安然走著自己的時令。直到所有的花都開過了,所有的葉都凋盡了,它才長舒一口氣,緩緩綻放。讀大學(xué)的時候,宿舍在一樓,窗外恰有一株梅,梅是老梅,與年輕的面龐相映成趣,成了我們寒冬臘月里蟄伏的小確幸。多
少年,“平時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的意境在我心中揮之不去。
揚(yáng)州八怪之首清代書畫家金農(nóng),善用淡墨干筆作花卉小品,尤工畫梅。也有《畫梅·老梅愈老愈精神》的詩作傳世——老梅愈老愈精神,水店山樓若有人。清到十分寒滿把,如知明月是前身。是老梅的真實(shí)寫照。老梅,不知陪伴過多少青春,聽過多少悵惘滿懷的歌謠,依舊蓬勃鮮活地向上長著。疏密有致的枝柯,如虬蟠一般,彎曲地向四面躬著,向八方展著。年輕的時候滿腦子浪漫想法,我想穿越千年,邀陸游來賞梅,他是那個癡情的人,而這里梅香如故;我想邀李清照來小住,聽誰家橫笛,撫慰漂泊天涯之苦;我還想邀陸凱來看梅,這里才應(yīng)該是《贈范曄詩》的出處。梅,讓泉城舜耕路40號上的山財(cái)(山東財(cái)大)充沛著古典氣息。
愛梅惜梅的人太多了,梅為妻,鶴為子,林和靖是其中最癡狂的一個,他在西湖邊把一個人過成了一個家。所以他寫下了“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的詩句,想必多少個日子,一個人什么也不做,就靜靜看梅花開在黃昏的冬季里。
如果一株植物是一盞燈,那么香味就是它的光。我探過頭去,想嗅嗅梅香。忽然,我被梅小心翼翼地?fù)崦讼履橆a。那朵花,涼涼的,滑滑的,有著木質(zhì)的清香味,樹脂的油香味,還有著山野的草木味。
在落雪的冬季,也有人像我一樣來看梅。我猜不到他是誰,只有一串通往燕柳湖的腳印成了告密者,無聲地指示著他的去向。何必知道他是誰,這世間多得是不怕冷的傲骨。在有暖氣的室內(nèi)待久了,也該到冷的地方來呼吸呼吸新鮮空氣,冷總是更適合省察內(nèi)心,思考是形而上存在的,不然長長的冬天,德國哲學(xué)史上就不會有那么多如雷貫耳的哲學(xué)家。那震懾人心的哲學(xué)厚度和深度,也跟遠(yuǎn)處的群山一樣,讓人覺得此刻適宜保持緘默。
責(zé)任編輯車前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