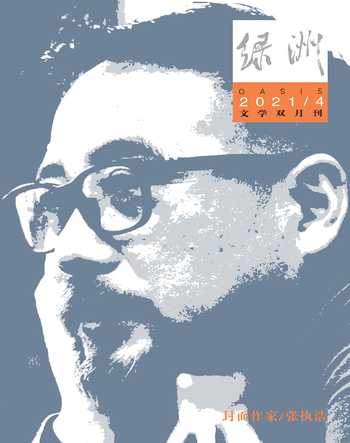嫁到郴州
朱小平
1
我嫁到郴州已有二十年。
婆婆家住房傍蘇仙嶺下,依郴江河畔,近百年來,老房子雖經幾番修葺,卻從未遷移
郴江,一名黃水。據史書《太平御覽》49卷引盛弘之《荊州記》曰:“黃箱山一名黃岑山,在東南三十里,其山郴水所出。”
北宋詞人秦觀,1097年三月被貶阪居旅驛郴州時,在郴州旅館寫下名詞《踏莎行》,下片結句“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我在蘇仙嶺“三絕碑”摩崖刻字上,讀到此詞的第二個版本:“幸自”改成了“本自”。古人作詩詞,也多是反復推敲的,“幸自”也好,“本自”也罷,反正秦觀在旅館視線所及的郴江,只可能是我們家現居的蘇仙嶺腳下這一片河面流域。
郴江全長75.7千米,系湘江支流,也是郴州市區的母親河。她發源于南嶺之一的騎田嶺之巔,沖出江口峽谷,穿行在郴山丘岡間,然后一路向北投入耒水的懷抱,終源匯聚于湘江。依此看來,我想“本自”應該更為確切吧。
剛來時,聽聞郴州有句流傳甚久的民謠“船到郴州止,馬到郴州死”。有些觸痛,好似自己已置身于一個山水荒蕪的絕地。
公交車緩慢駛過繁榮的商業街文化路,報出義帝陵站臺,才知公元206年,徏義帝沿水道遷都于郴。“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郴州竟是一個舿舟載來的城市。
唐宋時期,那些被貶謫到嶺南、海南的京朝官員,千百年前就曾涉水郴江。隋朝薛道衡《入郴江》有“揚帆溯急流”。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至郴江贈張署》有“山作劍攢江寫鏡,扁舟三轉疾于飛”。
翻開《光緒郴州直隸州鄉土志》,那時的郴江商業交通興旺景象,有文字為證:“南貨北往,北貨往南,悉上此經過,故沿河一帶,大店棧坊數十家,客貨至,為撥夫,為雇騾、為寫船只,絡繹不絕。”
我的腦海里頓時浮現出一幅《清明上河圖》,莫非北宋畫家張澤端也曾來過郴州?要不然,我怎么會感覺汴河上有郴江的影子?
2
當我從郴江歷史追溯中回神的時候,四樓窗前的桂花樹尖上,傳來婆婆邀約我散步的召喚聲。
我們平日里走得最多的路,是郴江白鹿洞橋至石油橋這一段游道。早上從鰲頭灣出發,沿河岸走半公里到白鹿洞橋邊市場買菜,傍晚反向石油橋,繞兩橋一圈歸家,婆婆的手機計步顯示六千余步。她玩手機比我溜,網購、頭條新聞、全民K歌、微信運動,無一不通,無所不能。
婆婆偶爾興奮得像個孩子,向我炫耀她又占領了朋友圈運動打卡封面。我知道她的好友并不多,且一年比一年少。但我沒說,怕掃了她的興。
這狹短的六千余步游道距程,卻縱貫了婆婆漫長的七十多年人生印跡。
婆婆出生于新中國成立的那年春天,有好幾個未曾謀面早夭的哥哥,她應該算是其父母真正擁有的第一個孩子。她的第一聲啼哭飄落在郴江白鹿洞橋與石油橋之間的河面上。
每每行至河道某個路段,她就會翻出記憶庫中的往事片段,講述我沒有見證到的——她的青春以及個人情感。講完總是重復發出苦盡甘來的感慨:“那時,哪能想到有今日的好生活啊!”
3
婆婆說,她的整個童年幾乎都泡在郴江里。
站在六中北校圍墻外的游道護欄邊,俯瞰郴江河水面,隱約可見幾方不太規整的天然大石頭,石頭上布滿毛茸茸的淺綠苔,小魚兒擺個尾,也能攪出一圈渾濁。
原先的河水是澄澈清亮的。母親牽著幼兒小手,挎一籃衣服,來到這個洗衣挑水的碼頭,小心緩慢地踏著石階一步一梯下河,幼兒坐在最后一級臨水的石梯上,小腳丫子在水中晃蕩,母親的捶衣板帶著節奏敲擊在平滑的石板上,那是世間最美妙動聽又最鏗鏘有力的搖籃曲。
碼頭右前方有座裸露在郴江河中間的荒草洲。婆婆童年時期還處在物質匱乏的年代,老是覺得胃空,對一切可食物品都充滿向往。趁大人忙碌沒空看管她,偷偷溜下挑水碼頭,劃拉幾招“狗刨”,游到荒草洲上找吃的,揪冬茅草芯生嚼,越嚼越甜;掀開石頭撿螃蟹、挖團魚蛋,煨在灶火里,滿屋子香噴噴;冬季用筲簊在河沿黑草叢下一撮,就有一海碗小河蝦,多鮮的味道啊!就算什么也不做,夏季泡在清澈的河水里找涼爽,心情也是愜意暢快的。
我喜歡成熟豐收的秋季,想起故鄉洞庭,平闊的湖面上,布滿密匝匝的綠葉紅菱,它們點綴在金燦燦的稻田與白水魚塘之間,構成一幅永恒的暖色系畫面。
蘇仙嶺后山卜里坪轄區張家灣在河對岸,是外公(婆婆父親)的故鄉。每年秋天外公從家山采摘一擔茶籽,光著干瘦的膀子,氣喘吁吁挑過河,身上盡是荊棘刮刺的痕跡。“哎喲,怎么把衣服搭在扁擔上?”路人這么問過外公。
“衣服爛了要買布補,皮刮爛了會長好。”外公窮怕了,把錢看得比命重要。
茶籽鋪在老屋坪場曬幾天,曬到茶籽殼裂開,外公摸搓著茶籽粒咧開嘴笑,當時年幼的婆婆極少見外公如此開心,只有臘月年關,外公在煤油燈下舔著口水,一遍遍數著手里那幾張薄錢時,曾經閃現這樣的笑。
茶籽一身是寶,茶籽殼引火煮飯,易燃耐久火力強;茶油炸出米面美食套環、蘭花根、燙皮、瓜片,揣著這些年禮,花五毛錢,買一張承載著婆婆的詩和遠方的火車票,去棲鳳渡外婆娘家走親戚看風景;茶圃(茶籽榨過油的茶渣)熬水洗出來的頭發柔滑黑亮,還是鬧魚(毒魚)的上好佳料,鬧死的魚放心大膽吃,安全無毒。
不知道是不是怕人哄搶,外公每次鬧魚都在夜晚。天擦黑時,外公躡手投幾塊茶圃在郴江河,年少的婆婆屏氣凝神等到半夜,她要負責站岸上打手電筒給撿魚的外公照亮,其時河面浮起一層白花花的魚,鱗光泛濫,她的作用只是在岸上看守那一大腳盆沒死徹底的魚,不再蹦回河里,并協助外公抬回沉沉地大腳盆。
鬧死的魚適合做熏干魚,嗜酒的外公,有了下酒的好菜。
酒,水一樣的流液,悲喜交織,有時是藥,有時是毒,變幻莫測。外婆討厭酒,夫妻倆經常在餐桌上當著兩個女兒“開戰”,相互嫌棄仇視,婆婆的耳朵里灌滿了他們的謾罵聲:外公喝到面紅耳赤,罵外婆“掃帚星”,生不出兒子,還克死了他的兒子;外婆則指桑罵槐地喊天,說老天沒開眼,不該收了好人,哭求大眼睛菩薩,收了眼前的惡人。
比婆婆小七歲的妹妹還不諳事,只顧著笑哈哈搶魚吃,她天性樂觀膽大敢闖敢拼,后來走上仕途,性格決定命運不無道理。婆婆則常被這樣的場景嚇得不敢上桌,餓了,就去郴江河里找生食祭牙口;愁了,就去郴江河岸打水漂(斜著丟小石片在水中,濺起水面一波三折)扔煩惱。婆婆一生扎根在郴江河畔的土地。
婆婆是靠郴江滋潤著長大的。
4
每逢中元節,鄰家祭祖燒冥幣紙錢是在自家屋門口,而婆婆卻要帶著晚輩沿河道走到石油橋,選定第三個河欄墩,才點燃香燭鄭重開啟祭拜儀式。
我當了書法老師之后,婆婆家祭祖的冥錢白包由我執筆。照著婆婆紙條上的姓氏輩分謄寫,她一再提醒:千萬別落下了給唐伯的那封白包。我很納悶:婆婆的父親是河對岸卜里坪張姓,母親是棲鳳渡李姓,姓唐的伯伯是誰?
唐伯就是外婆一生戀戀不舍的前夫。
外婆1914年降生在以魚粉聞名全國的郴城棲鳳渡,李姓鹽商家的二小姐。十四歲得了一場風寒,問診吃藥不見好轉,其父請來算命巫師施法,法師開示:速嫁人沖喜,方可救命。
外婆的父親長期從事食鹽買賣,跨過很多橋也走了很多碼頭。他挑著空篾籮筐與鎮上幾個小商販搭伴而行,自棲鳳渡步行郴州歇一夜,次日再步行去廣東坪石進貨,回來時,幾個人合租一輛騾子板車,貨物載在板車上,人緊跟在后面,一個來回大抵要七八天。來來去去的征途,結識了在郴州鐵路工作的唐伯,雖比女兒大了十歲,但相貌周正,為人和善,詢問得知唐伯尚未成家,當即把女兒許配給他。
唐伯家住處正是我們家現居位置。他家祖山在郴江邊四普莊山后,民國時期唐伯家境何等富足啊,為了便于祭祖臨時歇腳,竟買下三進三間大房。外婆嫁來一直住在這,土改時分出去左右兩進,僅剩一百多平方米地基。據外婆說,唐伯一家待她如同己出,夫妻萬般恩愛,婚后她的病真的奇跡般好了。
也不知是何種怪病,外婆婚后接連生了六個兒子,養到七八歲,莫名其妙突發暈厥不醒,一一夭折。
我問正在上醫學院的大崽,他根據癥狀分析,外婆的那些孩子,患的有可能是某種先天性心臟病,現代醫療技術可通過手術治愈。
1943年,外婆又染風寒,帶著最后剩下的幺兒,回棲鳳渡娘家休養,唐伯留守在家。他不是舍不得滿屋的財產,是怕外婆回家找不到他,就沒有躲進山里防空洞,有天在郴江河碼頭洗襪子,日本鬼子見他頭上戴著鐵路上的帽子,以為他是抗日兵,殘忍地在他身上連刺七刀,尸體隨著紅色河水沖到石油橋河段,被一塊石頭擋住,過路的好心人,找來鐵鍬鏟子,把唐伯埋葬在郴江河灘上。當天,日本鬼子在白鹿洞村殺死三個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唐伯是其中之一。
一個月后,外婆才從鄉鄰口訊中聞此噩耗,因當時鐵路已炸毀,她踉踉蹌蹌拖著病體趕到郴州,跪在河灘上的一堆新墳冢前,淚流成河……若不是身邊的幺兒支撐她活下去的信念,她真想縱身躍下郴江河,追隨亡夫而去。
短短三十天,外婆承受著人非物也非的悲痛,家被洗劫一空,徒留四壁空泥墻,幺兒巴巴地望著她,從未下過田地干過農活的外婆,開始挖土犁田,種菜種糧。
時間制造傷痛又療愈著傷痛。
河對岸卜里坪張家灣的外公,1939年被國民黨抓去當了壯丁,三年后逃亡回來,妻子跑了,兒子丟在同族人家中寄養,養得瘦骨嶙峋,眼睛鼓起老大,說是患了“疳積癆”。上無片瓦、下無立錐的外公,有幸得媒人牽線搭橋,父子雙雙入贅外婆家里,算是有了落腳營生之地,可惜他視為珍寶的兒子與外婆六歲的幺兒,一年內先后因疾病不治而去。
外公重男輕女的思想,嵌入骨子到死未改。外婆生下婆婆時,他嘆一聲氣,多年后看到自己的大外孫女時,他還是一聲嘆氣,嘆息聲似乎更為沉重。1975年,外公因哮喘病復發去世。婆婆懷著小兒在腹中,他終究未能見到他的男丁后代,未能舒出那一口怨氣。
外婆八十九歲高齡逝世,她說享到了兩個女兒的后福,不枉此生。彌留之際,似乎仍有遺憾,老是對著婆婆念叨唐伯,念他的俊模樣,念他的體貼,念他悲慘的命運,囑咐婆婆中元節莫忘給唐伯燒衣燒錢,要燒在離他最近的河岸……
外公和外婆,兩顆傷痕累累的心,用各自身上的疤痂磨蹉對方一生。
5
有時候,用心聆聽長輩們的過往舊事,不妄自判斷誰對誰錯,也不失為一種孝順。
六十年代末,蘇仙嶺底下有一家木棚小酒館,用竹筒子定斤兩打散酒,也有人坐在酒館柜臺邊嘗酒試味,愛酒的外公在這里碰上了同樣愛酒的公公,酒逢知己。
婆婆還清晰記得第一次見到公公的細節:他左手還燃著煙蒂,右手就取下耳朵上別著的煙點上了,手指熏得跟湘西臘肉皮一樣,眼睛望著天花板上的屋檁條,講話“這里嘛——那里么——”操一系列停頓思考的拖音官腔,其實只是個燒煤炭開火車的,其實那只是公公湘西方言口音。只有初小文化的公公,1958年從花垣縣十八里洞苗族山村招工來郴州鐵路,生肖比婆婆足足大了一輪。
從婆婆的描述,我聽出了她一開始就沒看上公公,這也為之后的離婚埋下了伏筆。
我見到公公時,他已是面容慈祥的老人,晚年腿腳不好,一個人住在郴江河畔機務段單位房,固執著不肯來我們家。他話語不多,知道我們要去看他,總會買些好吃的在房子里等著,碰上年節,悄悄地封好紅包,塞進我們衣兜口袋。2017年,公公摔了一跤,傷得很重,在醫院躺了半年,也終究沒能爬起來,躺到了香山陵園長眠。
外公吃了公公從鐵路食堂端來了幾碗葷菜幾瓶燒酒,暈頭轉向替他說話,語氣斬釘截鐵,婆婆若敢不同意,就滾出家門,他招公公當兒子。外公唱完“紅臉”,外婆接著唱“白臉”,綿聲柔語勸導婆婆:“工人吃香呢,月月有薪水,不愁吃穿。”
公公拎著一套換洗的鐵路制服,從郴江河邊機務段單身宿舍,輕松走幾步把自己搬到婆婆家做了新郎。
“制服口袋里肯定有一本存折。”我這么說著逗婆婆。
“鬼呢!錢屑子都沒有,他那三十三元工資,全給他自己抽煙喝酒還不夠。”多年后,婆婆說起他時,仍舊悲憤交加。
河岸一側全是婆婆隊上的菜地,游道還是一條雜草叢生的崎嶇泥路。知情的鄰居背著婆婆,竊竊告訴過我:這條路你公公婆婆年輕時的“戰道”,冷戰時幾個月不見公公足跡,熱戰時兩人打得灰頭土臉,有次把“戰道”擴展,打折了隊上幾塊土剛結辣椒的辣椒樹。
那個年代城鄉差距大,公公瞧不起婆婆是農民,婆婆抱怨公公沒有家庭責任感。
婆婆成了鰲頭灣村史上首個主動起訴離婚的“巾幗英豪”。法院判決:兩個孩子,大女歸公公,小兒歸婆婆。
從不后悔離婚,如果時光倒流,打死也不離,對孩子傷害太大。這是很多離婚女人自相矛盾的感悟。
法官上門調解,只要公公說一句軟話:保證少喝酒,多回家吃飯。婆婆就會撤了訴狀繼續過,多少婚姻瓦解在一時之氣。
1984年,婆婆把上段婚姻消耗的體力精力,全身心投入到勞動發財致富之路上,種菜賣菜、養雞喂鴨、拖板車收潲水養豬,男人一樣干活。次年,她攢下了建一層毛坯房的本錢,壯起膽子向銀行貸款,推翻外婆的泥磚房,原地建起兩層紅磚樓房,樓下出租樓上自住。隨著農民工蜂擁進城務工,嘗到了出租房屋甜頭的婆婆,又加建了兩層樓。
1994年,隊上的菜地全部征收,變成飛虹路的醫院、學校、菜場、企事業單位,她成了城里人。婆婆買了養老保險,坐在家里一點點拾起年輕時的愛好,看書讀報,唱歌跳舞玩電腦,不讓一日虛度。
沒有雨的夜晚,白鹿洞橋上人影穿梭,我和婆婆閑散著停靠在橋邊,輕風送來綠化叢中盈盈花香,郴江兩岸七彩霓虹閃耀,透映在河面化作繁星點點,隔著紅綠燈的蘇仙嶺福地廣場,傳來熱鬧響耳的紅歌聲,婆婆笑說他們調子沒唱準,要在G調上,嘚,是這樣唱的:“黨的光輝照萬代——”
我不吹牛,婆婆確實唱得好聽。
責任編輯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