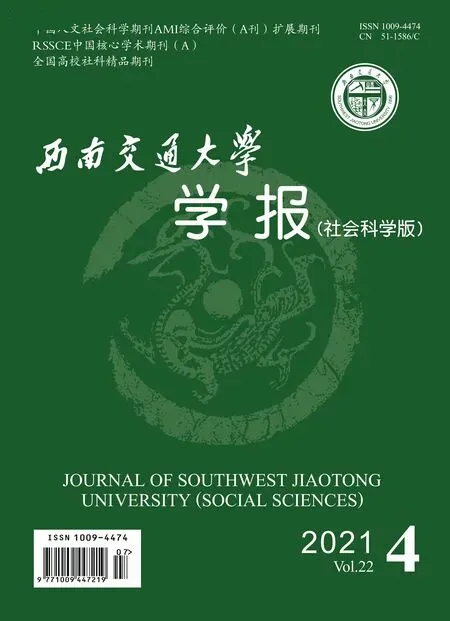《方言》“蝎、噬,逮也”解詁
一、與《方言》“蝎、噬,逮也”條相關的各家注解
揚雄《方言》作為我國最早的一部方言詞典,記載了大量的秦漢方言、口語材料,該書體量龐大,所涉詞條眾多,尤其在距今年代久遠的情況下,許多詞語傳承脈絡不夠清晰,全書更是充斥著大量為記錄方音而專門使用的特殊詞形,因而素以古奧難讀著稱。盡管自晉代郭景純以來多有為其專門作注者,但《方言》中仍舊有許多條目的考釋未能得到妥善處理,存在進一步挖掘和討論的空間。這也是今天的《方言》研究者需要著力關注并尋求突破的地方。我們接下來所要討論的就是一條這樣的材料。
《方言》卷七有一則記載:“蝎、噬,逮也。東齊曰蝎,北燕曰噬。逮,通語也。”〔1〕
對于該條內容的理解,戴震《方言疏證》言:“蝎、噬亦作遏、遾。《爾雅·釋言》:‘遏、遾,逮也。’郭璞注云:‘東齊曰遏,北燕曰遾,皆相及也。’”〔2〕戴氏顯然注意到了《爾雅》中“遏、遾,逮也”的訓釋當與《方言》該條記述相關,并對二者進行了系聯,這種處理應無甚疑義。因而圍繞《爾雅》“遏、遾,逮也”條的注釋,自然也就與《方言》此條的注釋形成了內容上的一致。
基于這一認知,我們可以相應擴大考察范圍。邵晉涵《爾雅正義》云:“‘遏’本作‘曷’。《小雅·四月》云:‘曷云能谷。’毛傳:‘曷,逮也。’”又“‘遾’本作‘逝’。《邶風·日月》云:‘逝不古處。’毛傳:‘逝,逮也。’通作‘噬’。《唐風·有杕之杜》云:‘噬肯適我。’毛傳:‘噬,逮也。’《釋文》引《韓詩》作‘逝’。‘逝’,及也。”〔1〕

華學誠先生在綜合考察各家觀點后,做出了蝎、噬之訓逮“當以方音轉語求之”的推斷,其《揚雄方言校釋匯證》云:“蝎、曷、遏、迨均為借字,疑其為逮或及之東齊讀音。”又“‘噬’蓋‘逮’之北燕讀音。《詩》中‘噬’、‘逝’雖通,義則并非訓‘逮’,毛傳非是。《邶風·日月》與《唐風·有杕之杜》之‘逝’和‘噬’,皆發語之詞。《邶風》朱熹集傳:‘逝,發語詞。’《唐風》朱熹集傳:‘噬,發語詞也。’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九:‘逝,發聲也,字或作‘噬’……‘噬肯適我’言肯適我也。’是《詩》之‘逝’、‘噬’為句首助詞,并無實義。《方言》以‘逮’訓‘噬’,當以方音轉語求之,《爾雅》亦源自古方言。毛氏引以解《詩》,誤已在前,邵、郝二氏復引毛傳證《爾雅》,乃通人之蔽矣。”〔1〕
或囿于全書體例之故,華氏并未進一步展開論證,且整體上采用了相對謹慎的持論方式。我們認為華氏這一推斷是可信的,本文即嘗試在此基礎上對該推斷加以論證申說。
二、舊注引據書證多誤信《詩經》毛傳
按照華學誠先生的觀點,《爾雅》和《方言》均有“噬(遾)”訓“逮”的記載。毛亨在為《詩經》作傳時,受《爾雅》影響,將本為句首助詞之“噬”解作“逮”,即相及義。后人為《爾雅》作注時又受毛傳影響,復引其觀點以證之。僅從邏輯層面而言,顯然就已經存在循環論證的問題。事實上,毛傳將“曷”訓為“逮”以及后人對其相應的發揮也存在類似情況。
下面我們需要首先考察的是《詩經》中的“曷”“噬”究竟應作何解的問題。《小雅·四月》云:“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谷?”毛傳:“曷,逮也。”孔穎達疏:“逮何時能為善。”理解作“及”“到”之義。然鄭玄箋:“曷之言何也”〔2〕,又王引之《經傳釋詞》謂:“《四月》曰:‘我日構禍,曷云能谷?’言何能谷也。”〔3〕均將“曷”理解為“何”。二解相較,不難發現訓“逮”一解存在較為明顯的問題,即文句中缺乏疑問副詞。聯系該詩上下文,“胡寧忍予”“爰其適歸”“我獨何害”“寧莫我有”等句都是以“胡”“爰”“何”“寧”等疑問副詞引領的疑問句。“曷云能谷”亦以疑問句作解為宜。但考之文獻用例,“云/云能”均無表達疑問之用法。因此,孔疏“逮何時能為善”一解也便無從談起。
而訓“何”一解,則于文意、文例皆可得通。文意上看,此句可譯為“看那山間泉水橫,一會清來一會渾。我卻天天遇禍患,哪能做個有福人?”王引之《經傳釋詞》:“云,語中助詞也。”王氏還例舉了《國風·邶風·雄雉》“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句,該句“曷云能來”與《四月》“曷云能谷”句式相似,可以互為參照。“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即言“道之遠,何能來也”〔3〕。此外還有《小雅·小明》“曷云其還?歲聿云莫”(什么日子才能夠回去?年歲將終)“曷云其還?政事愈蹙”(什么日子才能夠回去?公務越加繁忙)等句,“曷”之言“何”,“云”系語中助詞當無疑義。

以上《詩經·邶風·日月》與《唐風·有杕之杜》兩例中的“噬/逝”無論是作發語詞講,抑或是作疑問副詞講,均無較大窒礙。但理解為“等待”“相及”義則確如王引之所言“于義未安”。
既然我們排除了上述《詩經·邶風·日月》與《唐風·有杕之杜》中的詞例,那么究竟文獻中是否還能夠找到“噬/逝”訓“及”“到”的用例呢?答案是有的。《詩·大雅·抑》:“無易由言,無曰茍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俞樾《平議》:“逝,及也。言不可逝,猶言不可及,蓋即駟不及舌之意。”〔4〕應當說此一用例中“逝”的意義非常明確,當無爭議,“逝”即作“及”講。而考之“逝”字諸義項,其用作“及”講時,當與“遾”通。
三、“遏”“遾”“逮”三者在相及義上同源
既然我們贊同“蝎”“噬”之訓“逮”當以方音轉語求之,那么“蝎”“噬”與“逮”的具體關系究竟如何?這是需要我們進一步加以明確并溝通的。方言轉語籠統講,就是指的方言音轉現象,細究之則包括單純的借字記音與因方言音轉而產生的同源詞兩種情況。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前者具有明顯的臨時性質,而后者則一般發生在方言詞被共同語吸收后。兩種情況的核心區別在于,較之前者,后者還可以引入語義角度,實現音和義的“兩緯交叉”來幫助判斷。
迄今為止,在漢語詞源研究中最行之有效的同源詞音義關系的判定方法當是乾嘉以來學者廣泛使用后經陸宗達、王寧先生加以科學總結的平行互證法。孟蓬生認為將平行互證法應用于詞源學,其實質是在全面考察的基礎上利用歸納和類比的原理從大量同類現象中概括出音轉模式和義轉模式,使這些平行的同類現象之間構成互證關系〔7〕。它的基本公式是:a1∶ a2=b1∶ b2=c1∶ c2……這里的a1和a2代表兩個可以發生關系的音或義,也可以代表兩個同源詞〔7〕。這一公式的核心指向即判定和驗證一組具有孳乳關系的同源詞時,可以尋找另一組具有同類孳生關系的同源詞來進行互證。
這種平行互證法既是一種歸納法,同時也是一種類比推理。我們可以“從若干個體對象的某些共同屬性出發推斷它們有另外的相同屬性”,其優勢在于“使用平行互證法不必知道某個詞的具體讀音,只須了解其遠近分合關系。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古音構擬也還沒有一致的意見,只在相互關系中求同源的平行互證法可以保證我們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取得較為可信的結論”。“由于平行互證法是歸納和類比,它看重的是語言事實本身,不會使研究者從某種先入為主的音理出發抹殺暫時無法解釋或難以解釋的音轉現象。”〔7〕
試將這一公式應用在此條,如果我們將“蝎(遏):噬(遾):逮”看作“a1∶ a2∶ a3”的話,按照這一同源詞的判定公式,則需要對它們的平行關系進行補充。我們不妨具之如下:
《集韻·祭韻》:“堨,堰也。”《三國志·魏志·劉馥傳》:“興治芍陂及茄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陂塘之利。”〔8〕

《玉篇·土部》:“埭,以土堨水。”《正字通·土部》:“埭,壅水為堰。”《水經注·漸江水》:“太守孔靈符遏蜂山前湖以為埭,埭下開瀆,直指南津。”〔10〕
而對應于《爾雅·釋言》:“遏、遾,逮也。”遏、遾訓“逮”,既見于《爾雅》,表明它們已經進入書面語層面。黃侃論《爾雅》之名義即曰:“一可知《爾雅》為諸夏之公言,二可知《爾雅》皆經典之常語,三可知《爾雅》為訓詁之正義。”〔11〕


表1 “堨:澨:埭”音義關系對應表

表2 “遏:遾:逮”音義關系對應表
“逮”字從辵,隸聲。而隸字古文字從手持牛尾,表示“會及”“趕上”之義,實即逮之初文,可見“逮”字本義即為及、趕上。《爾雅》《說文》均謂“逮,及也。”《尚書·費誓》:“峙乃糗糧,無敢不逮。”孔傳:“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12〕《方言》亦謂“逮”乃“通語也”。
綜上,我們認為《方言》訓“逮”之“蝎”“噬”,本當從《爾雅》作“遏”“遾”,而“遏”“遾”應系“逮”字之方言音轉。此外,孟蓬生先生曾對章太炎的“孳乳”和“變易”兩術語進行改造,將它們應用來分析同源詞派生現象的兩大條例,其中“變易”例指“一個詞由于方言音變或古今音變而歧為兩個以上的同義詞。由變易形成的同源詞詞義和語法功能相同,所不同的只是讀音和字形”〔7〕。從這一角度看,“遏”“遾”之于“逮”,顯然正屬此類。
四、結語
王引之《經傳釋詞·自序》曾云:“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雖舊說所無,可以心知其意也”〔3〕,強調的正是在訓詁研究時要做到文意、文例方面考察兼備,立足事實分析辨證,而不輕易盲從古注舊訓。對于我國古代文獻典籍而言,早期很多傳注都深具篳路藍縷之功,但也往往受限于研究方法、學科思維甚或文獻以外的種種因素,不可能做到盡然周備。學術研究整體上呈現的應是一種螺旋上升的趨勢,這自然也要求我們在對待先賢研究時既要足夠重視、認真汲養,更要持一個相對嚴謹客觀的態度加以審視,尋求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