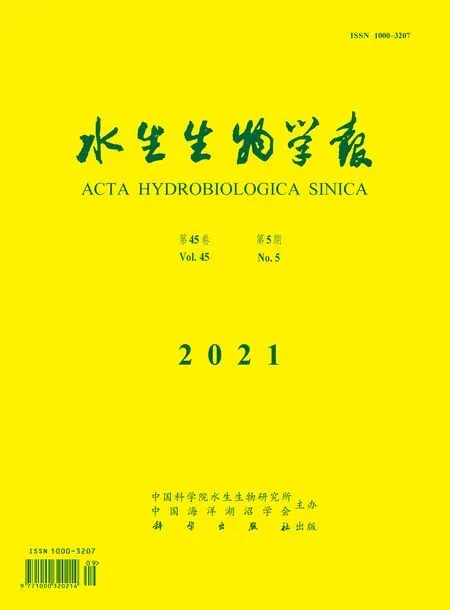四種鯉科魚類對捕食脅迫行為響應的種間比較
王 亞 付 成 胡 月 付世建
(重慶師范大學進化生理與行為學實驗室, 重慶市動物生物學重點實驗室, 重慶 401331)
在自然界中, 動物經常遭受不同形式的捕食脅迫。有研究者認為, 捕食者對獵物種群產生的非致命性影響通常大于直接的致命性捕食[1]。雖然動物種群中只有少數個體真正會被捕食者捕食, 但是大部分個體由于捕食脅迫的存在(非致命性影響), 主動或被動的在形態、生理及行為等方面表現出反捕食響應[1-4]。例如來自高捕食壓力種群的黑鯽(Carassius carassius), 其體高及快速啟動逃逸能力(最大速度、最大加速度等)均顯著高于低捕食壓力的種群[5]; 在遭遇捕食者后, 澳氏雀鯛(Pomacentrus wardi)顯著降低冒險行為以提高生存能力[4]。相較于低捕食壓力的埃氏短棒鳉(Brachyrhaphis episcopi)種群, 來自高捕食壓力種群的同類具有更高的活躍性和探索性, 對脅迫表現出更低的應激反應[6]。在諸多反捕食策略中, 魚類行為調節通常更為迅速和高效, 對于獵物魚應對捕食脅迫至關重要, 因此一直備受研究者關注[7-9]。
魚類行為特征中的探索性(Exploration, 個體對潛在捕食者、新棲息地和食物的行為反應)、活躍性(Activity, 個體由肌肉活動引發的運動行為狀態)和勇敢性(Boldness, 個體對已知環境危險狀況的反應)與魚類逃避捕食者密切相關[10]。在自然界中魚類種類繁多, 其在生理、生化特征和棲息地環境等方面的種間差異均可能對魚類的上述行為特征產生重要影響[11,12], 進而影響魚類對捕食脅迫的行為響應策略。然而到目前相關研究主要關注特定魚類的反捕食行為, 關于魚類對捕食脅迫行為響應策略的種間比較鮮有報道。魚類反捕食行為的種間比較有利于在種間水平建立魚類行為特征與生理功能及棲息環境等的關聯, 進而理解魚類行為策略種間分化的內在機制, 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
在遭遇捕食者時, 魚類可能會表現出反捕食行為以應對當前的威脅[2,13,14]。然而當捕食者暫時消失后, 魚類的行為如何變化則是非常有趣的問題。因為持續維持反捕食行為有利于其提高下次遭遇捕食者時的存活率[4], 但多數反捕食行為都是有代價的, 例如增加對捕食者的探索行為會增加能量消耗, 提高隱蔽場所利用率則會降低魚類獲取食物等資源的幾率[15]。因此, 早期經歷的捕食脅迫和當前環境中存在的捕食者對于魚類的影響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由此, 本研究目的旨在分別考查前期捕食脅迫經歷和當前環境中存在的捕食脅迫對獵物魚行為的影響, 并探討該影響是否存在種間差異。
為了探討魚類反捕食行為策略種間分化的內在機制, 本研究選擇鳊(Parabramis pekinensis)、草魚(Ctenopharyngodon idellus)、鯽(Carassius auratus)和中華倒刺鲃(Spinibarbus sinensis)等4種同水域生存的鯉科魚類幼魚作為獵物魚, 以其水域常見的天敵之一烏鱧(Channa argus)為捕食者。分別考查了前期捕食脅迫經歷(有、無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測定環境中有、無捕食者存在)對4種鯉科魚類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的影響。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魚的來源與馴養
實驗中用到的獵物魚鳊(1.3—3 g,n=200)、草魚(2—5 g,n=200)、鯽(2—4 g,n=200)和中華倒刺鲃(3—5 g,n=200)均購自重慶市合川區水產養殖基地。捕食者烏鱧(500—600 g,n=20)來源于重慶市南川區烏鱧養殖場。5種實驗魚分別置于長方形養殖水槽(2 m×1 m×0.5 m, 1000 L)中進行15d以上的馴養。在水槽中裝入曝氣后的自來水, 并且用充氣泵不停地向水中充入空氣保證到水中的溶氧水平接近飽和。每天上午10:00用解凍后的赤蟲(中國濱海駿業生物公司)搭配商業餌料對4種獵物魚進行飽足投喂1次; 捕食者烏鱧每隔2天使用新鮮的鰱肉片搭配商業餌料投喂至飽足1次。所有實驗魚均在投喂1h后用虹吸管清理剩余餌料和糞便, 然后進行每天1次的換水, 日換水量約10%。在馴養過程中水溫控制在(25±1)℃, 光周期為12L﹕12D。
1.2 實驗方案
馴養完成的鳊、草魚、鯽和中華倒刺鲃, 每種魚均隨機分為2組: 對照組和捕食(捕食脅迫經歷)組。對照組按照馴養期間的養殖條件繼續喂養,捕食組獵物魚與捕食者烏鱧在同一個水槽中混養,但通過鐵絲網將獵物魚和捕食者分隔開[16]。為強化獵物魚的被捕食風險, 避免獵物魚因無法被直接捕食導致其對捕食者無行為反應, 在混養水槽的捕食者一側放入不用于實驗測定的餌料魚, 供捕食者捕食, 以對鐵絲網另一側的獵物魚構成視覺和嗅覺等層面的刺激。捕食組除水槽中存在捕食者外, 其他養殖環境與對照組完全相同。15d后選擇身體健康、大小接近的4種獵物魚各20尾(體重、體長等數據見表 1), 選擇單尾魚分別在周圍可視環境中有、無捕食者烏鱧的條件下測定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實驗過程中水溫均維持在(25±1)℃。

表1 不同組實驗魚的體重、體長和樣本量(平均值±SE)Tab. 1 The body weight, body length and sample size of different groups (mean±SE)
1.3 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的測定
在本研究中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都采用實驗室自制的行為觀察裝置(圖 1)完成測定。該行為觀察裝置通過有機玻璃板組裝成長方體水槽(70 cm×35 cm×35 cm), 將水槽用不透明的有機玻璃板分隔成2個區域: 開闊區(55 cm×35 cm×35 cm)和隱蔽區(15 cm×35 cm×35 cm)兩部分。上述不透明有機玻璃板底部正中央有一個可以打開和關閉的小門(10 cm×10 cm), 小門打開時, 實驗魚可在開闊區和隱蔽區之間來回穿梭。隱蔽區內放置有塑料水草, 可為實驗魚提供隱蔽場所。行為觀察裝置的3個側面和底面均覆蓋有白色廣告紙, 用以減少外界環境干擾,同時增大實驗魚與背景環境的反差, 方便后期視頻分析; 觀察裝置的正面保持透明, 該側平行放置另一個刺激水槽(55 cm×15 cm×35 cm), 用于放置捕食者, 給予獵物魚視覺刺激。行為測定水槽及刺激水槽中水深均為10 cm, 以降低實驗魚在水體中的垂直移動[17]。實驗魚位于行為觀察水槽的開闊區時可清楚地觀察到刺激水槽中的狀況。行為測定時,刺激水槽中未放入捕食者烏鱧即為無捕食者存在的空白環境; 放入捕食者烏鱧則為有捕食者存在的環境。行為測定水槽上方安裝有與計算機連接的高清攝像頭(羅技Pro 9000), 用以拍攝實驗魚的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

圖1 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測定裝置示意圖Fig. 1 The device used to determine the exploration, activity and boldness
獵物魚和捕食者在行為測定前禁食48h, 以避免消化過程對行為的影響。分別在測定環境有、無捕食者存在的情況下進行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的測定: 將單尾實驗魚帶水轉移至上述行為測定裝置的開闊區域中(小門為關閉狀態), 隨后立即通過攝像頭拍攝獵物魚對陌生環境的探索行為, 持續20min, 即為探索性。40min后, 獵物魚基本上已完成對周圍環境的探索并逐步適應, 隨后開始另外20min的拍攝作為活躍性。在活躍性拍攝完成后,將開闊區和隱蔽區之間的小門打門, 用漁網快速下墜的方式(模擬捕食者襲擊)將獵物魚通過小門趕入隱蔽區域, 隨后進行60min的勇敢性拍攝, 期間小門持續打開。通過攝像頭記錄獵物魚第1次從隱蔽區域進入開闊區域所用的時間及實驗魚在開闊區域的累計停留時間。若獵物魚在60min內都未曾進入開闊區域則視為: 獵物魚進入開闊區域的時間為1h, 在開闊區域累計停留時間為0。所有視頻拍攝完成后通過“格式工廠”轉碼成avi.(15幀/s)格式, 然后采用動物運動軌跡跟蹤軟件EthoVision XT 9.0(Noldus, Netherlands)對視頻進行分析。探索性指標為實驗魚在陌生環境中的平均速度(cm/s)和運動時間比(%); 即為運動的時間占總時間的百分比, 其中運動狀態的判斷標準為實驗魚質心的移動速度大于1.75 cm/s[18]; 活躍性指標為實驗魚在熟悉環境中的平均速度(cm/s)和運動時間比(%); 勇敢性指標為實驗魚受到“襲擊”后首次出隱蔽場所時間(s)和在開闊區域累計停留時間(s)。
1.4 數據統計與分析
原始實驗數據經過Excel 2010進行常規計算后, 使用SPSS軟件(SPSS 17.0)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前期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對鳊、草魚、鯽和中華倒刺鲃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的影響使用雙因素協方差分析, 體重作為協變量。若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的影響顯著則進一步使用t檢驗做事后檢驗。所有的統計數據均以平均值±標準誤(Mean±SE)表示, 顯著水平為P<0.05。
2 結果
2.1 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對鳊幼魚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的影響
前期的捕食脅迫經歷顯著影響鳊幼魚的探索性(平均速度,F1,73=7.026,P=0.010; 運動百分比,F1,73=4.912,P=0.030; 表 2)。當測定環境中存在捕食者時, 捕食組鳊幼魚的探索性(平均速度、運動百分比)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 圖 2a和2b)。前期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對鳊幼魚活躍性(平均速度、運動百分比)的影響均不顯著(表 2)。測定環境對鳊幼魚勇敢性(在開放區域停留時間)的影響顯著(F1,75=6.532,P=0.013; 表 2)。對照組的鳊幼魚在有捕食者存在時表現出更高的勇敢性(在開放區域停留時間,P=0.02; 圖 2f)。

圖2 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對鳊幼魚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的影響Fig. 2 Effects of predation experience and measuring environment on exploration, activity and boldness in juvenile bream

表2 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對鳊幼魚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的影響Tab. 2 Effects of predation experience and measuring environment on exploration, activity and boldness in juvenile bream
2.2 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對草魚幼魚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的影響
前期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對草魚幼魚探索性2個指標的影響均不顯著, 但2種因素對這2個指標的影響均存在顯著的交互作用(平均速度F1.75=11.958,P=0.001; 運動百分比F1.75=18.784,P=0.001; 表 3)。在環境中無捕食者時, 捕食脅迫經歷導致草魚幼魚探索性(平均速度和運動百分比)顯著降低(P<0.05); 但當環境中存在捕食者時, 前期捕食脅迫經歷導致草魚幼魚探索性(平均速度和運動百分比)顯著提高(P<0.05; 圖 3a和3b)。在環境中出現捕食者時, 對照組草魚表現出探索性(平均速度和運動百分比)的顯著降低, 而捕食組卻表現出探索性的顯著提高(P<0.05; 圖 3a和3b)。
測定環境對草魚幼魚活躍性2個指標的影響顯著(平均速度F1.75=5.932,P=0.017; 運動百分比F1.75=5.183,P=0.026), 且2個因素對活躍性(平均速度和運動百分比)的影響存在交互作用(平均速度F1.75=16.393,P=0.000; 運動百分比F1.75=12.086,P=0.001; 表 3)。當環境中存在捕食者時, 前期捕食脅迫經歷導致草魚幼魚活躍性(平均速度和運動百分比)顯著提高(P<0.05; 圖 3c和3d)。此外, 在環境中捕食者的出現導致捕食組草魚活躍性(平均速度和運動百分比)顯著提高(P<0.001; 圖 3c和3d)。
前期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對草魚幼魚勇敢性的2個指標的影響均不顯著, 但2個因素對首次出隱蔽場所時間的影響存在顯著的交互作用(F1.74=4.727,P=0.033; 表 3)。當環境中存在捕食者時, 前期捕食脅迫經歷導致草魚首次出隱蔽場所時間的顯著降低(P=0.039; 圖 3e); 環境中捕食者的存在導致捕食組草魚首次出隱蔽場所時間顯著縮短(P=0.013; 圖 3e)。測定環境對草魚勇敢性指標中的在開放區域停留時間影響顯著(F1.74=6.297,P=0.014; 表 3)。但環境中出現捕食者時, 對照組(P=0.057)與捕食組(P=0.084)草魚在開放區域停留時間均未表現出顯著變化(圖 3f)。

圖3 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對草魚幼魚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的影響Fig. 3 Effects of predation experience and measuring environment on exploration, activity and boldness in juvenile grass carp

表3 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對草魚幼魚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的影響Tab. 3 Effects of predation experience and measuring environment on exploration, activity and boldness in juvenile grass carp
2.3 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對鯽幼魚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的影響
前期捕食脅迫經歷處理(平均速度F1.73=31.595,P<0.001; 運動百分比F1.73=39.331,P<0.001)和體重(平均速度F1.73=7.742,P=0.007; 運動百分比F1.73=7.883,P=0.006)對鯽幼魚探索性的2個指標均有顯著性影響(表 4)。無論在環境中有無捕食組, 捕食組鯽幼魚的探索性(平均速度和運動百分比)均顯著高于對照組(P<0.05; 圖 4a和4b)。
前期捕食脅迫經歷處理對鯽幼魚活躍性指標中的平均速度(F1.74=10.574,P=0.002)、運動百分比(F1.74=15.440,P<0.001)均影響顯著(表 4)。當環境中存在捕食者時, 相比對照組, 具有捕食脅迫經歷的鯽幼魚表現出更高的活躍性(平均速度和運動百分比;P<0.01; 圖 4c和4d)。此外, 在空白環境中, 相比對照組, 捕食組鯽幼魚也表現出更高的活躍性(運動百分比;P=0.025; 圖 4d)。但前期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均對鯽幼魚的勇敢性無顯著性影響(表 4)。

圖4 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對鯽幼魚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的影響Fig. 4 Effects of predation experience and measuring environment on exploration, activity and boldness in juvenile crucian carp

表4 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對鯽幼魚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的影響Tab. 4 Effects of predation experience and measuring environment on exploration, activity and boldness in juvenile crucian carp
2.4 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對中華倒刺鲃幼魚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的影響
僅體重對中華倒刺鲃幼魚的探索性(平均速度,F1.74=4.914,P=0.030; 運動百分比,F1.74=7.758,P=0.007)表現出顯著性影響(表 5)。
測定環境對中華倒刺鲃幼魚的活躍性(平均速度,F1.74=8.218,P=0.005; 運動百分比,F1.74=11.189,P=0.001)影響顯著(表 5)。具有捕食脅迫經歷的中華倒刺鲃在環境中有捕食者存在時表現出更高的平均速度(P=0.021; 圖 5c); 而無捕食脅迫經歷的中華倒刺鲃在環境中有捕食者存在時表現出更高的運動百分比(P=0.003; 圖 5d)。前期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均對中華倒刺鲃幼魚的勇敢性無顯著性影響(表 5)。

圖5 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對中華倒刺鲃幼魚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的影響Fig. 5 Effects of predation experience and measuring environment on exploration, activity and boldness in juvenile qingbo

表5 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對中華倒刺鲃幼魚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的影響Tab. 5 Effects of predation experience and measuring environment on exploration, activity and boldness in juvenile qingbo
3 討論
反捕食行為是魚類應對環境中捕食者的重要方式之一, 對于其提高捕食脅迫下的生存幾率至關重要[2,19]。例如增加的對捕食者的探索行為有利于獵物魚獲取更多的捕食者信息進而利于其做出更合理的應對策略[6]; 減少的覓食行為可降低獵物魚被捕食者發現的概率[8]。但是, 反捕食行為所帶來的覓食和生長的下降等不利影響可能會導致獵物魚在下一生活史階段的生存能力降低[4,20], 也即當前生存與未來生存可能存在權衡。因此, 獵物可能根據捕食脅迫的程度對反捕食行為做出調整可以降低反捕食行為所帶來的代價。已有研究發現, 孔雀魚(Poecilia reticulata)對飽足狀態下的捕食者表現出較少的反捕食行為[21]; 當前環境中無捕食者時, 來自高捕食壓力種群的寬鰭鱲(Zacco platypus)并未增加隱蔽場所的利用率[8]。本研究旨在考查早期遭遇的捕食脅迫經歷和當前環境中存在的捕食脅迫對獵物魚的影響是否一致, 及這種影響是否存在種間差異。
3.1 捕食脅迫對四種鯉科魚類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的影響
在本研究中, 僅在當前環境中有捕食者的情況下, 前期有捕食脅迫經歷的鳊幼魚表現出提高的探索性, 表明前期的捕食脅迫經歷對獵物魚對捕食者做出識別和行為反應具有重要作用[22,23]。以往關于鳊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22,24]。而當環境中無捕食者時上述結果不復存在, 這可能是一種在非危險狀態下減少反捕食行為以降低能量代價的行為策略。例如來自高捕食壓力種群的寬鰭鱲, 在當前環境中無捕食者時并未提高隱蔽場所利用率[8]。此外, 無論早期是否有捕食脅迫經歷, 在環境中有捕食者時鳊幼魚均變得更為勇敢(對照組和捕食組在開放區域停留時間分別提高了10倍和5倍; 捕食組P=0.140未達到顯著水平)。這表明在遭遇捕食者時, 鳊幼魚傾向于較為積極和對抗的行為策略。這可能與鳊本身具有較高的攻擊性有關。另外鳊為側扁型魚類, 體高很高, 因此很容易對捕食者形成口裂限制, 再加上其相對較強的運動能力[25], 捕食者對其威脅較為有限。
草魚在空白環境下捕食脅迫經歷導致探索性的降低, 而在捕食者存在情況下, 捕食脅迫經歷導致探索性的提高。活躍性的結果也頗為類似, 盡管在空白環境下對照組與捕食組草魚的活躍性顯著并不差異。可能因為對于草魚而言, 在空白的環境中, 具有捕食脅迫經歷的草魚通過降低探索性和活躍性來降低自己被潛在捕食者發現的幾率。而當較小的開放環境中已經出現了捕食者, 即使降低活躍性也無法避免獵物魚被捕食者發現, 維持較高的運動狀態, 時刻對捕食者保持警惕反而會更加利于生存[16,26]。值得注意的是, 對照組草魚在環境中存在捕食者時出現了探索性的降低。可能因為其缺乏捕食脅迫經歷, 進而對陌生的捕食者烏鱧并不了解, 因此暫時維持了較低的運動水平。另外, 結果發現, 前期捕食脅迫經歷(捕食者存在的情況下)和環境中捕食者的出現均導致草魚幼魚勇敢性的提高, 這可能也與捕食脅迫導致的應激反應有關, 也即在捕食脅迫存在情況下, 草魚采取了較為積極的行為應對策略。從整體上, 就草魚而言, 前期遭遇的捕食脅迫經歷和當前環境中遭遇的捕食者對其探索性、活躍性和勇敢性的影響較為類似。也側面反映出草魚對捕食脅迫更為敏感, 早期遭遇捕食脅迫造成的影響在無捕食者環境中依然保留。
無論測定環境中有、無捕食者的出現, 具有捕食脅迫經歷的鯽幼魚均表現出更高的探索性和活躍性。這表明無捕食脅迫經歷的鯽幼魚對其陌生捕食者烏鱧缺乏有效的識別, 因而未能做出適當的響應。反觀捕食組的鯽幼魚, 與草魚類似, 早期經歷的捕食脅迫使其一直維持著一定程度的應激狀態, 盡管這會帶來更高的能量代價[13], 但這種狀態的維持會提高鯽幼魚再次遭遇相同捕食者時的生存能力[27], 表明鯽幼魚可能采取的是一種犧牲生長而保障生存的適應策略。
中華倒刺鲃的探索性和勇敢性均未對捕食脅迫做出響應。然而, 活躍性的不同指標(平均速度和運動百分比)卻反映: 無論有無前期的捕食脅迫經歷, 在環境中出現的捕食者均會導致中華倒刺鲃活躍性的提高。這說明中華倒刺鲃也同樣通過維持較高的運動狀態來應對環境中已經存在的捕食者。劉海生等[16]也曾發現經過捕食者南方鲇(Silrurus meridionalis)暴露處理的中華倒刺鲃活躍性明顯提高, 與本研究結果較為一致。另外, 與鳊和草魚類似, 無捕食脅迫經歷的中華倒刺鲃也會對陌生的捕食者烏鱧做出一定程度的行為響應, 表明這3種魚對陌生的捕食者烏鱧均具有一定的識別能力,這與最近關于中華倒刺鲃的研究結果較為類似[13]。值得注意的是, 這種“識別”與獵物魚通過捕食脅迫經歷獲得的識別仍具有較大差距[13]。盡管如此, 在生境中遭遇陌生的捕食者時盡快識別該捕食者并做出反應對于獵物魚提高生存能力依然是十分必要的。
3.2 四種鯉科魚類反捕食行為的種間比較
高捕食壓力環境中的埃氏短棒鳉比低捕食壓力環境中的同類, 表現出更高的勇敢性、活躍性和探索性[27,28]。然而鱸(Perca fluviatilis)卻剛好與其相反, 在低捕食壓力環境中表現出更高的勇敢性[29]。對比之下, 本研究中捕食脅迫經歷和測定環境對鳊、草魚、鯽和中華倒刺鲃的影響也存在較大的種間差異。草魚明顯對捕食脅迫經歷處理和測定環境的影響反應更為敏感, 而中華倒刺鲃的反應則相對保守; 另外前期經歷過捕食脅迫的鯽持續維持一定程度的反捕食行為, 這可能是其能在高捕食壓力的生境中廣泛分布的重要原因之一[26]。4種鯉科魚類反捕食響應的種間差異可能與不同魚種自身的生理表型(如體高的大小和逃逸能力的強弱)和棲息環境中的捕食壓力有著緊密的聯系。4種鯉科魚類反捕食響應的相似之處則體現在: 當前環境中存在捕食者時, 4種鯉科魚類大部分會通過維持較高運動狀態的方式來應對捕食者。早期經歷的捕食脅迫與當前環境中存在的捕食脅迫對魚類的影響可能會存在較大差異。相比前者, 在當前環境中存在的捕食者對獵物魚的威脅則更為緊迫。但是早期的捕食脅迫經歷可幫助獵物魚對捕食者做出快速和準確的識別, 進而及時做出恰當的反捕食響應,因此對于魚類的生存也同樣至關重要[4,22,30]。當然,這種早期捕食經歷對于獵物魚產生的影響本身也是捕食者對獵物魚非致命性影響的一部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