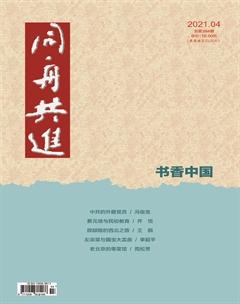潘菽:“紅色教授”與九三學社
張守濤


“人生活在世界上好比一只船在大海中航行,最重要的是要辨清前進的方向。回顧我一生走過的道路,雖然也曾迷失過方向,但所感欣慰的是,很快就認準了北斗,撥正了航向,并且最后終于找到了自己應有的歸宿。”這是《潘菽自傳》中的話。
誠如其言,民國時期中央大學“紅色教授”潘菽在人生路上逐漸辨清了前進的方向,選擇心理學作為自己的“北斗”,選擇共產黨作為自己的“航向”,“最后終于找到了自己應有的歸宿”,成為中國心理學奠基人、南京大學首任校長、中科院心理研究所首任所長。
十年定志、十年彷徨
潘菽出身書香門第,天資聰明,勤奮好學,少年時期就已閱讀了諸多先秦諸子及宋明理學著作,尤其仰慕宋代哲學家朱熹,期望將來也能成為像朱熹一樣的大學問家。1917年,潘菽中學畢業后,跳過兩年的預科,報考了北京大學哲學系,以優異成績直接考取了本科。北大校長蔡元培很欣賞潘菽的好學和多才,曾為他書寫條幅相贈。
北大讀書期間,正逢五四運動,潘菽滿懷愛國熱情參與了游行,并親手火燒趙家樓,成為被捕的32名學生之一。1921春,北大哲學系畢業后,潘菽公費留學。在選讀了一些教育學和心理學課程之后,尤其是受到正在攻讀心理學專業的蔡翹、郭任遠等朋友影響,潘菽對心理學逐漸有了興趣,覺得美國教育不一定適合中國,不如學一種與教育相關但更具根本性的學問,于是,他決定轉學心理學。
由于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復雜性,及中國社會條件和風氣不利于心理學發展,潘菽走的這條道路,正如他所言,“仿佛是山間之蹊徑,頗為崎嶇曲折,有時還要披荊斬棘”。當潘菽邁進心理學殿堂時,正逢國際上心理學派激烈紛爭,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潘菽絕不相信心理學不能成為科學,“心理學還不夠科學,正需要我們對它加強開展科學的研究”。為此,潘菽在國外學習了6年,先后讀了3所大學,終于在1926年拿到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學成回國。
潘菽回國時,中國心理學正處于創建階段,一些大學紛紛成立心理系。他被最早成立心理系的第四中山大學(即后來的中央大學)聘為心理學副教授,半年后升為教授,兼心理系主任,一直在該校工作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由于獲得了較好的對口工作,潘菽剛開始很是滿意,埋頭于心理學的教學與研究。中央大學理學院心理系當時只是個小系,有時一年只收一兩個人,但潘菽一樣認真備課,認真講解,從不草率。潘菽對學生和藹可親、循循善誘,學生都愿意親近他,有事找他談心,有困難找他幫助,有學生結婚還找他當證婚人。他從不以教育者自居,而是以自己的思想行為影響學生,有學生后來回憶說:“我說不出潘先生是怎樣教育我的,可是他又確實是時時刻刻地教育著我。”
潘菽在中央大學安心哺育自己鐘愛的心理學,“兩耳不聞窗外事”。但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內憂外患不斷,日寇侵華步伐在步步緊逼,如何能容得下“一張安靜的課桌”,“九一八”事變的炮聲還是把潘菽震醒了,“同時蔣政府在經濟上的破綻也日益顯露,學校的工資也要拖欠,研究費用和設備經費更談不上,我預見到我所追求的理想將難于實現。這是我在思想上產生彷徨的另一個原因”。此外,心理學派別越來越多,潘菽原以為可以通過實驗研究來確證心理學的科學性,可他“對心理學本身的問題也陷于彷徨無主的情況”。
盡管“彷徨無主”,盡管當時很多頗有才干的年輕心理學者紛紛轉行,但潘菽的志向并沒有動搖。他在報刊上以《為心理學辯護》等為題,接連發表文章,竭力爭取社會對心理學的了解、重視和支持,并鼓勵心理學同仁認清心理學的價值所在,敢于知難而進有所作為,共同開墾中國科學領域中的這一“半荒區”。
十年探路、十年依傍
1933年5月14日,潘菽的哥哥潘梓年(時任上海“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兼中共江蘇省委機關報《真話報》總編)被叛徒出賣而被捕,關押在國民黨南京警備司令部拘留所。潘菽為營救胞兄奔走呼號,拜請蔡元培、邵力子等社會名流施加壓力。同時,潘菽又以家屬身份,前往探監,不斷送去藥品、食品,傳遞外界消息,終使潘梓年在1937年6月被營救出獄。在此過程中,潘菽對國民黨和共產黨有了進一步認識,“在設法營救的過程中我開始接觸了黨,對黨的綱領、性質及艱苦斗爭的情況逐步加深了認識,逐步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從此,我認清了應取的方向,擺脫了純學術的道路,決心跟著共產黨,投身于抗日救國的革命洪流”。
抗日戰爭爆發后,潘菽隨中央大學西遷重慶。由于剛開始對戰爭估計過于樂觀,潘菽沒有把家屬接去,整個抗戰期間單身在渝。“在這八九年緊張生活中,心神自難安定,一天到晚關心的是抗戰形勢的變化。前半階段,敵機時常來轟炸,有時夜里也來,使人日夜難安,自然很難談到研究工作。心理學教學工作則不能不堅持下去,但也只能把舊的知識一次一次重復著教。備課時間倒省了不少。夜幕垂下以后,總要到熟人朋友那里去走走、聽聽、談談。”如此,潘菽開始不再“一心只讀圣賢書”,而是創建“九三學社”,成為著名的“紅色教授”。
起初,在長兄、《新華日報》負責人潘梓年介紹下,潘菽參加了郭沫若組織的“中國學術研究會”。因為長兄的關系,潘菽經常去新華日報編輯部,了解一些抗戰或延安情況,也參加《新華日報》組織的一些活動。后來,潘菽聯系五四時期同時被捕的北大老同學許德珩,建立了一個座談會,并經周恩來、潘梓年授意,邀請原先“自然科學座談會”的人陸續加入,逐漸發展到30余人。剛開始取名“民主科學座談會”,但一直沒有公開。1945年9月3日,大家在開會談到座談會名稱時,潘菽建議就用9月3日這個世界反法西斯勝利日命名座談會,稱為“九三座談會”,獲得與會人員一致同意。
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和蔣介石和平會談,在張治中寓所接見了潘菽、梁希、涂長望、金善寶等教授。潘菽在會見中提問毛澤東:“共產黨為什么把自己付了很大代價解放的一些地區讓給國民黨呢?”毛澤東講,為了避免內戰,達成全國統一,共產黨人向來以民族大義為重。隨后,毛澤東站起來,在椅子后面退了兩步說:“讓是有限度的,讓一步、兩步是可以的,再讓第三步就不可以了”,并作了一個還擊的手勢。“毛主席深刻而生動地闡述了當時國內外的形勢及我們黨的主張,使我們受到極大的鼓舞和教益”。

毛澤東還特地會見了九三座談會負責人許德珩夫婦,明確建議,九三座談會應辦成永久性組織。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鼓勵和指導,九三座談會決定更名為“九三學社”,于1946年5月4日舉行成立大會,宣告九三學社的成立,發表九三學社國是主張。之所以取“學社”這個名稱,是潘菽“認為‘九三原來團結的主要是科技、高教、醫藥等方面的人,‘九三成為政治團體后仍應本著這個宗旨。但這方面的知識分子在那時雖然很多人都有進步的要求,卻又不愿沾政治的邊。所以‘九三這個團體不宜采用政治色彩較濃的名稱,才可以使較多的人加入。這也是‘九三應起的主要作用”。潘菽作為“九三學社”主要創建人之一,在成立大會上當選為中央理事,此后一直是九三學社主要領導人(新中國成立后,潘菽負責南京九三學社工作,1958年后一直擔任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
隨著共產黨逐漸取勝,九三學社打算解散,理由是“民主與科學”共產黨可以做得更好,不需要九三學社了。但周恩來對潘菽說,九三學社不僅不能解散,而且要作為參加新政協的民主黨派,繼續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與共產黨一起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九三學社成為當時團結各界人士、擴大共產黨統一戰線的紐帶和橋梁之一,在反蔣擁共幫助共產黨取得政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1946年9月3日,抗日戰爭勝利一周年之際,九三學社發表《為國際民主勝利周年紀念宣言》,主張立即停止內戰,實行政治協商會議,解散特務機構,嚴懲漢奸等,獲得廣泛輿論支持。
為響應共產黨提出的“民主聯合政府”號召,1944年,潘菽還和梁希、涂長望、金善寶等人在共產黨支持下,聯合包括竺可楨、李四光等著名科學家在內的一百多人共同發起組織了“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次年7月1日,中國科協正式成立,潘菽被選為常務理事,負責協會財務工作并擔任會刊《科學新聞》主編。潘菽等人還發起組織“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并倡議在聯合國設立科學組織或擴大原有的文教組織,因而有了后來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中央大學復員南京后,國共隨即展開決戰,潘菽的政治傾向更加鮮明。他以中央大學教授的身份,掩護中共地下黨及其外圍組織“新青社”的活動,為“新青社”保管過一批秘密圖書資料。1947年,中央大學中共黨支部的組建會議就在潘菽家中召開。他還不顧個人安危,保釋過以“危害民國”罪被捕的中大學生。
1948年5月,南京大專學校開展“五四紀念周”活動。5月4日,針對國民黨制定憲法、選舉總統等行為,潘菽在“民主與科學座談會”上指出五四運動所要求的民主,應當是整體的民主;中國的民主運動必須是社會改革運動,而不是什么“立憲”,國民黨憲法并不能解決問題。潘菽還曾在報刊上用隱晦的筆調寫道:“今天的陰云密布,風狂雨驟,未必就不是明天天朗氣清的前奏。冬天已經到了冰封雪融的時候,春天的到來也不會太久了。”國民黨政府為挽回敗局,曾組織了一個“官兵心理委員”,邀請心理學家幫助軍隊“鼓舞士氣”“振作精神”,力邀潘菽參加,被他斷然拒絕。他也不為當局的《國防月刊》“國防心理”專號寫文章,堅決與國民黨“絕緣”。
由于潘菽鮮明的態度,時人稱他為“紅色教授”。國民黨特務機構將他列入黑名單,日夜嚴密監視他的活動。1949年解放軍渡江作戰前夕,共產黨為了確保潘菽、梁希、涂長望三位中大教授的安全,防止國民黨敗退前對他們暗下毒手,派潘菽堂弟潘漢年將他們護送到上海,又轉赴香港。4月22日,“百萬雄師過大江”第二天,又將他們從香港轉送北平。不久,應周恩來邀請,潘菽、梁希、涂長望參加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會議。同年8月,潘菽返回南京,參加中央大學的接收改造和南京大學的籌建工作,被任命為南京大學教務長兼心理學系主任。
潘菽一直堅守著心理學這塊陣地。董必武曾邀潘菽去解放區生活,被他婉拒,因為“其實,要照顧家屬是一個理由,還有一個理由我卻沒有說,那就是為了心理學我還是留在學校里比較合適”。潘菽等教授熱衷參加眾多座談會,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學習、交流知識。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潘菽“世界觀開始轉變,初步地樹立了唯物主義的世界觀。這時再來考察心理學的科學問題就顯得明白了”。潘菽還為心理系學生開設了一門新課——理論心理學,試圖結合馬列主義來思考、解釋心理學的基本理論問題,探索心理學新的發展道路。
十年自強、十年播揚

新政權成立后,潘菽接替梁希(梁希出任中央政府林業部長)擔任調整后的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1951年被任命為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在1952年全國院系大調整時,考慮到儀器設備搬遷問題,潘菽沒有把南京大學留在四牌樓原址,而是搬到了金陵大學校址,將四牌樓校址留給了新成立的南京工學院(后來的東南大學)。潘菽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為南京大學做了一大貢獻,即保留了全國唯一一個心理系(1956年南京大學心理系并入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1955年,潘菽當選為中科院生物學部學部委員,是當時中國心理學領域唯一一位學部委員。次年,他與南大高濟宇等6位教授一批加入共產黨,隨后辭任南大校長,在中國心理學面臨巨大困難和外界壓力情況下,毅然提出并率領南方眾多心理學家北上北京,促使了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的創建,并擔任了首任所長兼中國心理學會會長。
“文革”結束后,潘菽感到時日不多,更加奮力工作。為盡快恢復和發展中國心理學,年已八旬的潘菽不顧體弱多病,重新挑起了心理研究所所長和中國心理學會理事長兩副重擔。他一方面不辭辛苦地做了大量組織領導工作,主持《關于意識的心理學研究》《教育心理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心理學卷》等書籍編寫,同時身先士卒,帶頭研究、播揚心理學。
在生命最后10余年里,潘菽共發表論文20多篇,出版著作5種,還先后培養了3名碩士研究生和4名博士研究生。他在心理學教學、科研及其領導崗位上整整工作了六十年,為中國心理學的奠基、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心理學會第四屆理事會理事長荊其誠教授指出:“我國心理學能有今天這樣的規模和繁榮,與潘菽同志的嘔心瀝血是分不開的。”心理學史專家高覺敷教授在一篇懷念文章中寫道:“毫無疑義,潘老是當代中國心理學的帶路人”,“是我國心理學界的泰斗”。
一次,女兒專門寫信給潘菽,以父女骨肉之情苦心相勸,勸他保重身體。他回了一張小小字條,上面寫道:“我專心一志,時間不夠用是事實,實無辦法。早睡不可能做到,除非放棄工作。”1988年潘菽因患腦溢血病故,結束了他曲折而堅定的六十年心理學歷程,享年91歲。
(作者系文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