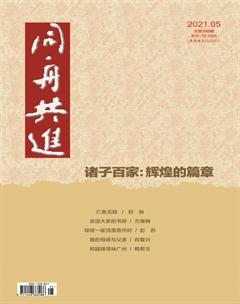走進大家的書房
趙珩:書房藏有家族四代人的檔案
早年讀過趙珩先生的《老饕漫筆》,很欣賞他筆下的“食話掌故”,一直想找機會認識他,約他寫更多老饕食話。后來又讀到《彀外譚屑》《舊時風(fēng)物》等作品,認識到趙珩先生在社會文化方方面面的掌故和歷史,都有很深的造詣和非常豐富的認識。
趙家是世家大族,自太高祖達綸算起,“一門六進士”。曾祖父趙爾豐為駐藏大臣,署理四川總督。彀外堂藏有家族四代人豐富的檔案,經(jīng)歷那么多時代變遷,這些檔案、史料大部分保存至今,這是趙珩先生最欣慰的事情。
彀外堂位于一棟普通居民樓里,趙珩先生在這里有三套單元,門對門兩套,一為彀外堂,另一套為夫人吳麗娛老師書房,樓下一套為生活起居。
方緒曉:讀您的《二條十年》,真羨慕您小時候的生活環(huán)境和閱讀啟蒙。少年時代的閱讀對您意味著什么·
趙 珩:這本書記錄了我1955到1964年住在東四二條的生活,正好是六歲到十五歲的童年和少年時光。少年時的閱讀對我影響非常大,后來人生的很多面向,在這里都能找到痕跡。
1956年時我8歲,上培元小學(xué),放學(xué)時喜歡溜達回家,每天必逛隆福寺。隆福寺是民國時期北平兩大書籍中心,另一個中心是琉璃廠。高峰時,隆福寺有二十幾家書店。但五十年代公私合營都并入中國書店,只剩下一家叫“修綆堂”,專營傳統(tǒng)的線裝書,按經(jīng)史子集四部擺放。我不懂古書,卻喜歡店里的氛圍,總愛在店里轉(zhuǎn)來轉(zhuǎn)去。時間一長,幾個老年店員都認得我,有什么不懂就問他們,慢慢地也明白了一些經(jīng)史子集,我的目錄學(xué)知識大概就是在“修綆堂”打下了一些基礎(chǔ)。
還有一家書店,是兒時記憶中難以忘懷的,在我家所在的東四二條對過的“曹記書局”。店里賣各類新書,但主要經(jīng)營小人書(連環(huán)畫),既賣也租,我小時候看的小人書,多是這家書局租的。我現(xiàn)在還藏著一套一版一印的《紅樓夢》小人書,還有老版的《三國演義》《水滸》《說岳》等小人書都還在。除了小人書,正經(jīng)讀傳統(tǒng)歷史書,應(yīng)該是從林漢達的《東周列國故事新編》和《前后漢故事新編》開始,這兩本書對我兒時影響很大。
小時候記憶力好,像《古文觀止》《論語》這些經(jīng)典文言文都能通背,而且很難忘記,直到現(xiàn)在我基本上還能背誦不少篇章。《古文觀止》中,我父親給我講過兩篇,一是《鄭伯克段于焉》,二是《歸去來辭》,從此對《古文觀止》印象深刻。上學(xué)時,老師讓讀的書都不怎么讀,就愛讀這些課外書。
小時候因為喜歡《水滸傳》,就想了解相關(guān)的歷史背景,剛好看到父親有線裝的《大宋宣和遺事》,這套筆記中的《元集》《亨集》里,有關(guān)于宋江等人的故事。后來又尋來余嘉錫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實》,俞萬春的《蕩寇志》等,繼續(xù)自己的《水滸》考據(jù)興趣。正是在這些由淺入深的閱讀中,開始了我這輩子與書的不解之緣。可見,孩提時期,家庭的閱讀氛圍和環(huán)境對孩子的成長多么重要。
趙家算不得望族,我們是漢族,但隸屬漢軍正藍旗籍。從太高祖達綸算起,“一門六進士”。曾祖一輩兄弟四個,除了曾祖父趙爾豐不是進士,其他三位都是進士。老大趙爾震和老二趙爾巽是同治甲戌科同榜進士。趙爾震做到工部主事三品頂戴,趙爾巽做到四川總督、東三省總督、奉天將軍等,后出任清史館總裁;老四趙爾萃光緒己丑科進士,三品銜,后辭官回泰安故里。曾祖趙爾豐雖然不是進士,也是道員出身。做到駐藏大臣,署理四川總督,也算封疆大吏。清末九位總督中,我家占了兩席。
曾祖趙爾豐膝下四子一女,我祖父趙世澤系幼子,家族大排行老九,被稱為“九爺”。初隨曾祖趙爾豐在四川,保路運動后,曾祖殉難,祖父逃出成都回到北京。辛亥革命爆發(fā)后,江蘇巡撫程德全宣布江蘇獨立,祖父應(yīng)召南下做程德全幕僚。程德全卸任后,祖父北上投奔退居在青島的曾伯祖趙爾巽。
1929年,祖父舉家從東北遷回北平,這是他顛沛流離一生中最閑適的一段時光。他博學(xué)多才,喜歡收藏碑帖、字畫,在當(dāng)時北京的古玩行,“趙九爺”的名聲可謂不小。他的收藏尤以碑帖見長,品質(zhì)很高。后來北平被日本人占領(lǐng),祖父堅決不出來做事,因此斷了經(jīng)濟來源。他的很多收藏就在那時候陸續(xù)賣了,散了。1950年初,祖父突發(fā)腦溢血過世,享年66歲。
父親1926年出生于齊齊哈爾。1929年遷回北平后一直學(xué)習(xí)、工作、生活于北京。他從小接受中國傳統(tǒng)式教育,在經(jīng)學(xué)和史學(xué)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后入讀輔仁大學(xué)經(jīng)濟系。1958年,父親由商務(wù)印書館調(diào)去中華書局,從此,他的人生就沒離開過“二十四史”的點校出版工作。

方緒曉:請帶我認識一下“彀外堂”里的書吧。
趙 珩:我家的書啊,沒什么稀罕的。著名藏書家、古籍目錄學(xué)家黃永年先生來看過,他有個定論,“你家的書是讀書人的書,不是藏書家的書”。收藏家韋力也來采訪過,他把所有的書都搬下來,過了一遍,他也同意黃永年先生的看法。當(dāng)然,也有幾部不錯的,但總體來說還是讀書人的書。
我的書房比較雜,什么類型都有,屬筆記最多。小時候在父親的大書房接觸中國古代筆記后,我一直在關(guān)注和收集筆記這種題材。中國歷代筆記,我的書房里應(yīng)該是非常全的,分成三類:史料筆記、讀書筆記和社會生活筆記。像宋代的《太平廣記》,可以稱之為史料筆記;清代李慈銘的《越縵堂讀書記》則是讀書筆記;而像《東京夢華錄》這一類,可稱為社會生活筆記。
筆記和隨筆、散文是有區(qū)別的,筆記還是史料,而散文、隨筆屬于文學(xué)。筆記是可以援引的,但有些筆記是不能援引的,如《清邁類鈔》。我的《老饕漫筆》《彀外譚屑》《舊時風(fēng)物》等就屬于筆記,只不過寫時用的是現(xiàn)在的漢語。
我的書房用一個字概括,就是“雜”,書畫、文玩、筆記、飲食、戲曲、北京史、郵票……我喜歡的東西太多。吳麗娛那屋書房是另一番風(fēng)景,她是典型的學(xué)院派,是陳寅恪陳門第三代弟子,她的老師是陳寅恪弟子——北大的王永興教授。
我們的書分類很清晰。二十四史的《宋史》以前都歸她(當(dāng)然,前四史是每人必備的),《資治通鑒》也是一人一部。其他的史學(xué)著作,宋元以前的都放她那邊,明清以后的則放我這邊。還有講制度史的,比如三通(《文獻通考》《通典》《通志》)則都在她那邊。
我們的書不交流,互相不看對方的書,也不涉獵對方的研究領(lǐng)域。吳麗娛是典型的研究型學(xué)者,邏輯思維很強。而我是形象思維的人,大腦里似乎儲存著很多膠片,記憶力很好,小時候記憶特別清楚,尤其是讀過的書,很多至今還能背誦。
方緒曉:如此規(guī)劃的書房容量,都經(jīng)歷過什么?
趙 珩:我家的書,一部分主要是繼承我父親留下的,大概占1/4,全部是經(jīng)史類的,其余的3/4都是我們倆后來慢慢積累的。我涉獵的領(lǐng)域太多,以至于各種書籍瘋長,當(dāng)然,也在不斷地淘汰和優(yōu)化。夫人做學(xué)術(shù)研究,書房基本是清一色的經(jīng)史類書和當(dāng)代研究著作,容量驚人,其規(guī)模比我有過之無不及。
在今天這個信息時代,紙媒是不會消失的。閱讀這個東西必然存在,書是有溫度的。書籍、書札、手稿等方面的收藏也越來越熱。雖說如今不通過讀書也能達到“黃金屋”和“顏如玉”,但對于個人的享受,沒法用“黃金屋”和“顏如玉”來比擬。
方緒曉:非常同意。我看到您家書房除了書,還有各種古玩、字畫等,那里一定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吧。
趙 珩:是的。我家書房里,大多數(shù)東西都有歷史。我的書桌、書柜、印泥盒、閱讀燈、筆筒、扇子、兒時的玩具等,都很有些年頭了。例如這個書柜里存放的大多是線裝書,雖如黃永年先生所言,沒有藏書家的書,但也有一些不錯的古籍,如明嘉靖本《白氏文集》等。還有像鄧之誠注本《東京夢華錄》,這是第一版,上面有鄧之誠送我父親的上款,這個版本只印有幾百冊。
書房中最讓我珍視的,是我們家族幾代人的檔案,總算是留下了一些。如我太高祖的詩集、高祖的墨跡、祖父的藏品,還有祖父當(dāng)年在江蘇都督程德全那里做幕僚時,替程德全撰的很多電文的底稿,尤其是祖父改編的很多昆曲本子。父親十三四歲的日記,以及很多手稿;母親年輕時的繪畫等等。
馬勇:我的書房,為用不為藏
1979年,恢復(fù)高考第三年,馬勇考入安徽大學(xué)歷史系,入學(xué)后到圖書館借的第一本書是侯外廬的《中國思想通史》,正是這本書影響了馬勇的學(xué)術(shù)方向,書中提到哪本書,就把那本書找來看,大學(xué)四年,幾乎把大學(xué)圖書館里與思想史專業(yè)相關(guān)的書都讀了一遍。
1983年,馬勇順利考上復(fù)旦大學(xué)歷史系研究生,師從著名思想史學(xué)家朱維錚教授。1986年畢業(yè)后分配到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從事近代史研究。
像大多數(shù)愛書人一樣,馬勇家每個房間也都是書,但多而不亂,不同書架都有各自的主題和分類,像客廳沙發(fā)背后,以書目、索引、年譜、日記等書籍為主。馬勇反復(fù)強調(diào),讀書目是做學(xué)問的第一要訣,要通過大量的閱讀書目和索引,慢慢梳理出自己的學(xué)問路徑,知道哪些書在哪里可以找到。
而談到書房的未來,馬勇也是愁上心頭。他說,人再長壽,生命也只是一個過程,而人過世之后,那些曾被我們珍視的書,就永遠失去了主人的守護,變得很“可憐”。
方緒曉:您的書房是怎么樣“成長”起來的?
馬 勇:我是農(nóng)村出來的,父親讀過私塾,對孩子讀書還是很支持的,我們小時候,如果你愿意讀書,就會給你創(chuàng)造條件。印象中,上世紀60年代邢臺地震,我們安徽家家都搭地震棚,我和大弟一人一個地震棚,在里面讀書,我的閱讀啟蒙差不多是從那時候開始的。但那時我們能讀到的東西很少,印象中只有浩然的《金光大道》《艷陽天》,還有巴金的作品。大概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我到新華書店買過一套魯迅的單行本,后來我把它們裝訂成冊。
1986年大學(xué)畢業(yè)到北京來的時候,我?guī)У娜抠Y產(chǎn)就是12個紙箱的書。為什么能夠在七年讀書期間積累那么多書呢?因為我是帶工資上學(xué),像有一套《中華大詞典》,就是我在讀本科的時候買的,當(dāng)時大概就30多塊錢。
剛來北京,我住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對面的東四頭條社科院宿舍院內(nèi),給我的是一個20平方米的里外間,根本談不上有書房。但宿舍離單位近,我的書都放在辦公室。到2005年搬家之后,才有了一個20多平方米的書房,但實際上每個房間都是書,樓下還有一個地下室也是書,加起來大概有三萬多冊書。直到退休前,才徹底把辦公室的書都搬回到家里來。
我是學(xué)古代思想史的,后來到近代史所工作,當(dāng)時的研究環(huán)境跟現(xiàn)在不一樣。那時候我們是剛來的年輕人,老先生不讓我們寫東西,也沒那么大壓力,就靜靜地讀了五六年書,算上本科,專心讀了十幾年書。
等到后來開始寫東西時,腦子里對歷史有無數(shù)種自由組合,也知道材料在哪兒,隨時可以調(diào)動這些資源。我寫東西面比較廣,得益于當(dāng)年閱讀比較系統(tǒng),可以從古至今打通。
方緒曉:在書房和圖書館之間,您是如何取舍的,比如哪些書收在家中,哪些去圖書館閱讀?
馬 勇:我的書基本是一個流動狀態(tài),所做題目相關(guān)的書都在我的書房,暫時不做的就搬到地下室去。需要參考和補充的基本是去圖書館,但很多時候,做研究需要借助更多的地方。比如,當(dāng)時我做蔣夢麟的研究,不少圖書館跑遍了卻沒找到太多的材料,這就需要借助臺灣、香港等研究機構(gòu)的圖書館。而我的書房本身,我保持它是流動的狀態(tài),隨著自己的研究變化而變化。我的書房是用的書房,而不是藏的書房,到現(xiàn)在為止,沒有一本書是因為藏而買的。
客觀造成我書多的原因是,我原來做古代史,所以積累大量的古代史方面的書,大學(xué)畢業(yè)后做近代史,又大量購買近代史方面的書。加之三十多年來,我的書都跟著題目走,不同的題目又增加了不同的書。比如,有學(xué)者找我合作做抗戰(zhàn)時期的中國思想文化,就增加了大量抗戰(zhàn)史的書。后來做嚴復(fù)的研究,關(guān)于嚴復(fù)的書基本上都收齊了,還去沈陽看嚴復(fù)的資料、手稿等。之后又做章太炎的研究,用三年的時間讀章太炎的資料,《章太炎全集》最后就是我參與一起合攏的。
到目前為止,我自主性的研究比較少,只有梁漱溟算是我自選的,還有幾本論文集。而我自己真正想寫的是“經(jīng)學(xué)史”和“儒學(xué)史”。上世紀90年代初,龐樸主持“中國儒學(xué)”項目時,曾約我參與,第一卷《儒學(xué)簡史》就是我寫的。
方緒曉:這么多研究項目,如此高速的圖書增長,您的書房如何容納得下,有什么好的書房優(yōu)化手段嗎?
馬 勇:我會隨著項目的變化處理一些書,主要散給像孔夫子、布衣書局這樣的二手書店。不散書,家里可容納不了。淘汰書很不忍,人都有占有書的欲望,但沒有辦法。別人送的書,我是不敢往外散的,這類書還不少,所以我通常放在書房最高處,免得不小心散出去,就很尷尬了。有一次,我在一個流動書攤看到自己送給一位老先生的書,可能是老先生過世后,家里人處理出來的。人的眼睛在這時候特別敏銳,一眼就看到自己的書了。

在書房里,經(jīng)常會碰到找不到書的情況。所以我一般先上網(wǎng)下載書的電子版,也許過不了多久,找不到的書又“自動”出現(xiàn)了。很多大型的書我一般保留電子版,比如《清實錄》國家清史檔案叢刊,還有如大象出版社出版、虞和平主編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全套30多萬,我買個電子版才100元。
方緒曉:我看您書架上有很多目錄學(xué)方面的書,這也是您學(xué)術(shù)研究的一部分嗎?
馬 勇:我很同意歷史學(xué)家陳垣的一個觀點:“人的學(xué)問最終是一個書目。”他通讀了《四庫全書》——一個人怎么可能通讀完《四庫全書》呢,他其實是在讀書目。我的太老師蔡尚思,一個假期讀完了江南圖書館,其實他也是在讀書目,后來,當(dāng)然寫了很多關(guān)于目錄的書。
會讀書目是做學(xué)問的第一要訣,你要通過大量的閱讀書目和索引,慢慢梳理出自己的學(xué)問路徑,知道哪些書在哪里可以找到。老一代學(xué)人非常重視收集和閱讀書目。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我在上大學(xué)時反復(fù)讀,這種書要讀下來,會在心里形成一個學(xué)術(shù)的版圖。這個是受張之洞的影響,他的《書目答問》就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舉要性書目。做學(xué)問,就是要從這兒進入。
現(xiàn)在有了互聯(lián)網(wǎng)之后,大家似乎對書目、索引類的書不注意了,認為網(wǎng)上都有。但我遇到這類書,依然都買。因為互聯(lián)網(wǎng)的檢索系統(tǒng)和我們以前讀書目在大腦里形成的檢索系統(tǒng),那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自己腦子的學(xué)問地圖和可以檢索的學(xué)問地圖相比,還是有自己的檢索系統(tǒng)踏實。另外,史料書、年譜長編一類的書,我都是遇到就買,盡管有些暫時不做,我也會收集起來,非買不可。
還有日記,我是見一本買一本。日記只要讀的多了,才能體現(xiàn)出故事,單獨讀一本日記是沒意思的,只有在不同記錄的佐證下,日記的價值才越發(fā)呈現(xiàn)出來,可以從中類比出一些史料的真實性。比如《胡適日記》,寫得當(dāng)然是很真實,但是胡適有好多東西不寫,于是,需要借助別的日記來看到他不寫的那些東西。比如,胡適與曹誠英的故事,他自己日記里沒記,通過別人的日記,慢慢就勾勒出來了。這些就是日記對于學(xué)術(shù)研究的獨特功用。
解璽璋:以書會友,風(fēng)義長存
解老師家的客廳有一面墻,擺著整整齊齊一排靠墻的書架,里外兩層碼著書和文件盒,看起來很有年頭了。解老師說,住進這所房子已十幾年,現(xiàn)在這排書架上,包括有二十四史、歷代筆記和特別多的年譜,還有早些年買的很多線裝書。文件盒里收納的是各種名家書信、朋友書信、讀者來信和投稿,還有各種戲票、電影票、戲劇海報等。很敬佩解璽璋、李輝老師等前輩對歷史資料的留存手法和運用能力,這是他們成為學(xué)者型編輯的基本素養(yǎng)。
解璽璋老師最初的閱讀從中國古典文化開始,抄錄和閱讀了大量中國古代典籍、線裝書,另一方面,他的思想方法又深受馬恩影響,抄錄和模仿他們的筆記和格言。最終,他選擇中國近代人物傳記作為自己的研究和書寫方向。這種古今中西的貫通閱讀,為他的寫作提供了大格局的視野,而傳統(tǒng)的抄卡片式研究法又讓他回歸到書寫本身,整個書寫過程,不僅是最終呈現(xiàn)作品,還梳理和留存的大量史料和研究路徑,這是當(dāng)下稀缺的學(xué)問本質(zhì)。
走入解璽璋老師書房,可以看到一位讀書人在學(xué)問之途的孜孜耕耘,臨走時,他拿一張舊卡片,題簽“以書會友 風(fēng)義長存”送給我,這張卡片我一定會珍惜、留存。

方緒曉:您的閱讀和買書,可以從哪兒開始追溯?
解璽璋:我的讀書啟蒙應(yīng)該追溯到在北京第二化工廠時,我所在的車間是生產(chǎn)硅材料的,要求技術(shù)水準很高,下放來的高級知識分子特別多,我屬于車間里文化水平最低的。但我們廠很重視青年工人教育,給我們辦夜校。
車間的知識分子師傅們都愛看書,互相傳遞和交流著書籍。對我閱讀影響最大的是陸俊師傅,他是宣傳科的,來車間看我辦的黑板報還有點樣子,就有意培養(yǎng)我。我一開始背古詩、古文,都是他一句句教的。他自己沒上過大學(xué),但他父親是中國人民大學(xué)教授,有家學(xué)根底。
他老帶我去琉璃廠、隆福寺等舊書店,上世紀70年代初,清理出很多舊書,像樣一點的在架子上擺著,沒函套的都在地上堆著,像小山一樣,特便宜。陸俊師傅喜歡中國古典文化,受他影響,那時候我主要看中國古代的書籍,把王力的那套四卷本《古代漢語》好好學(xué)了一遍。我的古文功底基本就是在工廠那些年打下的。
方緒曉:這么講來,感覺您一路是讀古典過來的,應(yīng)該是走古典學(xué)術(shù)這一路,怎么后來轉(zhuǎn)向了近代史方面研究?
解璽璋:的確,在工廠時就對古典學(xué)術(shù)有了濃厚興趣,1977年恢復(fù)高考,我報的三個專業(yè)都是北大的,一是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yè),二是圖書館系,三是考古系,當(dāng)年北大要300分,我差幾分沒考上,也沒填服從分配,就沒上成。半年后,參加了78級考試,陸俊師傅建議我考人大新聞系,因為他父親就是人大教授,結(jié)果就被人大新聞系錄取了。
上了人大新聞系后,聽方漢奇教授講《中國新聞史》,講到梁啟超,就開始對梁啟超特別感興趣。我跑到北京圖書館的報庫,當(dāng)時在北新橋那邊國子監(jiān)對面有一個柏林寺里,就天天來看梁啟超辦的《時務(wù)報》《國聞周報》等。那時的原報沒人看過,全是灰,在那兒讀了一學(xué)期舊報,做了大量筆記,之后寫了一篇論文叫《梁啟超新聞思想初論》,正好學(xué)校舉辦學(xué)生論文競賽,我就交了,還得了二等獎。方漢奇先生看了論文,主動跟我說,你畢業(yè)論文就寫這個吧,沒人像你這樣把舊報紙一篇篇讀過的。
畢業(yè)后分配到《北京晚報》,在副刊做文藝評論,寫影評、劇評、大眾文化評論等,后來的讀書,基本圍繞著工作展開了,尤其是電影理論書、電影史方面的書。還有戲劇、文學(xué)、藝術(shù)理論等方面。
但對于梁啟超的興趣一直沒有間斷,也沒有停止過閱讀梁啟超。直到退休以后,有了充分的時間,才重新系統(tǒng)讀任公的書,一點點重拾我在不同時期對他的認識。寫梁啟超對我的研究之路特別重要,讓我更加系統(tǒng)、深刻地認識傳記寫作的難度和高度。近二十年來,我讀的最多的書就是《飲冰室合集》,碰到問題,總從這里找靈感、找答案。

方緒曉:您對傳記寫作有些什么樣的體會?這種研究方法大概有些什么特點?
解璽璋:現(xiàn)在很多傳記最大的問題是虛構(gòu)成分太多,材料不確實的太多。我寫傳記盡量做到都有出處,如果有多種出處和說法,也盡量都放進來,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清楚。對于材料的可靠性來說,我認為書信要比日記可靠,日記中虛構(gòu)、主觀的東西太多,比如說《胡適日記》,本身就是寫給后人看的。墓志銘相對比較可靠,因為要刻在墓碑上,但因為是當(dāng)時人寫的,也有一些問題,中國人死者為大,往往有很多夸大成分,溢美之詞偏多,在引用的時候,要注意其可靠性。
寫傳記是特別小心謹慎的活兒,除了對材料運用要細心分辨,在引用資料時也不能過度解釋,尤其不能用今天的立場來解釋當(dāng)時的文獻,盡量要回到當(dāng)時的環(huán)境去體察傳主的情況和感情,在寫作中,我時刻警惕自己,要跳出來,不能陷入對當(dāng)事人的情感當(dāng)中。
除了日記和書信,年譜對寫傳記特別重要,年譜的脈絡(luò)能讓傳主的形象特別清晰,寫作中,要時時考察年譜,再根據(jù)年譜中提到的時間和事件,尋找相關(guān)的材料,就能事半功倍。我對做年譜的人特別欽佩。我的書房里年譜書特別多,基本上看到年譜都買。
當(dāng)然,傳主本人的文集和所有文章,當(dāng)然必須得看。傳記的研究方法其實很簡單,就是閱讀和掌握盡可能全面的資料,根據(jù)不同資料比對,才能更客觀地呈現(xiàn)傳主的真實性。我的研究方法還是最傳統(tǒng)的“抄卡片法”,當(dāng)年在化二廠時,師傅給我印了很多很多卡片,現(xiàn)在還在用,有些書中可能只有一兩條相關(guān)資料,抄出來就特別方便,不用再一一去翻書。抄卡片的功夫做到家后,把卡片一排,大致的思路就出來了。
方緒曉:除了中國古典文化,以及剛才談到的傳記,在您的閱讀史中,還有哪些著作深刻地影響了您?
解璽璋:要說特別具體的影響,還有《馬恩選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對我的思想方法特別有影響。馬恩的書我看得特別仔細,做了大量的筆記,劃了很多重點,這些筆記我都還保留著。比如《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導(dǎo)言中的這句話:“哲學(xué)把無產(chǎn)階級當(dāng)做自己的物質(zhì)武器,同樣地,無產(chǎn)階級也把哲學(xué)當(dāng)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閃電一旦真正射入這塊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
還有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xué)的終結(jié)》,我特別喜歡,一遍遍地讀,記錄了很多很多金句,比如談歷史:“不論歷史的進程如何,人們總是這樣來創(chuàng)造歷史的:各人都在追求自己的、自覺抱定的目的,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行動的欲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發(fā)生的各種各樣的影響的總和,就是歷史。”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的話,有時候真的特別棒。當(dāng)年在工廠時,讀到這樣的句子,可以想象對我的震撼有多大。而馬恩書中,這樣精辟的話比比皆是,我都一句一句抄下來,隨時翻閱。當(dāng)時還特別愛模仿,模仿列寧的《哲學(xué)筆記》,我也做他那樣的筆記。各種顏色分區(qū),劃板塊,這樣的筆記就特別一目了然。這個辦法就是學(xué)的列寧。
我很感謝工廠那些年的讀書生活,那些看似傳統(tǒng)卻深刻影響我的讀書方法,如今在我的研究和寫作中依然發(fā)揮著重要作用。那些年抄的書,記的讀書筆記,也是我書房中最珍貴的史料。
(作者系文化學(xu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