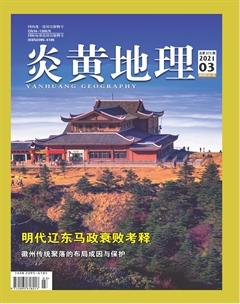山西聞喜縣博物館館藏《閑事碑》考釋
宋國民
《閑事碑》客觀反映了崇禎年間天災(zāi)人禍、匪患及民生狀況,作者還通過引用史料,對同一時期的全國各地的災(zāi)情進(jìn)行了對比,還原了明末社會動蕩,民不聊生的場景和社會真實狀況。加深了人們對中國歷史周期律的認(rèn)識。啟迪我們當(dāng)下要珍惜安定祥和的社會局面,加強(qiáng)糧食安全和社會治安管理,強(qiáng)化節(jié)糧意識,防患于未然,及時解決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各種矛盾、隱患,從而實現(xiàn)國家的長治久安。
明代崇禎年間天災(zāi)人禍不斷,人民遭受苦難,立碑告誡后人,要勤儉持家。
山西聞喜縣博物館收藏有一通《閑事碑》,原立于聞喜縣侯村。青石質(zhì),碑首呈半圓狀,額、身一體,高104厘米,寬55厘米,厚14厘米,碑額、碑身以兩陰線填刻云紋隔開,碑首正中豎刻“閑事碑”三字,左右各有兩道陰線圍成一豎匾狀,左右兩側(cè)分別刻“月”“日”二字在兩圓之中,“月”“日”兩字周圍有云紋烘托。碑身四周也裝飾有云紋。碑文12行,每行字?jǐn)?shù)不一,共約500字,書石字體工整,古拙厚重。碑文背面刻有崇禎六年九月創(chuàng)建關(guān)帝廟碑記,兩文同用一碑,說明當(dāng)時大災(zāi)剛過,天下初平,碑石短缺,民力尚艱,經(jīng)濟(jì)仍無恢復(fù)。
該碑刻立于清順治五年(1648年)四月,由邑庠生(縣學(xué)秀才)楊弘培撰文,楊俊士書石。楊弘培、楊俊士不見史載。
碑文全文如下:
太祖先帝不題。至崇禎年間,經(jīng)過兇歲,又遭亂變,著碑以曉后云。
崇禎四、五、六年,流寇犯亂,搶奪財物,殺擄男女,焚民房屋,不知其數(shù)。及七、八、九年,荒旱不收。八年又遭蝗蝻,田苗盡食。但見百姓草子食盡,榆皮食盡,游塵糟糠食盡。究至為母吃子,為子吃父,未能救民之生也。壯者走散于四方,老幼餓死于道路,人中之?dāng)?shù),十中去七。似此景象,百姓之疾苦,古來罕有。世間之餓莩,深可悲慘,人苦極矣,天否極矣!乃苦盡甘來,人事之必然;否極泰至,天公之定理。幸值九年,夏麥頗收,秋苗興盛,合時雨降。前此之死亡者不能復(fù)生,而存命者或有一線生氣矣,而民之悲懷至此作悅景矣。追憶兇歲,甚利害,亂變曾口口。先輩遭困苦,后輩要勤儉,凡我輩后睹此,當(dāng)謹(jǐn)防矣。故刻碑以曉后云。
崇禎十三年兇歲,麥價銀九錢一斗,口價九錢一斗,種時谷一錢一升。汾州茭草米七錢一斗,粳價七分一斗,游塵價五分一斗,蒺藜八分一斗。地中野草,羅馬兜兜,挖食凈盡。又遭狼蟲惡法,一群四十有余,將在地口茨藜口草人等,吃傷無數(shù)。
物件:麻油一錢八分一斤,豬肉一斤一錢八分,凈花一斤三錢,雞一只三錢,豬一口十兩,羊一只三兩。
邑庠生楊弘培撰
楊俊士書
順治五年四月立
碑文記載的內(nèi)容
碑文開宗明義首先說明了立碑的目的:“至崇禎年間經(jīng)過兇歲,又遭亂變,著碑以曉后云”,然后簡略記述了崇禎四、五、六年流寇犯亂,殺人越貨,民遭人禍,到崇禎七、八、九年,又遇天災(zāi),荒旱、蝗災(zāi)接踵而至,從而導(dǎo)致當(dāng)?shù)匕傩眨麟x失所,無糧可食,餓殍遍野,甚至出現(xiàn)父子母子相食的人間慘劇。最后作者劫后余生仍心有余悸,立碑告訴后人要勤儉節(jié)約,居安思危。碑文最后記錄了崇禎十三年又逢災(zāi)年,麥、谷、茭草米、野菜蒺藜、羅馬兜兜和豬、羊、雞肉、麻油的價格,及狼群出沒、傷害人畜的情況。
碑刻的時代背景
碑文描述的是崇禎年間聞喜一帶的天災(zāi)人禍,旱災(zāi)連年不斷,又遭蝗蟲肆虐,流寇作亂,百姓民不聊生,流離失所,父子母子相食,簡直是世界末日的人間煉獄。而這正是明末崇禎年間整個中國的縮影。崇禎年間,內(nèi)憂外患,內(nèi)部朝廷大臣黨爭加劇,財政匱竭,軍事軟弱無力,又有各地大規(guī)模農(nóng)民起義不斷爆發(fā),外有后金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的虎視耽耽,并不斷侵城掠地,騷擾百姓,明政府只能被動防守,加上崇禎年間正處于小冰河期的鼎盛期,破壞性大的自然災(zāi)害全國每年都有數(shù)次,至于小型災(zāi)害每月都有發(fā)生。明末崇禎一朝十七年間自然災(zāi)害頻頻發(fā)生,主要有旱、蝗、澇雹、震等幾種,其中旱、蝗、澇這三類自然災(zāi)害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危害最大。連年大災(zāi)使得崇禎時期頻鬧饑荒,持荒之久、波及之廣、災(zāi)害之重,為歷代所罕見,給社會政治經(jīng)濟(jì)生活帶來巨大影響,從崇禎元年(1628年)開始,地處黃土高原的陜北地區(qū)首先遭到大旱的襲擊,從此開始,大旱幾乎連年不斷,沒有絲毫收斂跡象,至崇禎十一年(1638年),旱情急劇擴(kuò)展,陜西、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等省頻傳旱情,競至赤地千里,川竭井涸,顆粒不收。崇禎十二年(1639年)旱災(zāi)開始由北向南迅速蔓延,一時之間遍及西北、華北、華東和中南地區(qū),范圍之廣,在中國歷史上實屬罕見。就在朝廷難以舉措之時,更為嚴(yán)重的旱災(zāi)又在崇禎十三年和十四年降臨,各省旱災(zāi)面積陡然大增,農(nóng)民顆粒無收。
甘肅旱災(zāi)成片,地裂干燥,荒野遍布,“人相食”的慘劇竟然不再聳人聽聞;陜西“絕糶罷市”,木皮石面皆食盡,人口十亡八九;山西“汾水漳河均竭,民多餓死”;河北“九河俱干,白洋淀涸,尸骸遍野”;河南“禾木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獸皮蟲蠅皆食盡,民餓死十之五六,流亡十之三四,地大荒”;江蘇、淮北大旱“黃河水涸,蝗蝻遍野,流亡載道”。另外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的旱情也日益嚴(yán)重。崇禎十五年,旱情仍較嚴(yán)重,掙扎在死亡線上的人民與日俱增。在旱災(zāi)肆虐的同時,大規(guī)模的澇災(zāi)也在明王朝賴以生存的江南財富集中區(qū)蔓延,將明王朝拖入更深的危機(jī)之中。隨著旱災(zāi)蝗災(zāi)接踵而至,蝗蟲大量孳生在旱年,旱災(zāi)和蝗災(zāi)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當(dāng)年蝗災(zāi)極其普遍,發(fā)生蝗災(zāi)遍及黃河以北地區(qū),且連年不斷,可以看出,崇禎年間水、旱、蝗三大自然災(zāi)害并發(fā),在空間上遍布南北,波及范圍廣,在時間上,年年有災(zāi),持續(xù)時間長,在受災(zāi)程度上,多災(zāi)并發(fā),民不聊生,山西人口由崇禎初年間的1024萬人下降至620萬人,陜西、山東死亡人口也在數(shù)百萬之上,如此嚴(yán)重的自然災(zāi)害使明政府陷入風(fēng)雨飄搖之中。全國糧食價格也通漲到史無前例的高度,人們兩手空空,沒有繳納賦稅的能力。人民生計艱難,而政府處境也非常糟糕,甚至沒能力支付軍餉,以維持邊防和驛遞。
民國七年版《聞喜縣志》記載:“崇禎四年,闖賊自西來,殺擄男婦甚眾;崇禎七年,土寇孫啟秀聚據(jù)中條,殺掠甚橫;崇禎八年乙亥大饑,人相食;崇禎十二年,乙卯七月蝗;十三年庚辰大饑,邑境斗米銀八錢,人相食,城中居民黃昏不敢獨出”。
該碑碑文與縣志史料相互印證,真實地反映了明代末年社會動蕩,天災(zāi)人禍,民不聊生的場景和社會現(xiàn)狀。
碑刻的歷史價值和啟示
碑刻記載了真實的歷史,目的是讓后人吸取教訓(xùn),免蹈覆轍,讀史明理,它給我們的啟示,一是要高度重視糧食安全,民以食為天,永遠(yuǎn)牢記農(nóng)為邦本,食為政首。盡管當(dāng)今人類的經(jīng)濟(jì)活動已高度非農(nóng)化,人們糧食之外的消費需求日趨增加,但糧食的不可替代性永遠(yuǎn)不會改變,農(nóng)業(yè)的基礎(chǔ)地位永遠(yuǎn)不會改變。二是大興勤儉節(jié)約之風(fēng),牢記先輩困苦教訓(xùn),樹立珍惜糧食,拒絕浪費的理念,一粥一飯當(dāng)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切實認(rèn)真踐行光盤行動。三是更加自覺地增強(qiáng)“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hù)”。只有這樣才能使們的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幸福,免受碑文中的人間慘禍。
在中國古代社會,個體小農(nóng)由于經(jīng)營的分散性和脆弱性,沒有能力從事大規(guī)模的防災(zāi)、抗災(zāi)活動。只有政府有能力集中人力、物力從事這項活動。明朝統(tǒng)治者也深知,與救荒相比,備荒是最為有效的災(zāi)荒救治方式,明朝歷代皇帝也重視備荒建設(shè),但“屢建屢廢”,尤其是在崇禎年間,內(nèi)憂外患,財政枯竭,國庫空虛,在天災(zāi)人禍面前,不僅沒有設(shè)法救濟(jì)安置災(zāi)民,而是繼續(xù)催逼稅賦錢糧,引發(fā)百姓大規(guī)模逃亡,成為“流寇”“盜匪”,致使農(nóng)民軍規(guī)模越來越大。因此,在碑文中,我們看到有關(guān)災(zāi)情、匪情、物價飛漲的記錄,但看不到地方政府的賑災(zāi)救濟(jì)災(zāi)民的記錄,說明當(dāng)時明政府角色缺失,國家功能嚴(yán)重喪失,地方官府已趨于癱瘓,沒有能力組織民眾抗災(zāi)救災(zāi),救災(zāi)民于水火,明王朝已陷入衰敗的惡性循環(huán)中。而正是如此,才加劇了災(zāi)禍的蔓延,最終導(dǎo)致明朝人亡政息。另外碑文中的物價記錄為我們研究明末崇禎年間社會經(jīng)濟(jì)和民生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
碑文作者希望后人記住先輩困苦教訓(xùn),勤儉持家。但作者囿于歷史局限,看不到造成這一慘劇發(fā)生的真正原因,是否明政府的腐敗無能和無所作為。另外作者也表達(dá)“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的無奈和沉重嘆息。
該碑雖名“閑事碑”,但碑文內(nèi)容沉重嚴(yán)肅,絕不可以閑事視之,距今雖已372年,但讀來仍使人振聾發(fā)聵,心有余悸,前事不忘,后事之師,讓我們記住先民困苦的同時,更要銘記造成災(zāi)禍的原因,以史為鑒,避免重蹈覆轍。
作者單位:山西省聞喜縣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