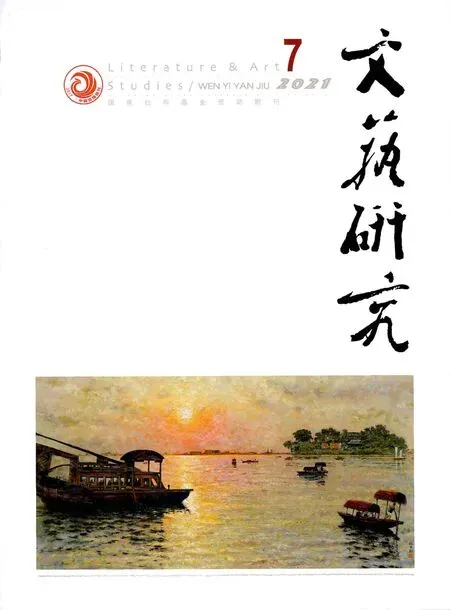湖邊的先祖:明刊《石湖志》圖繪的鄉(xiāng)族勢力與地緣策略
萬笑石
在現(xiàn)存歷代方志中,明弘治年間刊印的《石湖志》是較早重視圖像敘事功能的一部志書①。該書最初由莫震編纂,后由莫旦增修定稿并付梓于世。書中刻有一幅《莫氏慶壽圖》(圖1),展現(xiàn)了吳江縣莫氏家族為莫震賀壽的場景。圖中壽星端坐上首,身側(cè)榜題為“由庵,同知致仕,八十”。據(jù)《石湖志》記載:莫震,號由庵,官至延平府同知,六十二歲致仕里居②。結(jié)合榜題,可知《莫氏慶壽圖》描繪的是莫震八十大壽時的情形。
此次慶壽活動不僅繪有圖像,還記以文字,圖與文共同刊載于《石湖志》。據(jù)《石湖志》之“奉政大夫福建延平府同知致仕由庵先生莫公震”一條:
弘治戊申,壽登八十,而從弟邉雷壽亦如之,奉詔著仕服。從姪宏以訓(xùn)導(dǎo)致仕,年六十二,而旦亦年六十。誕日開宴,孫曾滿前,親友畢集,皆歆艷焉。③

圖1《石湖志》刊《莫氏慶壽圖》 明 木刻版畫版框23.4×13.6cm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作為當(dāng)?shù)氐墓倩率兰遥鸺捌浼易宓拇_令人“歆艷”。家族始祖本居湖州,自宋代徙居蘇州府吳江縣,仕宦者在宋代有廣德知軍莫子文,在明代有戶部左侍郎莫禮、延平府同知莫震、南京國子學(xué)正莫旦、湖廣安陸縣學(xué)訓(xùn)導(dǎo)莫宏、訓(xùn)導(dǎo)莫潛④。其中莫旦、莫宏和莫潛分別為莫震的子、侄、孫,三人都出現(xiàn)在《莫氏慶壽圖》中,各自榜題為“男旦,斈正”“姪宏,訓(xùn)導(dǎo)”“孫潛,生員”(此時莫潛尚未為官)。除卻幾位家族驕子,圖中還有多人前來祝壽,他們占據(jù)廳堂各個角落,甚至延伸至庭院,顯示出慶壽活動的盛大與隆重。
然而,《莫氏慶壽圖》所繪盛況與《石湖志》文本中的“親友畢集”有所不同。除了侍從,圖中成年男性皆以榜題標(biāo)注身份,可知都是莫氏家族成員,隨侍的女性和兒童亦應(yīng)同屬族中親眷。因此,《莫氏慶壽圖》沒有描繪任何參加壽宴的友人。為何《莫氏慶壽圖》與《石湖志》記載的文本存在出入?如何看待它在一部方志中的圖繪意義?從《莫氏慶壽圖》到《石湖志》其余插圖,本文將揭示莫氏家族如何借助圖像彰顯自身形象、社會地位與地方認(rèn)同感⑤。
一、作為家族群像的《莫氏慶壽圖》
需要承認(rèn)的是,《莫氏慶壽圖》與《石湖志》相關(guān)文本的大部分描述相符。圖中莫邉雷拱手坐在壽星莫震的下首,頭戴烏紗帽,身著官袍,榜題為“弟邉雷,壽官”。比較前文所引《石湖志》的慶壽文本,其首句稱“弘治戊申,(莫震——引者注)壽登八十,而從弟邉雷壽亦如之,奉詔著仕服”,說明莫邉雷和莫震同年出生,弘治元年莫震八十壽辰,恰好莫邉雷也年滿八十,并被天子賜予冠帶。因此《莫氏慶壽圖》中的莫邉雷和莫震一樣著官員冠服,榜題稱之為“壽官”⑥。
《石湖志》記載的“從姪宏以訓(xùn)導(dǎo)致仕,年六十二,而旦亦年六十”以及“誕日開宴,孫曾滿前”也被《莫氏慶壽圖》如實(shí)描繪。“從姪宏”指莫邉雷之子莫宏,他以湖廣安陸縣學(xué)訓(xùn)導(dǎo)致仕⑦。在《莫氏慶壽圖》中,莫宏手捧杯盞,身側(cè)題有“姪宏,訓(xùn)導(dǎo)”。文本中的“旦”即莫震長子莫旦,他和莫宏在圖中分侍于香幾左右。至于“誕日開宴,孫曾滿前”,《莫氏慶壽圖》將其描繪為廳堂右側(cè)莫震的孫子莫潛和廳堂左側(cè)的孩童(榜題“曾孫四人”)。
除將友人減省外,《莫氏慶壽圖》幾乎完整刻繪出《石湖志》關(guān)于莫震八十壽誕的文字內(nèi)容,并且還透露出許多文本未曾記錄的信息。該圖遵照禮節(jié),將家族成年男性分作三個層次,每層之間留有一定空間。第一層最為尊貴,即坐于廳堂上首的莫震與莫邉雷。除他們二人外,其他人或行或立,皆無座位。第二層靠近兩位長輩,可視作承上啟下的核心層,從左至右分別是莫震長子莫旦(“男旦,斈正”)、莫邉雷之子莫宏(“姪宏,訓(xùn)導(dǎo)”)、莫震仲子莫昊(“男昊,生員”)和莫震孫子莫潛(“孫潛,生員”)。第三層立于最外圍,分別為“曾孫四人”“姪孫,義官”“壻蔣康”“壻盛會”“壻陳晉”“壻盛早”“孫壻趙寬,刑部郎中”,可知他們是莫震的曾孫、侄孫、女婿與孫婿。顯然,這三層布局以壽星莫震為基準(zhǔn),將男性親眷按照輩分和親疏關(guān)系排序,體現(xiàn)出有意安排的位序邏輯。
如此看來,《莫氏慶壽圖》是有意略去參加宴會的友人,才造成圖、志(記載)不符的情況。省略外姓友人的做法意味著,這不是一幅旨在還原真實(shí)慶壽活動的插圖,而是具有家族倫理色彩的群體肖像畫。
值得注意的是,《莫氏慶壽圖》并非尋常的家族群像⑧,其中繪有多位女婿與孫婿——“壻蔣康”“壻盛會”“壻陳晉”“壻盛早”“孫壻趙寬,刑部郎中”。這些外姓親屬在圖中的位置意味深長。一方面,他們立于堂下,與廳堂內(nèi)的眾人保持一定分割性。另一方面,廳堂內(nèi)外的兩個群體依靠階上的莫震侄孫進(jìn)行連接,又形成一個更完善的家族結(jié)構(gòu)。為了遵循莫氏家族的內(nèi)部秩序,作為外姓人的女婿與孫婿似乎理應(yīng)處于圖中人群的最外層。然而,如果考慮到人物的社會身份,會發(fā)現(xiàn)這種位置安排強(qiáng)化了家族內(nèi)部與外部社會之間的張力。根據(jù)榜題,孫婿趙寬為刑部郎中,官居五品⑨,在整個畫面中品級最高。但他緊貼院墻,卻是莫氏家族群像中最邊緣的人物。此時,趙寬在社會上的政治權(quán)威讓位于他在莫氏家族的身份等級,因而在《莫氏慶壽圖》中無法獲得更重要的位置。趙寬的站位進(jìn)一步表明,《莫氏慶壽圖》注重表現(xiàn)家族內(nèi)部的世系次第。
這種價值偏向很難適用于家族之外更廣闊的社會空間,而《莫氏慶壽圖》提供了一個非常典型的宗族環(huán)境予以支持,使家族秩序更具合理性。圖中的廳堂匾額揭示出莫氏慶壽的地點(diǎn)——壽樸堂。據(jù)《石湖志》記載,壽樸堂始建于元代初年,創(chuàng)建者為莫震的曾祖莫諟,因堂前種有樸樹而得名⑩。這是莫氏家族最引以為傲的廳堂,圍繞壽樸堂留下不少名人翰墨與繪卷。例如明代沈周、吳寬等人曾為壽樸堂題詩著文,另有中書舍人詹希元手書“壽樸堂”匾?,以及傳為謝環(huán)繪制的《壽樸堂圖卷》(圖2)?。與《莫氏慶壽圖》不同的是,《壽樸堂圖卷》重點(diǎn)描繪樸樹,壽樸堂被簡化為一座茅亭。《莫氏慶壽圖》雖也將樸樹的盤根錯節(jié)和枝繁葉茂展露無遺,但更強(qiáng)調(diào)壽樸堂的體量:廳堂屋檐高于樸樹頂端,建筑占據(jù)更多畫面。《莫氏慶壽圖》通過重點(diǎn)描繪壽樸堂,表明這是一幅展現(xiàn)家族成員在家族重要空間舉辦盛大活動的圖像。
以上圖像細(xì)節(jié)說明,省略前來祝壽的友人并非無心之舉。畫家擇取真實(shí)事件的部分片段,以家族秩序作為組織畫面元素的內(nèi)在邏輯,將《莫氏慶壽圖》有意塑造為一幅莫氏家族群像。此種描繪方式有何深層意圖?這值得我們進(jìn)一步探求。

圖2(傳)謝環(huán) 《壽樸堂圖卷》(局部) 明 紙本水墨25×98cm四川博物院藏

圖3莫氏慶壽圖(局部)

圖4戴進(jìn)歸田祝壽圖(局部) 明絹本設(shè)色40×50.3cm故宮博物院藏

圖5陳洪綬祝壽圖(局部)明絹本設(shè)色129.1×53.2cm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圖6蕭云從《離騷圖》之“彭鏗斟雉,饗帝壽長”1645木刻版畫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二、為逝者慶生
為了探討《莫氏慶壽圖》的潛在意涵,需要分析圖中的核心層人員,即莫旦、莫宏、莫昊和莫潛。這四人不像其他人那樣拱手而立,吸引著畫面人物和畫外觀者的視線。莫旦與另三人相對,左袖攏在胸前,露出右手。莫宏、莫昊和莫潛則分別持有杯盞、執(zhí)壺和饌盤。由于莫昊手持細(xì)頸執(zhí)壺,可以判斷為酒壺,而莫宏托舉的是酒盞。莫宏的躬身幅度最大,手臂前伸,因而成為最具動態(tài)的人物。在以祝壽為主題的《莫氏慶壽圖》中,莫宏敬酒的動作也由此成為畫面焦點(diǎn)(圖3)。明代許多畫作都描繪了祝壽敬酒,可與《莫氏慶壽圖》的敬酒方式進(jìn)行對讀。以戴進(jìn)《歸田祝壽圖》(圖4)為例,辭官還鄉(xiāng)的端木智坐于廳堂,在他面前,一人執(zhí)細(xì)頸酒壺,一人奉酒盞。圖中的敬酒環(huán)節(jié)并未出現(xiàn)在圖卷前的壽序中,體現(xiàn)出畫家的個人構(gòu)思。此類現(xiàn)象在晚明也很常見。陳洪綬《祝壽圖》(圖5)僅題“楓溪陳洪綬寫壽”,并無他言,但有一名小女子手捧蓮花杯從直頸敞口壺中冒出,向一位男性祝壽敬酒。蕭云從《離騷圖》有“彭鏗斟雉,饗帝壽長”一圖(圖6),繪堯帝端坐、彭祖獻(xiàn)上雉羹,還有一名更靠近堯帝的女子,敬獻(xiàn)一件三足酒爵;不過圖后文字全然未提到敬酒祝壽,敬酒元素是由畫家主動增添。以上圖像與《莫氏慶壽圖》一樣,將未見于文本的敬酒環(huán)節(jié)作為畫面焦點(diǎn),但圖繪的敬酒方式卻有很大區(qū)別。《歸田祝壽圖》《祝壽圖》與《離騷圖》中的敬酒者距離壽星很近,因此敬酒對象明確指向畫面中的壽星——端木智、長髯男子和堯帝。反觀《莫氏慶壽圖》,莫宏距離坐在主位的莫震較遠(yuǎn),二人之間還隔著高腳香幾。莫宏的上半身和手臂朝向畫面左側(cè),面部和兩只腳尖則偏向廳堂左下角,似在朝著距他更近的莫旦行進(jìn)?。根據(jù)莫宏在圖中的身姿和位置,很難判定他是否在向壽星莫震舉杯敬酒。莫宏更像要將酒盞遞向莫旦,而莫旦露出右手,與莫宏形成呼應(yīng)。
事實(shí)上,若莫氏家族只選一名代表為莫震敬酒祝壽,莫旦才是合理人選,而非莫宏。論尊卑,莫宏雖屬家族中為數(shù)不多的官員,但他所擔(dān)任的安陸縣學(xué)訓(xùn)導(dǎo)為流外官,未入九品;而莫旦為南京國子學(xué)正,官居九品?。論親疏,莫宏是莫震從侄,而他身旁的莫旦是莫震長子,描繪敬酒時不應(yīng)舍直親而擇旁親。不論從圖中人物的姿勢位置、社會身份還是親疏關(guān)系看,都沒有莫旦旁觀莫宏向壽星敬酒的道理。
為了解釋《莫氏慶壽圖》的敬酒圖式,需了解常見于明代祝壽語境的禮儀概念——獻(xiàn)爵。獻(xiàn)爵即敬酒,爵代指酒器。前文所述《離騷圖》就將祝壽酒器繪作三足酒爵,不過該圖對獻(xiàn)爵的描繪流于表面,并未涉及具體儀節(jié)。明萬歷年間的《程氏墨苑》則表現(xiàn)得更為豐富,書中有一塊墨餅圖樣(圖7),一面繪三件三足爵,另一面篆書“父乙爵”三字。圖后附文《父乙爵將進(jìn)酒》,從內(nèi)容看,實(shí)為三段賀壽祝辭。《程氏墨苑》展現(xiàn)了如何在祝壽敬酒時借用最基本的獻(xiàn)爵儀節(jié)——三獻(xiàn)爵和三祝——即敬酒三次,每次獻(xiàn)一爵并配以一段賀壽祝辭。
《莫氏慶壽圖》雖未將祝壽酒器繪作三足爵,也未表現(xiàn)三獻(xiàn)爵與三祝,卻呈現(xiàn)出更復(fù)雜的獻(xiàn)爵意涵?。在官方禮典中,禮儀的執(zhí)行需要許多輔助角色,這類人被稱為執(zhí)事者。以明代品官祭祖為例,在獻(xiàn)爵前的進(jìn)饌環(huán)節(jié)就已需要多名執(zhí)事者托奉食盤;到了獻(xiàn)爵環(huán)節(jié),執(zhí)事者還承擔(dān)斟酒等準(zhǔn)備工作?。執(zhí)事者負(fù)責(zé)奉食、注酒、傳遞并擺放酒盞,確保繁復(fù)的儀式井然有序、莊嚴(yán)肅穆。《莫氏慶壽圖》中的持杯者莫宏、執(zhí)壺者莫昊和奉盤者莫潛,其角色可能類似于參與酌獻(xiàn)和進(jìn)饌的執(zhí)事者,而露出右手的莫旦更像準(zhǔn)備就緒的獻(xiàn)爵者。
考察莫旦、莫宏、莫昊和莫潛在圖中的方位,也與獻(xiàn)爵者和執(zhí)事者在祭祖時的站位相仿。壽樸堂應(yīng)為一座坐北朝南的廳堂,莫旦靠近廳堂南端的臺階,與北端的壽星莫震隔著一座高腳香幾,在他東側(cè)侍立著核心層的其余三人(圖8)。《大明集禮》刊繪的品官祭祖家廟圖也是類似布局(圖9)。該圖以階為界(“阼階”和“西階”),上下劃分出祠堂內(nèi)外兩個空間。獻(xiàn)爵者同時也是祭拜者,應(yīng)處于堂內(nèi)南端靠近階的“主人拜位”,與祠堂北端的先祖神位隔著一座香案。這幅家廟圖未標(biāo)明執(zhí)事者在獻(xiàn)爵時的位置,但堂內(nèi)東南角設(shè)有獻(xiàn)爵所需器物,包括“酒注”“盤盞”與“酒”。結(jié)合前文所述執(zhí)事者的角色,他們應(yīng)在祠堂東南角準(zhǔn)備獻(xiàn)爵物品,再走向獻(xiàn)爵者所處拜位,輔助酌獻(xiàn)。在莫震、堂內(nèi)香幾、莫旦和其他核心層人員之間連線,再以同樣方式處理上述家廟圖中的對應(yīng)人員和器具,會形成非常相似的三角形結(jié)構(gòu)。

圖7程大約 《程氏墨苑》之“父乙爵將進(jìn)酒” 明木刻版畫 版框24.3×15cm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9《大明集禮》之“家廟圖”1530木刻版畫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作者標(biāo)注)
再看莫旦和其他核心層人員的朝向,也類似于祭祖獻(xiàn)爵時的獻(xiàn)爵者和執(zhí)事者。《大明集禮·品官享家廟儀》之“酌獻(xiàn)”一條記錄了獻(xiàn)爵程序,由于祀主眾多而儀節(jié)基本相同,本文僅引用為高祖考妣獻(xiàn)爵的部分:
主祭奉高祖考盤盞,位前東向立,執(zhí)事者西向斟酒于盞,主祭奉之奠于故處。次奉高祖妣盤盞亦如之。奠訖,位前北向立。執(zhí)事者二人舉高祖考妣盤盞立于主祭之左右。主祭跪,執(zhí)事者亦跪。主祭受高祖考盤盞,右手取盞祭之茅上,以盤盞授執(zhí)事者反之故處。受高祖妣盤盞亦如之。?
首先,主祭即獻(xiàn)爵者面朝祠堂東側(cè),執(zhí)事者面朝西側(cè)為他斟酒。獻(xiàn)爵者再面向北側(cè)的神位,將酒盞奠于神位處。之后獻(xiàn)爵者保持北向立,執(zhí)事者取回酒盞,一同跪拜。獻(xiàn)爵者祭酒后,再由執(zhí)事者將酒盞放回神位。《莫氏慶壽圖》雖未描繪如此繁復(fù)的流程,但莫旦和莫宏等人分別符合獻(xiàn)爵者和執(zhí)事者在獻(xiàn)爵伊始時的朝向,莫旦和獻(xiàn)爵者一樣“東向立”,莫宏等人如“執(zhí)事者西向”。
倘若將《莫氏慶壽圖》的祝壽敬酒與祭祖獻(xiàn)爵相對應(yīng),就能比較合理地解釋莫宏持杯和友人消失等原因。手持酒盞的莫宏像在扮演一名執(zhí)事者,而莫震的長子莫旦才是真正向壽星敬酒的人,他露出右手,等待從莫宏手中接過酒盞。以祭祖獻(xiàn)爵的方式描繪祝壽敬酒,還可以解釋為何圖中官階最高的趙寬無法進(jìn)入廳堂。有學(xué)者研究,明代出嫁女子已加入夫宗,因此不得參與父宗的祭祖活動?。女兒與孫女尚且不能參加,遑論女婿與孫婿?《莫氏慶壽圖》將姻親置于堂外,又剔除外姓友人,可能也出于對祭祖儀式的模仿,以更貼合家禮的氛圍。
可是《莫氏慶壽圖》的題材是慶賀長輩高壽,何故借鑒已逝先祖的祭奠儀式?考察《石湖志》的成書過程,《莫氏慶壽圖》的刊印時間應(yīng)在莫震去世之后。莫震逝于八十壽誕的次年(1489)仲冬,而《石湖志》“科貢”一條記錄到弘治十二年,即1499年,這也是書中出現(xiàn)的最晚年份?。所以《石湖志》至少在莫震去世十年后才能成書,刊刻出版當(dāng)更晚。從這個角度看,《莫氏慶壽圖》是一幅為逝者慶生的圖像,融合了莫氏家族為莫震慶壽和祭奠的雙重意味。
三、作為《石湖志》插圖的《莫氏慶壽圖》
既然《莫氏慶壽圖》是一幅帶有家族私密性和祭祖色彩的版畫,那么如何看待它在《石湖志》中的圖像意義?這部志書的插圖集中在卷一,除了《莫氏慶壽圖》,還繪有御書“石湖”、山水、村落等公共空間以及先賢像贊(表1)。

表1《石湖志》插圖
如表中所示,《莫氏慶壽圖》是《石湖志》中唯一展現(xiàn)家族空間及家族活動的插圖。為何在地方志書中會刊印一幅家族圖像?這與《石湖志》的編撰性質(zhì)密切相關(guān)。《石湖志》由莫震及其長子莫旦編寫,是一部私撰志書,難免夾雜個人色彩?。在《石湖志》中,最具作者私人特質(zhì)的就是《莫氏慶壽圖》。究其初衷,應(yīng)是莫旦在增補(bǔ)先父遺著時,決定以父親為主角制作一幅隱含祭祀意味的家族群像,表達(dá)對《石湖志》最初的編纂者莫震的紀(jì)念與祭奠。
不過,《石湖志》的私撰屬性還不足以解釋《莫氏慶壽圖》作為《石湖志》插圖的存在意義。在圖像主題上,這幅家族群像和書中的多幅插圖存在一定共同之處,需要進(jìn)行整體解讀。
相較《莫氏慶壽圖》的委婉表達(dá),《石湖志》中還有三組插圖直接與祭祀莫震相關(guān),分別為《石湖鄉(xiāng)賢祠圖》(圖10)、十三幅先賢像贊中的莫震像贊(圖11)和《綺川亭圖》(圖12)。其中《石湖鄉(xiāng)賢祠圖》呈現(xiàn)比較完整的祠祀環(huán)境,繪有祠堂、園景以及前來游覽和祭拜的士紳。祠堂題匾為“石湖鄉(xiāng)賢祠”,堂內(nèi)設(shè)有香案,置一爐二瓶,為祭祀時典型的三供組合。案前供奉十三塊神主,最右為莫震——“大明進(jìn)士奉政大夫福建延平府同知致仕由庵先生莫公震”。考查眾神主位次和稱謂,俱與《石湖志》卷二“石湖鄉(xiāng)賢祠”以及卷四“鄉(xiāng)賢”所記相同?。值得注意的是,石湖鄉(xiāng)賢祠建于弘治七年?,祠堂內(nèi)供奉神主而非塑像。這順應(yīng)了當(dāng)時江浙地區(qū)鄉(xiāng)賢祠的革新風(fēng)潮?。


圖11《石湖志》刊《大明進(jìn)士延平府同知莫公像》

圖12《石湖志》刊《綺川亭圖》
對應(yīng)《石湖鄉(xiāng)賢祠圖》中的十三位名賢神主,《石湖志》還繪有十三幅先賢像贊。像贊的稱謂從簡,不如祠堂神主名稱完整,但勝在展現(xiàn)清晰的人物儀容。同《莫氏慶壽圖》中的形象一樣,莫震肖像亦身著官服(圖11)。其像贊列于眾多先賢最末,與他在石湖鄉(xiāng)賢祠和《石湖鄉(xiāng)賢祠圖》中的位序相同。他的贊辭由其孫婿趙寬撰寫,文末特別提到莫震受饗于鄉(xiāng)賢祠:“令終祠鄉(xiāng)賢而饗蒸嘗者也。”?不少學(xué)者指出,父祖入饗鄉(xiāng)賢祠是地方家族在本地權(quán)勢地位的重要體現(xiàn),能夠賦予家族“巨大的權(quán)威力量”?。因此,可以理解為何莫氏親眷對莫震入祀石湖鄉(xiāng)賢祠抱有強(qiáng)烈的自豪感。
而在莫震入祀石湖鄉(xiāng)賢祠的前一年,石湖地區(qū)已有另一座祠廟先行奉祀莫震,《石湖志》也繪有這座祠堂的圖像。可惜插圖已殘損,沒有任何神主和題匾信息,僅存右側(cè)對聯(lián)“潔祠宇而薦蘋葉,敬仰英靈之如在”,表明圖中建筑的祠堂屬性(圖12)。據(jù)《石湖志》卷二“祠祀”一欄,石湖地區(qū)僅記兩座祠堂,一為石湖鄉(xiāng)賢祠,另一座為綺川亭:
綺川亭,在莫舍村,范文穆公別墅之一也。洪武中里人莫芝翁建奉文穆及廣德知軍莫子文二位。久廢,弘治六年吳江金知縣洪重建,增奉文穆而下鄉(xiāng)賢共一十二人,有記刻石。?
綺川亭最初為宋代范成大的別墅之一,位于莫氏家族世代居住的莫舍村,故而莫舍村又名“綺川”?,莫氏家族亦稱“綺川莫氏”?。明洪武年間,綺川亭由莫震的曾祖莫諟(號“芝翁”)改建為祠堂,奉祀范成大與莫家先祖莫子文。弘治六年,吳江知縣金洪又增設(shè)十人,其中最后一位祀主為莫震?。由于《石湖志》僅錄石湖鄉(xiāng)賢祠和綺川亭兩座祠祀,書中殘缺的祠廟圖像應(yīng)為《綺川亭圖》。根據(jù)綺川亭的奉祀信息,《綺川亭圖》應(yīng)同《石湖鄉(xiāng)賢祠圖》一樣繪有莫震的神主,并且處于圖中眾多神主的最右端。
莫震以神主或像贊的形式出現(xiàn)在《石湖鄉(xiāng)賢祠圖》《綺川亭圖》和先賢像贊,為理解《莫氏慶壽圖》的圖像意義增添新的視角。《莫氏慶壽圖》中的莫震是慶壽事件的主角,他位于廳堂上首,左手扶腰帶,右手置膝上,以明代表現(xiàn)尊者的圖式化坐姿接受族人禮拜,儼然一幅家族領(lǐng)袖的模樣。而在《石湖鄉(xiāng)賢祠圖》《綺川亭圖》和先賢像贊中,莫震以國家官員和地方精英的面貌反復(fù)出現(xiàn),并與前代名賢共同享有被祭饗和瞻仰的權(quán)力,只是他作為最后入祠的地方鄉(xiāng)賢,其神主和肖像只能位列最末。在《石湖志》中,作為一族之長的莫震與作為地方先賢的莫震遙相呼應(yīng),這些莫震的形象連接起莫氏家族空間與地方祠祀空間,在家族內(nèi)部秩序與地方權(quán)力場域之間起到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因此,《石湖志》中的《莫氏慶壽圖》不僅僅是一幅獨(dú)立的家族群像,還與其他插圖構(gòu)成互文關(guān)系。憑借這些帶有祭祀色彩的圖像,《石湖志》呈現(xiàn)出綺川莫氏憑借逝去的先祖從家族走向地方的象征圖景。
四、湖邊的先祖
莫氏家族所走向的“地方”,主要涉及綺川和石湖兩個區(qū)域。石湖地區(qū)包含綺川,但二者并非簡單的從屬關(guān)系。從區(qū)劃屬性看,綺川即莫舍村,“屬范隅鄉(xiāng)一都八圖”?,受吳江縣范隅鄉(xiāng)管轄,更貼近行政區(qū)劃。石湖作為太湖支流,其本質(zhì)是自然地理空間,空間內(nèi)的聚落分布具有跨政區(qū)特征。據(jù)《石湖志》“總敘”之“石湖”一條:
北屬吳縣靈巖鄉(xiāng)界,南屬吳江縣范隅鄉(xiāng)界,蓋兩縣交會之間也。?
石湖北接吳縣,南接吳江縣,湖邊土地分屬異縣的兩個鄉(xiāng)域,位置關(guān)系可參考明正德元年刻《姑蘇志》之《本朝蘇州府境圖》(圖13)?。具體而言,石湖地區(qū)僅包括《石湖志》“鄉(xiāng)都”一欄所刊載的吳縣靈巖鄉(xiāng)一都和吳江縣范隅上鄉(xiāng)一都?。
《石湖志》“祠祀”一欄只記載了綺川亭和石湖鄉(xiāng)賢祠,便是出于石湖地區(qū)特殊的地理屬性。限于《石湖志》對鄉(xiāng)都范疇的界定,只有位于吳縣靈巖鄉(xiāng)一都和吳江縣范隅上鄉(xiāng)一都的祠祀才能入選這部志書,而兩縣之內(nèi)更具官方屬性的廟學(xué)鄉(xiāng)賢祠以及其他著名祠廟皆被排除在外。最終,只有吳縣的石湖鄉(xiāng)賢祠與吳江縣的綺川亭膺選其中。

圖13《姑蘇志》刊《本朝蘇州府境圖》(局部) 明木刻版畫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14《石湖志》刊《石湖山水圖》

圖15《吳江志》刊《石湖山水圖》1488木刻版畫[《中國方志叢書》,(臺灣)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
雖然《石湖志》所刊載的兩座祠祀分屬兩縣,莫氏家族卻在這兩處都占據(jù)明顯優(yōu)勢。石湖鄉(xiāng)賢祠中,13位“鄉(xiāng)賢”中僅有5名吳縣人,另8名為吳江縣人,吳江人中又以綺川人、尤其綺川莫氏為重;祠內(nèi)共有4名莫氏族人,占祠祀總?cè)藬?shù)近三分之一。而綺川亭的12位先賢中,只有范成大屬于寓居名賢,其余俱為綺川本土鄉(xiāng)賢,其中共有5位來自綺川莫氏,人數(shù)約為總?cè)藬?shù)的42%,幾乎獨(dú)占綺川亭半壁江山?。如前文所述,鄉(xiāng)賢祠是地方勢力競逐的權(quán)力場。單從這兩座鄉(xiāng)賢祠的入祀情況看,綺川莫氏實(shí)乃石湖地區(qū)首屈一指的著姓望族。
因此,作為莫氏私撰方志的《石湖志》十分注重石湖地區(qū)的祠祀圖像,尤其強(qiáng)調(diào)對石湖鄉(xiāng)賢祠的刻畫。除了《石湖鄉(xiāng)賢祠圖》和13位鄉(xiāng)賢像贊,書中的《石湖山水圖》(圖14)也與石湖鄉(xiāng)賢祠有關(guān),這座祠堂靠近畫面中央,成為石湖地區(qū)的核心地標(biāo)。參照莫旦早先編纂的另一部志書,可以進(jìn)一步證明莫氏家族對石湖鄉(xiāng)賢祠的重視。莫旦于弘治元年出版的《吳江志》已刊載過一幅《石湖山水圖》(圖15),此時尚未創(chuàng)設(shè)石湖鄉(xiāng)賢祠,圖像重點(diǎn)展現(xiàn)群山和湖水,通往石湖鄉(xiāng)賢祠的行春橋位于畫面右側(cè)靠近邊緣處。而在石湖鄉(xiāng)賢祠建立后,莫旦眼中的石湖景觀發(fā)生改變,他將行春橋和石湖先賢祠放在《石湖志》刊《石湖山水圖》的畫面中心。莫旦在刊刻《石湖志》時特意扭轉(zhuǎn)了石湖山水圖像的最初構(gòu)圖與觀看視角,以凸顯莫氏家族與石湖鄉(xiāng)賢祠在石湖地區(qū)的核心地位。
與石湖地區(qū)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綺川莫氏在吳江縣域的社會影響。仍以地方祠祀為例,除卻綺川亭,吳江縣內(nèi)的祠廟少有祭饗莫氏先祖的情況。據(jù)弘治元年《吳江志》,僅莫震的父親莫轅一人入祀?yún)墙h學(xué)鄉(xiāng)賢祠?。其時該祠共祀15人,明人有四,莫氏先祖能名列其中已十分難得。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族中再無人入祀本縣祠廟。直至明嘉靖年間,莫旦入祀?yún)墙h學(xué)鄉(xiāng)賢祠,但莫轅已不再受饗于此?。從祠祀情況看,綺川莫氏在吳江縣、綺川和石湖地區(qū)的地位差別太過懸殊,顯然莫氏家族在綺川和石湖更具盛名。這也說明莫氏家族勢力主要植根于縣級以下的基層社會,難以在本縣及更上層政區(qū)進(jìn)行拓展。
為了向外擴(kuò)大家族聲望,莫氏“另辟蹊徑”,秉持跨縣域的發(fā)展策略。至遲從莫震62歲致仕返鄉(xiāng)起,他已在有意識地塑造“石湖人”的地方身份。莫震先仿照古人蘭亭集會與香山九老會,組建石湖敘情會,又寫下《石湖敘情會詩序》:
予歸石湖,擇親友之賢而有禮者,相與結(jié)為敘情之會,每月會于一家……皆石湖人。?
為了更貼合“石湖人”身份,綺川莫氏必然要走出吳江縣,涉足吳縣地域。莫震生前游走于石湖地區(qū)的集會活動,逝后還進(jìn)入?yún)强h的石湖鄉(xiāng)賢祠,接受兩縣士庶祭拜。《石湖志》作為莫氏父子的私撰方志,不僅刻繪石湖地區(qū)重要景觀(御書碑、御書亭、石湖鄉(xiāng)賢祠),還圖繪出莫氏族人身處其間的蹤跡,將家族史融入石湖地區(qū)的地方史。通過聚會、入祠與修志,綺川莫氏從人物、空間、歷史三方面實(shí)現(xiàn)了家族的跨縣策略。
如此復(fù)雜的策略得以實(shí)現(xiàn),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南宋御書“石湖”碑提升了石湖一帶的地方認(rèn)同感與文化凝聚力。御書“石湖”二字為南宋孝宗手書并賜予范成大,范氏刻碑初置范村重奎堂,后世將其移至石湖湖畔,并設(shè)御碑亭?。《吳江志》與《石湖志》刊《石湖山水圖》均繪有御書亭,表明御書亭是不可或缺的石湖地標(biāo),《石湖志》刊圖更將御書亭放置在畫面核心處。不僅如此,除了祠祀圖像和《莫氏慶壽圖》,《石湖志》其余插圖皆與亭內(nèi)御書碑相關(guān)。《石湖志》卷一先繪《御書石湖》,展現(xiàn)御書形象;再繪《石湖山水圖》《范村圖》,分述此碑在明代與宋代的不同位置;隨后為《石湖鄉(xiāng)賢祠圖》《綺川亭圖》兩幅祠祀圖像;再次繪《宴集圖》《莫氏慶壽圖》,其中《宴集圖》的活動地點(diǎn)即御書亭,亭內(nèi)石碑刻有“皇帝御書”“石湖”字樣;最后為石湖鄉(xiāng)賢祠祀的名賢像贊。御書碑與御書亭是石湖地區(qū)獲取獨(dú)立文化身份的重要物證,理應(yīng)在《石湖志》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而據(jù)莫旦《石湖鄉(xiāng)賢祠記》,該祠的創(chuàng)建緣由便是吳縣縣令史俊發(fā)現(xiàn)御書碑、重修御碑亭,次年接任的知縣鄺璠仿照西湖鄉(xiāng)賢祠,于御書亭后立石湖鄉(xiāng)賢祠?。御書碑、亭與這座祠堂既有因果關(guān)系,在明代還同處一地,因此《石湖志》對御書碑、亭的詳細(xì)圖繪,也能彰顯石湖鄉(xiāng)賢祠的歷史與文化地位,表明莫氏先祖入祀的重大意義。
綺川莫氏得以實(shí)施跨縣策略的第二個重要因素,是綺川在吳江縣獨(dú)特的地理位置。已有學(xué)者注意到,吳江縣在三江五湖的割裂下顯得四散飄零?。單論綺川所在的范隅上鄉(xiāng)一都,就分散于水域各處。據(jù)《吳江志》:“莫舍村一名綺川,在一都,石湖西,橫山下,地接吳縣靈巖鄉(xiāng)界。”?該書又稱:“橫山去縣治西北三十里,在吳縣境內(nèi)……一支為陸墓山,則在吳江一都之地,吳江有山惟此而已。”?可知綺川位于吳江縣西北角,地處吳縣橫山支脈腳下(圖16)。結(jié)合《姑蘇志》刊《本朝蘇州府境圖》(圖13),綺川應(yīng)與吳縣接壤并位于石湖西南側(cè)的陸地;而吳江縣大部分轄區(qū)位于綺川東南方向,與綺川隔湖相望。綺川與毗鄰的吳縣更具地緣親近感,促使位于石湖地區(qū)西南部的綺川莫氏朝向西北部的吳縣發(fā)展家族勢力。

圖16綺川位置示意圖 《吳江志》刊《吳江縣疆域之圖》(作者標(biāo)注)

圖17《吳江志》刊《范文穆公綺川亭圖》

圖18壽樸堂、綺川亭與石湖鄉(xiāng)賢祠位置關(guān)系(作者標(biāo)注)
莫氏家族由南向北的發(fā)展策略,具體體現(xiàn)在與家族先祖密切相關(guān)的三處空間——壽樸堂、綺川亭和石湖鄉(xiāng)賢祠。如《石湖志》刊《石湖山水圖》所示,石湖鄉(xiāng)賢祠位于行春橋旁,同側(cè)還有姑蘇臺;結(jié)合前述《本朝蘇州府境圖》,行春橋在石湖北端,姑蘇臺在其西側(cè),所以石湖鄉(xiāng)賢祠應(yīng)位于石湖西北角。而壽樸堂和綺川亭位屬綺川,當(dāng)在石湖西南側(cè),二者均在石湖鄉(xiāng)賢祠以南。至于壽樸堂和綺川亭的相對位置關(guān)系,可綜合《本朝蘇州府境圖》和《吳江志》刊《范文穆公綺川亭圖》(圖17)加以分析。《范文穆公綺川亭圖》同時描繪了壽樸堂和綺川亭,其中“壽樸”位于畫面左側(cè)岸邊,“綺川亭”在右側(cè)臨湖處,水面上題有“石湖”,后方群山標(biāo)有“上方”。據(jù)《本朝蘇州府境圖》,上方山位于石湖西岸,故而《范文穆公綺川亭圖》的視角大致為由東向西,畫面右側(cè)的綺川亭相對靠北,左側(cè)壽樸堂則位于綺川亭的南面。綜合三座建筑的地理方位會發(fā)現(xiàn),它們皆坐落于石湖西側(cè),最南端為壽樸堂,其北側(cè)為綺川亭,再向北是石湖鄉(xiāng)賢祠(圖18)。因此,莫氏家族的跨縣策略不僅符合社會學(xué)意義上的發(fā)展路徑,從家族(壽樸堂)、村落(綺川亭)步入石湖這一更廣闊的地域空間(石湖鄉(xiāng)賢祠),還具有明確的地緣指向性。綺川莫氏憑借對逝去先祖的祭奠,順沿石湖西岸的壽樸堂、綺川亭與石湖鄉(xiāng)賢祠,開拓出由南向北的跨縣征途。
結(jié) 語
本文以《石湖志》刊《莫氏慶壽圖》為研究起點(diǎn),發(fā)現(xiàn)該圖有意脫離對真實(shí)事件的忠實(shí)再現(xiàn),將慶壽圖轉(zhuǎn)化為一幅具有隱喻性質(zhì)的家族肖像畫。該圖以祝壽敬酒作為圖像敘事的核心線索,借助明代禮儀知識組織畫面,使作品暗含莫氏族人祭祀莫震的禮儀意味,從而融合了慶生與祭奠的雙重意涵。這幅帶有祭祀色彩的家族群像還拓展了肖像畫的功能,與《石湖志》其余插圖共同展現(xiàn)出莫氏家族的勢力發(fā)展策略:先在縣級以下的基層社會構(gòu)建自身地位,再通過跨政區(qū)的方式排除吳江縣范隅鄉(xiāng)以外的本縣勢力,憑借石湖地區(qū)的歷史文化資源引入?yún)强h士紳的地方認(rèn)同,最終實(shí)現(xiàn)提振家族聲譽(yù)、擴(kuò)大家族影響力的目標(biāo)。
作為一部私撰方志,《石湖志》通過刊載與莫氏家族相關(guān)的版畫插圖,在地方史書寫中串聯(lián)起一部莫氏家族史。受限于方志的敘述框架,《石湖志》中有關(guān)莫氏家族的文字信息散落于書中各處,難以自成體系。圖像為這部依附于地方史的家族史賦予更清晰而流暢的表述邏輯,出現(xiàn)莫氏族人形象的多幅插圖置于卷首,不僅互為勾連,還充當(dāng)閱讀指南的角色,提示讀者在瀏覽《石湖志》時重點(diǎn)留意哪些文本,而這些文本都將指向活躍在石湖的一個特定家族。就此而言,《石湖志》所刊繪的圖像比文本更有利于莫氏家族彰顯自身在石湖地區(qū)的鄉(xiāng)族勢力?。
值得注意的是,出版于弘治十二年之后的《石湖志》恰逢16世紀(jì)“地方主義轉(zhuǎn)向”(localist turn)浪潮?。為了加強(qiáng)地方社會內(nèi)部的關(guān)系紐帶,地方人士熱衷于撰寫方志,莫震與莫旦父子也身處其中。先后出版的《吳江志》與《石湖志》,圖文并茂地展現(xiàn)出莫氏家族在表達(dá)地方認(rèn)同時的兩個不同維度——前者以政區(qū)(府縣)為敘述框架,后者卻著眼于地理范圍更小(鄉(xiāng)都)且跨政區(qū)的地方社會。已有學(xué)者指出,地方認(rèn)同可以同時在多個規(guī)模層級的“地方”上生成?,而且應(yīng)突破以行政單位為基礎(chǔ)的研究架構(gòu)?。《石湖志》的撰寫與刊刻為超越行政區(qū)劃的地方認(rèn)同感提供了實(shí)例,而《莫氏慶壽圖》《石湖鄉(xiāng)賢祠圖》等版畫作品的圖像內(nèi)涵,只有放在多元化的地方認(rèn)同中才能獲得更好的理解。
① 關(guān)于歷代方志所刊插圖概況,參見陳光貽:《中國方志學(xué)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3頁。
② 莫震撰,莫旦增補(bǔ):《石湖志》卷四,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本,第16頁。
③ 《石湖志》卷四,第17頁。
④ 《石湖志》卷三,第2、8—10頁;《石湖志》卷四,第3—17頁。關(guān)于族中其余仕宦者,參見朱紅:《蘇臺煙云石湖月》,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170頁。
⑤ 地方認(rèn)同指個人或群體與地方互動從而實(shí)現(xiàn)社會化,通過這一社會化過程來建構(gòu)共享的身份認(rèn)同(朱竑、劉博:《地方感、地方依戀與地方認(rèn)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啟示》,《華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2011年第1期)。
⑥ 壽官是明代官方對于授予冠帶之耆老的頭銜(邱仲麟:《耆年冠帶——關(guān)于明代“壽官”的考察》,《臺大歷史學(xué)報》2000年第26期)。
⑦ 《石湖志》卷五,第2頁。
⑧ 關(guān)于家族群像一般形態(tài)的研究,參見吳燦:《明清祖宗像研究》,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2019年版,第79—151頁;吳衛(wèi)鳴:《明清祖先像圖式研究》,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20年版,第14—15頁。
⑨ 明代職官品級,參見陳茂同編:《中國歷代職官沿革史》,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435頁。
⑩? 《石湖志》卷三,第2—3頁,第2頁。
? 詩文有沈周《莫氏壽樸堂(成化甲午)》與王行《壽樸堂記》[沈周:《沈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頁;王行:《半軒集》卷四,永瑢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31冊,(臺灣)商務(wù)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20—21頁]。題匾信息見《石湖志》卷三(第2—3頁)。
? 徐邦達(dá)等學(xué)者將之命名為《壽樸堂圖卷》,認(rèn)為該畫時代為明初,引首與題跋皆真。據(jù)《平生壯觀》記載,明代宮廷畫家謝環(huán)曾繪《壽樸圖》,該圖引首、圖像和題跋與四川博物院藏《壽樸堂圖卷》相符。不過尚無法確定存世《壽樸堂圖卷》是否為謝環(huán)所繪(徐邦達(dá):《古書畫偽訛考辨》第3冊,故宮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206頁;劉九庵:《吳門畫家之別號圖鑒別舉例》,故宮博物院編:《吳門畫派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頁)。
? 需要指出,面部朝向只能作為參考,因《莫氏慶壽圖》是一幅家族群像,無論莫宏的行進(jìn)方向如何,可能都會露出完整五官。
? 陳茂同編:《中國歷代職官沿革史》,第435頁。
? 明代的獻(xiàn)爵儀式可用常制酒具,“爵匏皆以今酒器代之”(徐一夔等:《大明集禮》,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九年內(nèi)府刊本,卷二五,第52—53頁;卷二六,第43頁;卷二七,第26、52頁;卷二八,第14頁)。
?? 《大明集禮》卷六,第23—24頁,第24—25頁。
?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16頁;滋賀秀三:《中國家族法原理》,張建國、李力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頁。
? 《石湖志》卷三,第10頁;《石湖志》卷四,第16—17頁。今存《石湖志》為弘治本的觀點(diǎn),參見周越然:《言言齋古籍叢談》,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0頁。
? 明代私撰方志蔚然成風(fēng),私撰志書數(shù)量激增、種類駁雜,名稱也比較多樣,除后綴“志”字的情況,還有稱“記”“考”“錄”“略”“典”等(劉道勝:《徽州舊志研究》,安徽師范大學(xué)2003年碩士論文,第18—20頁;劉少華:《明清時期山東私修方志述論》,《中國地方志》2011年第6期;王同策:《方志與地方學(xué)研究》,廣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等編:《2014年廣州學(xué)與城市學(xué)地方學(xué)學(xué)術(shù)報告會論文集》,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2—294頁)。
? 《石湖志》卷二,第13頁;《石湖志》卷四,第16頁。
?????? 《石湖志》卷二,第13頁,第13頁,第8頁,第8頁,第1頁,第2頁。
? 明代中前期,江浙各地區(qū)的鄉(xiāng)賢祭祀形象受到孔廟改革影響,“易木主”“正謬俗”(張會會:《明代的鄉(xiāng)賢祭祀與鄉(xiāng)賢書寫——以江浙地區(qū)為中心》,東北師范大學(xué)2015年博士論文,第98—99頁)。
? 《石湖志》卷一,第21頁。
? 魏峰:《從先賢祠到鄉(xiāng)賢祠——從先賢祭祀看宋明地方認(rèn)同》,《浙江社會科學(xué)》2008年第9期。
? 《石湖志》列有《綺川莫氏族譜》(《石湖志》卷五,第13頁)。
? 綺川亭所祀12人,參見《石湖志》卷二,第13頁。
? 王鏊撰:《姑蘇志》,卷首插圖,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 可結(jié)合《石湖志》記載的祀主名目與各人籍貫進(jìn)行總結(jié)。考《石湖志》卷二“綺川亭”一條所列鄉(xiāng)賢姓氏,皆為明代初期莫舍村大姓:“莫舍村……其南村張氏,中村李氏,竹堂薛氏,蛻窩朱氏,俱國初大家也。”(《石湖志》卷二,第8—9、13—14頁)
? 莫旦:《(弘治)吳江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446號,(臺灣)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35—355頁。
? 曹一麟修:《(嘉靖)吳江縣志》,《中國史學(xué)叢書三編》,(臺灣)學(xué)生書局1987年版,第624頁。
? 陳奧荀纟襄、丁元正修,倪師孟、沈彤纂:《(乾隆)吳江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20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頁。
? 陳暐:《吳中金石新編》,王稼句選輯:《吳中文存》上,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57頁。
? 獨(dú)特的地理面貌引發(fā)了江南地區(qū)十分獨(dú)特的“吳江”問題,參見謝湜:《高鄉(xiāng)與低鄉(xiāng):11—16世紀(jì)江南區(qū)域歷史地理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版,第310—313、399—400頁;趙世瑜:《江南“低鄉(xiāng)”究竟有何不同?——〈垂虹問俗〉讀后》,《面目可憎:趙世瑜學(xué)術(shù)評論選》,商務(wù)印書館2019年版,第92頁。
?? 莫旦:《(弘治)吳江志》,第80頁,第83頁。
? 所謂“鄉(xiāng)族”并非僅限于鄉(xiāng)一級的地域,而是凸顯以往“宗族”概念所忽略的地域要素;相較于“宗族”,“鄉(xiāng)族”更強(qiáng)調(diào)血緣與地緣的結(jié)合,二者缺一不可(傅衣凌:《論鄉(xiāng)族勢力對于中國封建經(jīng)濟(jì)的干涉——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遲滯的一個探索》,《廈門大學(xué)學(xué)報》1961年第3期;森正夫:《圍繞“鄉(xiāng)族”問題——在廈門大學(xué)共同研究會上的討論報告》,成之平譯,曾仁壽校,《中國社會經(jīng)濟(jì)史研究》1986年第2期;鄭振滿等整理:《森正夫與傅衣凌、楊國楨先生論明清地主、農(nóng)民土地權(quán)利與地方社會》,《中國社會經(jīng)濟(jì)史研究》2009年第1期)。
? 包弼德(Peter K.Bol)指出,16世紀(jì)存在一種“地方主義轉(zhuǎn)向”,與明朝建立初期的國家主義形成對比。由于地方主義意識的興起,地方上的個人與團(tuán)體掌握更多的權(quán)力與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國家對地方社會的控制[Peter K.Bol,“The‘Localist Turn’and‘Local Identity’in Later Imperial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Vol.24,No.2(2003):1-50]。
?Yongtao Du,“A Local Identity Breakdown:Locality and the State in Huizhou’s Tax Controversy of 1577”,Ming Studies,Issue 81(2020):3-27.
? 楊國楨曾指出,地域共同體未必與行政區(qū)劃一致,存在跨政區(qū)現(xiàn)象(《森正夫與傅衣凌、楊國楨先生論明清地主、農(nóng)民土地權(quán)利與地方社會》)。關(guān)于跨政區(qū)現(xiàn)象的研究,參見學(xué)者對烏青鎮(zhèn)的分析(陳學(xué)文:《明清時期江南巨鎮(zhèn)烏青鎮(zhèn)的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中國經(jīng)濟(jì)史研究》1988年第2期;潘高升:《明清以來江南鄉(xiāng)鎮(zhèn)志編修與地方認(rèn)同——以〈烏青鎮(zhèn)志〉為例》,《江蘇地方志》2013年第6期;王旭:《宋代跨界市鎮(zhèn)——烏、青鎮(zhèn)關(guān)系考》,《中國社會經(jīng)濟(jì)史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