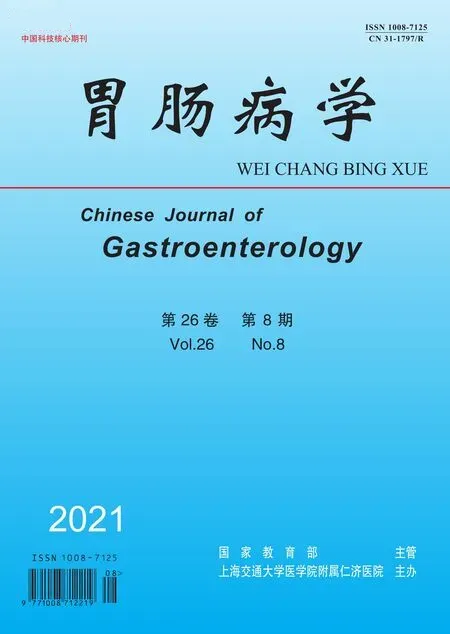NGAL在炎癥性腸病中的研究進展*
陳文軒 耿 麗 王丹丹 張目涵 張 哲 馮百歲
鄭州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消化內科(450014)
炎癥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是一種慢性復發性胃腸道炎癥性疾病,包括克羅恩病(Crohn’s disease, CD)和潰瘍性結腸炎(ulcerative colitis, UC),主要以反復發作的便血、腹痛和腹瀉等為臨床表現。目前IBD的發病機制并不完全明確,主要與環境因素、遺傳易感性、腸道微生物的穩態失調以及自身免疫功能紊亂有關。研究發現,急性期反應蛋白在IBD中急劇增高,其中中性粒細胞明膠酶相關脂質運載蛋白(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 NGAL)在中性粒細胞和腸上皮細胞中表達明顯增加,并通過其特殊的分子模式與不同的受體結合,在維持腸上皮細胞屏障和協調腸道菌群構成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此外,NGAL在IBD免疫調節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具有作為IBD臨床生物學標志物的潛能。本文就NGAL在IBD中的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一、NGAL的生物學特性
1. NGAL的基因定位:NGAL又稱脂質運載蛋白-2、噬鐵蛋白、24p3[1],是由178個氨基酸殘基構成的小分子糖蛋白。通過對NGAL基因的測序和克隆發現,其編碼區位于9號染色體上,是由3 696個堿基對組成的LCN-2基因編碼區[2],包括7個外顯子和6個內含子以及一系列啟動子,如核因子-κB(NF-κB)和CCAAT增強子結合蛋白(C/EBP)、糖皮質激素反應元件、維甲酸反應元件、雌激素反應元件等多個轉錄因子結合位點和核受體反應元件[3]。
2. NGAL的合成:NGAL于中性粒細胞中首次被發現,是中性粒細胞次級顆粒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已證實NGAL存在于內皮細胞、腎臟、胃腸道上皮細胞、平滑肌細胞、神經元和各種免疫細胞中,如巨噬細胞和樹突細胞[4]。目前已證實多種細胞因子在IBD的發病機制中發揮重要作用[5]。白細胞介素(IL)-17和IL-22可協同誘導腸上皮細胞內NGAL基因轉錄[6]。此外,IL-1β、IL-6、IL-10以及Toll樣受體(TLR)配體可通過激活NF-κB/STAT3途徑,促進NGAL的生成[7]。有研究表明,IBD患者中性粒細胞和腸上皮細胞中NGAL生成明顯增多[8]。
3.NGAL的形態結構及其受體:NGAL屬于載脂蛋白超家族,具有高度保守的三級桶狀結構,提供了一個疏水腔來結合各種親脂配體,包括維甲酸、孕酮、前列腺素、脂肪酸、類固醇、白三烯B4和血小板激活因子[1]。有研究表明,NGAL在機體以單體、同型二聚體以及與明膠酶基質金屬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MMP-9)共價結合形成大小為135 kDa(1 Da=0.992 1 u)的異二聚體三種形式存在[9]。NGAL有兩種不同的細胞表面受體,即溶質載體家族22成員17(solute carrier family 22 member 17, SLC22A17),又稱24p3R或NGALR2,以及低密度脂蛋白受體相關蛋白2(low 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related protein 2, LRP2),又稱Megalin。高水平24p3R在特異性細胞如巨噬細胞、中性粒細胞、肺和腸上皮細胞中表達,Megalin是一種多配體內吞噬受體,在某些類型的吸收性上皮細胞如甲狀腺細胞中高表達[10]。
二、NGAL在IBD中的研究進展
IBD是一種腸黏膜異常免疫反應、腸上皮細胞屏障減弱以及腸道菌群結構紊亂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胃腸道疾病。在小鼠和人類的結腸炎組織中,腸上皮細胞是產生NGAL的主要細胞,NGAL可獨立調節導致腸道功能紊亂的各個元素[11],包括同時對擾亂腸道菌群的抑菌作用、對損傷腸道屏障的修復作用,在免疫調控方面也發揮促炎/抗炎等雙重作用。有研究[12]認為NGAL可作為IBD的炎性標志物。
1.NGAL促進IBD患者腸道微生物穩態平衡:人體腸道內微生物數量約為1.0×1014個,種類超過1 000種,包括細菌、病毒、真菌等,與宿主形成了一個相互依賴又相互作用的微生態系統[13]。研究發現,IBD患者的共生菌與潛在致病性微生物之間存在動態失衡,如致病性大腸埃希菌增多、有益菌乳桿菌減少[14]。鐵對多種細菌生長至關重要,NGAL通過螯合鐵載體結合的鐵,抑制多種細菌的生長[15]。有研究發現,腸上皮細胞中NGAL通過與大腸埃希菌分泌的鐵結合蛋白Ent結合,形成NGAL-Ent-鐵復合物,抑制大腸埃希菌的增殖[16];過表達NGAL和外源性重組NGAL均能抑制巨噬細胞內分枝桿菌的生長,NGAL缺乏會促進受感染上皮內分枝桿菌的增殖,促進炎癥的發生。乳桿菌等一些有益菌群可產生短鏈脂肪酸、色氨酸及其衍生物、膽汁酸等,在維持IBD腸黏膜屏障中發揮重要作用。乳桿菌的增殖并不需要鐵,而通過基因修飾產生分泌NGAL的乳桿菌,提高了其在極端pH值、高濃度膽汁酸、氧化環境等極端狀態下的存活力[17],并明顯抑制大腸埃希菌的生長、降低腸桿菌素的活性。總之,NGAL在維持腸道微生物群穩態中發揮重要作用。
2. NGAL維持腸上皮細胞屏障完整性:腸上皮細胞在維持腸道屏障功能和預防腸道炎癥中起有重要作用,IBD患者腸上皮細胞和相關黏膜屏障存在明顯損傷[18]。NGAL與含鐵的疏水小分子鐵載體結合,將鐵載體轉運至上皮細胞內,激活胞質鐵依賴途徑,促進上皮細胞成熟。低氧誘導因子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作為上皮細胞穩定因子,可促進多種傷口愈合相關蛋白如黏附蛋白等基因的上調[19]。NGAL通過促進HIF-1α的生成,進一步增強三葉因子3(trefoil factor 3, TFF3)在上皮細胞的表達,增強腸上皮屏障保護功能。此外,NGAL可促進抗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血紅素加氧酶)的表達顯著上調,減少氧化應激對上皮細胞的損傷。一項體外研究[11]發現,NGAL對H2O2導致的上皮細胞毒性具有保護作用,而給予重組NGAL可促進損傷的單層結腸上皮細胞遷移,重建上皮細胞完整性。另有研究發現,NGAL可促進中性粒細胞向炎癥部位的遷移,在促進腸道炎癥發生的同時,促進上皮細胞雙向調節蛋白的產生,維持腸道屏障功能和增強組織修復功能[20]。由此可見,NGAL可保護機體免受氧化應激損傷,在維持腸上皮細胞功能中發揮重要作用。
3.NGAL在IBD腸道免疫中的抗炎/促炎機制:腸道免疫系統協調機制是一個復雜的生物過程,通過消滅入侵的微生物,保護宿主免受感染。NGAL主要通過其鐵螯合劑的功能在免疫系統中發揮重要作用[21]。IBD患者胃腸道存在異常的黏膜免疫調節,NGAL通過招募炎癥細胞(如中性粒細胞)和誘導促炎細胞因子,促進炎癥反應的發生。有研究發現,NGAL可通過誘導趨化因子受體2(chemokine receptors 2,CXCR2)和肝巨噬細胞分泌的巨噬細胞炎性蛋白2(macrophage inflammatory protein-2,MIP-2)與單核細胞化學引誘物蛋白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結合,促進中性粒細胞、巨噬細胞向炎癥部位的遷移[22],加重腸道炎癥反應。此外,在NGAL缺乏小鼠中,促炎細胞因子(IL-6、IL-8、TNF-α)、趨化因子(MIP-2和MCP-1)和抗炎因子(IL-10)等細胞因子的產生減少,下調多種細胞因子的mRNA水平[23],間接說明NGAL在調節機體多種細胞因子中發揮重要作用。
目前多認為NGAL參與腸道異常免疫反應的發生,但有研究發現NGAL通過與細菌衍生的鐵載體Ent結合,可防止髓過氧化物酶(myeloperoxidase, MPO)的失活,并進一步增強腸道中性粒細胞的抗菌功能[24],減輕腸道炎癥。自噬是一種機體對各種應激的自我保護反應,在緩解過度激活的炎癥和增強機體自我防御中發揮重要作用[25],自噬相關基因ATG16L1和IRGM的編碼突變增加了IBD的患病率。有研究[26]發現,與對照組相比,在NGAL/IL-10雙敲除的巨噬細胞中,自噬蛋白LC3-Ⅱ的形成明顯減少,而植入分泌NGAL的巨噬細胞后,可增加LC3-Ⅱ的生成,減輕腸道炎癥。由此可見,NGAL在調節機體促炎/抗炎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具體的作用機制仍有待進一步明確。
三、NGAL與IBD臨床檢測
NGAL為診斷急性腎損傷的生化金標準[27],其作為一種診斷性生物學標志物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有研究指出,在DSS誘導的結腸炎、沙門菌誘導的腸胃炎,以及TLR5敲除的自發性結腸炎小鼠中,NGAL水平均明顯增加[1]。Chassaing等[28]的研究證實NGAL為小鼠模型結腸炎的敏感生物學標志物。與健康對照組相比,編碼NGAL的基因LCN2是UC或CD患者結腸活檢中最常見的基因之一[29]。在IBD疾病活動期,NGAL在結腸組織、血清、尿液、糞便中均明顯升高,其濃度與臨床活動性和內鏡下病變活動性具有明顯相關性[30]。此外,NGAL在不同的生物液體包括膽汁、支氣管肺泡灌洗液、胸水、腹水和腦脊液[31]中可檢測到。
目前臨床上常用于檢測IBD的生物學標志物主要為鈣衛蛋白和乳鐵蛋白。一項對鈣衛蛋白和乳鐵蛋白評估IBD黏膜愈合敏感性和特異性的總結研究[32]發現,不同研究間糞鈣衛蛋白和乳鐵蛋白與內鏡下疾病活動性關系的結果不一致。而NGAL除在中性粒細胞中表達外,還可見于小鼠和人類炎癥性結腸組織中,腸上皮細胞是產生NGAL的主要場所。NGAL較鈣衛蛋白更能反映當中性粒細胞浸潤較少時腸道炎癥緩解的狀態[33]。且機體NGAL水平不受運動或飲食等干預類型以及BMI變化的影響,并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受運動或飲食調節的影響[34],這也為其成為IBD生物學標志物提供了條件。更有學者認為NGAL可與已建立的生物學標志物鈣衛蛋白相媲美[8]。
四、展望
綜上所述,NGAL在維持腸上皮細胞屏障和調節腸道菌群的組成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為采用基因修飾技術提高益生菌在治療腸道炎癥方面提供新思路,其本身的特性也展現了作為IBD臨床生物學標志物的潛能。此外,NGAL相關受體在小膠質細胞、神經元以及甲狀腺細胞等中表達,可進一步探索NGAL在IBD患者焦慮抑郁以及明顯消瘦中的作用。但由于NGAL具體作用機制存在諸多不同的觀點,仍需進一步研究深化NGAL在基因分子水平上的認識,促進NGAL在IBD治療中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