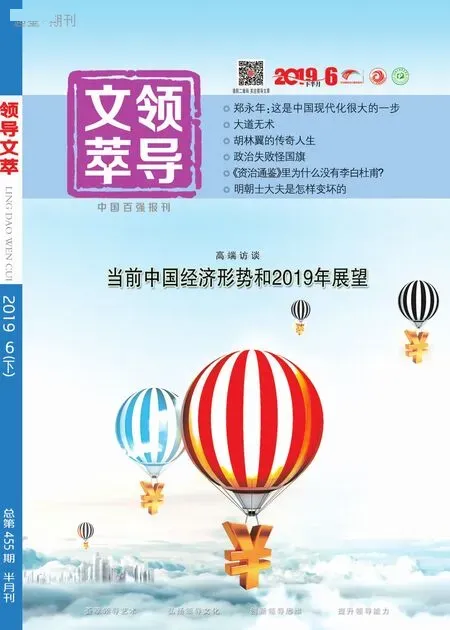涼州風范
余秋雨

苻堅要用一場長途跋涉的戰爭去爭搶一個文化人、一個佛教哲學家。
他派出呂光將軍,作為這場搶人遠征的司令。終于,在384年,呂光贏得了戰爭,搶到了鳩摩羅什。搶到了,就要送回長安,但路途確實是太遠了,走了一半,才到涼州,就是現在甘肅武威。到了涼州,呂光將軍聽到一個驚人的消息,派他出來搶人的國君苻堅已經下臺。苻堅先是慘敗于著名的淝水之戰,后又被殺。呂光想,既然這樣,我們為什么還要回長安呢?干脆,在涼州住下得了。反正有軍隊,一切都能安頓下來,他就做起了涼州的統治者。
那么,被他搶來的鳩摩羅什該怎么處理呢?呂光對他的學問并不太懂,但知道他是人人爭搶的寶貝,必須嚴加看守。就這樣,鳩摩羅什在涼州住了整整16年。
鳩摩羅什的父親是印度人,母親是龜茲國王的妹妹。他在龜茲,乃至整個西域,都是最高等級的佛教學者。這么一位大學者滯留涼州16年,能做什么呢?除了繼續精修佛理外,他還在漢語學習上下了極大功夫。正好呂光派到他身邊看守的那些士兵,來自中國很多地方,鳩摩羅什也順便學會了很多漢語方言。16年,已使他成為一位精通漢文的語言學家,這為他后來在長安主持翻譯工作,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他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位與唐代玄奘齊名的大翻譯家。玄奘很多翻譯,還要沿用他的經典譯法,例如《心經》里的名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最早就是鳩摩羅什的譯法,譯得準確而又凝練,無法更改。
說到他到長安主持翻譯工作,那又是另一場文化爭搶大戰了。原來,新的后秦君主姚興突然想到前輩有一個稀世寶貝遺落在涼州,就下決心要搶回來。涼州怎么肯放?因此姚興派出十萬雄師討伐涼州。結果,401年,鳩摩羅什被姚興搶到了,來到了長安。
同樣是由長安出發的爭搶,第一次,鳩摩羅什還很年輕;但是,這條爭搶的道路怎么這樣長呢?當他真到長安時,已經57歲。
為了爭搶一位文化人、一位哲學家、一位佛學家、一位翻譯家,居然一次次派出重兵爭搶,而爭搶的路途又非常遙遠。這樣的中國,雖然有點兒荒唐,卻讓我感到驕傲。這樣的中國,一定會孕育一個偉大的時代。
對涼州來說,幾十年的馬蹄,一會兒挾著一個文化大師來了,一會兒又挾著文化大師走了。但是,文化不像財富、權勢那樣,被搶走就沒有了,文化有根,有氣,有脈,只要來過就播下了種子。搶走了一位文化大師,卻搶不走那里已經形成的文化氛圍。沒有了鳩摩羅什的涼州,依然是文化中心。
因此,在鳩摩羅什被搶走的38年之后,又有浩浩蕩蕩的軍隊來搶文化了,那就是北魏王朝的軍隊。他們的胃口很大,一口氣搶走了3萬人。
這下,涼州總該空了吧?也沒有。到這3萬人被搶走80年之后,浙江上虞出生的僧人慧皎編的十四卷《高僧傳》所載僧人,一半是涼州高僧。
被爭搶走的涼州文化,在各地蔚然成風。首先是大同的云岡石窟,尤其是處于中心地位的“曇曜五窟”,接著是洛陽的龍門石窟,最終落腳于長安。幾乎整個黃河流域,都被涼州滲透了。考古學家宿白先生曾把這種現象說成是“涼州模式”,我在北大講課時把它改成了“涼州風范”。
“涼州風范”因為在文化上功勞巨大,竟然獲得了不可思議的報償,那就是出現了一個歸結性的世界級盛典。
一百多年之后,隋煬帝在涼州舉辦了一次隆重的“世界博覽會”。
隋煬帝在7世紀初期即位后,便接受裴矩關于進一步拓展西域商路的建議,讓河西走廊和涼州又一次鮮明地進入朝野視線。
山西人裴矩目光遠大,在我看來,他是當時少有的“宏觀經濟學家”。他以“互市”的觀念來反對古代的貿易保護主義,而且編制《西域圖記》標明絲綢之路的三條行經路線,因此是重新疏通國際通道的關鍵人物。在他的鼓動下,隋煬帝居然在609年到河西走廊上與涼州并列又相鄰的張掖,隆重舉辦了一場由西域27國參加的貿易盟會。
隋煬帝下令,涼州、張掖兩地的仕女必須盛裝出席。除了大量商品的展示外,涼州樂舞、西域諸藝和中原藝術家悉數會聚。參與的人群,擺出了綿延數十里的陣仗。西域各國使臣、商賈,再度為中國文化的宏偉氣魄所震撼。
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古代“世界博覽會”。初看似乎以貿易為重點,其實是中原王朝與西域各國全方位交流的重新啟動。
因此,這又是以最鮮明、最隆重的方式,展現了中國文化的世界身份。
隋煬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親臨河西走廊的中原帝王。他親自重新疏通絲綢之路的壯舉,讓我聯想到他的另一壯舉——開鑿大運河。一條橫向的走廊,一條豎向的運河,這實在是中華文明的兩大命脈。他在位僅僅十四年,竟然準確地握住了這兩大命脈,實在很不容易。不少史書對他頗有貶抑,因為他過于好大喜功、奢靡無度,但是我對他的一些大思路,卻頗為肯定。
隋煬帝一死,唐朝就建立了。唐朝的話題很多,但顯然一直保留著濃重的涼州風范。在此,我們不妨看兩首《涼州詞》。
一首是王之渙的:
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 ? 不度玉門關。
另一首是王翰的: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這種豪放樂觀的壯士情懷,正是唐文化的主調。那么多唐代詩人心中,怎么也放不下這個涼州。
(摘自《中國文化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