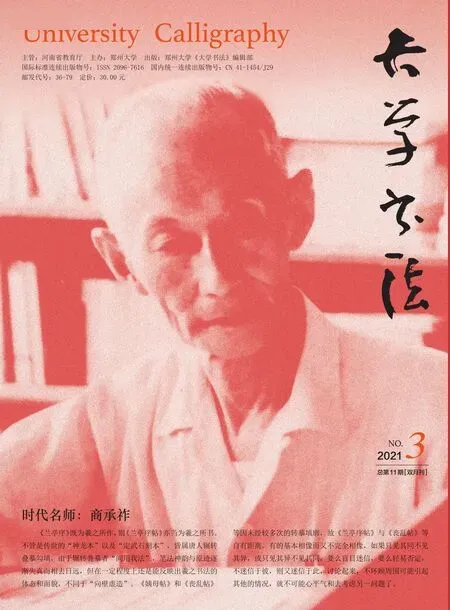書家品韻:從《快雨堂題跋》看王文治對“韻”的追求
⊙ 郭德法
引言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號夢樓,江蘇丹徒(今江蘇鎮江)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擅長詩文,精于音律,篤信佛教,精研釋典,其書法以行書和小楷見長,清人梁紹壬在《兩般秋雨庵隨筆》中提道:“國朝書家,劉石庵相國專講魄力,王夢樓太守專取風神。時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1]王文治在其詩文集和題跋中對劉墉評價頗高,文曰:“吾于近時善書者,服膺劉石庵前輩久矣。”[2]逢遇劉石庵皆敬稱其為“前輩”,可見其對劉墉的尊重與認可,后世論書者常將二人對舉,亦足見王文治的書學成就之高。《快雨堂題跋》保存了王文治對所見碑帖字畫的題跋評語,本文力圖從學書理想、學書方式、審美鑒賞三個方面勾勒出其書學理路上對“韻”的追求。
《說文解字》注:“韻,和也,從音員聲。”后世書論家常組詞連用,“神韻”指作品中傳遞的神采,“風韻”指營造出的格調。
一、學書理想——追慕晉人風韻
王文治在《論書絕句三十首》中評價王羲之:“醉本蘭亭付辨才,一篇繭紙萬瓊瑰。菁華已向昭陵閟,宗派還從定武開。”[3]對歷代公認的書圣王文治同樣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對于王羲之的傳世作品一直心慕手追,在“定武蘭亭”后跋曰:“余從事于《蘭亭》者三十年,從事于定武者二十余年。”[4]在沈繹堂臨蘭亭后跋曰:“《蘭亭》一帖,為書家之普門,唐宋諸名家,未有不從此入者。”[5]可見王文治不僅推崇王羲之的書法,不遺余力地去學習,而且認為唐宋名家無不從《蘭亭》中汲取養分。在王文治的作品中有很多“禊帖集聯”創作形式存世,由此可佐證王文治對《蘭亭》以及王羲之其他諸帖所下的功夫。
通過對《快雨堂題跋》通篇的理解分析,筆者注意到王文治并不像以往推崇王羲之的書家一樣以右軍獨尊,他所追求的是以右軍為代表的晉人風韻:
右軍諸子帖,與右軍正可參觀,何忍并去之?黃長睿之說,吾不敢憑。右軍諸子及諸王、諸謝,皆可與右軍參觀,方可想見晉人風格。[6]
從此段跋語我們可以看出,王文治在取法上并未囿于右軍,而是客觀評價晉代諸賢的成就,并表現出對晉代以諸王、諸謝等氏族為代表的書家共同營造的“晉人風格”的神往。
二、學書方式——求神重韻
(一)版本選擇——重視神韻

王文治 行書 《卿云愛景》聯 故宮博物院藏
在版本選擇上,王文治與前人秉持相同的觀點,即重視學習古人真跡,王文治重視真跡是因為他認為與刻本相較,真跡更能傳達出筆墨韻味。如在黃素《黃庭經》臨本真跡后跋曰:“余向時曾獲經眼,匆匆未及審定臨仿。然自一見以后,數日內腕下頓去許多塵滓。”[7]王文治表示見到真跡后,雖然未能臨仿,然而真跡所傳達的筆墨韻味便可糾正平日的習氣,頓去腕下塵滓,生動地表現出真跡在王氏認知體系中的重要位置。
王氏進步之處在于既重視真跡又能客觀評價不同刻本的價值,肯定了流傳的每種刻本皆具有一種韻味,善學者當綜合參觀,兼而取之。武進李兆洛在《快雨堂題跋·序》中言及:“評書如相人,可得神采于骨骼之表;刻帖如觀寫生,即極神似,然其顧盼謦欬不相親矣……蓋其真跡不可得見,不得不求諸碑刻。”[8]這一論點與多數書家所認知的書作一經上石便會下真跡一等相符合,而不同翻刻版本也會因刻工水平的不同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真。對于不同刻本王文治則從“韻味”上給予包容和肯定。如在《閣帖》后跋曰:“重摹之本,每本必具一種勝處,自是臨池者指南。”[9]又在《宋拓十七帖》后跋曰:“然每觀一帖,必有一帖之獨勝處。”[10]在《玉版十三行》后跋曰:“二玉版皆渾厚圓妙,各擅其長,臨池家宜參觀之。”[11]在《宋拓圣教序》后跋曰:“此本真宋拓,雖墨氣太濕,又另其一種風味。”[12]通過以上跋語可以看到王文治并沒有像考據家一樣以版本的年代作為評價其價值的最重要標準,而是以藝術鑒賞家的審美視角去發現不同拓本的價值,并提出不同版本各具韻味,善學書者宜參觀之。
(二)臨摹——以韻為上
臨摹古代經典法帖是書法學習的必由之路,關于臨摹的方法,歷代書論家多有提及,對后世影響較深的則以唐代孫過庭的《書譜》和南宋姜夔的《續書譜》為代表。孫過庭提出“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主張忠于原帖,精準臨摹。姜夔在《續書譜》中對孫過庭這一觀點進一步引申:
摹書最易,唐太宗云“臥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亦可以嗤蕭子云。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于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幾案,懸之座右,朝夕諦觀,思其用筆之理,然后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拓,乃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毫發失真,則神情頓異,所貴詳謹。[13]
由孫過庭、姜夔兩家可看出前代書論家多是主張通過精細臨摹,爭取做到毫發不失,以期最大程度地從古人經典作品中汲取養分,反哺自己的藝術創作。王文治關于臨摹的觀點則是主張“求神重韻”。在《論書絕句三十首》中盛贊米芾“只應釀蜜不留花”一語似可看作他對臨摹的態度,如:
至元代趙承旨,所傳真跡,亦尺牘居多也。但其摹仿右軍處,幾于千篇一律,未免太似。惟香光書札,任意揮灑,純任天真,出于古人蹊徑之外。此數札,望之若率意而成,而妙處為他人所萬不能及,良可寶也。[14]
古人云:“善學書者,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不善學書者,如優孟之學孫叔敖。”此卷臨信本書,絕不相似,然余甫開卷即知之,其寒峭之氣,逼人肌骨,能傳信本之神故也。[15]
王文治明確提出“善學書者”重在學習古人的精髓、神韻,對于只是追求字形相似的人則稱為“不善學書者”。這些貌似與前代論書者相悖的論點無不彰顯出王文治對于臨摹已不再苛求字形上的相似,而轉為對“韻”的追求。
在選取臨摹范本時,我們多會選擇書家所作的經典作品直接作為取法對象,因其是“一手資料”,最為完整地保存了書家創作時的整體風貌,便于我們更為系統純粹地接受古人。對經過后人臨摹的作品,歷代書論家普遍認為其中必然摻雜臨書者的個人“習氣”,較原作已不再純粹,故而下原作一等。王氏在《快雨堂題跋》中對名家的臨摹作品卻發出了不同的聲音:
竊謂古帖雖致佳,必得名家臨之而精神倍出。其似與不似之間,乃是一大入處。似者踐其形也,不似者符其神也。形去神在,若接若不接之間,而其消息出焉。以似為不似,以不似為似,非似非不似,即似即不似,重重秘密,帝網交羅。[16]
在這段近乎禪理的辯證論述中,王氏不僅對董其昌的臨摹作品做出肯定,而且進一步指出似與不似乃是學古的一大入處。經典作品經過名家臨摹之后的“二次創作”不僅不會消釋其精髓,反而會使二位書家的優點加以結合,相得益彰。如:
然予竊愛真米書,尚不如愛香光所臨之米書,何以故?米書魄力雖大,而平淡處尚有未至,故云林評跋,以為似子路未見夫子時。香光深得右軍平淡之趣,其臨米書,正如菩薩應愿為梵天主,以佛力加被,恢恢乎有余地矣。[17]
這段題跋中王氏指出相比“米書”更愛“香光所臨之米書”,原因在于米書魄力雖大,但是缺少平淡,而董其昌從右軍處得平淡之趣,故而米書經董臨之后兼具二人的魄力與平淡,故而相較原作韻味更豐富。
(三)創作——融禪宗思想求格調淡雅之韻
王文治在詩文中自述:“余弱冠時取趙州‘放下’之語名其齋,時初學為詩,亦初學坐禪。”[18]王文治年譜中亦有記載:“文治自弱冠即喜修禪,四十以后,始兼修念佛。比年來,以念佛為禪,復以禪念佛,禪凈并運,將終老焉。”[19]王氏素有慧根,耽于釋典,精研禪理,并將禪宗思想運用到書法藝術中,曾言“吾詩與書皆具禪理”。其承董其昌余韻亦是善于以禪論書的書家,融禪宗修習于硯田深耕之中,從禪宗思想中拈出“淡”字運用于自己的藝術評論及書法創作中,如在董臨懷素后跋曰:
董文敏深于懷素草書,興到疾揮,頗得驚鬼神、走龍蛇之意。宋元以來書家擅狂草者,皆不能及,以其淡也。余因習董書,始悟素師淡處,因素師又悟右軍淡處也。顏、柳皆得右軍淡處,惟文敏知之,亦文敏能習之。[20]
跋文指出“淡”意是董其昌由懷素上溯右軍的一大關捩,后世書家學習右軍當由此處經意。
三、審美鑒賞——觀書品韻
(一)書家品韻,懸判可定
王文治是當時頗有名氣的鑒賞家,汪承誼在《快雨堂題跋》卷后提及:“先生書名冠當代,鑒賞之識卓絕一時,收藏家得其片言,輒為增色。”[21]從“心農中書以收藏甲吳下,遂相契厚。中書所收藏,太守必加墨焉”[22]中亦可得以佐證。王文治自言其鑒賞方式為“書家品韻,懸判可定”。在《褚臨蘭亭真跡》后跋曰:“書家品韻,懸判可定。予于法書名畫,不倚考據,專貴眼照。”[23]此論使他與乾嘉時期興起的考據學派鑒賞風格劃開明確的界限。王文治對考據學派的態度還可見于袁枚《隨園詩話》:
王夢樓云:“詞章之學,見之易盡,搜之無窮。今聰明才學之士,往往薄視詩文,遁而窮經注史。不知彼所能者,皆詞章之皮面耳!未吸神髓,故易于決舍;如果深造有得,必愁日短心長,孜孜不及,焉有余功旁求考據乎?”[24]
(二)不滿于考據家的煩瑣考證
王文治對于書法鑒賞不滿于考據家的煩瑣考證,對待所有的鑒賞作品都以其表現的韻味為評判標準,所以對待同一件作品的祖本與翻刻本,他常提出獨到見解,表現出與考據派截然相反的鑒賞方式,如在《宋本蘭亭》后跋曰:

王文治 行書 《瓜架》軸 故宮博物院藏
余嘗見宋刻數本,決非定武祖刻,而奇古縱宕之趣,竟有祖本所弗能及者,此刻其一也。聽聲者,考定武于紙色墨色及已損未損、點畫連斷之間,然定武真面目,究竟未見。真鑒者,審玩于神明氣韻之內,故但是宋刻,皆可參究,而于右軍血脈,直可潛通,何論定武哉?[25]
此論通過“真鑒者”的鑒賞方式道出自己的觀點,對于考究紙張年代、墨色新舊、筆畫連斷等煩瑣細節的考證方式表示不屑。
(三)對具有較高藝術水準的“偽作”給予肯定
正因標準不同于其他鑒賞家,其對具有較高藝術水準的“偽作”也給予了肯定態度。他曾引用董其昌將《李秀》《云麾》刻入《鴻堂》的典故申明這一觀點:
昔董文敏見宋刻《李秀》《云麾》,嘆為稀有,刻之《鴻堂》。后重見唐刻,又題云“云霞變滅,金鐵森翔”,而不復追論前碑之偽,非自護其短,以前碑奇古高秀,亦自可傳也。余于古帖,專取眼照前人,不倚考據,雖懸判處或有舛訛,而真偽自是分明,優劣亦復不昧。請以俟諸后來之真鑒者。[26]
這段跋語充分表現出王氏鑒賞是從純藝術的角度出發,對每件作品的藝術水平都能給予客觀評價,并對其“書家品韻,專貴眼照”品鑒方式得出結論的真偽做出回應。
結語
王氏書中跋語多有重復引申處,篇幅所限,此處所引未必詳備,然滴水可知海味,故不做過多羅列。本文通過追慕風韻、學書求韻、觀書品韻,梳理了王文治書學過程中對“韻”的追求,為全面了解其書學思想梳理了脈絡。王氏習書求“韻”的成功案例,提醒我們今天的書法創作當注重作品的格調、韻味,著力于作品所呈現的整體風貌,力爭雅致而有余韻。
注釋:
[1]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M].清道光振綺堂刻本.
[2]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83.
[3]王文治.論書絕句三十首[G]//國朝書人輯略.清光緒三十四年刻本.
[4]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9.
[5]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73.
[6]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4.
[7]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19.
[8]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1.
[9]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1.
[10]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17.
[11]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20.
[12]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33.
[13]姜夔.續書譜[M].明刻百川學海本.
[14]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68.
[15]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68.
[16]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67.
[17]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70.
[18]王文治.王文治詩文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9.
[19]王平.探花風雅夢樓詩:王文治研究[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229.
[20]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69.
[21]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127.
[22]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1.
[23]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7.
[24]袁枚.隨園詩話[M].清乾隆十四年刻本.
[25]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10.
[26]王文治.快雨堂題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