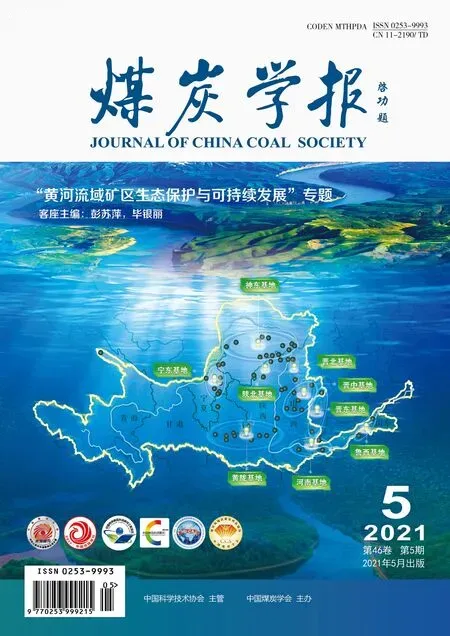風沙采煤沉陷區地表生物結皮土壤碳排放對水熱因子變化的響應
黨曉宏,劉 陽,蒙仲舉,高 永,魏亞娟,翟 波,劉禹辛
(1.內蒙古農業大學 沙漠治理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8; 2.內蒙古杭錦荒漠生態系統國家定位觀測研究站,內蒙古 鄂爾多斯 017400; 3.內蒙古自治區水利科學研究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4.中央與地方共建高校特色優勢學科“風沙物理”重點實驗室,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8)
我國煤炭資源開采具有空間上的不均衡性,主要集中在西北干旱區、半干旱區和西南山區[1]。據統計,截止到2005年,我國采煤沉陷區面積已達700 km2,且以每年約200 km2的速度增長。預計未來,我國采煤沉陷區面積將達到6.0×104km2[2]。由于我國煤炭資源主要采用井工開采工藝[3],導致原有的生態平衡被打破,形成大面積的采煤沉陷區,其地質、水分和土壤環境均發生了極大程度改變。例如:土地沙化、土壤結構破壞、生物多樣性降低。這些變化改變了原有土體結構的水肥運移規律,從而改變了采煤沉陷區生態系統碳循環過程[4]。
生物結皮是由細菌、真菌、地衣、藻類和苔蘚等隱花植物分泌的多糖物質與表層土壤顆粒相互作用形成具有生命活性的復合體[5],廣泛分布于干旱、半干旱區[6-7],成為荒漠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表明,生物結皮能提高土壤結構穩定性,增強土壤抗風蝕能力,具有改善土壤水文環境,增強土壤碳氮儲蓄能力[8]。CASTILLO-MONROY等[9]研究發現,地衣結皮覆蓋區是利比亞半島土壤碳的主要釋放源;王愛國等[10]發現藻類結皮和苔蘚結皮土壤CO2通量較去除生物結皮后呈現下降趨勢,同時土壤CO2通量的降低程度與生物結皮的組成和生物量呈正相關。齊玉春等[11]研究表明,古爾班通古特沙漠混生結皮在降水后,土壤碳排放速率顯著高于裸地。管超等[12]研究發現,增溫能抑制生物結皮碳排放。可見,生物結皮土壤碳排放強度與土壤水分和溫度密切相關。然而由于荒漠生態系統缺少水分和養分,導致生物結皮在碳源(匯)方面存在較多不確定性。
近年來,關于生物結皮對土壤碳循環的研究較多,而對風沙采煤沉陷區生物結皮土壤碳排放的研究鮮有報道。因此,為了準確掌握采煤沉陷區生物結皮類型與土壤碳排放間的關系,對采煤沉陷區不同結皮類型土壤碳排放進行實地測定。李家塔煤礦沉陷區位于黃土高原與毛烏素沙地接壤的晉陜蒙交界區,生態環境異常脆弱。經過多年的礦區生態綜合治理,礦區生態環境得到極大地改善,林分內分布大面積的生物結皮,其種類相對豐富,具有一定代表性[13]。基于此,筆者以毛烏素沙地采煤沉陷區為研究區域,以該地區典型生態修復樹種小葉楊林和沙柳林內的生物結皮為研究對象,對各林分類型下生物結皮的土壤碳排放日動態、土壤水熱條件進行實地原位動態監測,通過建立回歸方程明確沙質土壤水熱條件對不同林分類型下生物結皮土壤碳排放特征的影響,為采煤沉陷區生態修復中區域碳匯/源的評價提供借鑒。
1 研究區域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位于毛烏素沙地東北緣,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上灣鎮李家塔礦區(110.0°E~110.4°E,39.2°N~39.5°N)。氣候類型為中溫帶干旱、半干旱大陸性季風氣候,具有冬季漫長嚴寒,多風沙,夏季炎熱,蒸發強烈,晝夜溫差大,季節性溫差懸殊,無霜期短等氣候特點。年均降水量350 mm左右。地貌類型主要為波狀沙地和黃土丘陵溝壑地貌。地質條件復雜,在基巖上覆有黃土、沙土、風積沙等,且地表層面土壤多與粉煤灰結合形成夾層現象。研究區地表常年分布有大面積生物結皮,由于水分條件、生物種類和發育階段的不同,生物結皮顏色各異,主要呈綠色、黑色、黑褐色和黃綠色等。研究區生物結皮主要利用春季融雪、降雨、凝結水進行生長,并在干旱缺水季節和氣溫低于0 ℃時進入休眠狀態。礦區優勢種為小葉楊(Populussimonii)、沙柳(Salixpsammophila)、零星分布楊柴(Hedysarummongolicum)、檸條錦雞兒(Caraganakorshinskii)、油蒿(Artemisiaordosica)、蟲實(Corispermumhyssopifolium)、克氏針茅(Stipakrylovii)、羊草(Leymuschinensis)、百里香(ThymusmongolicusRonn)等[14-15]。
1.2 研究方法
1.2.1樣地選擇和布設
本試驗于2019年4月中旬(春季)進行,選擇小葉楊林地、沙柳林地和恢復裸地為試驗樣地。試驗樣地選擇地勢相對平坦、微地形相對一致的區域。在各樣地分別設置3個20 m×20 m的樣方,3個樣地間相距不足20 m,利用5點法在每個大樣方內設置5個2.0 m×2.0 m的小樣方作為監測點。調查每個樣方內的結皮類型(圖1)、結皮厚度、結皮蓋度等。具體情況見表1。
1.2.2土壤碳排放測定
選擇晴朗無風或微風天氣進行測定。利用ACE土壤碳通量自動監測系統(品牌:英國ADC;型號:ACE)對不同生物結皮類型土壤呼吸速率進行同步測定,每次測量時長為30 min。開始測定前12 h,用枝剪去除圈內地上草本植物并清除枯落物,利用取樣器(高8.0 cm,直徑34.5 cm的鋼圈)垂直壓入土層5.0 cm,并保證生物結皮的完整性。每種結皮覆蓋樣地制作5個取樣點即為5次重復。樣方設置在植物冠幅邊緣。將土壤碳通量自動監測儀自帶的水分和溫度探頭插入5.0 cm的土壤層中,同步測定土壤的溫度和含水量。為了保證研究結果的代表性,觀測時間7:00~18:00,觀測頻次為1次/h。連續觀測7 d,分別記錄生物結皮土壤碳排放速率、地表5.0 cm深度處土壤溫度、地表溫度和土壤含水量。
土壤CO2排放速率與土壤溫度、土壤含水量關系分別采用線性模型、指數模型、對數模型、多項式函數模型進行擬合,最后通過赤池系統(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準則和決定系數R2篩選出最優擬合方程,最后通過極大似然值判定擬合方程的優劣。
Rs=a+bT+cW
(1)
Rs=a+bT+cW+dTW
(2)
Rs=aTbWc
(3)
AIC=2lnL+2P
(4)
式中,Rs為土壤碳排放速率;a,b,c和d為擬合參數;T為土壤溫度;W為土壤含水量;L為回歸方程的極大近似然函數;P為回歸方程的獨立參數個數;AIC值越小說明擬合方程越優。
1.2.3數據處理
用Excel 2007對監測土壤碳排放數據進行整理,剔除異常數據。采用SPSS 22.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對3類土壤碳排放CO2排放進行差異顯著性分析,同時采用Eviews 10軟件對荒漠地區土壤碳排放速率與土壤溫度和含水量進行相關分析。利用Origin Pro 2018作圖。
2 結果與分析
2.1 生物結皮土壤碳排放速率及環境因子日動態變化規律
由圖2可知,3類結皮碳排放和環境因子日動態變化存在一定的差異性。3類結皮土壤碳排放速率日均值由大到小依次為藻類結皮(0.47 μmol/(m2·s))>蘚類結皮(0.45 μmol/(m2·s))>地衣結皮(0.44 μmol/(m2·s))。土壤碳排放速率的日變化均呈現出“單峰”曲線特征,其中藻類結皮的土壤碳排放速率“峰值”出現在12:00,蘚類結皮的土壤碳排放速率“峰值”出現在12:30,地衣結皮的土壤碳排放速率“峰值”出現在13:00。土壤碳排放日變幅由大到小依次為蘚類結皮地、藻類結皮和地衣結皮,其值分別0.10~0.83,0.05~0.77和0.12~0.77 μmol/(m2·s)。3類結皮下5.0 cm深度土壤溫度和地表溫度呈現出相同趨勢,整體表現為藻類結皮>地衣結皮>蘚類結皮。3類結皮的土壤含水量出現最低值時間各異,蘚類結皮在13:00達到土壤含水量的“谷值”,藻類結皮在14:00達到土壤含水量的“谷值”,地衣結皮在17:30達到土壤含水量的“谷值”,其時間最遲。
2.2 土壤碳排放速率與主要環境因子的關系
2.2.1土壤碳排放速率與土壤溫度的關系
由圖3可知,土壤碳排放速率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變化趨勢。3類結皮土壤碳排放速率最大值時間相差約30 min。藻類結皮12:00達到土壤碳排放峰值0.77 μmol/(m2·s),其次為蘚類結皮在12:30達到峰值0.83 μmol/(m2·s),最后為地衣結皮在13:00出現峰值0.77 μmol/(m2·s)。通過回歸擬合發現3類結皮土壤碳排放速率與土壤溫度的擬合關系均為二次函數關系;土壤碳排放速率與0~5 cm表層土壤溫度呈順時針環狀分布,其中以藻類結皮最為明顯。對3類結皮土壤碳排放速率和0~5 cm土壤溫度進行分段擬合發現,相同土壤溫度情況下,上升階段顯著大于下降階段(p<0.01),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土壤碳排放速率都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導致的時間滯后效應。

圖3 采煤沉陷區3種類型結皮土壤碳排放速率與土壤溫度回歸擬合Fig.3 Regression fitting of soil carbon emission rate and soil temperature three typical biologically-crusted soils in coal mining subsidence area
由表2可知,由于生物結皮土壤碳排放速率對溫度的響應不同,3類結皮的土壤碳排放速率與0~5 cm土壤溫度均呈現二次函數關系,其決定系數分別為0.59,0.46和0.64(p<0.01)。

表2 土壤碳排放速率與土壤溫度的回歸方程Table 2 Regression equation of soil carbon emission rate and soil temperature
2.2.2土壤碳排放速率與表層土壤含水量的關系
由圖4可知,3類結皮表層土壤含水量變幅較小。其中,蘚類結皮為0.17~0.30 μmol/(m2·s)、藻類結皮為0.17~0.27 μmol/(m2·s)、地衣結皮為0.19~0.32 μmol/(m2·s)。

圖4 采煤沉陷區3種類型生物結皮土壤碳排放速率與土壤含水量回歸擬合Fig.4 Regression fitting of soil carbon emission rate and soil moisture in three forest stands in coal mining subsidence area
通過擬合回歸發現,3類結皮土壤碳排放速率與土壤含水量最優關系均為二次函數。其中蘚類結皮土壤含水量決定系數R2為0.45,且達到極顯著水平(p<0.01)。藻類結皮和地衣結皮土壤碳排放速率與土壤含水量決定系數R2分別為0.14和0.13,但均未達到顯著水平(p>0.05)。
由表3可知,對土壤碳排放速率日峰值為界限將土壤碳排放速率與土壤含水量進行分段擬合發現,3類結皮土壤碳排放速率與土壤含水量最優擬合關系均呈二次函數。其中蘚類結皮土壤碳排放速率與表層土壤含水量呈逆時針環形分布,而藻類結皮和地衣結皮土壤碳排放速率與表層土壤含水量呈順時針分布。

表3 土壤碳排放速率與土壤含水量的回歸方程Table 3 Regression equation of soil carbon emission rate and soil moisture
2.2.3土壤碳排放速率與土壤表層溫度、含水量的關系
由表4可知,采煤沉陷區3種類型結皮土壤碳排放速率與表層土壤溫度和土壤含水量的協同關系均達到極顯著水平(p<0.01)。3類結皮土壤碳排放速率與表層土壤溫度和土壤含水量擬合方程均表現為方程(1)變異解釋率最低,方程(2),(3)擬合效果較好,其中方程(3)的擬合效果最好,方程(1)在土壤碳排放速率對土壤溫度和濕度協同響應研究中適用性最差。采煤沉陷區3種類型土壤含水量和土壤溫度可以解釋其土壤碳排放速率的57.8%~82.5%。通過分析AIC發現,蘚類結皮在土壤碳排放速率對土壤溫度和濕度協同響應研究中適用性強于方程(2),(3),可以解釋其58.3%的土壤碳排放情況,但藻類結皮和地衣結皮,擬合方程(2),(3)可以較好的解釋土壤碳排放速率,解釋系數在57.8%以上。

表4 土壤碳排放速率與表層土壤溫度和含水量的回歸擬合關系Table 4 Regression fit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oil carbon emission rate and surface soil temperature and water content
3 討 論
土壤碳排放速率是一個復雜的生化過程,其排放強度受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共同影響[16]。本研究顯示3類生物結皮土壤碳排放日動態變化各異。土壤碳排放速率日均值由大到小依次為藻類結皮(0.47 μmol/(m2·s))>蘚類結皮(0.45 μmol/(m2·s))>地衣結皮(0.44 μmol/(m2·s)),說明結皮類型是導致碳排放強度的主要因素[17]。該研究結果與胡宜強等[18]對沙坡頭生物結皮的研究結果一致。表明隨著生物結皮的演替,生物結皮的土壤呼吸速率呈遞增趨勢且均高于裸地。生物結皮的形成增強了土壤碳排放速率[18],這可能是由土壤溫度導致的。藻類結皮溫度(13.27 ℃)高于蘚類結皮(12.50 ℃)和地衣結皮(12.97 ℃)(表5),導致土壤酶活性升高,加速了土壤有機質的分解,進而導致土壤微生物呼吸加速[19],從而增強了土壤碳排放速率[20]。但是,與毛烏素沙地非采煤沉陷區相比(土壤碳排放速率為0.63 μmol/(m2·s))[21],采煤沉陷區各類生物結皮碳排放速率較小。因為采煤沉陷區土壤有機質含量較低,導致碳排放的減弱。加之春季氣溫較低,土壤干燥,導致生物結皮生理活動幾乎處于休眠狀態,因此導致采煤沉陷區生物結皮碳排放低于裸地碳釋放[22]。說明生物結皮的覆蓋,降低土壤碳呼吸速率。

表5 生物結皮土壤碳排放速率及溫濕度比較Table 5 Comparison of soil carbon emission rate,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of biological crust
本研究顯示蘚類結皮、藻類結皮和地衣結皮土壤碳排放日變化速率分別為0.17~0.30,0.17~0.27和0.19~0.32 μmol/(m2·s)。可見,藻類生物結皮土壤碳排放日變幅小于蘚類結皮和地衣結皮。該研究結果顯著低于管超等[19]對騰格里沙漠生物結皮的研究。這主要與土壤溫濕度有關。研究表明,土壤呼吸速率與土壤表層溫濕度呈顯著正相關[23]。本研究中,監測時間為春季,土壤溫度和含水量分別在3.87~18.46 ℃,0.17~0.32 m3/m3,遠遠小于其他季節土壤溫濕度。土壤溫濕度較低,抑制土壤酶的活性,降低了土壤有機質的分解,從而抑制土壤微生物呼吸。本研究顯示土壤碳排放速率日動態均成單峰曲線特征,其中蘚類結皮和地衣結皮的土壤碳排放速率“峰值”出現在12:30,藻類結皮的土壤碳排放速率“峰值”出現在14:00。與趙東陽[24]對黃土高原土壤蘚結皮的研究結論一致。該研究結果表明,砂土和砂質壤土蘚類結皮碳呼吸峰值出現在14:00。3類結皮土壤含水量均表現為先降低后升高的趨勢,即為清晨和傍晚含水量較高,土壤含水量隨著溫度的升高而逐漸降低。土壤碳排放是酶促作用的結果,隨著一天當中晝夜的變化,土壤溫度和土壤水分等環境因子也會發生改變,這使得酶促反應中的各類酶活性不同,進而導致酶促反應的異質性,3類生物結皮土壤碳排放產生日動態間的差異[25]。研究中還發現,5 cm土壤溫濕度日變化曲線峰值出現時間滯后于3類土壤碳排放速率,且土壤碳排放速率與土壤溫度和水分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但是導致土壤溫濕度滯后性的原因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溫度對土壤碳排放速率的影響局限在土壤表層[26]。土壤溫度和土壤含水量對于碳排放有較大影響,并呈顯著線性關系。土壤碳排放是一個復雜的生物地球化學循環過程,是環境、植物、土壤共同作用下的過程[27-29]。也有多數研究發現,溫度是影響土壤CO2排放的重要因素[30-31]。研究中發現,土壤碳排放速率日動態變化與0~5 cm土壤溫度變化趨勢基本吻合,均在早晨8:00以后,隨著土壤溫度升高土壤碳排放速率驟然升高,午后土壤溫度降低,土壤碳排放速率隨之降低,但生物結皮土壤碳排放速率“峰值”都早于土壤溫度“峰值”,2者時間上存在著滯后現象[32-35]。相關研究發現,造成土壤碳排放與土壤溫度時間上的分離的主要原因是溫度的混合效應。同時,生物因素也是影響土壤碳排放和土壤溫度間滯后關系的重要環節,包括植物的光合作用和根系生長、枯落物以及微生物的動態變化的共同影響[36]。土壤溫度影響了土壤的酶活性。在低溫環境下,土壤酶的活性受到限制,隨著溫度的增加活性增強,當超過最適溫度后,酶活性急劇下降,甚至降解。由于根系呼吸和土壤微生物呼吸都需要酶的參與,因此土壤溫度會影響土壤碳排放速率[37]。整體而言,土壤碳排放速率時間變化對表層土壤溫度的響應均達到了極顯著水平,這與趙東陽[24],辜晨[38]研究結果一致。本研究中發現,李家塔采煤沉陷區3類結皮土壤含水量較低且變化幅度較小。水分對土壤碳排放作用相對較小,可能是結皮覆被區的微生物,能夠利用少量的水分刺激其生理活性[39]。只有蘚類結皮的土壤含水量和土壤碳排放速率之間存在一致的動態變化,2者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土壤含水量對于土壤碳排放的影響主要集中在對植物和微生物的能量供應和對其體內的二次分配作用,與此同時,對土壤通透性和氣體擴散進行調控[40]。
4 結 論
(1)毛烏素沙地北緣采煤沉陷區3類結皮碳排放速率的日變化特征曲線基本一致。總體上呈現“不對稱鐘形”的“單峰”曲線特征,土壤碳排放速率峰值出現在12:00~13:00。土壤碳排放速率日均值由大到小依次為藻類結皮(0.47 μmol/(m2·s))>蘚類結皮(0.45 μmol/(m2·s))>地衣結皮(0.44 μmol/(m2·s)),說明隨著生物結皮演替,其土壤碳排放速率逐漸增強。
(2)3類結皮土壤碳排放速率與表層土壤溫度和土壤含水量均呈二次函數關系。土壤含水量與土壤溫度可以較好的解釋土壤碳排放速率,擬合方程中2者對于土壤碳排放速率的解釋系數在57.8%以上,說明土壤溫度和土壤含水量能顯著影響土壤碳排放速率。
(3)毛烏素沙地采煤沉陷區生物結皮覆蓋可有效抑制土壤碳排放。在風沙采煤沉陷區生態修復過程中建議多建植小葉楊和沙柳等鄉土樹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