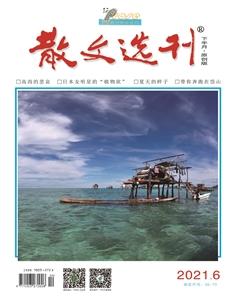裁縫老張
康華英
老張是個裁縫。說是裁縫其實有些名不副實,他不過是做一些縫縫補補的小生意。鋪子很小,是一間大概幾平方米的土屋。有風的時候,風從磚縫里“嘩啦啦”地吹進去,冷得很。他的身體似乎不錯,好像從來沒病過,一年365天除了春節幾乎沒見他關過門。每天不管我早自習多早,或者晚自習多晚,都能看到他在小屋里踩著那臺百花牌縫紉機,“咿咿呀呀”。
老張中午通常用電飯煲煮飯,一竹筒米,一個青菜。他從不在旁邊的餐館買著吃。那幾平方米的小房子塞滿了人們送來縫縫補補的衣物,有時候電飯煲好像都沒地方放了。
我上下班時總能看到三三兩兩的婆婆和爹爹,坐在老張鋪子門口,嘮著家常,聊著天兒。任憑過路的車輛和人們喧嘩,老張總是不緊不慢地踩著他的縫紉機。有時候,我帶幾件不太穿的衣物,讓老張幫我縫縫,或者熨熨。他極認真地縫補熨燙,弄好后還小心地掛在墻上,然后幫我折疊好,只收取三五塊錢。那時候我總在想,在人們幾乎不穿打補丁衣服的年代,老張的鋪子一月到底能掙多少錢?能維持他的日常開銷嗎?他家里是否依靠這錢維持一家老小的生活?日復一日,這種疑慮在我腦子里越來越強烈。
幾年前冬天的一個周末,我路過老張店鋪的時候,突然看到老張的鋪子關門了。第二天,仍舊不見開門。一周后的清晨,我又看到老張了。不過,這一次看到他的店鋪已經由之前的位置搬到了馬路對面。還是學校出來那條巷子,不過,這次比之前面積更小,而且不是單獨的屋子,是倚在人家不常用的車庫的防水臺下面,用兩塊藍色的布遮擋著。冬天的風一吹,“嘩啦啦”地響,和他縫紉機的踩踏聲一起,“咿咿呀呀”。
我不知道老張經歷了什么,心里總有些放不下。回到家,我翻出了我出嫁時陪嫁的布料。多年沒打開箱子,布料上有些折痕。我輕輕地熨平這些折痕。我想著,這些布也許老張用得上。
下午放學的時候,我去了老張的店鋪。我明顯看到老張比從前老了許多。他仍舊戴著一副黑色邊框老花鏡,臉上有明顯的皺紋,兩鬢也有些花白。他正瞇縫著眼,一只手壓著衣物,另一只手邊哈著氣邊轉動著縫紉機。因為地方太小,我幾乎是站在外面。風使勁兒地吹起那兩塊用來擋風的藍色的布,一晃一晃,高高低低,左左右右,像蒙古高原上迎接遠方客人的哈達。老張見到我,憨厚地笑了笑。我拿出布料來給他,老張的嘴角搐動了一下,反復說著“謝謝,謝謝”。交談中,我得知他并不是本地人,而是鄰村高德畈的,兒女都已成家。我想著從高德畈騎自行車過來,來回至少得一個小時以上,而老張每天風雨無阻堅持了大半輩子。老張看出了我的欲言又止,他笑了笑,說道,一月千把塊錢兒吧,個人生活費還是沒問題的。既能減輕兒女負擔,又能給附近的人縫縫補補。我說,鋪子怎么換位置了,這太小,也不擋風。老張咳了好一會兒,說道,前幾天身體突感不適,去醫院了。人老了,不中用了,那個房子也租不起了。我也沒有別的手藝,只能做做這個。現在的位置不錯,不要錢,是好心的主人讓我免費搭的。
說完,他哈了哈手,又轉起了他的百花牌縫紉機。一陣風吹來,老張打了一個冷戰,他又咳了一會兒。那有些花白的頭發,在風里一顫一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