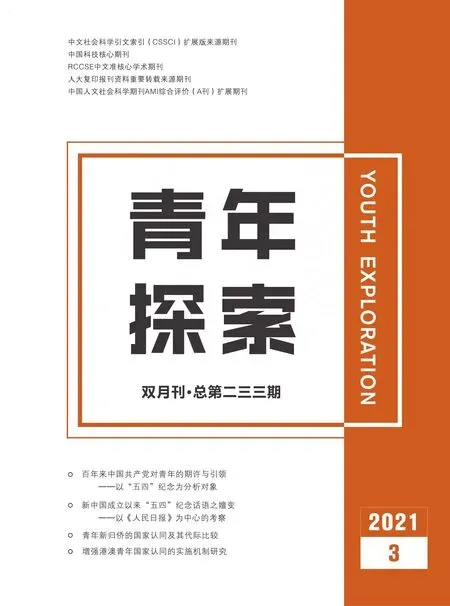育兒差距:家庭教養方式的實踐與分化
一、導言
家庭是社會再生產的重要場所[1]。近年來中國家庭的親職論述較以往有了較大的轉變。首先,親子關系從側重于傳統孝道規范下的社會交換向強調親子內在關系的情感滿足轉變;其次,父母角色從單一管教孩子的執行者向科學育兒的學習者轉變;第三,在多年素質教育改革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家長在教育方式上從過去“填鴨式”向注重孩子的個性、品行多元綜合素質培養轉變。
親職論述的時代轉變呈現出家庭教養方式整體朝向更為密集的發展趨勢,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導致競爭的加劇,家長越來越擔心自己的孩子可能落后于他人,為此越來越多的家長特別是中上階層的父母開始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努力參與、干涉其學習與生活,以期其可以脫穎而出。伴隨著密集型教養方式的盛行,當代家長也面臨更多的焦慮、壓力與不確定,特別是這種對父母的經濟、文化以及時間資源上有較高要求的教養方式使得不同家庭背景下的父母在理想的親職論述與實際的教養實踐中不可避免地面臨著斷裂,陷入矛盾。
本文將在當前親職敘事的脈絡與時空環境下聚焦不同家庭背景下的父母所面臨的教養理念與教養實踐間的內在矛盾困境,了解不同家庭背景下的父母是如何通過對比不同世代的教養實踐來展現自身的教養理念,試圖發現資本的累計與轉變在不同家庭背景間影響其家庭教養方式的內在機制,探究在社會場域中家庭教養方式是如何通過不同類型的資本再分配來協商不同家庭背景間的差異與社會不平等。
二、文獻回顧及理論框架
在家庭教育研究領域中,家庭教養方式(Child-rearing)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對此話題的論述最早可以追溯到盧梭、洛克等理論大師。隨著現代心理學的發展,鮑德溫等心理學家進一步劃分了家庭教養方式的基本維度,鮑姆林德、麥考比等則分別提出了有關家庭教養方式的理想類型。這些以心理學為主要取向的研究主要從個體心理與親子互動的視角審視了家庭教育的過程與模式,缺乏對社會文化背景、社會地位等社會因素的系統討論[2]。
隨著社會學者逐漸進入家庭教養方式的研究中,上述研究缺陷一定程度得到彌補,其中父母社會地位如何型塑家庭教養方式以及對子女日后成就的可能影響受到了學者們普遍關注。梅爾文·科恩是最早對家庭教養方式進行社會學探討的學者,其通過對華盛頓地區和意大利都靈地區家長教養態度的相關數據,建立了最初有關家庭社會地位與教養觀之間的聯系,提出影響父母教養態度與價值觀的關鍵是職業,不同階層的職業對個體的要求不同,其中中產階層職業較為注重人的自主能力,而勞工階層則強調絕對的服從。教養觀的差異也進一步影響家長與子女間的互動方式,其中中產階層父母較為重視孩子的自主性,因此多采取溝通互動的雙向交流模式[3];與之相對,勞工階層則注重強調服從,因此多采取指令性為主的單向方式。隨后尤里·布朗芬布倫娜的研究也進一步證明和發現,中產階層的父母在親子互動中更加民主、平等與包容,勞工階層的父母則更為強調子女的服從[4]。與上述學者側重于階層間教養需求與表現不同,布迪厄認為教養方式的階層差異主要來自于客觀化的地位以及慣習,資本與品位在代際間的傳遞促成了階級關系的再生產[5]。拉魯則在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基礎上重新定義了家庭教養方式,認為文化資本不僅指對高雅文化的欣賞能力,還包括與社會機構,如學校等相適應的一系列策略與風格,借以更好地幫助個體適應環境[6]。
美國社會學家拉魯在其著作《不平等的童年》一書中詳盡地呈現了不同家庭背景的父母在家庭育兒方式上的差異。中產階層父母通過采取“協同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方式培養孩子的才藝和表達能力,并在與孩子日常溝通時注意運用“講道理”而非指令性方式與之交流。拉魯指出,在這樣的教養方式下,孩子容易形成“權力感”(Sense of Entitlement),善于捍衛自身權益,有助于其未來進入專業的白領勞動市場。與之相對,勞工階層的家長通常采取“自然成長”(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的育兒方式,認為孩子的成長應減少父母干預,在與孩子交流過程中采取命令的口吻,強調父母的權威性,且由于自身文化程度與職業階層地位較低,其對教師與學校具有較強的疏離感,面對制度常感到無力或挫折。因此在這種教養方式下成長的孩子,容易養成“局促感”(Sense of Constraint),傾向于服從和配合,符合勞動力市場中低端行業需求[6]。中國國內對家庭教養方式的研究日漸熙攘,且主要建立在拉魯的理想類型基礎之上,以定量分析為主。如,田豐、靜永超通過上海家庭調查數據的定量分析發現,中國城市家庭教養方式已呈現階層分化,但社會流動可改變教養方式[7]。黃超根據中國教育追蹤調查(簡稱CEPS)數據對中國青少年家庭教養方式的分布、階層差異以及其對青少年非認知能力的影響進行了分析,發現中國家庭教養方式以專制型和忽視型為主,呈現出較強的階層差異,同時教養方式對非認知能力有顯著影響[8]。劉浩利用2010年CFPS數據研究祖代與父代的社會階層對家庭代際流動和對家庭教養方式的影響,結果顯示不同階層的家庭有不同的教養實踐模式,且教養實踐模式存在多代間傳遞[9]。
可以看出,拉魯所提出教養方式的兩種理想類型對之后的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成為分析教養方式階層差異的基本分析框架[10],為家庭教養實踐研究提供了啟發性視角,但依舊存在值得商榷的方面。一方面,在階層的設定上,拉魯采取的是一種靜態的視角,即將階層視為既定的結構位置與二元范疇[11],同時她忽略了階層內部的異質性,未能捕捉到各階層家庭中不同社會群體在教養實踐中的差異性。雖然社會階層的形成可以從個體在社會領域所占據的地位理解,但由于社會領域本身是一個多維空間,每一個實際位置都可以根據多維坐標中的不同相關變量進行定義[12],因此簡單的將中產階層與勞動階層進行二元劃分,就等同于將階層視為勞動市場中的某一固定位置,忽略了對“階層過程”的分析[13]。缺乏反映社會同一階層但不同群體家庭發揮自身優勢的動態描述也就難以關照到階層內部可能存在的不同的教養價值觀與教養方式。因此,當我們關注中國社會中的家庭教養方式時,更應將其置于經濟社會轉型的背景下,考量社會不平等程度、教育回報率以及學業成績的重要性等因素對不同家庭背景下家庭教養方式的影響作用。
目前有關家庭教養方式的心理學與社會學研究主要以量化分析為主,對于教養方式的變與不變,通過哪種機制運作,顯示出怎樣的家庭背景間差異等仍有待質性分析進行深入探討。
在進行與階層相關的分析時,階層如何劃分歷來是學術界探討的熱點之一,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將對資本的占有作為劃分階級的主要標準,韋伯提出權力、財力和聲望“三位一體”的分層理論,新韋伯主義學者戈德索普主張階級是性質不同的群體,而非等級不同的群體,新馬克思主義學者賴特則是將物質資本、組織資本和勞動資本納入分層視野之中。實際上無論哪種階層劃分方法都只是作為基于理論事實的分析與假設,階級并非某種被物化的或刻板的印象,而是在特定場景下的一種“活的經歷”(Lived Experience),受到特定的歷史時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14]。那么究竟該如何生動地展現不同家庭背景間的界限以及家庭內部存在的異質性即成為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對此,研究認為,一方面可以借鑒布迪爾所提出的階級理論,通過資本占有與分配的不同體現差異性;另一方面還應結合經濟社會發展背景,綜合考慮在教育體制、勞動力市場等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等因素影響作用下教養慣習的代際斷裂以及可能存在的家庭內部異質性。
布迪厄的階級理論是在一種想象的社會空間中展開的,其考察了不同階級群體的結構處境與相互聯系,強調個體或群體行動者在遭遇一定時空情境時可能產生的變化,他將行動者不斷調節自身策略、習性以適應結構變化的過程稱為“社會軌跡”[15]。“社會軌跡”也進一步表明了布迪厄的理論旨趣,拒絕將階級視為簡單的再生產理論,資本的多重組成與相互間轉換視角,不僅可以用來解釋中產階層的教養策略與存在的優勢,描述工薪階層的父母如何利用有限的資源在結構限制下進行教養實踐,且還可用以分析不同資本間的轉變所呈現出的動態過程。
本文將社會經濟發展背景與階層理論相結合,認為在社會轉型背景下,不同的家庭背景依舊是預示文化教養選擇的重要標準,但需要綜合考量父母自身成長的社會經濟環境,將教育體制、勞動力市場等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教育回報率等因素納入分析框架。
綜上所述,本文認同并借鑒藍佩嘉的研究路徑[11],將家庭教養方式劃分為兩個層次:“親職敘事”和“教養實踐”。其中“親職敘事”指的是父母透過敘事性理解,描述個體的生命經歷是如何影響當前教養方式以及父母所認同的有關教養的文化規范;“教養實踐”則指的是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所采取的實際教養行為與策略。在探討親職作為一種階層化經驗時,本文加入了社會變遷視角,認為造成不同教養決策與方式差異性的本質在于父母自身成長的社會經濟環境,即無論哪種家庭背景下的父母在試圖塑造孩子行為與價值觀時,都是在為他們應對未來生活作出準備。在此過程中,作為某種特定的物質地位,使得不同家庭背景下的父母在資源配置以及轉換過程中具有不同的親職敘述與教養理想,不同家庭背景下的父母將面臨有關資源、時間等方面的不同約束,這些將導致不同的教育結果。研究將對下述問題展開討論:
首先,回應以往研究,探討在不同的經濟社會背景下,當代中國父母教養方式到底是承自父輩的教養慣習的延續,還是透過反思與上一代斷裂?代際間教養方式斷裂或延續的傾向與父母自身的教育背景或職業是否存有聯系?
其次,不同家庭背景下的父母其教養理想與教養實踐間是否存在矛盾或沖突?在社會經濟轉型時期,面對教育體制、勞動力市場等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高教育回報率的時代背景下,他們又將如何在具體的教養實踐過程中協商界限,如何定義自身教養實踐的合理性?
最后,在教養實踐中,不同的家庭背景如何與性別相交織,如何透過差異性性別化教養方式落實教育策略的分化?
三、研究方法與樣本情況
(一)研究方法
研究者于2019年11月初至2020年3月中旬陸續通過滾雪球的方式尋找合適的受訪對象,通過半結構式訪談了16位不同家庭背景的父母,期間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無法面談,采取微信視頻通話的方式進行訪談。
在社會地位的界定上,研究承繼以往學者對社會地位的劃分,將職業和受教育水平作為主要指標。具體來說,職業上參考李強提出的“國家社會經濟職業地位指數(ISEI)”,將ISEI分值在41~66分的群體視為中產階層,ISEI分值在16~40分的群體視為工薪階層[16],雙薪家庭中父母雙方若不屬于同一階層,則以較高者為準;受教育水平上,將(父母中至少一位)具有大學本科學歷作為中產階層指標。
由于訪談的目的在于了解父母在教育領域的做法,因此提出的具體問題是開放式的,具體提問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研究者“多聽少發言”,主要由受訪對象回憶自身孩童時期的教養方式,以及自己對孩子教育的想法與實踐;第二階段是研究者作為提問者,對受訪對象描述的具體情節追問細節,并回答背后的原因和對自己的影響;在訪談的最后,研究者嘗試提問一些較為抽象性問題。隨后,通過反復研讀訪談筆記,對資料進行編碼等工作后,概括出每位受訪者的基本樣貌,并按照不同編碼背后指涉的概念進行整理分析,厘清彼此間關聯,進而形成貫穿不同家庭背景家長教養方式的主軸。
(二)樣本情況

表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四、親職敘事與教養實踐
(一)親職敘事
1.“斷裂”還是“延續”?
訪談中,當詢問教養方式是否受到兒時的影響,無論哪種家庭背景下的被訪者幾乎都表示影響有限,甚至有一些被訪者還會強調自己會“刻意避免從前的路”。所不同的是,在表達與上一輩教養方式的差異性時,中產階層的態度更為“堅決”,而工薪階層則相對“柔和”。例如在對“是否會打罵孩子”問題的回答上,不同家庭背景的父母的回答也存有一定差異:
“我和先生都覺得現在的社會環境和我們成長那時候差別很大,不可能還按照自己小時候那樣子教育現在的孩子,小孩子哪有那么聽話懂事呢,總有犯渾的時候,但是我們很少會打罵,最初孩子爺爺總說我們慣著孩子,后來為了減少相互間影響,我們就沒和老人住一起。”(Z01)
“我們現在教育孩子肯定不能和以前完全一樣啊,時代變了嘛!以前我爹不高興了抬手就打,現在只打他(小孩)肯定不行,你只是打他也不服氣,打了也沒用。孩子該打還是要打,但還要講究點新方法,你要讓他知道你為什么打他,你是在為他好。”(L01)
顯然,雖然同樣是表示不愿受上一輩教養方式的影響,但不同家庭背景下的父母在程度上有較大差異,中產階層的父母往往不僅很明確地表明自己的教養方式有別于當年父母的打罵教育,且會在行動上身體力行;而工薪階層則對打罵教育一邊持保留態度,一邊又會在教養實踐中實施這一做法,與此同時也會注意到孩子的情感,在這里權威管教與情感關系儼然成為了相輔相成的教養做法。
雖然不同家庭背景下的父母都表示自己不愿受到自己父母的影響,但他們也承認很多時候在自己的潛意識里還是會延續原生家庭的教養慣習。比如受訪者Z02說:“人家都說你找愛人的時候不妨先看看他的父母,如果是女孩就看看她的媽媽,男孩就看看他的爸爸,多半都有父母的影子。我覺得這個‘影子’可能是很難擺脫的,就比如我雖然不認可我媽媽那種從小教育我的方式,但是我自己依舊“繼承了”她的很多做法,我老公也是一樣,他自己也說他自己很多時候的反應就像他爸爸當年。”對此,她表示自己會通過多讀書、聽一些與教育孩子相關的課程來思考與反思自己的行為。與中產階層的Z02不同,L02雖表示自己會不知不覺地重復自己父親的做法,但同時也承認“雖然覺得這樣好像并不是最好的辦法,因為沒有什么效果,但是也不知道還能怎么做,更沒心思和那個精力去琢磨這個事。”
現代國家的發展趨勢之一即社會的專業化,伴隨著育兒工作的專業化與技術化趨勢越來越明顯,遵從育兒專家的指導、做學習型父母逐漸成為現代家長,特別是中產階層父母認同的教養策略[17]。通過對專家體系的認可與依賴,專家知識的介入不斷提醒著中產階層的父母需透過反思與內在對話,并在此過程中對源自于原生家庭的無意識、自然化的教養慣習進行“再加工”,并在日常的教養實踐中不斷加以審視與反思,從而幫助自己成為“更好的父母”。與中產階層不同,其他階層的父母在面對自身延續原生家庭的教育慣習上,常表現出“不知道該怎么辦”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挫敗感。一方面,由于家庭背景導致的資源不足使得工薪階層較難具備與中產階層相似的教養理念;另一方面,經濟壓力與時間不足也阻礙他們獲取更多的認知資源和學習新的教養理念,因此更傾向于采取簡單、直接等立竿見影的教養策略。
2.“密集”還是“寬松”?
雖然育兒習俗在不同國家中有不同表現,但教養孩子的文化卻不斷隨著時代發生變遷。寬松型的教養方式是如今很多“70后”“80后”父母的成長記憶,但在今天當這些曾經的孩子成為父母后,卻秉承了比自己父母更密集的教養方式[18]。密集型教養方式的特征之一,即注重與孩子的溝通和協商。訪談中發現,中產階層家庭往往具有較為清楚的規則、平等意識,鼓勵孩子按照規則與家長溝通或協商,對此Z04的態度可謂十分堅決,他認為“體罰或打罵孩子都是過時的一種野蠻做法,很多時候小孩子沒有自覺性,所以你要和他首先制定彼此都能接受的規則,這個規則一定不能是你自己定的,而必須是和孩子一起協商定下的,給予孩子平等的權利,他才會有受到尊重的感覺,才能做得更好。”
按照今天父母參與孩子的教養方式看,更多的參與孩子生活的行為常被中產階層父母視為是一種“標準”的教養方式,雖然他們自己并不是這么長大的。談到自己成長的經歷時,Z03表示,“在我小時候,放學后和小伙伴一起玩到太陽下山才回家吃飯是常有的事,家長最多問問作業是不是寫完了,一般不會特別安排額外的學習,寒暑假在記憶中基本就是自己和朋友撒歡的玩”。然而,Z03在談到“自己是怎樣的父母時”這樣說:“我們今天在思考自己當初接受的教育與我們對自己孩子有什么不同時,會發現我們今天對孩子日常生活的參與和干預程度遠勝于我們父母。實際上,在有自己孩子之前,我和先生一直以為我們會是那種寬松型的父母,也認為孩子應該擁有無憂無慮的童年,但是真的到了自己做父母時才發現,你想的和實際社會環境讓你做的完全不是一回事。現在孩子們面臨的競爭壓力大很多!”
從Z03的敘述中我們會發現,一方面中產階層的父母內心傾向成為“寬松型”的父母,認為孩子應該擁有無憂無慮的童年,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清醒地意識到所謂的無憂無慮的童年只是一種想象中的理想狀態,或者說只是孩子進入充滿競爭壓力的社會之前的一個十分短暫的階段,中產階層父母心目中“無憂無慮的童年”也只是一種被建構出來的短暫狀態。
當密集型教養方式作為一種標準化的教養規范受到全社會推崇時,工薪階層也受到了影響。訪談中發現,雖然工薪階層父母一定程度上秉承了父輩的“打罵教育”但同時也注意到了溝通的重要性,“與孩子做朋友”類似的說法時常出現在被訪者的口中。L02說,“有時候氣急了肯定會打他,但是我也會注意平時多關心他。只是我們平時比較忙,如果有時間的話,比如放假都會帶他去玩,晚上也會聊聊班里的事。不過他不是太喜歡說,但他說的話,我們都挺愿意聽的。”然而,也有部分受訪者表示并不太認同“溝通”的效用,如一位父親(L04)表示,“小孩子不聽話時,你只和他說教可能沒有用,他比你還會說呢,所以該打還是要打,你打了他才怕你,才知道厲害。”
在談及在教養孩子上有什么想法時,L03表示“首先是想她成才啊,但是到底怎么培養沒想過,就是盡量創造條件,做好家長能做的吧。”再進一步追問“您覺得孩子的童年應該是怎樣的”時,被訪者L03的回答是這樣的:“童年就該是無憂無慮的吧,否則怎么叫童年呢?人一輩子不容易,在還沒長大的時候,就別逼她了。”
顯然,工薪階層的父母在秉承權威管教的同時也注意到了與孩子間的情感維系,但一方面,由于自身條件導致的資源不足,使其缺乏密集型教養方式中的文化資源,為生活努力打拼的困境以及時間、精力上的不足使得他們也很難耐心地對待孩子的問題或去學習新的教養理念;另一方面,工薪階層在職場中的工作特性使得他們較少重視口才的訓練,因此所養成的階層秉性也與中產階層所重視的溝通、說理等相距較遠,他們的職場經驗更加重視服從的重要性[19]。此外,同樣面對“無憂無慮的童年”,中產階層的家長認為這是一種被刻意建構出來的短暫狀態,而工薪階層的父母則認為父母的責任應該是避免對孩子施加額外的壓力,采取較為寬松的教養方式。
(二)教養實踐
1.家庭背景差異下的教養方式異質性表現
全球范圍內,年輕人就學年限越來越長,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在不斷刷新紀錄[20],因教育資源緊缺而使得家庭上的壓力越來越大。即便是在最富裕的國家中,公眾對教育資源的需求程度也遠高于供給[21],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實施的是競爭性入學。伴隨著對教育資源的競爭,其他教育階段的競爭也隨之形成,在訪談中發現,一些中產階層的家庭選擇將孩子送入私立教育機構,接受更為國際化的教育。Z05表示她和先生放棄了家門口的公立小學,選擇了一年學費12萬元的私立學校,她詳細地描述了當初入學面試時的情形:“……完全不同于我想象中的面試,一進門就是一張大桌子,上面有3個iPad,但是卻有四個孩子,老師要求玩一種游戲,但是這種游戲需要兩個小朋友合作,接下來就是四個孩子的表現,老師沒有任何的干預,只是靜靜的觀察,最后錄取的標準也不是誰的游戲得分高,而是那個在這個過程中表現最得體、與其他小朋友合作最愉快的那個孩子。所以,你能明白這個學校看中的是什么了吧?不同于普通的只會教孩子課本知識的學校,這樣的學校更注重孩子的性格與情商,所以孩子通過考試后,我們毫不猶豫選擇了這里。”
隨著社會的發展,“軟技能”日益成為人力資本中極為重要的表現形式,其中人際交往能力與行為品行,如團隊精神、創新精神等日益成為決定未來職場工作效率的重要因素,這些技能的習得不僅來自于家庭,也是學校教育的副產品[22]。顯然,中產階層的父母認識到了這一點,在選擇教育的培養路徑上,他們更傾向于孩子能夠成長為無所畏懼、勇于質疑的“有思想”的人,雖然私立學校是否就一定能達到這一目標尚未可知,但很顯然,對公立學校相對統一的教學計劃與標準化的學校制度規則的不滿,讓那些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中產階層父母做出了不同的選擇。Z05就明確的表示,“我們對孩子的培養方向是國際型人才,以后是打算送孩子出國念書的。”為此,她表示十分感謝這個時代給予了家長更多的教育選擇,“也正是不必像我小時候那樣,千軍萬馬擠高考這一條獨木橋,才讓我能毫不猶豫的對孩子采取這種不只看考試分數,而更注重性格培養和創新、挑戰的(教養)方式。”
在跨國資本以及人才流動日益頻繁的社會背景下,中產階層尤其是具有較強經濟實力的父母而言,對孩子的教育訴求已經超越了國界,“教育的國際化”作為一項具體的策略或想象期待,使得他們將對孩子的教養重點從過去重視單一的課業成績轉變為更為全面的教育模式,強調多元學習的“雜食教養”(Omnivore Cultivation)[23]。
有兩個孩子的Z03說:“我們家兩個孩子,除了參加了必要的語數外課程學習,還報了跆拳道、聲樂班、美術班、樂高積木和小主持人。孩子有些潛在的東西(能力)你不去接觸一下,就很難發現,還有些東西(能力)誰也不是天生的,需要專門的培養。孩子的表現也證明這了一點,哥哥跆拳道現在已經是紅帶加黑杠了,妹妹小主持人比賽去年拿了個一等獎。雖然我們也說不是太看重這些,但是也不得不承認這些對他們未來(擇校)肯定是有助于加分的。”對于孩子未來的發展,自己與先生同為博士學歷的Z03表示,他們的家庭從經濟水平看只能說中等,談不上多么殷實富裕,以現有的經濟實力看,雖很難像一些富裕家庭將兩個孩子都送出國讀書,但會量力而行地為孩子報一些家庭可以承擔的“夏令營”,以便幫助孩子在日后的升學中有更多的優勢,在面臨擇校時有更多的選擇;同時他們還十分注重與孩子的溝通與陪伴,不僅成員間可以就某一問題暢所欲言、各抒己見,且家庭定期以舉辦“讀書交流會”的形式彼此交流學習,還會安排全家一起看話劇、聽音樂會等活動。由此可見,一方面,家庭經濟資本的投入推動了中產階層家庭孩子的體制化,在參與各種課外活動的過程中獲得的成績、證書等也將成為制度性的文化資本,有助于孩子在未來激烈的競爭中占據優勢;另一方面,家庭文化資本通過向孩子傳授知識形態和語言技能,幫助他們形成自如、淡定的氣質。
通過對不同中產階層家庭的訪談發現,雖然同為中產階層家庭,經濟資本優勢的家庭與文化資本優勢的家庭,孩子在未來可能走的道路有所不同,但無論是哪種資源優勢下成長的孩子,作為社會未來可能出現的“新精英”群體,其都需要擁有“面對權威或者擁有特權的自如、淡定、如魚得水、不卑不亢的氣質”,而這些作為教育場域中的慣習都需要經過從小在各種儀式場合中反復練習,才能鐫刻在身體中,流露在言談舉止的細節中[24]。
訪談中發現,面對激烈的社會競爭,工薪階層的家長往往表現出比中產階層更為強烈的希望孩子可以通過體制內升學這一途徑實現階層向上流動的意愿。L05在社區邊上的一家美發店打工,她的孩子就在附近上小學,訪談中她表示,孩子最初留在老家蔡甸由老人照管,因為了解到武漢市區的教育比較好,因此到了學齡期時就把孩子接到了自己身邊,為了在武漢市區上學,自己和丈夫早在兩年前就貸款買了一套小居室,由于工作的便利,自己經常可以和社區的很多媽媽們交流如何教小孩,哪里的輔導班老師認真負責,自己也給孩子報了一些課程,但是她基本上報的都是對考試有幫助的課程,比如數學課、作文課和書法課。當問及為什么沒有報一些藝術類的課程時,她這么回答:“我覺得我的小孩也不會有什么藝術的天份,那些彈彈唱唱的事不如踏踏實實的好好學習對他以后有用,我和他爸爸都希望他長大能夠成為讀書識字,有文化的人。”L05還表示,自己每個月都會找老師聊聊孩子在學校的表現,同時班上也有同學的家長來店里美發,她也會借機和家長聊一聊,“有一些有關升學信息的微信公眾號還是老師和有的家長推薦給我的,我有時候也會看一看,但是更多的還是和他們直接聊天來了解情況,感覺這樣更直接一些。”
可見,由于工薪階層普遍缺乏文化資本,在教養孩子的過程中時常感到力不從心,但他們也會通過自身努力,尋求可以沖破自身家庭環境壁壘的社會資本,以轉換為可能幫助到孩子的教養資源。與此同時,工薪階層的父母雖表示自己也會通過網絡等新媒體方式進行育兒學習,但在實際自我評估時往往通過關鍵人,如老師、身邊其他家長等的評價來反身性看待自己的教養實踐。
與中產階層不同,工薪階層的家長雖也表現出“希望他成才”的殷切期望,但也面臨來自經濟、時間和能力上的窘迫感。在此現實背景下,一些工薪階層的父母表現出“順其自然”的態度。L06和丈夫在菜市場租賃了一個賣菜攤位,每天早上四點多就要起來上貨,9歲的女兒有很強的自理能力,L06說:“我們兩口子都是進城務工的農民,如今靠賣菜算是在城市安了家,孩子以后就全看她自己了,是學習的料,就走拿筆桿子的這條路,要不是這塊料,也不強求。我和他爸爸也是這么和她說的,學習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們文化水平低幫不了你啥,全靠你自己。”較大的勞動強度以及自身資源的緊缺導致家長不可能以孩子為中心,所謂的親子活動都是鑲嵌于日常的生活之中,家庭組織化程度相對較低,父母的教養角色也多以“養”為主,而非“育”。
與L06相類似,訪談中的工薪階層家長反復強調,如果孩子不是學習的料就不勉強,這種將孩子的才能視為先賦性資質而非后天培養的看法與只注重學校考試分數的做法類似于布迪厄所提出的“追求必需品”的階級品位[12],從而體現出與中產階層因不同處境而導致的階層教養慣習。
2.家庭背景差異下的教養實踐性別異質性表現
“重男輕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備受詬病的一大現象,有觀點認為家長因性別對孩子采取不同教養策略與文化有著密切關系[25]。隨著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男女平等”成為社會共同認可的社會規范,很多年輕的父母會聽從一些專業性育兒書籍中專家的意見,盡力用一種性別中立的方式教養孩子,如不給孩子購買具有性別角色意義的玩具,女孩也可以買小汽車,男孩也可以玩洋娃娃。然而,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是:一方面女性的教育回報低于男性,另一方面,女性的教育投入卻往往高于男性[26]。本研究在對不同家庭背景父母的訪談中發現,雖然在對女孩的教養實踐過程中,不同家庭背景下家長的表現顯示出一定的差異,但整體上看在對待女孩的教養方式上呈現出較以往較大的區別,不同家庭背景在女孩的教養上均呈現出一定的密集化趨勢。
分析: 雙子葉植物過量吸收生長素類似物后,形成層的細胞分生能力加強,產生腫脹,破壞了韌皮部的運輸功能,使植物因有機物運輸受阻而死。同時,這還破壞了植物正常的代謝,使植物呼吸作用加強,但不會產生ATP,造成植物細胞的損傷并浪費大量能量[5]。正常的生長素則容易被植物代謝掉,不會產生此危害。單子葉植物因能迅速使人工生長素類似物失活,所以除草劑也不會對單子葉植物產生效果。
Z06是一名律師,她說:“雖然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遭遇到歧視的現象依舊存在,但是那些真正優秀的女性并不一定會差,且從整體看越是好的工作,越是憑個人實力說話,因性別產生的歧視其實越少。”與Z06相類似,工薪階層的L05表示,“我還是覺得小孩子無論男孩還是女孩,都要多管教,多關心,小時候不管,家長是輕松了,但是以后孩子就會吃虧,現在多管一點,孩子未來也能有個好出路。”與此同時,這位母親還拿自己和曾經的同學做比較,認為導致彼此人生不同境遇的關鍵并不在于性別,而是受教育水平。“我的那些同學,讀了大學的最差的也不會差到哪去,沒讀什么書的,再好也有限。”
由此可見,女性的分化是造成現代家庭教育中對女孩教養方式改變的因素之一。如果一個社會中女性的薪資以及社會地位都普遍低于男性,且在女性群體內部在薪資和社會地位上不存在較大差異,那么家長也沒有太多動力去培育家庭中的女孩;但當女性內部逐漸出現分層,家長看到了精心培育女孩可能會帶來的希望,也就更有動力去精心培養。
除了女性內部的分化外,現代社會帶給女性生活方式的變遷也是造成部分家庭加大對女孩教養投入的因素之一。隨著從事與男性一樣工作或獲得較高薪水的女性越來越多,不愿意結婚的女性也開始增多,中國很多生養了女孩的家庭逐漸意識到與傳統社會相比,現代女性的生活方式更加豐富,因此教養女孩的方式上也較以往有了不同。此點尤其體現在訪談中的中產階層家長身上。Z07是一位曾有美國留學經歷,7歲女兒的父親,他說:“其實我覺得以后不結婚的人肯定會越來越多,我的女兒也不一定會結婚,結不結婚都沒關系,女性在社會中早已不再依附于男人或婚姻而是個人實力。因此,我們家對孩子的培養可以說是忽視性別的”。
雖然如今人們普遍認可家長應平等地對待不同性別的孩子,并提出在育兒過程中避免性別刻板印象,然而長期受文化力量的影響,不同背景的家庭在教養問題上表現上性別差異。
Z07是一位對孩子十分嚴格的父親,他表示雖然家庭中秉承平等的教養理念,但對女兒無論是生活習慣、生活態度、言談舉止還是道德品行、學習方法等都十分注意,他說:“為了女兒以后可以憑借自己的實力更好地獨立生活,我們除了要求女兒在功課上要優異,且日常生活方面也有家規,比如見人要打招呼、進屋要脫鞋換鞋,物品要擺放整齊等等,細小的事情也有規矩,我們覺得這些看似是小事,但一切的井井有條、克制自律都是孩子必須要養成的品行。”與之相對,同為女孩父親的L03雖也表示希望女兒“成材”但是在具體教養策略上并沒有太多的規劃,而是選擇順其自然成長的方式,“孩子成材當然好,但是也要順其自然,女孩子普普通通的,有個一技之長,能養活自己也挺好。我們也不知道怎么教育,盡量吧。”
由此可見,中產階層在教養孩子上不因孩子性別而存在太大差異,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都希望能夠既表現出良好的教養,又兼具國際化通用型人才的特點。與之相對,工薪階層的父母在教育觀念上更強調孩子應擁有一技之長,期望孩子未來可以按照自己的價值觀自由自在地生活。
在男高女低的婚配坡度文化下,父親多充當家庭經濟資源的主要供給者,母親的文化資本,即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活動的參與對孩子的社會化過程具有十分顯著的影響[11]。訪談中發現不同家庭背景的父母在參與孩子日常教育的實踐中,均呈現出一定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父親在大多數被訪家庭中的作用多集中在提供經濟支持,而母親則需承擔一系列具體的家庭責任,投入更多的時間、精力和智力。換句話說,在特定的親職教養場域中,父親以提供經濟資本為主,母親則側重于從文化資本維度對子女的教育提供幫助。通過訪談進一步發現,不同家庭背景的母親在為子女提供教育支持的過程中,特別是在維系家庭—學校關系方面往往呈現出較大的群體性差異,大致可以歸納為“服務型”和“陪伴型”兩種理想類型。
訪談中工薪階層的母親多以“服務型”為主,指的是母親們在教育支持過程中側重于從基本的生活層面提供保障,盡量確保孩子獲得相對較高質量的教育。被訪者L01表示自己平時的日常生活主要集中在照顧家人特別是小孩身上。在談到孩子平時的學習安排時,她說:“學習上我們也給孩子報了語數外三科的課,但我主要負責接送他去上課,現在孩子大了,我感覺父母的作用也只能是生活上管吃管穿這些。”這位母親表示由于自己文化程度不算高,在輔導孩子功課上時常感到力不從心,雖然給孩子報了培優班但對于學習效果到底如何也沒有特別清楚。對于這位母親來說,在對孩子的教育過程中,一方面正常的教育支出尚不構成沉重的生活負擔和經濟壓力,但另一方面自身文化程度的欠缺使她時常面臨其他方面的困擾,具體表現在與處于叛逆期的孩子溝通上,以及每當面對孩子不夠理想的成績常常感到無所適從,L01表示自己讀書并沒有很好,以前不覺得怎樣,但是慢慢孩子越來越大了,覺得好像很難知道孩子心里想什么。“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也不愿意和我說,說起來最發愁的是他的學習,馬上就要面臨中考,但是他成績不行,我很擔心他能不能讀高中。我們只能給他提供外在環境,就是你要什么學習資料啊,要上什么課程啊,但是只是出錢沒有辦法解決根本性問題,我也不明白為啥一直學不好呢?!所以就在成績下來后的當天就去找他們班主任,問為啥孩子成績不行,我說孩子有時候會說在課堂上老師比較少叫他回答問題的,但是很明顯老師當時不是很高興,大概就是說老師都是一視同仁,是孩子自己問題。但是孩子的問題是什么,他又說不清楚。”顯然這位母親一方面對孩子的成績表現出了失望,因為她相信家庭為孩子提供了一切可以提供的條件,但是結果卻不是她希望看到的;另一方面,她并不擅長與老師溝通,詢問老師的方式也是首先指出老師可能存在的不足,導致老師對孩子成績不好的問題過早地就以含糊的防御性言論結束了。因此,盡管她確實為子女獲得高質量的教育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對于“服務型”母親來說,其依舊深深地感到與子女的日常教育需求相差甚遠,難以理解他們的行為以及令人不安的成績。
雖然在實際的家庭教養過程中,母親常作為陪伴者角色出現在孩子身邊,但不容忽視的是由于近年來隨著教育市場化發展,校外培訓價格也水漲船高,為提供足以保障孩子教育的經濟資本,單靠父親一人工作難以支撐日益增加的家庭開支,因此對于很多工薪階層家庭來說面臨的是母親的陪伴的時間同樣受到擠壓,甚至空間分離。受訪者L08的丈夫常年在外跑運輸,而她自己在一家私營企業工作,經常需要加班。對此她表示“不怕你笑話,我兒子今年小學五年級了,我只參加過2次家長會,更別說什么課外活動了。因為他們學校的這些事基本都是安排在工作日,我上班是不能或者很難請假的。老師對此確實很有意見,所以我也很害怕接聽到老師的電話,或看到老師的留言,我和孩子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你在學校乖乖的,千萬別惹事,惹了事媽媽沒時間去學校處理。”現代社會中越來越多的父母需要離家工作,與此同時勞動彈性化和電子科技的普遍使用也進一步導致辦公時間無限延長,這些都導致了家庭生活與工作之間的界線日益模糊化工薪階層家庭表現得更為明顯。
與“服務型”相對應的是更多出現在中產階層中的“陪伴型”母親,她們往往承擔著為孩子創造有利于學習的各種家庭環境,同時對于學校要求的各種活動也積極響應。受訪者Z08是兩個孩子的母親,生育了第二個孩子后不久,大女兒也到了學齡期,因丈夫經濟收入尚可且時常出差加班,她索性決定先在家做一段時間的全職媽媽,陪伴好兩個孩子。對此,Z08介紹說自己一開學就報名了女兒班上的家委會,對學校舉辦的運動會、讀書會、郊游等各種活動都積極充當志愿者。與此同時,她日常對孩子的情緒、心理和飲食營養等也都十分關注,“孩子剛剛上學,對小學生這個角色還需要一定的轉換時間,我在家的話更加方便,每天接送她上學路上可以談談心,不會覺得有了弟弟就忽略了她。我這個女兒只喜歡吃肉,不愛吃菜,對此我還專門看了營養學的書。”此外訪談中還發現,在與孩子的教育接觸中一些中產階層母親非常注重打造孩子的學習空間,如Z08曾略帶有驕傲地表示“現在房價雖然很貴,但是我和先生依舊賣了之前的房子換了這套大四居室,以后兩個孩子各一間,同時還有一間大書房,是我們和孩子平時在一起讀書的房間,我們家每周都會安排固定的閱讀時間,我們覺得固定的時間、固定的場所,可以增加孩子們對閱讀的儀式感。”
面對當前教育競爭下沉、競爭更為激烈的社會環境,“陪伴型”母親通常還會積極尋找各種有利于孩子的資源。Z02的兒子今年上六年級,她早在孩子剛入學的那年起就注冊了類似“家長幫”等論壇的ID,手機APP上更是裝滿了各種孩子用得上的軟件,對此,她表示:“現在競爭十分激烈,家長只能暫時忘掉自己,全心陪伴在孩子身邊。孩子學習時間也很緊張,因此我會幫助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整理每次的錯題,低年級時特別注意幫助他一起預習,整理錯題等。”這些通常都要占用Z02很多時間,但是這位母親堅持認為,“作為家長,每個階段都有自己的責任,現在就需要放棄掉那些可有可無的事情,將自己的工作和中心都放在孩子身上。”
當然,盡管“陪伴型”母親通常都會盡自己所能陪伴在孩子身邊,但實際生活中她們也會遭遇幫不上忙和無可奈何的時候,而每當這時她們的內心似乎都會產生強烈的不安和愧疚感。受訪者Z09表示,“雖然我也讀過大學,但是,現在孩子們的功課我怎么覺得比我們那時候要難好多……嗯,心里還是覺得有點愧疚,孩子來問你,你自己卻不會。”在面對自身的文化資本在幫助高年級孩子學習的過程中遇到困難時,“陪伴型”母親會積極想辦法以彌補自身這一短板,如送去課外輔導班學習,與授課老師保持良好的溝通關系,利用個人社會關系收集盡可能多的升學資訊。Z09表示孩子剛上幼兒園時,就從同事那里得知孩子有一定的藝術發展會對未來升學有好處,因此從四歲起就給女兒請了揚琴老師,每周去老師家里學兩次琴,目前已經學了近十年。除此之外,“陪伴型”母親通常也更注意和老師保持良好的互動關系,根據Z09的介紹,一般每個月她都會在網上和老師聊幾句有關孩子的近況,并認為這些交流對了解孩子和幫助孩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除了聽老師的建議外,這位母親還會將孩子的一些品質或特長主動介紹給老師。“我們孩子上幼兒園時,在與老師溝通中曾介紹過他喜歡講故事,那個老師知道后就很鼓勵孩子的這個行為,特意安排時間和機會讓他去別的班給大家講故事。雖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對我的孩子來說就是很大的激勵與鍛煉。我就想,如果我沒有和老師介紹過孩子的這個愛好,可能他就失去了這樣的鍛煉機會。”
由此可見,在型塑文化資本的過程中,不同家庭背景的母親在購買教育資源、與教師和其他家長互動、主動協調自身教育經驗等方面呈現出異質性。其中工薪階層的母親主要是為孩子提供生活物質層面的經濟支持,而中產階層的母親還擅長利用其他社會和文化資源,為孩子提供額外的教育資源。
五、小結與討論
本文通過個案訪談比較了當今社會不同家庭背景下的家長在家庭教養理念與教養實踐間的差異,研究發現,在不同群體中,除了存在收入、身份等方面的差異,還存在一定的“育兒差距”,具體表現在對孩子的培養途徑與精英的塑造上分歧日益明顯、對女孩的教育期待以及母親在維系家庭 — 學校關系方面呈現出群體性差異。
第一,通過對不同家庭背景的家長在教養理念與教養實踐的對比中可以發現,不同家庭背景的家長對孩子的培養途徑與精英的塑造上分歧日益明顯。擁有經濟或文化資本的家庭往往傾向于采取更為密集的教養方式,注重對孩子“軟實力”等綜合素質的培養,且在面對競爭越來越嚴峻的社會現實背景時,私立教育、海外留學等一定程度充當了“安全閥”的角色,使得這些家長可以更加坦然地采取自己理想的教養方式,而其他家庭背景的家長依舊只能被動地信任和選擇應試教育,甚至自身對生活的辛勞感受進一步強化其對孩子采取順其自然的教養方式。
可以預見,這些差距將會成為一個閉環中的鏈條,成為影響階層流動的重要因素。目前,越來越密集、越來越看綜合素養,以成就為導向的教養方式已經逐漸成為在社會資本中占有優勢的群體的某種慣習;比如我們在訪談中發現越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越有可能共同撫育孩子,越可能花費更多的時間在孩子教育上,越可能采用有助于孩子在未來社會立足或有助于提升階層的教養方式。與之相反,對那些已經處于弱勢的工薪階層家庭中,父母卻面臨越來越緊迫的約束,這些約束使得他們很難采取中上階層的成就導向做法。由此,育兒差距不僅加劇了來自弱勢家庭背景下孩子所要面臨的挑戰,且也將成為阻礙未來社會流動的壁壘。
第二,雖然整體上看不同家庭背景的家長在對待女孩的教養方式上均呈現出一定的密集化趨勢,但不同背景的家庭在教養女孩上依舊表現出差異。中產階層在教養孩子上不存在性別差異,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都希望能夠既表現出良好的教養,又兼具國際化的視野。與之相對,工薪階層的父母在教育觀念上更強調孩子應擁有一技之長,期望孩子未來可以按照自己的價值觀自由自在地生活。
現代社會中,家庭在對待女孩教養上所表現出的異質性也進一步印證了“個體所表現出的學歷、性別甚至容貌等方面的因素并不全然是其自身努力的結果,很大程度上還可能是父母親所屬階層的產物”[27]。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現代社會中男女之間的差異、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階層差別雖仍存在,但較以往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反而是女性與女性之間的差別因其家庭背景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別正在不斷擴大。
第三,研究通過關注母親在型塑文化資本中存在的群體差異性,重點分析了其在為子女提供教育支持的連續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異質性,不同家庭背景的母親大致分為“服務型”和“陪伴型”兩種理想類型。其中,工薪階層的母親多以“服務型”為主,在教育支持過程中側重從基本的生活層面提供保證,盡量確保孩子獲得相對較高質量的教育,中產階層的母親則為“陪伴型”,她們除了為孩子提供基本的生活需求外,還更擅長利用其他社會和文化資源,為孩子提供額外的教育資源。
最后,研究通過對不同家庭背景下家長的教養模式分析,體現了家庭背景與教養理念如何交織并型塑個體的社會行動,個體教養理念的價值性建立在其所實際擁有的資本基礎之上,即不同家庭背景看似相似的教養實踐的背后常存在不同的行動動機與行動意義,而相似的教養期待又常因行動者所擁有的資本差異而呈現出不同的教養實踐。由于本研究沒有涉及到縱向的資料,因此雖然發現了教養慣習的代際斷裂,但卻未能深入探究不同家庭背景父母教養方式變遷的內在機制,特別是經濟社會的發展對家庭教養方式產生怎樣的影響,這都有待于今后更為深入的分析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