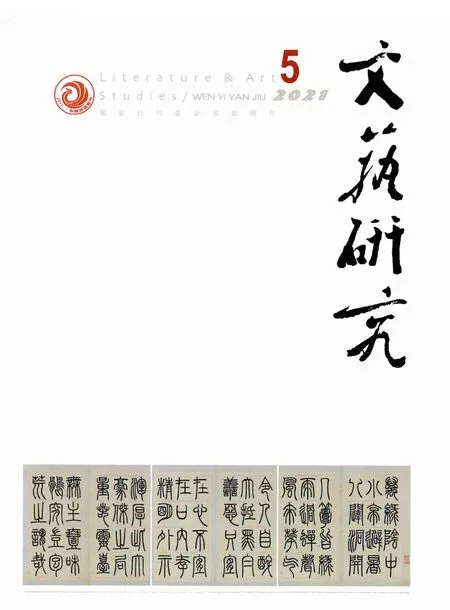“后當代藝術”:重回真實的三種理論路徑及其問題
董麗慧
就概念史而言,“當代藝術”(contemporary art)一詞在20世紀80年代隨著新藝術的市場化進程迅速普及,成為全球新自由主義經濟的表征。21世紀最初十年,“當代藝術”一詞進入歐美科研機構,在制定規則和反規則之間實踐著悖論的學院化、學科化、體制化進程。進入21世紀10年代,由于市場化、體制化以及數碼時代新技術的挑戰,這一“當代藝術”命名正面臨被拋棄的危機,對其最直接的反抗當屬“后當代藝術”(post-contemporary art)命名的提出。
本文認為,近十年來出現的后當代藝術理論,以行動主義藝術(activism art)和實在論唯物主義藝術(realism materialism art/RMA)為兩種主要理論路徑,除此之外,泰瑞·史密斯(Terry Smith)構建的三重同時代性/當代性(contemporaneity)理論架構,又試圖對上述兩種后當代藝術加以收編。無論這三種理論路徑在具體建構思路和模式上存在何種差異,其出發點均是對21世紀以來已成范式的當代藝術的反抗,均不同于20世紀末哈爾·福斯特(Hal Foster)為新前衛藝術正名的、拉康意義上作為心理創傷的《重回真實/實在》(The Return of the Real,1996)所提出的觀念,而試圖回到三者所認定的不同“真實”(the real):它們或直接介入社會活動的“現實”(reality),或提出介于現實主義和傳統唯實論兩種實在論(realism)之間的“基礎實在論”(infrarealism)①,或以多元架構圖繪一個多種時空和多重現實共存的、作為同時代真實現狀的全球圖景。本文試圖厘清歐美當代藝術學界基于重回“真實”的問題意識,并圍繞后當代藝術展開的這三種理論路徑,探討其可能性啟示及存在的問題。
一、行動主義藝術路徑:從后當代藝術到“后占領狀況”
據史密斯考證,“后當代”一詞誕生于對“后現代”的戲仿,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零星出現,但并未產生重要影響。1989年,以杰姆遜為首,杜克大學出版社開始編輯出版“后當代介入”系列叢書,早期以后現代主義理論為主,至今已出版百余種與文學和文化研究相關的理論書籍。2011年,該叢書重新闡釋了指導理念,提出“理論以其‘后當代性’代表著歷史,通過為未來指明新的方向,識別當今知識潮流中的進步性”。2007年,兩位伊朗裔建筑師在公開發表的對話中使用了“后當代”一詞,以指稱進入21世紀后面向未來的新建筑。近十年來,藝術領域對這一詞語的使用漸多,2015年紐約同名非營利性藝術機構成立,旨在支持藝術家“影響未來觀念、系統、社群的發展”。“后當代藝術”一詞還出現于藝術家約瑟芬·梅克塞泊(Josephine Meckseper)2005年創作的櫥窗裝置作品的標題“后當代藝術的完整歷史”(The Complete History of Postcontemporary Art)中,該作品于次年參加了惠特尼雙年展②。
“后當代藝術”一詞真正作為術語進入理論討論始于近十年。藝術家利亞姆·吉里克2010年在《當代藝術不足以解釋那些正在發生的》一文中寫道:“‘當代藝術’這一術語的特點是它的過度使用。這一‘當代’已經超出了具體的當下,同時吸納了專門的、頑固的利益群體……從研究生工作室項目里出來的人就是當代藝術家……當代藝術同時變成了歷史、一個學院派的學科。”③在吉里克看來,受到朗西埃意義上的藝術體制(regime)操控,學院化的“當代藝術”命名本身已無法用于描述真正鮮活的當代藝術現象,亟需“新的術語和界定”,吉里克找到的替代詞是“最近的藝術”(current art)④。實際上,這一命名方式并非原創,早在“當代藝術”一詞依附于“現代藝術”的“寄生期”就已出現,這也就解釋了吉里克何以將當代藝術的起源追溯至藝術中對天才和創造力的強調,以及19世紀以來的工業化。因而,“最近的藝術”一詞無論從歷史溯源還是現實能指的層面,顯然都不足以取代“當代藝術”。值得注意的是,在對“最近的藝術”的論述中,吉里克同時使用了“后當代”一詞提問:“我們如何避免‘后當代’成為歷史性懷舊或僅僅是排除自我的政治性認同?”⑤在這里,“后當代”是“最近的藝術”的另一個稱謂,指現行藝術體制之后的、更有活力的新藝術,其具體形態包括社會參與性藝術和激進的行動主義藝術⑥。
明確以“后當代藝術”指稱行動主義藝術的耶茨·麥基,因兼具大學當代藝術教師和社會活動藝術家身份,對當代學院化的藝術教育和社會化的藝術創作、及其分別涉及的當代藝術體制化和市場化問題格外關注。在2009年對《十月》雜志“當代”問卷的回應中,麥基指出當代藝術正面臨問題,他認為,當代藝術恰如布魯諾·拉圖爾所言的行動者網絡的“準物質”(quasi-object),是一個由諸多“演員”組成的復雜系統(包括藝術家、藝術品、批評家、藝術史家、策展人、收藏家、藝術管理者、政府機構、非政府機構、大學、私人基金、廣義的寫作和新聞報道、觀眾等等),同時又被裹挾在被奧奎·恩威佐(Okwui Enwezor)稱為“后殖民星叢”(postcolonial constellation)的全球網絡中⑦。在麥基看來,當代藝術的陳腐首先體現在它的體制化和專業化,“三明治藝術家”如同快餐加工業或流水線上的從業者;其次體現在將藝術家塑造成娛樂明星以取悅觀眾的消費主義心態;最后體現在將當代藝術視為批判性分析對象的當代藝術理論研究中,其中以“當代性”理論研究為代表,形成了學院化自成體系的當代藝術系統⑧。
麥基認為,與當代藝術深陷體制和市場難以自拔不同,在以行動主義藝術為代表的后當代藝術中,藝術家不僅是活動的服務者或藝術裝飾的提供者,而且是運動的直接組織者,真正實踐了本雅明意義上的“藝術家作為生產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事件,麥基稱之為打破藝術界和學院體制限制的一件“審美政治化作品”,一個“藝術事件”,一次“反資本主義的儀式”⑨。正是在這一反抗經濟全球化和藝術系統體制化的意義上,麥基將包括“罷工藝術”(strike art)在內的“占領”(occupy)稱為“后當代藝術”,以2011年為分界,區別于現行“當代藝術”的命名。麥基認為,“罷工藝術”不僅尋回了現已陳腐的當代藝術中逐漸中斷的先鋒藝術傳統,致力于反體制、反學院、反商業,挑戰藝術和非藝術的界限,同時,作為總體性藝術項目的后當代藝術(而非僅僅是當代藝術中的某種藝術現象),是從根本上對資本主義經濟基礎這一當代藝術化身的自反⑩。
在2014年發表的《論藝術行動主義》一文中,格羅伊斯提出用具有實用性的、活生生的“設計”取代去功能化的、僵化的“藝術”之名,用“設計的美學”取代“藝術的美學”,目的是以直接參與社會運動的激進藝術,在藝術系統之外尋找抗拒整體審美化(total aestheticization)幻象的革命性出口?。在格羅伊斯看來,當代行動主義藝術“是一種新狀況,呼喚新的理論建構”?。正是針對這一新狀況,尤其是“占領華爾街”以后的藝術現狀,麥基在其2016年的專著中使用了“后占領狀況”(post-occupy condition)一詞(明顯模仿“后現代狀況”)。不過,與此同時,隨著對行動主義藝術研究、理論建構和命名的細化,在該書中,麥基不再使用更為泛化的“后當代藝術”一詞作為對“當代藝術”的反抗,據此可以認為,麥基通過強化作為行動主義的“占領”,徹底放棄了從“當代”到“后當代”這一看似仍處于線性演進路徑中的命名方式。悖論在于,這種對“當代”的放棄,仍然是通過繞回線性演進的“后現代(狀況)”來實現其理論建構的。
二、“以客體為導向的本體論”路徑:作為“實在論唯物主義”藝術的“后當代”
盡管麥基放棄了對“后當代藝術”這一命名的使用,2016年,“后當代”議題卻隨著第九屆柏林雙年展(BB9)和蒙特利爾雙年展及其展評被觸發。其中,BB9策展團隊DIS藝術小組在其在線藝術雜志DIS上,邀請奧地利學者阿曼·阿瓦內西安和倫敦金史密斯學院的蘇海·馬利克,組織了一次探討“后當代”理論及藝術和設計的專輯?,開啟了不同于行動主義的建構后當代藝術的另一條路徑,這也是迄今為止對后當代理論最為集中的一次討論。而在此期間發生的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的政治事件,也被認為預示著作為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表征的歷史性的當代藝術的終結?。
阿瓦內西安和馬利克將“后當代”定義為“思辨的時間復合體”(speculative timecomplex)。這個詞由“思辨”和“時間復合體”兩部分組成,就“思辨”而言,這一定義基于“思辨實在論”(SR/Speculative Realism)及與之相關的“以客體為導向的本體論”(OOO/Object-Oriented Ontology),二者作為術語的活躍期均始于2010年前后,它們引領著西方理論界近年來的“思辨轉向”(speculative turn)?。簡言之,OOO和SR理論嘗試跳出以往客體和主體、唯物主義和形而上學、自然和人工等諸種二分法,尤其注重將技術作為一種客觀物/對象(object),是唯物主義哲學和形而上學的思辨在互聯網和數碼時代的有機結合。其理論出發點是批判笛卡爾至康德以來反客觀性的關聯主義(correlationism)?,其現實語境是后網絡(post-internet)和后真相(post-truth)時代對于知識、事實、真實的重審和試圖對真理(truth)的追回?。在此基礎上,這一思辨的后當代理論,將后網絡時代已全面技術化的時間本身視為客觀存在的物/對象,以區別于將時間視為僅存在于主觀意識中的某種認知關系的觀念,同時又強調這一時間不是過去、現在、未來這些單體元素的簡單物質性、線性拼湊,而是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集合,具備超出其中任何一個單體元素的系統特性。
那么,時間何以成為客觀存在的物?為了與關聯主義的形而上時間相區別,后當代理論的“時間復合體”借鑒了法國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關于社會技術系統與記憶工業的理論。斯蒂格勒認為,人類歷史就是“技術體系”不斷進化的歷史,技術發展在給人類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在不斷破壞穩定的人類文化,動搖和重構人類社會的基礎,而“時間性”正是在人性與技術這一既相互依存、又充滿不確定性的張力關系中得以彰顯的,“是技術的進步開啟了時間的擴延”?。比如,以照片或電影鏡頭這類“等同于時間的畫面”為代表,斯蒂格勒區分出凝結在影像中、具有不確定性的“第三記憶”(或稱“圖像意識”),即由技術發展而實現的記憶的物質性記錄,以區別于胡塞爾的“第一滯留”(即實時知覺)和“第二滯留”(即長時記憶)?。然而,技術的持續進步并不能許諾給人類一個進步的未來,人類在幻象及其破滅中“迷失方向”(disorient)。斯蒂格勒認為,“當代的迷失方向,是無力實現劃時代成倍增長的經驗,它同速度、同追求速度所導致的記憶的工業化、同為追求速度而開發的技術之特性息息相關”?。在這里,后當代理論借用了斯蒂格勒對于時間和“技術系統”關系的論述,認為作為個體的人和作為整體的人類經驗已不在社會復合體中居于首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包括非人的“技術系統”在內的復雜社會系統、包括互聯網在內的社會基礎設施和關系網絡?。在這個意義上,“后當代”正是因其非人化和與社會技術系統的依存,而區別于新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至上的“當代”。
后當代理論雖認同斯蒂格勒對社會技術結構的論述,但二者在對待技術與藝術的關系上存在分歧。首先,后當代理論對時間的研究并不依附于作為記憶影像的文化符號,反之,SR和OOO藝術的一大特點就是對文化符號及其社會政治權力闡釋模式的拒絕。哈曼主張回到作為物/對象的作品,而不再致力于闡釋作品和藝術家、社會、文化的關系?。SR和OOO理論的倡導者進而推出了“實在論唯物主義藝術”概念,其首個活動是2010年在泰特美術館舉辦的“實在物”(The Real Thing)短期展覽和研討,該活動主要探討非人類的宇宙議題,作品涉及死亡、人口縮減、語言失序等主題,是一次嘗試去人類中心主義的藝術實驗?。同為RMA的倡導者,馬利克更直接地提出“摧毀當代藝術”,因為“當代藝術是一種關聯主義”,這里的“當代藝術”指的正是基于文化闡釋、身份政治和個體經驗的“后觀念藝術”?。在馬利克看來,“藝術應當作為一種理性實踐,去除一切揮之不去的經驗狀況。概念,而非感覺;理性和形式化,而非放縱和失控;中立而不受影響:這就是理性的約束力,它直接導向現實(the real),摧毀不定性的當代藝術”?。其次,在與當代藝術的關系中,斯蒂格勒仍希望以審美經驗反抗記憶的工業化和社會技術系統的操控,而后當代理論在本質上反對以個人的、非實體的審美經驗作為救贖當下的出口,這正是基于對當下影像生產、體驗式經濟和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失望,“當代藝術已不僅是最近新自由主義經濟和政治記錄的受害者,更是以左翼批評的視角將其邏輯強加于各種標準之上,幫助構建了這一重組的矩陣(matrix),成為事實上的幫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區別在于,后當代理論的研究對象是時間的實體在場本身,而不是斯蒂格勒“第三記憶”意義上的“等同于時間的畫面”。
阿瓦內西安和馬利克所主張的回到時間在場本身,指的是回到一個確證的、客觀的“當下”(present)。首先,說這一后當代的“當下”是確證的,針對的是現代和當代以來批判的、解構的“當下”。后當代理論認為,從現代時間觀(以否定辯證法在持續的批判中被抽空實體的“當下”為代表)到當代時間理論(以德里達意義上解構的后現代或當代永恒缺席的“當下”為代表),無一不是對“當下的去優先化”。其次,說這一后當代的“當下”是客觀的,針對的是當代非實存的“當下”。后當代的“當下”是以時間復合體存在的客觀物,其中,實存的技術系統取代了非客觀的人類經驗,而當代的“當下”恰恰是對于時間的經驗,這一“當下”基于關聯主義想象,因陷入以過去看未來的幻象而造成了“當下”在事實上的缺席。因而,這一“后-當代”(post-contemporary)在構詞方式上類似于具有實體意義的“明天-今天”(tomorrowtoday)結構,“后-當代”即“以明天為導向的-今天”,它反對的是基于過去的推測而發生的現在,以及在當下到來之前就已被確認的、發生在過去的未來。最后需要強調的是,這一“當下”是以未來為導向的。這一后當代理論的“后”,針對的并非僅僅是物理意義上的前后次序,而且是在當前社會技術系統下的優先權,是preemptive一詞所對應的政治上的優先決策權,經濟消費中基于大數據和算法鎖定客群和分配人格、軍事和反恐行動中先發制人的“先”(pre)?。在這個意義上,阿瓦內西安認為,如果按照德文將“當代”一詞指認為“時間的同志”(zeitgen?ssisch),那么,“后當代”則是“未來的同志”,即“后當代”不再與早已被過去鎖定的那個非客觀、非確證的“當下”為伍,而是以全新的未來為逃離當代矩陣的出口。落實到藝術上,阿瓦內西安和馬利克認為,全面審美化的當代藝術本質上是“反未來”的藝術,而后當代藝術才是真正“以未來為方向進入當下”的藝術?。
三、同時代性/當代性路徑:收編“后當代”和“后占領”
與上述兩種試圖以后當代藝術來反抗和超越當代藝術的理論路徑不同,史密斯認為,后當代藝術的提出并非當代藝術的終結,相反,這不過是其“當代性”三重架構中一種新出現的復古現象。所謂“復古”,指的是這一藝術現象仍然是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一脈在當代的延續。史密斯認為,現代—后現代—當代—后當代的線性敘事在根本上仍是基于西方中心主義的,因而,與其說后當代是超越當代性的,不如說它是現代性在當代的復歸?。
20世紀80年代末,卡林內斯庫曾將面貌相悖的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先鋒派、媚俗藝術、頹廢描繪為“現代性的五副面孔”,在2000年的中譯本序言中,他又提出“現代化”是現代性的第六副面孔的可能性?。如果沿著卡林內斯庫現代性諸面孔的思路續寫21世紀的藝術現象,那么當代藝術、后當代藝術、當代性均可繼續成為現代性的第N副面孔。但是,在史密斯看來,當代藝術的當代性在主體和時空觀念上與現代性存在著徹底斷裂,他在2004年組織召開的“現代性≠當代性:20世紀之后藝術和文化的二律背反”(Modernity≠Contemporaneity:Antinomies of Art and Culture after the Twentieth Century)學術研討會首次將當代藝術的“當代性”議題從“現代性”中脫離并與之并置。
史密斯認為,當代性是諸種狀況(conditions)的合體,是與他人同在的我們生存于其中的復雜狀況:
它不再是“我們的時代”(our time),因為“我們”不包括它的矛盾性;它也不是“一個(單數的)時代”(a time),因為如果“現代”將自身定義為一個時期,并且把過去分成多個時期,在當代狀況下,分期則是不可能的。?
首先,史密斯的當代性與現代性的主體在分類依據上有著本質不同,現代性的主體是“全球”(globe),當代性的主體是“星球”(planet),這受到斯皮瓦克“星球性”(planetarity)理論影響。斯皮瓦克認為,全球化中的“全球”是在抽象想象中存在于電腦和互聯網上的、無人真實居住的虛擬空間,而人類實際生活在這一“全球”之外?。如果說現代和后現代時期的主體“我們”指的是“全球”(以及以歐美為中心的世界一體化趨勢,如“全球化”)、“國際”(以及國家集團組織,如“共產國際”)、“世界”(主要指對全球政治版圖的劃分,如“三個世界”戰略思想),那么這一現代和后現代時期的“我們”對地球空間的認知和劃分,仍建立在地緣政治的基礎上,是囿于國家與國家之間的(inter-national)、強調國家主體和現代秩序的、有疆界和限制的。因為人類與“全球”的關系在根本上是二元對立、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主客體關系,這一“全球”就不可避免地成為外在于人類責任感和生命可持續發展訴求的、進行不平等利益交換的政治空間,這一“全球化”的結果必然是趨于一致的同化。
與之相比,“星球性”中的“星球”則強調將地球作為一種去除了地緣政治區隔和經濟利益交換的自然空間(natural space),人類并非操控者或征服者,而是借住其上的棲居者?。在這個意義上,作為現代性主體的“全球”是政治性的,是有利益差異的政治經濟體在競爭和趨同原則下尋求共識性(consensus),而作為當代性主體的“星球”則是天然的(natural),是無利益差異的同時代人(coeval)在合作和共存原則下尋求他異性(alterity)。如果說前者是在利益差異的基礎上尋求有限的一致性,那么后者則是在利益一致的基礎上尋求無限的可能性。
其次,就當代性作為多重復雜狀況而言,繼現代性創傷和后現代主義衰微之后,“當代藝術”和“當代性”的英語表達均不再冠之以“主義”(-ism),抽象的宏大敘詞讓位于當代藝術對當代生活和思想的復雜多元重疊狀況的圖繪。在對時間和空間的認識上,這一復雜狀況與從現代性到后現代狀況的線性敘事有著根本架構和認知維度上的不同。在認知維度層面,史密斯的當代性在空間上基于“星球性”(而非政治經濟意義上的“全球化”空間),追求多元共存(而非多元競爭);在時間上則基于對多樣的時間性或作為復數的時間觀(temporalities)的一視同仁(而非以過去—現在—未來的線性發展敘事和求新的進步觀作為唯一評判體系),追求異時共存(而非抹殺異時價值):“當代性在于感知力的徹底分裂(這一分裂是日益增長、無處不在、持續存在的),在于對同一個世界不同的觀看和評判方式,在于不同時間(asynchronous temporalities)實際上卻同時存在,在于多元文化和社會多重沖突的偶發可能性,在于所有這一切所彰顯的迅速增長的失衡。”?
那么,對應到系統架構上,史密斯將當代社會已無可避免的現代性—當代性的線性發展視為當代性或“當代狀況”中的一個脈絡、一種歷史資源或問題的遺存,而不是一以貫之的全部當下狀況。具體就當代藝術架構而言,與基于現代—后現代—當代—后當代線性發展的“當代藝術”命名不同,史密斯嘗試以當代性理論圖繪一個能夠容納當下不同時空價值觀的世界圖景,即居住在同一個星球的同時代人,以基于不同的文化、歷史邏輯、時間觀和維度的發展狀況,生發出的不同藝術脈絡和藝術現象。與卡林內斯庫為現代性描繪諸種面孔的架構方式類似,史密斯為當代性描繪了三種當代藝術的框架,而相比于卡林內斯庫,史密斯的每種框架之下又包含了當代藝術的更多副面孔。此外,在不同框架之間,史密斯更以康德的二律背反(antinomy)將三者聯系成為一個有機又充滿悖論的整體,在這個意義上,史密斯的當代性可稱為當代藝術的三種悖論,它們是共存于當下的三種趨勢,也是三股彼此矛盾、朝不同方向運動的力量?。
第一種趨勢是當代持續存在的現代主義藝術,指基于戰后歐美藝術范式的演進、在當今作為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表征的當代藝術。從時間上看,這一趨勢始自20世紀50年代后期,以反權威、反藝術神話、反個人英雄主義、反精英敘事為特征。從地域上看,這一趨勢發端于歐美,隨著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影響著其他后發國家的當代藝術創作。就藝術風格而言,它發生在抽象表現主義藝術衰落(波洛克1956年去世)之后,經歷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晚期現代藝術(包括情境主義、新現實主義、新達達、偶發藝術、行為藝術、波普藝術、極少主義、大地藝術、貧窮藝術、觀念藝術、政治介入藝術、批判體制藝術、女性主義藝術等)、20世紀80年代的后現代藝術(包括新表現主義、超前衛、照相寫實主義、圖像一代、街頭藝術等)、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復古感官主義(或稱“懷舊煽情主義”“仿真主義”,以英國YBA、杰夫·昆斯、馬修·巴尼等為代表)、再現代主義(remodernism,以新形式主義、理查德·塞拉等為代表)和景觀建筑(spectacle architecture)。這一趨勢的特點是有著清晰的從現代藝術發展至今的藝術脈絡和一以貫之的藝術邏輯,常被當代藝術教科書奉為唯一正統,而其本質是西方中心主義在當代的延續,詹姆斯·埃爾金斯稱之為“北大西洋藝術”?。
第二種趨勢是轉變中的跨國藝術,指后殖民轉向以來,前殖民地和歐美周邊國家在沉重的歷史、文化、記憶的基礎之上,關注本土和全球之間的沖突和生存體驗等議題,更多強調身份政治的當代藝術。相比第一種趨勢自歐美向全球的拓展,第二種趨勢更強調在地性,它甚至是反全球化的。從時間上看,這一趨勢在不同國家發端的時間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不等。從地域上看,與發生在歐美的第一種趨勢相比,第二種趨勢發生在前蘇聯和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以及史密斯所稱的“第四世界”(指穿梭在不同國家和文化間的移民、散居者、流亡者)。就藝術風格而言,第二種趨勢常借鑒第一種趨勢的當代藝術“風格”,但更注重傳達多元意識形態、國家、身份等內容。因而,與第一種“風格”演進清晰的當代藝術趨勢相比,第二種藝術趨勢的特點是“以內容為導向”(content-driven)、為本土文化發聲、關注差異和不同、展現當代生活中沖突的多樣性。
第三種趨勢是真正具有當代性的藝術,指進入全球互聯網時代以來,新一代藝術家打破地域限制,共享情感和交流網絡,表達全球共同的當代體驗,關注涉及人類共同利益的議題(比如生態環境、社交媒體、國際政治、新科技等)。這一始自21世紀的最新藝術趨勢,雖然比前兩個趨勢更為后發,但勢頭強勁。如果說前兩種趨勢均基于各自的文化和歷史脈絡,是過去的藝術范式在當代的滯后和延續,第三種趨勢則屬于年輕人的、具有新生力量,它輕裝上陣,面向未來,充滿希望。
相比之下,第一種趨勢可對應現代主義以來的全球同質化,它扎根于深厚的歐洲經典文化藝術資源,基于西方中心主義,抹殺個體差異的求同,以達成共識為目的;第二種趨勢可對應后現代主義開啟的身份多元化,它背負沉重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苦難,基于后殖民轉向,強調個體差異的對抗,以撕破共識的虛偽性為目的;第三種趨勢則是21世紀以來同代人作為命運共同體的差異性共在,它既無傳承深厚文化資源的精神使命,也無承擔沉重歷史文化苦難的身份訴求,而是基于“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或“星球性”(即反對政治化的全球性)、在生存利益一致基礎上的多樣性共存,以達成充分保障個體差異的共通性為目的。
史密斯這一宏大的“當代性”架構體系在其2001年離開悉尼大學的告別演講中初露端倪;在2009年的“中國當代藝術·國際論壇”上,史密斯闡釋了對“世界藝術:當代潮流”的三分法?;其完整的“當代性”體系則在2011年出版的當代藝術史教科書《當代藝術,世界趨勢》中呈現出來。此后,在上述當代性三種悖論的基礎上,史密斯繼續以關鍵詞的方式不斷豐富其“元世界圖像”(meta-world picture),即“當代世界圖景”(world-picturing)的三種元圖像(metapicture),2019年更新了最新版本(見下表)?。其中,史密斯將“后當代”納入第一種世界圖景的元圖像(即“持續的現代性”),在藝術風格上對應第一種當代藝術趨勢,即基于西方中心主義的“北大西洋藝術”;將“占領”列入第三種世界圖景的元圖像(即“同時代的差異”)中,這似乎解釋了行動主義藝術以“后占領狀況”取代“后當代藝術”所彰顯的試圖跳出西方中心主義藝術模式、轉而強調同時代人共享和創造真正具有當代性的當代藝術的訴求。

泰瑞·史密斯的“當代性:元世界圖像”表
結語:重回真實的可能性及其問題
可以看到,基于將當代藝術理解為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表征這一共識,以及對當代藝術的市場化和體制化的反抗、對依賴于復雜技術系統的后網絡和后真相時代的反思,2010年以來出現了兩種以“后當代藝術”為名反抗當代藝術的理論嘗試。第一種行動主義的路徑,試圖徹底顛覆當代藝術體制、打破自啟蒙運動以來日益審美化的藝術概念桎梏。第二種基于“思辨實在論”和“以客體為導向的本體論”的后當代藝術理論,以互聯網時代客觀存在的技術系統對抗非客觀的、與新自由主義合流的個人審美經驗,以“當下”作為“時間復合體”的客觀實體性,反抗非實體的關聯主義文化符號闡釋。二者作為反當代藝術或持續拓展“當代藝術”命名的新嘗試,均試圖以不同于此前已達成共識的當代藝術敘事,為正在發生的當代藝術敞開更多可能性。
這兩種后當代藝術路徑的共同之處在于:反對作為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或被稱為“新封建主義”)表征的當代藝術,反對21世紀以來全面體制化的當代藝術,反對流水線式可預期的、幻象的、全面審美化的、屬于特權者的未來。不同的是,行動主義的后當代藝術以述行(performing)的方式實踐對市場化和體制化的反抗,而基于“思辨實在論”的后當代藝術則寄身于后網絡時代與技術系統絞合在一起的“時間復合體”本身,反對的主要是強調身份政治、個人經驗和符號闡釋的后觀念藝術。
二者共同的問題是,當這兩種后當代藝術理論落實到具體作品上,迄今尚未形成突破性的影響。行動主義的后當代藝術因化身為政治運動而使其行動本身失去了藝術價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格羅伊斯稱其為“設計”而非藝術。基于“思辨實在論”的后當代藝術則一方面主張排斥藝術體驗,回歸理性、知識、形式、概念等可確證的對象,另一方面執著于不加評論地展示客觀的“當下”,而使在其理念指導下的藝術要么成為復歸理性的新形式主義(也被稱為“僵尸形式主義”),要么成為與仿真(simulation)合謀的后網絡時代的日常生態?。第九屆柏林雙年展“變裝的當下”(The Present in Drag),即在后一理論指導下不加批判地呈現互聯網、技術、消費無所不在的后網絡時代的“當下”,而使展場變成了毫不回避商品營銷的賣場。
那么,如果說行動主義的后當代藝術以化身為政治運動的方式瓦解了當代藝術,“實在論唯物主義”的后當代藝術以化身為后網絡時代技術與消費狂歡的方式消弭了當代藝術,史密斯則以其作為當代性表征的三種當代藝術架構,反向收編了后當代藝術。史密斯的當代性討論及其理論架構,試圖將上述兩種后當代藝術全部納入其中,其構建當代世界圖景的三種元圖像,可以說是目前學界對當代藝術最為系統的理論化建模。其中,現代性在當代演進的現代—后現代—當代—后當代這條脈絡,僅作為當代性與當代藝術三個主要框架中的一種,即當代持續存在的現代主義藝術。如果如卡林內斯庫所說,“現代性只是又一個用來表述更新與革新相結合這種觀念的詞”?,那么史密斯的當代性則是對現代“求新意志”(及作為其源頭的西方神創論意義上的“新”)的唯一正統性的終結。與這種求新的現代性在當代的持續發展并行、共存的,還有基于后殖民轉向的“轉變中的跨國藝術”,以及基于“星球性”和數碼時代跳出地緣政治及冷戰思維的真正具有同時代性/當代性的藝術。就對“當代藝術”和“當代性”概念的使用而言,在史密斯看來,“當代藝術”一詞與“當代性”一詞中的“當代”有著本質區別:“當代藝術”的“當代”作為形容詞,它的實體始終不可避免地處于缺席、游離、空洞的狀態,永遠留有一個等待被填充的空間;而“當代性”的“當代”則是西方語言中“當代性”(contemporaneity)一詞不可分割的主體,它自成實體,本身就是充滿了復雜性和多重向度的當下在場(presence)。
盡管史密斯的理論力求在差異共存中超越地域偏見和政治版圖,然而顯見的是,其“元世界圖像”體系仍然難以避免對“他者”的持續建構。比如,其中被界定為“反向現代化”的中國當代藝術,可以說再一次遭遇了西方理論的誤讀與持續的后殖民想象。國外學者對中國當代藝術作品解讀中的這種虛擬敘事并非特例,高名潞曾舉例說:“2005年匹茲堡當代藝術國際研討會上,詹明信(即杰姆遜)就用中國女藝術家尹秀珍的作品反復強調全球化的在地這個命題;泰瑞·史密斯思辨地論證王晉的攝影作品如何再現了人的主體性和現代性之間的悖論關系,以及人性如何被全球化經濟所異化。這種思辨方法一般不注重藝術家的最初想法,所以和藝術家的創作意圖,也就是真正的在地邏輯其實并沒有太多關系。”?而針對史密斯將“當代性的藝術”定義為“一種文化的無家可歸者的狀態”,高名潞犀利地指出其中存在的身份問題:“這種‘文化的無家可歸者’貼切地表達了類似當代澳大利亞(史密斯的國籍)這樣一個‘沒有英國歷史的英屬殖民地’的文化身份感受,而非全球的、普遍性的當代經驗。”?
縱觀歐美學界后當代藝術的諸種探索可以看到,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已成范式的主流當代藝術在西方學界持續面臨著危機。無論是“后當代”還是“當代性”的理論嘗試,都是對從20世紀后半葉至21世紀第一個十年間建構起來的市場化、體制化、后網絡時代作為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表征的“當代藝術”概念的反抗。這一危機既意味著終結,也意味著機遇與挑戰,意味著一種可稱為“北大西洋藝術”模式的危機或終結,一種他異性文化與藝術資源可能性的回溯與發掘。而這一“當代藝術”概念的危機及對其命名的反抗,并非更廣義的、實踐意義上的當代藝術的危機,恰恰相反,這是對真正在世界范圍內活躍的當代藝術實踐的再思考,是將更具實體性和在地性的、更真實的當代藝術現象凝結為新的藝術理論和藝術哲學的新嘗試,是后網絡、后真相甚至后疫情時代對當代藝術何以與真正的時空俱進、當代藝術理論何以重回在場等現實問題的持續推進。那么,在此國際語境中,非西方學界應當基于何種真實的在場為“(后)當代藝術”貢獻何種智識資源,亦是一個亟待當代中國學者思考的問題。
① Graham Harman,“Fear of Reality:On Realism and Infra-Realism”,The Monist,Vol.98(April 2015):126.
②? Terry Smith,Art to Come:Histories of Contemporary Art,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19,pp.304-305,pp.355-361.
③④⑤⑥ Liam Gillick,“Contemporary Art Does Not Account for That Which Is Taking Place”,Industry and Intelligence Contemporary Art Since 182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6,pp.2-3,p.2,p.9,p.117.
⑦ Hal Foster et al.,“Questionnaire on‘The Contemporary’”,October,Vol.130(Fall 2009):64-65.
⑧⑩ Yates McKee,Strike Art: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Post-Occupy Con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Press,2016,pp.29-32,pp.66-68.
⑨ Yates McKee,“Debt:Occupy,Postcontemporary Art,and the Aesthetics of Debt Resistance”,South Atlantic Quarterly,Vol.112,No.4(2013):784-803.
?? Boris Groys,“On Art Activism”,In the Flow,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Press,2016,pp.43-60,p.45.
? Armen Avanessian and Suhail Malik(eds.),The Time Complex:Post-contemporary,Berlin:Merve Verlag Press,2016.
?? Saelan Twerdy,“Morbid Symptoms:In Search of the Post-contemporary at the 2016 Montreal Biennial”,Momus,November 22,2016,https://momus.ca/morbid-symptoms-in-search-of-the-post-contemporary-at-the-2016-mont real-biennial/.
? 格雷漢姆·哈曼在1997年首次使用“以客體為導向的哲學”(OOP/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一詞。2006—2009年,伊文思(Aden Evens)和布蘭特(Levi Bryant)開始使用“以客體為導向的本體論”一詞,自2010年在喬治亞理工大學召開首個專題會議后,該詞在西方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思辨實在論”與之并行,倫敦金史密斯學院在2007年召開同名工作坊,2010年哈曼編輯出版了同名文集。Cf.Graham Harman,Speculative Realism:An Introduc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18,p.9.
? 梅亞蘇認為,西方哲學至康德為止,要解決的主要問題首先是對實體的思考,從康德以來,發生了否定樸素現實論的轉折,從此,思考主客體關系的相關性成為西方哲學第一位的問題,而這一日益偏離了樸素現實論的相關主義(或關聯主義),正是OOO和SR群體所反對的哲學基礎。梅亞蘇認為,“現代哲學的‘舞步’的核心,就存在于對關系之優先性這一觀念的信仰之中,那是一種對相互關系的建構之力的信仰”,“任何一種哲學理論,只要它否定樸素現實論,就都可能被視為相關主義的變形”,“只要是持守這種認為相關性具有無法被超越的特性的思想傾向,我們都將其稱為相關主義”(甘丹·梅亞蘇:《有限性之后:論偶然性的必然性》,吳燕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5頁)。
? Graham Harman,Object Oriented Ontology:A New Theory of Everything,London:Penguin Random House,2017,pp.3-4.
?? Bernard Stiegler,Technics and Time,2:Disorientation,trans.Stephen Barker,Redwoo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1-2,p.7.
? 李洋:《電影與記憶的工業化:貝爾納·斯蒂格勒的電影哲學》,《上海大學學報》2017年第9期。
???? Armen Avanessian and Suhail Malik(eds.),The Time Complex:Post-contemporary,p.7,pp.37-38,pp.13-15,p.36.
? Graham Harman,“Art and OOObjecthood”,in Christoph Cox,Jenny Jaskey,Suhail Malik(eds.),Realism Materialism Art,Bard/Berlin:Sternberg Press,2015,pp.102-104.
? Christoph Cox,Jenny Jaskey,Suhail Malik(eds.),Realism Materialism Art,p.27.
? 后觀念藝術(post-conceptual art,或譯為“后概念藝術”),即觀念藝術之后的藝術。這里的“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或譯為“概念藝術”)指的是20世紀60年代主張回歸藝術語言和智性思辨的藝術思潮,以約瑟夫·科索斯(Joseph Kosuth)和“藝術與語言小組”(Arts&Languages)等觀念藝術家為代表。后觀念藝術繼之而起,反對回歸單純的藝術思辨,強調面向復雜的現實世界,在藝術創作中表達多元身份、個性感受和個體經驗。后觀念藝術的興起也被部分當代藝術研究者認為是現代藝術與當代藝術的分水嶺。Cf.Peter Osborne,Anywhere or Not at All:Philosophy of Contemporary Art,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Press,2013,pp.24-27.
? Suhail Malik,“Reason to Destroy Contemporary Art”,Realism Materialism Art,p.191.
?? 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藝術、后現代主義》,顧愛彬、李瑞華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3頁,第361頁。
?? Terry Smith,“Introduction:The Contemporary Question”,in Terry Smith,Okwui Enwezor and Nancy Condee(eds.),Antinomies of Art and Culture:Modernity,Postmodernity,Contemporaneity,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8,p.8,p.9.
? Gayatri C.Spivak,Death of a Disciplin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p.72.
? Terry Smith,“Defining Contemporaneity:Imagining Planetarity”,The Nordic Journal of Aesthetics,Vol.24,No.49-50(2015):168-172.
? Terry Smith,Contemporary Art:World Currents,London:Laurence King,2011,pp.8-13.
? James Elkins,The Impending Single History of Art:North Atlantic Art History and Its Alternatives,to be published by de Gruyter.http://www.jameselkins.com/index.php/experimental-writing/251-north-atlantic-art-history.
? 泰銳·史密斯(即泰瑞·史密斯):《背景敘述:現當代藝術,世界趨勢,中國》,陳漫兮編:《什么是中國當代藝術?2009中國當代藝術理論批評研討會論文文集》,四川美術出版社2010年版,第339—341頁。
? Terry Smith,“Defining Contemporaneity:Imagining Planetarity”,The Nordic Journal of Aesthetics,Vol.24,No.49-50(2015):165.Terry Smith,Art to Come:Histories of Contemporary Art,pp.355-356.
?? 高名潞:《西方藝術史觀念:再現與藝術史轉向》,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44頁,第5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