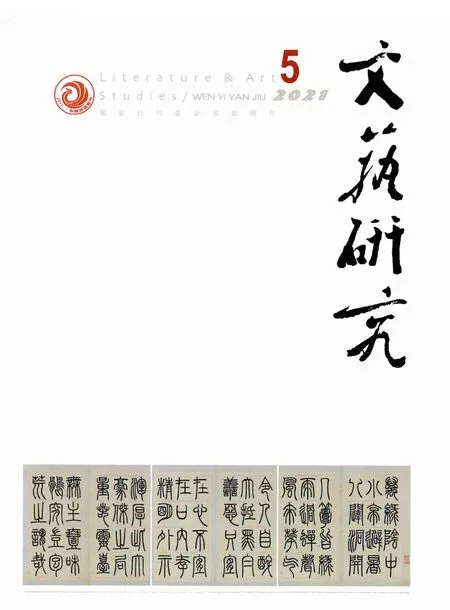克拉考爾的“羊皮書”:蒙太奇、現實與歷史書寫
——重讀《電影的本性——物質現實的復原》
孫 柏
一、克拉考爾的“羊皮書”
迄今為止,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的《電影的本性——物質現實的復原》(Theory of Film:The Redem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以下簡稱《電影的本性》)仍是電影理論史上一部地位尷尬的著作。一方面,它自1960年出版后不久就被奉為經典,是涉足電影研究的人文學者無法繞過的巔峰之作;另一方面,它雖然被無數次地、反反復復地閱讀,卻幾乎沒有人能夠讀懂。“物質存在”“生活流”“攝影機-現實”“風吹樹葉,自成波浪”等說法為人們所耳熟能詳,但是內在于克拉考爾著作的何謂“現實”的理論難題,不是被過于輕忽地納入既有的現實主義來吸收,就是被草率地當作無法自洽的概念缺陷而拋棄。就連克拉考爾的摯友阿多諾都譏刺他這方面的思想是一種“天真的現實主義”①,這在很長時間里幾乎成為對他的一種定評②。
這一局面在相當程度上是由《電影的本性》中不穩定的“現實”概念造成的。表面上看,這部著作的寫作目標和基本內容很直接明了,克拉考爾說,“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深入考察照相性質的影片的真正本性”,“電影按其本質來說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樣,跟我們的周圍世界有一種顯而易見的近親性。當影片紀錄和揭示物質現實時,它才成為名副其實的影片”③。克拉考爾不僅排斥電影的一切形式化實踐,甚至認為電影史上的絕大部分作品都因為或多或少的人為干預特征而損害了“攝影機-現實”的非藝術品質。因此,克拉考爾是從電影的內容而非形式出發,嘗試去建立一種“實體的美學”,由于照相與世界的這種近親性,電影的本性即由作為其拍攝對象的內容所決定,電影幾乎等同于它所記錄和揭示的物質現實。

克拉考爾《電影的本性》書影
然而,克拉考爾之所謂“現實”并不像表面呈現的這樣簡單。在整部《電影的本性》中,到底何為“現實”,其實語焉不詳,或者說始終存在兩種不同的理解方向。一方面,它似乎被當作不言自明、無可爭辯的事實存在而接受;另一方面,在與克拉考爾的真正思考連接得更為深刻的地方,它卻又因為歷史本身造成人類生活既有現實的毀滅和墮落而遭到拒絕。也就是說,《電影的本性》之所謂“現實”,在哲學的層面上,是有著明確的現象學視域作為理論支撐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物質現實;而在歷史的層面上,又緊密關聯著19世紀末以來“西方的沒落”、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帶給人類的空前浩劫。如果不能認識到克拉考爾是在“奧斯維辛之后”人類文明的絕境中寫下這部著作的,就無法真正理解他所說的“物質現實的復原”(這里的“復原”一詞為redemption,實即帶有強烈宗教意味的“救贖”)究竟意味何在。《電影的本性》誠然是一部電影理論的恢弘巨著,然而若僅在電影研究的界限之內來閱讀,恐怕永遠無法抵達它的真義:克拉考爾的確自始至終都在談論電影,但這是作為彼岸受到召喚的電影,而此岸的現實及其歷史則被懸置。
事實上,克拉考爾的《電影的本性》只能被當作一部思想著作來閱讀,它所提出的命題關乎歷史,關乎電影媒介的本體論與他那個時代的人們所身處的歷史維度之間的根本聯系,而現實的存廢就位于這一根本聯系的關節處。這樣一項任務與其說是體現于它所論述的內容(電影),不如說是由它的整個書寫形式所決定的,準確地說,是由它的書寫策略(借由“攝影機—現實”來實現的耦合)所決定的。針對《電影的本性》的這種書寫策略,米里亞姆·漢森(Miriam Hansen)給出的定位頗具參考價值。她指出,克拉考爾的這部著作帶有一種根本的“羊皮書性質”(palimpsestic quality)④,它不能僅僅通過其自身獲得理解,而是必須被放置到龐雜的互文關聯和時代語境中重讀,唯其如此,才能使它不再只是作為一段過往“歷史”的陳跡被束之高閣,而重新成為“我們自己的歷史的一部分”⑤。漢森格外強調,《電影的本性》并不是一次成書的文本,反復書寫、修訂、增刪使這部著作最終變成了一個體量龐大的超文本,最終付印的文字和那些被劃掉、抹去的痕跡共同構成一次次復雜的難題性的展開。面對這部著作,我們不能僅限于在那些已然凝固、靜止的表述中去提取意義,因為這里沒有真正的一次性給定的答案,而是不得不去探尋那些從印刷的文本中消失的內容——那些被放逐出去的幽靈般的存在,最終會以某種不可預期的方式歸來,到那時,由那些幽靈消失處的空白所決定、所書寫的《電影的本性》,也將以一個全新的面貌回歸。
如果沿著漢森提示的“羊皮書”式的理解路徑,我們不難發現,第一個提出應對《電影的本性》一書進行跨躍式閱讀的,實際上就是克拉考爾本人。他在晚年不期然間覺悟到,關于“照相的方法”的討論幾乎成為貫穿他畢生思考的一條重要線索。作為思想著作的《電影的本性》,必須在與克拉考爾的身后遺作《歷史:終結前的最終事》(History:The Last Thing Before the Last,1969)的對照閱讀中,才能真正顯現出它的意義和價值所在。而且,在克拉考爾個人的著作序列里面,《電影的本性》的核心關切也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早期著述。在《歷史:終結前的最終事》開篇,克拉考爾便坦陳:
近來我突然發現對歷史的興趣實際產生于我在《電影的本性》一書中試圖思考與挖掘的一些觀點。……某一瞬間我認識到,歷史與攝影媒介、歷史現實與攝影機現實之間存在很多相似之處。后來,我不經意間重讀自己《論攝影》的小文,發現自己在20世紀20年代的這篇文章里就已經對歷史主義和攝影進行了比較,這讓我非常震驚。
克拉考爾認為,歷史和攝影致力于一個共同的目的,那也是他本人數十年來的紛繁著述所試圖達成的一個共同目的:“使那些由于尚未命名而被忽略或誤判的生存模式和目標得以復原。”⑥
從錯誤的現實概念以及誤入歧途的歷史觀念的覆蓋下,去重新發現那個“未知領域”(terra incognita),是歷史與攝影可以互相觀照的共有能力。更為重要的是,這兩者之間不僅存在著一種隱喻的關系,而且就像克拉考爾1927年的《論攝影》(Die Photographie)中那句被廣為引用的格言所表達的那樣:“轉向攝影是歷史孤注一擲的賭博。”⑦可以說,正是攝影媒介的問世給了歷史一個自我救贖的機會,攝影媒介本身實際介入和參與到歷史的構建過程之中,從而有可能形構一種新的歷史形態,或者不妨極言之——歷史本身攝影化了。攝影幫助歷史徹底告別一切帶有線性時序因果的目的論,盡可能地擺脫政治、經濟、社會范圍的規定框架,轉而去接近日常“生活世界”。歷史充滿偶然性,其意義也不確定,特別重要的是,“歷史現實實際上是無止境的,產生自一片昏暗地帶,不斷地向后退縮和向前擴展至開放的未來”⑧。攝影和電影之所以蘊含著這樣的可能性,是因為作為它們媒介本體特征的記錄和揭示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將人的主觀意愿強加給這個世界。和包括安德烈·巴贊在內的許多同時代的思想家一樣,克拉考爾提出這樣的歷史思考,是以資本主義的現代性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帶給人類的空前毀滅為背景的,如果人類文明自我成就的這些內容被稱作“歷史”的話,那么這樣的歷史是毫無希望而毋寧被拋棄的。《電影的本性》便以攝影和電影媒介自身的名義加入到這一反歷史的歷史書寫中。
二、重思“照相的方法”
關于“照相的方法”的討論實際上貫穿了克拉考爾的整個著述生涯:從早年《法蘭克福報》時期的《論攝影》,經過《電影的本性》寫作期間單獨發表的《照相的方法》(1951年),再到《電影的本性》最終完成稿中的更新版本,最后是《歷史:終結前的最終事》的核心章節。由于克拉考爾將電影的本性定義為照相的延伸,這組互文性論述在他的電影本體論和歷史哲學中占據著極為核心的位置。在《電影的本性》中,克拉考爾一再重申:攝影的基本特性就是記錄和揭示。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似乎更多是在對攝影媒介的發展脈絡進行梳理的時候,作者不得不從他所敘述的歷史中接受的一個認識。而在《照相的方法》⑨和《歷史:終結前的最終事》⑩這兩個文本中,克拉考爾自己也會使用“天真的現實主義者”這一說法,來指稱那些自19世紀以來堅信攝影就是“給自然照一面鏡子”的持論者。可見,克拉考爾對于照相本性的看法從來都不是定于一尊、確鑿無疑的。
在1927年的《論攝影》中,“現實”還不是中心概念,實際上,在那篇文章的具體表述中,它的位置是被“自然”或“自然元素”所占據的。克拉考爾的思考是通過對“記憶圖像”和攝影的辨析,圍繞歷史展開的。一幅攝于1864年的祖母的照片,在歲月的流逝中,被剝奪了它得以被拍攝下來的那個具體的時間和空間,它不再是現實本身,而是不可挽回地淪落為現實的灰塵。在這樣的情形中,攝影總是與“記憶圖像”相抵牾,因為后者必然攜帶著為前者所過濾的歷史的紋理;這倒并不是說,記憶圖像總是會處在一個充滿細節的時空流轉過程中,而是說它總是與特定主體的真實性內容緊密地關聯在一起———一個人會記起什么樣的過去,總是因為那個過去的時刻對他(她)而言有著特殊意義。但是“攝影再現”以一種完全外在的機械性接管了這種主觀視角,這也正是克拉考爾在后來重建給祖母拍攝一張照片的場景時,特意要引入《蓋爾芒特家那邊》中的那個著名段落的原因。在那里,普魯斯特的“主要用意是要描繪一種心理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我們完全被不由自主的回憶所壓倒,以至于無法看清我們周遭的事物”?。這句話呼應了1927年文本中的一些重要表述,例如:“記憶并沒有把一個事件狀況的總體的空間表現或者時間進程考慮在內。”?在克拉考爾復雜的、經常過于纏繞的論述脈絡內部,這樣的文字貫穿起一些連續一致的思想線索。在這里,“記憶圖像”并不理所當然地具有倫理優越性,“周遭的事物”,即當前處境本身,決定了現在與過去的復雜關系,而主觀的盲目則使人完全無法切入這一外在性的部署中,因而也喪失了通過真正主體性的介入來改變它的機會。借助“記憶圖像”和“攝影圖像”的對比,克拉考爾已經在提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辯證關系:“個人”始終需要被作為一個社會學范疇來考慮;從個人的角度規避社會(比如作為歷史的一種再現形式的懷舊),折射的只是對共同體正日趨瓦解這一事實的征候性拒絕。
根據同樣的辯證原則,克拉考爾也謹慎地保持著對攝影圖像的警惕審視,他對電影女明星純粹供人消費的圖像的分析就發揮著這種制衡作用。較之于家庭相冊中作為個人私藏的祖母照片,女明星的圖像從一開始就陷入社會性的裹挾——以畫報雜志為載體的過剩圖像的“暴風雪”——之中。她,準確說是“它”,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已經徹底疏離了為攝影媒介提供基本相似性保障的那個真實的生命(漢森特別指出,在克拉考爾的上下文里,畫報上的女明星圖像的參照物也不是她本人,而已經是電影銀幕上的形象了,這一圖像的實質最終不過就是印刷品上的點陣?),而且還進一步被鋪天蓋地的類似圖像(度假酒店、名人政要、親子生活等等)所淹沒。在克拉考爾稱之為“并置”(Nebeneinander)的影像形態之下隱含著某種真正的恐懼,不僅是面對消失和死亡的恐懼,因為圖像被從事物自身剝離,而且是對攝影提供的“順勢療法”本身的恐懼,它以承諾保存世界的方式讓世界死去:
每個記憶圖像都會使人想起對死亡的回憶,而照片通過堆砌禁止了對死亡的回憶。在畫報中世界變成了可以被拍攝的現在,而這被拍攝下來的現在完全被永恒化了。被拍攝下來的這個現在已經從死亡中被搶救過來;實際上它臣服在死亡腳下。?
因此,在攝影媒介所展現的潛能中,實際存在著兩種死亡:直接由鏡頭帶來的死亡和剪輯(克拉考爾所描述的“并置”)造成的死亡。影像本身就意味著一種木乃伊化,是在人還活著的時候便已為他/她制作好的死者面模,所有看上去活生生的面孔之下無不先在地隱藏著一顆“死神的頭顱”;剪輯呈現的則是死亡的死亡:對死亡這一自然權利的剝奪是現代性最極致的罪愆,它的集中表現就是奧斯維辛——那堪稱理性精神、科學主義和科層制管理的高度結晶的成果。影像的機械復制生產也內在于資本主義的工業社會機制,特別是它的“暴風雪”式的堆砌,以一種滑稽模仿的姿態展示整個世界本身的碎片化。
因此,克拉考爾關于照相本性的思考從一開始就包含一個真正棘手的難題,這也是他在《論攝影》中不規律地將論述對象從攝影引向電影的含混嘗試所凸顯出的難題,在這里,電影成為了攝影的潛能,而它所依據的原則卻遠遠超出了所謂“照相的本性”,而寄身于與之對峙的一面:剪輯。在文章開篇不久,克拉考爾假設未來會出現一種與歷史主義相對應的“大電影”(Riesenfilm),它作為對時間的攝影,“能夠全方位地拍攝下在時間上相互關聯的所有事件”,因為“根據歷史主義,內在時間流逝的完全反映同時就隱含著在這一時間內進行的內容的意義”?。就電影理論的自身脈絡而言,我們可以認為,克拉考爾1927年提出的這類表述已經預示了巴贊著名的“完整電影的神話”以及“鏡頭段落”等概念了。但是在文章結尾,電影(而非攝影)再次受到作者的召喚,卻被委派去執行另外的任務:由于照片的總體性只是實現了“自然的一般存貨目錄”,那么將事物有效組織起來的工作就可以托付給電影。真正對位地解決畫報因胡亂拼貼而制造的混亂的就只能是電影,盡管它還需要在恢復事物的正常秩序和提供陌生化的“夢境”之間艱難權衡:
反映在照片里的廢物的混亂只有通過復興自然元素之間的每個慣常關系才能整理清楚。激活這些自然元素是電影的其中一個可能性。在每一處部分和片斷拼接起來組成陌生畫面的地方,電影就實現了這樣的可能性。?
這種論述張力在《電影的本性》中被大大削弱。如果我們對比閱讀關于“照相的方法”的文字在不同文本之間的細微出入,就可以具體感受到這一變化。參照1951年單獨發表的《照相的方法》,《電影的本性》完成稿里消失的不僅是“天真的現實主義者”的措辭,同時被弱化的還有關于攝影一個重要方面“即時攝影”(instantaneous photography)的理解。19世紀,即時攝影的發明徹底改變了攝影機與拍攝對象的時間關系。在即時攝影出現以前,由于曝光時間過于漫長,“攝影機-現實”便只能局限于風景,而人像攝影則淪為一種可怕的象征性死亡過程——因為每一次照相都意味著一個隨時間自然延展的生命被壓縮進一個凝固的時空鑄模。這和電影的媒介特質正好形成鮮明對照:由于畫格與畫格之間的間隙以及填充這間隙的黑暗,電影制造的是“一秒鐘24次死亡”?。電影的媒介可能性是以即時攝影為技術前提的,籠統地談論“照相的本性”缺乏必要的嚴謹,因為電影只能是“即時攝影”的延伸,而不是一切照相的延伸。即時攝影的另一個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將影像從一個時空連續體中切割并分離出來,另一方面,它還能使這被孤立的局部影像繼續保持對世界完整性的暗示。在《電影的本性》中,克拉考爾把對即時攝影的強調挪到了另一段文字中?,而且刪除了對英國光化學家威廉·阿布尼(William Abney)專題著作的引用;更重要的是,克拉考爾悄然抹去了“照片并不復制自然……并武斷地切斷它們與周圍環境的聯系來使自然變形”?這樣的字句,將即時攝影或抓拍(snapshot)吸收進照相的方法與未經改動的現實之間一般的近親性當中?,以確保攝影與世界的絕對同一。這樣的處理損失掉了電影媒介的重要潛能,偶然性被更多地賦予鏡頭,剪輯則從根本上被忽略了,因為在電影中,任何鏡頭都被在場和缺席的場面調度所支配,它在呈現某一事物的同時,也指示著銀幕邊框以外世界的不可知,并因此總是召喚著下一個鏡頭的出現——這是構成電影本體層面的懸疑,它將已知引向未知,將實然引向應然。剪輯當然并不真正提供解決,即以這一個鏡頭作為對上一個鏡頭的懸念的回答;剪輯只是打開可能性的空間,打開鏡頭與鏡頭之間乃至畫格與畫格之間的縫隙——電影的這一潛能,悉拜即時攝影技術所賜。
1951年的文本留下了從《論攝影》到《電影的本性》論述重心轉移的痕跡,但在《電影的本性》的擴展內容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關于“憂郁”的插入段落,它遙遙呼應著克拉考爾的早年思想。根據精神分析理論,憂郁產生于拒絕承認失落的客體,正是這關鍵的一點使它區別于哀悼。因為在哀悼的儀式中,被哀悼的對象得到承認并且最終在符號界中被埋葬;而憂郁則是一種心理防御機制,憂郁者無法接受客體喪失的事實,并且把它摒除在意識之外,或者在世間萬物的表象中徒勞地追索這一失落的客體,或者在一片茫然中轉向自身,對身處其間的一切事物都若即若離?。克拉考爾引述前人觀點,肯定“憂郁和照相的方法之間的這種密切的關系”,認為憂郁者在茫然中“恍若與萬物同歸一體”,與普魯斯特筆下處于陌生人地位的攝影師的態度近似?。憂郁的觀念恰如其分地勾勒出了攝影與歷史、攝影與死亡的關系,它以一種具體而富有感染力的方式描繪了電影現象學、電影符號學都重點關注的本體論特質,即不考慮銀幕的分界,僅就攝影機鏡頭的范圍而論,影像媒介也總是已經同時投射出物像的在場和缺席。攝影(以及電影)一經問世,就意味著在把握到世界的同時便失去了它:“這個世界可以被拍攝下來,因為它所追求的就是消解在屈從于瞬間抓拍(Momentaufnahmen)的空間連續體中。”?在做這樣的理解時,克拉考爾的確傾向于把即時攝影看作對世界的完整一體的保證。他在描述19世紀中葉攝入鏡頭的紐約街頭人群熙攘、車水馬龍的景象時用到“萬花筒”修辭(在這一點上,1951年的文本?和《電影的本性》中的文字?基本一致),此時現實的構成主義特征便又伴隨著一幅由碎片拼貼而成的馬賽克畫面浮現在我們面前?。
三、并置:克拉考爾的剪輯和蒙太奇
在電影理論史上,克拉考爾從來不會被當作一個蒙太奇論者,這里不必重復他關于為什么要把剪輯歸于電影的技術特性而非基本特性的解釋?。然而,他的基本思想方法的原則卻是電影式的、蒙太奇的。這就是他在《歷史:終結前的最終事》的最后所總結的“肩并肩”(side by side)原則:
我在這里提出的“肩并肩”原則希望可以被應用于永恒和暫存之間的關系,以及一般和特殊之間的關系。……它指向的是一個中間地帶(in-between)的烏托邦——位于我們已知的土地中間空洞里的未知領域。?
盡管語境和內涵不盡相同,但是這里的“肩并肩”和1927年《論攝影》里面的“并置”難道不是同一種原則的表述嗎?英語side by side不就是德語Nebeneinander的直接字面翻譯嗎?
實際上,這一思想方法并非克拉考爾的原創,在他的老師格奧爾格·齊美爾那里可以找到它的清晰來源。而且,克拉考爾曾經非常自覺地對這一方法展開討論,以考察齊美爾“穿越一般世界的方式”:總體性的展開越是詳盡無遺,現象所處的位置就越分散,而各個現象之間的每一種關聯都被認為是應該予以說明的。在齊美爾那里,“本質的總體一致性的關系對立于類比(Analogie)的關系”?。更確切地說,作為方法論的更新,“類比”已經替換了總體性的訴求,帶來把握這個世界的新的可能性。因此,在齊美爾“穿越世界的旅程中,他總是努力把相距最遙遠的事物聯系到一起。人們往往會留下一個突出印象,齊美爾總是想在我們身上激發起一種關于多樣性的存在相互聯系的統一感,他想要傳達其總體性(這個總體性實際上從來不可能完整地向他展現),至少是接近它。所以他更傾向于去探索表面上彼此之間完全陌生、且是來自極為不同的物質領域的客體之間的關系”?。當然,克拉考爾與齊美爾之間的差別也不應該被忽視,前者的思想發展甚或超越了后者由穿越現象而達致總體性的認識。特別是在《電影的本性》和《歷史:終結前的最終事》這些晚期文本中,正是“總體性”本身被廢止或懸置了。“并置”不再是服務于確認世界的結構性實存的現象連接,而是變成了更多基于任意性和偶然性的諸事物之間的碰撞,這使得揭示一個完整世界圖景的意圖被碎片式拼接的激進潛能所替代。在這樣的理解中,克拉考爾把他在齊美爾那里習得的認識論方法進一步朝著他的好友瓦爾特·本雅明著名的“寓言”概念轉移:“每一個人、每一個物、每一種關系都可能表示任意一個其他的意義……所有具有意指作用的道具恰恰因為指向另外之物而獲得了一種力量。”?
因而,在復制世界和創造世界之間的猶疑、兩歧,幾乎可以直接被翻譯為電影理論中剪輯和蒙太奇之間的張力關系。這一難題不僅早已蘊含在《論攝影》的兩難選擇之中,而且仍然以某種不得已的后傾姿態纏繞著《電影的本性》的寫作。盡管在1927年的文本中,克拉考爾認為畫報上“這些照片的并置系統地排除了開放給意識的(社會)聯系”?,但是《電影的本性》最終結語提出的“人類大家庭”不是同樣訴諸墨西哥、“暹羅”、印度、美國“肩并肩”攜手前行的美好愿景嗎?“使人類走向這一目標的過程成為可見的任務理應落在照相身上;只有照相手段才有可能記錄下在許多地區共同的日常生活的各個物質的方面。”?
與這一基于美國式和平(Pax Americana)的“天真的普世主義”相契合,《電影的本性》的文字籠罩在一種異樣的祥和氛圍之中。作為一位猶太流亡思想家,克拉考爾在這部用英語寫就的理論著作中很少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猶太人經歷的歷史浩劫(Shoah),在幾乎貫穿始終的客觀實證主義色彩的筆調中,他一直勉力克制情感流露,使自己沉浸在一種就事論事、超然世外的淡泊之中,最大程度地調遣了這樣的本體論著述自身可能具有的姿態性。對比《從卡里加利到希特勒》(From Caligari to Hitler,1947)以及克拉考爾的著作一貫攜帶的歷史與現實關切和社會批評視野,這一情形難免令人心生疑惑。
不過,一個鮮有的例外出現在該書接近尾聲處對“我們時代的電影”與恐怖之間關系的討論中,這里提到的恐怖幾乎不言而喻,就是當時人類剛剛遭遇的歷史的恐怖。在相關的論述中,克拉考爾引入了一個具體影片的例子:法國導演喬治·弗朗敘(Georges Franju)的《動物的血》(Le Sang des Bêtes)。這部1948年的紀錄片以一種極其冷峻的風格將巴黎一座屠宰場內部的血腥畫面與外面安靜、祥和的城市生活和街道景觀并置在一起。有趣的是,克拉考爾在他的文字中以同樣冷峻的筆調帶入了另一重并置:“我們在觀看排列成行的小牛腦袋或關于納粹集中營的影片中橫七豎八的人體之后,本來隱藏在恐懼和想象的幕布后面的看不見的可怕景象便恢復了其原來面貌。”?弗朗敘的影片不知是否在諷刺性地暗示,在剛剛過去的戰爭歲月里,法國維希政權與德國法西斯暴行之間存在一種曖昧關系,但克拉考爾用幾乎是蒙太奇的方式,將巴黎屠宰場與納粹集中營并置在一起。我們不免要問,這難道不正是愛森斯坦在《罷工》(Strike,1925)里的那個著名段落所使用的手法(屠宰場殺牛和工人遭屠戮的場景被平行剪輯在一起)嗎?在接下來關于電影“揭露”功能的論述中,克拉考爾說明了這種蒙太奇技巧更一般性的法則,即“讓可見的物質現實和我們的現實概念進行對質”,前者總是對后者——即“我們的物質世界概念”“我們的錯誤的現實概念”——構成質疑和挑戰。就這一對攝影機功能的理解,克拉考爾高度贊揚愛森斯坦、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在20世紀20年代的工作,因為在那些代表蘇聯蒙太奇學派乃至整個世界電影藝術最高峰的作品中,他們“很注意在這些方面進行的種種的對比”?。

弗朗敘《動物的血》劇照
弗朗敘影片中的屠宰場畫面與納粹集中營里堆積如山的尸體鏡頭的并置,也就是克拉考爾在他這段文字里所完成的蒙太奇,出其不意地制造了某種對質,即他引用的例證與整個論述平靜、客觀的語調之間的對質,他作為僥幸逃生的流亡猶太知識分子的恐怖記憶與當下安逸自得的學術生活的對質——最終,也就是凝視和深淵之間的對質。這是克拉考爾也必須面對的“奧斯維辛之后”的倫理困境。正如海德·施呂普曼所言,克拉考爾“理論的主題是電影——但不是簡單地作為晚期資本主義現象的電影,也不是希特勒上臺以前的電影,而是奧斯維辛之后的電影”?。對于這樣一位“幸存的主體”來說,“一方面,大規模的毀滅在克拉考爾的歷史哲學中完全被忽略了,然而另一方面,克拉考爾深切地希望電影能夠對這種恐怖加以主題化。他的電影理論有兩個基礎,一個是明顯的,一個是隱藏的:它是對電影的反思,同時也是對電影中所映現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恐怖的反思和反映”?。

愛森斯坦《罷工》劇照
四、“現實”概念的難題性
這一悖論,這一有待“復原”的物質現實與“錯誤的現實概念”之間的“對質”,將我們帶回克拉考爾“現實”概念的不穩定性。《電影的本性》關于“現實”的表述的確并不連貫一致,甚至在克拉考爾認為電影媒介的兩個最基本功能,即記錄和揭示之間,也存在顯而易見的矛盾。關鍵在于,之所以“記錄”和“揭示”還能夠成立,是因為克拉考爾似乎假定我們仍然可能擁有某種本真的現實。然而這樣的假設完全建立在一個否定的認知程序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它必然要以“我們錯誤的現實概念”為前提。正是因為我們對于現實的理解已完全被種種錯誤認識所支配,本真的現實便只能存在于錯誤的現實概念的界限之外,即存在于克拉考爾所說的“未知領域”。
實際上,圍繞這一已呈難題性的“現實”,克拉考爾并不情愿命名的那種“對質”(因為他畢竟也加入了轉向攝影的“孤注一擲”,不會愿意背負概念創制的使命),在與他大致處于同一時代的思想家那里,倒有可能得到某種理論的映現。這里要提到晚期拉康理論的一組核心對立:現實(reality)與實在界(the Real,亦可直譯為“真實”)。所謂“現實”,始終處在社會-符號秩序的組織、結構、部署過程之中,不過是受意識形態支撐的幻象,但這一符號化過程永遠看不到它真正得以完成的那一天,因為它總是被一個內在固有的障礙所阻撓、干擾,這就是總也無法被符號界徹底吸收并組織到“現實”的有機構成中的“實在界”。因此,按照齊澤克的闡發,電影之所以是藝術而不是現實的再現,就在于它本身即展現了實在界與現實的對立?。我們去看電影,并不是為了例行公事地去完善我們對于“現實”的確認,恰恰相反,我們看電影是受到一個內在于我們自身的欲望游戲的驅使:我們期待著遭遇到恐怖、震撼、驚駭,在這種創傷性的快感內核的沖擊下,不僅是現實,而且是保障我們把現實經驗為“現實”的那種結構本身被瓦解了,我們只能期待著從那里一享激進之快感。電影與既存世界的關系,或者克拉考爾期待電影去“復原”的物質現實與“錯誤的現實概念”之間的“對質”,質言之,正是實在界與現實之對立,克拉考爾的蒙太奇也正是實在界與現實之間的“并置”。當然,這種理論借鑒只是有助于我們理解和闡發《電影的本性》并在這部“羊皮書”上不斷重寫的權宜之計,畢竟從哲學的基本立場來看,克拉考爾并沒有從現象學更向前邁進一步。
克拉考爾的“現實”思考始于毀滅——歷史的毀滅。從根本上說,《電影的本性》并不是關于電影的,而是在對經歷戰爭毀滅之后人類的生存境況和精神狀況發言。由于理性自身的朽蝕和意識形態的分崩離析,人類曾經擁有的全部概念、范疇、話語、敘述,以及由它們所承載的超越性價值和世界觀,都已灰飛煙滅。但是,人反而因此獲得了一個歷史性的機會,一個救贖的機會,通過電影攝影機這一媒介,來復原我們與不為任何“錯誤的現實概念”所覆蓋、所遮蔽的物質現實的親近感,“深化了我們跟‘作為我們棲息所的這塊大地’(迦勃里爾·馬賽爾語)的關系”?。對于《電影的本性》的作者來說,“現實”總是已經意味著奧斯維辛之后的現實,總是已經意味著現實的灰燼和廢墟,從這灰燼和廢墟中似乎還可以偶然瞥見曾經真實存在過的現實的影子——這便是克拉考爾的“天真的現實主義”的根源,它只存在于回憶和追認中。出于同樣的理由,它也必須被寫作“現實”,即寄身于這一已不復成立、只能付諸虛擬的概念之中。克拉考爾沒有創制新的概念來挽回“現實”的可理解性,是因為他把這個救贖的可能留給了電影,而非任何概念化的工作。現實永遠處于現在進行時的構造當中,換言之,“現實”并非一個名詞,而始終是一個動詞。只不過,在克拉考爾思考它的現在時當中,現實正在消失,正在蛻變為它的影像,同時也寄存于它的影像。這使我們有理由直接挪用阿多諾在《否定辯證法》中關于奧斯維辛之后哲學的可能性的經典表達?,來理解克拉考爾的現實主義:現實之所以幸存,只是因為它錯過了實現的機會。而電影似乎可以幫助我們重新贏回這個機會,幫助整個人類歷史重啟開端:
電影,然后是世界,尚未開始存在。
① Theodor W.Adorno,“The Curious Realist:On Siegfried Kracauer”,trans.Shivery Weber Nicholsen,New German Critique,No.54,Special Issue on Siegfried Kracauer(Autumn,1991):160.
② Dudley Andrew,Concepts in Film The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9.
③????????? 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電影的本性——物質現實的復原》,邵牧君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81年版,《自序》第1、3頁,第33頁,第24頁,第21—22頁,第25頁,第36頁,第393頁,第387頁,第387—389頁,《自序》第6頁。
④ Miriam Hansen,“Kracauer in Exile:Theory of Film”,Cinema and Experience:Siegfried Kracauer,Walter Benjamin,and Theodor W.Adorno,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2,p.255.
⑤ Miriam Hansen,“‘With Skin and Hair’:Kracauer’s Theory of Film,Marseille 1940”,Critical Inquiry,Vol.19,No.3(Spring,1993):469.
⑥ Siegfried Kracauer,History:The Last Thing Before the Last,Princeton:Markus Wiener Publishers,1995,pp.3-5.引文出自杜玉生待出版中譯本,特此感謝。
⑦?????? Siegfried Kracauer,“Die Photographie”,Das Ornament der Masse:Essays,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77,S.37,S.24,S.35,S.24,S.39,S.34,S.34.
⑧⑩? Siegfried Kracauer,History:The Last Thing Before the Last,p.45,p.52,pp.216-217.
⑨??? Siegfried Kracauer,“The Photographic Approach”,in Johannes von Moltke and Kristy Rawson(eds.),Siegfried Kracauer’s American Writings:Essays on Film and Popular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12,p.208,pp.207-208,p.205,p.210.
? Miriam Bratu Hansen,“Kracauer’s Photography Essay:Dot Matrix-General(An-)Archive-Film”,in Gerd Gemünden and Johannes von Moltke(eds.),Culture in the Anteroom:The Legacies of Siegfried Kracauer,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2,p.95.
? Laura Mulvey,Death 24x a Second:Stillness and the Moving Image,London:Reaktion Books,2006.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哀悼與憂郁癥》,馬元龍譯,汪民安、郭曉彥編:《生產》第8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頁。
? Martin Jay,“The Extraterritorial Life of Siegfried Kracauer”,Salmagundi,No.31/32,10th Anniversary Issue(Fall,1975-Winter,1976):57.
?? Siegfried Kracauer,“Georg Simmel”,Das Ornament der Masse:Essays,S.320,S.239-240.
? 瓦爾特·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李雙志、蘇偉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頁。在這個譯本里“allegory”被譯為“寄喻”。
?? Heide Schlüpmann,“The Subject of Survival:On Kracauer’s Theory of Film”,New German Critique,No.54,Special Issue on Siegfried Kracauer(Autumn,1991):112,112.
? The Pervert’s Guide to Cinema,written and presented by Slavoj?i?ek,a documentary directed by Sophie Fiennes,an Amoeba Film/Lone Star/Mischief Films Production,2006.
? Theodor W.Adorno,Negative Dialektik,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66,S.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