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文字,看到個性 讀《陳夢家紀事:一朵野花》
子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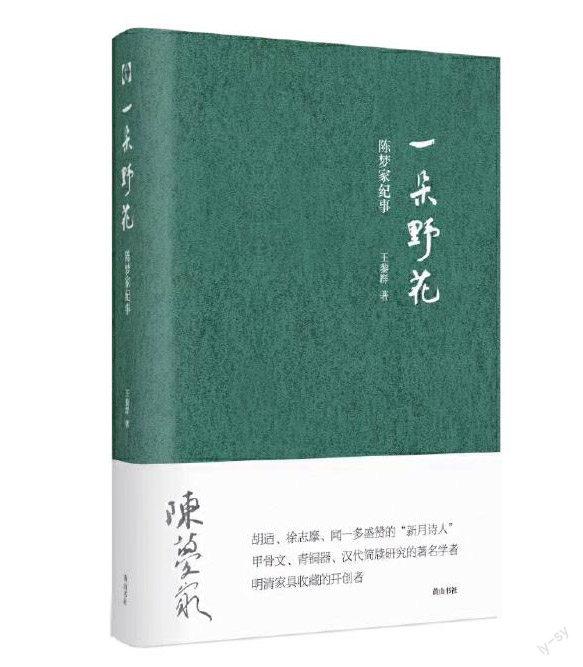
對歷史人物的記述,詞典和傳記的目標不盡一致。詞典要的是準確和簡明扼要,傳記則要在準確的前提下力求豐潤。豐,要求材料富足;潤,要求表述縝密優雅。
拿對陳夢家的介紹來說,詞典的篇幅不可能長,一般幾百字足矣。但生平和成就這些基本信息卻要既準確又簡潔,新月派后期代表性詩人、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的身份和主要著述成果應該讓人一目了然。
可是若要為陳夢家編著年譜、傳記,就不能這樣專撿關鍵詞用了。關鍵詞也需要,但應作為綱目,更需要的是支撐關鍵詞的諸多證據。說到證據,可就多了,陳夢家本人的著述、書信、日記等文字,其用過的器物、文具,與其有關聯的人物留下的涉及他的文字和實物,以及與之相關的歷史檔案和文獻,都需要廣泛采用。
有了材料,還需一番甄別與考據的功夫,因為并非所有材料皆可拿來就用。稀見的材料固然不易得,但材料的使用尤其需要講究,這里面就包含著考證、辨析、取舍等環節。
年譜、傳記所要求的準確而豐潤,并不容易做到和做好。
董寧文主編“開卷年譜系列”之二《一朵野花:陳夢家紀事》今春出版,懷著喜愛和期待讀完,便想到了上面那些話。
這本書的裝幀設計招人喜愛,是因為它和“開卷”系列的書一樣,都有著一種特別的風味。軟面精裝,大開本,翠綠的封皮和白色書名構成的色彩對比強烈而顯沉靜,扉頁還有一幀以陳夢家的詩《一朵野花》為主題的藏書票。就這幾樣,已把“開卷”品格彰顯足了。
至于書本身,也有幾句話可說。一是不以“年譜”名之,而曰“紀事”,這樣做的好處是回避了年譜的純學術色彩,突出了“事”。實際記述中也大半(后面部分編年性較突出)避免了純粹按編年順序記述的體例,而往往將一段時間中的“事”提煉出數端,以小標題形式一一道來。與此相關的第二點就是,沒有像通常的年譜那樣完全按年頭立標題,而是像傳記那樣分了章和節。如第一章為《童年時期》,第二章為《新月詩人》,第三章為《西南聯大教授》,以下直至第八章《最后七年》,基本以陳夢家生平事跡為序,而每一章都是陳夢家人生的重要一段。我個人比較贊成這樣的方式,拙編《吳伯簫先生編年事輯》也是如此處理的。
還有一點,也是最有意思的一點,即該書在基本的記述中,有大量的資料引述,也就是通常所謂以材料說話。這些材料,既有陳夢家的自述,也有其親友的旁述,大量親友書信和日記的引述更是一大特色。譬如以趙蘿蕤日記印證夢家上世紀50年代初期的“思想狀態”,又譬如以夢家1957年3月25日致某人的信佐證他對漢字簡化的觀點,以1958年夢家致趙蘿蕤的不少信件體現出他當時的處境和心態,很耐人尋味。還有就是借用了一些學術界研究成果,以資參考,我覺得也是一種很好的補充。比如第七章就引述《夏鼐日記中的陳夢家》一文,借以觀照陳夢家在1957年被列為“右派”的原由。雖說這樣有些簡單化嫌疑,但作為提供給讀者參考的資料,還是有意義的。
我很贊賞作者“把遺忘的歷史再串聯起來”的寫作態度,而且就本書言,作者的努力也基本上實現了這一目標。特別是對于陳夢家在五六十年代所遭受的無休止的質疑和迫害,本書沒有回避,而以豐富的史料給以記載,同時寫下了陳夢家在學術問題上堅持獨立思考和深謀遠慮的品格。尤其是他對簡化漢字的意見,如今看來,真可謂空谷足音。
當然,這本書也有遺憾的地方,如在書稿的具體行文和后期統稿方面粗疏了些,留下一些本該避免的錯訛,盡管不影響大局,但會讓讀者在閱讀中陷人不必要的疑惑。譬如幾處前后表述不對應處,涉及到陳夢家生日、陳夢家姊妹兄弟排行的表述有誤,1952年1月和2月條目中“全校”“學校”指的究竟是清華大學還是燕京大學?史學界到底是“四大右派”還是“五大右派”?“后記”開頭“今年”所指是2018年,最后落的時間卻是2020年……諸如此類。
撰寫年譜、傳記類著作不易,《一朵野花:陳夢家紀事》給讀者刻畫出一個有才華的詩人和有開拓性的學者形象,透過文字,讓讀者看到了譜主的個性,已屬難能可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