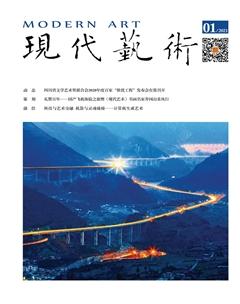浪漫抒寫與女性主義表達

蔣峰
JIANG FENG
四川電影電視學院編導系講師,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比較電影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四川省電影家協會會員,四川省文學藝術發展促進會副秘書長。
2020年,由華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品,新西蘭導演妮基·卡羅執導的影片《花木蘭》,作為又一部好萊塢瞄準東方題材的重量級大片,讓人備受期待,然映后表現卻不盡人意。對比好萊塢曾經拍出的經典東方題材電影《末代皇帝》《臥虎藏龍》《功夫熊貓》,此次《花木蘭》似乎有失好萊塢的“水準”,無論是對人物性格張力的刻畫,還是對恢弘場面的營造大都在“輕量”的意象化表達中淺嘗輒止。但在批評的同時,也應看到西方創作者們基于對異域文化的想象把中國故事進行了一定創新的浪漫化抒寫,此外又表現出了對女性主義意識的強烈關注,這些新的亮點也都值得我們再次審視和鑒賞。
一、對東方故事的浪漫抒寫
在人們對藝術品的審美鑒賞習慣中,總是對充滿想象力的藝術作品表現得尤為熱衷。藝術家們也常將旺盛而充沛的想象力作為自己藝術創作的杰出天賦。那么,在藝術創作中,對異域的文化想象有時無疑更能激發人們的創作思維。在這部迪士尼影片公司2020年出品的《花木蘭》中就可見一斑。出自中國傳統文化的花木蘭,其替父從軍、征戰沙場、載譽而歸、卸甲還鄉盡孝的故事,經過史學家的歷史考證,已證明了她的真實性,因此故事本身具有很強的現實主義色彩。但在電影《花木蘭》(2020)中,創作者對其的影視化改編已經超越現實,融入了較多的魔幻元素,對中國生命哲學中的“氣”以及傳統文化價值觀中的“忠、勇、真”也進行了更多富有浪漫色彩的抒寫。 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影片將花木蘭、女巫兩人與眾不同、強于男兒的生命特征,歸咎于身體內在“氣”的強大。“氣”的確在中國人的生命哲學中占有重要地位,如莊子的“人之生,氣之聚也”,即“氣”作為一種生命特質,能夠運化萬物。但莊子強調的“氣”,亦歸屬于他提出的大自然中無所不在的“道”。其所謂“道法自然”,指出萬事萬物的運行法則都是遵守自然規律的。大自然是現實的,那么“氣”也同樣是現實的。但在影片中,具備強大之“氣”的巫女競能夠利用“氣”進行隨意的變換身形,人鷹不分且多寡互成。在整個影片的時空環境中,導演以現實主義的思維呈現普遍群體的生命屬性,卻唯獨對女巫大開綠燈,使其法力無邊,無人能敵。從合理性上看,這無疑違背了中國哲學中“萬物相生相克”的生命邏輯。這種非理性的假定性設置,其實體現出的是創作者努力迎合西方人對東方的神秘想象,即對“氣”進行了一定魔幻色彩的呈現,從感官上看更能給人帶來驚奇的觀影體驗。
此外,影片對花木蘭的成長建構,主要借助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忠、勇、真、孝”四個價值觀來呈現這一歷程,其中對“真”的表達,也明顯表現出奇幻色彩。“孝”主要表現在劇情結構中的花木蘭因“孝”而替父從軍,最終也因“孝”而棄官回鄉的故事緣由。“勇”主要表現在對花木蘭在軍中生活時不畏艱難、敢打敢拼和在戰場上臨危不懼、勇往直前的精神塑造。“忠”則表現在對花木蘭不受女巫的蠱惑和引誘,冒死營救帝王的善良本性的刻畫。但相較來看,“真”是導演更加著力展現的價值元素。影片中展現出的花木蘭自小便元氣強大,愛舞槍弄棒,但她的這一行為卻被世俗所不待見,從她的父母到周圍鄉親都在無形中逼迫她做一個乖巧的女子;在隨后的軍旅生活中,她也必須通過隱藏真實身份才能替父從軍,時時刻刻扮演一個虛假的“花軍”。其中,影片對誓師大會上花木蘭無法念出“真”這一品德的細節刻畫,體現出她一直以來受制于虛假自我身份的痛苦。最終,在與巫女的戰斗中,激發出自我對“真”的訴求,實現了個體生命意識的突破。在這一情節中,花木蘭一旦決定做真實的自己,其便可以做到潛能的激發和戰力的劇增,無疑導演對“真”的凸顯刻意拔高到了奇幻的層次,但也難免讓人感覺到劇情的虛假,劇情的“逼真性”已流失于對概念的刻意闡釋中。所以,在這部迪士尼版的《花木蘭》(2020)中,西方創作者對這些在中國人的個體生命成長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元素進行的奇幻想象,呈現出了對東方故事的浪漫化抒寫的外在風格。但對這些價值觀的表現,一定程度上也有失客觀的自然規律。
二、凸顯女性主義的題旨揭示
在東方語境中,花木蘭替父從軍的故事,重在彰顯人物的忠孝和勇敢。從表現手段上看,創作者渴望通過女子“弱”的審美意象,來凸顯人的內在精神的崇高和潛能的巨大,從而激勵更多的人效仿隨行。這與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以“丑”的意象來彰顯敲鐘人卡西莫多內在精神的崇高,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然而對西方創作者來說,他們似乎更看重花木蘭女性意識的崛起,因此這部迪士尼版的《花木蘭》,便講述了天生具有強大“元氣”卻只能壓抑自我的花木蘭,借助替父從軍的契機,于嚴酷慘烈的戰爭中激發出本真的生命意識,實現自我解放的生命歷程。比較可見,在主題立意上,迪士尼版的《花木蘭》更傾向于西方文化中常見的注重對自我個體生命意識的抒寫。
此外,花木蘭的女性身份,又與西方文化中注重女性主義表達的創作習慣相吻合,因此影片在改編中又強調對女性主義的深刻指涉,尤其是影片在北魏與柔然二元對立的矛盾沖突中,有意增設的女巫一角,更凸顯出這一內涵。片中,女巫的法力強大,她幫助柔然統帥攻城破寨,誘捕北魏皇帝。而女巫本是北魏子民,她之所以背叛投敵,正是其與生俱來的強大“元氣”,不為世人認可,被妖魔化后遭驅逐出境,一生顛沛流離。她對北魏的憤恨走入極端,渴望借助柔然的勢力,報復北魏王朝,以證明自己的能力。但在兩軍對戰的一場戲中,女巫抓住孤軍深入的花木蘭時,并未置其死地,又暴露出其并非弒殺成性的軟弱一面,且對同為女性的花木蘭抱有極大的同情心。因為,在花木蘭的身上映照出女巫自己的影子,且當花木蘭隱藏在虛假的身份中而無法展現出真正的自己時,她又勸說花木蘭只有尋回自己才能發揮出強大的潛能。
巫對女性命運的悲觀看法,固執地以為展現出潛能的花木蘭終究會和她一樣,不會被世人認可,從而也掀起反叛的大旗。當她計謀得逞,端坐在皇位上,卻看到花木蘭被委以重任、率軍前來拯救帝王時,她的執念被瞬間瓦解。最終,在花木蘭遭遇危險時,甘愿用生命拯救這個沒有重蹈自己覆轍的女孩,從而與社會達成和解,也救贖自己背叛國家的罪行。影片著力刻畫的兩位女性角色,一個是女巫作為一個不被世人所接受的女性,其渴望通過強力的報復以實現對他人的懲戒;另一個是花木蘭作為一個深受性別壓制的高能女孩,其利用自己的忠勇睿智和超越男性的表現,贏得社會對女性的尊重。這契合了女性主義電影常常表現出的,通過擺脫女性作為男性的附屬物和視覺快感對象,展現出女性的主觀能動性和強勢身份,以再現女性在銀幕上的創造力和主導力。
三、輕量化表達缺失情感共鳴
《花木蘭》(2020)作為美國迪士尼公司瞄準中國市場制造的工業大片,一般情況看本應賺得盆滿缽滿,但實際卻僅取得2.7億元的票房成績,結果可謂慘淡。從影片本身看,主要體現為影片在內容和形式上的輕量化表達未完成中國人對該題材的心理期待。花木蘭替父從軍的故事在中國早已家喻戶曉,因此觀眾對故事情節的總體走向已經有了心理預設。如果劇情與原有的故事結局大相徑庭,便難以引起中國觀眾的情感共鳴,如果亦步亦趨地講述原有的故事又將陷入敘事的俗套,給觀眾帶來審美的冷淡。因此,從改編上看,留給創作者發揮的空間其實已被大大縮小。雖然,導演巧妙地融入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并對其進行一定浪漫化的抒寫,以期探究出東方文化的精髓和氣質,讓人耳目一新。但在影片的后半部分表現中,部分情節的表現力度較弱,缺乏一定的合理性。比如,影片中對女巫最后命運的設置,其不做任何掙扎的死亡結局就讓人感到不明所以。
片中,被原生民族拋棄的女巫對自己的國家懷有著強大的仇恨心理,她幫助柔然王子報復北魏,渴望推翻皇帝的統治,以建立自己的王朝。女巫宏大的報復目的,顯現出的是她強大的反叛意志。一般情況下,這種反叛意志是難以被感化的,即使人物最終感到后悔,但結果也多是人物在難以回頭中做最后的垂死掙扎,在形式上常常是慘烈、悲壯和令人惋惜的。但在這部《花木蘭》中,坐上皇位的女巫只因看到花木蘭被男權社會認可,就疏解了內心的強大仇恨,并立刻引導花木蘭前去營救帝王,最后還甘愿為保護花木蘭而赴死。這種情節的展現,缺乏了對反派角色在陷入命運深淵后極度抗爭的刻畫,未能營造出那種悲壯、慘烈、使人嘆息的情感體驗,因此該情節難為觀眾所認同。此外,在對花木蘭被激發出超強個體生命意識的一場戲中,影片只是表現出花木蘭在觀念上決定要做自我后,便成功實現了生命的再生。無疑,這種情節的設置未能實現,對深陷絕境的人如何在極端環境中激發出頑強的生命意志并最終使其絕處逢生的振奮場面的刻畫。
對比來看,在中國人對該類題材的審美意識中,早已被各類國產古裝片中眼花繚亂、高超精湛的武打技巧和氣勢恢宏、壯烈悲慘的戰爭風貌,以及逼入絕境又能力挽狂瀾的人物精神意志等,培養出了刁鉆的胃口。因此,這部在武打技巧、戰爭風貌、精神意志等各方面都淺嘗輒止,追求一種“輕量化”的意象表達的《花木蘭》,自然不能引起成年觀影群體的心靈振奮。
此外,在這部迪士尼版的《花木蘭》中,亦可看到好萊塢電影在對中國題材的把握上,表現出一種有意挪用卻無意求真的創作成見。除了上文提到的對“氣”的表現有失客觀,對“真”的表現過于奇幻化外,從史實上看,南北朝時期的花木蘭也是不可能住在中國南方的筒子樓建筑中的。但對西方的創作者而言,這似乎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筒子樓的建筑是最符合西方人對中國人大家族生活觀念的想象。綜上可見,西方創作者在改編中國題材時,常將邏輯真實讓位給審美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