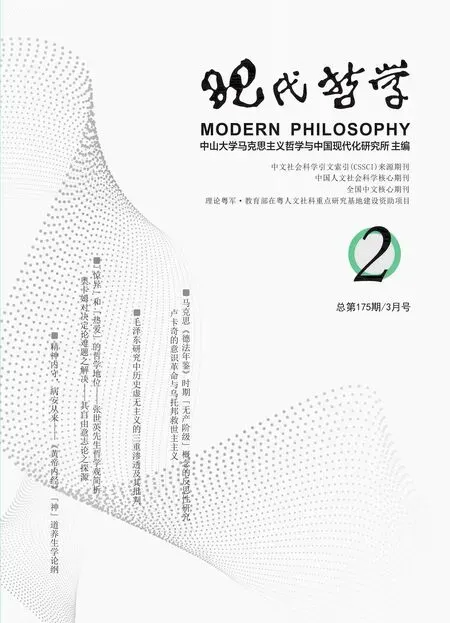論作為一門欲望發生學的列維納斯哲學
王光耀
如果說“主體性如何成其自身”是貫穿列維納斯前后期思想的明線,那么,“欲望的多重樣態”便是在暗中結構著列維納斯思想的隱線。列維納斯在對主體性的生成史的考察中,揭示了主體性的三重發生維度:通過對他物的占有與享用而建立起家政式的內在生活的權能主體性,通過與他人面容的相遇而被喚醒與引發出的無限回應著他人的倫理主體性,以及在與他人的親密性關聯中與被愛者建立起內在二元世界的愛欲主體性。與主體性的三重維度相平行,存在著欲望的三重樣態:源于自身匱乏的“需要”(besoin)以及疊加在需要之上的感性享受(jouissance),在他人面容的觸發下被喚起的朝向絕對他者的“形而上學的欲望”(le désir métaphysique),以及情愛關聯中呈現出的“愛欲性的欲望”(le désir érotique)。與對任何對象都保持著漠然的深度無聊相反,無論是主動生成還是被動引發,每種欲望樣態都意味著對于對象的并不漠然的趨近、渴求與投身,使得主體性處在一種富有生機的活性狀態中。通過對每重樣態的欲望的屬己特征的揭示,以及對不同樣態的欲望相互之間的張力關系的整體考察,我們將能夠更為深入地理解主體性如何成其自身的發生歷程與內在機制。在這個意義上,筆者將嘗試揭示,列維納斯的哲學思想可以被整體性地理解為一門欲望發生學。
一、需要-享受與“圍繞自身的旋轉”
在日常用法中,“欲望”概念通常與“需要”聯系在一起。然而,即便是“需要”這一流俗意義上的欲望概念,列維納斯在其哲思中也并未忽視這一范疇的復雜內涵。在其文本可以發現,“需要”概念實際上適用于兩種不同層面。第一重意義上的需要處在生物學層面,源自于主體生理-心理上特定的缺乏,尋求具有特定指向的生理-心理滿足,比如由饑渴感引起的吃飯喝水的需要。這個層面的需要通過對他者的吸收和消化來緩解自身的缺乏,維持自身存在的安穩,乃至于強化自身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列維納斯用“嚙食”概念來形容需要帶給客體他者的否定性特征:“在需要中,我可以嚙食實在的事物,通過吸收他者來滿足我自己。”(1)[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朱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97頁。第二重意義上的需要同樣源自缺乏,但并非生理學上的特定缺乏,而是一種回復原初整全存在的渴求或者融入源始的絕對同一者的渴望。比如,柏拉圖《會飲》中阿里斯多芬所講述的兩性同體的神話,便是將愛欲理解為一種被分離開的存在對于回到原初的整全而自足狀態的永恒需要;而普羅提諾談及的“迷狂”狀態,便是從“太一”中流溢和分離出來的靈魂對于“太一”這一源始的絕對同一者的回返。
然而,在需要的這兩個層面之外,列維納斯卻告訴我們,需要“不能被解釋為單純的缺乏”,因為“人在其需要中自得其樂,他為其需要感到愉悅”(2)同上,第94頁。。也就是說,需要不單純是一種痛苦的匱乏,還可以是一種對被需要之物的愉悅的依賴,“作為愉悅的依賴,需要可被滿足,就像一種被充滿的虛空。生理學從外部教導我們說需要是一種缺少。人能夠對其需要感到愉悅,這表明,在人的需要中,生理學的層面被超越了”(3)同上,第94頁。。這種對于需要之被實現過程本身的愉悅,正是列維納斯著重談論的疊加在“需要”概念之上的“享受”范疇。
誠然,生活總是由一些為了滿足自身需要而進行的各種具體事項所組成,比如工作、勞動、進食等。這些活動的實現有著明確的目的和效用,它們是使生活得以進行的燃料,構成生命存在得以延續和擴展自身的條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依賴于這些實現活動,以之為生。但是,這些存在活動在進行的同時也被我所感覺、所體驗,它們充實、滋養、愉悅著我的生活。可見,維系著生活之延續的實現活動所具有的意味,總是要比其單純的功用性目的多出一層。比如,進食的功用性目的是飽腹,但在身體對能量的吸收和獲取之外,我們也從進食中獲得滿足、愉悅。這在需要之實現過程中多出的一層就是列維納斯所謂的“享受”:“對于行為(l’acte)來說,那種從它的實現活動本身中獲得滋養的方式,恰恰就是享受。”(4)E. Levinas, Totalité et Infni,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1, p. 83.我們“思考、吃飯、睡覺、閱讀、勞動、曬太陽”(5)[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91頁。,同時也感覺、體驗和享受這些行為,在存在行為之上疊加的這一層又成了生活本身的構成性內容。可見,生活具有一種自反性的結構,如同人們意識著他們的意識、感覺著他們的感覺,人們也“生活著他們的生活”(On vit sa vie)(6)同上,第89頁。。在“意識”或“感覺”一詞的寬泛的意義上,“生活著他們的生活”似乎同樣可以歸并在“意識著他們的意識”或“感覺著他們的感覺”的名下。
但在列維納斯這里,“生活著他們的生活”這種自反性結構里有著一種獨特的疊加,這種疊加具有厚度的,而且不斷增生。首先,由前述可知,在對存在行為的自身覺知之上疊加有一層對被感覺到的行為本身的享受。我存在著,感覺到我的存在,同時也享受著我的存在,從而獲得一種存在的愉悅感、美妙感,這一愉悅感、美妙感疊加在存在行為之上,構成一種“位于實體性之上的榮光”(7)同上,第93頁。。其次,享受又可以是“對享受的享受”(la jouissance est jouissance de la jouissance)(8)E. Le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The Hague: Mart Nijhoff, 1974, p. 92.,愉悅又可以是對愉悅的愉悅。這當然不是無限后退,而是一種多重的增生與疊加,具有“……(對(對……的享受)的享受)……”的結構。比如,我在吃面包的過程中獲得一種感性的愉悅,而我在獲得享受的同時又享受著這一享受。這種增生與疊加并不處在對最終享樂的目的論式的追求的序列之中,也并非盲目地處在一種不斷重復的、追求享樂之強度的循環之中。享受的增生與疊加發生在享受的每一個當下,每一層享受都是自身的一個終點:“感性是享受,它滿足于所予物,它自滿自足……它直接處在終點處,它完成了,它終結了……”(9)[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117頁。而每一層的增生和疊加又構成一個新的享受的當下,“每一次幸福都是第一次發生”(10)②③ [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93、90、91頁。,正是這總是多出的一層構成“生活的魅力”②與“生活的珍貴處”③。
在此,如若回溯笛卡爾談論“什么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時所枚舉的序列,那么我們可以在這個序列中加上“享受”。人的存在不僅是“在懷疑,在領會,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覺”(11)[法]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錄》,龐景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7頁。,也是“在享受”。這并非是一個無關緊要的添加。在列維納斯的研究中,“享受”是疊加在“我思”之上的一層嶄新的結構,它是“自成一格的”(sui generis)——在懷疑、領會、肯定、否定、愿意、不愿意、想象、感覺所有這些我思行為之上,有著對這些行為本身的感受與享受,它們充實著生活,使生活愉悅或悲傷。享受不是位于生活的諸種情緒序列中的某種偶然的情緒狀態,而是生活與生活本身之間的自反性關系:“過生活,就是享受生活。”(12)[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95頁。在這個意義上,“享受”被列維納斯提升為生存論范疇:“享受并不是諸種其他狀態中的一種心理學狀態,不是經驗心理學的感受性的心境,而是自我的顫栗本身。”(13)同上,第92頁。
可見,享受作為一種疊加在存在行為之上的情態,使得此在不再停留于單純作為缺乏的“需要”層面,不再停留在“赤裸的存在意志”(14)同上,第91頁。的層面,不再單純被“存在之努力”(le conatus de l’être)所規定,而是有著“對存在的越出”(15)同上,第93頁。,亦即對單純為了生存而斗爭的越出。享受使得此在的在世存在變得柔和,具有愉悅感和美妙感,使得存在成為值得欲求的,引人欲求的。在這個意義上,列維納斯談及“對生活之愛”:“生活并不是赤裸的存在意志,不是對于這種生活的存在論的Sorge(操心)……生活是對生活之愛,是與這樣一些內容的關聯,這些內容并不是我的存在,而是比我的存在更珍貴。”(16)同上,第91頁。如果說無聊、厭倦意味著對生活、對存在的一種漠然姿態,意味著生活本身沉陷于無意義感中,那么列維納斯所揭示的由“享受”所建立起的對生活的愛便意味著生活富有生機與活性。在對生活的享受中,我們欲求著生活,認同著生活,將生活認之為我的生活,將自我的存在凝聚在一種安穩幸福的“安好意識”(la bonne conscience)中,從而建立起“一個本土性自我的在家的實存”(17)同上,第95頁。。
二、形而上學的欲望與圍繞他者的離心運動
作為需要的欲望源自于主體自身的缺乏,尋求自身的滿足,但并非任何欲望都可以被“缺乏-滿足”這一對范疇所規定。在與他人的“面對面”關聯這一事態中,列維納斯發現了另一種欲望樣態,他稱之為“形而上學的欲望”。
他人面容現象的獨特性體現在其言說或凝視之中,列維納斯將之稱作一種基于自身、從其自身而來的表示、表達或呼喚。這一自身表達對于自我具有一種觸發性的力量,將自我拉入到與他人的呼喚-回應這一關聯事態中。在這一事態中,列維納斯發現了他者的不可還原性或無限性。所謂他者的無限性,并不單純因為他者在內容上的不可窮盡性,而在于如下原因:其一,面容并非任何現成之物,而是發生性的、有待來臨的,在其無盡的凝視與言說中不斷從其自身而來打開著自身;其二,面容總是有可能隨時中斷自身、撤離自身、隱匿自身,甚至于其顯現總是一次性的,當下乍現、轉瞬即逝,即發生即消隱;其三,自我無法像直接體驗自身的心靈生活那樣去體驗他人的心靈生活,而總是處在對他者的共感式的想象之中;其四,自我對他者所傳遞意味的理解總是要借助于“能指鏈”的運作,亦即他者的表達總是要經受拉康所謂的符號界編碼的閹割,或者列維納斯所謂的“言說”(dire)總是要在“所說”(dit)中被把握。就前兩點而言,他者的面容無法被凝固為任何現成的在場,總是有著溢出和剩余,總是以自身差異化的方式呈現;就后兩點而言,一旦嘗試去把握和理解他者面容傳遞出的意味,他者就必然會落入自我的想象式誤認或能指鏈編碼的轉譯,因而總是以一種變異了的方式呈現。于是,他人面容的臨顯根本上是無法被達及的,總已經被錯失,總已沉入到無法被再現的過去。正是由于這樣一種獨特的顯現方式,列維納斯在面容現象中發現了不可還原的他者性,他將之稱作“絕對他者”,具有“他異性”(altérité)、“外在性”(extériorité)、“無限性”(infinité)等特征。
然而,他者如果只是單純在認知面前具有一種不可窮盡和不可達及的特征,實際上還無法喚起自我的欲望,如果有的話,也不過是一種對于未知的好奇。事實上,他人的面容帶給我的不僅僅是剩余和溢出的經驗,同時還有一種觸發性的力量,這一觸發由面容的凝視或呼喚帶來。在面容的凝視或呼喚現象中,面容位于可見性與不可見性的交界處,如同敞開的窗口,其后是他者不可見的欲望的無盡深淵,經由面容的凝視或呼喚一再地逼臨于我。這一凝視或呼喚的逼臨將自我置于其目光或話語的焦點之下,將一種迫求回應的重量和緊迫性施加于我,由此觸發或喚醒了一個回應著他者之呼聲的賓格自我,列維納斯將之命名為“己”(Soi):“在對他人的回應中,主體性只是賓格的無限被動性,這一賓格并非它本會經受的由主格開始的變格的結果……一切事先就是賓格——己之非同尋常的條件或無條件性。”(18)E. Levinas, De Dieu Qui Vient à L’Idée,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2004, p. 143.可見,“己”作為通過他者的觸發而被喚醒與創生的主體性,同時也是朝向他者、回應他者的主體性,其自身性便是作為他者的自身:“通過諸他者而在自身之中”(19)Ibid., p. 143.,“‘由于他者’(par l’autre)并且‘為了他者’(pour l’autre)”(20)E. Levinas, 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 p. 161.。作為回應的主體性,己本身就是在呼喚-回應這一事態中誕生的,或者說己本身便是呼喚-回應這一充滿張力性的關系事態:因他者的呼喚而處在不得不回應的賓格位置上,并由此反身意識到自身的“己”(21)就這種自身意識是對意識的被喚向陌異他者因而“處在尚未及于與自身的重合之處”這一事態的意識到而言,它同時也就是一種“不安意識”(la mauvaise conscience)。(See E. Levinas, De Dieu Qui Vient à L’Idée, pp. 143, 258;朱剛:《通往自身意識的倫理之路——列維納斯自身意識思想研究》,《世界哲學》2015年第4期;朱剛:《不安意識作為原意識——再論列維納斯的作為第一哲學的倫理學》,《哲學研究》2019年第11期。)。
呼喚引發了回應,而回應無法真正抵達呼喚,總已經有著延宕與錯失,由此,“呼喚-回應”之間的分隔符既是一種連接和傳遞,又是一種不可抹消的間隔。就時間性建構而言,這一不可抹消的間隔表現在:他者的凝視或呼喚對于主體性的觸發與創生,作為已然發生的過去,處在不可回憶的“過去”維度中,作為有待來臨的將來,處在超出前攝的“將來”維度中,由此便打破了先驗自我的內在時間意識的自發綜合與源始統一,亦即打破了胡塞爾所揭示出的滯留與前攝相互引發而構建起的時間回環結構(22)正如列維納斯所說:“在意識那散布為前后相繼的瞬間的時間性中——盡管如此,諸瞬間卻在滯留與前攝、回憶與預期、歷史記述與預測中被共時化了——有一種他異性能夠打破這種同時性,能夠打破前后相繼的瞬間向著再-現之在場的聚集,于是,意識發現自身被關涉于不可回憶者。”(See E. Levinas, De Dieu Qui Vient à L’Idée, p. 165;關于列維納斯對時間性的談論與胡塞爾之間的關聯與區分,參見王恒:《解讀列維納斯的〈意向性與感性〉》,《哲學研究》2005年第10期。)。而就欲望的生成與建構而言,呼喚-回應之間的不可抹消的間隔表現在:在他者面容的凝視或呼喚中,他者究竟試圖傳達何種要求和欲望?由于面容現象本身的自身差異化的運動與無盡的溢出,由于自我對面容的把握總已經以一種變異的方式進行,他者在其凝視或呼喚中所敞開的欲望深淵對于自我而言構成巨大的謎。我該如何辨識?我該如何回應?我該如何滿足他者的欲望?他者渴求回應,而我無從真正知曉他者的欲望之謎因而無法真正回應,我的回應便總是不足夠的,總是有著錯失的可能,總是需要一再地回應。這一事態喚起自我無盡的焦慮與不安,由此使得來自于他者的凝視與呼喚對于自我而言具有一種侵入、攪擾和創傷性的特征。然而,恰恰因此誘發自我朝向這一他異性深淵的欲望,“這一深淵令人眩暈地吸引著主體,后者根本無法停止”(23)[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70頁。。
列維納斯將這種被他者面容的無盡的凝視與呼喚所激發起的、無法停止地朝向他者的欲望命名為“形而上學的欲望”。與“需要”相比,“形而上學的欲望”具有截然不同的五個特征:其一,形而上學的欲望并非源自于自我的某種特定缺乏,尋求滿足和占有,也非阿里斯托芬式的對于原初整全狀態的返回的渴望,亦非德國浪漫派式的對于精神依歸之地的鄉愁,而是由他人面容的凝視與呼喚所激發與喚醒,朝向絕對他者的趨近但無法抵達和占有的運動。其二,與需要所具有的圍繞主體自身旋轉的向心運動不同,形而上學的欲望是圍繞陌異性他者進行旋轉的離心運動。朝向他者,意味著經受他者的陌異性帶來的攪擾,因此總已是自身他異化的運動。其三,與形而上學的欲望相伴隨的基本情態并非滿足、幸福、享受,而是焦慮、受苦、不安。他者如同深淵一般攪擾著我,如同晦暗的謎一般牽引著我,乃至破碎著我的同一性,置我于坐立不安的焦慮與創傷之中。可見,形而上學的欲望并不如同需要那樣尋求對自身存在的保存與強化,恰恰相反,形而上學的欲望拆解自身存在的同一性,在自我借以凝聚自身的安穩的殼上切開無法彌合的裂縫。在這個意義上,走向他者,在列維納斯看來,“如同走向死亡”(24)[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5頁。。列維納斯用一系列近似于精神分析語匯的詞來形容他者的這種侵入、攪擾和創傷性:糾纏/困擾(obsession)、不安(in-quiétude)、失衡/精神失常(déséquilibre)、譫妄(délire)、精神之難于呼吸(essoufflement de l’esprit)。其四,在時間性上,需要建立起的是共時性的時間,形而上學的欲望則將自我帶入到與絕對他者的關聯之中,帶入不可回憶的過去與不可預期的將來這一“異-時性”(dia-chronie)之中。其五,需要通過對客體的獨立性的否定活動強化和穩固了自我既有的同一性,形而上學的欲望則不僅拆解和破碎自我固有的同一性,同時還深化自我。形而上學欲望所指向的陌異性他者既是絕對的外在性,又內置于主體性的最深處,既是破壞著主體性之安穩與同一的異己性力量,同時又是創生性和構成性的,引發著具有嶄新樣態的主體性——由于他者而朝向他者、為了他者的倫理主體性。
三、愛欲:需要與欲望的兩歧性
在“需要”(作為流俗意義上的欲望)以及“形而上學的欲望”之外,列維納斯在“欲望”這一范疇之下還談論了“愛欲性的欲望”。對于列維納斯的愛欲觀的詳細內涵,筆者在此不作過多談論(25)參見王光耀:《論愛欲關聯中的意向結構——解讀列維納斯的“愛欲現象學”》,《中國現象學與哲學評論》第24輯,中山大學現象學與文獻研究中心編,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年,第289—313頁。,而是側重于對愛欲性的欲望與需要以及形而上學的欲望之間的區分與聯系的考察。

顯然,從表面看來,列維納斯的愛欲觀在不同時期存在重大變化,甚至如論者所指出的,是一種“結構性的大挪移”(29)參見余君芷:《論列維納斯哲學中“愛欲”理論的轉變》,《理論月刊》2019年第12期。。但在筆者看來,如果認同列維納斯在中期代表作《總體與無限》中對于愛欲的兩歧性的判定,那么前期和后期著作對于愛欲的不同定位,不過是對愛欲的兩歧性內涵的不同向度的偏重。前期偏重愛欲關聯是一種與不可還原的他異性的關系,同時注意到愛欲尋求感性享受的維度,并且恰恰是在愛欲尋求滿足的不可能性中彰顯出被愛者的他異性。后期偏重愛欲的享受與占有的向度,同時注意到愛欲關聯并非與現成之物的關聯,而是與倫理性他人的關聯,愛欲中的享受這一維度的展開必須以面容式的存在者為前提。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列維納斯對愛欲的兩歧性的強調才是其愛欲觀的核心,持有這一觀點去解讀前后期相關文本,就會覺得列維納斯的愛欲觀的轉變實際上沒有達到一種“結構性的大挪移”的程度,毋寧說自洽和連貫的成分更大,只不過在不同時期對愛欲問題所側重的維度有所不同。
在做出以上預備性說明之后,我們可以聚焦到愛欲所具有的兩歧性這一獨特特征,以此厘清愛欲性的欲望與需要以及形而上學的欲望之間的關聯與差異。在愛欲關聯的意向結構中,就愛欲的意向相關項而言,兩歧性特征體現在被愛者“既顯現為需要的對象同時又保持住他的他異性的可能性”(30)[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245頁。。作為需要與感性享受的對象,被愛者具身化為他者之“肉”(le charnel)(31)同上,第248—249頁。,在其過度的裸露中展示著通常被遮蔽的隱秘事物,引誘著愛者不斷去激發出被愛者身心的愛欲化狀態。盡管如此,被愛者畢竟并非任何現成存在者,而是能夠在其面容中自身表達著的他人,處在其不可還原的他異性之中。唯有這樣一種能夠以面容的方式表達自身、展露自身的存在者,才有可能過度地裸露自身,才有可能以一種愛欲性身體的方式將自身呈交為享受的對象。由此,在愛欲關聯中,被愛者既能夠顯現為需要與享受的對象,但這一顯現又以其自身的他異性為前提,并且始終保持著其他異性。反過來說同樣成立:在愛欲關聯中,被愛者既以面容的方式表達自身,但這一“表達的純粹性已經由于快感性/情欲性的歧義而紊亂”,呈現為一種“超逾面容的面容”(32)同上,第251頁。,亦即由于快感、過度的裸露、隱秘性的在場而轉化為他者之“肉”的面容。
就愛欲的意向活動而言,愛欲的兩歧性特征體現在“需要與欲望的同時性、色欲與超越的同時性”(33)同上,第245頁。。一方面,尋求生理-心理的享受與滿足是愛欲活動的一個構成性要素,無論是精神性的相互感通,還是在撫愛中肉身的相互激發,皆有著愉悅與快感。另一方面,和在現成之物中尋求滿足的需要與享受不同,愛欲源自他人對自我的原初的吸引,渴求打開生命之間的通道,由此呈現出近似于形而上學的欲望的結構。但愛欲所具有的這種需要與欲望的同時性恰恰意味著愛欲既不可以還原為需要,也不可以還原為形而上學的欲望,并且正是在這種雙重的不可還原中展現著自身的獨特性。
愛欲與需要-享受的差異體現在:就需要而言,需要體現出主體對客體的否定性特征,亦即否定對象的獨立性,將其納入到自我的支配之中;愛欲盡管也有尋求滿足與占有的意向,但在他者的不可還原的他異性中發現了占有和融合的不可能性。就享受而言,盡管愛欲中有著感性的愉悅,但愛欲關乎的并非無面容的元素性事物,而是有其自身感覺的他者之“肉”。不僅如此,在被愛者目光的凝視下,愛欲的綻現本身總是會伴隨著羞感與心慌意亂的可能性。由此,與圍繞自身旋轉的單極化的享受不同,愛欲關聯根本上是一種二元性結構。
愛欲與形而上學的欲望的差異體現在:盡管二者都關涉于他人之他異性,但愛欲具有“撫愛”(la caresse)(34)同上,第247頁。這樣一種獨特的肉身化的意向活動。撫愛并不構造對象,也并非背負無限重量的倫理回應,而是激發與撩撥起他者肉身的愛欲化狀態。正如薩特所說:“愛撫不單純是輕撫:它是造就。在愛撫他人時,我通過我的愛撫使他的肉體在我的手指之下誕生。愛撫是使他人肉身化的整套儀式。”(35)[法]薩特:《存在與虛無》,陳宣良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478頁。不僅如此,愛者在激發著他者之肉的同時也為他者的撫愛所激發,從而不斷生成著自身的“肉”。由此,愛者與被愛者在撫愛的交互激發中,構筑著愛者與被愛者的互為纏繞著的感覺織體,亦即薩特所說的“雙重的互相肉身化”(36)[法]薩特:《存在于虛無》,第479頁。,或如列維納斯所說,愛欲中的快感“以交互主體性的方式結構化了”(37)[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257頁。。
可見,在主體性的成其自身的歷險中,如同需要與形而上學的欲望,愛欲性的欲望同樣有其極為獨特的位置與功能。對于列維納斯而言,愛欲既不能被還原為一種為了獲得他人之承認的斗爭,這一斗爭欲望著他人的欲望對我的欲望的承認;也不能被還原為一種經由他人面容的呼喚與凝視而喚起的倫理性的“形而上學的欲望”;亦不能被還原為一種通過與他人的融合而恢復自身存在的原初整全性的渴求;也不能被還原為一種認知性的活動,在對陌異之物的好奇心的牽引下,不斷地將未知轉化為已知;更不能被還原為一種對他人的自由進行征服、占有與抹消的欲望。愛欲,意味著切近他人之他異性的可能性,意味著彼此身心的交互激發、敞開、牽引與感通的可能性,意味著主體間以具身化的方式深度連結和滲透在一起的可能性,意味著與他人建立起柔和而熱烈的親密性關聯的可能性。最終,在愛欲雙方的既區分又融合著的運動中,還孕育著創生嶄新主體性的可能性。
四、結 語
列維納斯的哲學通常被整體性地標記為一門他者哲學,但列維納斯更加基礎性的問題意識實際上在于如何在奧斯維辛之后重建一門主體性哲學,既能擺脫傳統主體性哲學蘊含的總體化、同一化等傾向所導致的對他者的暴力、對差異的抹消,又能揭示和捍衛一種別樣的主體性,亦即在本源處承擔著善、能夠對他者負責的倫理主體性。對倫理主體的揭示無法脫離開其與主體性的其他維度之間的張力關系,于是,列維納斯哲學整體上向我們展現出一幅“主體性如何成其自身”的圖景,或者用列維納斯本人的話來說,一出“自我實存歷險”的“戲劇”(38)同上,第266、276、278頁。。在這出戲劇中,欲望的多重樣態與主體性的多重維度之間具有一種本質相關的平行關系。其中,“需要”相關于致力于自我保存與提高的自我中心式的權能主體,建立起的是自我與相對他者之間的占有與享受式的關聯;“形而上學的欲望”相關于圍繞他者進行離心式旋轉的倫理主體,建立起的是自我與絕對他者之間的呼喚-回應式的倫理關聯;“愛欲性的欲望”相關于與他者交互感通、親密關聯著的愛欲主體,建立起的是自我與愛欲對象之間的具身化的愛欲關聯。
可見,列維納斯并非只是專題性地思考欲望的某種樣態,而是在欲望與主體性的生成建構的本質相關性中對欲望問題進行系統性思考。將需要-享受、形而上學的欲望、愛欲從經驗層面上的生理-心理狀態提升為生存論范疇,其意義不單純在于揭示出欲望的不同樣態,而在于這三種不同的欲望樣態皆指涉著源初地引發與塑形著自我存在的那些本質性的發生機制與關聯結構,因而是自我實存歷險中的本質性的構成環節,參與組建著主體性的不同維度。進而,通過對欲望的多重樣態之間的張力性關系的考察,也就可以映射出主體性的多重維度之間的交錯性的張力關系。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列維納斯的哲學可以被整體性地理解為一門欲望發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