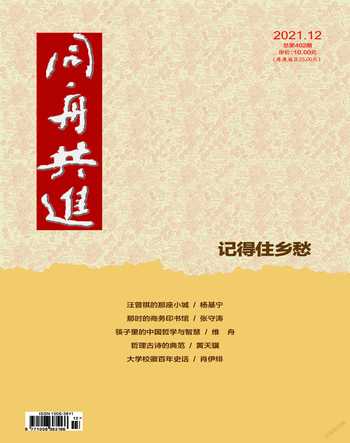馮卓懷與曾國藩
李超平
在曾國藩的朋友圈中,有算得上一生摯友的,如郭嵩燾;有先友后敵的,如沈寶楨。而馮卓懷則是一個與他由親而疏又由疏而親的朋友,這種失而復得的友誼比較少見。
馮卓懷,字樹堂,湖南長沙人,生于清嘉慶十八年(1813)十一月,道光十九年(1839)湖南鄉試解元。他隨后進京參加會試,就此結識了剛于上年考中進士、同是湖南“小鎮做題家”的曾國藩。論年齡,他比曾國藩小兩歲;論科舉資歷,他比曾國藩遲5年中舉;論籍貫,兩人都屬湖南長沙府。兩人很快成為摯友,馮卓懷有段時間甚至和曾國藩同住,兼給他長子曾紀澤做家庭教師。
他們的關系好到什么程度?曾國藩在家信中說馮樹堂是如唐鑒、倭仁一樣“躬行心得”之人,“極為虛心,愛我如兄,敬我如師”。又說馮樹堂“進功最猛”,不免有點遺憾自己的九弟不能與他“日日切磋”。這時的馮卓懷一心準備參加會試,努力用功是必然的;他還教曾國藩靜坐。對此,曾國藩常在日記里怨艾自己,也學馮樹堂那樣訂立嚴格的日課來自我約束。此外,兩人還互相點評日記,曾國藩往往會寫一些比較尖刻的批語,而馮卓懷則輕易不置一詞。
正逢馮卓懷三十初度,針對他科舉艱難的窘況,曾國藩專門寫下《反長歌行》勸勉。次年九月,曾國藩出任四川鄉試主考官,行旅中倍感孤寂之際,寫下《梓潼道中有懷馮樹堂陳岱云》一詩,可見彼此交契已深。當曾國藩于咸豐二年(1852)在安徽太湖縣小池驛聞母去世、急急趕回家之際,可巧馮樹堂正在池州知府陳源兗處,遂陪他乘船歸湘,曾國藩因之自道“堪慰孤寂”。
馮卓懷堅持到咸豐三年(1853)春再次會試不第,才通過會試后的大挑,選取了湖南武岡州的學正一職。但未及上任,曾國藩開始創辦湘軍,馮卓懷和郭嵩燾等一起幫他籌餉,以功保舉代理四川萬縣知縣。盡管曾國藩對他們未能隨營出征有些不快,但為了好友仕途順利,還是專門致函時任四川總督的前輩王慶云,以聞馮卓懷有循聲為由,委婉地請求關照。馮卓懷先后在四川萬縣、彭縣、華陽等縣任職共4年,勤勉有加,擬調貴州升職,卻與上司不協,就以祖父去世守孝為由辭職。
咸豐十年(1860)四月,曾國藩獲代理兩江總督,躊躇滿志,致信邀長期賦閑的馮卓懷出山幫忙。馮卓懷于十一月十五日與章壽麟等人來到安徽祁門縣城,旋即奉命督辦縣城各處的碉樓。不過,因為施工方案上的一個小事項未能完全遵循曾國藩意旨,他被聲色俱厲地當眾訓斥,頓感顏面殆失,遂拂袖而去。
雖然曾國藩并未在日記中具體記述此事,但還是能在次年二月初七給郭嵩燾兄弟的信中窺見端倪。他不但要求郭嵩燾把馮氏帶走的《瀛寰志略》一書取回,還要代為把去年贈自家的三百兩銀子退還二百兩,理由是“受之太覺無名”。這顯然是一種從此互不相欠的姿態,可見芥蒂之深。
當馮卓懷的名字再次出現在曾國藩日記中,已是同治三年(1864)四月初一。他聽聞馮卓懷絕意官場,即使郭嵩燾力邀其加盟幕府也沒有答應,便專門致信,既謝他規勸曾國潢不要干預湖南地方公事,也希望他盡快復出,無論是去廣東還是四川,都請他能“不以一時纖介之嫌,而誤終身出處之義”,但規勸未奏效。
直到同治十年(1871)三月十八日,曾國藩在日記中透露,馮卓懷于當天來到南京,次日入兩江督署。他說這是30年前的老友,祁門一別已10年不見,但還未見老態。而在家信中,他坦陳自己最近開始反思往年開罪別人之處,除在祁門與馮卓懷有過“口角失歡”,至今心中有愧外,其次就是與李元度的矛盾。因此,馮卓懷的到來使曾國藩的精神負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脫。
馮卓懷此行是為好友吳廷棟回霍山縣老家終老事宜而來,并順帶為涂宗瀛到安徽六安地區尋覓百年之地。他還帶來畫師為曾國藩作肖像,但不甚理想,便又于二十六日約來幕僚吳嘉善,用濕版攝影法為曾國藩照相。吳嘉善不僅是算學家,還是極少數最早學習西方攝影術的中國人之一。曾國藩現存唯一的照片可能就是這次照相所留。
馮卓懷回湘后,曾國藩于七月初二日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首先就為當年在祁門“侵侮良朋、輕離賢俊”之舉表達真誠的歉意,這次南京重逢后,他已“稍釋積年之愧”。他也對馮卓懷將去湘鄉為其尋找百年吉壤表達謝意。自咸豐八年(1858)六月重新出山后,曾國藩已有13年沒有回過老家。在四月初一日的家信中,曾國藩提及自己疝氣雖已愈,眩暈未發,但“目光昏蒙日甚,作字為難之至”,說明他也明白老境已至,已認真地和老友商談身后歸宿問題。由此可見,南京之行是一次和解之旅、交心之旅,時間終歸把矛盾消弭殆盡。
據郭嵩燾日記透露,馮卓懷于八月間兩次去湘鄉,踏遍山水,一共遴選出12處地方,以東臺山之穴位為首選,并逐一繪圖說明。隨后又叫上郭嵩燾一起到東臺山實地論證。東臺山海拔323米,古有“東臺起鳳”之景,列湘鄉八景之首。
這次聯合勘查至九月二十五日結束,他們隨即將結果函告曾國藩。曾國藩就此復信馮卓懷,認為東臺山之選事關本縣文運,不能因一己之私引起士民反感,決定放棄,擬在另外11處備選清單中再作選擇。不過,3個多月后,曾國藩便在南京辭世,那11處地點因各種原因均未能選中,他最終落葬于長沙平塘鎮的伏龍山之陽。
時光荏苒,惹人遐思。曾國藩去世10年后,光緒八年(1882),年屆七旬的馮卓懷自感將不久于人世,就寫下一篇自傳編入馮氏族譜,文中包含一些早年與曾國藩交往的細節。與曾國藩不同,馮卓懷原是苦出身,9歲喪父,倍嘗人生艱難。自中舉后,他一共參加了8次全國會試,但均與進士無緣。在京城長期滯留期間,除與曾國藩、郭嵩燾朝夕相處,還結識了理學大師唐鑒和倭仁,理學名士何桂珍、吳廷棟等。他自認為立身祈向、詩文字法方面得益于曾國藩的影響;刻己勵行,則得益于唐鑒、倭仁及吳廷棟諸先生的啟迪;朋友中則以陳源兗、江忠源、郭嵩燾、郭崑燾尤為深交。而他又深感自己生性頑鈍,人生毫無成就,以一介布衣終老,因此“清夜追思,愧負良友”。字里行間,他對故舊只有感恩,沒有抱怨,但也無可避免地流露出些許自卑心理。這是因為相較于師友,自己顯得“碌碌無為”。深究起來,這無疑與咸豐十年那場并不算嚴重的爭執直接相關,它極大改變了馮卓懷的人生軌跡。
當然,諸友并未對馮卓懷另眼相看。郭嵩燾在長沙與他過從甚密,郭崑燾、曹光漢與他結為兒女親家。他也不至于真的一事無成,除了仕宦生涯以清廉、公正贏得一塊《去思碑》、一本《安鄉政令》,他還主修了《萬縣志》,編撰了故友江忠源的遺集,在籍以課徒為業,以其聲望主持族務,于岐黃、堪輿之術有較高造詣。
作為長期在曾國藩身邊的密友,歐陽兆熊后來曾道出曾、馮兩人當年沖突之事,還對馮氏作出概括性評價:“為人古執,不通世情,好面折人過。”由于有馮氏的前車之鑒,歐陽兆熊跟曾國藩約定只閑住營中,不受差遣,這樣一來也就減少了沖突或分歧的發生,保全了兩人的友誼。他還把馮卓懷其人其事寫入自己的《水窗春囈》一書,馮氏的逸聞因之被多本晚清筆記小說所援引,名曰“有節之士”。
(作者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