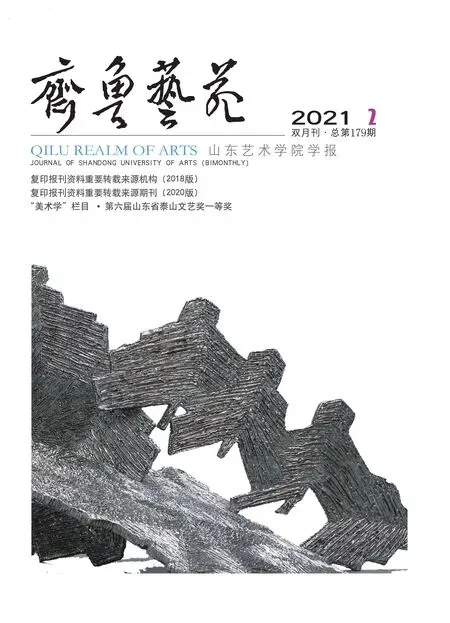從厚涂表現的形成看日本畫的戰后轉型
陸 樂
(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上海 200000)
日本文化受到中國的深遠影響,人們總愛將兩國的藝術相比較,而中國畫與日本畫是其中非常鮮明的一對坐標。但如今提及日本畫,人們便會聯想到其厚重的顏料層與豐富的色彩,卻很難從中看到傳統繪畫的影子。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日本畫基本保持著與中國畫相似的以線造型、薄涂淡染的繪畫手法,雖也有少數畫家用如油畫般厚涂顏料作畫,但并非主流。二戰后,厚涂表現的形成致使日本畫與中國畫在觀感上呈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樣貌。那么,為何戰前一直保持傳統畫法的日本畫在戰后突然改走厚涂之風?關于這個問題的解答,與繪畫觀念乃至社會的變遷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一、厚涂表現的形成
如果像社會學所說,藝術是社會的一面鏡子,[1](P25)那么日本畫一定是其中最明亮的一面。縱觀日本畫史,可以說每一次社會的變革日本畫都從未缺席。不論國粹主義引發的新日本畫運動,還是大正民主帶來的表現主義熱潮,亦或是軍國主義掀起的新古典主義。毋寧說,日本畫的整個發展史都可看作是日本社會跌宕的回響。而伴隨著二戰的失敗,社會再次迎來巨變,日本畫亦隨之翻開新的篇章。
戰后,由于戰時以天皇為核心的軍國主義思想向美式民主的轉變,推崇歐美、貶低傳統的風氣再次彌漫,如同明治的“全面歐化”時期一樣,帶有明顯矯枉過正的傾向。當時,被認為具有軍國主義傾向的傳統文化形式一一遭受審查,甚至歌舞伎表演也大都不被允許。[2](P310)緊張而又對立的氣氛中,飽受“國粹主義”(1)國粹主義:明治20年代日本社會的主流思潮之一,在日本近代發展史上曾經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國粹主義是日本近代由全盤西化走向民族化、本土化的一個歷史拐點,同時它也是日本由謀求民族獨立轉而走向侵略擴張的帝國主義這一過渡性階段中出現的民族主義思潮。影響的日本畫,自然也無法逃脫嚴厲的打壓與批判。此時,以往美術學校中看似理所當然的日本畫科,亦面臨著被取消的危險。(2)1948年武藏野美術學校(現武藏野美術大學)重開時,就有部分教員不贊成設立日本畫科。其中,兒島善三郎最為激進,認為日本畫實在過于簡單,但如果非要教授,一兩個禮拜也足夠了。參見:[日]日本美術院.日本美術院百年史(第八卷)[M].東京:日本美術院,2004.與日益蓬勃的西洋畫相比,日本畫逐漸被貼上“弱勢”“過時”“缺乏現實感”的標簽,將其歸為二流、三流藝術的聲音也日漸高漲。[3]
來自外部的壓力,在日本畫內部以世代交替的方式所演繹。從1890年代開始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一直支撐、奠基、自我變革、推動發展的畫家們大約跨越了四個世代。[4]至戰后,第一代畫家早已隕歿。幕末到明治出生的第二代日本畫家如橫山大觀、川合玉堂都已相繼去世或至暮年。而以小林古徑、鈴木清方為代表,明治中期出生的第三代畫家也并沒有在戰后改變固有的畫風。此時,日本畫的戰后變革便落在了正值盛年的第四代畫家手中。1947年43歲的福田豐四郎于《讀賣新聞》發表了《日本畫的危機》一文,直擊痛點,指出日本畫因循守舊的弊端,并決心打開視野走向國際。[5]以此為開端,畫壇逐漸涌現出一些具有開拓精神的美術團體,求新求變,力圖通過學習西方現代繪畫,以幫助自身擺脫困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屬“創造美術”和“泛真實美術協會”(パンリアル美術協會)。
于1948年成立的“創造美術”,由東京、京都的13名畫家組成。其宗旨在于抵制日本畫壇的封建因襲勢力,追求立足于東方美基礎上的新美,以創造出具有世界性的日本繪畫。[6](P15)而以三上誠、下村良之介、大野崇為首的“泛真實美術協會”也于同年成立,并在次年發表的宣言中寫道:“打破因襲的殿堂,從廣闊的、科學文化的視野中發掘傳統的生命力,以世界為基礎對傳統進行再審視……不論是主題還是肌理都應沖破傳統的局限性,為開拓膠彩(3)膠彩:1930年玉村方久斗結成的方久斗社,就將日本畫按照材料與畫法稱為膠彩畫,意在使脫離一些既成的概念,特別是作為日本畫概念的束縛。將日本畫稱為膠彩畫的觀點,在如今的日本畫壇其仍占有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做出更多的努力。”從二者的宣言與綱領中不難看出,打破因循守舊的牢籠,而將本民族的藝術推向世界是二者共同的夙愿,亦或是當時日本畫壇的共同夙愿。在創造美術與泛真實美術協會的引領下,西方現代油畫中的色彩、肌理與造型語言被引入到日本畫中,盡管這種偏向于西方繪畫的傾向受到了種種批判,卻也給予“日展”“院展”的畫家以刺激,致使一種類似于油畫厚涂的表現開始流行起來。
但藝術是一個集體的行為,[7](P1)一個新表現的確立僅僅依靠畫家的意愿是難以支撐的,繪畫材料上的支持也同等重要。然而戰后初期的顏料開發相對于繪畫的發展是滯后的。戰前作為主要顏料的天然礦物顏料,不僅價格高昂、色相單一,而且限于自身屬性也無法進行油畫般的混色與調和。(4)天然的礦物顏料由于每種顏色都出于不同的材料,同等顆粒大小的顏料同時融于膠液中,會出現明顯的分層。質量重的向下沉,質量輕的向上浮,從而影響發色效果。對于顏料所帶來的掣肘,當時的畫家川端龍子就曾抱怨:“提及顏料的不自由,我亦深有同感。如果如綠松石一樣的寶石也能被制成顏料,那該多好!”[8]實際上,川端的話反映了當時畫家創作時一種普遍的矛盾心理。既渴望如同油畫顏料般的自由表達,但又難以避免礦物顏料所帶來的局限,而要消除這一矛盾,若只是通過開發更多的礦物顏料亦是很難解決的。
需求帶動生產。依托于本國良好的化工基礎,日本畫顏料迎來了空前的發展。隨后,1952年中川惠次以胡粉著色制出的水干繪具(日語名詞,指繪畫顏料)開始投放市場,1955年后以人造原石粉碎制得的新礦物顏料亦得到蓬勃發展,1968年上尾繪具工房也開始了以方解末著色為基礎的合成礦物顏料的開發,加之后續樹脂顏料的相繼問世,戰后的日本畫顏料體系逐漸成形。[9](P153-154)(圖1)而其中的新礦物顏料不僅通過高溫技術具備了如天然礦物顏料般的穩定性,還通過粉碎釉料的手段獲得了與之相似的折光性及砂狀的顯性特征。(圖2)不僅較大程度上還原了天然礦物顏料的顯性特征,還實現了與油畫顏料相同的色域及可調和的物質屬性,為日本畫厚涂表現的形成奠定了物質基礎。

圖1 戰后日本畫的主要繪制材料圖像來源:《日本畫入門》
不可否認,一個表現形式的產生絕不是由某個天才或組織湊巧創造出來的神秘事物,而是與生產它、消費它的社會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這樣的論調中雖然充斥著極端解構主義的色彩,但日本畫的厚涂表現就是在這樣的不斷磨合中形成與發展的。借用美術評論家弦田平八郎的話來說:“戰后的日本畫,提高了西歐近代的造型意識,更加趨近于西洋,同時伴隨著戰后新顏料體系的形成,更使得可以與油畫相媲美的厚涂表現成為可能。”[10]

圖2 顯微鏡下的巖繪具(左側為天然巖繪具, 右側為新巖繪具)圖像來源:《日本畫的傳統與繼承》
二、與“傳統”的疏離
社會巨變下孕育出的表現方式,也同樣反映出極具革新性的色彩。與中國的水墨相似,厚涂表現并非特指某種專門的技法,而是戰后日本畫在表現上的一種共同傾向。事實上,在江戶時期尾形光琳等畫家的屏風畫或是貼了金箔的隔扇畫中也多見厚涂顏料的手法。[11]但與之不同的是,光琳的厚涂主要是平涂色塊,意在配合畫面中的平面裝飾效果,而戰后日本畫的厚涂則是通過反復堆疊顏料來塑造對象,并追求豐富的色彩與肌理效果。(圖3)而這種表現方法,亦起到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應,主要影響分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傳統線條的消失。實際上,日本畫的發展便是不斷提倡色彩、弱化線條的過程。自明治初期,費諾羅薩(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5)費諾羅薩(Ea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西班牙裔美國人,1882年在龍池會名為《美術真說》的演講中首次提出“日本畫”概念,之后與岡倉天心等人領導了新日本畫運動,被稱為“日本美術的恩人”。就提出日本畫改良的主旨是模仿西洋繪畫“Painting”,貶低以水墨為主的“Drawing”,致力于推廣日本畫的“色彩化”。[12](P486)而明治中期“朦朧體”(6)朦朧體:一種繪畫表現形式,從明治時代的橫山大觀、菱田春草等人的某些試驗性繪畫演變而來。“朦朧體”受到西方繪畫的刺激,直接表現自然空氣和光線,并進而把技法的重點從線條轉移到色彩。的出現也更加深刻地履行了這一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戰前的“色彩化”浪潮雖風生水起,卻未動及線條根本,甚至到了大正、昭和時期,由于小林古徑的推崇,曾一度有復興的趨勢。[13](P18)

圖3 日本畫厚涂表現橫截面示意圖圖像來源:作者繪制
直至戰后,厚涂表現的流行,才使得線條徹底失去了在日本畫中的主導地位。而這一點,通過東山魁夷的作品《殘照》便可窺見一斑。(圖4)畫面中,畫家以重疊群山為對象,不拘泥于細節,更專注于整體氛圍的把握,運用色面替代了線條,傳統的留白亦不見蹤影。而不斷疊加斜接的色層,更是形成了豐富而又微妙的色階,由近及遠,營造出氤氳的暮丘之氣,無疑是日本畫“色彩化”的完美呈現。亦如日本學者河北倫明所言:“如果說戰前的日本畫還多少殘存著東方傳統線描之余暉的話,到了今天線描的影子則日趨淡薄,無疑與中國國畫的差別比過去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明顯了。”[14](P4)

圖4 東山魁夷 《殘照》 1947年圖像來源: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
其次,是繪絹的邊緣化。在繪畫中,藝術技巧的嬗變也會使得某種材料獲得或失去藝術資質。[15]戰后的日本畫家們為了承載較厚的顏料層并防止繪畫過程中支持體潮濕所引起的褶皺,通常會選擇在較為厚實且富有韌性的云肌麻紙、麻布甚至是木板上進行繪制。而作為傳統日本繪畫中重要支持體的繪絹,因其遇水變軟易皺、輕薄易破,難以承載厚重的顏料層,在戰后不再是日本畫繪制的首選。
但繪絹的邊緣化不僅僅是一種繪畫材料的衰落,更是一類繪畫的失語。刊登在1991年《藝術新潮》中的一篇文章就寫道:“現代日本畫中幾乎遺忘了絹本技法。雖然如今的日本畫幾乎都畫在紙上,但據自平安時代的大和繪以來,絹上作畫都一直被作為日本畫獨特的表現手法,靈活的暈染技藝和由自然而生的空間表現都是其畫面的特點。到了大正時期,歐洲學畫歸來的年輕畫家們,在摸索如何使日本畫活用西洋式的遠近感與空間表現的同時,習慣性地選用古老的繪絹作為載體。在他們的畫面中通透的空氣感,以及風景、人物,甚至于整個空間的氛圍都在絹布上得以完美呈現,展現出獨特的魅力。而這是現代日本畫中麻紙上厚涂的方法絕對無法表現的。”[16]而今雖在日本畫展覽中依舊可見絹本繪畫的身影,但也多是作為畫家的個性之選。
再次,是卷軸裝裱的隱退。裝裱方式的改變,一直以來也是日本畫變革的重要標志。明治初期,在“文明開化”風氣的推動下,繪畫由壁龕藝術向展廳藝術轉變,致使傳統的卷軸裝裱(軸裝)也開始被西方的額框裝裱(額裝)所取代。(7)1882年和1884年先后兩次舉行的內國繪畫共進會,都明確要求畫面需要進行額裝,禁止使用軸裝繪畫參加展覽。參見:[日]古田亮.日本畫とは何だったのか——近代日本畫史論[M].東京:株式會社KADOKAWA,2018.但至昭和,由于軍事與政治上的成功,民族自信高漲,卷軸又被作為傳統文化重新納入繪畫展覽的范式中(8)1907年開辦的文省部展覽,又重新將屏風、卷軸畫納入展覽會的藝術形式之中。參見:[日]古田亮.日本畫とは何だったのか——近代日本畫史論[M].東京:株式會社KADOKAWA,2018.(圖5)。而戰后,厚涂表現在物理上因繪制的顏料層較厚,又多用動物或植物膠進行粘合,故而徹底風干后質地堅硬且脆,一旦成畫便決定了其不能卷折的特性,使得軸裝徹底隱退,額裝終成為主流。(圖6)
由此,從畫面到選材再到裝裱,日本畫實現了戰后初期對于固有“傳統”的打破,并通過吸收西方現代繪畫完成了戰后的轉型。但此時的日本畫也無疑比任何時候都更加趨近于西方,日本美術評論家桑原住雄生動地將其比作由“日式點心”向“西式點心”的轉變,意指戰后日本畫雖內在仍富有日本精神,但在各個方面已與油畫非常趨同。[17](P175)

圖5 1909年第三回文展展覽現場,可見當時還有軸裝 展示的作品圖像來源:日展公益社團法人

圖6 1958年第八回日展展覽現場日本畫展廳 全部都是額裝作品圖像來源:日展公益社團法人
三、厚涂表現的反思
實際上,日本對于西方的移植本就是功利的與實用的。不論是從明治初期的歐化主義風潮之后出現的傳統與國粹主義,還是從大正民主主義之后興起的法西斯主義,抑或是從戰后歐美化風潮之后引發的回歸傳統的傾向都可以看出,當日本為了擺脫民族危機與實現國家的獨立富強時,他們迅速吸收外來文化以壯大,但一旦目的達到,或當西方的文化移植危及日本的根本利益時,他們又會進行反擊與批判。[18](P7)而進入20世紀50年代,日本社會和生產秩序初步恢復,工農業生產增長很快,情況就如1955年《經濟白皮書》所宣布的那樣,日本已經度過了戰后的艱難時期。[19](P110)隨著國力的增強,日本人的自信也有所恢復,社會中再次出現了“回歸日本”的現象。
這種“回歸日本”的風潮映射在日本畫上便是對于“傳統”的再重視。事實上,經歷過戰后初期的洗禮,日本畫不論在畫面、選材還是裝裱上都已更加趨近于西畫。評論家水尾比呂志更是在看完第八回日展后直言不諱地說日本畫與西洋畫的展覽分類都是多余。[20]這種對于日本畫西化傾向的質疑不斷發酵,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達到了高潮。此時的日本畫家受到西方現代繪畫的影響,在厚涂表現的基礎上,大膽地將油畫、坦培拉、水彩等應用到創作中,打破了日本畫與洋畫之間材料的界限。如阿多諾所言:“藝術材料缺失或更新也將帶來藝術技巧及其構造形式的更遷。”[21]伴隨著厚涂的“失控”與材料的多樣化,關于“什么是日本畫”的詰問亦引發了畫壇的廣泛討論。
1984年5月印發的《美術手貼》雜志,便刊載了以《作為二十一世紀美術的日本畫》為主題的座談會紀實,邀請了著名畫家加山又造、川崎春彥與平山郁夫進行討論。會中三人就戰后日本畫的厚涂表現進行了反思性的探討:
川崎春彥:(現在的日本畫)顏料依舊涂得很厚,畫面也顯得很臟。
加山又造:那應該叫做肌理,主要受到了美國材料觀念的影響,追求畫面的觸感。肌理、材料、色階都進入了日本畫。(后略)
平山郁夫:相較于油畫強烈的肌理效果,線條的表現力確實明顯處于弱勢。如今的日本畫中充斥著各種各樣折衷的表現。為了適應這些,厚涂似乎也會必然出現。
加山又造:對此有許多爭議,他們并非非要厚涂顏色,而是出于與洋畫畫面效果的對抗。但即使像委拉斯貴支畫中那種類似于暈染的手法,最厚處也不過就是一厘米左右。這樣說來,我們到底該如何定義日本畫呢?似乎又很不甘心。(節選)[22]
就像對話中所指出的,畫家們對日益“失控”的厚涂表現不僅表達了擔憂與質疑,甚至面對著日趨西化的日本畫,連其概念似乎都變得難以定義。80年代的一則展評更是批評道:“如今的日本畫,失去了具象的目標,為了變形而變形,為了抽象而抽象,而厚涂也僅僅是為了獲得與油畫一般的肌理而已。”[23]至此,這是否就意味著戰后日本畫向厚涂表現的轉型是失敗的呢?
答案是否定的。實際上,日本畫作為一種文化稱謂其本身就缺乏明確的界定標準。在區分油畫與膠彩畫時,由于材料與表現間的辯證關系,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如果區分西洋畫或是日本畫則需要花費更多的精力。人們通常要使用形式、構圖、色彩等更專業的詞匯,對畫面中代表“傳統”的符號進行甄別,借以界定二者相異的文化內涵。但日本所定義的“傳統”又是極為曖昧的。就像哥倫比亞大學的學者所言:“人們開始討論所謂的‘國粹’——盡管對于該如何定義國粹,人們幾乎沒有達成任何共識。”[24](P187)同理,如若詢問日本人何謂傳統繪畫,自古以來的大和繪、南畫、琳派繪畫等似乎都可以作為日本傳統繪畫的象征。
正是基于這種不確定的“傳統”,亦造就了日本畫特殊的發展模式。如日本學者丸山真男總結的,日西融合一直以一種庸俗化的佛教哲學方式在進行——“某物即某物”,或“物物一如”等。[25](P15)誠然,從菱田春草將琳派與印象派結合,以及竹內棲鳳運用水彩技法革新南畫一樣,日本畫的發展近乎于遵循著“西洋”與“傳統”相對應的原則在進行。介于這樣的規律,二戰后,由于西方現代繪畫的沖擊,日本畫也同樣開始重視與挖掘材料本身的美。這種藝術的物質化趨勢和日本畫材料自發的特殊性相輔相成,厚涂表現的形成似乎也是必然。
但與戰前不同的是,厚涂表現并未與傳統的繪畫形式相銜接,而是將繪畫材料特別是顏料當作“傳統”的載體。以至于有激進者言之:“‘現代日本畫’畫壇為了強調出傳統繪畫與其他畫種的區別,硬是加上了‘傳統’兩字,這就變成了‘現代的傳統日本畫’。不過這里的‘傳統’所包含的內容僅僅指那些如今不值一談的顏料、絹、紙等繪畫載體的特性罷了。”[26](P27)而后,隨著20世紀80年代材料界限的打破,在繪畫形式與材料上日本畫都較之以往更加趨向于西洋,“傳統”也變得越發難以辨識,而這也是引發畫壇激烈探討的根本緣由。
然而,困境亦帶來機遇。可以說在日本畫發展道路上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日西融合,雖然推動了日本畫的發展,但無疑也打破了日本繪畫發展中原有的常性,將自身限制在了西方的語境中,造成了“西洋”與“傳統”間難以調和的歷史困境。(9)黑川雅之在其《日本的八個審美意識》一書的序言中寫道:“現在的日本人都已經淪為西方世界觀的奴隸了。”但自厚涂開始,在形式與材料上對于西洋的模仿走向極致后,畫家們不得不開始直面自身。他們或者拓展新的表現領域,或者在傳統領域中尋求發展。表現手法或以日本傳統繪畫為基礎,或受中國傳統繪畫啟示,或學習西方(特別是意大利中世紀)壁畫、蛋彩畫,或受西方當代藝術造型影響,甚或積極吸取傳統設計乃至動畫藝術要素。[27]就如畫家西山英雄的觀點:“我認為日本人畫的畫都可稱為日本畫。”[28](P3)此時,人們也開始以更加宏觀的角度看待日本畫,其概念也從狹義的日本畫引向廣義的日本畫,定義也越發開放且具有包容性。
小結
事實上,東亞的美術都帶有相同的煩惱,亦可稱為一個命中注定的共同問題。那就是兩者都擁有著傳統美術與外來美術并存或對立的格局。[29]與日本不同的是,以水墨畫為代表的中國畫傳承路徑更具有連續性,相對固定的材料及繪畫語言也造就了中國畫中不可動搖的筆墨體系。而作為明治后出現的近代日本畫,一方面汲取西方“現代”的養分,尋求自己身的發展與蛻變;另一方面,又極力延續著傳統日本畫的形態。基于日本畫中傳統的不確定性,日本畫的畫家也以極其矛盾的心態在“傳統”與“現代”的繪畫形式之間搖擺徘徊,甚至呈現出傳統繪畫形式與西方繪畫一一對應的發展形勢。而厚涂表現的確立,無疑打破了這一局面,雖然在繪畫表現、材料選用及裝裱都更加趨近于西方繪畫,但隨著西方架上繪畫的衰弱,同樣也標志著以厚涂表現為開端的對油畫的模仿走到了盡頭,日本畫也不得不從自身出發,選擇屬于自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