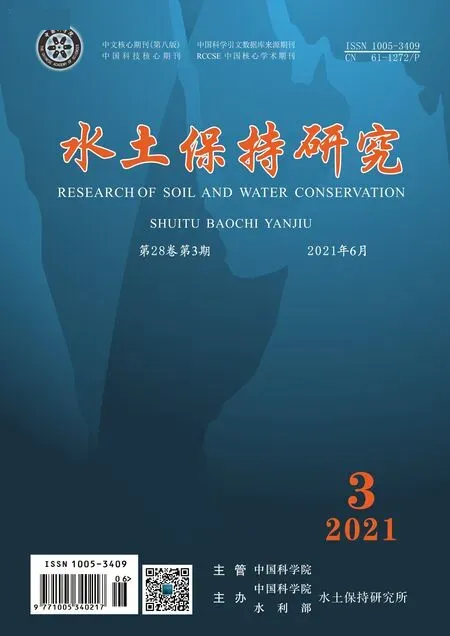河谷型城市“三生”空間競爭與生態環境效應
——以蘭州市為例
馮 濤, 石培基, 張學斌, 劉春芳, 張韋萍
(1.西北師范大學 地理與環境科學學院, 蘭州 730070; 2.甘肅省土地利用與綜合整治工程研究中心,蘭州 730070; 3.西北師范大學 社會發展與公共管理學院, 蘭州 730070)
城市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最為劇烈的地區,而土地是城市地域空間的實體表現形態與核心主體[1],也是全球環境變化和可持續化發展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2-3]。緊湊集約、功能互濟、宜居宜業、順應山河的用地方式,是河谷型城市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空間支撐。但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的快速發展,各種土地利用類型的爭奪與沖突日趨激烈[4],在生態文明和綠色發展成為主流的當下,明晰“生產—生活—生態”功能間的作用機理及博弈過程,既是科學開展國土空間開發的前提[5],也是河谷型城市在較強空間約束下實現“生產集約高效、生活宜居適度、生態山清水秀”目標的必然選擇。“三生”空間是指生產空間、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是在傳統土地利用分類基礎上,以土地類型主導功能和人的發展層次需要為導向進行空間劃分的結果。其中生產空間以提供工農業產品為主導功能,包含農業和工礦生產空間;生活空間以提供人居環境為主導功能,包含城鎮和鄉村生活空間;生態空間以提供生態產品、生態服務和緩沖隔離區為主導功能,包含林地、草地、水域和其他生態空間等[6]。
近年來學者們從不同視角、方法和尺度開展“三生”空間競爭格局及其生態環境效應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 關注時空演變格局及其對應的生態環境質量指數變化。如苑韶峰、楊清可、焦露、白如山、羅剛等學者,通過土地利用轉移矩陣、重心遷移模型、生態環境質量指數、土地利用功能轉型的生態貢獻率等方法,分別從經濟帶[7]、三角洲[8]、省域[9]、都市圈[10]和市轄區等[11]不同尺度進行了研究。(2) 構建“三生空間”沖突模型進行分析和模擬預測研究。如廖李紅借鑒景觀生態指數方法,構建空間沖突指數進行分析[12];趙旭構建空間沖突測度模型,測算“三生”空間沖突變化[13];陳喜東對蘭州市主城區建設用地增長與空間布局進行模擬,并分析其景觀生態格局響應特征[14];張磊基于三生空間用途沖突的互斥視角,形成工業用地的空間配置方案[15]。(3) 關注“三生”空間演變引起的生態風險或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變化研究。如趙越基于景觀擾動指數與景觀脆弱指數,構建土地利用生態風險模型,研究區域土地利用風險時空變化與驅動力[16];秦方采用改進的當量因子法,對河南新鄭市土地利用轉型及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進行評估[17];周文霞采用修正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系數,測算蘭州市土地利用變化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18]。(4) 關注“三生”用地的耦合協調時空分異。如王成結合國土空間規劃“三生”空間理論與耦合協調模型,定量測算鄉村三生空間功能及耦合協調度[19];張軍濤對中國省域尺度三生空間的耦合協調水平及其空間分布特征進行了實證分析[20]。
國內“三生”空間演變格局及其生態環境效應相關研究成果日趨豐富,但多數集中于長江流域和東部發達地區,而對黃河流域和中西部地區的關注較少,特別是地理約束趨強、梯度特征顯著、“人—地—城”矛盾突出的上游河谷型城市的新近研究更為缺乏。隨著“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21],如何優化河谷盆地“三生”空間與生態環境,成為支撐黃河上游地區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本文以蘭州市為例,分析和揭示河谷型城市“三生”空間的競爭格局及其生態環境效應規律,以期為河谷型城市國土空間規劃與高質量發展提供決策參考。
1 研究區概況、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蘭州古稱“金城”,是黃河上游典型的高原河谷型城市,甘肅省政治、經濟、文化與科技中心,絲綢之路經濟帶重要的綜合性交通樞紐,轄5區3縣(含蘭州新區),總面積約為13 083 km2。地勢西南高東北低,海拔1 358~3 670 m,河谷盆地與黃土丘壑發育,分為山地、半山地與河川地,境內分布有黃河、湟水河、大通河、莊浪河、宛川河等黃河流域干支流水系。常住人口379.09萬(2019年末),城鎮化率81.04 %,主要集中分布在不同等級的串珠狀河谷盆地之中。
1.2 數據來源
1995年、2018年兩期土地利用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http:∥www.resdc.cn)的“中國多時期土地利用/土地覆蓋遙感監測數據庫”(CNLUCC)。該數據基于美國陸地資源衛星Landsat MSS,TM/ETM和Landsat 8,采用人機交互目視判讀方式解譯,總精度88.95%。CNLUCC分類體系為兩級,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設用地、未利用地6個一級土地利用類型和25個二級土地利用類型。DEM來自地理空間數據云(http:∥www.gscloud.cn/)GDEMDEM 30 m分辨率數字高程數據。

圖1 研究區概況
1.3 研究方法
1.3.1 土地面積變化強度
(1)
式中:Ri表示土地面積變化強度;St和St+1分別表示土地面積變化前后兩個年份對應的某類“三生”用地總面積。
1.3.2 土地類型轉移矩陣 土地利用類型轉移矩陣可以表示不同類型“三生”用地相互轉換的面積及所占比例信息,進而確定研究區土地轉換的主導類型,其數學表達式如下:
(2)
式中:S表示土地面積;n為土地利用類型總數;i和j分別表示轉型前后的土地類型。
1.3.3 土地利用重心 土地利用重心是指研究區內某土地類型的平均分布點位,土地重心的遷移方向和距離,可以表示土地在特定方位的變化強度。
(3)
式中:Xt和Yt分別表示研究區第t年某類用地重心的經度和緯度;Sti表示第i個土地斑塊的面積;Xi表示第i個土地斑塊的經度;Yi表示第i個土地斑塊的緯度;n表示該類型土地斑塊總數。
1.3.4 海拔與坡度分異 將蘭州市分為“1 500 m及以下,1 501~2 000 m,2 001~2 500 m,2 501~3 000 m,3 000 m以上”5個海拔區間,以及“0°~2°,2°~6°,6°~15°,15°~25°,25°及以上”5個坡度區間,分析各類“三生”用地面積變化與地形的關系,探究河谷型城市“三生”空間競爭的地形梯度特征。
1.3.5 生態環境質量指數 依據“生產—生活—生態”土地類型主導功能分類,結合蘭州市土地利用類型特點,借鑒李曉文與崔佳[22-23]的研究成果,將生產空間劃分為農業生產空間(耕地)、工業生產空間(其他建設用地);生活空間劃分為城鎮生活空間(城鎮用地)、鄉村生活空間(農村居民點);生態空間劃分為林地生態空間、草地生態空間、水域生態空間和其他生態空間(裸土地)。“三生”空間的生態環境質量指數見表1。

表1 土地類型主導功能分類及其生態環境質量指數
1.3.6 土地利用功能轉型生態貢獻率 指某種土地利用主導功能地類變化對所導致的區域生態質量改變的貢獻率,可定量表示各類功能用地的相互轉換對區域生態環境的影響,有利于探討造成區域生態環境變化的主導因素[6],其表達式為:
(4)
式中:LEI表示土地利用功能轉型生態貢獻率;LE0和LEt分別表示土地利用功能轉型前后的生態環境質量指數;LA表示發生土地功能轉型的面積;TA表示研究區土地總面積。
2 結果與分析
2.1 “三生”空間面積變化與轉移類型
河谷型城市“三生”空間分布深受地形條件制約影響,伴隨著快速城鎮化進程,生產、生活空間顯著擴張,生態空間總體萎縮,但不同類型、不同區域的生態空間情況有所不同。由附圖3可以看出,生產空間、生活空間作為人類活動的主要場所,具有靠近河流水源與平整土地的特點,主要分布在黃河干流、湟水河、大通河、莊浪河、宛川河河谷及其支流溝谷地帶以及秦王川盆地;生態空間受人類活動干預較小,主要分布在河谷盆地外圍的廣大黃土丘壑區,近郊的連城、吐魯溝、興隆山等森林公園或自然保護區,以及遠郊的高海拔山區。
由分析統計可知,1995—2018年期間,工礦生產空間和城鎮生活空間分別擴大為原有的11.36倍和1.94倍,呈現快速擴張態勢,主要集中于秦王川盆地南部(蘭州新區),城關區雁灘、九州、青石片區,安寧區西部,榆中縣和平鎮與永登、皋蘭縣城。與此同時,農業生產空間(減少7.87%)、草地生態空間(減少2.23%)出現面積萎縮;林地生態空間(增加3.67%)、水域生態空間(增加5.19%)面積小幅增加。其他生態空間(裸土地)增加40.32%。
蘭州市“三生”空間類型轉換中,農業生產空間和草地生態空間成為轉出面積最大的兩類用地,“耕—草”互轉成為最顯著的土地轉換方式,說明在農牧交錯的黃土高原河谷地區,農牧兼營的生產方式下,“退耕還草”與“占草開耕”的行為同時存在(表2)。此外,轉換面積超過100 km2的土地轉換方式還有:農業生產空間轉為工礦生產用地、農業生產空間轉為城鎮生活用地、農業生產空間轉為鄉村生活用地、林地生態空間轉為草地生態空間、草地生態空間轉為工礦生產空間、草地生態空間轉為林地生態空間。由此可知,1995—2018年蘭州市快速的土地城鎮化進程中,城鎮生產—生活空間對耕地和生態空間的擠占較為顯著,林地和草地兩類生態空間的彼此轉換,也較為突出。

表2 1995-2018年蘭州市“三生”空間轉移矩陣 km2
2.2 “三生”空間梯度分異與重心遷移
蘭州市“三生”空間地形梯度特征見表3—4所示,農業生產空間在河谷川區和階地總體萎縮,并向海拔2 500 m以上、坡度15°以上的高海拔坡地“躍遷”,體現出河谷盆地型城市土地開發與“占補平衡”進程中,耕地從河川地逐步被“邊緣化”的總體特征,高坪地區農田提灌設備的完善,高原農業生產技術的推廣推動了這一進程。工礦生產空間與城鎮生活空間在海拔1 501~2 000 m、坡度6°以內的河谷地帶快速擴張,并向海拔2 500 m以內的高臺高坪及緩坡地帶蔓延,呈現明顯的“爬升效應”,主要是受房地產開發和工業園區布局的影響,反映出河谷型城市有限的土地儲量與生產、生活用地剛性需求的矛盾。鄉村生活空間在各海拔和坡度區間小幅擴張,與農村宅基地的適度發展相符。林地生態空間在河川地區萎縮,較高海拔地區擴張,體現了生態空間在河谷川區讓位于城市建設,轉向山區的特征。草地生態空間在各海拔、坡度地區均有萎縮,成為生產、生活空間擠占的重點對象。水域除河谷川地略有萎縮外,均有小幅擴張,是由于伴隨著“耕地上山”,相應的水渠、坑塘等水利設施有所增加。其他生態空間(裸土地)在3 000 m以上地區因森林恢復而減少,而在1 500~2 000 m,2°~6°的緩坡臺地,以及6°~15°坡度的黃土丘壑區小幅擴張,主要原因是草地退化與耕地撂荒。

表3 蘭州市“三生”空間海拔分異變化 km2

表4 蘭州市“三生”空間坡度分異變化 km2
各類空間在河谷盆地內的競爭十分激烈,工礦生產空間、城鄉生活空間的擴張在河谷平坦地區占據優勢,海拔2 000 m以下地區擴張351.02 km2,坡度6°以下地區擴張357.42 km2。城鎮空間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具有明顯的“擴張效應”與“爬坡效應”,爬坡強度隨海拔和坡度增大而遞減。由于城鎮空間對農業空間、生態空間形成擠占、脅迫和抬升影響,使得耕地質量下降、水土流失等生態風險和隱患不容忽視。
蘭州市“三生”空間重心具有相對獨立而明顯的位移。城鎮空間重心移動幅度明顯大于農業空間和生態空間。受到蘭州新區開發建設的影響,工礦生產空間重心向北偏東方向遷23.63 km,城鎮生活空間重心向北偏西方向移動14.50 km,均從安寧區遷移至皋蘭縣境內。其他生態空間(裸土地)重心向西偏北方向移動15.42 km,側面印證了蘭州市東南方向的榆中縣和平鎮、定遠鎮等地開發強度較大。耕地、林地、水域重心移動幅度較小,說明蘭州市農業生產空間與主要生態空間的基本格局保持穩定。
2.3 “三生”空間轉型的生態環境效應
“三生”空間因主導功能的差異,致使生態環境質量也存在客觀差異,可以通過賦值方法確定各類用地的生態環境質量指數。結合表1信息可知,蘭州市共有7種大小不等的生態環境質量指數。為便于進行生態環境質量的變化分析,將生態環境質量指數由低到高7個等級依次賦值為1~7,對應賦予1995年和2018年“三生”空間土地柵格,并用2018年的生態環境質量數據與1995年的生態環境質量數據進行柵格相減運算,將差值在[-2,+2]的像元分布區定義為生態環境質量穩定區,差值在[+3,+6]的像元分布區定義為生態環境質量改善區,差值在[-6,-3]的像元分布區定義為生態環境質量惡化區,結果見圖2。
經計算可得,蘭州市生態環境質量穩定區面積9 960.630 9 km2,約占土地總面積的96.44%,說明全市生態環境質量總體穩定。生態環境質量改善區面積為123.668 8 km2,約占土地總面積的1.20%;生態環境質量惡化區面積為243.700 3 km2,約占土地總面積的2.36%。可以得知,蘭州市“三生”空間轉換面積比例較小,生態環境質量總體平穩,但在“三生”空間的邊緣地帶,生態改善和生態惡化兩種趨勢并存,生態改善區面積約為惡化區的50.76%。生態改善區主要分布在蘭州市主城區南部皋蘭山,榆中縣夏官營與興隆山,蘭州新區西北部的上川鎮—秦川鎮西部;生態惡化區主要分布在城關區北部的大沙坪、九州片區、青石片區,安寧區北部與北濱河路東段,皋蘭縣水阜鎮、九和鎮、黑石鎮,以及蘭州新區東南部的中川鎮和西岔鎮一帶。全市生態環境質量總體呈現“南高北低”的格局態勢,是因為主城區南部地勢起伏較大,土地開發難度較大,保留了林草等生態空間,生態環境質量指數較高;而主城區北部存在較多的房產開發項目和工業區項目,“削山造地”使得部分生態空間轉為生產與生活空間,加之蘭州新區的設立與開發,使得秦王川盆地部分農田和草地轉為建設用地,因而北部的生態環境質量指數有所下降。

圖2 蘭州市生態環境質量變化區
分析不同用地轉換方式對生態環境質量變化的貢獻,有助于河谷型城市生態風險管控與生態格局優化。研究表明,促進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的主要行為因素依次為:(1) 退耕還草(LEI=81.39%),廣泛分布在黃土溝壑地區;(2) 退耕還林(LEI=7.15%),集中分布在永登縣大通河流域連城鎮、河橋鎮,蘭州新區北部上川鎮、西岔鎮北部,榆中縣宛川河流域夏官營鎮、金崖鎮、龍泉鄉;(3) 草地向林地自然演替(LEI=3.76%),主要分布在永登縣連城自然保護區,吐魯溝國家森林公園,榆中縣興隆山西部,永登縣北部武勝驛鎮山區;(4) 荒山草被恢復(LEI=2.05%),分布在榆中縣興隆山區新營鎮、甘草店鎮,G30(連霍高速)北龍口沿線,以及永登縣七山鄉南部—苦水鎮西部山區。致使生態惡化的主要行為因素依次為:(1) 占草開耕(LEI=63.63%),廣泛分布在黃土溝壑地區;(2) 占草開工(LEI=9.83%),集中分布在蘭州新區東南部,安寧區—皋蘭縣毗鄰的部分房地產企業開發用地,皋蘭縣水阜鎮、九和鎮與黑石鎮,以及城關區九州、青石片區等地;(3) 占林開耕(LEI=4.66%),主要分布在永登縣大通河谷兩側(連城鎮、河橋鎮)與莊浪河沿岸,紅古區湟水河沿線,西固區柴家臺,七里河區G75蘭海高速北段及八里窯鎮,榆中縣興隆山山麓局部地區。(4) 草地退化(LEI=3.31%),主要分布在永登縣苦水鎮西部山區,榆中縣清水驛鄉東部山區,高崖鎮,園子岔鄉,以及城關區北部青石片區。
3 結 論
(1) 以蘭州市為代表的河谷型城市,發展空間深受地形約束,“三生”空間競爭沖突十分劇烈。城鄉生活空間和工礦生產空間以河谷川區為中心,呈現“立體式”快速擴張,“爬坡”效應明顯,受蘭州新區建設影響重心明顯北移,對農業生產空間和生態空間形成較強的擠占、脅迫與抬升作用。
(2) 受城鎮空間擴張沖擊和生態環境建設影響,草地生態空間大幅減少,農業生產空間總體減少,但林地和水域生態空間小幅增長,均向更高海拔和坡度的外圍郊區轉移;其他生態空間(裸土地)以中等海拔與坡度地區為核心有所擴大,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撂荒和地產開發等因素引致的生態風險不容忽視。
(3) 蘭州市生態環境質量總體穩定,呈現“南高北低”的格局態勢,主城區邊緣的山麓臺地以及蘭州新區南部成為“三生”空間競爭的主要地區,改善區面積只占惡化區的50.76%。耕地和草地的相互轉換,成為影響全市生態環境質量變化的主要貢獻因素,退耕還林、草地向林地演替、荒山草被恢復是生態改善的重要因素,占草開工、占林開耕、草地退化是生態惡化的重要因素。
狹窄的地域空間約束與城市發展擴張對土地的需求,是導致河谷型城市“三生”空間競爭的主要原因。蘭州市未利用土地資源較少,后備土地資源嚴重不足,生態空間被生產空間與生活空間擠占、壓縮的過程中,生態風險依然較大,這與汪建珍等之前的研究結論一致[24];在蘭州市生態環境質量變化的區域差異方面,由于研究時段和測度方法的差異,與潘翔的研究結論存在一定共識和不同之處[25]。建議在蘭州市國土空間規劃與管控過程中,加強對草地生態功能的重視,處理好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與城鎮開發邊界的關系。受方法手段和數據精度影響,本研究尚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針對生態環境效應的變化測度,只針對土地類型轉換導致的部分,對于其他細節因素(如植被種類差異、時相變化、氣候變化等)引起的下墊面變化暫未考慮;生態環境質量指數的賦值主要引用已有研究作為依據,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觀性;對于生態空間的劃分,未考慮不同植被覆蓋度造成的內部差異等,今后將針對這些問題開展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