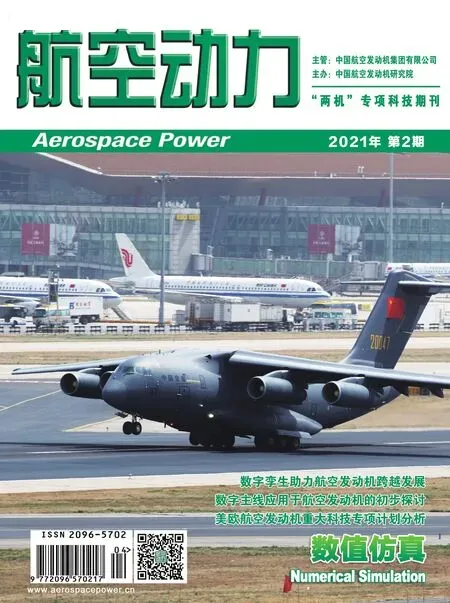航空發動機內流全場流動的大渦模擬
■ 張漫 王錚鈞 王晶 孟晟 馬靜 / 中國航發商發
航空發動機整機內流場的大渦模擬是目前國際仿真技術的前沿。多部件耦合仿真可以消除部件獨立仿真的“邊界效應”,充分評估貫穿于發動機部件之間的流動特征,可在多部件匹配優化、整機氣動性能評估中發揮作用,并應用于日益發展的數字孿生、虛擬樣機等技術中。
航空發動機是一個前后流通、各部件耦合工作的整體。在常規的發動機設計過程中,首先采用低維、時均的計算方法對發動機總體性能進行分析,獲得壓氣機、燃燒室、渦輪等部件在交界面處的氣動熱力參數,這些參數通常以一維集總的“點”或二維分布的“線”的形式表征;然后根據交界面的氣動熱力參數要求,通過邊界條件賦值將整機分解為各個獨立的研究對象,分別開展壓氣機、燃燒室、渦輪三大核心部件的設計分析與試驗測試;完成后再裝配成核心機或整機開展部件匹配調試與整機性能測試。
在各部件獨立開展的仿真分析中,作為邊界條件的氣動熱力參數空間維度低且不隨時間發生變化,無法準確反映貫穿于部件之間并隨發動機運行瞬變的三維、非定常特征。例如,壓氣機喘振造成的燃燒室進口流量脈動與不穩定燃燒、燃燒室出口旋流高溫熱斑在渦輪葉片中造成的非均勻熱負荷等。這種由于部件“邊界效應”而人為引入的缺陷,使得各部件計算獲得的流場與真實發動機整機流場存在偏差,極大地影響了部件獨立預測分析結果與整機試驗結果的一致性。
筆者及研究團隊以航空發動機核心機為研究對象,采用湍流燃燒大渦模擬技術對高壓壓氣機、燃燒室、高壓渦輪耦合通流流場開展數值仿真,介紹了幾何模型、數值計算模型中的一些要素,并分析了整機內跨部件傳播的非定常特征以及上下游部件的相互影響效應,以期初探整機內流場數值仿真技術的可行性及其在工程應用中的技術價值。
航空發動機內流多部件耦合仿真技術
從20世紀60—70年代開始,工業界逐漸采用計算流體力學(CFD)方法對航空器外流進行仿真,并將計算結果作為工程設計的參考[1]。進入21世紀后,科學研究進一步重視湍流的非定常效應,試圖通過優化或控制流動過程以提升航空器內、外流的氣動熱力性能。因此,一種對湍流流動時間、空間尺度均足夠精確的大渦模擬方法(LES)在業界逐步推廣,成為目前分析航空發動機內部氣動熱力特征的先進工具之一。
然而,航空發動機各部件之間的氣動熱力狀態,包括溫度、壓力、馬赫數(Ma)、雷諾數(Re)等,差異極大,導致多部件耦合的氣動熱力仿真除了要具備寬速域、可壓縮的求解方法外,還須結合實際物理特征,建立恰當的數學模型。在葉輪機械中,葉片表面邊界層轉捩、分離以及通道中二次流、端壁間隙流是主要流動現象,因此數值仿真中須建立恰當的湍流模型與近壁面條件;在燃燒室中,大尺度旋流、剪切與回流用于強化燃料與空氣摻混與穩定火焰,因此數值仿真中須充分評估流動、混合與化學反應時間尺度的差異,建立微尺度下流動與燃燒耦合作用的燃燒模型。當前,上述主要計算方法在各部件的獨立仿真中均有著長足發展、日趨成熟。例如,法國歐洲科學計算研究中心(CERFACS)在2009年開展了環形燃燒室大渦模擬[2],在2019開展了3級壓氣機的大渦模擬[3]。
進入21世紀以來,為進一步提高發動機整機內流的認識,科學研究率先嘗試進行了發動機整機氣動熱力流場的仿真。2003—2006年,斯坦福大學針對PW6000整機內流開展仿真計算[4],在其研究中,采用可壓縮的雷諾時間平均方法(URANS)模擬壓氣機和渦輪內流,采用不可壓縮大渦模擬方法模擬燃燒室流動。這一嘗試在當時是突破性的技術研究,但是由于需要在旋轉部件與燃燒室之間進行仿真方法的切換,導致部件之間的湍流特征時間尺度并不一致,因此該工作所開展的多部件耦合仿真,只是幾何流道耦合,而不是流場的物理過程耦合。

圖1 核心機計算模型示意
最近10年,大規模高性能并行計算技術的快速發展為發動機整機耦合仿真帶來了新的契機。2020年,CERFACS采用20億網格單元、14400核計算節點、仿真分析了DGEN380商用飛機發動機內部的流動與燃燒過程,并揭示了貫穿整機內流場的非定常現象[5]。
航空發動機內流大渦模擬方法
核心機幾何模型
筆者及研究團隊采用一核心機計算模型(見圖1)進行壓氣機、燃燒室和渦輪的耦合仿真。其中壓氣機為10級高壓壓氣機、燃燒室為頭部中心分級的短環形燃燒室、渦輪為兩級高壓渦輪。在整機模型中,燃燒室周向共有18個頭部,每個頭部對應的周向角度為20°。為節省計算資源,數值計算域周向角度取值20°,這一周向角取值可包含一個完整的單扇區燃燒室。為保證非定常計算中葉輪機械轉子葉片、靜子葉片交界面尾跡傳遞不受周向簡化的影響,采用了稠度不變的原則,將原方案中每排壓氣機、渦輪葉片數調整為燃燒室頭部數量的整數倍。因此,本文采用的數值計算域可在發動機周向進行周期性拓展。
在壓氣機與渦輪的幾何建模中,保留由葉型、端壁、機匣所形成的主流流道,省略級間引氣、盤腔引氣、端壁泄漏、氣膜冷卻等次流流道與對應空氣流量的變化。在燃燒室的幾何建模中,保留火焰筒內、外環腔流道,火焰筒內流道以及伸入燃燒室內的燃油噴桿,省略火焰筒氣膜孔、火焰筒懸掛、支撐結構等幾何細節,省略了燃燒室擴壓器、火焰筒內環腔的引氣流路與對應空氣流量的變化。但是,在燃燒室實際工作中,燃燒室內、外環腔空氣經火焰筒壁面冷卻孔流入火焰筒內流道,匯合頭部燃氣流向高壓渦輪。該部分冷卻空氣量占燃燒室總氣量的30%以上,因此不可忽略。在研究中,采用自行開發的火焰筒壁面源項法模擬燃燒室內、外環腔流入燃燒室的冷卻空氣[6](見圖2)。

圖2 壁面源項法對火焰筒壁面氣冷結構的建模示意

圖3 包含壓氣機、燃燒室與渦輪的多部件耦合流道示意

圖4 完善后的燃油二次霧化模型
整個計算域(見圖3)進口為高壓壓氣機支板進口,設置均勻分布的總溫、總壓,并忽略進口空氣的湍流脈動特征。計算域第一處出口為燃燒室火焰筒內、外環腔出口,根據計算出的燃燒室流量分配設置環腔流出流量,并以此流量作為火焰筒壁面源項法中的輸入氣量添加入火焰筒內。計算域第二處出口為高壓渦輪第二級轉子葉片出口,邊界條件設置為靜壓出口。作為燃料的航空煤油以液態形式通過燃燒室內若干離散的噴嘴進行噴射。
在壓氣機、渦輪的靜子葉片流道與燃燒室中,除火焰筒內側壁面外,其余固體壁面為絕熱無滑移壁面。在壓氣機、渦輪的轉子葉片流道中,設置轉子葉片局部流道為旋轉域并根據實際轉速設置域的旋轉速度。葉輪機內流場采用正交網格進行劃分。燃燒室頭部旋流器、火焰筒內流道采用正交網格進行劃分,二者之間的過渡區域采用非結構網格進行劃分,計算域網格總數約為3000萬個。
數值計算模型
為兼顧壓氣機、渦輪中的高馬赫數流動以及燃燒室中的低馬赫數流動,選擇可壓縮的流場求解方式。湍流模式采用Dynamic Smagorinsky-Lilly模型并結合標準壁面函數處理近壁面流動,氣、液兩相流模型采用項目團隊自行開發的二次霧化模型(見圖4),燃燒模型為增厚火焰面模型,化學反應機理為兩步簡化的航空煤油代用燃料(C10H23)與空氣的化學動力學機理。計算域空間離散為二階迎風格式并添加了限制器,時間步長為2×10-7s,求解器選擇雙精度。上述主要計算模型在項目團隊的前期工作中,已通過基礎試驗數據完成了精度與適用性驗證。
計算中,通過監測壓氣機、燃燒室內預置測點的速度脈動與渦輪出口流量判斷流場的計算結果是否達到統計學穩定。計算穩定后,繼續計算7個非定常脈動周期并在期間保存有效計算數據進行統計平均,隨后終止計算并進行結果分析。數值計算工作在中國航發商發高性能計算平臺HPCCII上開展。
航空發動機內流大渦模擬結果
跨部件傳播的非定常特征
圖5為計算獲得的壓氣機與渦輪內流中徑葉高處熵分布與燃燒室中2000K的溫度等值面分布。由圖5可以看出,從壓氣機第一排轉子葉片開始,每一級葉片均產生了明顯的非定常尾跡,這一尾跡流入下一排葉片中,與該排葉片自身的尾跡相互疊加,逐級向下游發展。為定量表征非定常脈動特征在發動機中的傳播,在計算域中取3個典型位置監測速度隨時間的變化,分別位于壓氣機末級導向葉片內部、燃燒室擴壓氣出口、高壓渦輪第一級導向葉片進口(如圖5中P1、P2、P3位置)。

圖5 整機內流場瞬時熵與燃燒室中的火焰面分布

圖6 發動機內3個典型測點氣流速度隨時間的變化特征
圖6 為P1、P2、P3測點速度隨時間的脈動特征。從圖中可以看出,壓氣機末級導向葉片通道中,有著明顯的非定常速度脈動,這是由于上游多級壓氣機轉子所產生的。在前置擴壓器出口,由于氣流在自由通道中突擴,上游速度擾動被顯著衰減,到燃燒室出口時,速度脈動幅值進一步衰減,但是在火焰筒出口仍能觀測到上游非定常流動對下游的影響。
上下游部件的相互影響
為分析多級壓氣機尾跡對燃燒室出口熱斑的影響,對比計算了考慮上游壓氣機與省略上游壓氣機時的火焰筒溫度分布特征(見圖7)。可以看出,當計算中耦合上游壓氣機時,燃燒室出口高溫區在周向、徑向所占區域比忽略上游壓氣機所呈現出的結果更寬一些,燃燒室中時均的高溫火焰面更緊湊。分析認為產生該現象的原因在于壓氣機轉子尾跡掃掠對燃燒火焰帶來了非定常擾動,強化了燃料與空氣的混合程度,使得火焰面更為緊湊,也使得旋流火焰的擴張角度有所提高。
結束語
通過仿真分析可知,發動機上游產生的非定常流動會向下游傳播,并影響下游部件的流動特征。通過初步研究可以看出,發動機內流場多部件耦合仿真,可消除部件之間的邊界效應,完整地分析空氣從發動機流入至流出的全部過程,并揭示之前無法分析的多部件內流耦合作用關系,有助于進一步提升各部件性能設計水平。同時,整機內流仿真也可在數字孿生、虛擬樣機等技術中發揮作用,配合其他學科的仿真方法,進一步助推數字化發動機的實現。

圖7 燃燒室時均火焰面形狀與出口溫度分布云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