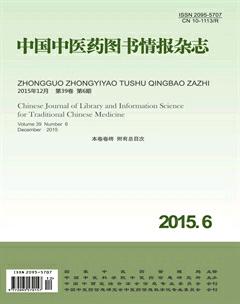基于簡易信息聚合技術的圖書館立體閱讀推廣服務模式研究
譚衡亞 李慧芳 楊建 粟之敦 文潔

摘要:本文闡述了圖書館立體閱讀推廣服務的內涵與意義,以及簡易信息聚合(RSS)技術對圖書館立體閱讀推廣服務的促進作用。分析了圖書館立體閱讀推廣模式的構建要素(主體、用戶、渠道、載體、活動),從樹立品牌、閱讀引導、多方合作3個方面提出了具體的構建策略,基于RSS技術的實際應用,提出該服務模式的實現方式。并以重慶大學圖書館為例,對該閱讀推廣服務模式的實際應用進行介紹。
關鍵詞:圖書館;立體閱讀;簡易信息聚合;服務模式
在當前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浪潮下,科技更新速度不斷提高。目前紙質圖書閱讀量逐漸下滑,更多的讀者開始借助互聯網等技術來獲取信息。這表明當前人們更加追求閱讀的行為是否實用,是否有便捷的信息獲取方式。圖書館應通過閱讀主題推薦等方式吸引更多的讀者,做好圖書館的閱讀推廣服務工作。
1.圖書館立體閱讀推廣服務
1.1圖書館立體閱讀推廣服務的內涵
立體閱讀是圖書館對閱讀進行推廣的一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圖書館傳統的圖書服務思維方式,體現出多層次、創造性的特點,并且更加系統、立體。圖書館通過開展多樣化的閱讀推廣活動,如展現某一作品的多種藝術表現形式,或者將某篇文章的原著和譯著進行對比展示等,能夠提高讀者的閱讀興趣,并加深對作品的理解。圖書館開展多種時空交換的方式,采用多媒體技術,運用多樣化的形式來進行閱讀主題的推廣活動,這種活動的模式就稱為立體閱讀。
1.2圖書館立體閱讀推廣服務的意義
如今圖書館可以將立體閱讀作為一種重要的信息傳播媒介,并根據需要不斷進行拓展。立體閱讀的概念正在不斷得到延伸,但其核心內容依然是依據閱讀展開的,且以整合圖書館資源為主要任務。當前很多學者已經認識到閱讀推廣的重要作用,在閱讀推廣方面進行深入研究,并試圖通過多樣的方式來對信息進行閱讀。立體閱讀有十分豐富的媒介,并改變了傳統的閱讀方式,提倡將傳統閱讀與新興媒介結合起來,進而為讀者提供更為立體、快捷、個性化的信息服務。立體閱讀是圖書館提高讀者理解能力,并促進圖書服務質量提高的有效途徑。
2.簡易信息聚合對圖書館立體閱讀推廣服務的促進作用
根據立體閱讀的相關概念,在開展立體閱讀服務過程中需要多媒體技術、圖書以及互聯網等多維度材料的相互配合,并且需要與主題活動相關工作人員的積極參與。但是由于互聯網技術以及人力等方面的限制,當前圖書館在開展立體閱讀時還存在一些問題,如沒有充分發揮互聯網的作用、無法及時向讀者提供實時閱讀信息等。而采用嘉年華的閱讀方式,雖然可以吸引讀者的目光,但很難滿足讀者對新知識的需求。這與圖書館沒有充分應用網絡技術有關。
簡易信息聚合(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RSS)技術是一種訂閱互聯網上信息的方式,就像訂報紙、雜志、短信服務一樣,通過RSS,您可以訂閱互聯網上感興趣的內容。該技術的應用能夠有效實現信息在線共享。使用RSS技術時,首先需要下載并安裝RSS閱讀器,仔細觀察一些網站,可以看到被標記為“XML”或“RSS”的橙色圖標;點擊黃色的RSS閱讀器訂閱,會在瀏覽器中新打開一個網頁(這個網頁有可能全部都是代碼);直接復制網址,然后在個人電腦的RSS閱讀軟件上選擇增加訂閱選項,粘貼網址,輸入網址名稱,點擊確定,設置更新此訂閱時間、目錄等。這樣一個RSS閱讀器就訂閱成功。當需要時,直接通過該RSS本機客戶端瀏覽網頁內容,在線閱讀,隨時獲取所需的信息。在不打開網頁的情況下,讀者也可以利用RSS搜索工具來閱讀相關網站內容。
RSS的應用空間較大,我國一些圖書館已經利用RSS技術開展了相關的閱讀服務工作,并將RSS技術應用于立體閱讀服務中。當前RSS技術已經為圖書館閱讀推廣活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圖書館可以借助RSS這種簡易信息聚合閱讀器,促進立體網絡空間發揮其真正的作用,構建立體網絡閱讀平臺,進而解決閱讀信息的時效性問題,以此促進立體閱讀服務的順利推廣。
3.基于簡易信息聚合技術的圖書館立體閱讀推廣服務模式構建
3.1模式的基本要素
圖書館基于RSS的立體閱讀推廣服務模式的構建要素,具體包括主體、用戶、渠道、載體、活動等5個方面。圖1為圖書館基于RSS技術的立體閱讀推廣服務模式的大體架構。其中主體是開展立體閱讀推廣活動的組織結構,如圖書館專門的推廣部門、學生志愿者等,他們為推廣活動的實施提供了保障。用戶為閱讀推廣活動的參與者,如教師、學生等,并倡導用戶的主動性與交互性。閱讀推廣的平臺即為渠道,如圖書館自建渠道以及新媒體平臺等。立體閱讀推廣的載體有電子書或者紙質圖書等,這是進行閱讀推廣的必備條件。而多樣化的活動形式是閱讀推廣的重要內容,也關系到活動開展是否能夠取得預期效果。
3.1.1主體 圖書館在開展立體閱讀推廣活動過程中,不僅需要構建完善的組織結構,即推廣活動的主體,也需要加強與其他結構的溝通與合作,并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參與其中。圖書館作為閱讀推廣的主體毋庸置疑,但也需要健全的組織機構提供保障。因此,圖書館不僅需要加強對閱讀推廣的重視,也需要各部門加強協作與交流。同時圖書館可以發揮自身吸引志愿者的優勢,讓讀者志愿者參與到閱讀推廣活動中,最大限度地激發讀者的興趣。
3.1.2用戶 雖然圖書館并沒有固定閱讀推廣的主要用戶群體,但依然以學生和教師居多。目前部分圖書館開展的閱讀推廣活動僅將對象限定為學生,忽視了教師群體的需求。實際上教師也是數量龐大的閱讀群體,且教師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學生的閱讀傾向,并通過一定的方式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因此,圖書館在開展閱讀推廣實踐時應該將教師納入重點用戶中。
3.1.3渠道 開展形式多樣的閱讀推廣互動,并改變傳統的推廣方式,能夠在提高閱讀者興趣的同時減少推廣實踐的阻力。目前大部分圖書館的閱讀推廣實踐多在校園內開展,與閱讀者溝通有固定渠道,如宣傳欄、網站論壇等。在新媒體的應用方面還較為少見,如還未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臺。因此,圖書館不僅應該利用固有的推廣渠道,也應該充分借助新媒體,讓渠道得到拓展。
3.1.4載體 在互聯網以及信息技術高度發展的推動下,圖書館的信息載體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圖書館在閱讀推廣實踐中不僅應該利用紙質閱讀載體,也應該借助現代科技來豐富閱讀載體,如通過手機、互聯網等進行形式多樣的閱讀推廣實踐,以滿足現代人的閱讀需求。當前電子閱讀與紙質閱讀是相互分離的,圖書館應該做好電子閱讀的數據統計與推廣工作,并依托數字加工等技術來發現更多的閱讀載體。
3.1.5活動 圖書館開展立體閱讀推廣服務的實例說明,品牌活動能夠取得較好的效果。這是因為開展品牌化的活動,不僅可以在讀者中形成較大的影響,也可以保持活動的傳承性,并為活動的后續開展創造條件。開展品牌閱讀推廣活動要求新穎有創意,并且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在實踐過程中對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創意、營銷能力等有較高要求。
3.2模式的構建
3.2.1精心調研策劃,樹立立體閱讀推廣品牌 立體閱讀推廣首先以圖書館為核心主體,主要的推廣形式有“讀書”和“讀人”兩種。在開展推廣活動中,應該做到精心策劃調研,充分掌握讀者的閱讀興趣和愛好。同時在選題策劃方面應有所創新,盡量選擇質量高、讀者愛讀的作品作為主要推廣內容,在宣傳推廣過程中多與讀者互動。通過上述措施,可以保障立體閱讀推廣服務的順利實施。
在按照慣例開展立體閱讀活動時,還可以在這些活動中有目標、有選擇地樹立立體閱讀品牌,以激發讀者參與的積極性。比如在“讀書”活動中將“圖書漂流”樹立為活動品牌,或構建相關“圖書漂流”網站,進而讓圖書資源得到高效利用。
3.2.2集成網絡資源,發揮數字閱讀引導作用 現代人更加熱衷于網絡閱讀,圖書館要充分利用該趨勢來開展網上立體閱讀推廣工作。網上推廣主要形式是“讀媒”,可以通過以下方式來實現。一是開展數字化資源閱讀服務,讀者可以選擇常用的數字化閱讀器來瀏覽所需內容;二是構建圖書館官網,借助推薦閱讀書目和構建網絡溝通平臺的方式,打破空間與時間限制,讓讀者加深對推廣主題的理解;三是利用微博等社交網絡工具積極進行立體閱讀推廣,如可以開通微博來發布相關閱讀資訊,還可以同時轉發各類與閱讀相關的微博信息,以吸引讀者前來瀏覽;四是構建移動圖書館,用戶可以從移動終端設備上對圖書館資源進行查閱,并可以獲取閱讀和業務查詢等服務。在集成各類網絡資源的過程中,圖書館應該做好讀者數字閱讀的引導工作,讓讀者獲取更多有價值的資源,以提高立體閱讀的有效性。
3.2.3增強合作與交流,確立多方合作的保障機制圖書館與其他圖書館、其他機構聯合起來,一起進行立體閱讀推廣實踐,即館外立體閱讀推廣,這樣可以讓活動規模得到拓展,并吸引更多的讀者。具體實踐措施包括兩種。一是加強與其他圖書館的交流合作,建立區域性圖書館聯盟,聯合開展“圖書漂流”等系列立體閱讀推廣活動。二是加強與其他機構的交流合作,如出版、文化機構等,聯合開展精品圖書展覽等活動。通過多樣化的推廣形式,充分整合與利用各機構的資源,真正實現資源的利用價值。
3.3模式的實現條件
根據RSS技術的應用原理,圖書館可以運用3種方式來實現立體閱讀推廣服務。
3.3.1借助RSS信息聚合服務模式 圖書館可以依托Web技術開展信息聚合服務,對專屬學科的RSS數據源進行搜集整理,并利用RSS聚合工具構建專門的信息聚合門戶,進而為用戶提供閱讀推廣服務。并在RSS聚合門戶中管理各種立體閱讀資源,然后借助網頁導航為用戶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務。閱讀者只需要進入RSS聚合門戶導航頁面,就可以獲取與立體閱讀主題相關的所有內容。
3.3.2建立閱讀博客空間 隨著博客的產生與發展,催生了RSS這種簡易信息聚合閱讀器。圖書館可以結合RSS的特點來構建立體閱讀博客空間,讓讀者與圖書館、讀者與管理員之間形成立體的交流關系,進而構建一個立體閱讀交流社區。讓對閱讀主題感興趣的讀者之間能夠有效交流溝通,并且分享最新熱點信息,把握多種文獻資源之間的聯系,以此獲得更多感興趣的閱讀信息。
3.3.3借助RSS的個性化信息推送功能 近年來,很多圖書館開始借助RSS技術進行個性化信息推送服務,并在聚合門戶構建中更加注重個性化。圖書館可以借鑒這種個性化信息服務模式,根據用戶的需求建立相應的特征信息庫,并將基于RSS的圖書館立體閱讀服務模式分為信息獲取與存儲、RSS應用、個性化服務、系統管理幾個模塊來進行構建,在了解讀者需求的基礎上,為他們提供個性化的立體閱讀推廣服務。
4.應用實例
本文以重慶大學圖書館為例,對基于RSS的圖書館立體閱讀推廣服務模式的應用進行闡述。該館將信息服務作為基準,堅持文化育人的服務理念,將讀者作為服務中心,結合RSS的應用特點開展了“書友會”、閱讀品牌推廣等形式多樣的立體閱讀推廣活動。
4.1完善閱讀推廣架構的具體措施
重慶大學圖書館于2012年設置了文化育人中心,并將其作為立體閱讀推廣的主要部門,負責本校的立體閱讀推廣活動。該館在不斷補充傳統圖書文獻資源的同時,也根據讀者的需求擴充了電子閱讀資源。廣泛收集讀者意見,在分析讀者意見與圖書閱讀量的基礎上,及時補充館藏資源。該館一直以來將讀者作為服務核心,并將閱讀推廣作為重要職能。重慶大學圖書館也非常注重與其他圖書館的合作,并借助外界力量來開展閱讀推廣實踐。該館有自己的媒體渠道,也可以獨立開展各種文化服務活動。此外,該館根據讀者需求開展了新書推薦等一系列閱讀推廣活動,力求打造重慶大學的閱讀品牌。
4.2通過“書友會”增強與讀者的互動
重慶大學圖書館構建了“書友會”組織,讓教師和學生參與其中,并在各種活動中與這些教師和學生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同時基于RSS信息聚合門戶開設了網上虛擬“書友會”,通過積分獎勵、書評等方式與讀者進行在線交流,在與讀者互動中促進了立體閱讀推廣的有效開展。
5.小結
圖書館構建基于RSS的立體閱讀推廣服務模式,屬于一項具有挑戰且長期性的工作。圖書館不僅應該結合RSS的特點來合理精心策劃,還需要借助互聯網等新技術來保障閱讀推廣實踐的可操作性,不斷拓展立體閱讀推廣渠道,吸引更多的讀者加入,以便更好地促進立體閱讀的深入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