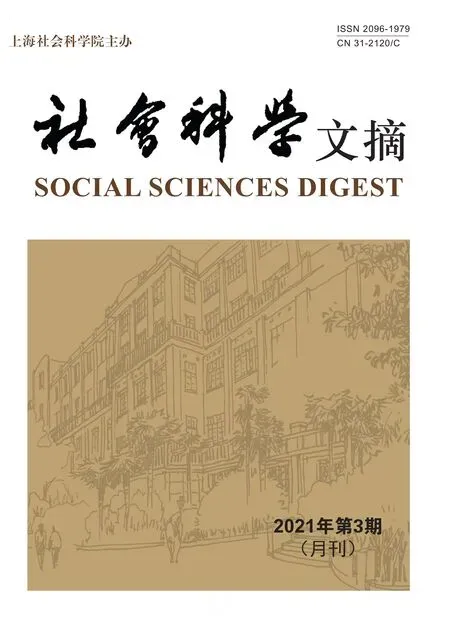財政聯邦主義與財政分權指標
——基于合約理論視角的再審視
除了基于經濟增長業績的地方官員晉升競爭之外,財政分權制度也是理解中國地方政府行為的一個重要視角,因為它通常被視為中央與省級政府之間關于財政收入的某種分成合約——若省級政府在整個財政收入中所分享的比例越高,則省級政府就越有動力采取各種行動來推動經濟增長和擴大稅基。為了檢驗這些激動人心的理論推斷,學者們構造了形形色色的中央與省級政府間財政分權指標,并將其視為財政分成合約的分成系數,作為核心解釋變量用于各種計量分析之中。
盡管大量的經驗研究豐富并加深了我們對相關問題的認識,但有個重要現象始終令人困惑,即:針對同一問題,采用不同的財政分權指標,得到的回歸結論卻不盡相同,甚至相悖。即便毛捷和馬光榮等學者重提該現象并重點批判了現行指標的同分母問題,但一些基礎性問題始終被回避而未被深究,即:各種財政分權指標具有清晰的經濟學含義嗎?真的可被視為省級政府感受到的財政激勵強度嗎?在全國統一且相對穩定的分稅制下,這些指標在地區之間具有一致性并在年份之間具有穩定性嗎?若非如此,原因何在?回答這些問題非常重要,否則我們很難相信某個回歸結果真的為某理論假說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
本文認為:只有收入側指標比較契合第二代財政聯邦主義的思想;即便如此,現行收入側指標不僅存在同分母問題而不可被視為財政收入分成系數,而且存在嚴重的結構性問題,而其數值大小又受各省份的經濟規模、發展水平、經濟結構以及央地之間復雜的策略性行為等因素的影響。由此,本文再次發出警示:在省級層面講述第二代財政聯邦主義的故事,現行的財政分權指標存在嚴重缺陷而應慎用。
財政分權指標的本質及必備特征
(一)財政分權制度的激勵邏輯及其實證策略
Jin等將中國故事精煉為如下模型:

其中,e、B和C分別表示地方政府發展當地經濟的努力程度、由此所導致的新增GDP(更準確的應是“稅基”)和私人成本,且令B'>0,B''<0,而C'>0,C''>0。另外,γ表示稅制所決定的針對GDP的綜合稅率,λ表示地方政府對當地新增財政收入γB的分享比例。這就意味著,地方政府發展當地經濟的最優努力e*應滿足一階條件:λγB'(e*)=C'(e*)。
不言而喻,構建一個恰當的財政分權指標FDit是相關實證研究得以展開的前提條件。盡管學者們已構建了形形色色的財政分權指標,但要保證其既符合經濟學邏輯和財政分權實距,又具有良好的數據可獲得性,卻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工作。
(二)邏輯迥異的三大類財政分權指標
學者們構造了三類測度中央與省級政府之間財政分權程度的指標,即:收入側財政分權指標、支出側財政分權指標和財政自主度指標。雖然這三類指標被廣泛用于經驗研究中,但這三類指標的構建有著迥異的經濟學邏輯。
1.收入側指標。大致而言,收入側指標用于測度地方政府根據財政分權制度而對其轄區所產生的財政收入的分享程度。學者們構建出多種收入側財政分權指標(參見表1)并將之用于相關經驗研究中。
2.支出側指標。由于在財政分權體制中地方政府的支出大小主要取決于其所承擔的事權或者支出責任,因此支出側指標在本質上是反映特定財政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對其轄區內所有政府支出責任的承擔比重,而非地方政府所分享到的財政收入權利。按照常理,支出側指標不適宜作為財政分權制度下地方政府所感受到的激勵強度的代理指標。

表1 現行收入側指標的構建方法
3.財政自主度指標。該類指標最基本的構造形式為“地方政府財政缺口/地方政府支出”,其中:財政缺口等于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與財政收入之差。雖然該指標越大,通常意味著地方政府的財政自主度就越低,但其形成原因復雜,很難據此簡單地推斷其經濟學含義。
(三)收入側指標構建的基本原則
若試圖在第二代財政聯邦主義下考察財政分權制度對省級官員發展當地經濟的激勵強度及其后果,則只有收入側指標才比較符合該經濟學邏輯。然而,構建一個與該理論相契合的收入側指標并非易事,因為: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中央與省級政府之間的財政收入側分權安排在本質上是一個復雜的、高維度的分成合約——涉及多個稅種、多個稅率和多種分成比例。
為了便于論述,不妨將這個復雜的分成合約表述為:分稅制規定i省在t年對第z個稅基(Bitz)按全國統一的稅率(γtz)征稅;而后,該省政府按一個固定比例(λtz)來分享產生于該省的稅收收入(γtzBitz)。事實上,這其中包含著兩個層次的制度安排:(1)國家對i省的n個稅基(Bit1,Bit2,...,Bitn)按稅率γt=(γt1,γt2,...,γtn)進行征稅;(2)中央與省級政府之間按分成向量λt=(λt1,λt2,...,λtn)分享財政收入。在這種制度安排下,i省在t年產生的財政收入為而該省政府分享到的財政收入為
既然如此,一個很自然的妥協辦法就是,通過某種加權方法而將復雜的多維度分稅制轉變為一個單維分成合約,即i省按一個財政分權綜合指標來分享該省總財政收入,比如:

盡管該測度并非新思想且其科學性也存疑,但為了保證該測度與其所依賴的合約理論盡可能相符,我們認為的構造至少應遵循一些基本原則。第一,分母應該是那些受當地政府管轄并受其行為影響的經濟體所產生的、可供中央和當地地方政府分享的財政收入。第二,分子應限于那些構成分母且根據財政分權安排而被地方政府分享的財政收入。換言之,那些不應納入分母的財政收入也不應被計入分子之中,哪怕它們可以被地方政府支配。因此,收入側指標的數值應小于1,除非中央政府基于當地財政收入而給予巨額轉移支付。第三,收入側指標的分子不應包含那些不隨當地稅基變化而變化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哪怕它們可由地方政府自主支配。這是因為:即便財政分權制度讓地方政府獲得了這部分可支配的財政收入,但卻不具有分成合約的性質,從而不會對地方政府產生額外的激勵。另外,每個地方政府的收入側指標應具有足夠的穩定性。
現行收入側指標及其合理性的再審視
盡管這些收入側指標被廣泛地用于經驗研究之中,但可能并不適用于講述與收入側財政分權相關的激勵合約故事,因為它們并不符合收入側財政分權指標應具備的一些基本特征。
(一)同分母問題
如前所述,收入側財政分權指標的分母應該是省轄區內各自所產生的財政收入。然而,從FD1到FD6,各省級政府財政分權指標的分母被統一為“(人均)全國預算內收入”或者“(人均)中央本級預算收入”,又或者“(人均)中央本級預算內外收入”。這就導致了廣受詬病的“同分母問題”。
我們知道,在1994年之后分稅制在全國范圍內基本統一且相對穩定,因此各省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總額和人均財政收入將主要取決于各自的經濟規模、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等因素。換言之,那些存在同分母問題的現行收入側分權指標主要是綜合性地反映了各省份的經濟稟賦差異,而不是財政分權程度的差異。進而,那些以該類財政分權指標為核心解釋變量的計量回歸結果更應該被解讀為“在該財政分權體制下,那些經濟規模更大和發展水平更高的省份更有能力(不)采取某些行為”,而不應被解讀為“財政分權程度更大的省份受到更強烈激勵而更積極地采取某些行動”。
現在,針對同分母問題,我們可做三點總結。第一,所謂的現行收入側財政分權指標本身并不能反映中央政府和各省地方政府之間的收入側財政分權程度,甚至沒有明確的經濟學含義,其值域空間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分母的選擇。第二,對于那些用“全國預算收入”“中央本級預算內收入”和“中央本級預算內外收入”做共同分母的指標(FD1、FD2和FD3),它們之間的橫向差異主要反映了各省經濟規模的差異。同時,由于中國各省份之間的經濟規模差異巨大,因此這些指標的差異也非常巨大。第三,對于那些分母和分子采取了人均化處理的指標(FD4、FD5和FD6),它們之間的橫向差異主要反映了各省份發展水平的差異。同時,由于中國各省份之間的經濟規模和發展水平存在嚴重差異,因此,在任何一個年份,這些指標在省份之間的差異也非常明顯。
(二)現行收入側指標的結構性問題
現行收入側指標的分子,即:一省地方政府所分享到的(人均)財政收入,不僅取決于其GDP規模或人均GDP,還內生于其經濟結構。由于財政分權制度涉及眾多的稅種,而不同的稅種又有著不同的稅基、稅率以及分享比例,因此,只要兩個省份的經濟結構不同,分母取值相同的收入側指標的數值就會存在差異,哪怕這兩個省份的GDP規模和人均GDP相同。
除了人均GDP水平較高之外,具有如下經濟結構特征的省份,分母取值相同且被人均化處理的收入側指標(FD4、FD5和FD6)通常也比較高:(1)城市化水平較高且城鄉差距較小,稅基寬厚且可征性較好;(2)第二產業較發達,以至于制造業企業規模較大、增值稅的一般納稅人較多;(3)城市經濟尤其是第三產業越發達,不僅營業稅的稅基越寬厚,而且與土地相關的收入也越豐厚。
此外,在營業稅屬于地方稅的時代,隨著第三產業占比增加而第二產業占比下降,地方政府對財政收入的分享比例會加速上升。正因為此,盡管原本屬于地方固定收入的所得稅收入從2002年起改為中央-地方共享收入而導致這些指標進一步下降,但隨著第三產業相繼成為各省的第一大產業,這些指標又在2005年前后開始見底回升。這就促使中央在2016年全面推行“營改增”改革。
上述分析也意味著,即便是那種相對比較合理的財政分權指標也存在比較嚴重的內生性問題,因為它的分母(一個省份所產生的財政收入)和分子(該省地方政府所分享到的財政收入)都嚴重受到當地經濟結構的影響。
(三)財政分權與央地策略性行為
前面的分析都暗含假設:中央和地方政府會忠實地執行既定的財政分權制度。然而,在既定財政分權制度下,現實中的中央與地方政府還會發生復雜的策略性互動。這些復雜的策略性行為都將影響一個地區實際征收到的財政收入的來源結構、總量以及該地區地方政府實際的分享比例。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現行收入側指標的縱向不穩定性實際上也嚴重損害了這些指標的合理性。照理說,至少對于同一個省份,合理的收入側財政分權指標應該具有相對穩定性,否則我們難以相信地方政府真的會據此形成理性的預期并采取相應的行動。
進一步討論:誰是更好的財政激勵系數
(一)一個可能的替代方案:省級地方財政收入的GDP占比
如前文所言,第二代財政聯邦主義的核心思想可精煉為式(1)所描述的地方政府官員效用函數以及使其最大化的一階條件:λγB'(e*)=C'(e*)。若給定生產函數B和成本函數C,則地方政府的最優努力e*取決于財政分權指標λ和綜合稅率γ的乘積λγ,而不僅僅是財政分權指標λ。鑒于此,若假設地方政府追求自己可支配的財政收入最大化,并試圖考察財政分權體制對地方政府發展經濟努力的激勵效應,那么,以“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之當地GDP占比”,即

作為地方政府所感知到的財政分權激勵系數可能更符合第二代財政聯邦主義的精神。
然而,即便按前述基本原則構建起一個比較理想化的φit,該指標仍然面臨著與現行財政分權指標(FD1—FD7)和財政分權綜合指標相同的結構性問題——在全國統一的稅制和財政分權制度下,這些指標的大小在橫向和縱向上的差異主要源于各省的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等因素。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在計量分析中發現φit與某個變量(如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某種顯著的相關性,我們也很難簡單地將其歸結為地方政府受到財政分權制度激勵而產生的結果。此外,該指標很可能還具有其他的經濟學含義。比如,該指標在一定程度上刻畫了宏觀稅負水平。
可見,在多稅種、多稅率和多分享比例的財政分權體制下,試圖通過構造一些綜合性指標來測度各省級政府在財政分權制度下所感知到的財政激勵系數,無論是財政分權綜合系數還是財政收入之GDP占比(φit),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二)新近的探索:省內財政分權與單稅種分享
相對而言,考察市縣級政府對各個主要稅種的稅收分成情況及其反應,可能更具操作性和現實意義。當然,相對于某稅種的平均分成系數,稅收邊際分成系數才是一個更準確的激勵強度測度指標。遺憾的是,受制于數據的可獲得性,相關的實證研究可能不得不使用前一個指標。
類似的,在中央與省級地方政府層面考察消費稅、增值稅、所得稅以及營業稅的(邊際)分成率變化及其對地方政府行為的影響,不僅可避免現有財政分權指標所面臨的內生性困境,而且可能更具現實意義。
最后,我們還需指出,雖然本文主要是在第二代財政聯邦主義框架下重新審視各種財政分權指標的合理性,但還應辨析另一個重要的競爭性假說,即:驅動地方政府行為的最大動力是地方領導人之間的某種基于經濟增長業績的晉升競爭。在該假說下,地方政府并不直接追求自己可支配財政收入的最大化,但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財政收入構成了地方政府參與轄區間經濟增長競爭的財政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