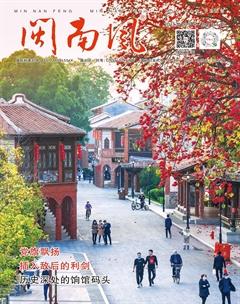離 別
楊西北
小時候,有一首好聽的歌讓我記住了,它會讓人牽腸掛肚。稍大后,我在《外國名歌200首》中看到它,原來這是一首夏威夷民歌,叫《離別》。這首歌似乎流傳得不是很廣,所以聽到的機會也不多,偶爾在電臺播音里聽過,幾分鐘就過去了,想再聽一下卻不可能,留下遺憾。過了若干年,科技飛速發展,出現了小度音箱這種可愛的東西,它有機器人一樣的腦子,你可以給它下指令,播放曾經面世的任何歌曲。有天我想到了這首夏威夷民歌,下了指令后,它卻播出其他的歌。我不甘心,又下了類似的指令,還是牛頭不對馬嘴。又一天,小度在播放音樂時,突然冒出這首歌,是男女聲二重唱,我很高興,非常專注地聽了,發現歌詞的譯法有些不同,旋律卻是恒久地動人。但是,它又消失了,只有一遍。也許歌名不同,無法再調出。這天,我在聽朱逢博和施鴻鄂的二重唱時,小度又延伸地播出男女聲二重唱的歌曲,《離別》意外地又出現。我趕緊對小度說,單曲循環。就靜下心欣賞。
這一聽,將近兩個小時。
一首歌,我怎么會聽那么久呢?這首歌原先譯本的開頭是這樣的,“看那烏云已遮滿了天空,啊,離別的時刻已經來臨。”有畫面,讓人產生聯想。這次聽到的開頭譯成“離別的時刻終于來到。”一下直指心上。歌的原意是表達一對情人分手時的傷感和依依不舍,但是旋律的回轉流動,卻不會如此拘謹,似乎俗世離別的感情都可以攬過去,朋友的,同學的,等等。
我是明白自己為什么一時會沉浸于這首歌。
因為上天的旨意,召走了一個中學的同學。我們都認識有半個多世紀,從清晨到夕照初起。召走就召走唄,令人不安和糾結的是它提前將消息傳遞,這將是最近的日子,哪一天未定,你等著就是了。再堅強的人恐怕也會被搖動。無常這家伙躡手躡腳地過來,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會伸出手。同學封鎖病情,不讓人知道。這也許是相當部分患者的心態。他一邊認真的治療,一邊以健康人的狀態出現在公眾面前。同學聚會時,他依然談笑風生。可是,只要醫療效果不佳,這就沒有辦法持久。終于有人從他的容貌和步態看出端倪,只是不愿往壞處想。他謝絕也害怕人們的探望。兩年前同學們商議要搞一本入學后數十年間的影集,因舊照難搜集,拖了時間,后來又商定就搜集到的先搞網絡版。他多次詢問進展情況。編排的同學緊趕慢趕,終于在他神志仍清楚時做出。聽說是他兒子扶著到電腦前,打開,逐頁慢慢觀看。
他是以這種方式向同學們作了告別。
我為什么會寫到他。許多年前,我還是一個知青的時候,他已調到縣農具廠。我曾被借到縣里搞宣傳創作,后來留在文化館打雜,沒有住宿的地方,就與他擠在農具廠宿舍的一張單人床,有半年多的時間。人生旅途中就這一回。我們朝夕相處,無話不說,知根知底,雖然興趣愛好大相徑庭,卻沒有影響到友情。后來農具廠改為家具廠,他成了廠長。這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廠呈現出來的生機得到了當時省委主要領導的欣賞。同學以后一直是企業界中人。他走后,我連續三個晚上在睡夢中夢到與他相關的情景,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們最后見的一面是他愛人將他扶出,他坐在客廳的躺椅上,吃了兩小口兒子買來的豬蹄包,喝了兩口蛋湯。談到同學的網絡影集時,他沒忘記說,某次合影有一個影中人不是同學,可以技術處理一下。坐了一會兒,他要回房間躺,無奈地對我說:“這次我遇到的這槌,是大槌。”這是他留給我的最后一句話。
他愛人后來說:“他不愿意面對。”又說:“其實我也不愿面對。”彼此都不談起病情。他是在昏迷中離去的。
生離死別是人之常情。又說人是感情的動物。凡涉及情的,有的便會一輩子難忘。
我叫停了小度的《離別》二重唱。歌詞我是記住的:離別時刻,我不憂愁傷感。你走之前,親熱地對我說了聲“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