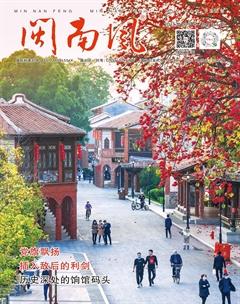村口的古榕
楊燕芬
“故鄉是一支清遠的笛,總在有月亮的晚上響起。”
想起故鄉,我總會想起不知哪里看來的那么一段文字,歷史長河進程,不管日月星辰如何變幻,村落建設的發展,一般會保留村中的古樹、廟宇、祠堂,特別是古樹,那是給在外地的游子回到家鄉的第一份“歡迎辭”。在我所在的閩南城鄉,這些古樹,充滿了靈性,一般以榕樹居多。
小時候,印象最深的便是村莊西邊社廟前兩棵相向而立的古榕。不知道它們種植于何時,每次問起樹的年齡,好似一個謎,誰也說不清。黃褐色的氣根,比起村中任何一位長者的胡須都要長;濃密的枝葉,趕超村中所有人的頭發量;滿地紫紅暗黃的榕樹籽,甩過全村年度人口數幾條街。每逢社戲日,村民們便在兩樹之間架起戲臺,拉上帷幕,看掌上木偶演繹歷史春秋、動靜相輔;聽七字調薌劇斗陣世間百態、悲欣交集。這兩棵古榕,從我記憶起,似乎就與社戲結下不解之緣。
最親近的,是我家老屋旁的那棵大榕樹。據有“百事通”之稱的爺爺講,這棵樹大概是在他爺爺年輕的時候種下的,他小時候也曾親眼見證過榕樹年輕的模樣。我家位于村子東邊的村口處,因為這棵古榕,我們這一旮旯幾十戶人家便被稱為“榕樹頂”,大有因此榕樹之功。從村口大隊部進村,首當其沖的便是祠堂,祠堂前有標配的池塘,池塘西面是學校。祠堂與池塘中間有上下兩層的紅磚大埕。越過大埕,迎面是個短促的急上坡,四季常青的榕樹在坡的最高處漸趨平緩右手邊位置,四五個大人才能環抱得過的軀干,成了我家豬圈的一面天然圍墻。從它樹枝上向下生長的垂掛氣根落地入土后成為“支柱根”,或附著在主干上日久年深“層巒疊嶂”,柱根相連,柱枝相托,煞是壯觀。
在樹干約兩米處分叉出三個大枝椏,中間位置寬敞可容七八人在此聚會。伸向土路邊的一杈,或許因為妨礙了樹下行人走路,自我懂事起,就只見它在延伸出半米左右的高處敞開了橫斷面,灰白干枯的中間空心部分在風雨中靜默著。另外兩杈,一杈伸向北面我家老屋二樓屋頂,一米左右寬闊的軀干,緩慢延伸上去約三四米長,像極了大型滑梯,在即將碰到樓房處來了個七八十度的折角向上努力伸展,好似另立門戶的下一代,枝繁葉茂,自我風流。大人們常常苦惱于積累在屋頂的腐葉,要在雨季來臨之前清理幾次。我們小孩子則樂于相邀來此“爬樹”,從分叉平緩處慢慢走到高處,再歡快地往回走。后來,隨著經驗豐富、年紀漸長、膽子也越來越肥,小伙伴們經常會嘗試著伸開雙臂,由慢到快地來回“滑滑梯”,因為“滑梯”下面是懸空的關系,這樣的滑滑梯雖驚險又刺激。于是,也經常成為我們的比賽項目之一。朝向村口的這一杈,應該才是主干,從分叉處起,就奮發向上,將近筆直地指向天空,傲然挺立,蒼勁挺拔,只在四五米高處部分才又有了分叉。周邊垂下的氣根,從潮濕的空氣中吸收水分,也長成了大小不一的“支柱根”模樣,或攀附在母樹身上層疊外出,或懸掛空中,給人以老態龍鐘之感。我小時候,村里的廣播便是架在此處,大有居高聲自遠的意味。自然,一般人也上不了那么高的地方去搞破壞。不過,有極品鄰居三兄弟爬樹特別厲害,每逢梅雨過后,常見他們上樹摘木耳,那是真正的純天然無污染的木耳哦。我自小就喜歡木耳,可惜我們姐妹幾個不敢也沒有能力去爬那樣高的樹,家人也不贊成不幫忙去占這樣的“便宜”。于是,每每看他們上樹,看他們炫耀似的拿著木耳從我家門前經過,我就“恨”得牙根癢癢的。
最可樂的其實是在樹下。枝葉擴展、遮天蔽日的榕樹下,是周邊百姓家的豬圈,大大小小十幾個,有兩三個只留有地基并無地上“建筑”,可能是年久失修被棄而不用。平常的日子,我會幫家人來此喂豬食、在豬圈墻角榕樹根四處挖蚯蚓喂雞鴨;也會跟著祖母或母親在樹下剝蓖麻皮、纏柴草卷、搓草繩;當然,和小朋友們在此捉迷藏躲貓貓,那些個豬圈和榕樹本身就是天然的屏障物。夏日的傍晚,榕樹下就是一座天然的涼亭,周邊的村民三五成群地搖著蒲扇在樹下乘涼、聊天,儼然成了信息交流中心,很是熱鬧;路過的行人也樂于在此做個短暫的休息、躲避風雨。如果再在樹下放些桌椅擺張棋局或講古說書,那是更古樸愜意不過了。
對于我們小孩子來說,這里還是我們的兒童樂園。放學后,書包直接放在奇崛嶙峋的樹頭處,在人來人往的土路上,無師自通地畫個等腰三角形,在三個頂角處各挖個拳頭大小的洞,就是我們玩彈珠的好去處了。有時為了將敵方的彈珠彈開,先把自己的彈珠彈進洞里,我們可跪可趴,哪有什么弄臟衣服的顧慮。也可以將食用后的蚶類貝殼頂部突出部分敲出個小洞,用繩子串起來,六七到十幾個不等,在地上跳格子;還可以在這里踢毽子、擲沙包、翻花繩。玩累了,安靜瞧大人們侃大山,發呆聆聽樹上鳥鳴啁啾、細看樹下螞蟻搬家等。直到有誰家的大人開始呼喚自己小孩回家吃飯了,人群才慢慢散開。記得當時年紀小,風在笑,物在跳,樹下的人兒歡騰鬧。至今想來,那是多么歡樂的童年生活啊!
后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這棵古榕竟然死了。按說,它的體格健碩,壽命也不過百多年,怎么說死就死了呢?毫無征兆地決然脫塵。村中人迷信地認為,這里原本就有棵樹,一棵榕樹,所以,現在雖然它死了,但應該再重新栽一棵。當然,它龐大的枯木樁處,從各種方面考慮都不是再栽樹的好地方了,但又要栽在“原處”,于是,我家早已不用的豬圈地成了最佳選擇。因此,我們家便把此場地貢獻了出來,還義務栽了一棵榕樹。可能真的此處風水寶地的緣故吧,新栽的榕樹見風就長,有水就潤,很快,枝繁葉茂了起來。可惜,當年的小伙伴們此時已陸續搬到更村口的“新村”安居樂業了。榕樹下,基本上只剩下幾位年紀較大的老人留守。再后來呀,城市建設的進程隨著九龍江南擴的步伐,整個村莊被夷為平地,規劃為市醫院新址。每次從市區出九龍江大橋經奧體中心回村里的安置小區看望親朋好友,只見幾十架起吊機繁忙地升降,工地一片轟隆。被圍擋住的村莊,找不到一塊熟悉的建筑物。曾經熟稔在心的一切,都已經在時代發展熱潮中灰飛煙滅了。幸好,清風中,一抹綠意搖曳眼前。啊,那是長在我家豬圈的那一棵榕樹,掩映著臨時指揮部的鐵皮屋,與村西口的那兩棵古榕,在風中互相問候。那份熟悉親切的鄉情,驀然溢滿心頭。故鄉還在,雖然已經面目全非,但是,已涅槃為城市進化的精品代名詞了。“古木穹枝云里歡,濃蔭蔽日隱童年。歷經多少滄桑事,依舊悠擎頭頂天。”
那一天,風塵仆仆的游子,遠道跋涉而歸,頗有“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者”的意味。看到村容村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深切感受到“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不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的鄉愁。可是,遠遠地望見村口的那棵古榕,在晨風暮雨中依然蒼翠蔥蘢,一身焦躁的灰塵便似乎卸下了一般,內心頓時輕松了下來。故鄉,我回來了!當然,還捎帶著更多的欣喜:我回來了,我的故鄉還在,我的根還在!也許是添了華發、換了容顏,但是,兒時記憶里的那棵老榕樹在清風徐徐中從容不迫伸開雙手,迎接她回歸的兒女,漂泊的心便有了歸宿。樹在,村在,老家就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