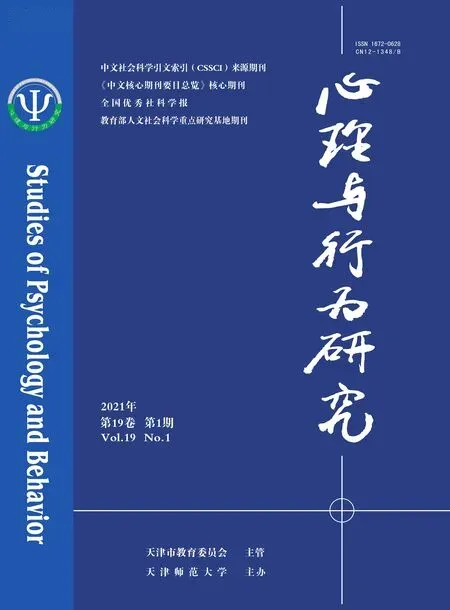自戀與攻擊行為的關系:觀點采擇和共情關注的調節作用 *
張 振
(河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新鄉 453007)
1 引言
攻擊行為(aggressive behavior)是指一切試圖傷害他人且對方竭力回避此傷害的行為模式,普遍存在于生物界,在靈長類動物中存在更復雜的表現形式(Keatley, Allom, & Mullan, 2017)。以往研究發現,38.7%的大學生遭受過校園暴力與攻擊(都芳等, 2018),而且攻擊行為會對受害者造成諸多不利影響,嚴重影響個體的身心發展和社會融入(齊春輝, 張振, 張倩倩, 2019)。攻擊的I3理論認為慫恿(instigation)、激化(impellance)和抑制(inhibition)是三個彼此獨立影響攻擊行為的認知過程(Finkel & Hall, 2018)。慫恿是指實施者與潛在受害者之間的社會性動態分離,往往導致強烈的攻擊欲望;激化是指強化攻擊欲望的過程;抑制則指削弱或克服攻擊欲望的過程。影響攻擊行為的諸多心理因素均可劃歸為上述過程,其中自戀(narcissism)和共情(empathy)就分別是激化過程和抑制過程中的重要影響因素(Decety, 2011; Krizan & Herlache, 2018)。
共情是指個體對他人觀點的感知及其伴隨的情緒反應,在建立良好關系、促進社會互動和抑制反社會行為中起關鍵作用(Vreeke & van der Mark, 2003)。共情的兩階段模型認為,共情包括認知共情和情緒共情兩種成分。前者強調從對方視角看待問題的觀點采擇,后者則突出對他人情緒體驗的替代性感受的共情關注(Decety, 2011)。該理論強調認知共情是情緒共情的前提,而情緒共情是認知共情的深化(張鳳鳳, 董毅, 汪凱, 詹志禹, 謝倫芳, 2010)。前人研究發現,觀點采擇能通過提升意圖理解、增強利他關注和降低不良策略的選擇來抑制攻擊行為(楊晨晨, 李彩娜, 王振宏,邊玉芳, 2016; Myers & Hodges, 2012),而共情關注可以通過增強負性情緒共享和自我-他人融合來削弱攻擊行為(Lishner, Hong, Jiang, Vitacco, &Neumann, 2015)。同時,觀點采擇能夠通過增強對他人需求的理解來促進共情關注,進而減少自戀者的攻擊行為(Hepper, Hart, Meek, Cisek, &Sedikides, 2014)。
自戀是個體憑借多種調節方式來維持自我處于相對積極狀態的能力,以浮夸且易變的脆弱自我、傲慢的特權感和共情的缺失為重要特征(Krizan & Herlache, 2018)。自戀與攻擊的關系備受國內外學者的關注。自戀的動態調節模型強調,自戀者具有夸張且脆弱的自我感知,需要不斷借助個人或社會行為來維持或提升其積極的自我知覺,而攻擊、暴力等社會不良行為則是其進行自我調節的策略之一(Morf & Rhodewalt,2001)。早期研究認為自戀者存在共情能力缺失,使得自戀者表現出更多的攻擊、欺凌等暴力行為(楊晨晨等, 2016;Lambe, Hamilton-Giachritsis,Garner, & Walker, 2018)。然而,近期研究發現自戀者具備一定的共情能力,在特定情境下也會借助利他、助人等親社會行為來提升自我感知(丁如一, 周暉, 張豹, 陳曉, 2016; Nehrlich, Gebauer,Sedikides, & Schoel, 2019)。研究者認為上述自戀者行為模式的差異根源在于自戀者具備共情能力與否,以及其是否愿意付諸共情能力(Pajevic,Vukosavljevic-Gvozden, Stevanovic, & Neumann,2018)。還有研究探討了共情對自戀與輟學青少年攻擊行為的調節效應,結果發現,在高、低共情組中自戀均能顯著負性預測攻擊行為,但是高共情組的效應值顯著低于低共情組(Barry, Kauten, &Lui, 2014)。
綜上所述,共情是制約自戀者行為模式的重要因素,共情能力會使自戀者意識到:攻擊行為不是提升自我的最優策略,進而有意識地減少攻擊行為。然而,鮮有研究檢驗兩種共情成分在自戀與攻擊關系中的作用及其效能差異。因此,本研究擬通過問卷調查法,檢驗觀點采擇和共情關注如何削弱自戀者的攻擊行為,以及兩者的抑制效能是否等同。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
以班級為單位,采用隨機整群抽取法從西藏拉薩某高校抽取592 名大學生參與本次研究。剔除無效問卷后(未回答50%以上的題目,或答題存在嚴重邏輯矛盾,或重復選擇某個選項),共收集有效問卷562 份,回收率為94.9%。其中,男生266 名,女生296 名;獨生子女107 名,非獨生子女455 名;被試平均年齡21.3 歲,年齡范圍為17~26 歲。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戀人格問卷
選用Ames,Rose 和Anderson(2006)編制、郭豐波(2017)修訂的自戀人格問卷。該問卷常用于非臨床正常人群的自戀評估,涉及自我評價、行為方式等,如“我將會成為一個偉大的人”。當前研究采用5 點計分法,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意味著自戀水平越強。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 為0.80。
2.2.2 人際反應指針量表
選取張鳳鳳等(2010)修訂的人際反應指針量表中的觀點采擇分量表和共情關注分量表。觀點采擇和共情關注分量表分別有5 道和6 道測試題目,采用李克特5 點計分,從“極不同意”到“極同意”依次由1 分過渡到5 分,分數越高表示觀點采擇和共情關注能力越強。本研究中觀點采擇和共情關注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分別為0.63 和0.64。
2.2.3 簡版Buss-Perry 攻擊問卷
采用Bryant 和Smith(2001)編制、國內學者翻譯并修訂的簡版Buss-Perry 攻擊問卷(張文武,呂梅, 杜琳, 杜亞松, 2009)評估受測樣本的攻擊行為,包含身體攻擊、口頭攻擊、憤怒和敵對4 個因子,共12 道題目。量表采用5 點計分,從“極不同意”到“極同意”依次由1 分過渡到5 分,分值越高意味著攻擊性越強。本研究中該問卷的Cronbach’s α 為0.80。
2.3 數據處理
使用SPSS19.0 進行描述統計分析和相關分析,運用宏程序P R O C E S S 插件,通過抽取5000 個Bootstrap 樣本進行調節效應和簡單斜率檢驗(方杰, 溫忠麟, 梁東梅, 李霓霓, 2015)。
3 結果
采用Harman 單因素法對數據進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檢驗,結果提取出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共11 個,最大公因子的解釋率為14.20%(低于40%),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 龍立榮, 2004)。同時,通過多重共線性檢驗發現所有預測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均不高于1.03,不存在明顯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3.1 描述性統計結果和變量間的相關
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及彼此之間的相關系數見表1。本研究發現自戀與觀點采擇(r=0.13,p<0.01)、攻擊行為分別呈顯著正相關(r=0.24,p<0.01);觀點采擇與共情關注存在顯著正相關(r=0.27,p<0.01);攻擊行為與觀點采擇(r=-0.1 0,p<0.05)、共情關注分別呈顯著負相關(r=-0.09,p<0.05)。
3.2 觀點采擇和共情關注的調節效應分析
鑒于調節變量均為連續變量,本研究采用PROCESS 插件中模型1 來完成中心化的調節效應分析。觀點采擇在自戀與攻擊行為之間的調節效應模型顯著,F(5, 556)=14.70,p<0.001,模型的解釋率R2為0.12。在控制性別和年齡后,自戀能夠正向預測攻擊行為(β=0.25,t=6.06,p<0.001),置信區間為[0.17, 0.32];觀點采擇能夠負向預測攻擊行為(β=-0.12,t=-2.96,p<0.01),置信區間為[-0.20,-0.0 4];并且自戀和觀點采擇的交互項顯著(β=-0.09,t=-2.40,p<0.05),置信區間為[-0.16,-0.02],表明觀點采擇在自戀和攻擊行為之間的調節效應顯著。同時,共情關注在自戀與攻擊行為間的調節效應模型顯著,F(5, 556)=12.98,p<0.001,模型的解釋率R2為0.10。在控制性別和年齡后,自戀能夠正向預測攻擊行為(β=0.22,t=5.45,p<0.001),置信區間為[0.14, 0.30],且自戀和共情關注的交互項顯著(β=-0.08,t=-2.36,p<0.05),置信區間為[-0.15, -0.10],表明共情關注在自戀和攻擊行為間的調節效應顯著。
為了更清晰地闡明觀點采擇和共情關注的調節效應,本研究分別采用選點法和J o h n s o n-Neyman 法進行簡單斜率檢驗(方杰等, 2015)。對于觀點采擇的調節效應而言,選點法分析結果發現,低自戀組(低于均值一個標準差)中觀點采擇不能顯著預測攻擊行為(β=-0.03,t=-0.53,p>0.05),而高自戀組(高于均值一個標準差)中觀點采擇能夠顯著負向預測攻擊行為(β=-0.21,t=-3.99,p<0.001)(見圖1A)。Johnson-Neyman 法分析結果發現,當自戀(標準化后)在[-0.25,3.39] 取值范圍時,簡單斜率的置信區間不包含0(見圖1B),簡單斜率顯著。同時,在此范圍內,自戀水平越高,觀點采擇與攻擊行為間的負性預測效應越強,即觀點采擇對攻擊行為的抑制效應值隨自戀的上升而增強。

表 1 描述性統計結果和變量間的相關(n=562)

圖 1 觀點采擇在自戀和攻擊行為關系中的調節作用圖(A)及其簡單斜率的變化(B)
對于共情關注的調節效應而言,選點法分析結果發現,低自戀組(低于均值一個標準差)中共情關注無法有效預測攻擊行為(β=0.03,t=0.46,p>0.05),而高自戀組(高于均值一個標準差)中共情關注能夠顯著負向預測攻擊行為(β=-0.14,t=-2.71,p<0.01)(見圖2A)。Johnson-Neyman 法分析結果發現,當自戀(標準化后)在[0.36,3.39]取值范圍時,簡單斜率的置信區間不包含0(見圖2B),簡單斜率顯著。同時,在此范圍內,自戀水平越強,共情關注與攻擊行為間的負性預測效應越強,即共情關注對攻擊行為的削弱效應值隨自戀水平的提高而增強。
4 討論
4.1 自戀與大學生攻擊行為的關系
以往研究表明自戀者存在更強的攻擊行為(Lambe et al., 2018)。本研究發現自戀對大學生攻擊行為存在正向預測作用,這與以往研究相一致,意味著自戀是導致攻擊行為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結果與自戀的核心概念相一致,鑒于自戀者的傲慢自大、自我中心性和敏感脆弱的自我高估,使其更傾向于將負性評價感知為威脅,直接體驗到強烈的憤怒情緒與受挫感知,進而誘發更高的攻擊性(楊晨晨等, 2016)。同時,該結果也印證了自戀的動態調節模型,即為實現自我感知的優越性,自戀者并不避諱將攻擊、暴力、欺凌等不適應行為作為自我提升的重要策略(Pajevic et al.,2018)。

圖 2 共情關注在自戀和攻擊行為關系中的調節作用圖(A)及其簡單斜率的變化(B)
4.2 觀點采擇和共情關注在自戀與大學生攻擊行為之間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發現,觀點采擇和共情關注均能夠負向調節自戀與大學生攻擊行為之間的關系,且自戀得分越高,觀點采擇和共情關注對攻擊行為的削弱效應越明顯。換言之,培養與提升觀點采擇和共情關注最有益于高自戀大學生。對于低自戀的大學生,觀點采擇和共情關注對攻擊行為的預測效果不顯著。高自戀者的核心特征是自我優越性、自我中心、共情缺失等(Krizan & Herlache,2018),而觀點采擇和共情關注能夠提升其對自我與他人的準確認識,更恰當地評估潛在自我威脅,采用更符合實際的自我提升手段,進而有效地抑制高自戀者的攻擊行為。相較而言,低自戀者能夠比較準確地認知自我,既不會過分解讀他人的負性評價,又不會采用不適宜的自我提升策略,因此觀點采擇和共情關注對攻擊行為的抑制作用可能不明顯。同時,自戀與觀點采擇、共情關注之間交互項均顯著且模式相似,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共情的兩階段模型(Decety, 2011),表明認知共情與情緒共情是共情的兩個基本成分,且存在較高的相關性。前人研究發現共情缺失會增強輟學青少年自戀者的攻擊行為(Barry et al.,2014),本研究結果與之相一致,再次證明共情是抑制自戀者攻擊行為的重要因素。
此外,觀點采擇和共情關注對高自戀者攻擊行為的抑制作用也存在兩方面的差異。一方面,基于選點法所得簡單斜率分析圖來看,相較于共情關注,觀點采擇抑制高自戀者攻擊行為的斜率更大,效果更明顯且效率更高。另一方面,基于Johnson-Neyman 法所得斜率變化圖可知,觀點采擇抑制攻擊行為的作用范圍也要優于共情關注,從自戀為-0.25 個標準分起即可發揮作用,意味著低于零標準分的少數低自戀者也能受益于觀點采擇的抑制效用。一項元分析研究發現,觀點采擇比共情關注更能有效地抑制攻擊態度與行為(趙陵波, 蔣宇婧, 任志洪, 2016)。當前研究結果與之相一致,表明觀點采擇比共情關注更能有效地抑制高自戀者的攻擊行為。此外,該結果進一步支持了共情的兩階段模型,強調認知共情是情緒共情的基礎,并能強化感同身受的情緒體驗(張振等,2019)。
4.3 啟示與不足
本研究揭示了自戀對大學生攻擊行為的預測作用,以及觀點采擇與共情關注的緩沖作用,支持了自戀的自我調節模型和攻擊的I3理論,能夠為高校管理與教育工作提供積極的啟示。首先,鑒于自戀能夠正向預測大學生攻擊行為,因此高校管理者在德育培養過程中應致力于降低大學生的自戀水平。其次,考慮到觀點采擇和共情關注均可有效抑制高自戀者的攻擊行為,因此高校教育者應注重通過認知訓練、角色扮演等形式增強大學生的共情能力,進而有效降低高自戀者的攻擊行為。最后,由于觀點采擇對高自戀者攻擊行為的抑制效用更顯著,因此,在資源受限時,教育者可優先提倡培養與訓練大學生的認知共情。
不過,本研究存在兩方面的局限:一方面,考慮到當前樣本取自西藏某高校在讀大學生群體,取樣范圍略窄,研究結論的普遍推廣性尚需檢驗。未來研究可于全國范圍內開展大樣本調查。另一方面,當前研究數據為橫段面數據,無法從嚴格意義上確定各變量之間的因果性論斷。未來研究可以結合交叉滯后設計和實驗研究法探究三者之間的因果關系。
5 結論
(1)自戀與觀點采擇和攻擊行為顯著正相關,觀點采擇與共情關注顯著正相關,攻擊行為與觀點采擇、共情關注呈顯著負相關;(2)觀點采擇和共情關注均可負向調節自戀與攻擊行為的關系,兩者都能顯著抑制高自戀者的攻擊行為,卻無法影響低自戀者的攻擊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