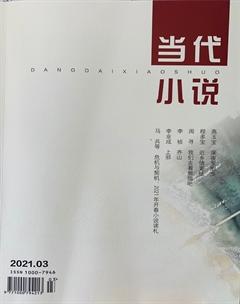黑香椿(短篇小說)
解永敏
1
北店子是黃河下游的一個渡口。
一條官道在渡口邊上穿過,過了渡口不遠便甩出一個三岔路口。繼續北上是去往京城的大道,往西則直通聊城,往東順著黃河走一大截再拐彎,也就奔大海而去了。
翠兒奶奶的香茗樓茶館,就是三岔路口上的一個小小驛站。
爺爺說翠兒奶奶驛站般的茶館雖小,卻也繁榮了很長時間,而且翠兒奶奶通過茶館結交下無數官方名流和社會賢達。當然,所謂的“賢達”,不乏各種幫人或打家劫舍之流。用爺爺的話說,亂世之年,誰能分得清誰是什么人?
民國二十八年臘月初十的那個傍晚,香茗樓茶館發生了一場涉及三方幾十人的大規模械斗。之所以說是械斗,因為所涉及三方手里都有槍,但誰都沒開槍,每一方的打手們所動用的差不多都是棍棒和就地取材的板凳,還有椅子甚或還有茶壺茶碗和暖水瓶。盡管都沒動槍,場面卻十分暴烈,十幾分鐘,有的頭破了,有的胳膊斷了,還有的在地上躺著嚎叫。
“那可真叫一個場面!”爺爺說。
我和堂弟小豆子喜歡聽爺爺說古。
“那時候,你們翠兒奶奶就是一朵花哩!”爺爺說。
“沒想到,一盆如花一般養著的香椿,竟然惹出一場打斗。”爺爺說。
“沒想到,李老三最后死在翠兒手里!”爺爺說。
“巧了,咋就會長出那樣一盆黑香椿呢?”爺爺說。
很多年之后,爺爺還說那是一個不尋常的傍晚,往日里這樣的時刻黃河河道里凄冷無比,光線暗淡,根本聽不到冰坨子的咔嚓作響,更看不到空氣中有一縷縷霧狀的塵埃飄動。
“怎么就在那樣一個時刻,發生了那樣一場械斗?”小豆子說。
“那樣一場械斗,咋就會和我們的翠兒奶奶有關?”小豆子說。
堂弟小豆子是個好奇之徒,對任何事情都喜歡探個究竟。
“唉!”爺爺嘆一口氣,“一下子很難說清哩!”
之前,爺爺經常會對我和小豆子使小性子,把一件事情剛剛說了個開頭,又立馬站起來往他居住的里屋走。然后說累了,等不累時再給你們講。任我和小豆子如何急著聽,爺爺依然不緊不慢地走回里屋,關上門,再也不理我們。
許多年來,翠兒奶奶在我和堂弟小豆子心中就是一個謎。
翠兒奶奶是濟南府里大戶人家的閨女,大戶人家的閨女嫁到北店子這樣一個荒涼之地本就有些不可思議,再嫁給爺爺這樣一個窮得丁當響的跑冰漢,就更不可思議。當然,翠兒奶奶再嫁是因她不爭氣的丈夫,剛結婚三個月就暴病而死。
有人說,翠兒奶奶之所以嫁來北店子做豆漿生意的王家,是因她父親賭博輸了錢,讓人家打得滿臉滿身都是血,多虧王豆漿出手相救,幫他還了錢,才算了事。而翠兒奶奶的老爹是個義氣之人,為報答王豆漿,當即將翠兒許配給王豆漿的次子,并稱隨時可來花轎抬人。
關于翠兒奶奶嫁進王豆漿家之事,還是省略少講,聽爺爺述說為一盆黑香椿所發生的械斗,好像更有意思。于是,我和小豆子哄著爺爺,生怕他再一次使小性子,使我們不能完整地聽那樣一場三方大規模械斗的故事。
那一天,我和小豆子從爺爺嘴里聽到這樣幾個并不連貫的詞:國軍十六營,土匪李老三,好人洪六子,抗日縱隊……
這是怎樣一個故事?
國軍十六營咋會來到北店子?
土匪李老三不是在禹城一帶活動嗎?
還有好人洪六子,又是怎樣一個角色?
這些疑問只能由著爺爺慢慢說。
小豆子挺聰明,從保著溫的小茶壺里倒了杯茶遞到爺爺手里,讓爺爺潤潤嗓子。
爺爺接過小豆子遞過來的茶杯,輕輕抿了一口,又抬頭望了望我們,說這么多年過去了,那樣一場打斗怎么就讓人忘不了呢?
我們知道,爺爺對翠兒奶奶一往情深,翠兒奶奶的任何事情他都忘不了。這些年,他給我們講了許多關于翠兒奶奶的故事,一個漂亮溫柔、賢惠淑德的女人形象,早已立于我和小豆子心中永遠不倒了。
2
“知道嗎?你們翠兒奶奶娘家很闊氣。”爺爺說。
對于翠兒奶奶濟南府的娘家,爺爺已經給我和小豆子講過無數遍,但他再講的時候,依然將翠兒奶奶的娘家從頭說起。我們知道,翠兒奶奶的漂亮賢淑,令爺爺心生驕傲;翠兒奶奶娘家的闊氣,同樣令爺爺心生驕傲。在那樣一個兵荒馬亂的年月,爺爺一個在黃河上背著腦袋跑冰的漢子,能夠娶上翠兒奶奶這樣一個漂亮女人,不想心生驕傲都不行。雖然翠兒奶奶曾經有過丈夫,雖然翠兒奶奶曾經的丈夫已經暴病而死,但爺爺能夠娶上翠兒奶奶這樣一個大戶人家的女人,依然和燒了八輩子高香差不多。有與爺爺年紀差不多的人告訴我們,翠兒奶奶在北店子渡口開起那爿香茗樓茶館后,很有些達官貴人青睞于她,但誰也沒想到最后她竟跟了我們的爺爺。
爺爺說記得給你們說過,你們翠兒奶奶病重時,郎中開的藥方里急需一味叫“貔砂”的中藥,去了很多藥鋪都找不到這味藥,郎中說那只能自己想辦法了。“貔砂”也就是貔子屎,而且必須是白貔子拉出來的。那年月貔子本來就很少見,貔子屎就更難尋了,何況還得是白貔子。但俺根本都不怕難尋,將黃河堤下葦子地里的好幾個貔子洞點著柴火用煙熏,熏得差不多時再爬進洞里尋找白貔子屎,而且還和一只白貔子打了幾個回合,滿身滿臉都是血道子,最后硬是把“貔砂”這味藥給尋回來了。
我和小豆子被驚得目瞪口呆。
早年的白貔子是一種很傳神的動物,形似兔,比兔粗壯,常在夜晚路邊迷惑人。后來,這種動物差不多絕跡了,致使很多生物學家連嘆可惜。爺爺竟然為給翠兒奶奶尋一味藥,與白貔子大戰幾個回合,真真了得!
關于爺爺大戰白貔子的故事,還是留待另一篇小說里細講,這里繼續說翠兒奶奶與黑香椿的故事。不過得先把爺爺在黃河上跑冰的營生說清楚,用爺爺的話說這事不說清楚,他和翠兒奶奶為啥能在一起,還愛得死去活來,好像很無厘頭。
“都是因了一趟跑冰的營生。”爺爺說。
“那趟營生搭上一只腳,一只腳換來你們的翠兒奶奶。”爺爺說。
當時,正值天寒地凍,是黃河里淌冰的季節,一河道的大冰坨子隨著激流飛一樣向前沖撞著,任何船只也沖不得,任何人也過不了河,能過河的也只有跑冰的漢子們。跑冰漢子都有一身跑冰功夫,撐一根長長的白蠟桿子,從順流而下的一塊冰坨跳到另一塊冰坨,就這么一塊冰坨一塊冰坨地跳著,也就跳到了黃河的那一岸。
正是這顯現著奇異般功夫的無數次跳躍,使跑冰漢子們靠著冬天黃河上跑冰的營生得以養家糊口。爺爺說翠兒奶奶之前找了兩三個跑冰漢子,后來才找到他。翠兒奶奶是黃河北店子渡口上出了名的美人兒,之前她找的幾個跑冰漢子,還沒接下營生就有些不正經了。有的說可以不要翠兒奶奶的錢,跑冰回來陪著睡一夜就行;有的說可以少要錢,跑冰回來得讓摸摸身子,哪怕摸上一把或兩把翠兒奶奶的兩只奶子;還有的說跑冰人本來就不容易,想讓翠兒奶奶好生疼一把。對了,說這話的跑冰漢子還有進一步的解釋,說真疼假疼不管,只要讓跑冰漢子感覺到一個漂亮女人在疼自己就夠了。聽了跑冰漢子的叨咕,她眼一瞪,腳一跺,爆了粗口:“狗日的!真是狗日的!”
“你們的翠兒奶奶竟然會罵人,還罵得那么粗糲。”爺爺說。
“當然,跑冰漢子不正經也是出了名的,在黃河上玩命本來就不知道哪天隨了閻王而去,見到漂亮女人一準兒要先犒勞一番嘴巴。”爺爺說。
之后,翠兒奶奶又找到了爺爺。
爺爺說他見到翠兒奶奶時心里一緊,想這個俊女人咋會來找俺呢?
翠兒奶奶找爺爺的時候,關于酬勞金的事爺爺說他提都沒提,不正經的話一句也沒說。當然,爺爺不是喜歡說不正經話的人,他一生行得正,從不隨意調戲人家的女人,只對翠兒奶奶說老子跑冰避女人,跑冰那天你不準去河邊,事俺足足地給你辦好。翠兒奶奶聽后點點頭,爺爺也點點頭,一樁營生也就成了。
3
爺爺和翠兒奶奶成就了一樁營生,也成就了一樁姻緣。
爺爺每每對我和小豆子說起他和翠兒奶奶的故事,臉上都顯出心滿意足的樣子。
當然,潛在那滿足背后的一定是幸福,盡管這樣的幸福很苦澀。
爺爺說不然就不會如此記掛那場大規模的械斗,通過那場大規模的械斗,他對翠兒奶奶太擔心了,而且一直擔心。
那場大規模械斗的發生,是在爺爺完成了與翠兒奶奶的那樁營生之后。
爺爺和翠兒奶奶成交的那樁營生,完成起來并不輕松。那時候,黃河里的河勢太險,大塊大塊的冰坨子順流而下,有的冰坨子在水里打著旋兒,旋出一股水桶般的卷流;有的緩慢地往前移動著,而閃亮的冰坨子邊上看去像無數把鋒利的刀刃。還有的冰坨子干脆斜立著往前奔,那寒寒的樣子似一張吃人的虎口,像是立馬要把走近它的人吞并了。
爺爺說跑冰漢子在那樣的季節里誰都不想接營生,既然接了翠兒奶奶的營生就得有誠意,就得把營生給人家完成好,否則會在跑冰行當里臭了聲名。
“聲名很重要,毀了聲名也就摔了吃飯的家什兒!”爺爺說。
“行當就是吃飯的家什兒,誰都不想把家什兒丟了。”爺爺說。
“跑冰漢子雖然粗糲,說話卻是一句一個釘。”爺爺說。
一個寒冷刺骨天上飄著大朵雪花的黎明,蜿蜒的黃河大堤和遼闊的黃河灘上雪厚過踝。到了夜間,稠密的黑暗在潮濕凄冷的黃河大堤上,不斷釋放著咔咔嚓嚓的像要置人于死地的響聲。那一刻,北風也就硬得寒人,敲打著黃河大堤上樹木光溜溜的枝條,敲打著凄冷的黃河大堤。一些麥秸草堆就起來的垛子和房舍,宛如深黑色的巨大鳥獸靜伏在幽幽暗暗的堤根兒。爺爺說堤根兒是他夜晚的棲息地,那時的他沒有像樣的家,只能也必須棲息在黃河大堤的堤根兒。
晨曦微露,河谷嘯嘯,爺爺踏著茸茸積雪走向黃河灘涂。黃河河道里的冰勢清楚地裸露在臘月早晨的曦光里。一塊塊褐亮的冰坨子緊緊相連,托著渾黃的泥沙和鳥的或是其他什么的糞便如匍匐緩進的隊伍,望一眼就讓人想到什么叫壯觀。
“壯觀是后來一些文化人的說法,窮到家的跑冰漢子哪里知道壯觀不壯觀!”爺爺說著,伸出兩個指頭彈了一下小豆子的額頭。小豆子搖搖頭,沖爺爺做了個鬼臉,爺爺又說,“最寒冷的季節才能跑冰混口飯吃,過了那個季節黃河里能沖船了,甚至都有人敢游水過河了,跑冰漢子的飯碗也就空了。”
在這樣的季節里成就了與翠兒奶奶的一樁營生,爺爺竟然連酬勞金都不談,這恰恰撬動了翠兒奶奶那顆柔軟的女人之心。爺爺說他當時之所以不談酬勞金,一是認為翠兒奶奶這樣的寡婦之人開一家茶館不容易,一天掙不了幾個錢;二是上來就和女人談酬勞感覺不爺們兒,營生做成了,盡著人家賞就是了。不過,營生做成后翠兒奶奶沒賞給爺爺酬勞,原因是他們的關系一下子發展到了沒辦法再要錢的程度。
繼續說與那場械斗有關的事。
與那場械斗緊密相連的是一盆黑香椿。
那盆黑香椿多虧了爺爺的那次跑冰,沒有爺爺的那次跑冰,就不存在那盆黑香椿的出現,沒有那盆黑香椿的出現,就沒有那場大規模的械斗。因此,爺爺說這件事的發生與他有直接關系。
那天清晨,爺爺跑冰的時候怎么也沒想到翠兒奶奶會出現在黃河灘上。
之前,爺爺反復對翠兒奶奶說,他跑冰要絕對避開沒蛋的。
“沒蛋的,知道嗎?”爺爺說。
“你就沒蛋,得避開!”爺爺說。
爺爺分明看到了翠兒奶奶滿臉的嬌羞,她兩只手不知往哪里放了,叉在一起翻來覆去地揉搓著。然而,翠兒奶奶最后還是什么也不顧,爺爺跳上第一塊冰坨子的時候,眼睛余光里就出現了翠兒奶奶跪在僵硬的冰泥灘上,沖爺爺的背影一下一下磕頭的情景。
那一刻,翠兒奶奶凄凄的淚眼不敢有瞬間眨動,她生怕漏掉爺爺在冰坨子上的每一次跳躍。在她看來,爺爺由一塊冰坨子跳上另一塊冰坨子,就是一次生命的投擲,將自己投向心靈的天國,盡管天國在人的心靈中神圣得一塵不染,翠兒奶奶還是時刻盼望著爺爺遠離天國的邊緣。在她做女人的生命途中,第一次在意識里為天國邊緣筑起高高的柵欄而全身心投入到了祈禱中。后來,翠兒奶奶告訴爺爺,他那次跑冰在黃河河道里跳躍了十八次,也就是跳上過十八塊冰坨子,翠兒奶奶也就磕了十八個頭,直到第十八個頭磕完,她才看到爺爺翻過對岸低矮的河堤,朝著遠處去了。
那一日,翠兒奶奶始終等在黃河邊上。
整個上午,翠兒奶奶被一股氣味所籠罩。
那是一股香糊的燒紙氣味。這樣的氣味使翠兒奶奶猶如望見了爹媽接受女兒孝心時的笑臉。神志告訴她,自己陷進魔怔中了,可她偏偏相信那股氣味是從黃河對岸的小樹林里傳過來的。于是,她眼前再一次出現了爹媽的面容,她“嗷”的一聲哭了起來,沖著滔滔的黃河水,沖著爺爺遠去的背影。
“那樣的營生也不算營生,就是去你們翠兒奶奶爹媽墳上燒了七刀紙,替她磕了三個響頭,因為那天是她爹媽的祭日,她爹媽是同一日被人殺害的。”爺爺說。
“想想也可憐,濟南府大戶人家的閨女,竟落草在北店子渡口開茶館。”爺爺說。
4
爺爺心里什么也藏不住,只要與翠兒奶奶有關的事,他早晚都會說出來。
我和堂弟小豆子早就感覺到了,爺爺是在述說中享受曾經的快樂,也是想讓我們分享他曾經的快樂。那樣的快樂雖然雜糅著辛酸與苦澀,但對爺爺來說辛酸與苦澀中的快樂也是快樂。
爺爺說那次跑冰去到黃河南岸的小樹林里,他找到了翠兒奶奶爹媽的墳,燒了紙,上了香,磕了頭,又按照翠兒奶奶的囑托,去了濟南府翠兒奶奶的娘家。
“你們翠兒奶奶的娘家,只剩下一個四合院了。”爺爺說。
“那四合院好嗎?”小豆子說。
“非常好,現在很難再找到那樣一個四合院了。”爺爺說。
“里面房子多嗎?”小豆子總想把一切弄明白。
“不僅房子多,其他也多。”爺爺說。
“其他是什么?”小豆子說。
“其他就是其他。”爺爺說。
翠兒奶奶娘家是濟南府的大戶人家,大戶人家體現最明顯的就是很不一般的四合院。房子規規矩矩圍成四方,影壁墻上畫著梅蘭竹菊,院子里還有水有樹,既有北方建筑的深厚和淳樸,又有江南水鄉的輕巧和靈秀,但因翠兒奶奶爹媽的被殺,這樣一個位于五龍潭畔的四合院,卻成了兇宅。
爺爺按照翠兒奶奶的囑托,翻墻進到院子里。翠兒奶奶忘不下娘家那棵石榴樹,她卻叮囑爺爺,家里的任何東西都不準拿,只把父親留在石榴樹下的一小盆月季根帶回來。
爺爺找了半天,終于在石榴樹下的秫秸窩里找到了那個紫釉小花盆。橫看豎看,也沒看出里面是否種有月季根。沒想到,翠兒奶奶見到那個紫釉小花盆時,一下子抱在懷里哭了起來。這時候,爺爺才知道翠兒奶奶的真正身世,才知道翠兒奶奶的老爹老媽是在同一個夜晚被同樣的匕首刺進了心臟。但也正是那個被爺爺揣在懷里帶回來的小花盆,影響了爺爺返回時在冰坨子上的跳躍。快到岸邊時,他從一塊冰坨躍起之后一下落到另一塊冰坨子的邊緣上,爺爺的身體失去了平衡,而腳下那塊冰坨子隨著他身子的搖晃又瞬時斜立成了冰扇。爺爺攀住冰扇的邊緣,兩腿泡在渾濁的水里。這時候,“咔嚓”一聲響,冰扇飛劍一般刺向河灘,爺爺的左腳也隨著那一聲“咔嚓”不知了去向,褲腿和淋淋血水黏合在了一起。
“跑冰漢子最后能活著就不錯了。”爺爺說。
“跟俺一起跑冰的,最后沒剩下幾個。”爺爺說。
爺爺丟掉那只腳,也就丟掉了跑冰的營生,成了香茗樓茶館里的沖茶人。而有機會天天陪著翠兒奶奶,他說也是巴不得的事。之后,翠兒奶奶告訴爺爺,她的爹媽是因一筆債務被欠債人雇兇殺害的。那是一個夏天的夜晚,月亮像銀盤一樣掛在天上,柔和的月光照得大地如白晝。翠兒奶奶的爹媽像往常一樣,坐在石榴樹下聊天。聊得正開心,大門口墻上突然飛來兩把明晃晃的匕首,爹“啊”了一聲,媽一點聲也沒出,就同時倒在石榴樹下。翠兒奶奶說那不是一般殺手所為,警察局破案破了半年多,竟一點線索也沒找到。再后來,翠兒奶奶的娘家就敗落了,四合院很快荒蕪得到處蒿草萋萋,沒有一點生氣。
“怎么會發生這樣的事?”小豆子說。
“殺手咋會同時殺掉兩個人?”我說。
“那樣的年月,發生這樣的事一點也不稀奇。知道咱們老城里的大圩首嗎?光天化日之下,賣黃河刀魚的年輕人因為在那里出攤多要了三個銅板,竟被人一棍子把腦袋給敲開了花,而敲他的人臨走還沒忘記把一簍子上好的黃河刀魚提走了。”爺爺說。
是啊,那樣的年月發生什么樣的事,如今的我和小豆子都難以想象。
翠兒奶奶沒想到,爺爺幫她帶回來的那盆月季根,竟然惹出一樁禍事。
翠兒奶奶告訴爺爺,她爹喜歡花,家里除了花工在院子里養的幾十盆花卉,就是她爹精心培養的一些小盆月季、蘭草和杉樹盆景。她說老爹最喜歡那盆黑月季。每年春天或夏天,月季總能開出純黑色的花。老爹會喊上好友,一邊品茶,一邊賞花,還一邊討論有關生意上的事。
爺爺說每次看到那盆黑月季,翠兒奶奶都很激動,她總是睹物思人,望著那盆月季像望見了老爹老媽,臉上淚水漣漣。令爺爺和翠兒奶奶想不到的是,來年春天,月季發芽開花時節,花盆里竟然長出一棵小樹苗。小樹苗開始是一個芽,隨著天氣的轉暖,那芽越長越大,漸漸有了稈,稈上頂著的是幾片油亮亮的葉子。葉子烏黑奇香。翠兒奶奶和爺爺發現不對勁了,那根本不是一盆月季,而是一盆黑香椿。
“老爹咋會養香椿呢?這小盆里明明是那棵黑月季啊!”翠兒奶奶說。
后來,爺爺說也許小盆里有月季花的根,也有香椿的根,開春的時候月季花沒生芽,香椿長了出來,香椿長勢旺,也就奪掉了月季。
翠兒奶奶望著小花盆里的黑香椿難受了好多天,而后又高興起來。她之所以高興,是因為香椿同樣純黑如墨,指頭粗的稈上頂著六七片墨一般的葉子,且奇香無比。放在窗臺上,太陽一照,香氣灌滿整個香茗樓。于是,翠兒奶奶被驚著了,她怯怯地問爺爺,見過如此漆黑的香椿嗎?爺爺說沒見過。她又問,聞到過這么香的香椿嗎?爺爺說沒有。之后,香茗樓女老板的黑色香椿便在北店子出了名,很快就傳到了國軍十六營營長謝光頭、土匪頭子李老三和一個叫洪六子的耳朵里。
謝光頭和李老三在北店子一帶十分了得,洪六子卻有點鮮為人知。
爺爺說洪六子是個大人物,小豆子問這人物大到啥程度?爺爺說比謝光頭和李老三兩個加起來還要大。而這加起來到底有多大,爺爺卻說不清。后來,我和小豆子查了半天資料,又問了一些老年人,才知道洪六子是定慧寺里的老和尚,人們都說這老和尚曾在少林寺修煉過,身手不凡,幾個半大小伙兒都到不了他跟前。
小豆子說定慧寺的老和尚怎么能比謝光頭和李老三加起來還要大?
爺爺說是洪六子的武功大,不是說他的人大,他人即使個子高,長得胖,又能大到哪里去呢?
望著爺爺,我和小豆子無言以對。
5
爺爺告訴我們,謝光頭不是本地人,從小在東北遼河岸邊長大,曾是東北軍的一個排長,后來不知為何成了北店子渡口國軍十六營的營長。他有一本家叔叔在南京國民政府做官,很可能是沾了光,一下子從東北提拔到北店子十六營。
李老三是本地人,從小偷雞摸狗不干正事,長大后不知怎么竟然混成了土匪頭子,打家劫舍是他的家常便飯。
對于謝光頭和李老三光顧翠兒奶奶的香茗樓茶館,爺爺說也難怪,有這么一棵香飄渡口的黑香椿,翠兒奶奶又有人樣子,當然會被他們注意上。
“順著北店子渡口邊上的那條灰蒙蒙的小街由南往北走,眼睛一亮時,稍有臉面的人物都會走進香茗樓茶館。”爺爺說。
“其實,你翠兒奶奶遠比她的香茗樓茶館名氣大。”爺爺說。
香茗樓茶館門面不大,只有四間青瓦房,前邊有個小院,院前臨街有兩間小房子,門臉是敞開的兩扇大窗戶,一扇窗戶占去半間墻面,窗臺向外接出半尺多長的青石板,青石板下有煙道,一看就知道是茶館燒水所用。青石板不平整,分出依次三個臺階,三個臺階走完也就進了香茗樓茶館的前門廳。
謝光頭和李老三那天一前一后,隔了不到半個時辰,相繼走進香茗樓茶館。
爺爺說他們開始各在一個房間里喝茶,后來不知怎么都走出了房間,在門廳里嚷著問老板娘哪去了?翠兒奶奶聽到喊聲,立馬趕過來賠笑臉。
謝光頭和李老三都像大爺,誰也不搭理誰。謝光頭是堂堂國軍營長,根本看不上李老三。李老三走到哪兒身后總跟一幫嘍啰,也就不把謝光頭放在眼里。
謝光頭拿眼瞥了瞥李老三,心想這熊樣,老子哪天剿了你!
李老三沒拿眼瞥謝光頭,那氣勢卻像在對謝光頭說,狂啥?不就一管酸不管咸的國軍營長嗎?
兩個人各懷鬼胎,誰也沒對誰說啥,但都在喊老板娘。
翠兒奶奶一邊給謝光頭賠笑臉,說謝營長稀客,有啥吩咐盡管說,再怎么也得滿足謝營長的需求。一邊又轉回頭來笑對李老三,說夜兒呢還在說,這陣子咋不見三爺來了,不過您這么大的爺,平時忙著呢,哪有時間光顧俺這小店,對吧?
“有龍井嗎?來一壺!”翠兒奶奶正說著,謝光頭亮開嗓子喊道。
“龍井產自哪里都不知道,還來一壺?球毛!”李老三拿眼踅摸著謝光頭嘟囔道。
“放你娘的屁!”謝光頭使勁跺了一下腳。
想必謝光頭一直在支棱著耳朵聽,李老三很輕聲的嘟囔他都聽見了。
隨著謝光頭的罵聲,四周拉槍栓的聲音驚得人打哆嗦。
李老三知道不是謝光頭的對手,畢竟人家是正規軍,他是土匪。土匪和正規軍之間差著的不是級別,而是實力。因而,聽到罵聲李老三一點也不惱,而是將一種少有的笑容送到謝光頭面前,說:“謝營長,至于嗎?你喝你的龍井,俺喝俺的茉莉,咱可是井水不犯河水噢?”
“老子喝龍井,你鬼孫子說風涼話作什?”謝光頭說。
“天地良心,俺從不風涼好人。”李老三說。
“老子就是好人!”謝光頭說。
“對,謝營長是好人,俺豈敢風涼!”李老三說。
話說到這里,謝光頭不再搭理李老三,而是沖翠兒奶奶說:“聽說老板娘有盆黑香椿,搬出來賞賞?”
翠兒奶奶臉上掛著暖人的笑:“一盆破香椿有啥好看的,等長好了,一準兒送給謝營長嘗鮮哩,最好吃的是香椿炒雞蛋呢。”
“俺就想看看還沒長芽的黑香椿是啥樣,聽說長出來葉子純黑,咱們北店子能有如此金貴的香椿,奇事一樁啊!”謝光頭說。
“奇倒不奇,只是顏色不一樣罷了,香椿要不微紅,要不微綠,俺這小盆咋就長出黑葉呢?”翠兒奶奶說。
“如此新鮮的玩意兒,老板娘別舍不得讓人賞噢?”謝光頭說。
“你堂堂國軍營長,賞盆香椿還不小菜一碟?弟兄們,去把那盆香椿找來讓謝營長賞賞。”這時候的李老三說話倒硬氣了。
“慢!人家的東西豈有硬來之理?老板娘,去年下屬曾來討要過幾片黑香椿芽,軍中廚子炸了,實在好吃。只是未睹芳容,今兒是專門跑來賞賞。”謝光頭說。
翠兒奶奶不好再拒絕,她喊了聲跑堂的小二,小二慌慌進屋去了。
等著小二的那會兒,謝光頭又瞥了眼李老三,臉上顯出不經意的表情。
李老三剛才極盡巴結的話,更讓謝光頭心生鄙視,他很想告訴李老三,你一土匪頭子,管老子賞不賞香椿做什?即便老子不賞香椿賞一泡屎,又與你何干?
這時候,小二把那盆還剛萌芽的黑香椿端了過來。翠兒奶奶剛想說話,謝光頭和李老三以及他們各自帶的人呼啦啦圍了上去。
李老三什么時候身上的匪氣也難改,即便是在謝光頭這樣的國軍營長面前,依然想充老大。沒等謝光頭看清那盆剛萌芽的黑香椿什么樣,他已伸開雙手將小盆抱在了懷里,并喊道:“二弟,咱把這盆剛冒芽的香椿買下,老板娘要多錢給多錢,錢對咱來說從來不是事哩!”
“放下!”
“給老子放下!”
李老三話一出口,隨即引來兩聲呵斥。
說“放下”的是謝光頭,說“老子”的是洪六子。
爺爺說當時沒誰發現洪六子站到了翠兒奶奶身后,就連翠兒奶奶也沒察覺洪六子是啥時候進來的,而洪六子說著話往前挪動著腳步,高大的軀體很實在地將翠兒奶奶擋在了身后。
爺爺說洪六子是個還俗的僧人,之前在少林寺習過武,還曾做過定慧寺的住持,還俗后在馬家院專心侍弄三畝田園,種花種草,種菜種谷。他不悲不喜,不怒不樂,一天到晚勤懇勞作。有喜花者找他要花種子,有勤勉者找他要菜種子,他都很痛快地答應。有人問他住持做得那般好,為啥還俗?他笑笑說,紅塵無忌,人非草木,六根皆凈,而五行有序,陰陽俱在。因而,大家猜測他是為了一個女人,之所以在馬家院專心侍弄三畝田地,也是在等待女人的到來。后來,沒見他等到女人,卻見他成了一支隊伍上的管事。
洪六子的隊伍趕不上謝光頭的十六營,十六營槍炮光亮,無人敢惹,洪六子的隊伍穿著破爛,手里大多是自造的抬桿,還有拴著紅纓的槍頭子。但不管怎樣,也是一支隊伍。翠兒奶奶曾對爺爺說,北店子一帶隊伍眾多,只感覺洪六子和善,幾次從門口路過沒有任何騷擾,下雨時門外積水,還會令手下幫著排水。爺爺那次跑冰把腳丟了,多虧洪六子送了幾包白色粉藥,用山西陳醋拌了抹上很快好了起來。
誰也沒想到,在這樣一個時刻洪六子單槍匹馬出現在了香茗樓茶館,還大聲呵斥著李老三。
李老三啥時候受過這般呵斥?
李老三仰著臉惡狠狠地問:“狗日的,想死?”
李老三比洪六子矮了半頭,面對洪六子他只能仰起臉來說話。但他根本沒想到,那“想死”的話剛一出口,洪六子“啪”的一個耳光甩了過來,李老三“嗷”的一聲怪叫,旁邊拉槍栓聲也就此起彼伏了,但也只是拉拉槍栓而已,持槍者雖怒目圓睜,槍口正對著洪六子,卻誰也不敢扣動槍機。因而,李老三的怪叫也就成了叫罵,他先沖手下罵道:“混蛋!開槍打死狗日的!”隨著他的話,洪六子第二個耳光又“啪”地一下甩了過來,李老三沒再怪叫,而是將抱在懷里的花盆“嗖”的一下沖洪六子砸了過去,洪六子一歪頭,花盆落在身后翠兒奶奶的懷里。誰也沒看清咋回事,翠兒奶奶已把小花盆接在手里,而且蹭地一下翻轉過來。她那看上去白白嫩嫩的秀手,竟像捏酒盅一樣將小花盆翻著捏在手里。花盆里的泥土嘩啦落在地上,露出一堆盤根錯節的花根。花根中間,竟有一把閃著寒光的匕首。這時候,李老三從懷里掏出盒子炮就要朝洪六子打,槍還沒響,匕首已從翠兒奶奶手里飛了出去,直直插進李老三的喉嚨,李老三撲騰摔在地上。這時候,在場的所有人手里都提起了家什兒,有舉著板凳沖人頭砸的,有將棍子輪成一個圓圈兒的,還有干脆把茶壺茶碗拋擲得丁當作響的。一時間,香茗樓茶館成了習武之地,從里到外,完全是一片狼藉……
6
之后的許多年,北店子渡口一帶沒有人再跑冰。
爺爺的一只腳被鋒利的冰塊削掉了,他成了香茗樓茶館的沖茶人,而且這“沖茶人”的角色跟隨他很多年,一直到翠兒奶奶走了又回,再走了又回,爺爺說他一直是個“沖茶人”。那幾個和他一樣曾經的跑冰漢子,對爺爺“沖茶人”的角色很是眼羨,紛紛學著他的樣子找其他事干了,黃河上跑冰的營生也就漸漸成了歷史。
“‘沖茶人不是老板,后來成了老板。”爺爺說。
爺爺臉上的表情很豐富,是一種幸福,還是一種失落,甚或是一種模棱兩可,我和小豆子誰都猜不透,爺爺只說老嘍,有些話能告訴你們,有些話不能告訴你們。
那次械斗之后,翠兒奶奶連招呼都沒給爺爺打一聲就跟著洪六子走了。
爺爺以為翠兒奶奶看上了洪六子,但幾個月后,隨著日本鬼子的到來,北店子周圍多了一支神出鬼沒的抗日縱隊,有人看到領頭的就是洪六子和翠兒奶奶。
爺爺說隊伍里不僅有之前洪六子的人,還有土匪李老三的人。李老三死后,洪六子帶著翠兒奶奶闖進坐落于黃河大堤下一片柳樹林里的土匪窩,靠其三寸不爛之舌,說通了李老三的二掌柜和三掌柜,使大部分土匪成了他們的手下。而謝光頭的十六營,也因挨了日本人一頓炮彈四散而逃。好在謝光頭很爺們兒,領著副官和護衛小隊也加盟到了抗日縱隊中。
“開始相互碰來碰去,后來都成了同路人。”爺爺說。
“北店子的人看到過,你翠兒奶奶和洪六子和謝光頭,帶著的那支隊伍很是浩浩蕩蕩,每次在黃河大堤上行走,都能揚起滿天的沙塵。”爺爺說。
爺爺說縣志上有記載,洪六子和翠兒奶奶,還有謝光頭,領導的那支縱隊經常被日本人追得在黃河北岸跑來跑去,有一次甚至被逼得一個個跳進黃河,身上滾滿黃膠泥藏進水草叢里才得以脫險。當然,他們也沒讓日本人占便宜,先后端掉了日本鬼子的五個炮樓,殺掉了兩個翻譯官,還俘虜了一名日軍少佐。
“那是你們翠兒奶奶的功勞。”爺爺說。
“你翠兒奶奶竟然自幼練過拳腳,這是誰都沒想到的。”爺爺說。
正是這點功夫,讓翠兒奶奶聲名大振,以至于日本人投降后,她回到香茗樓茶館養傷,上級接連幾次來人勸她隨隊伍去東北,無奈她傷勢太重,靠中醫調理兩年多,依然因嵌入肺部的彈片難以取出,落下久咳不止的毛病。盡管后來爺爺為給她尋一味“貔砂”,曾在黃河大堤下的葦子地里與白貔子大戰幾個回合,卻終也沒能留住翠兒奶奶的性命。
翠兒奶奶跟隨洪六子走后,爺爺將花盆里盤根錯節的花根分成四份,自己留一份,另三份送給了茶館里的三個伙計。爺爺那份春天冒出一個小芽,到秋天小芽才長出兩片葉子。然后,兩片葉子隨著冬天的到來枯萎掉了,只剩下小拇指粗的一根獨稈。而又到了春天,獨稈上呼啦啦長出三根小枝,葉子也漸漸濃密起來。爺爺將其放在屋外窗臺上,抽空澆點水,施點肥。五月的時候,再看那個花盆,竟然開出一朵黑里透紅的月季花。爺爺煞是稀罕,他小心翼翼地將其移到廳堂的八仙桌上,天天看不夠。
爺爺說另外三個伙計回家后都把花根種在了院子里,結果都長出了香椿。第一年香椿葉子很小,顏色卻透黑,而且奇香無比。第二年,香椿瘋了似的長,且稈壯葉肥,還成簇成簇地繁衍。有一個伙計告訴爺爺,他家那簇香椿生命力極強,根須從院子伸到屋里,把鋪在地面上的八仙磚都給頂了起來。
“黑香椿能吃嗎?”小豆子問。
“好好的香椿怎么不能吃?”爺爺說。
“如今咋沒再見到過黑香椿?”小豆子說。
“黑香椿本來就少,估計那樣的香椿后來也變異了。”爺爺說。
爺爺告訴我們,從那時開始,北店子一帶的人們漸漸種植起了香椿,每年春天很多人家靠賣香椿賺些油鹽錢。而每一次吃到香椿時,爺爺腦子里都會幻化出翠兒奶奶的形象。
然后,爺爺會癡癡地自言自語:“俊啊!真叫一個俊哩!”
我們知道,爺爺說的是翠兒奶奶。
責任編輯: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