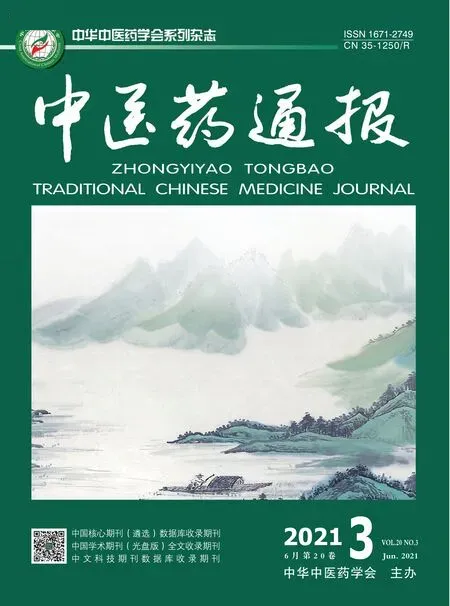陶弘景《本草經集注》成書背景探賾※
●季文達 李應存,2▲ 吳新鳳 章天明 陳 旭
陶弘景(公元456—536 年),一名勝力,字通明,自號華陽隱居,學者稱其為貞白居士,丹陽秣陵(今江蘇南京)人。陶弘景歷經南朝之宋、齊、梁三朝,為道教上清派宗師,宋末之時為諸王侍讀。梁朝時,陶弘景隱于茅山,潛心修道,但朝廷之事常以書信向他咨詢,時人稱之為“山中宰相”。其一生雅好攝生,精研藥術,長于煉丹鑄劍,通曉天文、歷算、地理,琴棋書畫無所不工,博學多才,著作豐富,在道術、醫(yī)學、科技、文藝諸領域多有建樹。
陶弘景精研醫(yī)藥,承其“祖世以來,務敦方藥”[1]27的家族傳統(tǒng),平素多“游藝方技,覽本草藥性”[1]27。陶氏學術作風嚴謹,細究《神農本草經》藥物之名類,誠如其書云“醫(yī)方香藥分劑,蟲鳥草木,考核名類,莫不該悉”以“盡圣人之心”。其勤研醫(yī)術而好著作,《梁書·陶弘景傳》言陶氏“性好著述”,后世考其所著書籍共八十余部[2],而《隋書·經籍志》記載與醫(yī)學相關者包括《本草經集注》七卷、《太清草木集要》二卷、《陶氏效驗方》六卷、《名醫(yī)別錄》三卷、《太清諸丹集要》四卷等10部著作。此外,陶氏增補葛洪《肘后救卒方》,作《補闕肘后百一方》九卷。
1 《本草經集注》概述
《本草經集注》是一部條理分明、考訂嚴密、搜羅甚廣的本草學巨著,是繼《神農本草經》之后,影響本草學發(fā)展的至關重要的著作[3]。該書是在《神農本草經》的基礎上,對晉以前名醫(yī)記錄進行系統(tǒng)整理和注釋而成的綜合性本草著作。它既繼承了前代本草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又總結了當代本草的學術成就,是對中藥理論及應用經驗全面而系統(tǒng)的總結。其在多方面對《神農本草經》所構建的初始的中藥理論體系進行了改善與創(chuàng)新、發(fā)揮,使我國本草學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它不但有歷史意義,而且還有現(xiàn)代的應用價值。其所記載的豐富的用藥經驗,仍為現(xiàn)代臨床所參用。故陶氏本草被后世稱為本草學著作的典范,是對我國本草學的繼承與發(fā)展,甚至對當代世界藥學的發(fā)展都有著不可磨滅的光輝功績,是祖國中醫(yī)藥學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
《本草經集注》原卷因年久失佚,所幸二十世紀初以來,在敦煌和吐魯番先后尋見《本草經集注》的手抄本殘卷,使其原貌得以重見天日,并使得本草學和文獻學研究在一些千載難明的問題上取得了更進一步的突破,可謂彌足珍貴。
2 成書背景探賾
2.1 社會背景
2.1.1 魏晉南北朝時期對實用醫(yī)書的需求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發(fā)展的上升時期,也是中國歷史上戰(zhàn)爭最為繁亂,政局動蕩的時期。據(jù)明末清初的學者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統(tǒng)計:魏晉南北朝時期戰(zhàn)爭最多,共有1677次,平均每年4.6次,魏晉南北朝時期無論戰(zhàn)爭總數(shù)還是年平均戰(zhàn)爭次數(shù)都在中國歷史朝代中排在第一位[4]。由于當時中國社會長期處于動亂割據(jù)的狀態(tài),戰(zhàn)亂、饑荒、疾疫危害著人民的生命,促成了醫(yī)藥在本草學、方劑學、脈學、針灸學、骨傷科等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據(jù)整理,魏晉南北朝有書名記載的醫(yī)著共計496 種,方劑類書籍占到30%以上,其次是本草類及養(yǎng)生書籍。方書的大量涌現(xiàn),而醫(yī)經類書籍所占比例相對較少是這一時代醫(yī)學的鮮明特點[5]。這都說明了魏晉南北朝時代對疾病治療需求的急迫,而本草學又是服務于方劑學的,可助臨床醫(yī)家加深對藥物的理解與應用,指導臨床遣方用藥。《本草經集注》在《神農本草經》的基礎上總結并增補了魏晉名醫(yī)的用藥經驗,如甘草、桔梗止咳,棗仁止汗安眠,陳皮、半夏止吐,桑螵蛸止遺溺、遺精,薏苡仁利水消腫等,較《神農本草經》對藥物作用的記載更具有臨床實用性,在此戰(zhàn)爭繁亂的年代,更便于醫(yī)家快速掌握藥物的臨床應用。
2.1.2 魏晉南北朝時期道家醫(yī)術的發(fā)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紛亂,政治恐怖,士大夫大多追求清靜無為、自由放任的生活,對人們的思想管控大為減弱,世人更推崇老莊的虛無思想,道教思想在此時期得到了流通和發(fā)展。陶氏不僅著《本草經集注》以總結前人的本草學術成就,亦是為了記載仙經道術所需之藥,便于道教修仙、煉丹之術的傳承與發(fā)展,如序言:“道經、仙方、服食、斷谷、延年、卻老,乃至飛丹轉石之奇,云騰羽化之妙,莫不以藥導為先。用藥之理,又一同本草。”[1]45另外,從陶注中可以發(fā)現(xiàn),陶弘景對藥物進行論述時都會特別指明用于仙經道術之藥,如藥物“白青”下注述:“此一方不復用,市人亦無賣者。惟《仙經》三十六水方中,時有須處。銅劍之法,具在《九元子》術中。”[1]298陶弘景清楚地說明了白青的作用,其在醫(yī)方中不用,市場也無人售賣,但在三至六水方中卻要用到,據(jù)考證,此為道教的煉丹法[8]。《仙經》在《本草經集注》中多次被引錄,例如在“理石”“澤瀉”“莨菪子”“茯苓”等藥物注述中。因此,可見陶氏著此書亦是為道家子弟修仙術、煉丹藥所備。
2.1.3 魏晉南北朝時期造紙技術的革新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造紙行業(yè)不僅繼承了漢代的造紙技術,而且開拓了新型的造紙原料,優(yōu)化了當時的造紙設備,使得造紙技術工藝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造紙業(yè)初步形成規(guī)模。由破布為材料而制成的麻紙物美價廉,潔白受墨,書寫之后可舒卷開來,誠如晉人傅咸《紙賦》中所言:“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弊,以為己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
這一時期,紙已經成為中國常用的書寫材料。紙的普及,有力地促進了當時科學文化的傳播和發(fā)展。陶弘景一生著作八十余部,與造紙技術的革新有著密切的關系。
2.2 學術背景
2.2.1 醫(yī)籍的整理、發(fā)微之風 從先秦兩漢到魏晉南北朝,隨著醫(yī)學理論和經驗的不斷積累和豐富,先祖所輯之書逐漸無法滿足醫(yī)家臨床運用的需求,故逐漸掀起了一場著作整理、發(fā)微之風。其中,王叔和于泰康元年,撰《脈經》十卷,其序中自述“今撰集岐伯以來,逮于華佗經論要訣,合為十卷”“其王(遂)阮(炳)傅(□)戴(霸),吳(普)葛(洪)呂(廣)張(機),所傳異同,咸悉載錄”[7](注:“傅”所代指之人目前無從考證)。而皇甫謐習針術,據(jù)《靈樞》《素問》《明堂孔穴針灸治要》十二卷、《難經》諸籍,使“事類相從,刪其浮辭,除其重復,論其精要”[8],撰《針灸甲乙經》十二卷,成為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系統(tǒng)性針灸專著。后世眾多醫(yī)家則在《神農本草經》基礎上對藥物數(shù)目及臨床療效進行增補,如敦煌遺書《本草經集注》(日本卷編號:龍.530,現(xiàn)藏于龍谷大學圖書館)序中言:“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等,更復損益(注:《神農本草經》)。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三十一,或三百一十九。”[1]26此外,陶弘景增補葛洪所著的《肘后救卒方》,作《補闕肘后百一方》九卷。
2.2.2 本草學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 中國經后漢、三國時代及魏晉南北朝時代,戰(zhàn)亂頻發(fā),古籍頗多散佚且多有傳訛、錯簡。因而,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等醫(yī)家對《神農本草經》更復增補改動,導致藥物數(shù)目不一,上、中、下三品混糅,冷熱錯亂,草石不分,蟲獸不辨,藥物主治互有得失。因此,在諸多錯亂之下,整理和注解《神農本草經》已是勢所必然。
隨著醫(yī)家對臨床療效的不斷追求,以及國內外物資的交流、買賣更為頻繁,新藥物的發(fā)掘與認識亦在進程當中,使得醫(yī)家選用藥材范圍更為廣闊。因此,除了整理與注解《神農本草經》錯亂之處外,還需要對新藥物進行增補與收錄,從《本草經集注》中可見,新添了《神農本草經》未載的藥物,如檳榔、蔥、蒜、檀香、乳香、蘇合香等外來藥材。由于前人所增補的《神農本草經》版本諸多,雜亂于世,無法滿足醫(yī)家對藥物的正確認識及對新藥物的了解、應用所需,陶弘景的《本草經集注》便應時而生。
2.3 個人因素陶弘景出生于書香世家的士族家庭,陶弘景的父親陶貞寶亦精通醫(yī)術,“父諱貞寶,字國重,……深解藥術,博涉子史……”[9]1042。陶弘景承其“祖世以來,務敦方藥”的傳統(tǒng),且陶弘景成長于作為南朝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京都建康,家學淵源與社會環(huán)境使他自幼養(yǎng)成了好學習的習慣。陶氏自幼聰明且好學,十歲便“讀書萬卷余,善琴棋,工草隸”[10]。
因得葛洪《神仙傳》,晝夜專研學習,便有養(yǎng)生之志,長大后好醫(yī)術,“性好著述……尤明陰陽五行……醫(yī)術本草”[9]1044。《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中記載陶氏行醫(yī)求世的志向:“贍恤寒棲,拯救危急,救療疾恙,朝夕無倦。”[9]1044他兼欲濟人,周濟、援助有難之人,醫(yī)治疾患,朝夕不知疲倦。但對于陶弘景來說,治病救人也只是一時之功,“可以傳方遠裔者,莫過撰述”[9]1044,其更渴望自己所學之術得到流傳與繼承,以著書的形式流澤萬世。因此,陶氏學識淵博,明五行而善醫(yī)術本草,且常行醫(yī)救人以積累大量的臨床經驗,這都是陶弘景能夠撰書立作的基本條件。
3 小結
《本草經集注》這部本草學上的舉世之作,不論在南朝還是后世皆對本草學的傳承與發(fā)展有著巨大的貢獻。陶弘景博學多識,精善醫(yī)術,又好著述,加之當時社會、學術背景的影響,將重修、增補《神農本草經》為己任以整肅修正,承上啟下,使得成書以前的本草學術得以總結,流澤萬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