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歐文太太》小說集后記
陳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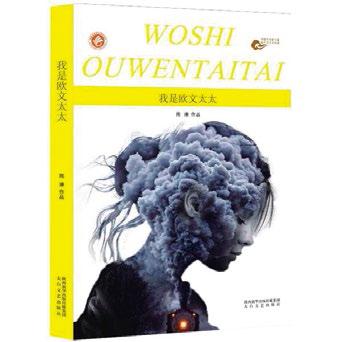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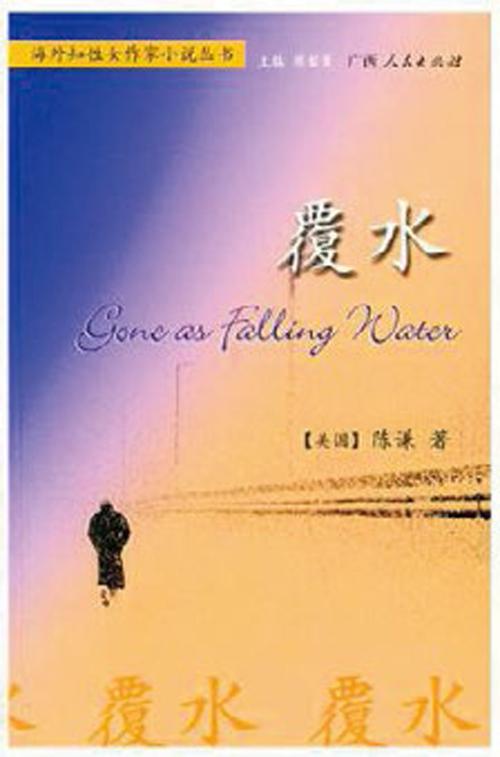
在這個炎熱的夏天,我一路奔波,從北美出發,到華東,再去往馬來西亞檳城。又折回,終于回到故鄉南寧,能夠喘口氣,坐下來整理被這東奔西跑的日程拉下的種種事務——為自己將在年內出版的小說集《我是歐文太太》寫個后記,便是其中之一。
從新世紀初出版了長篇小說《愛在無愛的硅谷》之后,這十多年里,我主要在寫那種被稱為“大中篇”的小說,動輒七八萬字,五六萬字更不在話下。在這個浮躁的時代,一邊在說文學已經邊緣化、信息碎片化,沒人有心思讀小說,可出版市場上卻是長篇為王,中短篇小說少人問津。所以大家看了我在那兒吭哧吭哧寫一些體量不算小,卻又無法當長篇出賣的玩藝兒時覺可惜。說蠻好拉一拉抻一把,整成部長篇什么的,好賣。在這個時代,“好賣”確實是個有著魔力的詞,讓人聞之難免腦袋一熱。可熱度一散,還是能記起自己之所以選擇寫小說,是由著喜愛而不是沖著“好賣”。在這樣的寫作中,重點就是表達。我只能一意孤行,由著性子“嘩嘩嘩”地不長不短地寫下來,圖的是盡興。這本集子里收入的,便是我以這樣的寫作方式,在近年寫下的一些中短篇作品。
《繁枝》刊發于2012年第十期的《人民文學》,獲得了廣泛而正面的反響,帶來許多的獎項。在《繁枝》的寫作過程中,當我攜同錦芯和立蕙姐妹穿越于家族歷史的叢林,經歷著她們的心頭之痛時,伴隨我的是慘烈的牙疼。這個奇妙的生理現象,今日思之,仍令人驚悸。我相信,如果你將它讀下來,一定能體會到我當時經歷過的身心煎熬。在不少關于《繁枝》的評論里,都有“家族血脈”“愛恨情仇”這樣的字眼,其實從我打下第一個字起,我覺得自己只是牽著錦芯和立蕙那對姐妹的手而已,我想要做的,不過是由著好奇心,從她們人生的波折起伏里看出“故事為什么會發生”——這便是我的小說觀。由于篇幅所限,《繁枝》在雜志刊出時作了刪節。而此次書中收入的是更全的版本。
書中的另一部中篇《蓮露》,則是以心理醫生的視角切入的中篇小說。我對心理學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這與我的小說觀密不可分。當要真的以一位心理醫生作為敘事主體,我才發現,只有興趣是遠遠不夠的。非常感謝我的好友、臨床心理醫生童慧琦博士的幫助和引領,讓我將這場挑戰對付下來。
在寫作《蓮露》的過程中,面對著眾多的素材,我清楚地意識到,如果要達到心目中的藝術真實,必須做減法。這是一種全新的經驗,顛覆了我對寫作的認識——藝術在有些時候應當低于生活。換句話說,生活可以復雜、精彩到令藝術黯然。寫作的樂趣之一,是在其中完成個人的成長,《蓮露》的寫作,正是讓我體會到了這樣的過程。
在寫作中篇的同時,我寫了數量非常有限的短篇小說。大家經常會論及長、中、短篇小說的寫作難易。以我看來,如果以“寫得好”為要求,它們各有其難。但以我的寫作實踐而論,短篇小說確實最不容易。其難度在于“精”——它是生活的一個橫截面,要截得漂亮,要心明眼快力足,不能拖泥帶水有毛邊。
多年前,我寫過一部懸疑類型的中篇小說《殘雪》,在我的寫作實踐里,那是一個異數。《我是歐文太太》從《殘雪》那個開放的結局里起步,試圖將曾經撒落一地的冰塊拾起,裝上一款看得出來龍和去脈的迷你雪橇。對我而言,這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因為在短篇有限的構架里,我必須放下這些年來令我迷戀的、在闊大的中篇容量里對“故事為什么會發生(Why)”反復追究并演繹的展示,學習如何用有節制又具深意的語言,講述好“發生了什么”。而短篇的魅力,恰恰就在這樣的過程中凸顯。
而另一部更短的小說《麒麟兒》,是我為國內前衛而勇敢的《財新》雜志所寫的。《財新》曾嘗試開辟短篇小說專欄,出高稿酬廣招優秀短篇。《麒麟兒》正是應雜志的文化主編徐曉老師的邀約寫下的。它的核心枝干生長于一個我親耳聽過的真實故事,我甚至仍能記得講述者那駭然痛苦的表情。在幾千字的篇幅里,我嘗試梳理命運肌理,以讓心中的沉痛得以消解。
我同意“小說是一種手藝活”的說法。我同時又更愿意說,在好的技法之上,對人類生存困境進行思考和追問,應該是小說存活下去的理由。好的小說,應該能夠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他人、理解生活,進而在面臨生活的選擇時,行為有所依據。如果從小說中我們不能找到榜樣,卻能夠體察到警醒,也是收獲。作為寫作者,我做不到對生活里的各種問題提供答案,但我一向都對針對生活本質提出問題有著濃厚的興趣。如果大家看完這部小說,對其中的每一個角色能夠有所理解,對他們如何能夠獲得更好的結局有所思考,我的作業應該就及格了。
感謝太白文藝出版社和責編的扶持。更要感謝在茫茫書海里選讀此書的讀者們,你們是我的知音,也是我寫作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