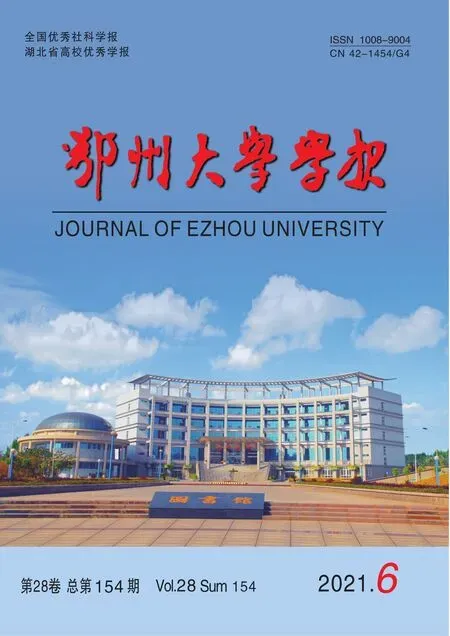論“三孩”政策下兄姐對未成年弟妹的扶養義務
張夏希
(福州大學法學院,福建福州 350108)
家庭作為貢獻主要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基本單位,其重要地位不容小覷,是國家和社會的角色定位無法代替的。因此,其也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首要因素,家庭關系的和諧直接關乎到人民的幸福生活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宗親觀念濃重的文明大國,以家族為本位、以宗親思想為指導的社會觀蔚然成風。尊崇愛老愛幼、長幼有序的家族治理結構,形成互相幫助、相互扶持的倫理道德體系,最直接體現這一點的是親屬之間扶養義務的存在。恩格斯認為:父親、子女、兄弟、姊妹等稱呼,并不是單純的榮譽稱號,而是代表著完全確定的、異常鄭重地相互義務,這些義務的總和構成這些民族的社會制度的實質部分。[1]由于家庭內部分工的不同、年齡、身體狀況的差異,勢必導致家庭中存在相對弱勢的群體,基于親情關懷和人權保障,家庭港灣為其帶去的溫暖和親屬之間物質和精神上的照料是其受保障的主要來源,也是一個家庭凝聚力和團結度的集中體現。
一、扶養義務之現實依據
扶養一詞的范圍可從廣泛化和特定化兩個層面來理解,在我國理論上與實踐過程中,從廣泛化的角度分析,扶養指的是法律規定的特定親屬,如“三代以內的直系血親”、“近親屬” 之間具有在物質上提供幫助、在精神上提供支持以及在生活中提供保障的相對性的權利義務關系。主要存在三種扶養形態,即長輩對晚輩的“撫養”,如父母對子女的撫養義務;平輩之間的“扶養”,如兄弟姐妹之間、夫妻之間的扶養義務;晚輩對長輩的“贍養”,如子女對父母的贍養義務。[2]
而特定化的扶養將范圍限縮于平輩之間,即兄弟姐妹之間和夫妻之間產生的物質幫助、精神寄托和生活扶助的權利義務關系。兄弟姐妹之間基于不可割舍的血緣關系而產生的扶養義務,其并非可以基于自由意志而選擇是否締結兄弟姐妹關系。該扶養義務的正當性不僅來自于親情關系而產生的道德義務,也來自于家庭作為一個整體由于不同分工所產生的對平等、公平價值取向的追求。兄、姐作為家庭成員中的一員,其享受家庭總生產資料帶來的物質基礎保障,如衣食住行教育方面的保障,在精神上享受著家庭賦予的關懷與安全感。當家庭集體做出改變人口決策、調整家庭結構而選擇生育弟、妹時,鑒于權利義務的對等原則,兄、姐也應當相應分攤家庭在資源重新整合的范圍內產生的風險,本著最有利于家庭發展的初衷,齊心協力將家庭資源配置達到最優化。當父母年邁,家庭主要勞動力轉移至兄弟姐妹身上時,弟、妹也可幫助兄、姐承擔贍養父母的責任,使得兄、姐不至于承擔太大贍養壓力,整個家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再次得到彰顯,內部風險得到合理分配和控制,抵抗外來風險防御能力也得到強化。
隨著《民法典》的出臺,婚姻家庭編成為《民法典》中的獨立一編,第1075 條沿用了《婚姻法》的規定,“有負擔能力的兄、姐,對于父母已經死亡或者父母無力撫養的未成年弟、妹,有扶養的義務。由兄、姐扶養長大的有負擔能力的弟、妹,對于缺乏勞動能力又缺乏生活來源的兄、姐,有扶養的義務。”但值得注意的是,該條規定在現實中的適用基礎存在爭議。“三孩”政策的放開,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人口增長,在其為國家帶來人口福利的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使得家庭關系惡化的問題。最典型的情況是,明知沒有扶養能力的父母仍要堅持生下弟、妹,使得剛成年的兄姐背上扶養弟、妹的沉重義務。因此,扶養義務適用條件的嚴格把握還需要進一步深入探究。
二、扶養義務之歷史沿革
(一)古代中國扶養義務的根基
“親親”、“尊尊”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核心內容。“親親”即要求親近應當親近的人,是家族血緣關系親疏遠近的體現。“尊尊”指的是尊重應當尊重的人,是國家統治階級地位維護的必然要求。[3]人人崇尚的“孝悌之道”也是產生于對“親親”、“尊尊”的普遍認同和嚴格遵守中,是人性偉大光輝的體現。濃厚的家長本位思想混合著根深蒂固的階級意識,父權至上的家庭等級觀念使得家長的權力在內部得到高度集中。包括對家庭財產的支配權、對子孫的懲戒權、對家庭事務分工的安排權以及對子女婚姻的干涉權。同時也存在相應義務,如家庭成員犯罪的連坐義務,對家庭成員的監護、扶養義務。在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以“五服”制度來劃分親屬的遠近關系,進一步加強民間習慣和道德要求與親屬關系的緊密聯系。[4]
而家族龐大、人丁興旺的古代家族內部少不了兄弟姐妹之間的相互扶持起到的作用。一方面是因為古代人的平均壽命不長,生育年齡跨度較大,導致兄、姐和弟、妹的歲數差距較大。由于古代醫療條件的極其有限,自然災害頻發而無相應預防機制,以及戰爭的頻發、徭役的繁重,導致古代人的生命健康權得不到充分保障,平均壽命相對于現代人來說較低。據歷史考究,夏、商時期人的平均壽命不超過18 歲,周、秦大約為20 歲,漢代22 歲,唐代27 歲,宋代30歲,清代33 歲,民國時期約為35 歲。[5]而中國一直以來作為農業大國,最依賴的是勞動力和生產力,勞動力的短缺使得人口成為競爭優勢,老百姓競相生育往往導致出現扶養負擔超過扶養能力的局面。因此,家中的長兄長姐就自然要承擔起扶養晚輩的義務,這也是“長兄如父”、“長嫂如母”的來源。
另一方面,生育、養育孩子的成本相比于現代來說低很多,兄弟姐妹之間的扶養負擔較輕。根據經濟學上相關產品價格對需求的影響可知,影響需求的兩方面因素包括替代品和互補品的價格。基于當時迫切需要生產力的農業經濟視角,人力的替代品是牛、馬等大型畜生。然而,在當時,無論在南方還是北方,牲畜的數量十分短缺,即使有,價格也十分高昂。因此,可以作為人力替代品的價格相當高。而人力的互補品自然是使得人類得以正常生長的基本生存保障。“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缊袍敝衣”正是當時人們的真實寫照。沒有過多娛樂、教育方面的支出,僅是為了滿足基本生存需求以維持勞動的能力,因此其互補品的價格偏低。當商品的互補品價格相對偏低,而替代品的價格明顯高昂時,對該商品的需求自然大大提升,反之也是如此。
(二)近現代以來扶養義務的法定化趨勢
到近代以來,人權思想開始得到社會的重視,子女人格的獨立性逐步得到認可,健康和諧的親子關系成為關注的對象。從最開始的“戶本位”的家族觀念轉化為“親本位”的親屬法,最后發展成為“子女本位”的親屬法。[6]1911 年起草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是舊中國第一步民法典草案,其中的親屬編中有規定“家長”扶養的權利義務,但由于清政府被推翻而導致該草案未頒布施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主要存在規制父母子女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以及對夫妻之間的婚姻關系進行調整。而關于兄弟姐妹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還未涉及。1950 年《婚姻法》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步法規,是當時為了改造舊式婚姻家庭關系的重要工具,表明了黨和政府力求破除封建主義婚姻制度的堅定立場。1950 年《婚姻法》內容較為精簡,主要涉及夫妻關系與父母子女關系,僅在禁止結婚的事由中將兄弟姐妹關系包含其中,而未對兄弟姐妹之間的扶養義務作出明確規定。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社會矛盾開始轉化,婚姻法也在與時俱進地進行相應調整。1980 年對《婚姻法》進行修改,在第三章“家庭關系”中增加了扶養義務的主體,即有負擔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和有負擔能力的兄、姐也須在一定條件下承擔扶養義務。而這里對成年兄、姐施加的扶養義務是單向的,并不具有相對性,未對弟、妹成年后是否要對無法生存的兄、姐進行扶養做出規定。而在司法實踐中,會發現存在不少這樣的現象,即兄、姐犧牲自己的權益甚至是上學的機會,含辛茹苦地扶養弟、妹,供弟、妹讀完大學后,自己在晚年生活得不到保障時,弟、妹卻拒絕對哥、姐進行幫助和扶持。為了填補這一法律漏洞,2001 年《婚姻法》對此進行修正,在規定有負擔能力兄、姐的扶養義務的同時,也明確了該扶養義務具有相對性,即有負擔能力的弟、妹滿足條件時在同等范圍內也要承擔起對兄、姐的扶養義務。這一修改使得扶養權利義務的規則體系更加完善,符合權利義務一致性的法律原則。不僅有利于弘揚中華民族互幫互助的優良傳統,而且也解決單向性扶養義務所帶來的弊端,滿足現代立法的價值導向。[7]
三、扶養義務之適用條件
(一)父母已經死亡或者父母無力撫養
父母是子女撫養義務的第一順位人,而當父母去世或喪失撫養能力時,該責任便落到了有負擔能力的兄、姐身上。其中,包括父母雙雙去世,或者父母失蹤后的宣告死亡。父母喪失扶養能力,指的是父母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缺乏扶養能力的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父母已經無法維持弟、妹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包括自始無法扶養以及嗣后無法扶養。自始無法扶養是指父母明知其一開始便沒有扶養能力而仍然選擇生下弟、妹,如其家庭收入原本就不足以支撐其家庭開銷或者僅夠維持現狀而無法支撐多孩的開銷,以及父母均享受低保待遇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無經濟來源。而嗣后無法扶養指的是因突發事件導致家庭產生重大變故,父母一時間喪失了扶養能力,如父母雙方均因觸犯刑法而鋃鐺入獄。要從嚴認定父母是否具有扶養能力,結合父母的經濟狀況、家庭開銷、身體狀況綜合認定。嚴防父母為了逃避責任而將其扶養義務不正當地轉移給兄姐。例如,在父母身體健朗的情況下,有工作能力卻不愿去工作的情況下,不得將對未成年子女的扶養義務施加給有負擔能力的兄、姐。
(二)弟、妹屬于未成年人
兄、姐承擔的扶養義務仍不同于父母對子女的撫養義務。根據《民法典》第1067 條規定,父母給付撫養費的義務并不因子女是否成年而截然不同,就算成年但不能獨立生活的子女,也有權利要求父母給付撫養費。而兄、姐的扶養義務只限于對未成年的弟、妹承擔,成年的弟、妹盡管喪失勞動能力并缺乏經濟來源,兄、姐對其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扶養義務,更多是出于道德上或親情的關懷。
(三)兄、姐具備負擔能力
兄、姐只有在有負擔能力的情況下才須承擔扶養義務。首先,兄、姐必須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如果兄、姐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自身都無法照料本身,需要依靠他人的照顧,何談對弟、妹的扶養照顧能力。其次,兄、姐具備勞動能力,有穩定的工作和持續的收入來源。但是兄、姐的負擔能力還需要在其有余力的情況下來認定。如果其收入僅夠支撐自己的生活開銷,并且在兄、姐擁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需要扶養的情況下,如果要承擔對弟、妹的扶養義務將會大大降低自身以及其家庭生活質量時,要謹慎認定兄、姐在此時是否還具有負擔能力。自然,當兄、姐自身都無生活來源且缺乏勞動能力時,便不能被認為具有負擔能力。《德國民法典》1603 條規定,扶養義務人以不危害與其身份相當之生活為限度。《瑞士民法典》第328 條也規定,受扶養的權利人僅以無此幫助生活將陷入貧困者為限;兄弟姐妹之間無充分財力時,不負擔扶養義務;父母及配偶的撫養義務不以上述條件為限。其認為,以權利人方面生活維持所必要為限度。兄弟姐妹承擔扶養義務時,扶養義務人的經濟狀況必須在生存線以上,保有足夠的支出和儲蓄以供其養老。即使兄、姐不具備負擔能力,也可由具有負擔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來承擔撫養義務。
(四)該“扶養義務”屬于生活扶助義務
兄弟姐妹之間的扶養義務以不改變扶養義務人的生活現狀為基礎,區別于夫妻之間的生活維持義務。夫妻關系屬于密切的共生關系,共同生活的特性決定著其為利益共同體,相互具有生活維持義務,應當達到同一生活水平和生存標準。夫妻之間為了保持對方生活,即使犧牲自己部分利益也在所不辭。而生活扶助義務相對于生活維持義務來說負擔較小些。成年兄、姐對未成年弟、妹的扶養義務并非無限擴大,需要根據人均年消費支付金額,結合當地的生活水平、低保金額來判斷,扶養義務的前提應當建立在盡力而為的基礎上,并非強制要求兄、姐傾家蕩產、砸鍋賣鐵以此來負擔扶養義務。在還有余力的情況下,履行適當的扶養責任是應當的。盡管物質匱乏,但在精神上給予慰藉和支持也很有必要。生活扶助義務在性質上主要是起到輔助的作用,迫使扶養義務人的生活水平直線下降是不值得倡導的。
(五)扶養義務具有雙向性
該扶養義務在兄弟姐妹之間是相互的,具有相對性和雙向性,只是根據年齡的不同具有時間上的先后性。在弟、妹還未成年時,負有扶養義務的兄、姐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讓渡出自己的部分利益扶養弟、妹長大,這種以血緣和親情為紐帶的利他行為自然應當得到同等的回報。弟、妹在成年后,對喪失勞動能力并失去經濟來源的兄、姐基于公平、對等原則,承擔相應扶養義務。
四、生育權行使之合理限度
在現代社會中,生育行為不應當是一時沖動的結果,而應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決策。固然,生育權是父母天然享有的個人權利,屬于絕對權的范疇,原則上任何人不得干涉和破壞。但在家庭經濟學理論中,生育被視為家庭的集體行為,其前提是家庭內部成員的協商一致。因為涉及到家庭內部人員分工、資源整合等問題,屬于重大的家庭生產行為。這一行為旨在適當調整家庭內部的資源分配、調整家庭人員結構,從而使得整個家庭的福祉增加,充分發揮家庭優勢的能動性。家庭作為一個集體,以集體的力量為生產生活保駕護航,提供堅實的后盾,每一個參與其中的家庭成員的意志都應當得到尊重。因此,不僅應當考慮胎兒的利益,也應當考慮家庭中其他成員的利益以及接受程度。只有在每個成員相互配合、相互幫助的情況下,才能使得這一行為效益得到最大化。[8]
微觀經濟學中的“邊際孩子合理選擇理論”被引入人口決策中,以此來幫助人們判斷家庭人口決策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其默認人是具有理性的動物,應當根據生育孩子產生的收益和支出的對比進而做出綜合判斷。生育孩子產生的收益如情感上的滿足、經濟風險分攤的作用、保險的效用等等。而生育孩子的成本則包括生產的費用、因生產而付出的機會成本、保障孩子基本生長的費用以及教育的費用。這一理論也能幫助父母預先判斷自己的扶養能力,要求父母在行使生育權時不能肆意行使,濫用權利。要衡量自身是否具備扶養的條件和能力,是否做好成為父母的準備,是否從最有利于胎兒利益的原則出發。如果在父母本身已不具備扶養能力的情況下,仍然不計后果地生下孩子,而將扶養的義務轉嫁給已成年的兄、姐,使得后者的利益沒有得到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屬于濫用自己的權利損害他人利益。
五、相應配套社會保障機制的完善
我國從2013 年起開始提倡“雙獨生子女可生二胎”的生育政策,到2016 年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大力宣傳二胎對家庭人口結構改善的好處,希望能逐步利用人口紅利的優勢來減緩社會步入老齡化的速度。在二胎政策取得良好成效后,2021 年5 月底,國家進一步提出“一對夫妻可生育三個子女”的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本著“誰受益誰付出”的原則,國家屬于既得利益的享有者,應當與公民一同分擔生育風險和扶養負擔。完善相應配套制度和設施,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消除人們因擔心無法承擔養育成本而不敢生的畏懼心理,以確保多孩政策的實施效果符合預期。
目前我國實行的生育保障措施中仍存在許多弊端。一方面,在制度整體設計中,無法形成一個統一、邏輯連貫的頂層設計。各個地區出臺不同的保障標準,城鄉之間適用不同的保障項目,內容參差不齊、過于零散、差異較大。另一方面,生育保障的范圍無法使得所有公民都受益,保障的公平性不足以覆蓋所有公民。在生育的醫療費用方面,職工適用職工醫療保險,非職工適用城鎮醫療保險,農民則適用農村合作醫療保險。而在生育津貼方面農民和非職工是無法享受與職工同等的待遇。往往就是無法享受的這類群體更加需要生育津貼的保障。而且,我國對于多孩的專項補貼仍未做出具體規定,多孩家庭的利益無法得到充分保障。
從國外進行的生育保障制度可以看出,生育津貼全民享有是各國的立法趨勢和努力實現的目標。生育保障政策在屬性上體現社會的福利化特征,彰顯著國家的人文關懷。在日本的生育保障制度中,其規定,對于家庭的第一胎和第二胎每月發放5000 日元,第三胎之后每月發放10000 日元。丹麥對于二胎及以上產婦發放生育津貼:二胎或者二胎以后的孩子每月2208 丹麥克朗,該補助金可一直發放到孩子年滿7 歲。德國也同樣實行對不同人口的家庭結構也實施了不同的生育津貼保障措施。俄羅斯還設定“母親基金”項目,即生育第二個以及更多的孩子可以申請補貼來進行房屋、子女教育費用以及養老金儲蓄等用途。在新加坡,政府會支付高額的托兒費給生育孩子的家庭。[9]
在注重人權保障、弱勢群體利益保護的國際化趨勢下,我國也應當盡快完善生育保障體系。在頂層設計方面應建立統一、整體性的生育保障制度。兼顧城鄉一體的協調發展,努力減少城鄉之間的差距,以求真正實現實質上的平等。另外,完善和強化生育津貼制度,擴大生育津貼的覆蓋面,從職工受益延伸至全體公民受益。[10]對于所有符合國家計劃生育政策范圍內的生育行為,都予以生育津貼的獎勵。國家在進行資源整合、再次分配的過程中,應當對弱勢群體傾斜盡可能多的關注,為公民分擔適當的扶養義務,以便更好地享受對人口紅利投資所獲得的回報。
六、結語
人口政策伴隨著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而適時地進行相應調整,在我國逐步邁入老齡化社會的進程中,以“三孩”政策的放開來促進人口的增長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血濃于水的親情是我們每個人在這個世上難以割舍、最基本的社會關系。家庭作為溫暖的避風港和堅實后盾,為我們遮風擋雨,提供生存保障和精神寄托。我們作為家庭中的一員,在享有權利的同時也應當承擔相應義務,為家庭分擔責任、分攤風險。弟、妹的出生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幫助兄、姐分攤父母的養老責任,在父母年邁時成為兄、姐的幫手以及情感寄托,為兄、姐減輕一定負擔,為家族的繁榮興旺提供動力源泉,《民法典》 對兄弟姐妹之間施加的扶養義務自然無可非議。但從法律上認定成年兄弟姐妹必須對未成年的弟、妹承擔扶養義務時應當要謹慎考量、從嚴把握,嚴格適用其構成要件,以防父母為逃避扶養義務的責任轉嫁。父母在行使生育自由權時要本著最有利于家庭和兒童利益的原則,理性而冷靜地權衡家庭條件以及各方利益后作出抉擇。同時,作為既得利益者的國家需完善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大對多孩家庭的保障力度,為其分擔生育成本和扶養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