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社火
薛志成
一
我屬豬,生在高山,游蕩在軒轅故里的大街上。至今,在世上漂泊了整整三個輪回。馬社火是陪我一輪一輪過來的。
每年正月初五開始,村子里都要唱三天“破五”戲,接財神。唱畢,休整一天,恰逢正月初九,玉皇大帝的誕辰,村子里人習慣叫“上九”。我不明白為什么把正月初九叫成了上九,父親告訴我,古人認為9是數中最大者,皇帝是真龍天子,九五至尊,頭頂的玉皇的生日自然是上九。
管它是上九還是下九,孩子們期盼的是這天的馬社火。
天還麻麻亮,數家院子里早晃著手電筒的光芒,時不時傳來牲口圈門“咯吱,咯吱”的聲響。隨后,有男人扯破了嗓門:“喂噯,娃兒,快起來穿衣裳了,騾子都吃了,你還咋著哩?”粗長粗長的聲音像極了高原上的西北風,嘶吼著,從這家竄出來,又從那家竄進去,瞬間劃破了村子的寧靜。
世上有三香:美人的嘴、黎明前的瞌睡、羊腦髓。這是鄉間傳的一句笑話,也是大實話。孩子們正香得受活,夢就被打成了碎花花。無奈地伸了幾下懶腰,猛地記起上九的馬社火,一骨碌翻出被窩,三下五除二,穿上厚梆梆的棉襖棉褲,鉆進炊煙彌漫的灶房,吃一只雞腿,喝一碗醋拌湯,心里熱乎乎的,即踅身出了門,朝畫花臉的戲臺飛了。
一溜煙工夫,頑皮的孩子在戲場擠了一大堆,有追逐打鬧的,有看畫花臉的,還有爬上戲臺蹭熱鬧的。
第一次見人家拿布帶子纏馬身子(扮馬社火的演員)的頭,我的腳就粘住了地。我很納悶,問父親為啥要纏頭。父親說,那長布帶子叫勒頭,頭被勒緊后,人的眉毛和眼就吊起來了,顯得格外精神。我細細瞅了瞅馬身子,果然眼豎起來了,眉毛也豎著飛起來了。
纏完頭,馬身子用手揉了一會兒臉。臉上的皺紋沒了,皮膚展脫了,干癟癟的臉也變得肉嘟嘟的。左手拿了小圓鏡,對著鏡子看了看,右手在臉上搽了幾下子白粉,又用海綿輕輕拍了拍,待看上去均勻了,屁股就坐在板凳上,腰挺得像根定海神針,一動不動了。
開始畫臉。
男女老少個個口一張都土得掉渣:“搭臉”。搭臉就是畫臉。畫什么臉,那必須提前預計好扮演的人物,一般是兩折子戲的角色,十個左右。《天官賜福》是年年必須的,有天官、黑虎、王靈官、劉海、文魁等五個角色。天官是老生,素臉。黑虎是凈,大花臉,黑色居多。王靈官也是凈,大花臉,數黃色和金色多。劉海是小生,素臉。文魁臉青得賽鬼王。剩下的角色,如《三英戰呂布》《二進宮》《桃園結義》《華山救母》,都扮演過。現在想起來,這些不都是弘揚正義的戲曲嗎?在我的記憶里,《三英戰呂布》扮演的最多。劉備是須生,素臉。關羽是紅臉凈,額頭上爬著好幾條黑色的臥蠶眉。張飛是凈,大花臉,色彩紛雜。呂布是武生,素臉。
但凡素臉,最好畫,說到底,除了打或肉色,或暗紅,或微紅的底色外,幾乎一個樣,僅僅是勾了眉毛和眼角,涂了口紅而已。大花臉就不一樣了,最難畫,要打底色,還要按它特有的臉譜去濃油重彩。該是印堂上一座寶塔,就不能現出一只手掌;該是丹鳳眼,就不能描勾獨眼;該是紅臉,就不能搽白臉;該是嘴大臉闊,就不能尖嘴猴腮;該是黑的多,白的少,就不能白的多,黑的少,以致黑白顛倒;還有,那些紋路、圖案以及過渡連接之處都有固定的模樣,不可隨意而為。
據說,馬身子一上馬,所扮演人物的靈魂或神靈就附體了。因此,畫臉是相當嚴肅的事,一般人無資格做這份神圣的活兒,也不敢毛遂自薦,只胸有成竹者才能擔當。他們一手執筆畫臉,一手常叉在腰間,又時不時地摁馬身子的胳膊和腔子,再三提醒:“喂,坐端坐直頭抬起!”那些人,多大字不識,沒有經過專門的美術繪畫訓練,更沒有審美的意識,但他們是確確實實的能人異士,畫起臉來從不照看臉譜,手里的功夫巧過了媳婦的繡花針,連人體彩繪大師也未必能如此得心應手,以致招引了眾人前來擠著圍觀。
馬社火的風姿是從裝扮開始的。天官頭戴九龍冠,黑三須,紅袍蟒纏身,手握如意鉤。文魁頭上束著鳳翎紫金冠,兩鬢紅發掩耳,似白鶴亮翅,紫蟒袍加身,一手文書一手筆。黑虎和王靈官,頭戴獅子盔,滿髯,著靠,一個黑來一個紅,前者揮的是單鞭,后者一手鞭一手磚。劉海戴的是軟氈帽,一身小生打扮,手里端個盤子,里面放滿了硬幣和黃紙錢。再看看《三英戰呂布》。劉備,侯帽,三髯,黃靠,一手舞劍,另一只手里還是劍。關羽,頭上夫子盔,長髯及胸,綠靠,手掄長桿大刀。張飛,頭戴八面威,開口髯,黑靠,手握一根蛇矛。呂布,帥盔當頂,白靠,插著背壺旗,挺著一桿方天畫戟。另外,凡是神仙者,帽盔或兵器上都粘有黃紙折的花兒。黃為貴,紅為忠,綠為義,黑為正,白為奸,在馬社火的裝扮里一目了然。
有黃發老人,神乎其神地說:“娃娃伙兒,看!那就是青龍偃月刀。關老爺當年提著這把神刀,溫酒斬華雄、斬顏良誅文丑、千里走單騎、出五關斬六將,真是天神下了凡……”唾沫星兒亂濺。
一切就緒,人們牽騾子而至,馬身子就上馬了。
其實,打我記事起,馬身子沒騎過馬,騎的是騾子。父親卻說,很早很早以前,家家都養馬,馬身子騎的是馬;后來,人們覺得騾子比馬干活有耐力,養起了騾子,馬身子就騎在了騾子的背上,但叫習慣了,仍叫“馬社火”,把馬身子騎騾子仍叫“上馬”。
馬身子一上馬,按秦腔戲里角色的出場順序排成了一列,儼然一個個神話中人或歷史人物面世。我最喜歡的還是《三英戰呂布》。張飛倒騎在騾子上,持蛇矛猛刺呂布,呂布使方天畫戟隔擋住了,關羽眉飛色舞,雙手掄起大刀緊跟在呂布身后,劉備舞著雙劍也攆追不舍。孩童時,只覺得精彩、熱鬧。后來,識了幾個字,讀了《三國演義》,一看到這情景,眼前就浮現出劉關張在虎牢關大戰呂布的場面,好像時光再沒有流淌,這一招一勢都定格在那群雄逐鹿的年月里。我也不由得拳頭握了再握,心弦緊了又緊。
大約早上九點左右,馬社火先到關帝廟和山神廟的院子里各轉了三圈,待燒香的人磕完頭,就挨家挨戶串門。馬社火的前頭是鑼鼓鈸。一人敲鑼,“鏘”的一聲,東頭敲了,西頭就能聽著。兩人抬著一面牛皮大鼓,一個人使勁兒、有節奏地掄鼓槌,“咚咚咚,咚,咚咚咚”,敲個不停。三四人拍鈸,“叮叮叮,叮咣叮咣”,和著鼓聲,驚天動地。馬社火的后頭,是一群群臉臟兮兮的,凍得鼻涕墜成線的孩子,吆喝著,追逐著。
這天,每家每戶大門都敞開著,門檻也都去掉了。聽到鑼鼓鈸聲近了自己家門,主人早早提了一串子鞭炮,立在大門口恭迎。馬社火一到,炮就噼里啪啦地響。進了門,馬社火在院子里轉上三五個圈圈。按老年人的說法:上正時月,鑼鼓鈸吵吵,驅邪;馬社火在院子里攘攘,一年吉祥。
大人小孩眼巴巴地瞅著劉海,盼著他早點灑金錢。忽的一下,劉海手一揚,一把黃紙錢在空中開了花,又紛紛揚揚地飄向院子。有人喊:“劉海灑金錢了!”說時遲那時快,一枚硬幣就在地上滾圈兒了。主家的孩子跑前去,忙撿起硬幣,興沖沖地交給母親。過后,那母親會用一小片紅綢布將硬幣包起來,然后縫在孩子的帽子上,說有財源廣進之義。
依稀記得我的帽子上年年有劉海灑給我的金錢,恨不得將它摘下來買顆糖吃。母親卻說,戴著,錢會越來越多。我聽了母親的話,渴望有好多錢買糖吃。不知什么時候,劉海的金錢掉了,無影無蹤。我哭了。母親說,傻孩子,劉海明年還會灑的。我笑了。
隊伍里有專門燒香的人,在上房的正堂點香燒紙磕頭作揖。完畢,主人按自己的經濟狀況,給燒香的人端的盤子里放上三五元錢或者一兩包奔馬香煙表示謝意。父親退休在家,心善加上對神靈的虔誠,出手闊綽些,每次都是一張手幾乎沒摸過的五元新錢、兩包奔馬香煙和一瓶上邽大曲酒。旁邊有一個人背著軍綠色的飯包,裝了禮物,出了門,馬社火也隨著出了門,向另一家走去。
下午三四點,門兒串完了,馬身子下馬卸妝。這時,總有些人拿了黃紙去托靈官的花臉,說小孩子哭鬧無常,用它禳解,挺靈驗的。之后,會長等幾人清點完所收的錢和煙酒,把錢和煙平均分給演員和所有組織人員,酒大家一起劃拳喝。
正月十五,一個社子里的十幾個村子都妝馬社火,從四面八方向廟院聚來,給九天圣母火星娘娘祝壽。偌大的一個廟院,馬社火每三個一并排,頭都挨著尾。加上咚咚咚鏘叮叮叮咣的聲響,那場面一個聲地叫好。馬社火表演一結束,社戲就連上唱。我們這等小孩子,一時半會兒聽不懂唱詞,不知誰從哪里聽來了一句,你傳我我傳他,傳來傳去,就傳成“頭戴八卦四棱子,頓頓吃的莜面丁丁子”。
正好,我們每年跟在馬社火的后面,瓜兮兮地吼著“頭戴八卦四棱子,頓頓吃的莜面丁丁子”,東家出西家進,還一個勁兒地蹦個老高,惹來大人家莫名的嬉笑:“你看那些沖棍子,一個比一個沖,都要上房揭瓦了!”
活潑調皮是孩子們的天性,在大人們眼里竟是特美的風景。
之外,還有更美的景致。一幫戴小帽子、穿一身青黑色衣服的老漢靠在墻角,悠閑地醉在冬日的暖陽里,吧唧吧唧地吸著旱煙鍋,你一句我一句爭議著當天的馬社火妝得如何如何,手激動地比劃著他們年輕時的馬社火又是如何的精彩與氣派。一個說,那些年他年年妝張飛,光看他使矛的姿勢,就知道長坂坡的英雄猛張飛是個啥樣;一個嗨了一聲,說那時候他年年的黑虎,手里的鞭不管咋拿著都鎮得妖魔抖三抖;一個說,那時候天官非他不行,誰叫他蟒袍一上身就有幾分文縐縐的仙氣……一個個口里冒著煙圈圈,夸著海口。上氣不接下氣的憨笑里全是童心未泯。
是啊!老漢娃娃,娃娃老漢,一樣的純真,高原上黃土的色調那樣的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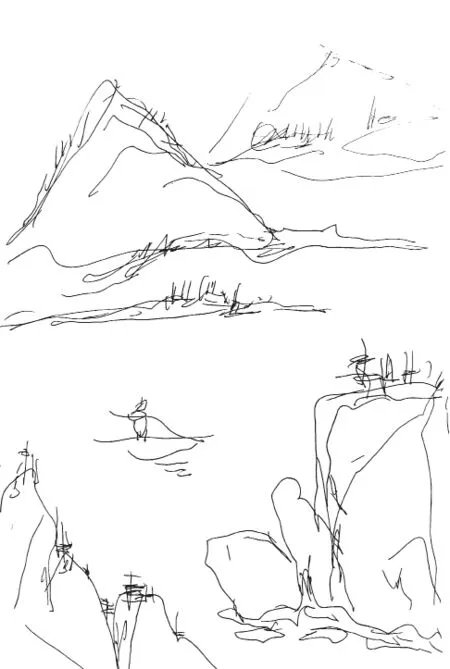
這些都是我頭一個輪回里的記憶。那時,我常嘲笑川區人的馬身子是步行的,是“走社火”。
二
到了第二個輪回,我再不是胡亂吆喝的小屁孩,鼻子里入了煙,懂了世事。
那些年冬三月,彩色電視成了農村的奢侈品,能從天明演到天黑,村子里人成天窩在炕上。
“破五”戲拉倒了,戲場子荒蕪了。不幾年,戲臺在一個暴風雨的夜晚悄無聲息地塌了,像沒娘的娃死了就死了,無人惦念。
一長者對眾人說:“正月初五是驅窮納福的日子,村子里得有個響聲才是!再說,我爺的爺的爺都不知道馬社火是啥朝代啥八年留下來的,咋能在我這一輩人里完蛋呢?要妝,一定要妝!就是到了孫子的孫子的孫子手里,馬社火還要妝!”這話從口里一出,一傳十十傳百,都說有道理。道理歸道理,到底咋辦?會長帶了人去關帝廟占卜,祈求關老爺問問上天能否將上九的社火挪到初五。他們擲了幾遍牛角,終得一上一下的陰陽卦,笑呵呵地出了廟門。
大家也笑了。
“破五”戲成了“破五”的馬社火,會長的家成了畫臉的“戲臺”。
可是,整個村子里沒有幾頭騾子了,強健的毛驢就上了用場。不過,關老爺騎的還是騾子,活生生的威風;不過,每家每戶給社火隊的錢可翻了不至幾倍,少者二三十元,多者五十元,煙的檔次也高了許多。
三
第三個輪回開始,村子里出了個懶漢——十五六歲的小伙子,不愛讀書不愛下地勞作,人們都罵他“二流子”。
眾人口里有毒,他果然和溝里的水一樣從村子里流出去了,音信全無。過了四五年,他又流回了村子,西裝革履,頭發有模有樣,再也不是亂蓬蓬的雞窩,暗暗溢著玫瑰香。
村子里人故意鄙薄說:“當大款了?!”
他說:“哪里哪里!錢倒是掙了幾個。”
他還給村民們說,在大山的背后很遠很遠的城市里滿是錢堆堆,關鍵是想不想去掙。幾年里,他獨個兒闖過疆下過海,扭過鋼筋掌過勺,現在也算小老板一個。
村民又問:“去城里真的能掙好多錢?”
他說:“這還有假?不僅能掙錢,還要啥有啥。比如女人嘛,要臉蛋有臉蛋,水淋淋的嫩;要胸有胸,哈密瓜的大;要腰有腰,楊柳梢的細。哪像咱這地方的,臉蛋紅得像柿子,胸平得像砥石,腰粗得釀醋缸,熊樣的漢子。”
眾人一聽,哈哈笑了,嘴上糟蹋著二流子壞透頂了,心卻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嘭地一聲,墜在大山里,墜在黃土上。
西北風那個吹,雪花那個飄。一個個漢子,一個個石碑。
也許,這是幾千年來黃土高原的漢子們第一次發出的對人生的感嘆,對人生的質疑,對祖祖輩輩所得益的大山和黃土的鄙棄。
在他眼里,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掙錢,不斷地掙錢,才能過上好日子。
二流子的話撥云見日,有本事的年輕人一個連一個地飛了,飛過大山,飛向城市。那里果真能掙錢,出門時身上空兜蔫著出,進門時錢滿兜憋著進。
地,自然種得少了。人們又嫌騾子性烈,食量大,全養了毛驢。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毛驢多了,一定有強悍的,個頭大的。挑選些攢勁的毛驢,馬社火依然上演了。
大山依舊偉岸,黃土依舊厚重,漢子卻不再有拔山之氣,不再有憨厚與率真。好面子,好攀比,典型的“城里人”。你給社火隊一百元,我照樣能拿出一百元,或者更多,就連那些關著門在外地過年的人也都托親房鄰居替他們給社火隊份子錢。搭了錢,不忘打個電話表示自己的存在,對老家的思念和對神靈的虔誠。
后來,鎮上大搞新農村建設,村子里往鎮上搬走了幾戶;縣城里開發新城區,村子里又搬走了幾戶;只開著門,孤寡老人守著院,子孫們常年在外務工的有幾戶;如我,吃“皇糧”遠走他鄉的有幾戶,老宅門上只守個鐵將軍;剩下的是種地的,合起來不到十戶人,并且種的都是方圓很近的、交通方便的地。去地里干活騎摩托,耕地用旋耕機,拉麥子有農用三輪車。誰還用毛驢!再說,養一只毛驢,一日三餐,一頓也不能少,得像祖宗一樣供著,多麻煩。
沒了毛驢,人們眼睜睜地瞅著卻沒法子演馬社火了。去年正月初五以下雪路滑為由沒有演馬社火。今年,我生命里第四個輪回才開頭,馬身子就徹徹底底地下馬了。
眾神仙再也駕不起祥云了,關老爺該夜走麥城了。
四
看到老家微信群視頻里馬身子步行著串門,城里生城里長的兒子問我:“爸爸,這些人把臉抹得花花的,穿得怪怪的,在干什么呀?”我一愣,嘴張了張,卻沒有勇氣對兒子說那是老祖宗留下來的馬社火。沒馬啊,為什么要說成“馬社火”去哄、去誤導一個腦子空白得像紙一樣的天真的孩子?我更恐懼,兒子的眼里馬社火好像是一幫子精神病患者在自我陶醉,在發瘋,在惡搞。最終,我還是說了,心里忐忑不安。
好友草根老兄在他的一首詩里寫道:
“十五歲那年迫不及待地攀上汽車
短短幾分鐘
小山村就被狠狠地拋向遠處
漸漸縮成一粒芝麻”
我突然想起自己也與故鄉漸行漸遠了,在我人生的后續輪回里,老屋塌了,芝麻小的故鄉還能容得下我這個游子嗎?容下容不下,只是西北風刮臉兒一刮而過的事。可是,芝麻小的故鄉里還有馬社火的影子么?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向重重大山望去,山后是我魂牽夢繞的故鄉。穿過遙遠的時空,我聽見了老祖宗的吶喊——咚咚咚鏘叮叮叮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