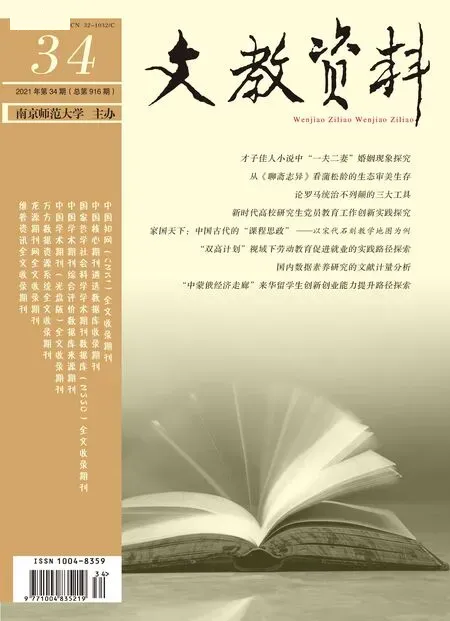虛擬偶像直播的傳播學分析與思考
黃博一
(南京藝術學院 傳媒學院,江蘇 南京 210000)
智能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加劇消融虛擬與現實之間的邊界,在人工智能(AI)技術、3D 建模技術、全息成像技術、5G 技術等智能信息技術的全面突破下,依附于二次元文化的虛擬偶像正在逐步突破“次元壁”,由“二次元”躍向“三次元”的現實世界,構建起智能信息時代革命性的交互方式和娛樂方式,開啟虛擬偶像的新紀元。[1]近年來,互聯網紅利漸漸消耗殆盡,短視頻領域如日中天,但也有略顯疲態的隱憂,無論是平臺主辦方還是內容生產方,都在不斷尋求破局方式。而在二次元領域,虛擬偶像配合直播互動鏈接粉絲,成為新選擇。隨著虛擬偶像粉絲帝國的逐漸崛起,嗶哩嗶哩網站、樂元素、騰訊、網易、巨人等互聯網巨頭紛紛布局虛擬偶像。大眾傳媒對于青年一代形象的建構更多是依靠成人的價值觀及世界觀,在很大程度上,青年處于被動地位,甚至是被異化的對象。[2]曾經依附于二次元文化的虛擬偶像正在逐步突破次元壁,從區隔于二次元產業(ACGN)圈中的小眾文化一躍成為一種不容忽視的新的文化現象。[3]虛擬偶像的誕生與發展根植于怎樣的社會語境?虛擬偶像直播受到青年一代熱烈追捧到底有著怎樣的生成邏輯?
一、虛擬偶像直播的現實語境
所謂偶像,是指被個體(或群體)認同,并受到極度尊敬、欽佩或者極其欣賞、喜愛和向往的形象化的象征性人格符號。簡單地說,偶像就是一種人格符號,一種自我認同的象征性人格符號。而虛擬偶像則是指以智能算法技術為內核,依托3D 立體影像制作技術、智能音聲合成技術和3D 全息投影技術等數字擬真技術,融合嵌入人的形象、語言、性格、心理等元素,集合打造而成的“超真”二次元影像形象,其運轉的內核是基于算法模型的程序編碼,即由二進制符碼匯聚而成的數據流。在本質上,虛擬偶像是智能信息技術、二次元文化和粉絲文化三者交互作用的產物。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虛擬偶像始于青年對理想中特定人格符號的崇拜心理,是當代粉絲文化在智能時代生成的一種“新偶像崇拜”。被一定數量的人喜愛、追捧和崇拜是偶像最基本的屬性,因此從狹義角度而言,虛擬偶像是被虛構出來的受到崇拜或摯愛的客體。在人工智能時代,虛擬偶像則是“虛擬場景或現實場景中進行偶像活動的架空形象”[4]。
虛擬偶像直播,意即以虛擬形象在新媒體上進行運營活動的視頻創作者們,運用虛擬人格設定、形象在視頻網站、社交平臺上開展虛擬偶像直播活動,往往使用面部捕捉裝置制造出一個二維或三維的動畫角色形象,以此做基礎對視聽者們進行或實時或評論回復性的互動。網絡虛擬空間給予了“人設”更多可架構的空間,由此虛擬偶像通過照片、視頻等方式分享自己的生活,營造更細節化的真實感,實現跨越虛擬與現實屏障的真實陪伴。正是網絡的不在場性,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官方回應的感覺,使粉絲有種被偶像回應的“錯覺”。而正是這種情感聯系的手段愈發強化了其在虛擬空間的陪伴感。加之動作捕捉和實時渲染技術的成熟,虛擬偶像直播互動也已被普遍運用。利用直播的形式將粉絲與偶像置于同一場域下,粉絲可以借助彈幕進行實時反饋,雙方均足以感知彼此正在做什么,足以感知旁觀者,足以感知自己正在被感知。對以“非真人拍攝的影像即為動畫”這一概念進行界定,虛擬主播的影像已經毫無疑問邁進可交互動畫的界定范圍之中,這便是與真人主播直播的最大不同之處。
在新時代融媒體語境下,自2017 年首次出現在視頻網站優兔(You Tube)的虛擬主播絆愛(Kizuna AI)以來,越來越多的虛擬主播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形成了一套日漸成熟的商業體系,虛擬主播在海外已經逐漸成為各大視頻網站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隨著越來越多的專業公司和個人工作室的成立,其職業門檻也被進一步提高,虛擬偶像直播行業無疑已經正式成為新媒介娛樂消費中的一部分。我國同樣有越來越多的視頻主播采用動畫形象進行直播或是短視頻的錄制,使其成為自身角色塑造的重要內容。在最初興起階段,其受眾大多來源于亞文化視覺領域下的二次元文化受眾者,或許可說,大眾對娛樂性精神消費的渴求進一步邁向多媒體領域。如今,虛擬偶像直播的受眾群體早已不止步于二次元文化受眾者,而是進一步邁向具有更多發展潛力的現實市場。
二、虛擬偶像直播的社會構建
(一)虛擬偶像人設的技術建構
在人工智能時代,技術驅動下的虛擬偶像有著不同的發展方向。微軟公司的人工智能助手“小冰”、蘋果公司的智能助手“Siri”和亞馬遜公司推出的智能語音“Alex”都有著偶像化運營的可能性。[5]虛擬偶像直播借助互聯網等虛擬場景或在現實場景中實現偶像活動,并不以真實形態與人們共處同一空間。從技術的角度看,虛擬偶像是數字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新技術的應用賦予了虛擬偶像“血肉之軀”,隨著科技的發展,三維計算機圖形技術愈發成熟,網絡虛擬偶像、游戲虛擬偶像、虛擬歌姬等紛紛涌現。虛擬偶像生態已步入繁榮期,虛擬偶像在具備聲音、動作等多重表演模態的同時實現與人類同時空互動的效果。[6]
起初視頻網站You Tube 進行短視頻類投稿的視頻制作主播Kizuna AI,其賬號持有者運用完成度較高的動作和面部捕捉技術與三維建模技術創作出了一個名為Kizuna AI 的動畫角色形象,以新時代的人工智能形象作為角色設定,完成了數個時長均為10 分鐘左右的視頻作品,該角色形象一炮走紅,不久虛擬偶像概念逐步為大家熟知。這段時期,虛擬偶像直播的創作尚且不具備實時傳遞性,但有別于真人直播的形象設計仍然牢牢抓住了大部分人的眼球。隨著新媒體技術的高速演進,2016 年進入了“網絡直播元年”,以移動微視頻、網絡直播為代表的全新視頻傳播媒介成為互聯網產業的重心,處在發展變化中的直播產業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參與及社會資本的追捧。此后,虛擬偶像直播便如雨后春筍般源源不斷地涌現。
(二)虛擬偶像人設的粉絲建構
虛擬偶像文化是典型的“參與式文化”,在亨利·詹金斯的理論中,粉絲被看作積極的消費者,而處在新媒體傳播語境下的粉絲群體對偶像文本進行解碼和再編碼的行為更具能動性。在傳統的偶像與粉絲的關系互動中,粉絲只作為其人設符號的消費者,而隨著虛擬偶像的誕生,粉絲的權利進一步擴大,他們在高度參與偶像角色編碼過程中,其意見成為官方修正偶像人設的重要考量。作為青年亞文化的二次元文化在青年群體中作為一種身份認同的重要文化形式得以存在和繁榮。[7]在參與虛擬偶像內容生產的過程中,粉絲依據自己對虛擬偶像的理解進行文本改編或補充,極大地拓展了虛擬偶像人設的邊界,而正是對人設符號不斷地賦予和解讀,使得虛擬偶像的生命力得以維持并煥發新生。
隨著媒體影像行業的進一步發展,對交互性影像畫面的需求也日漸增多,而虛擬偶像直播無疑是一個絕佳的表現平臺,業界不斷地嘗試發揮各種媒介特性的傳播范圍與話題熱度。新媒體的誕生使得意義生產的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既是內容的消費者,同時也是內容的生產者。[8]其結果證明,與傳統大眾傳播相比,網絡直播具有更強的信息交互、行為介入和情感帶動性,使得網絡直播產業在未來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這對傳統媒體行業的轉型、網絡經濟產業的興起與虛擬偶像直播的發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帶動作用。
2018 年后,大部分虛擬偶像已經由短視頻的投稿方式慢慢轉變為可作出實時交互反應的直播交互形式。2019 年,虛擬偶像主播成長趨勢達到了一個頂峰,平臺大量涌入以虛擬主播為創作載體的視頻上傳者。嗶哩嗶哩在第一季度財務分析報告里解讀了自身在虛擬主播業務上的增長,該季度有超過來自全世界的6000 名虛擬主播注冊在案,而觀眾人數接近600萬。可以說,網絡直播中用戶信息生產的多重共制,讓彈幕、視頻聊天室、主播間互動等的出現,極大拓展了虛擬媒介在信息傳播中的應用空間,直播中的用戶消費行為成為區別于傳統人際交往的重要體現,人們在網絡直播交往中產生的情感互動和交往依賴也逐漸成為情感社會化的重要平臺。自此,以“直播”為表現手法的虛擬偶像熱潮已經在大眾傳播媒介中達到了一個頗具話題的完成度。
(三)虛擬偶像與真人主播和動畫創作的比較
首先,虛擬偶像直播形象會帶來有別于真人直播的戲劇實現。榮格理論認為,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在不同的社交場合會產生出不同的人格面具。虛擬主播在此意味上便不僅僅是一個動畫中的角色,而是一個非鏡面性的、使聽者擺脫日常生活中的社交性人格面具,而位居其上的是符號性消費形象。即,當虛擬主播以二維動畫虛擬形象為中介進行溝通時,其表象中的特質通過社交媒體將這些符號化的特征顯示出來。而通過這些特殊的符號,其個體的人格特質也得到進一步穩固,雖說其扮演者仍然是一個實際存在的個體,但二維的虛擬形象在視聽者的心目中則會以相對穩定的、有別于現實生活中的動畫角色狀態存在,這是一種戲劇實現。“現代營銷學之父”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 指出,“想要在同類產品中脫穎而出,可以從標志與象征、名稱、聲音、相貌、行為舉止、肢體動作、素材這幾個層面出發”。虛擬偶像主播的角色塑造與創作發展同樣可說根植于此。與真人直播的不同之處在于,虛擬主播往往擁有二重人格特質,其作為被創造的動畫形象時具有社交人格面具的符號性,與其扮演者自身所具有的非社交性人格特質不需相近或相似,更有甚者會刻意進行背道而馳的演出,以此使得觀眾產生出凌駕于影像創作者之上的觀感,使得觀眾由可交互的、以多媒體平臺做媒介進行社交的網絡用戶之一,進化為第四面墻之外觀賞動畫影像創作的批評家,這種矛盾感同樣是真人直播所無法代替的。
其次,虛擬主播與動畫角色創作的差異度較大。新技術孵化的虛擬偶像已經不僅具備人類面孔等組成人體外形的器官,其“自由思維”的人工智能大腦也使虛擬偶像向人類身份偏移。[9]動畫創作的一大優越性在于,其相較于真人實拍電影擁有更為靈活夸張的表現手法。然而,虛擬主播的二維、三維形象往往依賴于真人演員的面部捕捉系統,其演繹面部表情的準確性遠高于對動畫角色形象演出感的需求,進一步講,虛擬偶像直播能夠作出的表情演出是極為有限的,乃至于是被束縛禁錮的。在此方面,虛擬偶像直播僅有在畫面以外的角色設定部分具有相應的商業性完成度,而在動畫表現方面具有較大空白。這一空白固然立足于資本最優化的抉擇,但同時也是因為虛擬直播這一載體表現形式篩選的結果,動畫角色形象的創作或許可說是藝術性與商業性雙重復合前提下的產物,而虛擬直播的角色形象完全依附于資本而誕生,是一種純粹的商業性產物,其作為一個社交人格面具的符號性被無限放大,所進行的演出必然會傾向于大眾的偶像化,即難以進行任何夸張或是有可能導致丑化偶像形象的演出,這一點顯然是和動畫創作中的夸張表現相悖。虛擬偶像主觀創作者的創作空間極為有限,塑造其形象更多是介于進行社交演出的演員及其幕后支持的商業資本。
再次,虛擬偶像主播進行的創作除卻具有實時互動性的網絡直播以外,同樣存在時長大多位于10 分鐘至20 分鐘的短視頻創作,這體現出了短視頻的視像傳播審美文化理念。動畫創作必然是連續不斷的、有持續性的過程,就算是10 分鐘以內的泡面番動畫,本身都必定位于一系列動畫創作中的單獨摘取段,而非獨立存在的短視頻載體。短視頻內容的生產與傳播依托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智能移動終端技術與基于高速網絡的移動技術應用,這是短視頻視像審美文化形成的基礎。短視頻平臺的功能設計為視頻制作提供了方便,形成短視頻視像內容制作與傳播的良性互動。算法推薦模式下的精準傳播推動了短視頻視像內容傳播走向智能化分發,更符合碎片化時代用戶的信息消費習慣,成為促進短視頻視像信息傳播的利器,短視頻視像傳播的平臺效應明顯。短視頻的審美文化特征主要表現在碎片化、淺表化、圈層化以及草根化,即虛擬偶像的短視頻創作往往會最大限度地表現出易于接受的核心內容,搭配易于辨認的自配字幕等。這種碎片化來自信息超載環境中的人類信息傳播特征,以碎片化的審美內容來填補人類時間與注意力的碎片化,形成了“微審美”特征,此種特征是作為具有一定體量要求的動畫創作形式所難以達到的,固然短片網絡動畫可以抵達類似效果,但一旦作品具有持續性商業價值,對作品中系統性設定的相對完整的認知便是必不可少的。
三、虛擬偶像直播的價值反思
首先是對教育價值的反思。虛擬偶像是年輕人在現實與虛擬的混雜中構建出的嶄新網絡文化現象,背后映射著青年人豐富的文化特質與生活樣態,它既是青年界定自我、表達自我、呈現自我的重要介質,又是青年人整體生活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虛擬偶像不僅代表年輕群體的符號和象征,而且折射了青年人的生存狀態、利益訴求、價值取向和文化心態,映射出當代青年獨特的“意義世界”,即在完美偶像中投射自我鏡像,在互動參與中實現自我價值,在虛擬符號中獲取身份標識。虛擬偶像雖有較為完美的外貌和人設,但本質上只是表演者,是被美化的可供消費的符號。人們對虛擬偶像的熱烈追逐,再一次印證了身體在消費神話中成為新的神話,身體已成為救贖品,在這一心理和意識形態功能中徹底取代了靈魂。將真實與擬像、現實與幻象之間的界限逐漸消弭或許就是消費社會的本質。[10]毋庸置疑,虛擬偶像作為年輕人開闊認知視野、彰顯個性特征、疏解精神困惑、獲取文化意義的重要方式,在青年人成長過程中具有積極正面的意義。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資本邏輯助推下偶像選擇和崇拜方式多元化導致的狂熱崇拜,使虛擬偶像直播產業在消費主義和娛樂主義的裹挾下逐漸偏離主流價值導向,影響了青年人積極健康文化心態的培育。[11]青年的價值選擇決定未來社會的價值走向,因此要強化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虛擬偶像直播產業健康有序發展,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文化生態圈,充分發揮網絡文化“育人化人”功能,并借力智能技術賦能,培育青年人積極健康的文化心態,推進中國特色網絡文化建設。
其次是對商業價值的反思。在虛擬偶像直播產業日益成熟的當下,其走向商業性同樣是一種必然。洛天依的商業合作從最初的游戲和動漫領域擴展到更廣泛的日常生活領域,與百雀羚、護舒寶、肯德基、雀巢咖啡、浦發銀行、長安汽車等多個品牌達成過合作,虛擬偶像代言領域的廣泛性和商業市場的號召力不容小覷。[12]而與動畫創作背后的商業性資本操作的不同之處在于,虛擬偶像形象在畫面設計完成的那一刻,其持續性的角色所有權便不再把握于繪畫創作者的手中,如何對該虛擬偶像形象進行進一步的培育與傳播,是演出者及統合相應形象的社交網絡關系性的資本社群所決定的。前文談及的虛擬偶像始祖Kizuna AI 在該形象于網絡上掀起熱潮,并具有相應程度的資本價值之后,其演繹者本身便出于商業性考慮被經紀公司代替,而在此層面上的消費群體本身是難以切實感受到差別的,因大眾實質消費的僅僅為最初被塑造出的社交符號本身。而相較于真實存在的演員,這種易于更替的虛擬形象在商業上的可提供價值與發展空間更具可操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