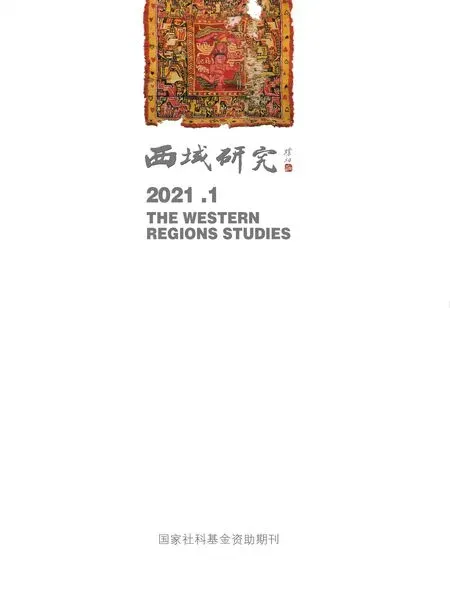輪臺詔與武帝的西域經營 ①
孫聞博
內容提要:伴隨漢匈戰爭及漢王朝西北拓境,“單于益西北”。為防止匈奴“兼從西國”,武帝堅持用兵西域。伐宛之后,武帝不僅在侖頭屯田,而且初步建立起“酒泉都尉—使者、校尉屯田—使者”的西域經營體系。征和四年,李廣利敗降匈奴,臣服車師后的西域經營是否繼續,引發爭論。武帝下輪臺詔,詳陳得失,實行了政策轉向。昭帝時,霍光仍行西域收縮戰略,鞏固邊塞后屯田伊循,加強對西域門戶的控御。宣帝親政,多“修武帝故事”,鄭吉屯田渠犁,數爭車師,武帝西域戰略開始恢復。以日逐王降漢為契機,鄭吉以輪臺、渠犁為中心立西域都護,并屯田車師,后者至元帝設戊己校尉,經營更趨鞏固。西漢后期,漢廷重向西域進取,終使城郭諸國內屬。這些背后,體現對武帝戰略的繼承,包含對輪臺詔得失分析的參考。班固將西域經營的成功,視作“昭、宣承業”。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1)《史記》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第3303頁。漢王朝在武帝統治時期,“外攘夷狄”,疆域大為擴展。其中,漢匈關系是左右變動的關鍵外部因素。與匈奴斗爭中,漢朝新拓進、建設的區域,由此具有更重要的戰略意義。這一背景下,漢對朔方、河西、西域的經營可以歸入一個大的單元。周振鶴著《西漢政區地理》,將“朔方、河西諸郡及西域都護府沿革”設為一章。(2)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下篇第三章,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5頁。從地方行政及人口流動角度而言,這是西漢中期屯田、移民、設置機構而形成的新的地域社會,在軍政功能、行政管理層面呈現自身特征。其中,漢對西域的經營,又是在河西全新郡縣規劃及治理基礎上,向西方的進一步伸展。宣元之世,西漢政府在西域先后設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3)周振鶴:《西漢西域都護所轄諸國考》(原刊《新疆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第44~46頁),收入周振鶴,李曉杰,張莉:《中國行政區劃通史·秦漢卷》第二編下篇第十一章,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493頁。圍繞漢代地方治理中的西域經營及其模式,學界多有考論。(4)參見李炳泉:《十年來大陸兩漢與西域關系史研究綜述》,《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第114~126頁;李楠:《近20年來兩漢西域治理問題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2017年第2期,第14~21頁。然而,專題探討武帝西域經營的成果,相對有限;(5)武帝屯田西域研究,參見管東貴:《漢代的屯田與開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五本第一分,1974年,第27~110頁;張春樹:《武帝時屯田西域侖頭(輪臺)的問題》(原刊《大陸雜志》第48卷第4卷,1974年),收入所著《漢代邊疆史論集》,食貨出版社,1977年,第123~130頁;施丁:《漢代輪臺屯田的上限問題》,《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20~27頁;張德芳:《從懸泉漢簡看兩漢西域屯田及其意義》(原刊《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第113~121頁),收入郝樹聲,張德芳:《懸泉漢簡研究》第六章,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39~258頁;李炳泉:《西漢西域渠犁屯田考論》,《西域研究》2002年第1期,第10~17頁;薛宗正:《西漢的使者校尉與屯田校尉》,《新疆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第105~110頁;武帝經營西域研究,參見田余慶:《論輪臺詔》(原刊《歷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3~20頁),收入所著:《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中華書局,2004年,第30~62頁;邵臺新:《漢代對西域的經營》第二章,輔仁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49~72頁;孟憲實:《漢唐文化與高昌歷史》第二章,齊魯書社,2004年,第30~46頁;汪桂海:《敦煌簡牘所見漢朝與西域的關系》(原刊《簡帛》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03~319頁),收入所著:《秦漢簡牘探研》,文津出版社,2009年,第169~193頁;王子今:《兩漢時期的北邊軍屯論議》,《秦漢邊疆與民族問題》第一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7~61頁;王子今:《“遠田輪臺”之議與漢匈對“西國”的爭奪》(原刊《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2輯,科學出版社,2009年),收入所著:《匈奴經營西域研究》第七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76~197頁;張德芳:《從懸泉漢簡看西漢武昭時期和宣元時期經營西域的不同戰略》,黎明釗編:《漢帝國的制度與社會秩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77~316頁;胡巖濤,徐衛民,姚柯楨:《論漢武昭宣時期的西域羈縻策略》,《新疆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第85~89頁,等等。思考武帝西域經營對宣元以后屯戍、設官的影響及意義者,更顯不多。實際上,武帝時期的西域經營為后世發展奠定基礎,也是理解兩漢西域治理的關鍵。武帝晚年所下《輪臺詔》,涉及西域經營的君臣爭論,包括武帝對正、反面經驗的分析與總結,對于認識武帝西域經營的開展及后續影響,頗為重要。這里立足正史、西北漢簡等基本史料,重新審視武帝西域經營的歷史背景、模式探索與制度成就。
一 伐宛之勝與武帝的西域經營體系
武帝前期的大規模漢匈戰爭,予強勁北胡以有力打擊。河南地的收復與河西地的拓土,更使漢王朝防線向北邊、西北大為推進,匈奴不得不愈向西北退卻。《史記·匈奴列傳》記:“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后,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6)《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第2914頁。單于庭當直上郡至張掖郡一帶,匈奴右方西移至酒泉、敦煌郡以北。整個河西的防務之任,由此變得愈加重要。不過,河西置郡雖然初步隔斷胡羌,但是因形勢發展,很快已不能完全滿足“斷匈奴右臂”的戰略目標。匈奴西退、進而與烏孫等西北國的靠近,使武帝產生新的憂慮。《鹽鐵論·擊之》大夫曰:“遼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紿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為巨患。是以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7)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定本)卷七,中華書局,1992年,第471頁。哀帝建平四年(3),揚雄上書也說:“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8)《漢書》卷九四《匈奴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3816頁。又,《漢書·西域傳下》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西〕,列(西)〔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9)《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第3928頁。班固以后見者審視“孝武之世,圖制匈奴”之略,便注意將“兼從西國”與“結黨南羌”并舉。具體措施層面,他不僅舉“乃表河(曲)〔西〕,列(西)〔四〕郡”,也舉“開玉門,通西域”。前者主要“隔絕南羌月氏”;而伴隨招徠烏孫東居故地未成,“以斷匈奴右臂”,卻需要同時依靠后者了。
元封三年(前108),趙破奴、王恢俘樓蘭王,破姑師。(10)《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第3171~3172頁。元封六年(前105),漢朝初與烏孫和親。張騫“鑿空”之后,漢廷開啟了“通西北國”的進一步實踐。不過,當時效果不盡章明。“烏孫和親后,漢朝沒有達到招徠‘大夏之屬’以為外臣的目的”,“因此,軍事上出現了向西再進一步的要求。”(11)田余慶:《論輪臺詔》,《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第46頁。值武帝后期,“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12)《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第3174頁。大宛之役,困難遠超預期,李廣利初征不利,隨后又發生“漢亡浞野之兵二萬余于匈奴”,于是,“公卿及議者皆愿罷擊宛軍,專力攻胡”。(13)《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第3176頁。“擊宛”的更全局目標服務于“攻胡”(14)《鹽鐵論·西域》文學曰:“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期而后克之。……其咎皆在于欲畢匈奴而遠幾也。”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定本)卷八,第501頁。相關分析還可參看蘇誠鑒《談〈史記·大宛列傳〉敘大宛之役》,《歷史研究》1979年第12期,第60~61頁,等等。,這里卻將“擊宛”與“專力攻胡”對舉,漢廷面臨是否還要開展西域經營的重大抉擇。當時群臣皆主罷兵,唯武帝不為所動,“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為外國笑。”“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實際意味著對匈奴“兼從西國”的無能力為。(15)《鹽鐵論·西域》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欲使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瓦解而附于胡,胡得眾國而益強。”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定本)卷八,第500頁。“已業誅宛”,指已將“誅宛”作為一項事業加以開展。遠征旨在以兵威震動整個西域,從而“連橫”西北諸國,共抗匈奴。箭已脫弦而出,武帝不愿放棄。出師四年,大宛降漢,漢王朝勢力由此進入西域。
《史記·大宛列傳》對武帝初營西域有所反映,前人征引雖多,仍可深入分析。內容計有三句,皆以“而”字啟首,恰可分作三組:
而漢發使十余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
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
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16)《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第3005頁。
先說首句。“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17)《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第2917頁。的結果是,城郭小國紛表臣服,漢廷于是開展積極外交,甚至派遣十余批使團赴大宛以西諸國,建立聯系。所行宣揚威德,意在“瓜分其援”,促成“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臂,曳劍而走”、“烏孫之屬駭膽,請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18)《鹽鐵論·西域》大夫曰。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定本)卷八,第499~500頁。的局面。《漢書·武帝紀》載,天漢二年(前99)“渠黎六國使使來獻”(19)《漢書》卷六《武帝紀》,第203頁。。敦煌漢簡又提到“出粟一斗二升以食使莎車續相如上書良家子二人癸卯”(1927)。(20)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991年,第294頁下欄。王國維斷“此簡乃太始三年以前物也”(21)王國維,羅振玉編著:《流沙墜簡》“屯戍叢殘考釋·廩給類”,中華書局,1993年,第155~156頁。。按《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記錄:“承父后續相如”“以使西域發外王子弟,誅斬扶樂王首,虜二千五百人”,“太始三年五月封”。(22)《漢書》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662頁。使者征發西域兵,這是傳世史籍所見最早史例。遠征七年后發生此事,一方面反映武帝堅持“誅宛”產生效果,兵威所及,西國臣從;另一方面,持節漢使及西域都護發西域兵的軍事模式,于此初現端倪。
再說次句。前方開展外交同時,“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敦煌當時尚未設郡,所置“酒泉都尉”屬郡下部都尉。敦煌漢簡記:
大始三年閏月辛酉朔己卯玉門都尉護眾謂千人尚尉丞無署就……(1922A)
□充□(1922B)

夜以傳行從事如律令(2438)(23)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第294、316頁上欄。
由于簡牘發現于今甘肅敦煌小方盤城附近,圍繞小方盤城遺址性質及玉門關遷移,沙畹、王國維、向達、方詩銘、夏鼐、勞榦、陳夢家等學者探討熱烈。其實,此簡并未言及玉門關,僅提到酒泉郡部都尉性質的玉門都尉。出土簡牘的小方盤城遺址當為酒泉郡玉門都尉府所在。《漢書·地理志下》“敦煌郡”下記轄縣“龍勒”,本注曰“有陽關、玉門關,皆都尉治”,(24)《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14頁。玉門關當在玉門都尉府西側,緊鄰今小方盤城。(25)近年分析又參見《一九九八年玉門關遺址發掘簡報》(執筆楊俊),張德芳,石明秀主編,敦煌市博物館等編:《玉門關漢簡》附錄二,中西書局,2019年,第295頁。前面提到,趙破奴等于元封三年破樓蘭、姑師,“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后來形成的河西四郡之中,張掖郡轄縣有玉門,顏師古引闞骃云“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于此”(26)《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14頁。。漢王朝經營河西,自酒泉向西的亭鄣終點應是玉門關,而非玉門縣。伐宛之勝,使得亭鄣又得續向西延,“西至鹽水,往往有亭”。新的起點,便是玉門。作為往日終點,它發展成為東、西兩條軍事交通線交匯的關節核心所在。“而敦煌置酒泉都尉”,應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所謂“酒泉都尉”,就是酒泉玉門都尉。漢代,都尉府除設都尉一人,還置丞、司馬、千人、候,不僅有烽燧候望系統,更重要是建立起常備武裝力量。這對遠征后保持漢廷對西北諸國的軍事震懾,意義重要。
而將“前方”漢使與“后方”敦煌軍事系統實現銜接的,便是“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由此,我們來看最后一句。前論初征大宛不利,武帝有“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為外國笑”的擔憂。《史記》所記“侖頭”,《漢書·李廣利傳》作“輪臺”,顏師古注“輪臺亦國名”。(27)《漢書》卷六一《李廣利傳》,第2699頁。“侖頭”位于龜茲東面,作為城郭小國,得以與引弓大國烏孫并列,成為“苦漢使”的代表,本身便值得注意。《史記·大宛列傳》記:“于是貳師后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28)《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第3176頁。李廣利二次伐宛,“兵多”遠勝前次,以致“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唯侖頭拒絕迎軍給食,可知“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為外國笑”并非隨意列舉。李廣利大軍連攻數日,方破侖頭,說明后者雖小,但防御能力較強。地處通西北國之要道、征伐大宛所必經,侖頭預見未來供給漢軍、漢使煩費無息,于是態度明確,不予合作。屠城是野蠻殘酷行徑,(29)王子今對“李廣利屠輪臺事”有所考論。《“遠田輪臺”之議與漢匈對“西國”的爭奪》,見氏著《匈奴經營西域研究》第七章,第177~181頁。但客觀上為漢王朝在西域要道旁建立一個可田可守、補給使者的軍事據點,提供了可能。該地原有的城防守御條件,也應是重要參考。
具體表述,《漢書》所記稍有差異。《漢書·鄭吉傳》作“初置校尉,屯田渠黎”,同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作“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同書《西域傳下》作“置校尉,屯田渠犂”。(30)參見《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第3005、3873、3912頁。關于“使者校尉”,余英時提到:“我在《漢書》中別的地方沒有找到使者校尉這一機構,很可能它只存在了非常短的時間,其主要功能是負責掌管所有派往西域的使者。《史記》卷一百二十三所說的使者的稱謂可能是不正確的。”(31)余英時著;鄔文玲等譯:《漢代貿易與擴張》第六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3頁注4。仔細觀察,《史記》僅記侖頭有田卒數百人,由使者領護,應屬漢廷在西域屯田的初始嘗試。始置使者的本官較低,可能并非校尉。《西域傳上》在輪臺之外,同時提到渠犂。“有田卒數百人”前有“皆”字,指輪臺、渠犂各有田卒數百人。這反映當地屯田發展,由輪臺向東擴展至渠犂。“置使者校尉領護”可讀作“置使者、校尉領護”,使者或仍領護輪臺田卒;新置校尉,將卒屯田渠犂。《鄭吉傳》《西域傳下》徑稱“置校尉,屯田渠犂”“初置校尉,屯田渠黎”,又反映渠犂地區后來發展更快、屯田更廣,可用“屯田渠犂”概稱當地軍墾的整體狀況。相應的管理者,也便主要稱校尉。需指出,使者是身份,由皇帝差使赴當地理事,以節為標志;校尉是職官,管理田卒,組織軍墾,以印綬為標志。前者應有本官,有職事者佩印綬,如衛候、衛司馬,也可以是校尉;無職事者無印綬,如侍郎、光祿大夫、期門郎,這里交代有所省略。后者是屯田校尉,更完整職稱為將田渠犂校尉。使者抑或校尉,并不“負責掌管所有派往西域的使者”。武帝由此初步建立起“酒泉都尉—使者、校尉屯田—使者”的西域經營體系。
二 輪臺詔與西域經營爭論的實質
匈奴“兼從西國”,由此漸難維持。伴隨西國紛紛向漢,雙方進而聚焦于西域東北側門戶車師的爭奪。《漢書·西域傳下》云:
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32)《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第3922頁。
伐宛后僅兩年,武帝便派匈奴故介和王成娩率樓蘭兵攻打車師。這比前論太始三年續相如“發外王子弟”,還要略早。由于匈奴右賢王援救,漢軍被迫退兵。征和四年(前89),武帝以李廣利為帥北征,馬通將四萬騎出西河從擊,路經車師北。成娩受命復率樓蘭等六國軍擊車師,在側翼實施保護。這次匈奴無法顧及,車師“降服,臣屬漢”。漢王朝對西域城郭諸國較為全面的降服,在武帝時期首次短暫出現。(33)太仆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武帝)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漢書》卷七三《韋賢傳附子玄成傳》,第3126頁。“右肩”,《漢紀》作“右臂”,《漢紀·孝哀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九》,張烈點校,中華書局,2002年,第510頁。劉歆概括武帝功烈,稱“并三十六國”。由“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而不涉及宣帝所置武威郡,所言或非寬泛之辭。
武帝經略西域,多倚重匈奴降眾與西域兵。《漢書·西域傳上》“于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34)《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第3876頁。前引“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提到“擊車師”“往伐宛”主要依靠屬國騎。早期屬國騎兵,主要來自河西匈奴渾邪王降漢部眾。今以匈奴降王兩次統樓蘭等西域兵圍攻車師,是以夷制夷的發展。西域參與抗匈奴、擊車師在各國職官系統中留下印記。《漢書·西域傳上》記:
鄯善國,本名樓蘭,……卻胡侯、……擊車師都尉、……擊車師君各一人。
疏勒國,……擊胡侯……各一人。
龜茲國,……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各一人,……卻胡君三人。
尉犁國,……擊胡君各一人。
危須國,……擊胡侯、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一人。
焉耆國,……擊胡侯、卻胡侯、……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
車師后國,……擊胡侯、……各一人。(35)《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第3875、3898、3911、3917、3918、3921頁。
等級上,侯高于都尉,都尉高于君;名稱上,擊胡、卻胡有別,一偏重出動出擊,一偏重使敵退卻。參與諸國主要位于北道。其中,鄯善、龜茲、焉耆等國設置相關職官較多,在軍事行動中曾發揮重要作用。
需要特別指出:武帝后期,李廣利在對外征戰上實際扮演前期衛青、霍去病兩人的角色,既有統領眾將軍出朔方、酒泉塞遠征匈奴、尋求決戰,又有親率眾校尉遠伐大宛、深入破敵。漢王朝經營西域,針對的是匈奴“兼從西國”,服務于降服匈奴的目標。隨著征和四年李廣利敗降匈奴,伐胡大業被迫停頓。這時,西域經略是積極鞏固還是同步暫停,君臣產生爭論。《漢書·西域傳下》“烏壘”“渠犁”條下載錄此事:
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谷,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36)“黃金采繒”,《漢紀》作“黃鐵錦繒”。《漢紀·孝武皇帝紀六卷第十五》,第265頁。可以易谷食,宜給足不乏。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各使以時益種五谷。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谷,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筑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征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逢火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愿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37)《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第3912頁。
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聯名上奏武帝,建議加快西域經營,實行積極防御。原來輪臺以東捷枝、渠犁曾是小國,地廣草豐,灌溉可耕田5000頃以上。從“可益通溝渠”“各使以時益種五谷”看,此為在原屯田基礎上進一步墾荒;“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或將既有規模擴大三倍。作為衛護屯田的偵查騎兵,斥侯以河西張掖、酒泉郡所遣騎假司馬(及所統騎兵)充任,并歸屯田校尉領導。西域屯田系統與漢王朝本土聯系,通過河西騎置實現。這也形成“河西騎置—屯田校尉—斥侯”的縱深經營模式。待耕作一年,糧草蓄積,“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累重”,謂家屬、資產。此屬募民徙邊,并向建設行政據點發展。然后,亭鄣線由輪臺、渠犁附近的連城向前修筑,威懾西國,輔助烏孫,以使匈奴孤立。這一設想,有將河西模式向西域推展、復制的意圖,以實現對后者更有力控制。為保障方案推行,桑弘羊等人還提出兩項配套舉措:一是擬派丞相征事行視北邊郡,加強守備;二是擬派漢使赴城郭諸國,溝通安撫。應當說,整體方案的考慮是比較周全的。這也是目前所見漢營西域最有雄心的計劃。
不過,群臣未曾料及,這一上奏沒有被武帝同意:
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車師千余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飼)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贏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眾。……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38)“死略離散”,《漢紀》作“離散略盡”。《漢紀·孝武皇帝紀六卷第十五》,第266頁。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霸)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39)“力本農”,《漢紀》作“務本勸農”。《漢紀·孝武皇帝紀六卷第十五》,第266頁。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40)《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第3912~3914頁。
元狩四年(前119)漢匈決戰之后,武帝也有一段時間未再出兵。參據《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和《匈奴列傳》及《漢書·武帝紀》,(41)《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第2940、2911頁;《漢書》卷六《武帝紀》,第197頁。征伐的馬匹人員損耗,短期難以恢復;霍、衛去世又使將帥人選,一時無以為繼。征和四年不欲出兵,直接原因與此頗為近似。“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人馬、將帥皆失,且對士氣民心打擊尤大。這也觸動君主,使之反思三十二年以來“外攘四夷”的功過得失。有別前次,武帝“既悔遠征伐”“深陳既往之悔”,對當時內外形勢的深刻認識,在輪臺詔中有所展現:“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屬于增賦;“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又屬增役。民眾負擔愈重,皆因邊備而起。接著,武帝迅速轉入對西域經略的具體分析。輪臺東至車師千余里,距離過遠。在爭奪后者的軍事行動中,前者無法提供有效的后勤保障。以開陵侯擊車師的近事為例,危須、尉犁、樓蘭等六國居長安子弟為配合行動,提前返回本國。他們沿道供給漢軍,并發兵佐助,圍降車師。然而,諸國無力供給漢軍返程。漢軍破城后雖獲糧甚多,得以休整,但因路途險遠,自載糧草仍不足保障班師。武帝不得不征發河西牲畜載糧,出玉門迎軍。而接應兵馬從張掖啟程,行進困難,依然無法順利支持。武帝深諳,唯有穩固控制車師,方能長久據有西域。輪臺屯田擴展,亭鄣西延,并不能有效解決這一問題。正面戰場因李廣利兵敗,漢軍損失慘重。此時加快西域經營,功效不彰,卻擾民良多。他還特別指出,連接西北諸國的北部邊防本身尚存問題,如求穩步推進,更應從此著手。
輪臺詔是否反映武帝末年的政治轉向,是學界關注的熱點。《鹽鐵論·刺復》文學曰:“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于四夷,……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后,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從法,故憯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42)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定本)卷二,第132頁。武帝因征伐四夷,用“奮擊之士”;待用度不足,又用“設險興利之臣”;百姓苦不堪命,巧詐避法,又用“憯急之臣”嚴究。三者發展存在先后,并迭為因果:用兵四夷而財匱興利,財匱興利而民多詐巧,民多詐巧而峻法嚴刑。又正因三者存在先后,迭為因果,故“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的政策轉向,必從“悔遠征伐”“不復出軍”的根本出發,方有轉變可能。(43)“止擅賦”對于減輕剝削,“禁苛暴”對于整頓吏治,也同樣必要。以武帝個人而言,他晚年對西域經營、進而對漢王朝戰略有所調整:對內休息,對外收縮,這與當時群臣的主流意見有所不同。輪臺詔反映了武帝晚年在反思既往與審視現狀之下的政策轉向。
三 “昭、宣承業”:西域經營的成功及其內涵
詔下兩年,武帝去世。桑弘羊、田千秋等先朝大臣繼續任事。武帝末年以“邊塞未正”“卒苦而烽火乏”,要求首先鞏固邊郡防務的旨意得到貫徹。《漢書·昭帝紀》記,始元二年(前85)“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44)《漢書》卷七《昭帝紀》,第221頁。,同時加強河南地、河西地兩個防區的軍備建設。《后漢紀·孝明皇帝紀下卷第十》載耿秉議兵事:“孝武時……漢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徙民以充之,根據未堅,匈奴猶出為寇。其后羌、胡分離,四郡堅固,居延、朔方不可傾拔,虜遂失其肥饒畜兵之地。”(45)《后漢紀》,張烈點校,中華書局,2002年,第187頁。昭帝時期,君臣繼續做這方面的努力。始元六年(前81),漢朝初置金城郡,(46)《漢書》卷七《昭帝紀》,第224頁。又進一步加強對西羌控御。在鞏固邊塞的基礎上,昭帝、霍光再次面臨是否經營西域。《漢書·西域傳下》云“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扜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犁地皆相連也”,并“佩漢印綬”。(47)《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第3916頁。“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通鑒》作“霍光用桑弘羊前議”,并系于元鳳四年(前77),(48)《資治通鑒》卷二三《漢紀十五》“昭帝元鳳四年”,中華書局,1956年,第770頁。表示實際主政大臣霍光對意見的采納。當然,任用扜彌小國太子而非漢朝官吏作為將田輪臺校尉,僅是恢復屯田的試探性做法。漢王朝對西域經營的一度收縮,有所體現。鄰國龜茲以此為患,窺測漢廷意志未堅,殺掉賴丹。樓蘭此時也傾向匈奴,數遮殺漢使。霍光暫未追究前者,但令傅介子刺殺樓蘭王,選立親漢新王,更國名為鄯善。同在元鳳四年,“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49)《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第3878頁。昭帝一代,漢廷對西域影響僅限門戶所在。這恐怕正是昭帝、霍光君臣遵從輪臺詔旨意,鞏固邊塞、穩步推進的反映。當然,伊循屯田的積極意義仍多:漢廷首次向西國派遣駐軍,并在該國置官屯田。加強對鄯善控御,為未來漢王朝勢力再次進入西域提供了條件。
宣帝即位,效仿曾祖,特別在霍光去世進而全面掌權后,更多“修武帝故事”。(50)《漢書》卷二五下《郊祀志下》、卷三六《楚元王傳》、卷六四下《王褒傳》、卷七二《王吉傳》、卷八六《何武傳》,第1249、1928、2821、3062、3481頁。宣帝所“修”、所“循”,多為武帝末期以前“故事”。漢王朝經武帝末葉、昭帝、宣帝初期的休整恢復,力量也有所蓄積。宣帝由此開始奉行更積極的對外戰略。霍光去世于地節二年(前68)三月,《漢書·西域傳下》記:
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谷,欲以攻車師。至秋收谷,吉、憙發城郭諸國兵萬余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于石城。……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犁。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谷以安西國,侵匈奴。……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果遣騎來擊田者,吉乃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犁千余里,間以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犁者勢不能相救,愿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余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乃得出,歸渠犁,凡三校尉屯田。(51)《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第3922~3923頁。
就在這一年,鄭吉以侍郎領護、司馬憙以校尉將屯渠犁,武帝西域屯田首次恢復。鄭吉以渠犁為基地,再爭車師,又可視作武帝末開陵侯擊車師的延續。軍力構成也與此前接近,既征發城郭諸國兵,又自將田卒,田卒規模更多至一千五百人。初次行動較為順利,車師被攻破,然而補給再次發生困難。鄭吉不得不罷兵歸田渠犁,積蓄糧草后二攻車師。匈奴也如武帝時期一般,再次干預。鄭吉、司馬憙態度堅決,敢于引兵逢迎。二次行動后,漢軍仍須返回渠犁補給,身處漢匈夾縫中的車師王逃亡烏孫,鄭吉便將王的妻子安置于渠犁。這樣,車師地出現權力真空。(52)《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第3923~3924頁。宣帝利用這一機遇,命入朝奏事已至酒泉的鄭吉立即返回,繼續在渠犁、車師兩處開展屯田,“積谷以安西國,侵匈奴。”《漢書·匈奴傳上》對此也有記述,“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余民東徙,不敢居舊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53)《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上》,第3788頁。“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的意義,以往重視不足。這是漢王朝在車師屯田的首次實現。為防范匈奴,鄭吉、司馬憙一度將全部渠犂田卒遷往車師,且屯且守。從鄭吉上書“漢兵在渠犁者勢不能相救,愿益田卒”看,武帝輪臺詔曾指出“輪臺西于車師千余里”的支援、補給問題,依然存在。建議增加車師田卒,固然“道遠煩費”,然當時未被采納,主要還是接界匈奴勢力尚強,以致車師屯田暫難維持。當宣帝令常惠率后方張掖、酒泉郡兵遙解匈奴之圍后,鄭吉便將全部車師田卒又帶回渠犁,“凡三校尉屯田”。這次雖然仍未成功,但是桑弘羊等“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的建議,或有實現。且因破車師之功,鄭吉由侍郎遷為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諸國。他在渠犁鞏固基礎,發展力量,以觀時變。
神爵二年(前60),外部機遇終于來臨。“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撣將人眾萬余來降。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迎日逐,破車師,皆封列侯。”(54)《漢書》卷八《宣帝紀》,第262頁。玉門關、懸泉漢簡對此有所反映:
神爵二年八月甲戌朔□□車騎將軍臣□□
謂御史□□ 御史大夫

制詔御史□□侯□□□敦煌酒泉迎日逐王 如律令

為駕一乘傳別□載……(Ⅱ90DXT0313③:5)(55)張德芳:《從懸泉漢簡看西漢武昭時期和宣元時期經營西域的不同戰略》,黎明釗編:《漢帝國的制度與社會秩序》,第294頁。
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乙丑縣泉廄佐廣德敢言之爰書廄御千乘里畸利辯告曰所葆養傳馬一匹騅牡左剽久生腹齒十二歲高六尺一寸□□敦煌送日逐王東至冥安病死即與御張乃始<泠定雜診馬死身完毋兵刃木索跡病死審證之它如爰書敢言之(1301)(56)張德芳,石明秀主編,敦煌市博物館等編:《玉門關漢簡》,第109頁彩色圖版,第245頁紅外線圖版。胡平生:《匈奴日逐王歸漢新資料》(原刊《文物》1992年第4期,第62頁),收入所著《胡平生簡牘文物論稿》,中西書局,2012年,第237~238頁。
廣至移十一月谷薄(簿),出粟六斗三升,以食縣(懸)泉廄佐廣德所將助御效谷廣利里郭市等七人,送日逐王,往來(167簡)三食,食三升。桉(案)廣德所將御□稟食縣(懸)泉而出食,解何?(168簡)(I 0309(3):167-168)(57)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0頁。
當年八月,車騎將軍韓增已請御史大夫丙吉簽發至敦煌、酒泉郡迎接日逐王及部眾歸漢的官吏傳信,以便沿途提供交通保障。日逐王入漢,自車師過玉門關,經河西走廊而至長安。敦煌縣懸泉置提供的傳馬送至冥安置病死,時在神爵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懸泉廄佐廣德不僅制作廄御畸利所葆養傳馬病死爰書,而且還曾帶領助御七人實地迎送。《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記:“歸德靖侯先賢撣”“(神爵三年)四月戊戌封”。(58)《漢書》卷一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672頁。簡牘、正史初步勾勒出日逐王降漢的經過。
控制西域的匈奴日逐王降漢,使當地政治格局發生深刻變動。鄭吉由此“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59)《漢書》卷七〇《鄭吉傳》,第3006頁。。清人徐松云:“至元帝時,屯田車師前王廷,方罷渠犁之屯,故《陳湯傳》言‘發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不言渠犁。”(60)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記(外二種)》之《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中華書局,2005年,第401頁。韓儒林又說:“按元康年間,鄭吉放棄車師土地,取其人民居住渠犁。及匈奴經營西域的日逐王降漢,就常情推測,所徙的車師國人必皆東歸故地,車師也由漢軍占領。所以元帝時毫不費力的設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憑藉西域以制匈奴的根據地,遂由渠犁東徙了一千多里。從此,渠犁之屯罷,車師代替渠犁的地位了。”(61)韓儒林:《漢代西域屯田與車師伊吾的爭奪》(原刊《文史雜志》第2卷第2期,1942年),收入所著:《穹廬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24頁。此時車師國人東歸故地、漢軍也重新進駐的推論,較符“常情”。不過,懸泉漢簡見有:
五鳳四年六月丙寅,使主客散騎光祿大夫□扶群承制詔御史曰:使云中大守安國、 故教未央倉龍屯衛司馬蘇于武強,使送車師王、烏孫諸國客,與軍候周充國載屯俱,為駕二封軺傳,二人共載。御史大夫延年下扶風廄,承書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A)(Ⅱ90DXT0113③:122)(62)據侯旭東參考張德芳、張俊民校改而重訂的釋文。《西北漢簡所見“傳信”與“傳”——兼論漢代君臣日常政務的分工與詔書、律令的作用》,《文史》2008年第3輯,第37頁。
孟憲實分析,“八年以后的西域情形發生很大變化,西域都護府已經設立。這里的車師王只能是烏貴,所以烏貴回西域或許是為了重新即車師王位。”(63)孟憲實:《漢唐文化與高昌歷史》第二章,第47頁。五鳳四年(前54),是西域都護建立后第六年。置戊己校尉之前,宣帝曾將舊王烏貴送回車師復位,以統撫東歸國人。由此而言,漢軍再屯車師,作用是輔助性的。《漢書·常惠傳》記:“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罰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64)《漢書》卷七〇《常惠傳》,第3006頁。同書《西域傳上》又云:“于是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治烏壘城,……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饒,于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65)《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第3874頁。鄭吉“鎮撫諸國”,立西域都護“于西域之中”、“與渠犁田官相近”的烏壘城,而非它地,仍然遵循武帝故事。而“屯田校尉始屬都護”,不僅包括比胥鞬校尉、(66)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第123~124頁。張俊民:《“北胥鞬”應是“比胥鞬”》,《西域研究》2001年第1期,第89~90頁;張德芳:《從懸泉漢簡看兩漢西域屯田及其意義》,郝樹聲,張德芳:《懸泉漢簡研究》第六章,第242頁。鄯善的伊循都尉,也應涉及將田車師校尉。“憑藉西域以制匈奴的根據地”,乃是在渠犁的基礎上,輔以車師,不宜理解為根據地的東徙。設立西域都護,渠犁屯田應未罷棄,也不便說車師代替渠犁的地位。隨著漢廷對車師控御加強,屯田發展,至初元元年(前48),元帝在車師前王庭設置將田車師戊己校尉。鄭吉當年“愿益田卒”的企望,終于實現。漢王朝對西域的經營,經歷曲折反復,至此臻于告竣。
昭、宣重向西域進取,固然取得突破性成果。然從衍生脈絡分析,這卻體現武帝君臣西域經營體系的重建及發展完成。《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裴注引《魏書》曹操曰“夫定國之術,在于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67)《三國志》,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第14頁。,將“以屯田定西域”歸之于武帝。《漢書·宣帝紀》正文及篇末贊曰,都沒有對設置西域都護這一重大事件加以提及。《漢書·敘傳下》又云:“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68)《漢書》卷一〇〇下《敘傳下》,第4268頁。“昭、宣承業”的表述,尤須留意。班固將西域都護的建立,將西域有效經營的實現,視作昭、宣對武帝基業的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