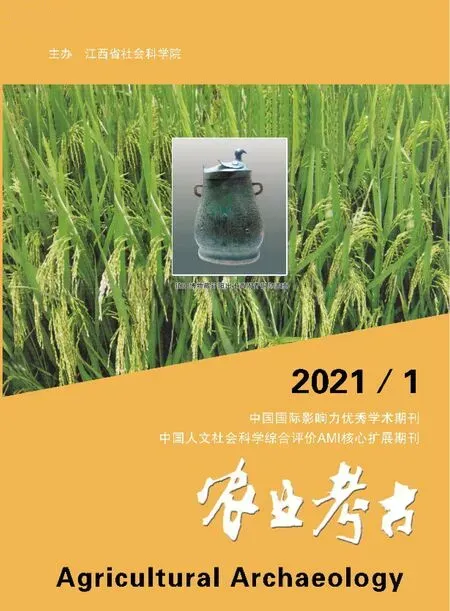何剛德《撫郡農產考略》農業經濟思想初探*
張志翔 何紅中 伽紅凱
張志翔,女,南京農業大學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農業史;何紅中,男,博士,南京審計大學新經濟研究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經濟史、政治經濟學;伽紅凱,男,南京農業大學中國地標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農業文化遺產、地標文化。
《撫郡農產考略》①成書于清末光緒年間,著者何剛德,福建閩侯(今福州市)人,光緒三年(1877)進士,歷任吏部主事,江西吉安、建昌、南昌知府,江蘇蘇州知府,民國間出署江西內務司司長,又任江西省豫章道尹,曾護理江西省長。其中,以任江西撫州②知府期間的成績最為突出。當時的撫州地區,“多童山赤壤”[1](序P1),加之水患頻繁,百姓生活艱難。何剛德認為,撫州原本是物產繁富的地方,但由于俗儒“鄙農學”,官府“亦不之督”,致使資源未得到充分開發,綜合導致農村的凋敝。他到任后,“勸辦農務”,即設立農局和試驗場,“墾開官荒四處,試種麻麥黍豆”[1](序P1);設農學課,講授辨土、用肥、殺蟲三科;利用公務之暇,奔走于鄉間田野,訪問老農,調查農產情況,并在此基礎上撰成《撫郡農產考略》二卷(上卷為谷類,以水稻為主;下卷分草、木兩類,分論經濟、園藝等作物)。
《撫郡農產考略》所述涵蓋撫州所屬各縣主要農產品種及其種植、加工與售賣等多個方面,取材廣泛,資料詳實,乃是一部全面的調查實錄,頗具史學價值。目前,學界關于《撫郡農產考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從自然環境和人地關系角度考察當時江西地區的農業經營方式③;二是專注書中所載水稻尤其是其地方品種之特色[5];三是探析著作所含農業生產如肥料制作與應用等技術[6],相對于該書記載的豐富內容而言,論及有限,尚有進一步拓展之空間。實際上,何剛德《撫郡農產考略》還是江西地區近代農業經濟轉型時期的代表性著作,其反映出的農業經濟思想具有鮮明時代特色,開創了全新的學術研究視角,但未能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
一、以價值為中心的商品經濟意識
中國傳統社會以自然經濟為主,雖歷經幾千年的發展、變化,但其表現出的自給自足特性和基本觀念始終根深蒂固。晚清時期,西方的文化與經濟思想已經沖開了中國的大門,然而大部分地區的社會形態和民眾意識并沒有發生明顯的嬗變。江西亦是如此,當地農民“日用飲食皆資于谷”[1](卷上P19),“郡人以種稻為本業, 草木乃其余事”[1](例言P1),自給自足的生業模式依舊非常明顯。即便是何剛德在撫州當地興辦農務、數年水患對當地的消極影響已經減輕的情況下,人們賴以生存的主要物資還是稻谷,“除自食外,臨川約余三四十萬石,金溪、崇仁約十萬石,宜黃約十余萬石,樂安、東鄉各數萬石,可以接濟鄰境”[1](卷上P15)。鄉民種植的農作物多以自用,生活水平依舊不高。
何剛德認識到自然經濟對生產的束縛與阻礙,在晚清動蕩、紛亂與革新的時局下,作為父母官,他努力興辦實事,亦在思想上不斷探索、求解紓困之道。難能可貴的是,何氏在記述撫州當地物產時說道,“播獲之遲速,土宜之深淺,谷石之輕重,價值之高下,在在不同”[1](卷上P1),明確引入了“價值”的概念,這無疑是對傳統經濟思想的重要突破。另一方面,我們知道在近代經濟學理論中,價值是商品的一個重要屬性,并通常通過貨幣來衡量進而成為價格,因此價格成為衡量價值的尺度;雖然囿于時代與自身的認識水平,何剛德未能從理論的高度對此進行闡述,但于“價值”相對的價格卻有著格外的關注。
以《撫郡農產考略》關于“稻谷”的記載為例,對各種水稻的品種、品質優劣以及在市場上的售價記錄甚為詳細。例如,在談到撫州所產名為“燦谷早”的水稻時,說其質量上等的,每石重一百二十斤,“每石價八九百錢,貴則一千三四百錢”[1](卷上P8),而一種叫“紅谷早”的早稻,則“谷價貴時一千二三百錢,賤時八九百錢”[1](卷上P19)。除了直接記述某一種稻谷的售價及其變動情況,何氏還將多種水稻的價格進行了比較闡述,一種名為“西鄉早”的水稻,“谷價最高,比他谷,貴數十錢”[1](卷上P7)而“大葉早谷”的價格又高于“西鄉早”,“每石比西鄉早高一二十錢,比他谷價益昂”[1](卷上P10);“寧都秥”“湖南秥”這兩種在價格上則不占優勢,“每石比西鄉早谷低百錢”[1](卷上P18)。 此外,他還注意到同一品種的水稻在不同市場所售價格也不同:“崇仁谷每石較樂安貴百錢,臨川又加貴百錢,宜黃谷價視樂安稍昂,金溪東鄉與崇仁同”[1](卷上P18),調查記錄不可謂不細致。
實際上,不僅是稻谷,撫州當地豆類、棉布、麻布、蠶絲等其他經濟作物的種植也給鄉民帶來可觀的經濟收益;而甘蔗、橘等水果以及煙葉、茶葉等的販售,利潤更高。《撫郡農產考略》對它們的售價情況做了記述(見表1),因而我們也可以比較清晰地掌握當時不同農產之間的相對價值差異及其可能帶來的盈利空間。

表1 撫州主要農產售價情況
何剛德《撫郡農產考略》對價值和價格的兼顧,歸根到底是對農產增值的重視,這顯然不同于前人特別是對農書編纂內容的選擇。一方面,傳統農書在論及農產時常以“概數”表達,鮮用具體指標量化,例如《農桑輯要》引《禮記·王制》說“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8](P2),《齊民要術·種谷》引《淮南子》曰“為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9](P54),即便是已具很強商品經濟意識、明末清初的《補農書》,在其附錄中仍講“瘠田十畝,自耕僅可足一家之食”[10](P177),未有更多“確數”描述;另一方面,鑒于水稻在南方農業中的重要地位,宋以降的農書對之多有記述,但強調的重點往往偏重于生產技術與經驗,從《陳甫方農書》[11]、《天工開物》[7]到《補農書》[12]、《梭山農譜》[13],涉及整地、浸種、育秧、移栽、施肥、耘耔、灌溉、防害等各個栽培環節,盡顯其詳。相較而言,《撫郡農產考略》雖在稻品上著墨較多,兼敘耕耘及收藏,但在述考農產時,或用錢,或用金銀,或用洋銀等貨幣價格進行價值衡量,反映了何剛德敏銳的商品經濟意識。
二、圍繞價格波動及供需變化創造盈利
關于農產品的價格,顯然《撫郡農產考略》之意圖并不在簡單的記述,而是要尋求其變動背后可能的利潤收益。眾所周知,農業生產具有明顯的季節性特征,因而農產品的價格受上市時間的影響較大。何剛德充分理解并利用了這一點,故他在書中強調可以利用農產品在不同時期的價格差異來獲得更加豐厚的盈利。
例如,“五十工秥”這種秥稻收獲時間早,“青黃不接之時,即已登場,故也。價初視他谷稍昂,亦以早出之故。若過半月,新谷上市,則無高下之分”[1](卷上P4);相比于其他糯米,“紅谷糯”的收獲時間早十天左右,“可以搶新, 得價最高”[1](卷上P37);白豆每升三十錢,五月成熟,“其時尚未獲稻,故鄉人恒藉白豆、綠豆、紅豆以換米”[1](卷上P71),也是利用時間差的優勢獲取更高的利潤。采摘季節對茶葉售價影響更為明顯:“臨邑西鄉茶,向通商販,今皆衰歇,茶每斤二百余錢。金邑,谷雨前摘者,值三四百錢,五月后摘者百余錢,立秋后摘者數十錢。東邑,茶上者僅百二三十錢。黃沙巖茶,葉粗味厚,價稍昂”[1](卷下P52)。這與茶葉本身的特性以及人們的消費習慣是一致的。
不僅是時間,何氏還認識到地理位置、交通條件等因素對農產市場的價格也會產生影響。根據《撫郡農產考略》所論,由于運輸不便,往往導致農產品的價格上不去,“樂安谷價最賤,以環境皆山,運行不便。上鄉水南地方,離城四十里,河道可達吉安;下鄉公陂圩,離城六十里,可達崇仁。秋冬水涸,不能行舟,銷路滯,故價賤也。崇仁谷每石較樂安貴百錢,臨川又加貴百錢,宜黃谷價視樂安稍昂,金溪東鄉與崇仁同”[1](卷上P3)。書中還提到,撫州當地為便于糧食運售特設置米棧,“每石價賤時八九百錢,貴一千二三百有奇。晚米味佳,鄉民多糶早谷,留晚谷自食。金溪之滸灣有米棧,購米運售他郡,以柳須白為最多”[1](卷上P24),通過改善交通運輸條件,顯然有益于銷售額的增加與價格之提升。
便捷的交通可以幫助拓寬銷售市場,撫州的農產品可以運至更遠的地方從而獲得更高價錢。例如,運到江西省城的柿餅能賣到每斤八十文[1](卷下P76);運到南昌販售的蔓菁和蕓薹,“根葉一擔值數百錢,子一擔三千余錢,油每斤七十余錢”[1](卷下P39-40)。為了獲取更高商品價格,人們還可以選擇國內他省的市場甚至遠銷國外。
例如,民眾日常生活必需的麻布,可以分為粗、嫩兩種,粗則做帳,嫩則做衣褂,“撫郡之布,郡城所出者為撫布,布幅寬一尺三寸,長一尺。其最粗壯可做棉花袋,售安徽之張家灘、河南之周家口”[1](卷下P5),李家渡的粗布正適合做棉花袋,瀏陽莊的麻布多用來做帳,售往煙臺、牛莊,遠及高麗,而崇邑的布都可以用來做衣料,“嫩莊售上海,中莊售漢口,又次莊售鎮江”[1](卷下P5)。整個撫郡一年的麻布收入大約三四十萬金,獲利頗豐。作為當地大宗農產品之一的燈芯草,同樣也頗受客商青睞,有客商來撫州收買燈芯草,運售到大江南北各行省,“每年出產約洋銀二十余萬元”[1](卷下P49)。
除了上述因素,何氏還認識到供需變化之于價格的重要性。我們知道,供需理論是近代經濟學體系中的奠基性理論,供需關系決定了價格在市場的變動并最終達到均衡。在中國古代史上,雖有歷代疏奏、食貨志、地方志等中關于經濟的闡述,亦不少涉及財經、賦稅、商貿、農產等實錄者,農書中更不乏農產加工、售賣的內容,但對價格波動背后規律的探析卻并不深入。至北魏賈思勰之《齊民要術》,曾指出時間會引起人們對某些農產品需求的變化從而影響價格,在思想認識上有了新的提高,而何剛德《撫郡農產考略》則更進一步,看到了生產供給也會對價格發揮主要的影響作用。
例如“紅谷早”,金邑百姓的日常飲食都依賴它,“豐年未能存儲,歉歲恒虞不足”,其價可高漲至一千二三百錢[1](卷上P19);“遲紅”的年產量可引起售價波動,“豐年價七八百錢,歉歲貴至二千有奇”[1](卷上P21);“胡瓜早”在豐收年時每石售價可達五六錢銀子,“若外商,販運者多。及兇年,有漲至一兩五六錢者”[1](卷上P14)。與之前的地方官員或農史學家相比而言,何剛德的認識更進一步接近價格波動及其均衡規律的本質。
三、提倡商品化農業生產與多種經營
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里,糧食生產必然占據重要地位,清末的江西撫州并不例外。通過上頁表1所記錄的農產品的售價,我們不難發現,種植糧食的獲利顯然是微薄的。因此,何剛德提倡在重視糧食生產的同時,還要發展商品化多種經營,將剩余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投入到經濟作物種植和手工業生產等方面。
何氏鼓勵撫州農民在糧田中套種經濟作物,如芝麻種在“棉花行中隙地”,綠豆又“附種在棉花地旁者”;“臨川多附西瓜地內,一隴西瓜一隴姜”,將生長期基本在三月至六月重合的西瓜和生姜間作;蠶豆則“多種于麥地及圃園內”[1](卷上P67)。如此,既可以保證糧食生產的量,還可以發展多樣化農業經營。另外,他還主張將不適宜種植水稻等糧食作物的土地充分利用起來,在不同地區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經濟作物的種植(見表2)。

表2 撫州各縣主要經濟作物的分布④
何剛德鼓勵商品化生產以獲取更高的經濟效益,實際上主要體現在要充分發揮名特產的優勢上。例如,撫州當地的小麥即為土產大宗商品的代表之一,“小麥收成較大麥半之,價值較大麥倍之。樂安之下鄉產麥五六百石,不敷本地之用。東邑每畝上麥可得錢四千, 售銷甚遠”[1](卷上P54);藕、蓮子、荷葉、藕粉等也是名產,“藕百斤值錢六七百,蓮子百斤值錢二十千有奇,荷葉百斤值錢二三百錢,藕粉百斤值錢十千有奇,紅藕粉較賤。藕十斤率得粉一斤。荷葉、藕粉銷路較廣”[1](卷下P12),受到市場的歡迎。
因水土條件的優勢,江西的煙葉、燈芯草也很出名。由當地煙葉制作而成的“露葉煙”頗受歡迎,“秧百頭值五六十錢,煙葉百斤貴時售銀七兩有奇,賤亦三四兩,宜邑煙葉每歲出產一二千金”[1](卷下P44);燈芯草不僅可做燈柱、燭心,還能搓繩貫錢或者織席,甚至可入藥,“臨川上田畝收草六七十捆,宜邑約收四十余捆,每捆均約十斤。燈草百斤價二十余千,賤亦十余千”[1](卷下P45),有較高的價格與收益。另外,撫州的環境條件正符合甘蔗、橘子等水果的生長,何剛德認為可組織鄉民廣泛種植。一畝田可種甘蔗五百多叢,而“每叢可發子蔗以二株,一叢重二十余斤,輕亦十余斤,計畝田可得蔗萬余斤”[1](卷下P11),臨川、崇仁所產甘蔗多運售南昌各處,一畝田可得錢三四十千;又江西所種橘類作物繁多,包括柚、柑、蜜桔、金橘等諸多品種,園林、屋角、洲地、沙地等處皆可利用種植,以增補家用。
何剛德對商品化生產的深度挖掘還體現在對肥料的利用上。當地所用肥料品種多、產量大,他認為不僅供本地使用,也可販售至外地,如“紅花草比蘿卜菜子尤肥田……其力量可敵糞草一二十石……草子一石賤時五六千,貴則十余千。出產甚多,運售建昌、饒州各府縣”[1](卷下P9)。他還多次提到將農作物枯槁用作商品交換,如豬肝豆,“枯可肥田,其力極厚……豆枯百斤值銀八錢,貴時一兩二三錢有奇。本地用枯約三分之一,其二均運往吳城、漢口等處,獲利較豐”[1](卷上P68);豆子亦可作肥,“春豆磨爛和草灰,窖二三日成臭氣,壅甘蔗極肥。東鄉人種蔗,必購此為肥料”[1](卷上P69),可增加豆子的使用價值與家庭收益。
四、重視農產品的加工增值
何剛德《撫郡農產考略》非常重視通過對農產品深加工增值獲益,包括糧食、棉麻、水果、竹木、蔬菜等各種在內,其方式多種多樣。對于稻米而言,在市場價格較低時,農戶可將其制糖以提高收益。黏稻中的“寧都秥”和“湖南秥”的“谷價俱低,每石比西鄉早谷低百錢。凡秥米均可煎糖,米一石可得糖一百零六七斤,每斤價三十二三錢”[1](卷上P18);又“西鄉早”可以釀火酒、煎糖、做粉條;“八月白”既可以做粉條,也可以做丸子;“袤腳老”可以釀燒酒,可以制粉條;“六谷糯”“柳條糯”“黃頸糯”“水雞糯”等可以做米花。不同品種有不同的加工方式,比直接售賣稻米要獲利更多。
何氏還主張將當地的甘蔗制糖。金溪、東鄉能煎砂糖,東鄉縣后又改煎白糖,并將種甘蔗煎糖與種稻兩者進行了比較:“計蔗千斤可得白糖七十斤、砂糖三十斤,以畝田八千斤蔗計之,可得白糖五百六十斤、砂糖二百四十斤。白糖每斤價百錢,砂糖每斤價四十錢,其利奇厚,較之種稻不啻十倍”[1](卷下P11),前者獲益更加豐厚。另外,金橘“可制金餞餅”,由于制作工序中金橘與糖的調配比例不同,又分為“濁水貨”與“清水貨”[1](卷下P73),售價亦有異,除了供近處居民食用,還遠銷湖北漢江河口各處,以致后來江西境內出現以蜜橘生產與加工為主的專業化村落,并形成了相當規模的商品基地。
相比黏米、甘蔗的制糖或果品蜜餞等的制作,何剛德關于農產加工后再銷售以提升經濟效益的思想,實際上在棉、竹兩個篇章中體現得更為直接、明顯。在“棉”篇中,《撫郡農產考略》寫道:棉花“可彈可紡,可以織布,可以做衣被,子可榨油”,重點還在于,何氏對不同品種棉花剝離出的凈棉量做了比較,“矮子種、毛子種,子花三斤可得凈棉一斤;鐵子種,子花三斤可得凈棉一斤一兩”,而“子花每斤值六七十錢,凈棉每斤二百錢;紫花稍貴,紫花布每匹多值錢一二百”,加工成品附加值更大且因物品而異,“棉花二斤四五兩可織成棉布一匹……棉布以臨川、崇仁為多,頓市莊尤好。同治間棉布價高,一匹值錢二千”[1](卷下P2)。棉籽同樣如此,每一百斤棉籽可以榨取味香可食的棉油十一斤與棉枯九十斤;棉油價格雖然比清油每斤要低二十錢,但棉枯每百斤卻值錢四百。
撫州多山,適合種竹。“樂邑環境皆山,東西廣八十里,南北長二百里,疊嶂重巒,平衍之區輒少”[1](附跋P3),品種繁多,用途廣泛。其中,“茅竹干最大,其用最廣,大者每株值二百余錢,小者亦值錢數十”[1](卷下P54);竹筍,“冬筍每斤值二三十錢,春筍半之。筍曬干,上者為玉蘭片,次合筍,再次明筍”[1](卷下P54)。由于竹子功用極多,加工后可獲利,故為部分地方致富的重要資源,如宜邑“地勢平原少而高崗多”[1](附跋P1-2),雖不及平原地區條件優越,但“亦以山糧戶為富戶,樹竹多故也”[1](卷下P54)。
竹子加工產業中的重要部分是造紙:筍杪可制毛邊紙,中節可做表心紙,挨根的部分最老則可造粗紙。其中,尤以金溪縣有名,“紙坊各村多以種竹造紙致富”[1](卷下P2)。當然,各處所造竹紙又有不同,“樂邑毛邊紙分上、次兩色;崇仁、宜黃斗方紙有廠紙、薄紙、戶紙三種”。價格亦有差異:“毛邊紙每擔上者貴時值錢七千,賤亦六千,次者貴時值錢六千,賤則五千;草紙每捆值錢二百有余,爆竹紙八九塊可售英洋一元,小竹莊紙五塊可售英洋一元”,且又各有所專,“崇邑工造紙,宜邑供販運”,實際上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如此,收益也是非常明顯的,例如,“宜黃紙:每歲所產十余萬塊,值銀二萬兩;樂邑所產,歲入約四千”[1](卷下P55),竹子加工業對于當地的經濟發展貢獻巨大。
難能可貴的是,何剛德還對西洋加工利用技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雖然晚清中國已經逐漸“開眼看世界”,但是當地鄉民尚不懂得時興的西洋加工技術,未能更好地延伸農產品的經濟價值,何氏對此感到惋惜。比如談到蘿卜,他說“西法并能以蘿卜釀酒,聞本省信豐各縣,蘿卜干統捐歲收萬金,郡產蘿卜甚多,僅供蔬菜之用,有利源而不知,疏淪日恃此涓滴之流以自給,可惜也”[1](卷下P18);又說“泰西人則取腦制造火藥,歲收大利”[1](卷下P60), 但當地多將樟腦作為藥劑使用,加上當時缺乏相關的先進加工技術與設備,導致蘿卜、樟樹等物產得不到很好的開發利用。顯然,何氏期望通過引進西洋加工技術創造盈利的經濟思想在當時是開放的,體現了不同于一般地方官員和士大夫的先進性。
五、結語
《撫郡農產考略》記錄了清末江西撫州地區豐富的農產品及特產的種植、加工技術與販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何剛德的農業經濟思想。此書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撰述完成后,因以何氏為主事的一批官紳如江召棠、黃維翰等的大力推廣,先是在當年便得到撫郡學堂刊印,后又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經蘇省印刷局重印,其中《種田雜說》部分更曾以連載形式刊登在光緒三十年(1904)的《江西官報》上,可見《撫郡農產考略》中農業經濟思想觀點對地方官員興辦農務之重要影響。可惜當時社會還處在新舊、中西思想的碰撞時期,“今天下競言農戰矣,設農會、購農報”[1](序P1),卻少有重視汲取農書舊法合理之處的,故書中提出的很多合理可行的舉措未能達到理想實效。
對于本研究而言,重在通過《撫郡農產考略》探析何剛德農業經濟思想之要義,但未就其來源因素及其與人生經歷的關系展開討論;又書中常提及“鄉人”“泰西人”“西法”等詞匯,不少主張有將東西農業經濟、科技進行比較與向其學習之意,反映了清末部分官紳和文士受外來文化影響的基本事實。這些都有待于做進一步的拓展研究,寄望于今后在此方面有所精進,并吸引更多的專家學者參與討論和探索。
注釋:
①現流傳于世的何剛德《撫郡農產考略》版本主要有:撫郡學堂刊印本、光緒丁未年蘇省印刷局重印本以及收錄在《續修四庫全書》農家類中的版本。本研究和該書引文皆出自光緒丁未年蘇省印刷局重印本,后文不再特別交代。
②撫州位于江西省的東部,境內多丘陵、山地,地勢南高北低。清代的撫州府轄臨川、祟仁、金溪、宜黃、樂安、東鄉六縣;現為撫州市,下轄兩區九縣,本研究所用“撫州”均指清代光緒年間撫郡地區。
③參見:王永厚《發揮地區優勢 繁榮農村經濟——〈撫郡農產考略〉淺析》,載《農業考古》1985年第2期。劉文祥,吳啟琳《地域環境與清末撫州農業經營方式——以〈撫郡農產考略〉為中心的考察》,載《農業考古》2015年第4期。許欣《江召棠的〈種田雜說〉》,載《農業考古》1987年第2期。
④此表改繪自劉文祥,吳啟琳《地域環境與清末撫州農業經營方式——以〈撫郡農產考略〉為中心的考察》,載《農業考古》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