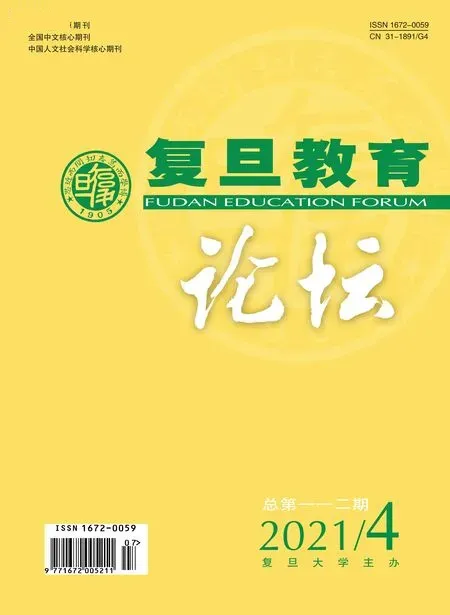中國教育的“新與舊”:紀念嚴復逝世一百周年
陸 一
清末民初,中國教育制度發生了劇烈的轉型,中國現代大學由此開端。作為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的重要創立者和學貫中西的翻譯家,嚴復是一位強立于亂世的志士。梁啟超說他的中學和西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毛澤東稱許他為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尋求救國道路的先驅。
1871年,正值清末洋務運動的風起云涌之時,少年嚴復以最優等的成績從船政學堂畢業。隨后他在海軍的實習中游歷了亞洲諸國,又作為中國第一批海軍留學生,進入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留學。學成回國后,正值戊戌變法的動蕩時期,嚴復雖然力主改革,但并不贊同康、梁的政見。由于深切體會到中西近代社會面貌的巨大差異,他認為中國的根本問題在教育,如果教育和學術事業無法更新,“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將見于乙,泯于丙者將發之于丁”。
嚴復因甲午戰敗而心生苦悶,對政局感到極度失望,他借翻譯《天演論》直抒胸臆,并先后發表五篇雄文——《論事變之亟》《原強》《辟韓》《原強續篇》《救亡決論》,對中國社會、學術與文化的積弊展開了深入、系統的批判和反思。這些作品的橫空出世,給國人的精神世界帶來巨大震撼。此后,學習工科與軍事出身的嚴復將翻譯西學“數部要書”視作“當今第一急務”,立志以此道為國人打開學習西方先進社會思想的大門,以教育和學術來開民智、救中國。
帶著強烈的本土問題意識,嚴復堅持自立自強的立場,憑借中西會通的眼光和古今對照的視角,博觀約取地開展西書翻譯事業。《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名學淺說》《法意》都是他精心選擇、研究、譯介的“要書”。他尤其推崇《群學肄言》,認為此書“實兼《大學》《中庸》精義而出之以翔實,以格致誠正為治平根本”。他在該書序言中提出:“群學何?用科學之律令,察民群之變端,以明既往測方來也。”“今夫士之為學,豈徒以弋利祿、釣聲譽而已,固將于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業有一合焉。群學者,將以明治亂盛衰之由,而于三者之事操起本耳。”可見其新民、新社會、新國家的志向。
嚴復的翻譯工作并不是簡單把兩個文明中相對應的概念語匯對接轉換,而是要在古老的中國文化中創生制作出全新的思想觀念。他要做的并不是外來文化的傾銷,而是在透徹理解西方思想精華的基礎上,把中國精神灌注其中,從而使新思想能夠在中國傳統中生根。這是真正意義上文明的“維新”。他曾直接批評中國學人與士人從閉關時的妄自尊大急轉至開放后的盲目崇洋:“大抵今人以中無所主之故,正如程正叔所謂‘賢如醉漢,扶了一邊倒了一邊’。”他希望《天演論》問世之后,“意欲蜂起者稍為持重”。
在教育實務方面,嚴復曾在上海演講《論教育與國家之關系》。他提出大學不僅要造就專門人才,養成師資人才,而且負有“保存一切高尚之學術,以崇國家之文化”的使命;大學所聘教習應“以本國人才為主”,選“本國學博與歐美游學生各科中卒業高等而又沉浸學問、無所外慕之人”,“優給薪水,俾其一面教授、一面自行研究本科。如此則數年之后,吾國學業可期獨立,有進行發達之機”。嚴復特別強調理工科的科學方法論,對文科則期望“東西方哲學、中外之歷史、輿地、文學理宜兼收并蓄,廣納眾流,以成其大。”
晚年嚴復對中國傳統有了更深的體認,認為“非新無以為進,非舊無以為守,且守且進,此其國之所以駿發而又治安也”。1921年10月27日,嚴復病逝于福州郎官巷寓所,距今整一百年。救亡的時代早已遠去,教育、學術、社會文化的改革更新仍是我們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