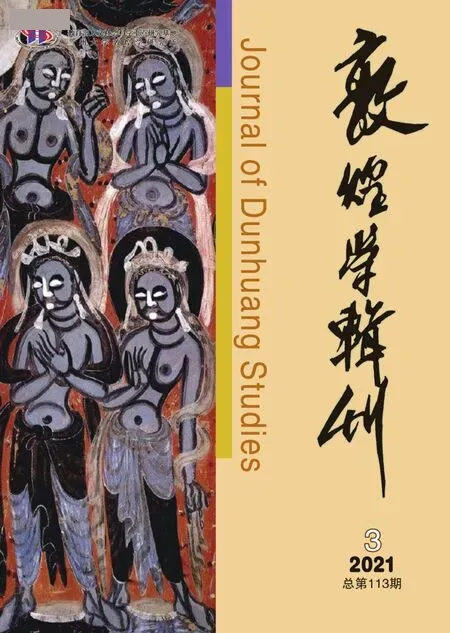北齊徐顯秀墓菩薩聯珠紋探源
沈 雪 鄭炳林
(蘭州大學 敦煌學研究所,甘肅 蘭州 730020)
徐顯秀墓位于山西太原王家峰村,即北齊時晉陽城附近,2002年被評為“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以下簡稱徐墓)。墓的甬道兩側和墓室內四壁等均繪有壁畫,共有300多平方米。此墓一經發掘就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墓中精美的壁畫為絲路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圖像資料。墓中北壁、東壁和西壁中出現的聯珠紋也引起了中外學者的諸多關注,尤其是東壁和西壁出現的聯珠紋,其圖案頗為相似,都是聯珠圈內有一人物頭像:頭戴寶冠,寶繒垂肩,面容安詳靜秀,與中原菩薩形象實無二致,故榮新江將這一圖案稱為“菩薩聯珠紋”(1)榮新江《略談徐顯秀墓壁畫的菩薩聯珠紋》,《文物》2003年第10期,第66-68頁。,本文延用這一名稱。
據徐顯秀墓志,徐為忠義人,其祖安,為懷戎鎮將。墓志稱徐為邊地少年,先入爾朱榮軍中,后追隨高氏,官至太尉。(2)常一民、裴靜蓉、王普軍《太原北齊徐顯秀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0期,第4-40頁。據考證,忠義郡當為蔚洲治下,此地人民多為懷荒等邊鎮舊民,對徐顯秀少時的邊鎮屬民身份當無疑議。(3)羅新、葉煒著《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201-203頁。六鎮之地除了鮮卑武將,還有粟特人,突厥人及其他少數民族,在多民族文化雜處的背景下,雖然徐為漢人,卻有可能熏染了較為濃厚的鮮卑習俗,且多與胡人有所往來。從徐墓壁畫和出土文物來看,有學者認為墓葬整體受祆教文化因素影響,甚至懷疑墓葬中之所以會出現不同年齡和身份的人骨,極有可能是因為施行祆教的葬俗導致。(4)郎保利、渠傳福《試論北齊徐顯秀墓的祆教文化因素》,《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4-122、155-156頁。聯珠紋圖案具有瑣羅亞斯德教即祆教背景,聯珠圈本身即象征光明。菩薩聯珠紋的聯珠圈和菩薩頭像各自關聯到不同的宗教背景,卻同時出現在同一個圖案中,其背后原因和意義值得深究。如徐墓壁畫中的這一菩薩聯珠紋確有極大可能是實際存在的紡織品,那么這一織物是哪里生產的?圖案的來源又是哪里?這背后隱藏的社會經濟文化脈絡值得一探。
一、是否為實際存在的織物
徐墓壁畫中菩薩聯珠紋出現在兩個地方:一為西壁牛車旁侍女的下半身衣服邊緣和袖口邊緣(圖1、圖2),一為東壁馬鞍袱的邊緣(圖3、圖4)。這兩處地方都是以紡織品的形態呈現的,那么有沒有可能這兩個織物圖像都是實際存在的菩薩聯珠紋織物?會否是畫匠的即興創作?本文認為這種菩薩聯珠紋織物應是實際存在的織物。

圖1 東壁備車圖侍女

圖2 侍女袖口處聯珠紋

圖3 西壁鞍馬局部

圖4 馬鞍袱上聯珠紋
從壁畫繪制情況來看,不同于同時代的北齊婁睿墓和灣漳大墓等,徐墓壁畫用筆簡練、快速,猶如行云流水,且人物形象和細節刻畫的非常生動,足見繪制者技法成熟、功力深厚。(5)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齊徐顯秀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7頁。以徐顯秀當時的地位和背景,負責繪制壁畫的人應是頂尖的工匠或畫師,更會根據徐家人的要求盡量將主人生前的尊榮表現出來,凡入畫的內容必要有所依據,所以人物服飾、畫面布局也都非常講究。雖然筆法流暢畫得很快(據發掘簡報,墻角還有沒來得及丟棄的剩余顏料),但畫面內容多是有所參照的,畫家自己創作、自作主張將菩薩面容繪入聯珠圈內的可能極小。

圖5 撒馬爾干大使廳壁畫 (采自《從波斯波利斯到長安西市》 粟特王出行圖局部)
再看馬鞍袱上的聯珠紋,與牛車旁侍女服裝身上的聯珠紋,菩薩面容、圖案構成均極為相似,只是顏色不同。這種聯珠紋織物裝飾馬鞍袱的形制可在中亞的壁畫和浮雕中找到類似的例子(圖5),圖5中壁畫雖然漫漶,仍可見馬背上鞍袱的邊緣飾以聯珠紋,只是其聯珠窠較大,撒馬爾罕壁畫中還有許多類似的聯珠紋“鞍袱”。所以徐墓壁畫中所繪聯珠紋馬鞍袱應為實際存在的織物。
除了菩薩聯珠紋外,北壁墓主人身前的兩位侍女,所著服裝上也有兩種圖案的聯珠紋,一為聯珠對獸對鳥紋,一為聯珠花卉。在我國出土的織物中均可找到類似的圖案(圖6、圖7)。因此,東壁和西壁畫中的菩薩聯珠紋也應是現實中存在的織物。從絲路沿線出土的聯珠紋織物來看,這種織物一般是錦、綺等,都屬于比較奢侈昂貴的,且多為胡人所穿著。那又為什么會出現在三位面容不似胡人的侍女身上呢?這三個侍女的情況有所不同:北壁兩位侍女立于墓主人身前,束發,頭戴四角冠,外著小袖衫,細觀其身上的聯珠紋織物不是作為錦緣,而是整件衣身都是用聯珠紋織物制成的,整體造型頗有胡漢融合的味道;西壁牛車侍女,其發型絕非束發,整體打扮更似西胡。史載北朝雜以戎夷之制,“爰自北齊,有長帽、短靴、合袴、襖子,朱紫玄黃,各任所好。高氏諸帝,常服緋袍”(6)[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45《輿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930頁。。又《北齊書》文宣帝詔曰:“……又奴仆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創出為奇,后以過前為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7)[唐]李百藥撰《北齊書》卷4《文宣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51頁。在這種社會背景下,侍女穿著如此華麗又“富有創意”就說的通了。整個墓室壁畫中只有三位侍女穿著此等昂貴獨特衣料制成的服裝,究其原因,當是因為身份有別于其他婢女(從三個侍女在壁畫中所處的位置來看,應是近身服侍的婢女),且也可以此烘托墓主人生前的榮耀與尊貴,至于為什么是聯珠紋織物,而非其他圖案的織物,應與徐顯秀鮮卑化的漢人身份和當時胡風當道的社會風氣有關。南北朝時隨著絲路貿易的興盛,各種異域風情的織物也已為人們所熟悉。又北齊時,朝野上下受胡風浸染甚深,“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鄴中遂多淫祀,茲風至今不絕后”(8)[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卷7《禮儀志二》,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163頁。。高氏皇帝祀胡天,常服緋袍,上行下效,侍女衣料中出現聯珠紋或身著胡服也只是這種風氣的反映罷了。新疆阿斯塔那206號墓就曾出土過一個頭梳高髻,身著精致間色裙的唐代女舞俑,身上所穿半臂就是聯珠對鳥紋錦制成。

圖6

圖7
從服裝形制上看,牛車旁侍女所穿服裝,下半身的菩薩聯珠紋應是作為鑲拼的衣邊和下擺的錦緣出現的,上半部分的聯珠紋當是袖口的錦緣。有研究者說這件衣服下半身
是間色裙,從已經發現的間色裙的圖像資料來看,這種可能性不大,因為間色裙的下擺通常不會再鑲拼這么寬的錦緣。只是若為胡服類的袍服,何以是右衽呢?史載“披發左衽”才是胡服的面貌(9)[唐]許嵩撰,張忱石點校《建康實錄》卷16,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646頁。。
在《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紡織(上)》中有一件北朝時期的袍服(圖8),同樣也為右衽,下擺的鑲邊也較寬,只是領口和袖口的款式與牛車侍女所著袍子不同(10)趙豐、尚剛、龍博編著《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紡織(上)》,北京:開明出版社,2014年,第219頁。。此處值得指出的是,圖8中領口及肩膀鑲拼其他顏色織錦的細節屬于粟特人服飾特色(11)在片治肯特壁畫,兩個國王舉辦的宴席的中可見。,而大袖和右衽屬于漢族服飾的細節,卻同時出現在這一袍服上,這恰恰是南北朝時期胡漢交融在服裝上的一個反映。另日本Miho博物館藏北朝石棺床J板塊右幅圖像,在下方“地上世界”中(12)姜伯勤著《中國祆教藝術史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79頁。,有一舞蹈女子,所穿袍服與徐墓中聯珠紋侍女所穿十分相似:交領右衽,下擺鑲邊上的圓圈應為聯珠紋,窄袖,且袖子較長,袖口有鑲邊(圖9)。這一石棺床為在華粟特人祆教信仰的一個反映,其中有諸多胡人形象,J板上方的四壁女神經學者比定為娜娜女神。此處有幾個細節值得探究:

圖8 北朝錦袍(采自《中國物質文化史·紡織(上)》圖4-5-2)

圖9 Miho博物館藏北朝石棺床 (采自《中國祆教藝術史》彩圖五)
第一,細看徐墓中胡服侍女袍服下擺,畫匠有淺淺地勾勒一條橫線,將衣緣圖案分成一橫一豎兩個部分描繪,注意比對勾線上下賓花細節即可發現-這與前述舞蹈女子袍服的細節不謀而合,雖然一個是墓室壁畫像,一個是石刻像,表現手法不同,但兩位工匠都將衣服的細節刻畫了出來,這只能說明這種袍服的衣緣就是這樣裁制拼縫的。且Miho石棺床雙闕上也有頭戴三棱風帽,身著交領右衽袍,腰束帶,足登長靿靴的人物形象,與徐墓壁畫中許多人物如出一轍。這諸多相似之處,應是不同領域的工匠對當時服飾形制的描繪與刻畫。因此,這件衣袍應是當時生活中常見的款式,且為胡裝打扮的女子所穿著,畫匠只是將現實生活中的服飾入畫而已。
第二,J板上的女子并沒束腰帶,上半身的交領衣襟也沒有鑲拼錦緣,只有下半身有錦緣,這個細節也與徐墓中一樣。但一般這類的袍服,通常會整個衣衽都裝飾錦緣。二者有別于常規卻一致的細節,正好說明,這類胡服就是真實存在的款式。至于是如何做到只在下半身鑲拼錦緣的,有可能采取了上下分裁的方法,裁剪方式類似于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一件出土于北高加索的卡夫坦(Caftan)。(13)這種袍服在中亞曾經非常流行,波斯人、粟特人都穿著這種服裝。這件卡夫坦專家將之復原后,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上下半身不是連裁的,而是在腰部開縫分裁,并于腰部側襟處縫了紐袢以閉合。(14)Nobuko Kajitani. A Man's Caftan and Leggings from the North Caucasus of the Eighth to Tenth Century: A Conservator's Report. 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 Vol.36,2001,pp.85-124.
第三,徐墓中胡服侍女的發型與J板中女子有相似之處,但J板中女子明顯腦后有發髻,徐墓中侍女則沒有。有學者指出阿旃陀17窟中有女子發型與該侍女發型類似。(15)在《試論北齊徐顯秀墓中祆教文化因素》中作者指出《東方的文明》一書中,圖19、20阿旃陀17窟壁畫中的女子發型,與徐墓中胡服女子發型類似。二者輪廓雖有相似,但17窟女子為卷發,徐墓中侍女則更像辮發盤在頭上。史載南北朝時高昌“女子頭發辮而不垂”(16)[唐]姚思廉撰《梁書》卷54《諸夷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811頁。,說明當時確有辮發不垂的發式。無論如何,總體上來看,徐墓中的這位女子整體是做胡人打扮。
北魏前期孝文帝改制前,拓跋鮮卑仍著鮮卑服飾,小袖袍在北魏早期墓葬和石窟中,十分常見,這種袍服基本上為交領,左右衽和對襟都有,長度及膝,在領口邊緣和下擺都有撞色的鑲邊。(17)孫晨陽主編《中國北方古代少數民族服飾研究·匈奴、鮮卑卷》,上海:東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45頁。可參見嘉峪關酒泉魏晉十六國墓畫像磚中人物(18)張寶璽編《嘉峪關酒泉魏晉十六國墓壁畫》,蘭州: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年,第15頁。和云崗石窟十七窟供養人形象。(19)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譯《云岡石窟》第2期第12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17窟圖版。孝文帝推行全盤漢化的政策后,褒衣博帶的漢服和袴褶這類受胡服影響出現的服裝,在人們的生活中都司空見慣。六鎮起義后,以高歡為首的統治集團多以鮮卑自居,反對孝文帝以來的漢化政策,服飾上又趨于胡化。如徐墓中所常見的,交領右衽的長袍、長靿靴搭配以及改良后的“垂裙皂帽”(三棱風帽)的形象,具是經歷漢化以后的鮮卑服飾。如牛車侍女所著衣袍,當是受西域服飾風格影響的胡服,其淵源可追溯到粟特人和薩珊波斯人所穿的卡夫坦(如前文所述大都會博物館的那件袍服),種類多樣,包括交領和對襟的款式。謝爾蓋.琴科夫曾基于中亞地區的考古材料地對5-8世紀的粟特服飾進行了整理和分類,其中就有交領、小袖的長袍。(20)Yatsenko S A,the Late Sogdian Costume(the 5th-8th cc.AD),Compareti M.Eran Ud Aneran: Studies Presented to Boris Ilch Marsa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http://www.transoxiana.org/Eran/Articles/yatsenko.html,2003.除了上文提到的Miho博物館藏北朝石棺床之外,關于在華粟特人的著裝,在北周史君墓、西安康業墓石槨中也有發現。如北周史君墓石堂南壁浮雕中舉杯的粟特人形象,也穿著交領右衽的袍子,衣衽、下擺和袖口均有鑲邊。(21)楊軍凱著《北周史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337頁圖版一四。
如上所述,徐墓中牛車旁侍女所穿袍服應是當時常見的胡服款式,用來做衣緣、下擺和袖口的菩薩聯珠紋也應是實際存在的織物。如此說來,此處真實地發生了“穿戴”和“使用”,但從當時的崇佛氛圍來看,卻有不敬之嫌。難道說,這就是為什么這種圖案的紡織品只是曇花一現,未在其他地方出現的原因?又或是聯珠圈內并非菩薩頭像?這些疑問應與其產地、輸出對象和圖案母題息息相關。
二、菩薩聯珠紋產地溯源
在目前發現的聯珠紋織物中,聯珠圈內經常出現的圖案有羊、鹿、野豬頭、天馬、含綬鳥、森木夫(senmurv)等動物,多具有宗教或文化含義的,聯珠圈本身也象征者光明。這類圖案早期通常與瑣羅亞斯德教(在中國稱之為祆教)聯系在一起,后來隨著這種紋樣在絲路上的傳播,其宗教含義慢慢淡化,裝飾性增強,并被各個地方的文化賦予新的內容傳承了下來。徐墓中所見的聯珠紋圖案明顯受到了薩珊波斯藝術的影響。然而,徐墓中的菩薩聯珠紋,其人物形象,無論是畫法還是人物面容,都是漢地的菩薩無疑。要誕生這種融合了祆教裝飾圖案、佛教偶像和中原藝術風格的織物,其產地需要同時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第一、生產條件:優秀的織工、生產材料(如絲),結構較為復雜的織機。
第二、社會背景:這類菩薩形象和聯珠紋織物同時廣泛存在于社會環境中,且為人所熟悉。
第三、輸出對象:通俗的講,就是生產出來給誰穿,或者是誰定制了這種織物。
聯珠紋織物從紡織材料上看,主要有絲織物和毛織物,尤其是絲織品,占大宗。菩薩聯珠紋織物若是產于漢地,那么極有可能是錦,且從我國目前出土的聯珠紋織物來看,確實錦比較多。眾所周知,我國的絲紡織業極為發達,著名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就屬于經錦,只是南北朝時戰亂頻仍,是否還有實力生產出如此精美復雜的織物呢?
自漢時起,已設有東西織室作為官營手工作坊,(22)[清]孫星衍,[清]莊逵吉校定《三輔黃圖》卷3,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01頁。產品有“錦繡、冰紈、綺縠”(23)[宋]范曄撰《后漢書》卷10上《皇后紀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22頁。。此時絲織業已非常發達,多集中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和四川地區,尤其是蜀錦,“幾欲奪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變而營織成,遂使錦綾專為蜀有”。(24)朱啟鈐著《絲繡筆記》,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8年,第5頁。后五胡入主中原之時,都非常重視對勞動人口的掌控,搜刮工匠歸政府管制,如拓跋珪攻占中山,即將“百工伎巧十余萬口”,遷至京師。且多承舊制,如石趙的中尚方、御府和織成署的織錦工巧,就有數百。(25)韓國磐著《北朝經濟試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7-168頁。鄴中織錦署織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斑文錦、鳳凰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不可盡名也”,除此之外還有“雞頭文罽、鹿子罽、花罽”。石虎“又嘗以女伎一千人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紋織成靴”。(26)[晉]陸翙撰《鄴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8頁。
由此可見當時絲織品不但種類豐富,產量也頗為可觀,且罽屬于毛織物,源自西域,說明胡人工匠當時亦不在少數。《藝文類聚》載:“梁皇太子謝勑賚魏國所獻錦等啟曰,山羊之毳,東燕之席,尚傳登高之文,北鄴之錦,猶見胡綾織大秦之草,戎布紡玄莵之花……又謝東宮賚辟邪子錦白褊等啟曰,江波可濯,豈藉成都之水,登高為艷,取映鳳皇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聲高趙縠。”(27)[唐]歐陽詢撰《藝文類聚》卷85《布帛部》,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458頁。北朝所產織錦,質量亦不在蜀錦之下,且各個品種的絲織物都繼續生產,絲路貿易發達,來自大秦的胡綾和印度的戎布還是隨著胡人商隊如約而至。
至北齊時,又設有涇州絲局、雍州絲局、定州紬綾局。(28)[唐]魏徵、令狐德撰《隋書》卷27《百官志》,第843頁。官營作坊如此發達,必然具備生產材料、技藝高超的工匠和相應的織機。民間也有許多貴族,家有小型作坊,私藏工匠,屢禁不止,如畢義云“家有十余機織錦”,并因此而獲罪(29)[唐]李百藥撰《北齊書》卷47《畢義云傳》,第658頁。。又祖珽嘗“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百余匹”與人賭樂(30)[唐]李百藥撰《北齊書》卷39《祖珽傳》,第514頁。,可見當時北朝確有出產西方風格的絲織物。(31)中亞的聯珠紋織物是緯錦,織機及織造技術與我國不同,一般計量單位用“張”,而產自我國早期的錦為經錦,計量單位用“匹”,后來因為絲路貿易的往來,我國才習得了緯錦的織造技術。從此處行文來看,用“匹”作為計量單位,應是產自山東無疑。青海、新疆等地都曾出土聯珠孔雀紋的織錦(圖10)。

圖10 聯珠孔雀紋錦(作者攝于青海藏文化博物館)
那么南朝是否也具備同樣的生產條件呢?自東晉以來,大批北人南遷,其中不乏諸多工匠,遂也將絲織技術帶到了南邊。南朝政府大力勸課農桑,“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又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32)[梁]沈約撰《宋書》卷54《孔季恭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540頁。益州此時仍是絲織品的主要產地。隋時,何稠曾為隋文帝制波斯錦,“錦成,逾所獻者”。其叔父何妥史載為細腳胡,入蜀后為南梁武陵王蕭紀主管金帛之事而致巨富(33)[唐]李延壽撰《北史》卷82《何妥傳》、卷90《何稠傳》,第2753、2985頁。。何氏作為細腳胡,據考即為粟特商胡,曾為蕭梁王室制作西方風格的絲綢和金銀器。(34)林梅村《何稠家族與粟特工藝的東傳》,收入榮新江、羅豐《栗特人在中國——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上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231頁。
從上述史料和考古材料來看,當時的北齊和南朝,都具備生產這類織錦的條件,但是菩薩形象是如何走入聯珠圈內,成為紡織品圖案的呢?為了探尋這一聯珠紋織物產生的來歷,有必要追究佛、祆在當時社會生活中的具體情況。
佛教和祆教都屬于外來宗教,或許在佛教進入中國初期,由于信眾對于佛教尚不甚了解,所以在瓦當或是其他器物裝飾中出現了佛教神祇的人物化形象,但隨著佛教中國化進程的深入,這種現象逐漸消失了。南北朝時,由于戰亂頻繁,統治者依賴佛教鞏固其政權故大力推崇,百姓希望從中找到精神寄托故信仰供奉。然而細究起來,南朝和北朝在佛教信仰方面的表現還是有區別的。北朝重在“力行”,南朝重在義理。北魏臣工自諸王以下,以致閹黨、羽林、虎賁等,多舍宅立寺。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饒益。故造像立寺,窮土木之力,為北朝佛法之特征。(35)湯用彤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41頁。《洛陽伽藍記》載:
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有佛殿一所,像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至于六齋,常設女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后汝南王悅復修之。悅是文獻之弟。召諸音樂,逞伎寺內。(36)[北魏]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5頁。
如上所見,舍宅立寺當為力行供奉的“虔誠之舉”,但實際對佛教的信仰頗為表面化,逞伎寺內實為不敬。北齊諸帝亦崇信佛法,卻也胡化甚深。《北齊書·神武紀下》記載:
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陜,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護軍祖瑩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37)[唐]李百藥撰《北齊書》卷2《神武帝紀下》,第12頁。
在這四十萬戶中也包括了西來附化之民萬有余家,其中不少應是西胡。(38)[北魏]楊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卷3,第161頁。何以見得呢?北齊諸帝多有喜握槊、胡樂者,且后來多有胡人近臣如穆提婆、高阿那肱受封高位,胡風之盛,胡人之多可見一斑。
相對北朝而言,南朝帝王即位,年歲稍長知學者,靡不講理佛學,并重學理。帝王之信佛者,多于佛寺設齋,又嘗于宮殿設四部無遮大會,或無礙法善會。會中帝或親行講經說法,大赦天下,并且為之改元。更有梁武帝、陳武帝舍身入寺。(39)湯用彤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302-303頁。究其根本,皆因南朝諸帝均以漢文化為出發點而接納佛教,與北齊高氏以鮮卑自居,看待佛教頗為不同。
徐墓中的兩處菩薩聯珠紋圖案,其菩薩形象頗為一致:頭戴三葉寶冠,寶繒束扎后垂下,面龐圓潤靜秀。這一風格的菩薩造像,在北齊境內十分常見(圖11、圖12、圖13)。(40)李曄《山西北朝菩薩造像研究》,南京藝術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6世紀天竺佛像一再東傳,高齊重視中亞胡伎藝和天竺僧眾,對北魏漢化政策的抵制,使得此時的北齊造像不再是“褒衣博帶、秀骨清相”,而是具有笈多時代秣菟羅藝術風格。(41)宿白《青州龍興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幾個問題——青州城與龍興寺之三》,《文物》1999年第10期,第44-59頁。但又不同于犍陀羅式的高鼻深目,此時的菩薩面容更為本土化,五官更為柔和圓潤。李裕群在論及成都出土的南朝佛教造像時曾指出,北齊鄴城地區和太原地區的佛教造像都受到了南朝的影響。(42)李裕群《試論成都地區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文物》2000年第2期,第64-76頁。從成都出土的菩薩造像來看,也可找到如徐墓中聯珠紋內的菩薩形象(圖16)。南北朝造像,此時都受到了笈多風格的影響,大量的僧侶或經西域沿陸路來到中國,或從海陸來到中國,隨之而來的一定也有擅長造型的域外工匠。這里考察其時絲路沿線發現的造像,或可發現一些與本文提到的圖案構成有關的線索。(圖14、圖15、圖16)

圖11

圖12

圖13

圖14

圖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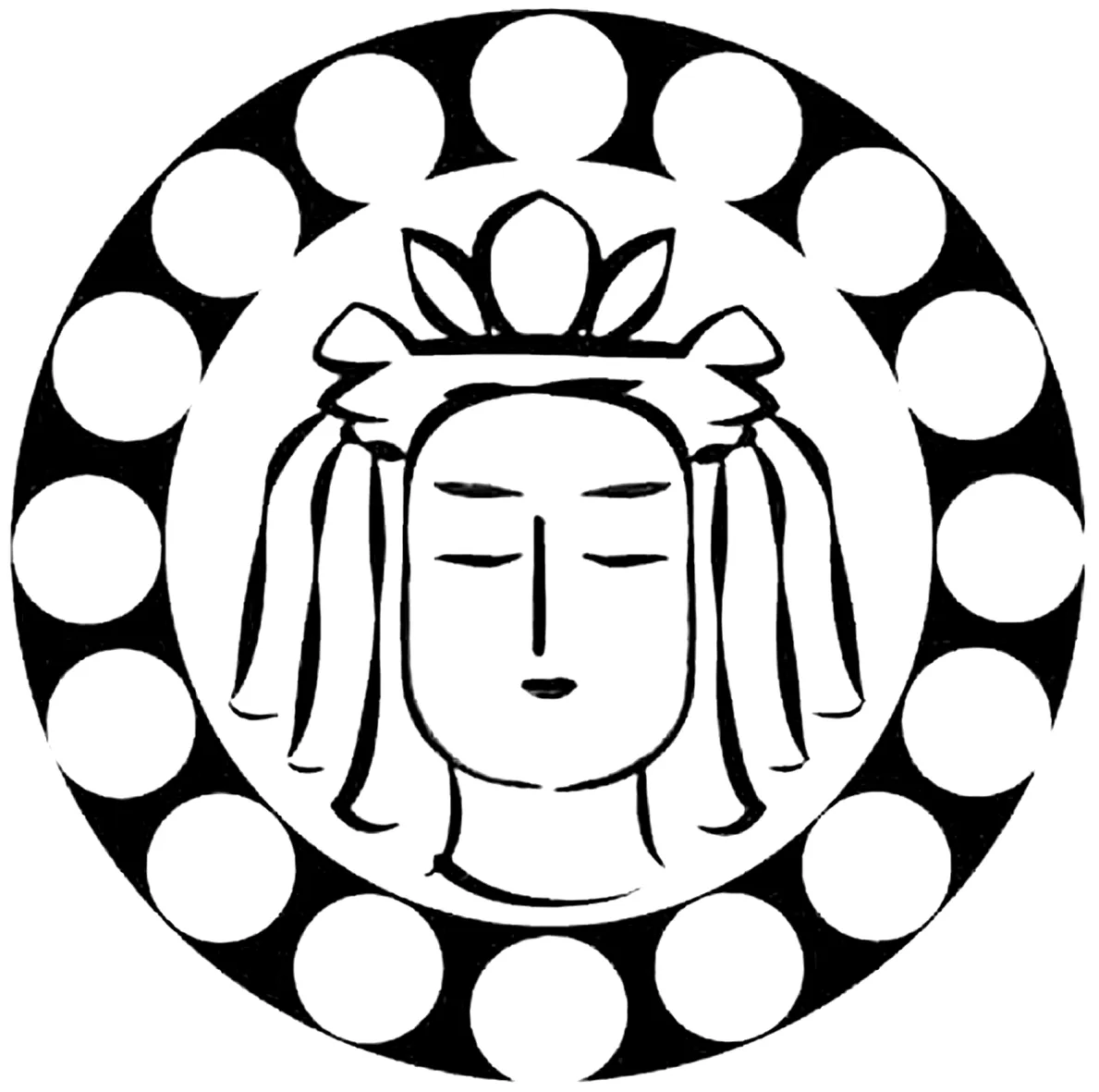
圖16
圖14來自印度中部地區,是笈多時代(5世紀晚期)。在印度,這種神龕是極為常見的寺廟裝飾形態,龕內的圓形部分俗稱月亮屋或牛眼睛,聯珠圈內,柔和的人物面龐是笈多時代的常見造像特征之一。(43)Bromberg A,the Arts of Indi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Himalayas at the Dallas Museum of Art, Dallas:Dallas Museum of Art,2013,p.55.這種神祇頭像與“月亮屋”的組合,在5-6世紀北方邦還可找到類似的構件,但神龕整體發生了一些變化。(44)在故宮博物院等編《梵天東土·并蒂蓮華:公元400-700年印度與中國雕塑藝術2》中圖95、103、106均為月亮屋型神龕,龕內是印度教的濕婆或戰神。笈多時代,統治者采取寬容的宗教態度,雕刻這些印度教寺廟的工匠同樣也負責雕刻佛教寺廟,所以這種壁龕形式并不一定是印度教獨有,也會應用到佛教寺廟的裝飾中。圖15是斯坦因在新疆焉耆明屋遺址發現的陶磚,6-7世紀,現藏于大英博物館內,菩薩頭戴三面寶冠,呈現出犍陀羅造像風格。這三張圖片中的人物面容并不相似,但是其聯珠圈+人物(神祇)的構成形式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彷佛在揭示著某種聯系。
本文認為菩薩聯珠紋織物產生的方式可能有兩種:第一,隨著絲路上西域、南北朝僧侶及商人往來于中西,這種圖案構成形式也隨之沿著絲路來到了中土,紡織工匠參考其他藝術形式,創作了菩薩聯珠紋。歷史上也不乏不同領域的工匠相互借鑒圖案的例子,比如紡織品中的勾連雷文在青銅器上出現,又比如固原北魏漆棺畫中的交波紋也有類似結構的圖案出現在織錦上;(45)趙豐、齊東方主編《錦上胡風:絲綢之路紡織品上的西方影響:4-8世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4頁圖21。第二,中亞地區已有類似構圖的聯珠紋織物傳入中國,紡織工匠將其本土化了。美國大都會館藏有一件王者半身像聯珠紋織物(圖17),這塊7-8世紀的中亞織物有兩層聯珠圈,聯珠圈內的人物形象與薩珊波斯王者的形象相近。菩薩在佛教中是釋迦摩尼的前世,是世俗中的王者。在佛教造像中,菩薩頭戴寶冠的形象,即與此有關。在敦煌莫高窟早期的菩薩造像中,其頭冠就受到了薩珊波斯王冠裝飾元素的影響。(46)趙聲良《敦煌石窟北朝菩薩的頭冠》,《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第8-17頁。如果將“菩薩”作為王者的另一種形象,代入聯珠圈內也合乎情理。

圖17 中亞出土半身像聯珠紋錦采自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品號 2008.79
那么,徐墓中的菩薩聯珠紋究竟是誕生于著裝“以創出為奇”的北朝,還是宮人會“服用射獵錦文”的南朝?(47)[梁]蕭子顯撰《南齊書》卷19《五行志》,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419頁。
如果菩薩聯珠紋出現在南朝,那么益州地區是最有可能的地方。這里同時具備了出色的生產條件、可參考的佛教造像以及往來于中西弘法的僧侶和經商的胡人,但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因為諸多僧侶布道宣教,大力推動了益州地區的佛學教義的發展,(48)曹中俊、李永平《益州佛教文化交流與絲綢之路河南道的關系:以僧侶、義理、造像為考察中心》,《地域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第28-41頁。加之南朝統治者不同于北朝的對佛教獨一無二的虔信態度,菩薩聯珠紋不可能誕生于益州。最根本的原因是,徐墓整體具有很濃厚的祆教信仰的暗示和裝飾趣味,在這一語境下,“菩薩頭像”出現在“胡服侍女”的服裝上,即“以佛入祆”,用佛教中的菩薩形象構成富有祆教意味的織物圖案來裝飾卡夫坦類的胡服。這里對比莫高窟420窟及402窟中出現在菩薩天衣上的聯珠紋,即可發現,莫高窟的兩處洞窟整體為佛教的語境,天衣上的聯珠紋是“以祆入佛”,成為佛教神祇服裝的裝飾圖案。兩相對比之下,徐墓中的菩薩聯珠紋如果出現在益州,則有悖于益州佛教的實際情況,即便此地有胡人會穿著聯珠紋織物,但紡織工匠既缺乏動機,也實無必要將菩薩頭像織入聯珠紋內。
結語
綜合以上論述,徐墓中的菩薩聯珠紋應當出產于北齊境內,其原因總結如下:
1.符合北齊“以創出為奇”的攀比、競奢的社會氛圍。
2.北齊當權者兼祀胡天,佛、祆并重,地位不相上下,如此上行下效,對佛教的信仰是為了滿足現實生活中的需要,并不深究義理,貴族甚至“逞伎寺內”,缺乏敬畏之心。
3.如徐顯秀這樣的貴族,即為這類織物的輸出對象:胡漢雜糅的成長背景,深染胡風的信仰,想要通過奇珍異寶彰顯尊榮的需要。
4.佛教造像遍布,頭戴三葉寶冠,寶繒垂肩,面容秀潤的菩薩形象已為人所熟悉。
5.隨西來僧侶一起傳布到中原的“聯珠圈+神祇”的圖案形式。
6.有生產能力織造媲美蜀地的錦,且已有按匹計數的“聯珠孔雀羅”,聯珠紋織物都已經開始了本土化生產。
菩薩聯珠紋織物的出現,從圖案上來看,是粟特美術形式伴隨著兩種不同宗教在絲路上的傳播,融入當時的北朝社會,并與中原藝術相結合。反過來,也體現了當時的人們是如何看待祆教與佛教,如何看待與之相關的服飾風格。從織物生產的角度,則反映了當時的紡織品生產還是比較發達的,不但沒有因為戰亂而減弱倒退,反而由于上層階級追求奢靡享受等原因,進一步發展,已經能夠吸收外來的織物風格并進行模仿和創新。從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來看,菩薩聯珠紋之所以曇花一現,也許就是因為人們對佛教的理解逐漸加深以及佛教地位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