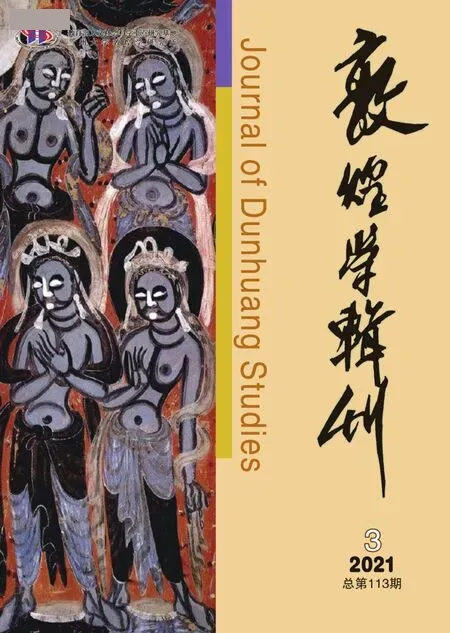數珠與菩提:佛教數珠的使用
李 翎
(四川大學 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5)
前 言
“佛珠”之稱,將珠串理所當然的歸屬為佛家之物。四川地區自宋代以來盛行一種菩薩造像,因其手持念珠,學界通稱“數珠手”。這種數珠手造像,又往往被認為是大菩薩觀音,故此樣式造像也稱“數珠手觀音”(1)李小強、廖順勇對四川現存數珠手造像進行了統計,確定有13例數珠觀音,3尊存有銘文,其中有銘文明確提到造“數珠手觀音”。參見李小強、廖順勇《大足、安岳石刻數珠手觀音造像考察》,《四川文物》2018年第1期,第45-54頁。。原始數珠,往往來自植物果實。佛教以及其他宗教中,都有許多意義非凡的植物。佛教經典中,我們常常可以讀到“吉祥果”“吉祥樹”(或樹王)之類的表述(2)如密教鬼子母形像手持吉祥果,這個吉祥果事實上是石榴。《阿育吠陀藥典》中的Bilva,《梵-和辭典》中也解釋其為吉祥果,事實上是印度人喜歡食用的木蘋果。,但這顯然是宗教性表達,從這樣的表述中,我們不能得知吉祥果是什么果、吉祥樹(樹王)是什么樹。正如菩提伽耶那棵現在大家公認的菩提樹,事實上并不結菩提子。

在印度歷史上,從植物宗教學的角度,一些大師坐于什么樹下禪定并獲得某個階位的證悟,那個樹即可稱為菩提樹,也就是說菩提樹只是泛稱。菩提,巴利語bodhi,《吠陀》語為bodhin,指(人的意識之第7識)末那識專注一處。佛教中指“無上智慧”(6)T. W. Rhys Davids and William Stede edited, Pali-English Dictionary,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1997, p.545.,中文最初譯之為“道”,或為“道之極者”(7)[南宋]法云撰《翻譯名義集》,《大正藏》,第54冊,第1060頁。。菩提樹只是宗教學意義上的一個名詞,沒有植物學樹種含義。《修行本起經》在談到佛得道的那棵樹時,稱其為“樹王”:“(喬達摩)于是復前行,望見……中有一樹,高雅奇特,枝枝相次,葉葉相加,花色蓊欝,如天莊飾,天幡在樹頂,是則為元吉,眾樹林中王,于是小前行……”(8)[東漢]竺大力、康孟詳合譯《修行本起經》卷下,《大正藏》,第3冊,第470頁。。“樹王”是什么樹?我們不得而知。又釋寶云譯《佛本行贊》提到那是一棵“好樹”:“(喬達摩)歷泉上過,行詣道樹。遙見好樹……”這棵好樹,也是高大的樹,但這仍然是文學性描述。筆者的問題是,制作數珠最有功德的材料,稱為菩提子,似乎與佛成道的菩提樹有關。但我們現在稱之為菩提樹的樹種,即菩提伽耶的那種大樹,事實上是榕樹且并不結子,制作數珠的菩提子來自別的樹。
一、相關的學術研究
觀音研究成果非常多,但具體到數珠或數珠手觀音,可以說幾乎沒有前人成果可資借鑒,有一些研究不夠深入的旁涉成果,在此可以舉出的論文有四川學者李小強、廖順勇《大足、安岳石刻數珠手觀音造像考察》(9)李小強、廖順勇《大足、安岳石刻數珠手觀音造像考察》,第45-54頁。,這是目前唯一一篇專文,是對相關造像進行的材料梳理。按李、廖之文的統計,現在四川大足和安岳共存13尊數珠手造像,其中3尊有銘文,一尊的銘文明確提到造“數珠手觀音”。從而我們可以判斷,那個時期這類造像,民間或已認定其為觀音菩薩。同時,文中也提到齊慶嬡的《江南式白衣觀音造像分析》(10)齊慶嬡《江南式白衣觀音造型分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14第4期,第52-69頁。。該文略有涉及數珠觀音,但內容不多。另外,施萍亭的《斯2926〈佛說校量數珠功德經〉寫卷研究》(11)施萍亭《斯2926〈佛說校量數珠功德經〉寫卷研究》,《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第31-41頁。也須提及。施氏此文雖然在日本寫本方面用了更多心思,但有價值的是文章注釋中提到教內有關數珠的八部文獻,這大大減少了筆者的重復勞動。施氏提到了最早的《佛說木槵子經》,但作者從數珠只與密教有關的觀點出發,沒有將之列入數珠的總體文獻中。
關注數珠的外國學者與中國一樣少。中國學者關注的少,是認為佛珠理所當然為佛教傳統之物。外國學者尤其是印度學者關注的少,則認為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而多余理論。所以,問題恰恰出在這里,一個大家忽略的小問題,暗藏著佛教史的發展軌跡。
2010年印度學者普拉旦耶·庫瑪爾尼(Pradnya Kulmarni)發表了《作為法物的印度教數珠》(12)Pradnya Kulmarni, Application of Hindu Rosary as A Magical Device, Bulletin of the Deccan College Research Institute, Vol.70/71, 2010, pp.419-428.,在這篇文章中普拉旦耶非常系統地介紹了數珠自公元前6世紀起,印度教禮拜儀式中使用數珠的歷史。文中詳細談到數珠使用的方法、意義、材質、珠子的數量等,是中國學者了解前佛教時期,數珠在印度文化中廣泛使用的極好材料。據普拉旦耶的觀點,使用數珠的目的是統計念誦神號次數。一般認為禮拜濕婆要念此神的1008個名號,重復多少次需要統計才有效。最早的計數器是繩結或植物種子,逐漸演變成珠子。對于統計念誦次數的數珠,普拉旦耶提到至少在《往世書》時代(公元前6世紀-筆者注)就有記載了。開始是統計稱誦神名的次數、繼而統計念誦密教咒語的次數。重復念誦與計數被印度教認為非常重要,次數越多、福報越大。這就是印度修行傳統中的“迦巴”(Japa)方式,即反復稱誦圣號,以至于將之作為護身符與身體的某些部位相應。反之,念誦時沒有計數,則無功無果。從統計念誦神的名號,發展到統計念誦咒語的次數,數珠的功用開始擴展到更多禮拜儀式中。在密教儀式中,咒語(密語)與密形(Yantra)結合才產生作用。所以在儀式當中,重要的咒語被反復念誦。由此,數珠在密教(此處不是指佛教之密教,而是印度教之密教,尤其是濕婆密教)中受到越來越高的重視,一些密教文獻也開始非常詳細的記載什么樣數珠的材質和多少棵珠子才最有效。從印度教角度來說,珠子的個數最常見的有兩種:一濕婆派,通用108顆或108的約數,如54、26、13顆等;二毗濕奴派,通常是72顆或72的約數,如36、18、9、3顆等。在脖子上或手腕上佩戴數珠,表明一個人是有信仰的。珠子的質地,一般使用兩種:一種是用圣羅勒(Ocimum sanctum)子作珠,這種子非常小。所以,常見的是用死人牙齒或骨頭做珠子。第二種非常重要,也是本文討論的重點,那就是一種喬本植物的種子,印度人稱為“濕婆之眼”。在這里普拉旦耶沒有解釋“濕婆之眼”的來歷,因為它是印度人人皆知的傳說和名稱,但對中國學者來說,理解這一點十分重要(后面將提到這個故事)。
印度傳統中,最早的珠串主要由漿果核、蓮籽、珊瑚、檀木等制成(更早的是繩結)。當念誦咒語時,以右手撥珠計數。我們再回到普提旦耶的文章上,普提旦耶似乎混淆了杜英樹與榕科的菩提樹。筆者在印度讀過的一個材料,顯示佛教的所謂菩提樹(大榕樹),即佛陀在其下獲得正覺的那種樹是印度傳統的吉祥樹,這類樹崇拜原本屬于土著大神濕婆(13)P.Ramachandrasekhar, Hnduism for All, New Delhi: Giri Trading Agency Private Limited, 2010, p.82.。而結果為菩提子的樹,叫“濕婆之眼”樹(或茹德拉之眼Rudraaksha),二者不同(14)Devdutt Pattanaik, Shiva-An Introduction, Mumbai: Vakils, Ferrer and Simons Pvt. Ltd, 1997, pp.101-102.。普拉旦耶也非常簡略的提到佛教、耆那教和晚近錫克教在數珠上的使用通例。他認為這些宗教都屬于(大)印度教分支,暗示在數珠的使用上只是延用傳統而已。佛教和耆那教用108顆、錫克教用27顆當手環。普拉旦耶文章一個顯而易見的觀點就是:數珠源自婆羅門教傳統。
美國學者柯嘉豪(John Kieschnick)所著《佛教對中國物質文化的影響》第二章《象征》中有“念珠”一節。在經典方面,除了施氏所列,柯氏還提到天息災譯《大方廣菩薩文殊師利根本》,這個材料非常具體提到珠子的使用與相關的儀軌。總之,作者的意思顯然是:數珠與密教有關(15)[美]柯嘉豪著,趙悠等譯,祝平一等校《佛教對中國物質文化的影響》,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第114-126頁。。另外,柯嘉豪在書中,對于數珠源于婆羅門教還是佛教并沒有給出準確的答案。他只是在書中提到:“寺院戒律和《阿含經》中都沒有念珠的記載,這說明念珠應該是在佛教叢林制度建立幾百年后才進入僧人的修行生活……一份早期婆羅門藝術品中出現了念珠……念珠是否從婆羅門教傳入佛教……支撐這一觀點的證據少之又少,且十分含糊”(16)[美]柯嘉豪著,趙悠等譯,祝平一等校《佛教對中國物質文化的影響》,第116頁。。同時,在他書中的一個注釋里,柯嘉豪指出日本學者望月信亨是唯一一個支持“念珠起源于婆羅門教”觀點的人(17)[美]柯嘉豪著,趙悠等譯,祝平一等校《佛教對中國物質文化的影響》,第116頁注釋3。。
除印度學者普提旦耶專論印度教的數珠傳統外,以上學者之論基本可以歸納為如下兩個結論:1.數珠是佛教傳統之物、數珠手觀音來自民間;2.中國佛教數珠的使用,屬于密教范疇。
二、漢譯佛教文獻中收錄的相關材料與分析:什么材料的數珠貴?
有關數珠的漢譯文獻,歸納前述共有9個:1.失譯東晉本《佛說木槵子經》(18)[東晉]失譯《佛說木槵子經》,《大正藏》,第17冊,第726頁。;2.阿地瞿多譯《陀羅尼集經》卷二之《阿彌陀佛大思維經說序分第一:佛說作數珠法相品》(19)[唐]阿地瞿多譯《陀羅尼集經》卷2之《阿彌陀佛大思維經說序分第一:佛說作數珠法相品》,《大正藏》,第18冊,第803頁。;3.寶思惟譯《佛說校量數珠功德經》(20)[唐]寶思惟譯《佛說校量數珠功德經》,《大正藏》,第17冊,第727頁。;4.義凈譯《曼珠師利咒藏中校量數珠功德經》(義凈與寶思惟本同,略有用詞上的繁簡差異)(21)[唐]義凈譯《曼殊室利咒藏中校量數珠功德經》,《大正藏》,第17冊,第726頁。;5.輸波迦羅譯《蘇悉地羯羅經》(22)[唐]輸波迦羅(善無畏)譯《蘇悉地羯羅經》,《大正藏》,第18冊,第603頁。;6.善無畏譯《蘇悉地羯羅供養法》(23)[唐]善無畏譯《蘇悉地羯羅供養法》,《大正藏》,第18冊,第692頁。;7.不空譯《金剛頂瑜伽念珠經》(24)[唐]不空譯《金剛頂瑜伽念珠經》,《大正藏》,第17冊,第727頁。;8.般若、牟尼室利合譯《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25)[唐]般若、牟尼室利合譯《守護國界主陀羅尼經》,《大正藏》,第19冊,第525頁。;9.般若譯《諸佛境界攝真實經》卷下《持念品第八》(26)[唐]般若譯《諸佛境界攝真實經》卷下《持念品第八》,《大正藏》,第18冊,第281頁。。除《佛說木槵子經》外,其他8部屬于密教文獻,正應前文普拉旦耶所說“因密教重視咒語的重復性,從而更多密教文獻詳細的討論數珠之材質和個數”。也正為此,筆者認為《佛說木槵子經》成為非常重要的早期文本,它暗示了佛教數珠與印度傳統之間的關系。下面以兩部典型的經典:失譯東晉本《佛說木槵子經》和寶思惟譯《佛說校量數珠功德經》為例,分析數珠材料的變化。
(一)失譯東晉本(317-420)《佛說木槵子經》
漢譯本存錄東晉失譯《佛說木槵子經》,這個經講述了一個因緣:國王波流離,因忙于國政無暇修持,從而擔心自己將來的命運,于是問佛該如何做?佛告波流離王,平時只要念誦佛、法、僧三寶之名即獲功德。功德多大,以念誦次數的多寡區分。可以木槵子108棵串珠,以之計數(27)參見[東晉]失譯《佛說木槵子經》,收錄于《大正藏》,第17冊,第726頁。。通過這部短小的佛經,我們得知三點:一制作數珠的材質為木槵子;二數珠用于統計念誦三寶名號次數的多少;三數珠為無暇修持的在家居士所用。
經文強調隨身攜帶108顆木槵子串,不停的念誦“佛陀達摩僧伽名”(即佛、法、僧三寶)分別滿20萬遍、滿一百萬遍等等,即可替代日常修行而得安樂或無上果位。而這樣簡便的稱名念佛,在中國凈土信仰傳入后才盛行。凈土經言:只要稱誦阿彌陀佛名號,人死之后,就可往生西方凈土(28)[日]永觀集《往生拾因》,《大正藏》,第84冊,第97頁。。言外之意,一個平日里無暇修行的人,只要臨死時自念或他人助念佛名,功德果報同樣。據說此法極為靈驗,各類《應驗記》常常記某人念佛號多少萬遍而獲往生(29)往生應驗故事集,歷史上很多,可參見《往生西方凈土瑞應傳》,《大正藏》,第51冊,第104頁。另外,可參見清代彭希涑撰《凈土圣賢錄》。該錄以中國古來著述,兼以耳目所及編輯成錄,收于《卍續藏》,第135冊。,但材料中似乎并未提及稱名念佛時以數珠計數。7世紀凈土大師道綽(562-645),勸人念阿彌陀佛名號時,仍然告訴信眾以麻豆計數(30)[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卷20,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762頁。。雖然,文中也提到法師曾經自己串木槵子來記數,并告知四眾此法,但似乎麻豆更為方便和流行(31)[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卷20,第762頁。。所以,雖然4世紀左右數珠的使用已經傳入中國,但到7世紀,一般的僧、眾仍然無珠可用。
(二)寶思惟(?-721)譯《佛說校量數珠功德經》
8世紀后譯出的一系列數珠密教文獻中,木槵子的功用被大大減弱了。《佛說校量數珠功德經》以文殊菩薩為利益諸有情之因緣,宣說數珠不同材質之功德大小:
若用鐵為數珠者,誦掐一遍得福五倍;
若用赤銅為數珠者,誦掐一遍得福十倍;
若用真珠、珊瑚等為數珠者,誦掐一遍得福百倍;
若用木槵子為數珠者,誦掐一遍得福千倍,若求往生諸佛凈土及天宮者,應受此珠;
若用蓮子為數珠者,誦掐一遍得福萬倍;
若用因陀啰佉叉(一種藍色的寶石?-筆者)為數珠者,誦掐一遍得福百萬倍;
用烏嚧陀啰佉叉(金剛子/菩提子-筆者)為數珠者,誦掐一遍得福千萬倍;
若用水精為數珠者,誦掐一遍得福萬萬倍。(34)[唐]寶思惟譯《佛說校量數珠功德經》,《大正藏》,第17冊,第727頁。
這些量化的對比,非常清楚的表述了哪種珠子更貴、更有效力。顯然《佛說校量數珠功德經》對菩提子與木槵子區分的十分清楚:“若用槵子為數珠者,誦掐一遍得福千倍……若用菩提子為數珠者,或時掐念或但手持,誦數一遍其福無量不可算計難可校量”(35)[唐]寶思惟譯《佛說校量數珠功德經》,《大正藏》,第17冊,第727頁。。可以看出,在密教時期,木槵子的福報已經大大減少。但值得注意的是經文特別提到,想要往生彌陀凈土或彌勒兜率天宮的信徒,要用木槵子珠。這是非常特別的,至少從文獻的角度可以說,直到8世紀密教時期,木槵子在中國依然保持做為凈土信仰的專用珠子。
為什么這個時候菩提子的福報突然如此之大呢?《佛說校量數珠功德經》講述了一個故事,以說明其法力超強的因緣:有一外道不信三寶,經常謗佛。因為他的兒子死于非命(被非人所殺),這個外道就想:“是不是因為我太過信邪教(不信佛法)?不知道諸佛法力如何,不防試試。既然如來是在樹下成道,如果佛真的獲得正覺,那么樹就會有感應”。于是這個外道把他兒子的尸體放到菩提樹下,說道:“佛樹如果真神圣,我兒子一定能死而復活”。于是,他坐在樹下連續七日稱念佛名。如此,七天之后他的兒子果然復活了。驚喜的外道皈依了佛門,稱此樹為“延命樹”。此后,佛成道的樹有了兩個名字:一曰菩提樹,二曰延命樹(36)[唐]寶思惟譯《佛說校量數珠功德經》原文云:“過去有佛出現于世,在此樹下成等正覺。時,一外道信邪倒見毀謗三寶,彼有一男,忽被非人打殺。外道念言:‘我今邪盛,未審諸佛有何神力。如來既是在此樹下成等正覺,若佛是圣,樹應有感。’即將亡子臥著菩提樹下,作如是言:‘佛樹若圣,我子必蘇。’以經七日誦念佛名,其子乃得重蘇。外道贊言:‘諸佛神力,我未曾見。佛成道樹現此希奇,甚大威德,難可思議。’諸外道等,悉舍邪歸正,發菩提心,信知佛力,不可思議。諸人咸號為延命樹。以此因緣有其二名,應當知之。”《大正藏》,第17冊,第727頁。。雖然經中將佛成道的菩提樹與結出菩薩子的樹混為一談,但是說明了菩提子的重要性似乎由此而來。
佛經中這棵可以起死回生、象征無上覺悟的是什么樹?其實沒有明確的答案,不同的經典有不同的菩提樹種類。《修行本起經》提到喬達摩苦行時,坐于娑羅樹下(37)見[東漢]竺大力、康孟詳合譯《修行本起經》,《大正藏》,第3冊,第469頁。。娑羅樹,學名Shorea Robusta,屬龍腦香科,高大的喬木。產于印度、孟加拉等熱帶地方。相傳,此樹乃過去七佛之第三佛:毗舍浮佛(Vessabhu)之道場樹(38)[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1,《大正藏》,第1冊,第2頁。經中記七佛成道之樹分別是:“毗婆尸佛坐波波羅樹下成最正覺,尸棄佛坐分陀利樹下成最正覺,毗舍婆佛坐娑羅樹下成最正覺,拘樓孫佛坐尸利沙樹下成最正覺,拘那含佛坐烏暫婆羅門樹下成最正覺,迦葉佛坐尼拘律樹下成最正覺。我今如來、至真,坐缽多樹下成最正覺。”。此外,拘尸那揭羅(Kusinagara)城外之娑羅樹林,是佛陀涅槃之樹(39)[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長阿含經》卷4,《大正藏》,第1冊,第24頁。。因娑羅樹高大、堅固,不易枯萎,所以佛典中常以此樹喻堅固。馬鳴的《佛所行贊》提到喬達摩是在閻浮樹下苦行、在吉祥樹(又稱菩提樹)下成道(40)馬鳴撰、[北涼]曇無讖(法護)譯《佛所行贊》,《大正藏》,第4冊,第8頁。。閻浮樹,學名為Eugenia Jambolana,屬桃金娘科的落葉喬木。分布于印度、錫蘭及馬來半島、中國海南、廣東、福建等地。隋代阇那崛多《佛本行集經》提到佛苦行于尼拘陀樹下。尼拘陀樹,按丁福保解釋就是榕樹。《佛說造像量度經》中說佛伸開手臂,其寬度與身高相等,即尼拘陀樹形(41)[清]工布查布譯解《佛說造像量度經解》,《大正藏》,第21冊,第936頁。。唐代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卷15記:“尼拘陀,此樹端直無節,圓滿可愛……唐國無此樹,言是柳樹者訛也。”(42)[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大正藏》,第54冊,第402頁。慧琳是西域人,后到京師,長期生活在北方,沒有見過南方非常常見的榕樹,故言“唐國無此樹”。但以上這些樹與菩提子皆無關系。
為什么早期的數珠以木槵子為之,其巨大功德以至于即使是手持便可替代日常的修行精進,完全不提別的材料。可是過了300年左右,它的功能大大減少,成為只用于往生凈土的法器?對于引發數珠材料更替的理由,可以給出的合理解釋就是:木槵子可能為佛教原創的器物,而菩提子,則與6世紀席卷印度以及東南業的古老濕婆密教有關(43)這個問題涉及到密教本質問題,需要另外的研究討論,在此不多涉及。。
四、宗教植物學與醫學
進入宗教系統的植物,通常是一些有特別藥理作用的植物。如前所述,木槵子在印度被認為可以袪鬼;娑羅樹,用以治療消化不良、淋疾等病癥;閻浮樹的果實具有止咳平喘的效用(44)在《阿育吠陀藥典》娑羅雙樹被認為可以治療燒傷、麻風病、皮膚病和梅毒等。參見孫銘、賈敏如等《〈印度阿育吠陀藥典〉所載169味單藥味藥的介紹》,《中國藥房》2019年第15期,第2075-2091頁。。
菩提子,不是榕科“菩提樹”(我們今天在菩提伽耶看到那棵菩提樹)所結的種子,這一點非常明確。上文提到的所有吉祥樹或菩提樹,幾乎都不結這類堅硬的珠子。大家熟知的菩提子,來自杜英屬喬木,學名為圓果杜英。它的葉子尖而瘦長,不似菩提樹的桃心形。其果實硬骨質,表面有溝紋。圓果杜英生長于海拔1100至1800米的森林中,在印度主要分布于喜馬拉雅山下段,這是一個重要的地理概念,這組巨大的雪山群,傳說是濕婆(Shiva)的居所。濕婆又稱雪山之主,他的妻子帕爾瓦蒂(Parvati)為雪山女神,這是理解菩提子(濕婆之眼)為濕婆派標志的重要背景。
印度傳統稱菩提子為Rudraaksha,即“濕婆之眼”(或茹德拉之眼,Rudra,為土著大神濕婆吠陀化的名子)。傳說濕婆看著持續數年的大暴雨導致的滅頂洪災,不禁為眾生悲傷落淚。從第三只眼中掉下的一滴淚落到黎明前的土地上,這滴淚水變成一棵漿果樹,就是Elaeocarpus Ganitrus,即圓果杜英,它的果核就是“濕婆之眼”。濕婆宣稱這個果核將會為人類帶來幸福、健康、護佑以及精神自由。因為這個種子是濕婆眼淚化成,屬于濕婆身體的一部分,人們佩戴它就能得到濕婆神給予的加持。這個神圣的“濕婆之眼”,正是所謂的金剛菩提子(45)P.Ramachandrasekhar, Hnduism for All, pp.81-83.。印度古典醫學著作《阿育吠陀》(āyurveda)記載:菩提子是重要的藥材,它可以治療身體因三大元素(土、火、風)失調而引發的疾病,尤其是顯現于皮膚上的病,如天花(或梅毒)和雞痘(46)P.Ramachandrasekhar, Hnduism for All, pp.81-83.。因為菩提子是濕婆的另一個形態,所以人們在喉嚨的位置佩戴哪怕只一顆菩提子,就可以抵御所有邪靈引發的病痛。由此,要求佩戴菩提子必須緊貼人的皮膚。印度教傳統學派的大師多佩掛菩提串,尤其是濕婆派信眾,身上披掛往往不只一串。印度冬季舉行的大型沐浴節,是在最冷的黎明前舉行,整個沐浴過程要佩戴菩提子。古代銘文顯示,佩戴“濕婆之眼”的人幾乎等同于濕婆(Rudra),同時濕婆也只接受佩戴神圣種子之人的禮拜。這句話是這樣寫的:Bina bhasma tripunden bina Rudraksha malaya Poojitoapi Mahadevo na syat tasya phalapradah.直譯過來就是“如果你沒有用圣灰在額頭上涂有三叉戟的圣記,或者脖了上沒有佩戴茹德拉之眼,向大天禮拜就沒有任何結果”。《濕婆往世書》記載:即使一個人沒有任何美德,只要他愛濕婆之眼,就不會深陷罪惡且得到解脫。愛濕婆之眼的人肯定不是壞人。在印度不分種姓、文化與性別,都喜愛佩戴濕婆之眼。但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要求是:他必須是一個信仰濕婆大神的潔凈之人(47)以上內容參見B.K.Chaturvedi, Gods and Goddesses of India 4: Shiva, Delhi: D. K. Publishers Distributors(P)Ltd.1996, pp.57-59.。
五、持數珠神圖像
中國唐代之前的造像,按柯嘉豪所列,最早的數珠圖像出現在南北朝,為麥積山第23窟一尊北朝菩薩。但經筆者辨認,23窟菩薩手持為當時流行的“桃形器”并非數珠。事實上,數珠圖像始于五代,宋以后流行,最初出現在觀音手上。以幾部主要數珠功德經的譯出時間比對(除《佛說木槵子經》),圖像出現的時間與之正相吻合。但圖像中持念珠者多為觀音而非經典所記的文殊或金剛手,那么問題就來了,民間為什么認為數珠手是觀音呢?
印度數珠的歷史雖然從文獻上可以追朔到《往世書》時代,但圖像實物僅始見于公元5世紀,它們同時出現在佛教與濕婆教造像中。
5世紀的實物圖像至少可以發現3例,最重要的是阿旃陀石窟第16窟,一處壁畫表現了坐著的圣人手持環形數珠,周圍是一些世俗人物。其中一個坐姿男子,身著華麗,雙手合十表情虔誠。筆者大膽推測,這或是一幅5世紀繪制的《木槵子經變相》。畫中華服者可能正是問佛如何修法的波流離王(48)之前對壁畫的解釋是:它表現了《堅伽國王》的故事。畫中堅伽國王正虔誠的聆聽苦行婆羅門那拉達(Nārada)開示,因此持數珠者是婆羅門那拉達。參見Dieter Schlingloff, Ajanta Handbook of the Painting, Vol.I.2011,Delhi: Indir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 and Aryan Books International, p.219.。5世紀印度教例子:有奧里薩邦博物館藏的八臂濕婆像,其中一只右手持數珠。當然,類似的例子應該還有一些,但總體不多。數珠的流行要到密教盛行的8世紀,印度遺存中的密教濕婆像,表現為怒相、多臂、舞立,其中必有一手持數珠。
結語
綜上,佛教不是最先使用數珠的團體。佛教使用數珠的習慣,應該受到婆羅門教傳統的影響,尤其與婆羅門教反復稱誦圣號的“迦巴”習俗有關。雖然數珠更多的使用于密教修行和儀式當中,但與密教無關、漢譯最早的《佛說木槵子經》所述“以木槵子108棵結串”顯然還是受到濕婆派108數字的影響。如果我們放下既有的認識,重新審視印度東部和北部,即克什米爾與奧里薩遺存中大量8世紀所謂的密教觀音造像,考慮到那里此時盛行的濕婆信仰,就會質疑這些手持“濕婆之眼”的觀音像是否是被誤讀的濕婆,進而思考大足、安岳地區突然出現的數珠手觀音像的來源與文化現象。
對數珠使用的觀察,可以透視出不同文化,甚至相互排斥文化間的合作與轉化現象。從而顯現出誕生于印度文化大背景中的佛教,吸取傳統信仰、婆羅門教思想以及修持方式之一斑,這是佛教學者不能回避的問題。同時,宗教學與植物學的密切關系也值得關注。當早期抽象神被人格化后,某些有宗教意義的植物也會歸屬到一些特定的神身上,并逐漸產生更多的神話和宗教解釋。在這個歸屬過程中,會發生植物借用與轉移現象。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進一步考慮,人們通過什么程序選取植物、在宗教儀式中如何使用這些植物的。本文所關注的數珠,只是諸多神圣植物進入宗教或者說進入佛教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