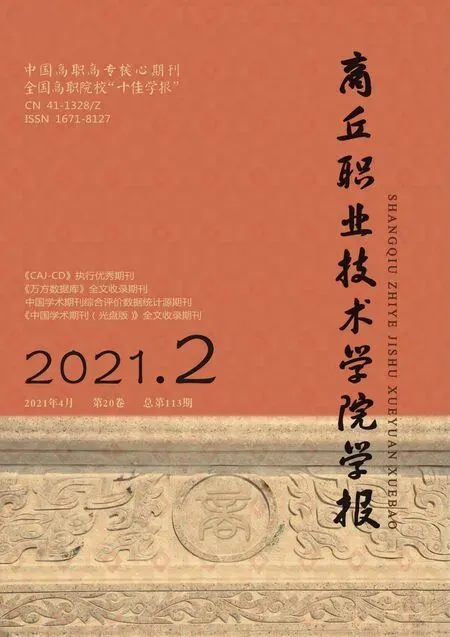“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現象探析
周鵬波
(聊城大學 文學院,山東 聊城 252000)
春秋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大動亂時期。王室衰微與諸侯圖霸,打破了國家以往的權力構架,激化了統治階層的內部矛盾,進而引發了社會的劇烈變革。伴隨著權力結構的調整和社會生活的變遷,周朝的禮樂制度也遭到了嚴重破壞,“盟禮”便是其中之一。《周禮注疏》載:“若《司儀》所云‘為壇十有二尋,王與諸侯殺牲歃血而盟’,則供珠槃玉敦。”[1]158由此可知,“盟”在周朝本是司儀主持下定期舉行的“官方活動”,王與諸侯共同參與。《禮記正義》亦稱:“唯天子巡守至方岳之下,會畢,然后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2]141-142可見,“盟”在起初并不具有貶義色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了統治階層的內部分歧。“盟”逐漸沾染上貶義色彩,是從諸侯勢力過大,進而忽視周王存在,肆意結盟開始的。春秋時期私盟盛行,加之《春秋》具有微言大義的特征,因而后世在解釋《春秋》時產生了“凡書盟者,惡之也”[3]15的觀點。從此種意義上來講,春秋時期的“盟”正在擺脫原有的禮制束縛,數量急速增加,性質由“公”轉“私”,并成為一種常見的社會現象。“葵丘之盟”正處于這種變化的關鍵節點,雖然宰周公作為王室代表參與了此次會盟,帶有一絲“公”的意味,但齊桓公才是“葵丘之盟”的實際主持者,并代為行使了周王的權力,儼然成為此次會盟的盟主。
《周禮注疏》云:“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1]889又《春秋左傳正義》云:“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4]41由此可知,殺牲歃血是盟誓禮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盟誓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天子諸侯在“盟”的過程中常采用殺牲歃血的方式誓告神明,以求化解諸侯間的嫌隙,締結互利共信的盟約。而殺牲歃血作為盟誓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其本質是借人對神明和血液的崇拜,從精神層面約束同盟者,進而為盟誓增添神圣感和儀式感。“陳牲而不殺”則是發生在“葵丘之盟”時的一種特殊現象,指諸侯在盟誓的過程中僅束縛“犧牲”而不以口飲血,可視為殺牲歃血儀式的一種簡化。
一、“陳牲而不殺”與“陳牲而不歃血”
公元前651年,齊桓公在葵丘會盟諸侯,史稱“葵丘會盟”。《春秋·僖公九年》載:“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5]123-125由此可知,“葵丘會盟”是由夏天的“葵丘之會”和九月的“葵丘之盟”構成。《禮記正義》稱“相見於郤地曰會,”[2]141“蒞牲曰盟 ”[2]141則“會”與“盟”在性質上有所差異。《春秋》中將發生于九月戊辰的事件稱為“盟”,因而本文依《春秋》經文之說,將其寫作“葵丘之盟”,以與該年夏天發生的“葵丘之會”相區分。稍有遺憾的是,《春秋》的敘述十分簡潔,尚未提及“陳牲而不殺”現象。直到《春秋穀梁傳》在闡釋《春秋》時才明確提出“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這也是現存最早記載“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現象的典籍: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5]124-125
《春秋穀梁傳》在描述“葵丘之盟”的細節時,寫到“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楊士勛疏:“雖盟而不歃血,謂之不殺。”[5]125他認為,此處所講“陳牲而不殺”,就是“陳牲而不歃血”。徐邈則云:“陳牲者,不殺埋之,陳云諸侯而已。”[5]125他認為,“不殺”是指并未殺死“犧牲”,即在盟誓過程中使用的是活牲。《禮記正義》:“盟之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2]142可見,“割牲左耳”應在“殺牲于坎上”之后。若盟誓使用的是活牲,割牲耳以取血的可能性也就很小。因此,楊、徐二人觀點的區別或僅在于盟誓儀式使用的是活牲還是死牲。
《孟子·告子下》將“陳牲而不殺”記為“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歸于好。”[6]334-335
一般觀點認為,《孟子》成書晚于《春秋穀梁傳》。如楊德春先生在《葵丘之會天子禁令考》中指出:“孟子所載葵丘之會天子禁令是在《春秋穀梁傳》關于葵丘之會天子禁令之記載的基礎上所進行的添枝加葉的發揮。”[7]既然《孟子》對《春秋穀梁傳》中的天子禁令有所借鑒,那么,《孟子》也必定學習過《春秋穀梁傳》關于葵丘之會的記載。將二書相比較,《春秋穀梁傳》和《孟子》鑒于“葵丘之會”與“葵丘之盟”在同一年且同一地舉行,都將其寫作“葵丘之會”,但實際皆指發生于九月的“葵丘之盟”。《春秋穀梁傳》的闡釋圍繞“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展開,有較為明確的時間標識。《孟子》所載“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歸于好”同樣出現在《春秋左氏傳》中,而《春秋左氏傳》所闡述的是“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4]358,則《孟子》與《春秋左氏傳》記載的應為同一事件,即發生于九月戊辰的“葵丘之盟”。除此之外,《孟子》將《春秋穀梁傳》中的“陳牲而不殺”記為“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孟子》的記載顯然更為詳細,似是楊士勛和徐邈觀點的結合。“束牲”即捆綁“犧牲”,若用死牲就不須捆綁,可見,《孟子》也認為盟誓中使用的是活牲。不歃血的記載與楊、徐二人的觀點亦相同。
結合《孟子》和徐邈的闡述,“不殺”應指盟誓儀式使用的是活牲。依據盟的流程,“不殺”就不可能歃血,那么“陳牲而不殺”便可以理解為“陳牲而不歃血”。進一步來看,不論盟誓過程中使用的是活牲還是死牲,“陳牲”本身已經實現了其作為盟誓用品的作用,也符合盟誓用牲的禮儀。此處不歃血則顯得更為特殊,這種記載與傳統“歃血而盟”的觀念相異,而且也未遵循“盟禮”的流程。從這方面來說,探討“陳牲而不殺”現象的關鍵在于分析不歃血,而不在于分析陳牲。
二、“陳牲而不殺”與“春秋盟誓不歃血”
周朝以禮樂治天下,禮儀被賦予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實際功用,以致成為維護國家穩定和王室統治的重要保證。即便進入“禮樂崩壞”的春秋時期,禮儀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特別是重要的禮儀環節,并不會被完全打破或廢除。盟誓過程中的“陳牲”“歃血”更多承載的是文化內涵和象征意義,因而被廣泛沿用于會盟過程中,后人盟誓時也很少簡化或廢除這兩個環節。依《左傳》記載,春秋時期的會盟多達200余次,但將“春秋三傳”所記載的“不歃血”事件進行匯總,也不過3處,可細分為13次,可見殺牲歃血在春秋時期盟誓過程中依然占據主流,不歃血的現象仍然十分特殊。相較于春秋盟誓不歃血,“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也展現出了其自身的特殊性。
關于春秋盟誓不歃血的記載如下:
(一)胥命于蒲
《春秋·桓公三年》載:“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5]37杜預《春秋左傳正義》載:“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4]157認為齊國和衛國在蒲地僅約定了言辭,并沒有舉行歃血的儀式,所以,《春秋》才將其稱為“胥命”。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胥,相也。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3]77同樣強調了此次事件不歃血,僅以命相誓,用以解釋胥命的含義。但何休的解釋略乏嚴謹,他將此次事件稱為“時盟”,此處的“胥命”和“盟”應為兩個概念,缺少“歃血”環節的“盟”才可稱為“胥命”,“盟”與“胥命”在此處絕不能同時出現。何休的闡釋顯然是想強調“以命相誓”,而忽視了歃血之于盟的重要性,將此事件定義為“不歃血之盟”。
(二)衣裳之會
《春秋穀梁傳·莊公二十七年》載:“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5]93-94衣裳之會是指諸侯間友好性的聚會,是不借會盟實現個人稱霸目的的聚會。楊士勛《春秋穀梁傳注疏》:“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寧毋,九年會葵丘。”[5]93-94依此所言,“九年會葵丘”即是衣裳之會中的1次,并且11次衣裳之會都不曾歃血。
(三)尋宋之盟
《春秋·昭公元年》載:“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5]277杜預《春秋左傳正義》稱:“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4]1142-1143盟誓歃血的先后一般是由會盟者的地位決定的,先歃血者往往是主盟者,其后按會盟者地位的尊卑依次歃血。春秋時期由于盟誓禮儀遭到破壞且會盟國家的實力差距過大,因而也會出現爭歃的現象。楚國害怕晉國先歃血,讓晉國的地位凌駕于楚國之上,因而采取了“尋盟”的方法,即“從舊書,不歃血”。
將以上“不歃血”事件相比較,可以看出,后世典籍因歃血問題而產生出較大的分歧。《春秋左傳正義》和《春秋公羊傳注疏》的觀點基本相同,他們認為,盟誓過程中不歃血,則《春秋》經文中不書盟。這也是“齊、衛胥命于蒲”稱為“胥命”而不寫作“盟”的原因,也是“楚、晉尋宋之盟”在《春秋》中寫作“會”的原因。詳細地來看,《春秋穀梁傳》所記載的“衣裳之會”與“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應屬于同一類型的事件,二者盟誓過程中都主動選擇不歃血。《孟子》所說的“初命”“再命”“三命”“四命”“五命”和 “胥命”中的“命”與《春秋穀梁傳》中的盟辭,都是指約定言辭。而“尋宋之盟”不歃血的起源在楚晉爭歃,爭歃又是一種備受指責的行為。前兩則材料中的不歃血與“尋宋之盟”中的爭相歃血顯然處于后人褒貶的兩極。
《春秋》經文載:“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5]124又《春秋左傳正義》和《春秋公羊傳注疏》皆認為,盟誓過程不歃血,則《春秋》經文中不書盟。那么依《春秋左傳正義》和《春秋公羊傳注疏》的觀點,發生于九月戊辰的“葵丘之盟”,必然進行了歃血的儀式。然而,《春秋穀梁傳》卻認為,“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歃血”,這便形成了顯著的矛盾,也展現出了“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的特殊性。
三、“陳牲而不殺”現象形成的原因
作為春秋前期最為盛大的會盟活動,“葵丘之盟”本可依照“盟禮”,在會盟儀式上殺牲歃血。然而《春秋穀梁傳》和《孟子》卻皆認為“葵丘之盟”不曾歃血,這背后具有十分復雜的原因。
一種觀點認為,齊桓公作為主盟者具有“信厚”的品質,不需要再以歃血的儀式來昭著信義。楊士勛《春秋穀梁傳注疏》載:“莊二十七年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則衣裳之會皆不歃血。而此會獨言之者,以此會桓德極盛,故詳其事,實余盟亦不歃血耳。”[5]125依此之意,“葵丘之盟”不歃血的原因在于齊桓公“信厚”。歃血是為了昭著信義,當誠信敦厚的齊桓公作為會盟的主持者時,信義也必然會在同盟國中彰顯,也就不必考慮再用歃血儀式來約束同盟者。同時,“葵丘之盟”展現了齊桓公高尚的德行,因而,《春秋穀梁傳》才會詳細敘述“葵丘之盟”“不歃血”的細節。
另一種觀點認為,諸侯畏懼齊桓公,不敢違背與齊桓公定下的盟約,因而可以省略歃血的環節。趙岐《孟子注疏》載:“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6]335杜預又曰:“諸侯皆束縛其牲,但加載書,而不復歃血。歃血,ヱ血也,言不敢負桓公之約也。”[6]336此觀點認為,齊桓公的政治霸業在“葵丘之盟”時達到全盛,諸侯畏懼齊桓公的勢力,因而也就畏懼齊桓公所制定的盟約,不需要再舉行歃血的儀式。
以上兩種觀點皆以齊桓公個人為中心,前者認為齊桓公“信厚”是不歃血形成的原因,后者認為諸侯畏懼齊桓公的政治霸業,所以不必歃血。綜合來看,這兩種分析是較為合理的。細察春秋盟誓時的“不歃血”現象,“胥命于蒲”與“衣裳之會”皆是可以歃血,但會盟者主動選擇不歃血的行為,以此強調會盟者的主體選擇性并以主盟者為中心。而“尋宋之盟”則是處于特殊狀況下,是為化解爭歃分歧而進行的被動選擇,這時則更應考慮會盟的背景和諸侯國之間的關系。同時,若將11次“衣裳之會”分開來看,春秋時期的不歃血現象共計13次,齊國主盟了其中的12次。“胥命于蒲”的主盟者是齊僖公,“衣裳之會”的主持者是齊桓公,齊僖公與齊桓公又是父子關系,從家族傳承來說,齊桓公“葵丘之盟”不歃血也應受到其父齊僖公的影響。
從所處歷史時期來看,“葵丘之盟”發生于公元前651年,尚處于春秋的前期。這時的“盟”并未完全擺脫禮制束縛,盟的性質也正在由“公”轉“私”。《論語·憲問》載:“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8]154宋朱熹注:“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8]154可見,齊桓公的圖霸策略便是“尊王攘夷”。歃血作為“盟”的重要標志,只有歃血才可以稱之為完整意義上的“盟”。倘若齊桓公在會盟中使用了歃血儀式,那么齊桓公就徹底違背了“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2]141的禮儀。如此看來,齊桓公在“葵丘之盟”時簡化了歃血儀式,恰恰是守禮的一種表現。據此可知,禮制的束縛和齊桓公“尊王攘夷”的策略也影響了“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現象的形成。
四、后世對“陳牲而不殺”的評價
“陳牲而不殺”現象產生于“葵丘之盟”,后世對“葵丘之盟”的認識也直接影響了人們對“陳牲而不殺”現象的評價。歷史上對“葵丘之盟”和齊桓公在“葵丘之盟”時的表現有截然不同的態度。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陳牲而不殺”是處于《春秋穀梁傳》話語體系中的現象,因而在評價“陳牲而不殺”時應該以《春秋穀梁傳》為中心,以《春秋左氏傳》和《春秋公羊傳》為參照。
《春秋穀梁傳》對“葵丘之盟”是持有肯定態度的,“陳牲而不殺”是其肯定“葵丘之盟”的重要依據。如“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5]124-125。其認為,《春秋》中將“葵丘之盟”所發生的日期詳細記為戊辰這一天,就是為了贊美齊桓公的行為。齊桓公在“葵丘之盟”時代替周襄王盟誓了“天子之禁”,并因周襄王未參與此次會盟,便簡化了歃血儀式,充分展現了齊桓公的尊王守禮。事實上,“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和“明天子之禁”都是具有褒義色彩的。另外,《春秋穀梁傳》在分析“陳牲而不殺”的原因時,認為“‘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5]125,同樣肯定了齊桓公的誠信厚德。總之,《春秋穀梁傳》在整體上肯定了“葵丘之盟”和齊桓公在“葵丘之盟”時的表現, 同時,對“陳牲而不殺”現象的評價也是較為積極的。
《春秋左氏傳》和《春秋公羊傳》對“葵丘之盟”與齊桓公多持否定的態度,評價也較為消極。如《春秋左氏傳》: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于行。”晉侯乃還。[4]358
“葵丘之盟”后,宰周公回國路遇晉侯,談及“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在宰周公眼中,“葵丘之盟”與伐山戎、伐楚的性質是相同的,是齊桓公不務德行、四方攻略的一種表現。宰周公作為王室代表參與此次會盟,因此,宰周公對“葵丘之盟”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王室對“葵丘之盟”的態度。
又如《春秋公羊傳》: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3]223
《春秋公羊傳》認為,“葵丘之盟”“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即齊桓公在“葵丘之盟”時過于驕傲自滿,以致9個國家在“葵丘之盟”后便違背了天子之命。其將“葵丘之盟”與“貫澤之會”相比較,認為齊桓公在“葵丘之盟”時已經喪失了“憂中國之心”,因而也就逐漸喪失了盟主的地位,評價也是消極的。
依據“春秋三傳”的評價,《春秋左氏傳》和《春秋公羊傳》并沒有涉及“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現象,這也絕非偶然。“陳牲而不殺”實際是齊桓公遵守禮制、擁護王室的一種表現,這恰好與《春秋左氏傳》和《春秋公羊傳》所要陳述的觀點相反。如果說《春秋左氏傳》和《春秋公羊傳》展示了“葵丘之盟”較為消極的一面,那么《春秋穀梁傳》中“陳牲而不殺”現象則表現了“葵丘之盟”恪守禮制的一面。因此,“陳牲而不殺”現象是“春秋三傳”書寫差異的具體表現,也是全面把握“葵丘之盟”的重要依據。
五、結語
作為春秋前期最為盛大的會盟活動,“葵丘之盟”正處于由“公盟”轉向“私盟”的關鍵節點。“陳牲而不殺”可以理解為“陳牲而不歃血”,可將其看作殺牲歃血形式的一種簡化,這種現象的形成不僅與齊桓公誠信敦厚、勢力強盛有關,而且也與禮制束縛、父子承襲、圖霸策略有關。將其與春秋“不歃血”現象相比較,《春秋左傳正義》和《春秋公羊傳注疏》皆認為盟誓過程中不歃血,則《春秋》經文中不書盟。而《春秋穀梁傳》則認為11次“衣裳之會”均未歃血,后世典籍在圍繞《春秋》經文的闡釋時產生了巨大差異。但結合不同典籍對“葵丘之盟”的評價,這些差異顯然是由于不同典籍對“葵丘之盟”的不同態度所造成的。《春秋穀梁傳》記載“陳牲而不殺”,就是為了肯定齊桓公的“信厚”以及“葵丘之盟”的積極作用。《春秋左氏傳》和《春秋公羊傳》對“葵丘之盟”持有否定態度,因而不會記載具有肯定意義的“陳牲而不殺”。總之,“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現象是我們全面把握“葵丘之盟”的重要依據,也是學界絕不可忽視的一個會盟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