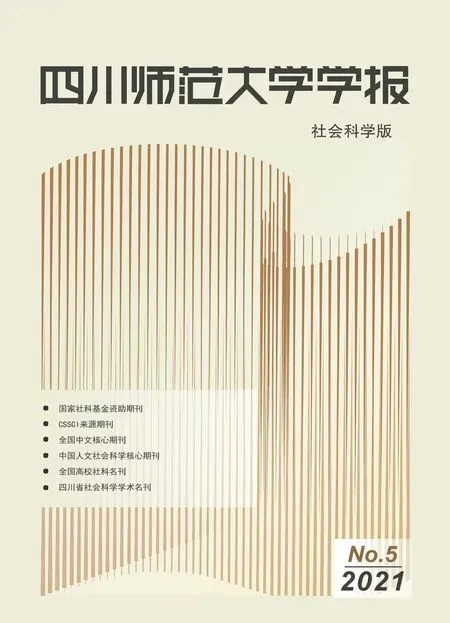“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
——以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為中心的考察
靳 寶
白壽彝先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著名史家,在中國民族史、中國通史、中國史學史等領域做出了突出貢獻,推動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設和發展。白先生獨立完成、自成體系的《中國史學史》第一冊,是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探索的一次總結,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認識的一次升華,是中國史學史發展方向的一次指引。以往學界關于《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的研究很豐富,但一般側重于分析白先生在本書中所闡發的具體問題,總結和評價他在中國史學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和貢獻,而對該書在白先生史學史研究探索歷程中的關鍵性意義挖掘不夠,尤其是對于書中所彰顯的“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念缺乏細致剖析和專門論述(1)相關成果有:瞿林東《白壽彝與20世紀中國史學》,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吳懷祺《中國史學發展辯證法的探索——讀〈中國史學史〉(第一冊)》,《史學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41-47頁;陳其泰《刻意的追求,新辟的境界——白壽彝著〈中國史學史〉第一冊評介》,《史學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48-54頁;施丁《成一家之言——評白壽彝著〈中國史學史〉第一冊》,《歷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125-133頁;周文玖《白壽彝史學史思想的發展歷程》,《回族研究》2000年第3期,第30-35頁;曲柄睿《溫故知新與繼承發展——寫在白壽彝先生〈中國史學史〉(第一冊)出版三十周年之際》,《史學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66-74頁;張越《白壽彝先生與新中國建立初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學史研究》2020年第2期,第47-58頁;任虎《繼往開來: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唯物史觀轉向》,《史學史研究》2020年第3期,第45-52頁;汪高鑫《白壽彝先生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的學術歷程》,《史學史研究》2020年第4期,第38-50頁;等等。這些研究成果對本文主題均有涉及,為本文撰寫作了很好的學術積累,給予了重要啟示。。故本文以《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為例,分析、闡釋白壽彝先生在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方面的學術追求、理論建樹和實踐創新。
一 學術上的追求
對于自己從事中國史學史研究,白壽彝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中總結道:“這四十多年,對于中國史學史的摸索,首先是暗中摸索,繼而是在晨光稀微下,于曲折小徑上徘徊,繼而好象是看見了應該走上的大道。現在的問題是,還要看得更清楚些,要趕緊走上大道。”(2)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2-183頁。所謂“大道”,就是他提出的“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3)白壽彝《關于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幾個問題——1983年4月6日在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的講話》〔原載于史念海主編《史學集林》第1輯(《人文雜志叢刊》第4期),1985年5月,第9-23頁〕,收入白壽彝《白壽彝史學論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321頁。這一史學建設與發展的大道。白先生的這一形象概括,隱含了他走上這一大道的艱辛歷程,即從思想萌發到意識明確,再到尋得一點途徑,最后大踏步前進這樣四個階段。
雖然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前,白壽彝先生已經接觸到馬克思主義(4)參見:張越《白壽彝先生與新中國建立初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學史研究》2020年第2期,第48-49頁。,但這種“接觸”還沒有體現在史學史教學與研究上。白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中總結說:“在解放前的這幾年,我所講授的這門課程,基本上只能說是按年代順序講解的史學要籍解題。當然,在沒有接觸馬克思主義以前,這種解題也是很膚淺,很難發掘出本質性的問題。”(5)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174頁。
白先生真正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并把它用來指導自己的史學史研究工作,是在20世紀50年代初(6)任虎《繼往開來: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唯物史觀轉向》(載《史學史研究》2020年第3期,第45-52頁)一文從白壽彝先生開設的中國史學史課程分析了這一轉向。。1951年,他在《光明日報》上發文稱:“我以為,我們應該先好好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在具備了一定的理論基礎上進行中國歷史的研究,在新的研究成果中來豐富理論的內容。”(7)白壽彝《學習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經驗,學習理論和實踐的聯系,改造我們的教學》,《光明日報》1951年6月30日,第5版“歷史教學”增刊。同年,白先生在他所列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中國史學史課程提綱中,開始注意到史學與時代的關系,注重史學思想的分析,特別關注史學思想的社會基礎以及史學思想在政治、學術文化上產生的影響。這份提綱,不僅呈現出一種“通識”觀念,而且有突破以往史學史“提要”式著述的初步意識。值得注意的是,這份提綱還專列有兩講,講述“毛澤東和歷史科學在中國的建立”,突出毛澤東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建立中的地位和影響。這說明“白先生是有意識地將中國史學史納入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話語體系進行史學史教學和研究的,新中國成立后白先生從事的史學史教學工作成為他的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新起點”(8)張越《白壽彝先生與新中國建立初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學史研究》2020年第2期,第56頁。。這份提綱也可看作白先生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思想萌發。
1957年,白先生參與侯外廬先生所主持的《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研究工作,并負責劉知幾、馬端臨史學思想的撰寫。這兩章的寫作,是白先生嘗試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古代史家史學思想的產生因素及學術價值。這樣的寫法,“與解放前研究史學史,具有質的不同,它不再是就書論書,不再是要籍解題式的思維方式。雖然它還屬于個案研究,且史學史與思想史不完全一樣,卻為史學史的發展帶來了曙光”(9)周文玖《白壽彝史學史思想的發展歷程》,《回族研究》2000年第3期,第31頁。。如果放在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這一學術追求歷程來看,白先生的這一撰寫反映了他在與侯外廬先生學術交往中受到啟發而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建設有了新的認識,即明確意識到史學思想在史學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認識到中國古代史學思想也有進步性。這也說明,白先生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意識逐漸明確。
進入20世紀60年代,隨著全國學習和研究史學史熱潮的興起(10)寧泊《史學史研究的今與昔——訪楊翼驤先生》,《史學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15頁。,白先生發表的關于史學史的文章多了一些。其中,《談史學遺產》與《關于中國史學史任務的商榷》兩文(11)白壽彝《談史學遺產》,《新建設》1961年第4期,第9-22頁;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人民日報》1964年2月29日,第5版。兩文又分別見于《白壽彝史學論集》,第462-486、595-601頁。,不僅提出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任務和范圍,還論述了史學遺產與馬克思主義史學建設的關系,比之以往認識又前進了一大步,顯示出他對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迫切心情。在白先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建設進程中,這是很有份量的兩篇理論文章,標志著他探尋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又前進了一大步,也就是他所說的“摸索出一點途徑”(12)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177頁。。
“文革”結束之后,特別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白先生提出史學史工作應“甩掉舊的軀殼,大踏步前進”(13)白壽彝《中國史學史上的兩個重大問題》,白壽彝《白壽彝史學論集》,第603頁。,把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中國史學史學科早日建立起來。所謂“甩掉舊的軀殼”,就是要擺脫以往史學史“提要式”撰述的影響,展開對中國史學史上重要問題的研究;所謂“大踏步前進”,就是要加快推進具有民族特點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設。具體而言,第一,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更加堅信,并在理論理解和實踐運用上都有了很大提升,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傳播與發展也作了梳理和分析(14)白壽彝(原署名“田孔”)《中國史學史上的兩個重大問題》,《史學史研究》1984年第3期,第1-2頁;白壽彝《六十年來中國史學的發展》,《史學月刊》1982年第1期,第1-6頁;白壽彝、瞿林東《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史學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6-26頁。前二文又載于《白壽彝史學論集》,第602-605、639-649頁;后一文又載于《白壽彝文集》第5卷《中國史學史論》,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73-509頁。。第二,明確提出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建設的藍圖和模式,大大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建設的步伐。《談史學遺產答客問》系列文稿的發表(15)白壽彝《談史學遺產答客問之一》,《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1-8頁;白壽彝《談歷史文獻學——就〈談史學遺產〉答客問之二》,《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1-8頁;白壽彝《談史書的編撰——就〈談史學遺產〉答客問之三》,《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1-8頁;白壽彝《談歷史文學——就〈談史學遺產〉答客問之四》,《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1-8頁;白壽彝《關于歷史文獻學問題答客問》,《文獻》1982年第4期,第12-23頁。,一方面豐富了史學遺產與馬克思主義史學關系的理論認識,另一方面探尋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獲得民族形式的路徑。白先生在《關于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正式提出“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這一宏大學術追求,并從歷史資料的二重性、史學遺產的重要性、外國史學的借鑒、歷史教育的重大意義、歷史理論與實踐、史學隊伍智力結構共六個方面進一步闡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建設的方向和途徑(16)白壽彝《關于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幾個問題——1983年4月6日在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的講話》,《白壽彝史學論集》,第307-321頁。。第三,注重對中國史學史發展脈絡及特點的把握和敘述,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對中國史學問題作具體分析。白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中寫道,“這幾年,我對于史學史的研究工作,可能有兩點比過去要好些。一點是對于史學史的各個時期,都分別地摸索一下,這對于全書的結構,可以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看法”;“第二點,這幾年學習對問題作具體的分析”,“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精髓,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中國史學史上有大量的問題,需要進行這樣的分析,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就我個人來說,還處在起步階段”(17)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180-182頁。。他的這些話說得很謙遜,但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白壽彝先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是執著的,對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追求是不懈的。而他對《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的撰寫,正是這一學術追求的重要彰顯。這一點,既體現在白先生持續而深入的理論探索上,也體現在他不斷創新的史學實踐上。
二 理論上的建樹
白壽彝先生深入分析中國史學中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因素,多層面論證中國史學有自己的理論、特點、方法和作用,系統闡明中國史學史的范圍和任務,這些都是他關于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重要理論建樹。
第一,經過持續而深入地分析中國史學發展過程,更加明確而堅定地回答了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以前中國史學領域里是否有唯物主義歷史觀這一重大學術問題。這一回答,對于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既是前提,也是基礎,具有理論指導意義。
在《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中,白先生在談史學發展規律性時,提出了“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唯物主義歷史觀因素”這樣兩個概念。他寫道:“所謂‘有唯物主義歷史觀’,是說用唯物主義說明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過程。所謂‘有唯物主義歷史觀因素’,是說這種觀點僅可用以說明人類社會發展中某些事實或某些方面,而不能用以說明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過程。”(18)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31頁。據此,他認為,在馬克思主義傳入前,在中國史學領域里沒有唯物主義歷史觀,但有唯物主義歷史觀因素的存在(19)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31、36頁。。他舉賈誼《過秦論》中的民本思想對人民力量的承認,舉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的經濟觀念所強調的物質條件對道德的支配,這些都是具有唯物主義因素的重要觀點。回望中國史學的發展,這類的事例不少,值得關注和重視。
早在20世紀60年代,白先生雖已認識到中國古代史學中曾經有過不同程度的正確看法,但他只是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供大家爭鳴(20)白壽彝《談史學遺產》,《白壽彝史學論集》,第482-486頁。,說明當時他的這一方面認識還不明確而堅定。到80年代,他寫作《中國史學史》第一冊時,隨著他對中國史學發展過程的深入了解和系統認識,特別是對中國史學遺產理論的不斷總結,促使他完全有理論勇氣、也有史學自信地明確回答幾十年來所關注的這一重大學術問題。而這一堅定回答,使唯物史觀與中國史學實際相結合有了更為精深的理論基礎和深厚的文化土壤,更加促使他深入思考優秀史學遺產的思想成果同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間的互動關系,也更有信心建設和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
白先生還認識到,“在中國史學史上,對于重視社會影響,有一個歷時久遠的優良傳統”(21)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43頁。。由此,他對史學的時代特點及社會影響的理論內涵作了深刻闡述。他指出:“關于中國史學在發展中所反映的時代特點及其對社會的影響,這是要把史學發展放在中國社會發展的總相中去考察的。這是很重要的問題。過去的和當代的學者對這兩問題,也都有所論述,而說得不多。這是中國史學史上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問題,是史學對于社會的反作用的問題,是應該努力探索的。”(22)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40-41頁。這一理論認識是在強調,對中國史學史研究,一是要從中國史學進程中去探求史學發展規律,二是要關注和分析史學發展中所蘊含的民族特點。
第二,在對中國史學遺產持續整理與深入研究基礎上,強調指出中國史學有自己的特點、理論和方法,從中可發現馬克思主義史學建設和發展的民族形式。
白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中指出:“史料的運用,史書的編撰和歷史的文字表述,都應該在史學理論的指導下進行。而且,不管史學家是否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他們事實上也是這樣做的。但史料的運用、史書的編纂和歷史的文字表述,都有自己的特點,都有相對的獨立性,亦即各有自己的理論、方法和作用。盡管它們還沒有形成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但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也可以說,已具有一定規模的雛形。因此,我們也可以分別稱它們為史料學、歷史編纂學和歷史文學。”(23)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19-20頁。這段話表明,中國史學史研究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要注重對中國史學自身理論的學習和總結。這也從深層次上表達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可有自己的民族特點這一重要認識。
接著,他在本書中闡釋了史料學、歷史編纂學和歷史文學各自的范圍、內容及性質等一系列理論問題。這是在以往多年的認識基礎上又一次新的總結和深化,不僅有些說法更加明確而堅定,對有些認識作了提升和細化,而且形成了一個理論體系。
在史料學方面,他指出,史料學可以包含理論、歷史、分類和實用這四部分(24)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20頁。。史料學的內容中,理論最為重要。理論部分實際上談的是史與論的關系,強調史料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的辯證統一,史料與歷史編纂的聯系與區別,史料與歷史文學的互動關系。這就把史料學的基本內容都講到了,既有理論概括,也有事例印證。他特別強調,史料學研究就是要通過探討史料特點和史料學發展過程,總結史料學的規律。白先生的研究設想之一,就是“搞出一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歷史文獻學”,因為“這對于建設有民族特點的新的史學會有很大幫助”(25)白壽彝《關于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幾個問題——1983年4月6日在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的講話》,《白壽彝史學論集》,第313頁。。
在歷史編纂學方面,他指出:“史書的編纂,是史學成果最便于集中體現的所在,也是傳播史學知識的重要的途徑。歷史理論的運用,史料的掌握和處理,史實的組織和再現,都可以在這里見個高低。”(26)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23頁。這就把歷史編纂學在史學史研究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說出來了。無論多么高深的歷史理論,多么豐富繁雜的歷史資料,它們的運用都要由史書編纂這一學術工作來體現,它們的價值呈現同樣離不開歷史編纂學的發展。中國在歷史編纂上既有豐富的實踐積累,還不乏理論思考,值得關注和總結。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在歷史撰述實踐上對中國史書豐富多彩的表現形式的借鑒和創新,就可以很好地推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設與發展。
在歷史文學方面,他對中國歷史文學傳統作了進一步概括,不僅從文學與史學的內在關系上豐富了史學意義上的“歷史文學”內涵,使歷史文學這一遺產更有生命力,而且提出了一個重要理論認識,即歷史文學的基本原則。他指出:“把我國的歷史文學的優良傳統總結起來,我想最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六個字:準確、凝練、生動。”(27)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28頁。這是白先生在批判繼承古代史學的基礎上,借鑒近代以來關于歷史文學的思考成果,結合自身史學實踐所進行的理論探索。可以說,“準確、凝練、生動”這一歷史文學的基本原則,是從歷史學的本質特點和中國傳統史學的經驗中概括出來的(28)周文玖《20世紀史家論歷史文學》,《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69頁。,呈現出鮮明的民族特色。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繼承和創新這些優良歷史文學傳統,對建設和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也是有益的。
第三,史學遺產是有生命力的,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這種生命力會更加強盛。這就為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找到了民族自身的生命之源和發展之力。
白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中指出,史料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很古老的了,但它們一直到現在還是有生命力的,并且在相當久遠的將來也可相信其有一定的生命力”(29)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21頁。。這實際上就是他一直強調的歷史資料的二重性問題。所謂二重性,是指史料是過去的,也是現在的,還是未來的;史料不僅是歷史資料,也是思想資料,還是其他學科的學術資料。歷史資料二重性的提出,突出和強調了史料在史學研究中的生命力,很好地把過去、現在和未來三者聯系起來,進一步加深了對史學遺產的理解。這一理論認識的價值,更在于使史學史學科建設和發展呈現出更為豐富的民族特點。正如瞿林東先生所言,“對于歷史資料作這樣的理解和運用,必然使歷史著作不僅反映著中國歷史的內容和特點,而且還帶著中國民族的精神傳統和思想傳統,顯示出鮮明的民族特色”(30)瞿林東《唯物史觀與史學創新——簡論白壽彝史學研究的理論風格》,瞿林東《白壽彝史學的理論風格》,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頁。。
歷史資料有它的二重性,客觀歷史本身也有它的二重性,史學遺產同樣有它的二重性。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中國史學遺產的生命力會更強盛。白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中明確指出:“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應該繼承這四部分的優良遺產,加以改造,并有所創新,從而建設我們的新史學,對社會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的研究作出應有的貢獻。”(31)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29頁。這里所說的“新史學”,就是指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32)1983年,白先生在《關于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幾個問題》的講演中說:“對史學遺產的這四個方面,我們應該進行總結,發揚優良傳統,為建設我們有民族特點的史學做出貢獻。”參見:《白壽彝史學論集》,第315頁。。
第四,在思想認識與史學實踐的基礎上,更加明確了中國史學史的任務和范圍。這為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提供了整體性說明,在學科建設上蘊含更深層的民族特點及史學意義。
白先生在繼承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關于“歷史”與“史學”這兩個概念的認識基礎上,再一次強調區別“客觀歷史”和“歷史記錄”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他之所以要把“歷史”和“史學”的意義弄清楚,是為了更好地解決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任務和分期這兩個重要問題(33)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1頁。。故他在《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中,再次明確提出并深入闡釋了史學的任務、范圍和史學史的任務、范圍。他認為,“史學的任務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過程及其規律。它的范圍可以包括歷史理論、史料學、編撰學和歷史文學”;史學史的任務是“對于中國史學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的論述”,它的范圍“包括中國史學本身的發展,中國史學在發展中跟其它學科的關系,中國史學在發展中所反映的時代特點,以及中國史學的各種成果在社會上的影響”(34)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11、29頁。。這兩個任務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沒有對歷史發展過程及規律的認識和總結,就不會客觀地認識和總結史學發展的過程及規律。白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中的這些理論論述,“是作者把40多年來思考的問題、發表的見解、積累的成果,經過歸納和提高,升華為理論的形式而構成一個整體”(35)龔書鐸、瞿林東《白壽彝先生的史學思想和治學道路》,《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1期,第9頁。。
建設有民族特點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當然離不開對外國史學史的學習和研究,這樣的途徑也是必不可少的。白先生在《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中談他的摸索和設想時指出:“如果在研究中國史學史的同時,還要研究西方史學史和東方史學史,好像是一句空話。但是,這些工作我們都必須要做。不寫兄弟民族的史學史,中國史學史就不算完整。不研究外國史學史,就看不出中國史學史的特點。”(36)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178頁。
白先生強調指出:“研究中國歷史學的特點,就是研究中國史學遺產的特點,對于我們建設一個有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很有幫助。我們建設有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必須是在我們過去的歷史學的基礎上,在對我們過去的史學遺產的總結的基礎上來進行工作。”(37)白壽彝《關于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幾個問題——1983年4月6日在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的講話》,《白壽彝史學論集》,第310頁。這一表述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在于,“一方面是,把中國史學遺產研究的重要性,提高到與當今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設和發展有直接關系的高度上來認識,從而為研究中國史學確定了位置、明確了方向;又一方面是,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設和發展同總結中國史學遺產聯系起來,這不僅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內容,而且也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民族特點找到了具體的形式和實現的途徑”(38)瞿林東《白壽彝先生和20世紀中國史學》,《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32頁。。《中國史學史》第一冊正是對這一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里程碑式的彰顯。
三 實踐上的創新
白壽彝先生始終把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作為他在史學史研究領域努力的正確方向和奮斗的宏偉目標(39)瞿林東《白壽彝先生和20世紀中國史學》,《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32頁;曲柄睿《溫故知新與繼承發展——寫在白壽彝先生〈中國史學史〉(第一冊)出版三十周年之際》,《史學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71-74頁。。他的史學史研究設想,重要的就是“要把中國史學發展過程及其規律能比較有系統、比較全面地寫出來”,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必須向這方面努力”(40)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192-193頁。。這一努力做好了,對于中國史學史研究,那就是一次“脫胎換骨”(41)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193頁。。《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的撰寫,就是對這一研究設想大膽而又有創新的史學實踐,標志著白先生“已經走上了大道”(42)施丁《成一家之言——評白壽彝著〈中國史學史〉第一冊》,《歷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128頁。。
《中國史學史》第一冊包括“敘篇”和“第一篇”兩大部分。“敘篇”的第二、三章標題是“中國史學史的分期”,第四章標題是“有關史學史的古今論述”。說“分期”,實際上是主要敘述中國史學發展脈絡,并放在時代條件下總結史學發展的民族特點。
《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中對中國古代史學發展過程的敘述,基本由兩大部分構成:一是略說每一時期的時代特點,二是概括與之相應的史學成就及特點。白先生在敘述每一時期的史學成就和特點時,基本上是從歷史觀點、歷史文獻、歷史編纂和歷史文學這四個方面進行分析和總結。當然,不同時期,這四個方面內容的側重點略有不同。從這四個大的方面入手概括中國史學在發展過程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在此基礎上嘗試揭示中國史學發展的規律,是白先生的重要史學貢獻。在分析具體史學問題時,白先生遵循辯證唯物主義,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樣的辯證分析和認識,今天讀起來,仍有眼前一亮的感覺,有些實為卓識(43)關于《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的辯證法運用,可參見:吳懷祺《中國史學發展辯證法的探索——讀〈中國史學史〉(第一冊)》,《史學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41-47頁。。
白壽彝先生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敘述,同樣放在中國史學總相中加以考察,辯證地看待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取得的成就。立足史學與時代的關系,白先生把1919年至1949年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進程分為四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自身的特點(44)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106-107頁。。在總結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取得豐碩成果的基礎上,他指出:“從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是在斗爭中逐步建立起來的。這個斗爭,一方面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命運息息相關,另一方面又與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息息相關。”(45)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118頁。這是一個帶有規律性的史學認識,揭示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自產生時起就與中國歷史命運、中國革命斗爭緊密相聯,具有鮮明的民族特點。
在敘述有關史學史的古今論述方面,白先生也是把它放在中國史學總進程中加以分析。他從漢唐史學史論述開始,主要討論了司馬遷、班彪、劉知幾、鄭樵、李贄、章學誠等史學家的史學史論述,既充分肯定了他們對于史學史總結和思考的貢獻,也指出了他們的時代局限性。白先生寫道:“從司馬遷到章學誠,都是封建時代的人物。他們關于史學史的論述,有的話說得很好,一直到現在,對于我們研究史學史很有用處。但他們都不可能提出史學史研究的必要,更不可能說要把史學史寫出專書,從而揭示中國史學發展的總過程。”(46)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159頁。雖然中國古代史學上存在唯物主義歷史觀因素,但并沒有形成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理論體系。隨著史學近代化,梁啟超嘗試對中國史學史進行專門研究,并設想撰寫中國史學史專著。盡管梁啟超在中國史學史學科開創方面作出了貢獻,但他并沒有看到馬克思主義“這種新生事物”,所講或設想的史學史專著仍帶有濃厚的史部目錄學的氣味。而馬克思主義史學高度重視史學發展脈絡及相互聯系,并從時代特點和社會影響兩個層面探尋史學發展的深層因素和社會價值,揭示史學發展規律,從根本上突破了以往目錄學模式下的史學史研究。故真正推動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取得質的飛躍的,還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白先生指出:“李大釗同志對于歷史觀之歷史的闡述,把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推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時期。”(47)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172頁。對侯外廬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中的史學思想論述,白先生給予高度肯定:“史學思想史畢竟是構成史學史的重要內容,應當特別重視。我們的史學史研究工作,應以這部書的已有成就為基礎,繼續前進。”(48)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172頁。
《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第一篇”為“先秦時期,中國史學的童年”,是以更加具體的實踐來摸索建設具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歷史觀點的初步形成”和“歷史知識的運用”這兩部分的撰寫,就是重要體現,前者是對歷史理論的關注,后者是對史學的社會影響和價值的闡釋。關于“歷史知識的運用”,他從三個大的方面進行分析:一是“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二是“疏通知遠”,三是直筆、參驗、解蔽,并且對每一方面又從若干層次作了深入剖析,提出了諸多新見解。這是以往史學史論著中很少涉及到的,更不要說有如此系統的論述。可以說,《中國史學史》第一冊對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建設確實作出了實踐意義上的重要開辟。
綜觀白壽彝先生關于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術追求、理論建樹和實踐創新,正是按照去認識、去實踐、去創造這樣的建設之路去努力,且成就卓著。白先生突出的史學貢獻,就是他以一個史學大家的通識和器局,對中國史學發展的方向和前景提出了人們可以認識和實踐的具體路徑,并經過他自身的史學實踐,證實了這一路徑是可行的。白先生的這一學術追求很高,也很實。他說:“要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要站在世界前列,不能一般化,真要拿出東西來。”(49)白壽彝《關于建設有中國民族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幾個問題——1983年4月6日在陜西師范大學歷史系的講話》,白壽彝《白壽彝史學論集》,第321頁。這樣的治史思想與方法,很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深入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