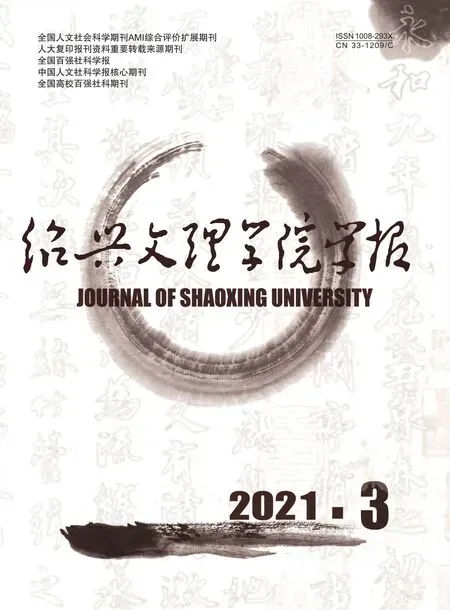越劇海外劇場翻譯研究
——基于洛杉磯越劇團演出錄像的分析
陶丹丹
(紹興文理學院 元培學院,浙江 紹興 312000)
越劇作為綜合性的現代劇場藝術,以感召心靈的精神價值、雅俗共賞的審美取向、獨樹一幟的表演風格,承擔著傳播中華文化、塑造國家形象的重大使命。劇場翻譯使越劇的思想內涵和藝術魅力在目的語語境中獲得新生,對提高越劇的可交流性、促進越劇觀眾的多元化發揮了重要作用,為越劇走出國門、參與全球化的文化交融開辟有效途徑。然而,越劇海外傳播雖已走過60多年的歷程,但是其海外劇場翻譯還有待改進和創新,國內不少越劇團的海外演出資料仍然缺乏質量保障[1]56。相較而言,一些海外越劇團的文本生產機制更加成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洛杉磯越劇團。劇團于2013至2019年在美國鮑德溫公園市演藝中心公演了54出越劇折子戲,通過中美合作的模式翻譯了演出字幕、報幕、海報、戲單等劇場文本,并將演出錄像發布在劇團網站[2]和目前全球最大的視頻分享平臺YouTube上。本文將結合劇場翻譯理論對部分演出錄像進行分析,旨在探究劇場翻譯在傳播越劇價值內涵上的規律性,為越劇翻譯理論的構建拓寬思路,也為越劇海外劇場翻譯實踐提供借鑒。
一、劇場文本及其翻譯特點
西方戲劇學經歷了從“劇本(drama)研究”到“劇場(theatre)研究”的轉型[3]58。法國戲劇理論家帕特里斯·帕維斯(Patrice Pavis)曾提出,戲劇翻譯研究應集中在舞臺表演層面的戲劇譯本上,而非一般文學意義上的戲劇譯本[4]41。戲曲是中國傳統戲劇,對戲曲翻譯進行研究,也需考慮翻譯文本與劇場表演的關系,加強與劇本翻譯研究的區分度,突顯戲曲翻譯研究的跨學科本質。
與注重文學性的劇本之作相比,劇場之作注重整體性的追求。劇場除其空間意義外,是充滿“誘意”與“解放”的藝術的“場”,是一個由劇本、表演、舞美及觀眾的反饋等因素共同營造的藝術整體[5]9。各種藝術符號協調創造,在觀演的互為主體中,形成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往復。劇場文本觀意在突出戲曲的舞臺性、表演性,認為應將戲曲視為“立”于舞臺上的“活”的藝術,因此比劇本文本觀更能體現戲曲的本質。劇場文本觀還認為,觀眾是劇場的一個有機因素,劇場文本不是單向度地取悅或教化觀眾,而是通過演員和觀眾雙方的互動,調動觀眾主動參與到戲曲藝術的整體創造之中。這種戲曲文本觀是對劇本文本觀的積極揚棄,強調對劇場整體意蘊的挖掘。
同樣,劇場翻譯也有著不同于劇本翻譯的特點。劇本翻譯傾向于“深度翻譯”,通過添加大量注釋,或配以導讀、鑒賞或評析性的文字,最大化地保留原作的語言形式和文化信息,幫助目的語讀者構建理解劇本所需的知識框架。劇場翻譯不再視原文神圣不可侵犯,考慮到劇場文本的特點,對原文的“某些叛逆是必須的”[6]1。首先,劇場文本具有瞬時性,譯文須在最短時間內抓住觀眾的注意力,因此,在保留原劇中心意旨的前提下,譯文通常作淺化處理。其次,劇場文本通過“高密度的符號”生產“復調式的信息”[7]5,譯文的簡潔也是因為語言以外的多重符號可以對譯文進行補充,使劇作之“意”的闡釋與舞臺之“象”的呈現相互交融,在“象”與“意”的互補中傳播戲曲的精神價值和美學價值。再者,劇場文本要遵守接受系統的演出習俗,適應目的語觀眾的接受能力,還要符合具體劇院的要求,因此,在翻譯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對一些語言成分進行適應性改造或創造性改寫。正如愛爾蘭翻譯家、劇作家大衛·莊士敦(David Johnston)所言,表面“忠實”的翻譯可能經常使一出外國戲劇拙劣無趣,如同從背面看一塊土耳其掛毯一樣黯然失色[8]9-10。可見,“忠實不美,美不忠實”是對劇場翻譯特點的經典概括。
二、越劇海外劇場翻譯的多層語境
劇場翻譯叛逆性的背后潛藏著一系列的語境因素。劇場交流可被視作在特定語境下,人們運用多種符號資源建構意義的過程。意義的生成受到文本外部或內部因素的制約。將這些因素按照不同層級進行分類闡述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劇場翻譯研究的主觀性,使劇場翻譯研究具有可觀察性、可描述性和可論證性。越劇海外劇場翻譯的語境因素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一)宏觀層面的文化語境
越劇海外劇場翻譯受到源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的制約。一方面,需要考慮新時代我國的文化戰略。自我國提出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以來,國家文化政策不斷加大對戲曲海外交流的支持力度,積極拓展地方劇種的海外演出市場,推動戲曲作為中國文化的金名片走向世界。越劇被稱為是“流傳最廣的地方劇種”,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海外傳播方面,有其得天獨厚的優勢[9]。越劇對外翻譯是為了弘揚中國文化的價值觀,完成跨文化的國家形象和民族身份建構。另一方面,這種在目的語文化以外策動的翻譯活動,必須關照目的語文化的需求或期望。歷史上無數的翻譯實踐證明,不符合目的語文化需求或預期的譯作很難為之接受。在西方戲劇系統中,越劇尚處于邊緣位置,欲穿越中心文化接受的屏障,越劇海外劇場翻譯不能囿于本國文化立場和視野,也要從西方文化視角出發思考越劇之于西方文化的價值,西方觀眾對待越劇藝術的態度等問題。翻譯時應更多關注越劇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的傳播,而非譯文和原文形式上的一致性,才有可能使這種與西方迥異的藝術為西方觀眾理解。
(二)中觀層面的情景語境
越劇海外劇場翻譯也受到傳播方式、媒介技術等情景因素的限制。傳播方式不同,翻譯策略也不同。目前越劇海外傳播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演出原汁原味的越劇或展映越劇電影,同時提供外語劇情介紹。譯文通常按照西方戲劇的敘事邏輯進行重構。二是在第一種傳播方式基礎上,提供唱詞念白的外語字幕。字幕譯配受到時空限制:時間限制是指字幕的出現要和唱詞念白同步;空間限制是指字幕投影設備有字數限制,譯文要精煉、明晰,避免分散觀眾注意力。三是演員配合越劇唱腔,用外語演唱越劇。譯文要滿足唱詞的音樂性,調整譯文語言的音韻,盡量合入音樂曲調。在使用同種傳播方式時,媒介技術對翻譯策略的選擇也起到關鍵作用。以字幕譯配為例,早期的劇場字幕顯示在舞臺上方字幕屏中,后來不少劇院將字幕屏置于舞臺兩側暗區,有的劇院還配有覆蓋整塊舞臺背景的字幕屏或在觀眾座椅背面安裝了小型字幕屏。2015年阿維尼翁藝術節上出現了一項新技術:用智能眼鏡觀看戲劇表演。智能眼鏡可以將文字、圖像疊加在眼前并描述舞臺上的對話或聲音效果,還可以提供個性化定制服務,觀眾可以根據個人喜好選擇字幕語言、字體大小、顏色和位置。這項技術使觀眾在劇院的任何位置都能舒適、自由地觀賞戲劇、閱讀字幕,提升了戲劇表演的可訪問性和劇場體驗[10]138。字幕屏的尺寸及其與觀眾的距離、字幕是否可調節等技術參數直接影響到觀眾注意力的集中方式,進而影響到翻譯策略的選擇問題。
(三)微觀層面的美學語境
越劇海外劇場翻譯還受到中西方戲劇美學思想的影響。越劇表演有鮮明的審美特色,融合了寫意與寫實的表現手法。寫意是指越劇繼承以歌舞化、虛擬化、程式化為特征的中國戲曲傳統,注重對形式美的提煉,追求總體上的意境和神韻。寫實是因為越劇吸收了話劇、電影的現實主義表演方法,重視人物性格和內心世界的刻畫,賦予人物鮮明的個性色彩和強烈的情感色彩,以真情實感打動觀眾。對形式美的追求使越劇富含韻律節奏、清辭麗句、詩情畫意,語言具有音樂性、說唱性和抒情性。不同于中國戲曲的意象論,西方戲劇的美學根基為摹仿說,認為戲劇藝術必須描摹和反映生活的真理,因此更偏重于寫實的傳統。西方戲劇表演以生活化的言語、動作來展示劇情,講究情節的曲折和沖突的尖銳,強調表演中理智的參與。對真實性的追求使人物對話在西方戲劇表演中占有重要地位,語言具有邏輯性、精確性和思辨性。但無論是表現表演之美還是情節之真、注重以情感人還是以理服人,詩意的核心或內涵意蘊共同存在。這就意味著翻譯時要在矛盾的兩端之間找到統一性,既要充分再現越劇的美學特征,也要兼顧西方觀眾的審美意趣。
三、洛杉磯越劇團劇場翻譯的多維策略
在多層語境制約下,越劇海外劇場翻譯也必然經歷一定程度的叛逆。洛杉磯越劇團的劇場翻譯實踐可作為典型個案加以證明。劇團成立于2003年,由美籍華人越劇演員和在美的越劇愛好者組成,以專場演出和學術交流相結合的方式傳播越劇藝術,這不僅增強了當地華人社區的凝聚力,而且贏得了美國主流社會的文化認同。2013年,洛杉磯越劇團獲得美國加州州政府及當地政府的獎勵,以表彰劇團對于傳播中華文化藝術、促進中美文化交流的貢獻。劇團在美國公演了《追魚·書館》《打金枝·闖宮》《張羽煮海·聽琴》《西園記·夜祭》《蝴蝶夢·圓夢》《柳毅傳書·湖濱惜別》等越劇折子戲,演出時保留越劇的原汁原味,并提供中英文劇情梗概和唱詞念白的字幕,還有中美主持人進行雙語報幕。考慮到劇場翻譯的語境因素,劇團從下列五個維度出發選擇翻譯策略,對原文本進行了適應性改造或創造性改寫。
(一)敘事建構
翻譯并不是簡單的語碼轉換,而是一種再敘事。每當一種敘事版本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時,總是會在新語境中被注入其他敘事元素,目的是要突出或抑制原文中隱含的敘事,從而操控人們對當前敘事的解讀。洛杉磯越劇團在劇場翻譯時采用的敘事建構策略主要有“標示性建構”[11]187和“文本素材的選擇性采用”[11]173。
標示是指用來指示或識別人物、地點、事件及敘事中其他關鍵元素的詞匯或短語。越劇劇目就是非常有力的標示性建構手段。例如,《追魚·書館》這場折子戲劇目用故事發生的地點作為標示,英譯時卻用事件代替地點,將“書館”改寫為The Romantic Encounter(浪漫邂逅)。改寫后的譯文符合西方戲劇重情節的美學觀,同時將鯉魚精和書生張珍之間的真摯愛情前景化,為觀眾了解劇情提供了一個詮釋框架。除了突出情節之外,越劇劇目翻譯有時還會強化沖突。以《打金枝·闖宮》為例,原劇名“闖宮”強調駙馬爺郭曖的單向行為,這個標示經過改寫后被譯為Argument(爭吵),突出郭曖與升平公主之間的矛盾,進而將觀眾引向兩人爭吵的根源:民間道德與皇家禮法之間的沖突。譯文既簡潔明了,又與西方戲劇講究沖突的美學語境相契合,能夠吸引西方觀眾的注意力。
文本素材的選擇性采用是通過添加或刪除一些敘事元素實現的,常用于越劇劇情梗概的翻譯。《張羽煮海·聽琴》的劇情介紹中有這樣一個句子“瓊蓮舍頜下驪珠,救其生還。”這句話在英文版本里對應的是“To save Zhang Yu’s life, Qiong Liangave up her human appearanceby losing the pearl under her jaw.”。“驪珠”是驪龍頜下的珍珠,若僅將其翻譯成pearl(珍珠),不足以充分展現龍女瓊蓮為愛犧牲的精神。譯文通過添加畫線部分信息,意為“舍棄人形”(下畫線為筆者所加,下同),強化了這種犧牲精神,此處的適應性改造對呈現追求婚姻自由的敘事立場起到推進作用。此外,考慮到劇場文本的瞬時性和字幕譯配的時空限制,對傳遞越劇價值內涵關系不大的次要信息,翻譯時通常作刪除處理。簡言之,在不背離原劇中心要旨的前提下,譯者可以有選擇性地參與敘事建構。
(二)語用對等
“對等”是翻譯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研究者們對此進行了分類,安東·波波維奇(Anton Popovic)區分了四種類型的對等:語言對等、詞形對等、文體對等和語篇對等;尤金·奈達(Eugene Nida)提出了形式對等和功能對等;阿爾布雷希特·諾伊貝特(Albrecht Neubert)認為對等包含語義對等、句法對等和語用對等;蒙娜·貝克(Mona Baker)將對等細化為五個層次,位于第五層的是語用對等。概括起來,對等主要涉及語言結構形式和語言使用效果兩方面。語用對等關注的是語言使用效果,意指特定語境中話語內涵義的等效傳遞,從而使目的語受眾獲得類似源語受眾所獲得的感受。
出于越劇海外劇場翻譯的交際目的,語用對等優先于其他層次的對等。劇場翻譯必須聯系觀眾,為了適應西方觀眾的理解和欣賞能力,譯者應當根據語境,將原作中人物唱詞和念白的語用意義用目的語恰當地表達出來。例如,《西園記·夜祭》里的丫鬟香珺有這樣一句念白“這真是冬瓜纏在茄棚里”,她以為書生張繼華把她當成她家小姐了。洛杉磯越劇團的譯文是“Ha, he completelygot hold of the wrong end of the stick.”。畫線部分習語的字面意思是抓住棍子的錯誤末端,語用意義是指搞錯、完全誤解,配合語氣詞Ha(表示驚訝)的使用,產生了與原文對等的喜劇效果,能夠拉近與目的語觀眾的距離。同樣,越劇唱詞中的成語也可以譯作對應的英語習語。《蝴蝶夢·圓夢》有唱詞為“真王孫若無假,也算得百里挑一難尋求”,其中的成語“百里挑一”形容人才出眾,對應的譯文是the cream of the crop,常用來指精英、佼佼者,因此,譯文傳達了等效的語用含義,另外,這個習語押頭韻,讀起來朗朗上口,給觀眾留下較為深刻的印象。語用對等還可以通過轉換意象來實現。唱詞“我弱水三千舀一瓢飲”(《蝴蝶夢·圓夢》)被譯作“You are the only beautiful rose in my eyes in this colorful world.”(在我眼中,你是這個多彩世界中唯一一朵美麗的玫瑰)。“弱水”比喻愛河情海,原文是說情愛心意很多,但我只取其中之一,譯文用“玫瑰”意象進行替換,因為玫瑰在中西方文化中都象征忠貞愛情,這種創造性改寫使西方觀眾能像源語觀眾那樣理解和欣賞原唱詞。
(三)文化適應
芬蘭戲劇翻譯研究者薩庫·阿爾多倫(Sirkku Aaltonen)指出,在當代西方劇場中,他國戲劇的譯作并不是為西方觀眾看見他者而打開的窗戶,而是幾乎成為讓他們看見自我的鏡子,因為那些熟悉的片段讓觀眾感覺更為安全[12]52。文化適應就是通過融合熟悉事物和陌生事物,淡化異質文化色彩的翻譯策略。除了受到中心與邊緣的文化關系制約外,文化適應也是考慮到劇場文本的瞬時性以及字幕譯本的時間、字數和技術限制。鮑德溫公園市演藝中心的字幕顯示屏位于舞臺兩側暗區,譯文如果太長,容易分散觀眾注意力,因此,劇場翻譯不能像劇本翻譯那樣,通過添加注釋的方式來傳遞源語文化內涵。
文化適應通常表現為借用西方觀眾熟悉的文化概念進行二度闡釋。以《柳毅傳書·湖濱惜別》為例,洛杉磯越劇團在其英文版劇情介紹中,將柳毅類比為Samaritan(撒馬利亞人),柳毅急人所難、千里傳書救危,撒馬利亞人路遇一個被強盜打劫、身受重傷的猶太人,不顧教派隔閡幫助他,兩者都有見義勇為的精神氣概,這也是中西方價值的共通點,譯文既傳播了重信義的中國傳統價值觀,又聯系了西方宗教文化,促進了越劇思想內涵的跨文化闡釋。類似的例子還有:將神話劇劇目《追魚》譯成Mermaid Legend(美人魚的傳說)。雖然鯉魚精和美人魚的外在形象不同,但都是真善美的化身,她們為了追求愛情,不惜犧牲自我的精神和高尚的情操是相通的。譯文通過創造性改寫,激活了西方觀眾的認知結構,減少了文化干擾。再如,《西園記·夜祭》唱詞“不煩月老牽紅線”的英譯是“no need to borrow Cupid’s arrow.”(不需要借丘比特之箭)。月老以牽紅線來匹配姻緣,愛神丘比特用利箭射中情侶。譯文回避了月老典故的出處,使用西方觀眾熟悉的文化概念,讓他們產生相應的文化聯想,有助于他們快速理解唱詞的文化內涵。
(四)情感顯化
越劇具有濃郁的抒情氣息,體現情感濃聚的性格色彩。西方戲劇則更加注重理趣,強調理智對情感的主導作用。在不同的美學思想影響下,目的語觀眾和源語觀眾的情感反應也可能大相徑庭。如何讓目的語觀眾重溫源語觀眾的情感體驗是越劇海外劇場翻譯的又一大挑戰。為此,譯者需要從目的語觀眾的角度出發,設法構建有可能產生相似情感的譯作語境,并對劇中人物的情感進行顯化,從而使目的語觀眾在跨文化意義上做到情感投入,最終建立和發展跨越時空的情感共鳴。
顯化人物情感的一種策略是在譯文中添加指示語和情感副詞。指示語又被稱為語境化線索,不僅表明演員與舞臺的關系,而且是連接身勢語和話語的重要橋梁[13]65,還對舞臺人物塑造起到決定性作用。越劇《打金枝·闖宮》講的是唐汾陽王郭子儀壽慶,幼子郭曖因妻子升平公主自恃高貴不去拜壽,怒而回宮打了公主。郭曖闖宮時有這樣一句唱詞“邁開大步進宮廷”,洛杉磯越劇團的英譯字幕是“Here I am striding ahead fearlessly.”。譯文以情景為參照,添加了空間指示語here(這里),達到了唱詞與動作的連貫性,引導觀眾把注意力集中到郭曖這個人物身上。原文“進宮廷”省略不譯,是因為舞臺布景可以對文本進行補充,避免了信息冗余。添加情感副詞fearlessly(無所畏懼地),更易于讓觀眾感受到動作化語言所體現的人物的情感態度,進一步突顯了郭曖年少氣盛的性格特點。另一種情感顯化的策略是合理使用夸張的修辭手法。例如,《西園記·夜祭》中的書生張繼華追悼玉英亡靈時唱到:“我手捧祭酒和淚悼”,對應的英譯是“tears of blood falling from my broken heart.”。譯文做出了適應性改造:首先,考慮到劇場表演的多重符號性,將“手捧祭酒”和“悼”省去不譯,譯文的簡潔使演員可以通過動作對語言進行補充,促進了語言和身體之間的交流;其次,在“淚”字上增添筆墨、適當渲染,譯作“滴滴血淚”,同時添加“從我破碎的心里流出來”,譯文通過這種夸張的修辭手法,表現出人物篤誠專一的性格。充分再現人物情感有助于增強譯作的感染力,也能夠幫助目的語觀眾增加對異質他者的情感理解。
(五)審美再造
受越劇美學思想的影響,越劇語言也注重形式美。無論是唱詞還是念白,越劇語言講究音節對稱、韻轍整齊、平仄抑揚,營造出一種和諧的音樂美。以感性、直覺、意象等方式表達思想情感,把情、景、意融合,產生富有詩情畫意的意境美。對偶、排比、反復、比喻、擬人等多種辭格的使用給越劇語言增添修辭美。越劇語言的這些審美特質應盡量在譯文中得到充分再造,同時必須兼顧當代英語的規范以及舞臺呈現的要求,否則就會干擾觀眾。
音樂美的再造要求譯文總體上做到節律對應,但不能因韻損義,最好還能與越劇的板式結構、唱腔曲調相配合。具體需要考慮譯文的音步、韻式、格律等問題。在譯文中使用與原文大致相仿的音步數。用英語中現有的韻式,或者創造出一種新韻式,對原文的音韻特征進行移植。考慮到漢語聲調帶來的音樂美感無法在英語中再現,可以用英語詩體的格律做出補償。意境美的再造主要涉及意象的處理。意象的塑造使越劇語言彰顯模糊之美,但這種模糊美感在講究邏輯性的英語中必然遭到磨蝕,加上劇場字幕翻譯要求精煉、明晰,“存象顯意”和“舍象顯意”的翻譯策略較為常見[14]32。修辭美的再造可以通過保留原文辭格或轉換辭格來實現,以達到和原文近似的修辭效果。
舉例來說,《柳毅傳書·湖濱惜別》有兩句唱詞是“夕陽西下晚霞紅,驪歌聲聲催歸鴻。”越劇屬于板腔體戲曲,在唱詞節奏上,依據其調腔特點形成了齊言的七字句、十字句。此例中的唱詞是七字句,分為三個音步,音步的節奏呈二、二、三方式分布,如“夕陽/西下/晚霞紅”。兩句唱詞分別在句首(夕/驪)和句尾(紅/鴻)押韻,第一句句內也有押韻(夕/西、下/霞)(第二句的“催/歸”在越劇舞臺語言中不押韻)。第一句唱詞平仄相交,聲調高低起伏有致,第二句唱詞聲調較平。“夕陽”“晚霞”和“歸鴻”等意象的并置烘托出離愁別緒和凄美的意境。兩句唱詞結構相似、字數相等、意義密切相關,用的是對偶的辭格,具有排列整齊、對稱均勻的美感;另一種辭格是擬人,體現在一個“催”字上,形象地表達了龍女三娘和書生柳毅的難舍之意。洛杉磯越劇團的英文字幕是“The setting sun kindled the sky. The farewell song hustled the parting.”。譯文進行了適應性改造,總體采用英語詩歌中的四音步抑揚格,創造了一種和原唱詞相仿的節律。setting/sun/sky/song 押頭韻,setting/parting和kindled/hustled 這兩組詞押尾韻,重塑了一種別樣的音韻之美。為了再造意境美,使用“存象顯意”的策略,將“夕陽”譯為the setting sun(落日),既保留了意象,又顯化了意思。使用“舍象顯意”的策略,舍去“歸鴻”這個意象,將其象征意義作明晰化處理,譯為parting(離別)。“晚霞”這一意象則通過隱喻辭格進行復現:kindle本義是指燃燒,此處的喻義是指落日映紅了天空。hustle作動詞時表示“推搡”,保留了原唱詞中的擬人辭格,和“催”字有異曲同工之妙。譯文的平行結構是對原唱詞對偶辭格的轉換。總之,譯文雖在細節上有所叛逆,但整體上有效傳遞了原唱詞的藝術魅力。
四、結語
越劇海外劇場翻譯是一種創造性叛逆。說越劇海外劇場翻譯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越劇作品引入到一個陌生的文學和戲劇系統。面對系統中多層語境因素的制約,無論譯者多么希望盡其所能地忠實于原作,在翻譯過程中必然會改變原作的一些內容,造成譯作對原作的客觀背離。說越劇海外劇場翻譯是創造性的,那是因為它賦予越劇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譯者只有發揮自己的藝術創造力才能去接近和再現原作,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觀眾開展一次全新的藝術交流,使之在一個新的歷史、文化、社會環境里獲得第二次生命。洛杉磯越劇團的劇場翻譯實踐表明,叛逆性與創造性是無法割裂的,它們是一個和諧統一的有機體。洛杉磯越劇團根據劇場文本的整體性、瞬時性和符號性等特點,結合當代西方觀眾的價值取向和審美期待,在敘事、語用、文化、情感和審美等維度對越劇折子戲的劇場翻譯進行了適應性改造或創造性改寫。這種改造或改寫具有叛逆性,也體現出創造性,兩者的融合促進了越劇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的有效傳遞。正是因為創造性叛逆,才使得經典越劇作品及其蘊含的中國精神得到了跨越時空的傳播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