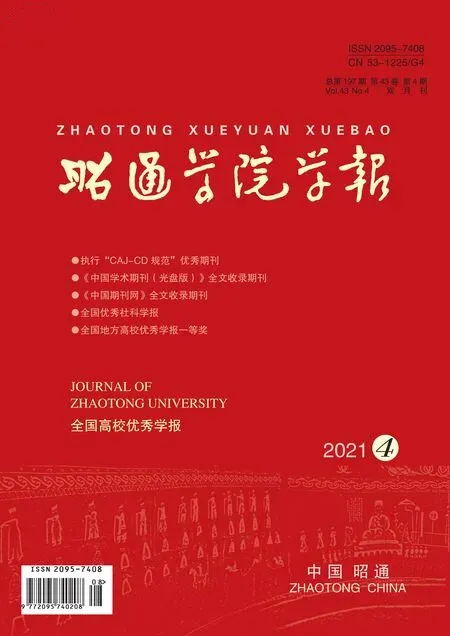論《亞孟森》中女性書寫的權力維度
張佳佳
(信陽學院 外國語學院,河南 信陽464000)
作為當代短篇小說大師,門羅確實“寫盡了女性的愛與哀愁”[1]1,尤其是女性個體作為“第二性”,在追尋自我的過程中與由男性主導的“規訓社會”碰撞時所遭受的痛苦和磨難。《亞孟森》是門羅的最后一部小說集《親愛的生活》中的第二篇故事——“這部小說集中最好的一個故事”[2]61。它記述了一個想要追求更高學歷的女大學生薇薇安的工作和情感經歷。為了積攢學費,她在遠離多倫多的小鎮上找到了一份在治療肺結核的療養院里為患病兒童教學的工作。在此期間,她逐漸迷戀上療養院里的主管醫生福克斯,最終迷失自我、委身于他卻被拋棄的故事。在門羅王國中,“規訓社會”通常體現為一種封閉狹隘的思想環境和冷漠、疏離的人際關系。薇薇安在前往亞孟森,了解亞孟森以及離開亞孟森的整個過程中生動呈現了一個原本懷揣夢想的“自由人” 如何在“亞孟森”這個“規訓空間”里迷失,陷入猶豫和掙扎,最終被“馴服”——用既定的“女性氣質”去取悅“主體”,卻仍然無法逃脫悲劇的命運。在此過程中也凸顯了門羅對女性個體的社會生存狀態的關注以及對兩性關系的哲學反思。
一、初入亞孟森——行為的規訓
在薇薇安乘坐火車前往亞孟森的路上,她遇到了一個“拎肉的女人”。當她和這個女人一起抵達亞孟森時,那些等待上車的女人都和這個“拎肉的女人”打了招呼,而當薇薇安跟著這個女人下車后,“所有人都移開了目光”[3]28。顯然,這個“拎肉的女人”在亞孟森中是持有某種“身份”的人,而薇薇安則像一個“闖入者”,所以她自從上車就承受著別人的打量和質疑。
“接下來是一片寂靜,空氣像冰。看上去一碰就碎的白色的樺樹皮上有黑色的印記,某種矮小雜亂的常青植物縮成團,像一只只瞌睡的熊。結了冰的湖面并不平坦,冰面沿著湖岸起伏,仿佛波浪在落下的一瞬間結成了冰。那邊房子的窗戶排得整整齊齊……”[3]28
彼時,初來乍到且懵懂天真的薇薇安正處于對新環境的浪漫幻想中——“如此寂靜,如此令人陶醉”[3]28。然而,微微安眼中亞孟森的自然環境實際上投射出缺乏律動和生機的現實環境,也預示了下文中亞孟森冷漠、疏離的人際關系和封閉狹隘的思想環境。在那個走在她前面的“拎肉的女人”眼中,薇薇安的沉默是可疑的。因此,她率先打破了沉默。當她得知薇薇安是新來的老師時,她說話的口吻就呈現出一種優越感——“不管怎么樣,他們不會讓你從前門進去的”,“你最好和我一起走。”“剛才你站在那兒的樣子像是迷路了。”薇薇安說自己停住腳步“是因為景色太美了。”“有些人可能會這么想。如果他們不是病得太重或太忙的話。”[3]29顯而易見,薇薇安忽視了這是一個伴隨著疾病和死亡的場域,她的天真爛漫和冰冷陰郁的療養院環境是格格不入的。
在跟著“拎肉的女人”進入廚房以后,薇薇安就開始接受一種“控制的模式”,“這種模式意味著一種不間斷的、持續的強制”[4]155——“你最好把靴子脫了,別在地板上留下腳印……把靴子拿起來拎著走……你最好穿著大衣,衣帽間里沒有暖氣。”“沒暖氣,沒電燈,只有從我夠不著的一扇小窗戶透進來的光線。”這一切讓薇薇安想到“這就好像在學校受罰,被關進衣帽間。”[3]28實際上,這個冰冷、黑暗、封閉的廚房衣帽間正是處于療養院權力透視下的“監視站”,在療養院,“一切權利都將通過嚴格的監視來實施”。[4]194接下來,被冷落的薇薇安“意外”發現了一個裝滿了無花果和棗子的包。此時的她饑寒交迫,然而,在思考了偷東西所違背的道德和被發現的風險之后,她放棄了偷吃的機會。就在此時,衣帽間里走進來一個女學生,她粗暴地扔掉課本、扯下頭巾、蹬掉靴子。昏暗的室內光線仿佛沒能讓她馬上意識到薇薇安的存在,而薇薇安卻瞬間覺察到自己所遭受的差別待遇——“顯然,沒人抓住她,讓她在廚房門口脫下靴子”。當這個叫瑪麗的女孩得知薇薇安是從多倫多來的新老師時,她說“我不知道他們為什么讓你待在這兒,這兒能把你屁股凍掉了。”[3]30這個直率、粗魯的女孩的話語表明薇薇安正承受著“權力的控制”。
療養院里的“權力活動中心”就是福克斯醫生的辦公室,他的“規訓權力既是毫不掩飾的,又是絕對‘審慎’的”。[4]200薇薇安被瑪麗帶到辦公室以后,福克斯一直以一種“年長的人的口吻”和薇薇安說話。[3]32這種居高臨下的口吻表明他急切地想要確定來自多倫多的薇薇安是否會厭倦療養院的工作環境。為了打消他的顧慮,薇薇安道出了自己初到亞孟森時的那種浪漫印象。她說這里很美,“就像——走進了一本俄國小說”。然而,這種浪漫的聯想卻引起了福克斯的懷疑和嘲弄。他追問,“真的嗎,哪一本俄國小說?”“那被逗樂的卻又咄咄逼人的表情”讓緊張的薇薇安在情急之中說出了《戰爭與和平》。當時二戰還沒有結束,微微安的回答又招致福克斯更具攻擊性的回應——“這兒只有和平,我得說。但我想如果你渴望的是戰爭,你早就參加了一個婦女組織,把自己送到海外去了。”毫無疑問,福克斯的話讓具有自我意識的薇薇安“感到氣憤和屈辱”。她當時就確定福克斯就是“那種會提些問題讓你掉進陷阱的人”。[3]32當福克斯覺察到薇薇安情緒的變化時,他略帶歉意地說,“好像現在每個年齡和資質合適的人都回到了體制當中”。[3]33福克斯所謂的“體制”,不過是為了實現對個體“行為”進行“精心操縱”,使個體“變得更有用時也變得更順從”的“權力機制”。[4]156因此,福克斯在交談中設置的言語陷阱都是為了實現對薇薇安的操控。在他明確了薇薇安的工作意圖之后,他安排薇薇安到護士長那里去了解具體事宜。
在療養院工作不到一個星期,薇薇安就發現了自己剛到療養院時所經歷的事情“極不尋常”——因為她“再也沒有見過廚房和工作人員用來放衣服和藏偷來的東西的廚房衣帽間”。[3]34此時她終于意識到自己成為了“被操縱、被塑造、被規訓的對象和目標”。[4]154從她進入亞孟森開始,就承受了旁人對“外來者”的矚目,那個“拎肉的女人”,也即主管廚房的人把薇薇安領到冰冷陰暗的衣帽間,讓薇薇安面臨“無花果和棗子”的誘惑和考驗,隨后出現的瑪麗把薇薇安帶到了福克斯的辦公室去面對他的審視,這一切顯然是精心設計的監視策略。薇薇安逐漸意識到整個療養院就是福克斯醫生掌權下的“規訓機構”。“醫生辦公室是不可涉足的地方,護士長辦公室才是問問題、發牢騷和安排日常工作的正式場所。”[3]34本質上,護士長辦公室就是實施“規訓監視”的“中繼站”,而整個療養院就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層級監視的空間”——福克斯-護士長-注冊護士-護士助理-看門人-“拎肉的女人”。這種“權力機制”使福克斯能夠洞察發生在療養院的一切細小事情。此外,福克斯的“權力力學”還體現在他給薇薇安提供的書面教學“指示”中,指示里表明:“慣常的教育理念不適合這里……完全忘掉打分這件事……忘記南美洲的河流……更應該教音樂、繪畫、故事……”[3]35這份文字說明詳細規定了薇薇安在具體教學活動中的行為規范。同時,這也是他“書寫權力”的體現。
不僅教學活動被操控,薇薇安的個人活動也會引人注目。因為住宿條件差,無法入睡的薇薇安只好在冰冷的下午離開房間。當她再次端詳療養院里的房子、樹木和湖泊時,她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當初是被“他們的神秘和威嚴迷住了”。[3]38這一切不過是封閉、狹隘的社會環境的假象。甚至,她這種隨意的“看湖”的行為也會惹人非議,讓旁觀者覺得她“沒有別的事做”。[3]39這種“把個人置于‘觀察’之下的做法”實則也是一種“規訓方法”。[4]254顯然,這些細致的規則、對生活和人身的吹毛求疵的監督,無不讓薇薇安感到壓抑,而這同時“又是規訓權力的一個特殊機制”。[4]199
二、深入亞孟森——思想的規訓
到了真正上課的時候,薇薇安發現那些患病的孩子在課堂上表現地溫順和心不在焉。他們似乎已經在福克斯慣常的“指示”下被規訓成了安靜聽話的樣子。這種服從和馴順的狀態讓薇薇安感覺到“臨時課堂里籠罩著失敗的陰影。”[3]36作為一個接受過高等教育且思想獨立的女性,薇薇安決心去改變這種沒有生氣的課堂氛圍。她從看門人那里找來了地球儀,開始以一種有趣且有序的方式教授那些曾被福克斯明令禁止的地理知識。事實上,薇薇安確實以一種熱情又謹慎的態度讓孩子們的精神振奮起來了。這種創新的課堂活動形式不僅體現了薇薇安作為一個獨立女性個體的創造性,也投射出她對“權力的控制”以及“那些權力所強加的各種壓力、限制或義務”[4]155的反抗。
但這種不服從操控的反抗行為很快就引起了福克斯的注意。當他走進薇薇安的課堂后,他沒有立即表示反對,而是加入到游戲中,用“一種怪誕的方式控制了課堂”。[3]37此后,福克斯改變了對薇薇安實行的監視策略,改由他本人執行對薇薇安的規訓。于是,他對薇薇安提出了共進晚餐的邀請。然而,福克斯提出的時間和薇薇安被邀請去看瑪麗演出的計劃沖突了。當薇薇安告訴福克斯時,福克斯身上再現了父權制社會中那種典型的男性氣質——“做出一切決定、主動采取措施、明曉一切事實”[5]17——“演出會很糟糕,相信我”,他甚至告訴薇薇安即使買了票也不意味著一定要去看。[3]43顯然,此時福克斯已經把薇薇安當成了一個“規訓個體”[4]213。 然而,他自己卻在約會當天遲到了。他對時間的控制也是其“權力技術”的體現。當他把薇薇安帶到他在亞孟森的住所之后,他又改變了規訓的手段,強化了“權力的效能”和“強制力”[4]227。他對薇薇安說:
“我是你的看門人和廚子。這里很快會變得舒舒服服,飯很快就好。不用幫忙,我喜歡一個人做。你愿意在哪里等呢?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客廳里翻翻書。你穿著大衣的話,那里不會冷得讓你無法忍受的。”[3]43-44
面對福克斯忽然的殷切和熱情,薇薇安顯然無法適從。她到客廳以后依然“感覺多多少少是被他命令過來的”。在薇薇安詳細觀察了客廳里的書以后,她發現“這些書暗示著主人渴望了解和擁有大量的各種知識。也許不是一個品味嚴格而固定的人”[3]44。此時的薇薇安堅定了自己的立場和聲音,在接下來的談話中,她冷靜且獨特的見解再次令福克斯側目。他一邊迎合著薇薇安的言論,一邊提出要為薇薇安準備一臺電暖器和一把鑰匙來方便她閱讀。這本質上體現了福克斯在規訓過程中彰顯的“謙恭而多疑的權力”,[4]193更甚者,在打探薇薇安的感情生活時,他直接提出“你有男朋友嗎?”[3]45這樣直白的問題。面對福克斯不斷拋出的問題,薇薇安一直小心應對,但福克斯很機警,他擅長試探和察言觀色,因此始終處于上風。為了“擊敗”福克斯,薇薇安把話題引向了福克斯的職業,而他無疑洞察了薇薇安的心理,所以做出了耐心細致的回答。當他對薇薇安說,“撒謊是可以被看出來的,你的臉會發燒”[3]46,此時的薇薇安已經在這場爭奪話語主動權的博弈中敗下陣來。最終,薇薇安還是被福克斯“那熱烈、微妙而機巧的懇求暗暗地打動了”。[6]253晚飯結束時,福克斯采取了更具侵略性的行動。“他把手放在了我的背上。手掌有力,五指分開,他幾乎是在用專業人士的手法估量我的身體。”實際上,不管是用餐時的談話、對身體的估量以及分別時福克斯留下的“倉促而熟練的突然一吻”[3]47都表明了他把薇薇安當成了要征服的“一個性伙伴”,“一個他用以探索他自己的他者”。[6]65這種“征服”也是一種規訓的手段。
盡管薇薇安在回味福克斯的行為時承認,“我喜歡那種感覺”[3]47,但真正面對福克斯家的鑰匙時,薇薇安卻沒有勇氣使用。她明白如果使用這個鑰匙,就要做好隨時面對福克斯的心理準備。在那種被觀察和規訓的權力空間中,“他是暴力、權力和堅定決心的化身”。[6]530她根本“無法享受任何平常的舒適,只能體會到讓人緊張和傷腦筋的而非令人開朗的快樂。”[3]47-48顯然,此時的薇薇安已經陷入了猶豫和掙扎。在來亞孟森之前,她是一個擁有著獨立追求和自主意識的女性個體,然而,亞孟森卻是一個“把女人限制在婚姻里面”[6]430的父權社會的縮影。療養院里那些和薇薇安年紀相仿的助理護士“大多結了婚,或訂了婚,或正在往訂婚的方向努力”。[3]34似乎只有結婚才能“既允許女性完整保持自己的社會尊嚴,又允許她作為愛人和母親獲得性的實現”。[6]379除了給自己找一個體面的丈夫,這些助理護士對什么都不感興趣。“任何在她們不知道的地方、不知道的人身上或不知道的時代里發生的事都必須受到懷疑。”她們“都不喜歡加拿大廣播公司”,“只要有機會她們就把收音機里的新聞關了,換成音樂臺”。[3]34-35但是,所有這些護士和助理都對福克斯醫生充滿了敬畏,這種敬畏是因為他們認為福克斯醫生“讀過很多書”并且具有“把人罵得體無完膚”的能力。[3]35薇薇安卻明白她們所敬畏的不過是福克斯醫生作為父權制社會化身的主動性和征服欲。一言以蔽之,這些不關心時事,在封閉、狹隘的療養院里安于現狀的女性正是規訓機構里被“馴服的”肉體。薇薇安身上依然保留的獨立意識使她還在抗拒這個封閉保守的“規訓空間”[4]162。
為了逃離這樣的環境,她甚至離開療養院,去亞孟森上的咖啡館里吃飯。她本以為自己在陌生的環境中“會感到更加自在,”但是她卻發現“咖啡館沒有女洗手間”。當薇薇安穿過啤酒吧的門去隔壁旅館找衛生間時,店里“飄出啤酒和威士忌的氣味”,還有能把人熏倒的“濃烈的香煙和雪茄煙霧”。薇薇安此時儼然意識到,即使遠離了療養院,依然逃不開由男性主導的規訓空間。這些啤酒吧里的男性“沉浸在男人的世界里,叫嚷著說他們自己的事,”他們“實際上很有可能更渴望暫時或永遠遠離女人。”[3]39由此,薇薇安發現,“這始終是一個男人的世界”。[6]69在亞孟森,根本沒有給女性個體預留自主生存的空間。薇薇安一直在規訓空間施加給她的“客體即他者角色和堅持自由之間猶豫不決”[6]56;與此同時,助理護士的取笑和慫恿使薇薇安漸漸被同化,那種成為“一個有男人的女人”[3]48的想法漸漸壓制和消減了她獨立自主的意識。
在第二次和福克斯約會的時候,薇薇安看到客廳里有一臺落了灰塵的電暖器,這個發現進一步打消了她的顧慮。當她被允許在廚房幫忙時,她甚至因為旁觀“他從容而全神貫注的模樣,簡練的動作”而心醉神往。此時她腦海中“閃現的一串串火花”和感受的“一陣陣寒氣”[3]49讓她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正在被征服。毫無疑問,她正處于一種“盲目崇拜的愛”[6]734中。在薇薇安快要屈從于福克斯的權威時,瑪麗突然闖進了他們的約會并且堅持為他們表演錯過的演出。但福克斯完全無視了瑪麗的表演,甚至粗暴地打斷了她。盡管瑪麗眼中盈滿了委屈的淚水,福克斯還是用絕情又嘲諷的話語把瑪麗送走了。
“他很粗暴。他如此粗暴,讓我吃驚。”——這是當時在場的薇薇安內心活動的真實寫照。雖然福克斯的言行令她感到震驚,但是當她想到福克斯是為了她才這么做時,她又為這件事感到愉悅。當福克斯回來的時候,她直接被領到了床上。福克斯對薇薇安是一個處女這一事實并不感到意外,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以破壞處女貞操這一必然行為,把那個身體毫不含糊地變成了被動客體,證實了他對它的獲取”[6]181,也完成了對薇薇安的規訓。
三、離開亞孟森——“主體”的喪失
在委身于福克斯之后,薇薇安就放棄了作為一個“自主”的人擁有的“主權”,“成為了一個被征服者,是獵物,是客體”。[6]733同時,她身上充分體現了一種屬于“他者”的“依附意識”[6]73。自從聽到福克斯說,“我真的打算和你結婚”,薇薇安就完全聽信了福克斯的安排——“極簡單的婚禮”“不用寫信告訴祖父母”“沒打算忍受有別人觀禮的儀式”“也不主張買鉆戒”“最好不要再一起吃晚飯了”……[3]53此時的福克斯(Fox)正如瑪麗給他起的綽號一樣——像一只狡猾的“狐貍”。在得到了自己的“獵物”以后,福克斯想盡所有的借口來逃避責任和壓力。然而,薇薇安對此卻毫無察覺。她不僅對福克斯的一切安排唯命是從,甚至還在別人取笑和逗弄她時表現得“沾沾自喜”,為自己要嫁給“一個外科醫生而感到激動”。[3]55她已經從一個“主體”變成“他的附庸”[6]491。當她想要“做一束捧花”時,也會首先想到“他會同意我捧一束花嗎?”[3]54她甚至打算隨時隨地為他“犧牲自己的羞怯感和自尊”[6]449。
然而,她想要做出的犧牲并未被已感到厭煩的福克斯珍視。當薇薇安沉浸在對未來的浪漫幻想中時,福克斯卻反悔了。“他說他無法把這件事做到底”“他只知道這是一個錯誤”。[3]57這樣的轉變讓薇薇安感到震驚和茫然。當她聽到福克斯對一個男性司機道歉時,她終于醒悟過來——告訴她真相的“是他和那個司機之間男人對男人的說話語調,他平靜而通情達理的道歉。”[3]57薇薇安終于明悟福克斯從未把她視為一個平等的存在,“她實際上也還是一直被規定為他者”[6]168。除了在規訓她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策略性的熱情和謙卑,福克斯身上更常見的是“漠視”她的“那種男性態度”[3]55。
接下來,福克斯繼續“發號施令”——“現在我開車送你去車站……給你買一張去多倫多的車票……我相當確定傍晚有一趟開往多倫多的火車……我會想出一個非常可信的故事……讓人把你的東西整理好……我會給你寫一封推薦信……”。相比此時迷茫又絕望的薇薇安,福克斯的語氣里有一種“輕松活潑的”,“如釋重負的歡快語調”[3]58。這種事無巨細的安排再次體現出福克斯身上那種“男性的權威”[6]676和精心計算的權力運作機制。最終,薇薇安絕望地登上了開往多倫多的火車。那種作為獨立女性殘存的羞恥心抑制了她想要跳下火車,跑到福克斯家里追問自己為何被拋棄的欲望。若干年后,薇薇安和福克斯在擁擠的人潮中相遇。福克斯那種“充滿了不安、警覺、和疑惑”的眼神再次喚醒了薇薇安沉痛的記憶。她在亞孟森不僅丟失了理想,丟失了愛情,也丟失了自我。
表面上看,薇薇安的悲劇是由于她對愛情的盲目追求造成的。本質上,她的幻滅是規訓社會“強迫她通過婚姻謀求社會地位和合法庇護”[6]426所導致的。文本中的福克斯正是亞孟森權力機制的縮影,他把自己的欲望投射在對薇薇安行為的監視、身體的征服和思想的規訓上,最終使薇薇安——一個懷揣著夢想和激情的女性個體成為了規訓空間中千篇一律的“馴順的”肉體。
門羅在故事結尾寫道,“關于愛,其實一切都沒有改變。”[3]61女性總是對愛情懷有浪漫的幻想和綺麗的憧憬,然而“真正的愛情應當建立在兩個自由人相互承認的基礎上;這樣情人們才能夠感受到自己既是自我又是他者”。[6]754《亞孟森》恰恰體現出門羅作品中“揭露的異性戀關系中的性別權力政治以及在此過程中女性對個體身份的探求”。[7]61作為一個溫和的女性作家,門羅所反思的不僅僅是愛情和權力、女性身份和生存,還有兩性和解共生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