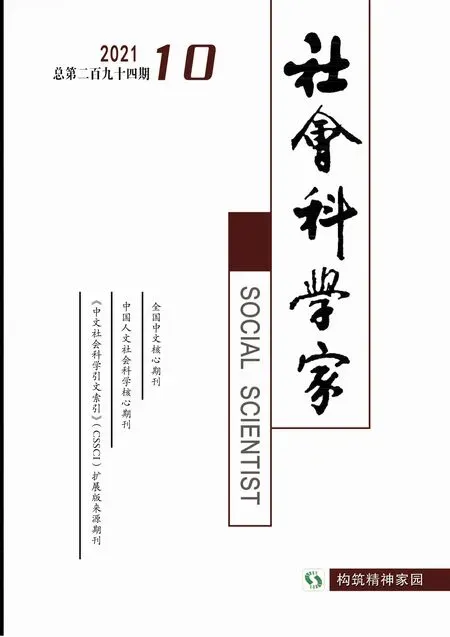“后理論”時(shí)代文藝學(xué)學(xué)科發(fā)展新論
——基于2020年的思考
趙華飛
(四川大學(xué) 文學(xué)與新聞學(xué)院,四川 成都 610065)
2020年是21世紀(jì)的第二十個(gè)年頭,也是全世界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沖擊的首個(gè)全球防疫年。2020年1月12日,世界衛(wèi)生組織正式將新型冠狀病毒命名為2019-nCoV(以下簡(jiǎn)稱新冠病毒),這一命名方式提示出以下饒富意味的事實(shí):人類不僅以“回溯”的方式把握過(guò)去,更以這一方式思考當(dāng)下、籌劃未來(lái)。但當(dāng)經(jīng)驗(yàn)事實(shí)的普遍性遭遇集中突發(fā)的不確定性時(shí),這一突發(fā)因素的全球化背景實(shí)際表明在人類生活與疫情之間的較量并非“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角逐,而是兩種“普遍性”的交鋒。疫情席卷全球后,齊澤克、朱迪斯·巴特勒、吉奧吉·阿甘本、阿蘭·巴迪歐、大衛(wèi)·哈維、讓-呂克·南希、羅伯托·埃斯波西托、布魯諾·拉圖爾、韓炳哲等理論家先后發(fā)表對(duì)于疫情的洞見(jiàn)與思考。齊澤克認(rèn)為,“病毒將徹底瓦解我們的生活基礎(chǔ),它不僅會(huì)帶來(lái)難以估量的傷痛,更將帶來(lái)比大蕭條時(shí)代更壞的經(jīng)濟(jì)震蕩。生活再也無(wú)法回到常態(tài),而我們只能從遭受蹂躪的舊日廢墟上復(fù)建一個(gè)新的日常。”[1]新冠病毒激活并更新了我們的“全球化”觀念。它迫使“全球化”從一個(gè)經(jīng)濟(jì)學(xué)或文化學(xué)概念轉(zhuǎn)化為每一個(gè)體的具身經(jīng)驗(yàn)。這一具身經(jīng)驗(yàn)層次的“全球化”以其不可否認(rèn)的具身性要求個(gè)體保持對(duì)于他者的充分關(guān)注與對(duì)話,從而彰顯出這一概念完全從感性層次表達(dá)人類整體狀況的內(nèi)在性。從世界范圍來(lái)看,多國(guó)的封城管理非但沒(méi)有隔絕人們之間的溝通,相反,借助于相似的“封閉”體驗(yàn),人們對(duì)于生存與命運(yùn)的感受從未如此接近。誠(chéng)如齊澤克所言,“我們?nèi)缃裨谕粭l船上。”[1]
如上所述,病毒不僅會(huì)帶來(lái)實(shí)質(zhì)的人身?yè)p害、經(jīng)濟(jì)破壞,更使日常生活與道德倫理面臨威脅與挑戰(zhàn)。但接受各種挑戰(zhàn),使倫理生活免于失序正是人的使命所在。李建中教授在疫情期間的網(wǎng)課導(dǎo)言中提出,“大寫的‘人’作為一個(gè)‘類’——人類,一旦進(jìn)入歷史就不會(huì)死去。或者說(shuō),人的精神和使命是不死的。”[2]也正因如此,疫情要求我們展開(kāi)對(duì)于自身與時(shí)代的深思。與嚴(yán)重、普遍的全球疫情相比而稍顯荒誕的是,近年來(lái)隨著生物科技的進(jìn)步與醫(yī)療革命的發(fā)展,人們的生命健康意識(shí)普遍增強(qiáng)。技術(shù)與生命間的關(guān)系也逐漸引發(fā)各界關(guān)注,“后人類”思想日漸成為國(guó)內(nèi)理論界的熱點(diǎn)話題。究其原本,“后人類”思想乃是一種主體性危機(jī)蔓延的表現(xiàn)。也正是在此危機(jī)之下,對(duì)于“意義”的不竭追尋才有了更加重要的價(jià)值。與此同時(shí),所有意義無(wú)不形成于歷史洪流之中,意義與時(shí)代間的張力同時(shí)要求一種更為開(kāi)放的人文觀念。因此,本文以下主要分三個(gè)部分對(duì)“后理論”時(shí)代下的文藝?yán)碚撍伎歼M(jìn)行評(píng)述。
一、新技術(shù)條件下的人文困境:從主體性危機(jī)到“后人類”反思
2000年以來(lái),隨著商業(yè)資本與媒介技術(shù)廣泛滲入文化知識(shí)領(lǐng)域,文化生產(chǎn)、消費(fèi)與傳播方式隨之經(jīng)歷重大調(diào)整。其中,以電影、視頻、互動(dòng)游戲?yàn)榇淼囊暵?tīng)媒介對(duì)于傳統(tǒng)媒介的擠壓與替代十分普遍,但此過(guò)程并不僅僅表現(xiàn)為文化傳播媒介的迭代與更新,還顯示出文化傳播過(guò)程中人與世界交互模式的深刻變化。文藝?yán)碚摷壹娂娬归_(kāi)對(duì)這一變化的描述與研究,如周憲便指出:在當(dāng)下電子閱讀時(shí)代存在一種從“沉浸式”到“瀏覽式”的閱讀轉(zhuǎn)向[3]。此類分析重點(diǎn)描述了“轉(zhuǎn)向”的發(fā)生,惜未就轉(zhuǎn)向之“何以”作出必要的理論分析,而究其何以不僅有望說(shuō)明某一“轉(zhuǎn)向”之緣由,也能由此廓清此一“轉(zhuǎn)向”與別一“轉(zhuǎn)向”間微妙而復(fù)雜的聯(lián)系,對(duì)于深刻理解變化中的時(shí)代因素,具有十分必要的價(jià)值。
正如時(shí)下日常所見(jiàn)的那樣:新媒介技術(shù)使不同時(shí)空的真假世界、虛擬世界以感性直觀的方式在我們眼前“直接”呈現(xiàn)。它們不僅沖擊了我們對(duì)于世界的故有體驗(yàn),也同時(shí)沖擊了我們將自身敘述為“一”的可能性。緣何如此?從闡釋學(xué)角度來(lái)說(shuō),人對(duì)于文本的闡釋乃基于其“前見(jiàn)”與“前理解”。也就是說(shuō),文本世界不僅實(shí)然地指涉了現(xiàn)實(shí)時(shí)空中的人及其世界,也正由于對(duì)此指涉關(guān)系的洞察,促進(jìn)了“理解”的真實(shí)發(fā)生。我們可以借助奧爾巴赫在《摹仿論》中對(duì)于“比喻”的論述,來(lái)進(jìn)一步分析這一“理解”的過(guò)程。奧爾巴赫認(rèn)為,“比喻”建基于一種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處于兩個(gè)事件或兩個(gè)人物之間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內(nèi),在此聯(lián)系中:
前者不僅指涉自身也同時(shí)指涉后者,后者不僅關(guān)涉前者也實(shí)現(xiàn)前者。聯(lián)系中的兩極獨(dú)立存在于時(shí)間中,但它們作為真實(shí)的事件與人物卻又共在于時(shí)間性之內(nèi),它們同在于歷史的生命之流,只有真正理解了它們彼此間的相互依存關(guān)系,理智的精神才是一個(gè)精神性行動(dòng)。[4]
可見(jiàn),“理解”作為精神性行動(dòng)要求一種對(duì)于文本與現(xiàn)實(shí)間“指涉”或“比喻”關(guān)系的理解。“比喻”也因此突破了修辭學(xué)內(nèi)涵,與“指涉”“理解”一樣期待一種主體性之于世界的實(shí)踐性影響,從而具有了存在論價(jià)值。“比喻”的存在論價(jià)值在美國(guó)學(xué)者喬治·萊考夫和馬克·約翰遜那里也得到了證明——盡管兩位學(xué)者是從語(yǔ)言學(xué)的角度切入分析,但同樣強(qiáng)調(diào)了“比喻”之于人類具有“賴以生存”之地位。可見(jiàn),當(dāng)我們還在“閱讀”“闡釋”世界時(shí),我們與世界間的關(guān)系便仍是比喻性的。這種“比喻”如奧爾巴赫所述,它是對(duì)兩種異質(zhì)世界間相互關(guān)系的體認(rèn)。其本身乃是協(xié)商性、對(duì)話性的歷史化過(guò)程。但“比喻”的這一過(guò)程在技術(shù)條件的無(wú)限迭代中被不斷壓縮成了直接“觀看”。不可否認(rèn)的是,“觀看”也是另一種閱讀,可當(dāng)不同“世界”在技術(shù)條件下目不暇接地“直接”出現(xiàn)時(shí),“理解”過(guò)程的復(fù)雜性便可能因響應(yīng)一種“觀看”的便捷性而被迫降低。尤其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此處先進(jìn)技術(shù)所標(biāo)示的兩項(xiàng)內(nèi)容深刻地改變了人對(duì)于世界的“理解”模式:其一,技術(shù)平面化所內(nèi)蘊(yùn)的去歷史化特征消除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對(duì)特定內(nèi)容進(jìn)行呈現(xiàn)的歷史面向。其二,先進(jìn)技術(shù)所標(biāo)示的“效率”與“速度”在這一“觀看”取代“比喻”的過(guò)程中發(fā)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同時(shí),“速度”并不僅僅只是物理尺度,正像保羅·維利里奧所提示的那樣,“速度”已經(jīng)成為當(dāng)代社會(huì)極為重要的文化變量,在地緣政治與生命政治間縱橫捭闔。可見(jiàn),當(dāng)“比喻”過(guò)程被要求“速度”與“效率”的“觀看”擠壓甚于替代時(shí),“理解”便不復(fù)是全然作為歷史化的“比喻”的“理解”。但“理解”畢竟是主體有關(guān)其與世界間關(guān)系的“理解”,因此,基于“理解”而得以成立的所有主體性敘述便同時(shí)在此影響下岌岌可危。而在媒介技術(shù)之外,生物工程與人工智能等尖端科技的高速發(fā)展,也在向人類主體性的傳統(tǒng)內(nèi)涵與地位發(fā)起挑戰(zhàn)。于是,人類終于在技術(shù)新變與資本運(yùn)作中成為理論視野中的“后人類”。
學(xué)者林秀琴?gòu)暮笕祟惖慕嵌确此剂水?dāng)下技術(shù)形態(tài)與人類主體性之間的張力關(guān)系。她認(rèn)為,經(jīng)由技術(shù)工具論、技術(shù)本體論到技術(shù)主體論的發(fā)展,技術(shù)身份不僅獲得重構(gòu),更對(duì)本質(zhì)主義主體性敘述形成了沖擊,從而建立起一種新的主體觀:后人類的主體是一種無(wú)中心、不確定、異質(zhì)性的主體。但林秀琴認(rèn)為后人類主義所強(qiáng)調(diào)的“去具身性”只是一種話語(yǔ)層面的理論預(yù)設(shè),主體之實(shí)存無(wú)法排除其現(xiàn)實(shí)身體。因此無(wú)論是“去具身性”對(duì)于主體的解放還是賽博空間對(duì)于經(jīng)驗(yàn)與權(quán)力的重構(gòu)都無(wú)法完全消解、取代現(xiàn)實(shí)領(lǐng)域內(nèi)的權(quán)力運(yùn)作。此外,她還指出虛擬主體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反思只有具備了足夠的批判性距離,才能成為建設(shè)性的“他者”。否則,賽博空間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的解放便無(wú)異于一場(chǎng)夢(mèng)囈。[5]
與林秀琴的看法不同,馬睿教授認(rèn)為“后人類”視野與思考或?qū)⒋龠M(jìn)人文知識(shí)話語(yǔ)的重置與更新。伴隨著全球化所激發(fā)的文化爭(zhēng)議,數(shù)字技術(shù)的爆炸式發(fā)展迅速波及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向科學(xué)、藝術(shù)、經(jīng)濟(jì)、政治、身體、意識(shí)等各領(lǐng)域不斷蔓延。她認(rèn)為,“面對(duì)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發(fā)展在社會(huì)文化各領(lǐng)域引發(fā)的經(jīng)驗(yàn)變動(dòng)和議題更新,有必要返回人類社會(huì)持續(xù)不斷的技術(shù)進(jìn)展這一基本事實(shí),返回人文知識(shí)與技術(shù)的持續(xù)互動(dòng)這一基本事實(shí),重新思考人文學(xué)科自身的發(fā)展路徑及其有效性,尤其是需要從學(xué)理上厘清基于啟蒙理性的人類觀與現(xiàn)代知識(shí)體系的根本關(guān)聯(lián)。探討人文知識(shí)超越現(xiàn)代性架構(gòu)、進(jìn)行整體性重置的可能性”。[6]馬睿重點(diǎn)考察并分析了數(shù)字全球化浪潮下的三個(gè)代表性領(lǐng)域,先后揭示出哲學(xué)層面上的主體及主體性危機(jī)問(wèn)題,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維度上的勞動(dòng)與資本問(wèn)題(“數(shù)字勞動(dòng)”引發(fā)的資源再分配問(wèn)題),以及新技術(shù)浪潮下的媒介與感性問(wèn)題。其后指出人工智能技術(shù)或?qū)⒂|發(fā)第三次知識(shí)形態(tài)的整體演變,并認(rèn)為在此意義上,后人類主義提出的以更新人類觀為核心進(jìn)而重建普遍知識(shí)的理論愿景是一個(gè)具有吸引力的起點(diǎn)。
二、焦慮中的探問(wèn):對(duì)“意義”的不竭追尋
可見(jiàn),“后人類”思想成為技術(shù)時(shí)代的理論熱點(diǎn),正是人類主體性危機(jī)的深刻表現(xiàn)。然而誠(chéng)如海德格爾對(duì)于語(yǔ)言及存在間關(guān)系的論述那般,人因分有語(yǔ)言而稱其為人。在此意義上,我們從來(lái)都是“講故事的人”。于是,一方面是飄搖的主體性:任何主體敘述在德里達(dá)所謂“延異”的困境中都將無(wú)可挽回地支離破碎;另一方面,“我們又生存于那個(gè)向我們講述故事而同時(shí)我們也向他人講述的世界之中”[7]。在此矛盾與焦慮中,碎片化、個(gè)體化的敘述如山洪奔涌、肆意傾瀉。但這些個(gè)體敘述在形式上的去中心化、去歷史化畢竟無(wú)法實(shí)然地將歷史從其自身完全清退,否則我們根本連其究竟為何都無(wú)從得知,又何以稱呼其為“碎片化”的敘述呢?因此,任何意義上的解構(gòu)都在歷史限定之內(nèi),正如斯圖亞特·霍爾所指出的那樣。
如果去除這種專斷的限定,世界上的“行動(dòng)”或者“身份”還有可能嗎?舍此,一個(gè)人還怎么斷定一句話是說(shuō)完了還是沒(méi)完?語(yǔ)言的延伸無(wú)窮無(wú)盡,其意指也永無(wú)盡頭,這些都是不用明說(shuō)的事實(shí)。但如果要確確實(shí)實(shí)地說(shuō)出某個(gè)特定事物來(lái),那么你必須停止繼續(xù)說(shuō)下去。當(dāng)然,一個(gè)再充分的停止都只是權(quán)宜之計(jì)。因?yàn)榈菆?chǎng)的下一句便有可能輕松抹除上一句的語(yǔ)言效力。所以這個(gè)“語(yǔ)言的停止”意圖何在?它標(biāo)示出語(yǔ)言的界限,標(biāo)示出想法,它說(shuō):“我要說(shuō)一些事情,一些確定無(wú)疑之事……就在此時(shí)此刻。”它當(dāng)然不是永遠(yuǎn)的界限,也不全意味著完全正確,它未曾受到任何給予無(wú)限正確之保證的支持。但就在此時(shí)此刻,在某種話語(yǔ)情境下,我們把這種未完待續(xù)的限定叫作“自我”“社會(huì)”“政治”等等。一個(gè)充分的停止,很好,確實(shí)。但就像有人說(shuō)的那樣,根本不存在什么充分的停止。以政治為例,如果缺乏權(quán)力對(duì)于語(yǔ)言的介入,那么意識(shí)形態(tài)的切分、定位、越界與破裂將無(wú)從談起。倘若缺乏語(yǔ)言的限定與停止,我將不再能夠理解政治言行。我甚至不知道它們何所由、何所憑。[8]
對(duì)于必要限定的接受,敘述與故事才有可能,身份和歷史才得以為繼。而所有“限定”與“停止”,都在要求敘述展開(kāi)對(duì)于意義的追逐。奧地利學(xué)者克里斯蒂娜·夏克特(Christina Schachtner)認(rèn)為,在敘述中,“何以有此一講”(how)是主導(dǎo)要素,它與故事“何所是”(what)緊密相關(guān)[7]。同時(shí),“敘述將各種事件、時(shí)間點(diǎn)、地點(diǎn)彼此整合起來(lái),由此構(gòu)筑為一個(gè)意義整體。這一整體包含著種種意義要素,當(dāng)這些要素被整合時(shí),便形成了一種并不具有內(nèi)在決定性的總體內(nèi)涵。”[7]當(dāng)然,對(duì)于“敘述”與“講故事”的理解也不應(yīng)僅僅局限于語(yǔ)言一途。夏克特認(rèn)為,“敘述”隨時(shí)、隨處可見(jiàn),甚至在留言和賬單上也可見(jiàn)。因此,雖然已經(jīng)來(lái)到了“理論之后”,但我們?nèi)栽凇艾F(xiàn)實(shí)之前”。“一切堅(jiān)固的東西”固然“都已經(jīng)煙消云散”,但展開(kāi)對(duì)于意義的追逐,卻仍是理論甚或人類的終極使命。文學(xué)意義在后理論處境中的地位,確實(shí)引發(fā)理論家的關(guān)注與擔(dān)憂。焦慮之外,有論者嘗試從全新的角度展開(kāi)對(duì)于文學(xué)及文學(xué)理論的梳理,由此展開(kāi)一種對(duì)于文學(xué)意義的全新關(guān)照。也有論者從文學(xué)藝術(shù)其“意義”的發(fā)生學(xué)層面對(duì)藝術(shù)作品內(nèi)涵進(jìn)行追蹤,還有論者從“交往”層面展開(kāi)對(duì)于文學(xué)意義研究之新路徑的探討,種種嘗試均可視為勇敢者的挑戰(zhàn)。
學(xué)者何成洲以“操演性”(performativity)為研究視角,察覺(jué)出西方文學(xué)理論從歷史語(yǔ)境化研究向文學(xué)介入性研究的具體轉(zhuǎn)變。通過(guò)對(duì)維特根斯特、奧斯汀、德里達(dá)、歐文·戈夫曼、朱迪斯·巴特勒等人理論觀點(diǎn)的梳理,何成洲提出將“操演性”引入文學(xué)批評(píng),實(shí)則是要以“作為行動(dòng)的文學(xué)”打破以文學(xué)文本為中心的文學(xué)研究范式,將“操演”與“文本”相對(duì)照與結(jié)合,揭示出文學(xué)意義生產(chǎn)的豐富性與多元性。他認(rèn)為薩義德《東方學(xué)》等著作中關(guān)于西方文化之于“東方”的建構(gòu),表明文學(xué)閱讀對(duì)于實(shí)際的文化認(rèn)知具有突出影響,并引述芮塔·菲爾斯基在《文學(xué)的用途》中的觀點(diǎn),提出文學(xué)研究的未來(lái)在于研究文學(xué)的使用,由此將突破文學(xué)研究對(duì)于文本意義之闡發(fā)或歷史語(yǔ)境之揭明等傳統(tǒng)范式。[9]
趙毅衡先生提出了“文本意向性”的觀點(diǎn)。他首先指出,“文本”乃是可以被揭示出一個(gè)合一意義的符號(hào)集合,并基于此將圍繞文本的意向性區(qū)分為:意識(shí)的發(fā)出意向性、意義的解釋意向性與居于兩者之間的文本意向性。他認(rèn)為文本意向性并非自明的意向性。通過(guò)對(duì)藝術(shù)學(xué)家萊文森與科拉克爭(zhēng)執(zhí)的分析,趙毅衡指出藝術(shù)作為人工制品,必定含有創(chuàng)作意向。但在藝術(shù)品成為其所是的環(huán)節(jié)中,藝術(shù)展示的重要性則被其他因素給遮蔽了。“在文化中,經(jīng)常是藝術(shù)展示(而不是創(chuàng)作),使文本得到?jīng)Q定性的意向。因?yàn)檎故締?dòng)了文化體制,把作品置于藝術(shù)世界的文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之中”。[10]換言之,在他看來(lái),正是藝術(shù)作品的展示意向性規(guī)定了藝術(shù)文本的意向性。接下來(lái),通過(guò)對(duì)“意向性”概念的學(xué)術(shù)史考察,趙毅衡指出“文本意向性”是符號(hào)文本體現(xiàn)出來(lái)的創(chuàng)造與展示意識(shí),是文本對(duì)解釋施加的文化壓力。也就是說(shuō),藝術(shù)作品的“展示意向性”指向一種文化范疇,只有把握這個(gè)文化范疇,才能把握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的“文本意向性”。
學(xué)者吳興明、張一驄認(rèn)為當(dāng)代生活世界中文學(xué)審美現(xiàn)象所顯示的意義品質(zhì),要求我們以交往論的思想視野對(duì)其進(jìn)行重新關(guān)照,進(jìn)而有望打開(kāi)文學(xué)研究新路徑。他們認(rèn)為,“無(wú)論是為消費(fèi)主義浪潮下的流行文學(xué)、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進(jìn)行合理化辯護(hù),還是展開(kāi)文化批評(píng),這些觀點(diǎn)的缺陷都在于:將文學(xué)的意義論窄化地集中在作品文本和讀者之間,本質(zhì)上還是一種主體哲學(xué)的單向視野。他們沒(méi)有注意到這樣一個(gè)維度: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和流行文學(xué)之所以在當(dāng)代生活世界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恰恰不是因?yàn)槲膶W(xué)作品作為意義媒介在讀者接受時(shí)的意義生成和重塑,而是文學(xué)作品作為交往媒介,在作為讀者的主體之間建構(gòu)起主體間平等的交往橋梁。”[11]
李怡教授提出了一種“地方路徑”的文學(xué)研究范式。他認(rèn)為當(dāng)前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所沿襲的外來(lái)沖擊/回應(yīng)模式需要改變。這一研究模式下的宏大敘述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對(duì)研究對(duì)象的總體性把握,但卻不利于厘清總體內(nèi)部不均衡、復(fù)雜、瑣碎的局部狀況,進(jìn)而提出應(yīng)從“地方路徑”的角度重審研究對(duì)象,進(jìn)一步挖掘與梳理中國(guó)社會(huì)與文化自我演變的內(nèi)部事實(shí)。他以李劼人的創(chuàng)作為例,說(shuō)明其小說(shuō)中所體現(xiàn)出的市民精神便根源于四川地域性的生活方式。此外,他認(rèn)為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區(qū)域經(jīng)驗(yàn),對(duì)此經(jīng)驗(yàn)的再挖掘,將不僅有利于我們對(duì)于區(qū)域演變的“地方路徑”的理解,更將獲得對(duì)于時(shí)代與歷史的深刻認(rèn)知,從而避免文學(xué)研究模式的單一化與表面化。[12]
三、對(duì)“文學(xué)性”的超越與回歸:沒(méi)有文學(xué)的文學(xué)理論
循前論可見(jiàn),對(duì)文學(xué)意義的追尋與探索,最終要基于具體的歷史條件與境遇。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由于經(jīng)濟(jì)模式的深入轉(zhuǎn)變,文學(xué)生產(chǎn)的外部環(huán)境發(fā)生劇烈變化,文學(xué)與時(shí)代要求間的張力逐漸顯露。20世紀(jì)90年代初,由于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對(duì)文藝領(lǐng)域的沖擊,隨之引發(fā)“人文精神大討論”。參與討論的知識(shí)分子紛紛表示對(duì)于人文精神喪失的憂慮。步入2000年后,國(guó)際資本對(duì)于全球市場(chǎng)的裹挾愈益深入,資本對(duì)于國(guó)別限制的沖破,一方面促進(jìn)了國(guó)內(nèi)政治、經(jīng)濟(jì)改革的調(diào)整與深化發(fā)展,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人們對(duì)于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條件下文藝本質(zhì)的再思與重審。與此同時(shí),錯(cuò)綜復(fù)雜的文化景觀開(kāi)始出現(xiàn),一邊是商業(yè)出版的日新月異,一邊則有人懷疑“文學(xué)已死”①美國(guó)學(xué)者希利斯·米勒的《論文學(xué)》(On Literature)在2007年被引進(jìn)時(shí),國(guó)內(nèi)出版社將其譯作《文學(xué)死了嗎》。其后圍繞“文學(xué)之死”的議題,張寧、張曉光、曾美桂等學(xué)者進(jìn)行了集中討論。由此可見(jiàn),即便其時(shí)“文學(xué)之死”的斷言只是基于某種程度的“誤讀”,但對(duì)文學(xué)“死亡”的預(yù)判與討論實(shí)則證明了時(shí)代與(傳統(tǒng))文學(xué)間的張力。。不僅文學(xué)被告終結(jié),一時(shí)間,從西方越洋而至的各種“終結(jié)”之聲喧嘩登場(chǎng),引發(fā)國(guó)內(nèi)理論界騷動(dòng)頻頻。
在“文學(xué)已死”的爭(zhēng)議背后,實(shí)則集聚了諸論者對(duì)于作為文學(xué)本質(zhì)之文學(xué)性的焦慮,對(duì)于作為“經(jīng)典”“傳承”的純文學(xué)處境的隱憂。然而正像學(xué)者劉大先指出的那樣:“當(dāng)精英知識(shí)分子反思‘純文學(xué)’的時(shí)候,他們可能無(wú)意識(shí)地依然在用一種源自18世紀(jì)的文學(xué)觀在進(jìn)行思考,在那種觀念中‘作者’是主導(dǎo)性的,并且有著‘干預(yù)’現(xiàn)實(shí)的能量,所以無(wú)論是李陀還是南帆,都是從文化與思想的創(chuàng)造角度進(jìn)入,而并沒(méi)有從文化產(chǎn)業(yè)與生產(chǎn)的角度進(jìn)入。但是,問(wèn)題在于,資本主義發(fā)展到這個(gè)階段已經(jīng)沒(méi)有外部,而文學(xué)則沒(méi)有內(nèi)部了。”[13]劉大先的評(píng)論提示出三個(gè)非常重要的問(wèn)題:其一,精英知識(shí)分子對(duì)于純文學(xué)的維護(hù)與擔(dān)憂,乃是一種本土的利維斯主義。正像伊格爾頓對(duì)于伽達(dá)默爾的批評(píng)那樣,我們似乎也可以發(fā)出以下疑問(wèn):純文學(xué)的傳統(tǒng)究竟是一個(gè)什么樣的傳統(tǒng)?“純”在哪里?又“傳承”自何處?其二,在新技術(shù)條件下的文學(xué)發(fā)展進(jìn)入到新階段之后,文學(xué)所期待的并非是對(duì)其本質(zhì)的再界定,也并非是依此界定為標(biāo)準(zhǔn)來(lái)爭(zhēng)取受眾的重新關(guān)注以便“死而復(fù)生”。它所期待的或許只是一種重新看待“何為文學(xué)”的眼光,因?yàn)槭聦?shí)上文學(xué)從來(lái)就未曾、也不會(huì)死亡。其三,變化已然發(fā)生。對(duì)于文學(xué)在其現(xiàn)實(shí)中的新處境,我們可以思考、質(zhì)疑、探討卻無(wú)法拒絕承認(rèn)其歷史現(xiàn)實(shí)性。抱守“文學(xué)性”進(jìn)而倡導(dǎo)“純文學(xué)”找回昔日榮光的呼聲只是一種帶有懷舊色彩的烏托邦理想。這種理想有其強(qiáng)烈的人文底色,但如果僅有人文精神而無(wú)現(xiàn)實(shí)關(guān)照,理想便不得不與其所理想之物一道滑落為虛構(gòu)。只有對(duì)處于現(xiàn)實(shí)進(jìn)程中的“文學(xué)表現(xiàn)”保持關(guān)注并進(jìn)行理解,才能進(jìn)一步思考文學(xué)之何以然、文學(xué)之何所為,也才能在具體歷史情形下發(fā)現(xiàn)解決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的可能性。因而也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理解成為一種真正的干預(yù)。
2004年,也就是在此番爭(zhēng)議方興未艾時(shí),金惠敏教授發(fā)表了《沒(méi)有文學(xué)的文學(xué)理論:一種元文學(xué)或者文論帝國(guó)化的前景》一文。文中對(duì)于在新時(shí)代條件下作為“沒(méi)有文學(xué)”的文學(xué)理論性質(zhì)的確認(rèn),激起多方爭(zhēng)議與討論。時(shí)隔十五載,2019年,金惠敏發(fā)表《闡釋的政治學(xué):從“沒(méi)有文學(xué)的文學(xué)理論”談起》。隨后,2020年末,《貴州社會(huì)科學(xué)》第11期同時(shí)刊發(fā)了《“文學(xué)性”理論與“政治性”挪用:對(duì)韋勒克模式之中國(guó)接受的一個(gè)批判性考察》(金惠敏撰)、《論文學(xué)理論的生成、功能和轉(zhuǎn)化》(章輝撰)、《“沒(méi)有文學(xué)的文學(xué)理論”:歷史、形態(tài)與公共性》(肖明華撰)等三篇文章。以上幾篇文章似是“舊事重提”,卻實(shí)然為“舊雨新知”,體現(xiàn)出關(guān)于“沒(méi)有文學(xué)的文學(xué)理論”這一理論命題的連續(xù)思考與公共闡釋。與近二十年的闡釋歷程相偕,歷史現(xiàn)實(shí)也發(fā)生了重大轉(zhuǎn)變。如果說(shuō)該命題首次被提出時(shí),它極欲突破囿限的理論氣質(zhì)使其在倡導(dǎo)文學(xué)純粹性的時(shí)代氛圍中備受爭(zhēng)議,因此尚屬理論前瞻的話,那么該命題在當(dāng)下的重提則不僅是對(duì)新千年以來(lái)文學(xué)研究發(fā)展境況的歷史總結(jié),更是一種現(xiàn)實(shí)要求與警醒。何以見(jiàn)得?
在《“文學(xué)性”理論與“政治性”挪用》一文中,金惠敏對(duì)韋勒克的在地化、語(yǔ)境化過(guò)程進(jìn)行了細(xì)密的梳理,并認(rèn)為“對(duì)于文論失語(yǔ)癥的焦慮,對(duì)于‘文學(xué)終結(jié)’于新媒介的哀嘆,對(duì)于文化研究的非美學(xué)指責(zé),對(duì)于‘美學(xué)復(fù)興’在‘日常生活審美化’中的期待,對(duì)于‘沒(méi)有文學(xué)的文學(xué)理論’的誤解,對(duì)于文學(xué)閱讀中理論介入的拒斥,對(duì)于西方闡釋學(xué)之無(wú)效于中國(guó)文本的指認(rèn),對(duì)于‘民族文學(xué)’和審美民族主義的捍衛(wèi),對(duì)于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是否為文學(xué)的懷疑,以及關(guān)于‘世界文學(xué)’是僅僅意味著越界還是必須作為經(jīng)典的爭(zhēng)論,等等,這些理論事件若是精細(xì)地磨洗辨認(rèn)起來(lái),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都游蕩著韋勒克內(nèi)外二分模式的幽靈。韋勒克仍然活躍在中國(guó)當(dāng)代文論之中,盡管未必總以‘在場(chǎng)’的方式。”[14]這一“韋氏模式”的始終“活躍”本身表明了一個(gè)狀況:盡管走過(guò)二十年,文學(xué)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的普遍介入并未在理論層面得到足夠重視與廓清,或被忽視被輕賤,或被強(qiáng)制闡釋在迷途。在廣義的文學(xué)表現(xiàn)與具體的理論研究中,它們本應(yīng)密切的聯(lián)系出現(xiàn)了中斷,且無(wú)彌合的跡象。如果說(shuō)當(dāng)年理論“失語(yǔ)”的提出更多源自“影響的焦慮”,而文學(xué)理論在今天的失語(yǔ)乃是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的失焦,對(duì)生活的失語(yǔ)。但本應(yīng)作為理論“失誤”的“失焦”與“失語(yǔ)”,不僅始終未被修正,還被某種更為隱蔽的文學(xué)本質(zhì)主義立場(chǎng)利用為批判工具。正是出于對(duì)此立場(chǎng)的抗辯與提防,金惠敏先生通過(guò)對(duì)于文學(xué)規(guī)律內(nèi)外之爭(zhēng)的歷史考察,說(shuō)明了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辯證關(guān)系,尤其指出當(dāng)“文學(xué)性”被“政治性”地挪用時(shí),論辯雙方未曾注意到的事實(shí)是:“文學(xué)性”已然不復(fù)他們眼中的“文學(xué)性”。“文學(xué)性”其意涵本身之能被消解,正說(shuō)明了這一概念本身的歷史局限性。
可見(jiàn),對(duì)此理論命題的重新討論確實(shí)基于一種現(xiàn)實(shí)關(guān)切。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沒(méi)有文學(xué)的文學(xué)理論”僅就其理論名稱而言確實(shí)具有“迷惑”意味。因此學(xué)者章輝在《論文學(xué)理論的生成、功能和轉(zhuǎn)化》一文開(kāi)篇便通過(guò)分析思維進(jìn)程的方式對(duì)“文學(xué)理論何以沒(méi)有文學(xué)”進(jìn)行了討論。他認(rèn)為“文學(xué)理論處于思維的中間位置,一方面,文學(xué)理論源于文學(xué)批評(píng)實(shí)踐,即實(shí)踐出理論,實(shí)踐出真知;另一方面,歷史上具有深刻影響的文學(xué)理論來(lái)自哲學(xué)家,如柏拉圖、康德、黑格爾、福柯、德里達(dá)等人都提出了深具影響力的美學(xué)和藝術(shù)思想。可見(jiàn),文學(xué)理論要么來(lái)自文學(xué)批評(píng)實(shí)踐,要么來(lái)自某個(gè)哲學(xué)思想體系,文學(xué)理論是派生性的,而非源生性的,其他思維領(lǐng)域成就了文學(xué)理論。”[15]學(xué)者肖明華則通過(guò)歷史梳理界定了“沒(méi)有文學(xué)的文學(xué)理論”產(chǎn)生的歷史條件、形態(tài)與公共性等問(wèn)題。他認(rèn)為自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理論研究領(lǐng)域的文化轉(zhuǎn)向?qū)嵢坏卮俪闪死碚搹奈膶W(xué)領(lǐng)域的“向外轉(zhuǎn)移”。在談及“沒(méi)有文學(xué)的文學(xué)理論”與“強(qiáng)制闡釋”的聯(lián)系時(shí),他指出“強(qiáng)制闡釋雖然號(hào)稱文學(xué)闡釋,但由于它對(duì)文學(xué)的闡釋恰恰是背離文學(xué)的,是不尊重文學(xué)的,以至于這種對(duì)文學(xué)的理論言說(shuō)事實(shí)上是‘沒(méi)有文學(xué)的文學(xué)理論’。”[16]肖明華在這里實(shí)際上區(qū)別了兩種“沒(méi)有文學(xué)的文學(xué)理論”:一種是“理論先行”“理論中心主義”的強(qiáng)制闡釋(作為一種背離甚于磨滅了文學(xué)生命的理論形態(tài)),另一種則是不囿于文學(xué)之內(nèi)而開(kāi)放于現(xiàn)實(shí)人生的“沒(méi)有文學(xué)的文學(xué)理論”。后一種理論形態(tài)名稱中的“沒(méi)有”,并非對(duì)于文學(xué)世界的拒絕,而是對(duì)于連同文學(xué)世界在內(nèi)的所有現(xiàn)實(shí)人生的邀請(qǐng)。
綜上,所謂“沒(méi)有文學(xué)的文學(xué)理論”乃是一種“沒(méi)有”偏執(zhí)于文學(xué)一端的“文學(xué)理論”。它并非對(duì)于文學(xué)的排拒,而意在強(qiáng)調(diào)理論的開(kāi)放性、對(duì)話性、可能性與現(xiàn)實(shí)性。因此,它既是對(duì)一種局限于追尋文學(xué)本質(zhì)之理論態(tài)度的質(zhì)疑與批駁,也同樣是對(duì)一種發(fā)展中的“文學(xué)性”的承認(rèn)與尊重。同時(shí),發(fā)展中的“文學(xué)性”也內(nèi)在地要求了一種更為開(kāi)放的主體性與人文性。因此,借由人文底色與人文關(guān)懷,“沒(méi)有文學(xué)的文學(xué)理論”乃是對(duì)于“文學(xué)性”的超越與回歸。
結(jié)語(yǔ)
2020年,身處“理論之后”與疫情之中的人類,在經(jīng)受一種日常的“非日常性”之同時(shí),不得不深刻反思自身的時(shí)代處境。雖然深陷重重危機(jī)之中,人類對(duì)意義的追尋永不會(huì)止步。此外,正像喬納森·卡勒在《文學(xué)理論入門》中就“理論”性質(zhì)所作的提醒那樣,文學(xué)理論應(yīng)始終以其“理解”實(shí)踐回應(yīng)于時(shí)代。而無(wú)論是文學(xué)還是文學(xué)理論對(duì)此意義追尋之旅的“捕捉”與“記錄”或許顯得有些“輕便”,但正如特里·伊格爾頓強(qiáng)調(diào)“詩(shī)是道德的陳述”那樣[17],文學(xué)形式倫理的意義在“條分縷析”之價(jià)值觀大行其道的當(dāng)代更有其鮮明的位置與內(nèi)涵。因此,德國(guó)大儒狄爾泰才會(huì)堅(jiān)信,“今天詩(shī)化過(guò)程的發(fā)生與過(guò)去無(wú)異。詩(shī)人們的創(chuàng)作,使他們的形象真實(shí)地呈現(xiàn)在我們眼前,這點(diǎn)便是明證。因此,詩(shī)化的過(guò)程機(jī)制,其心理結(jié)構(gòu)與歷史差異都能得到很好的研究。借助于詩(shī)學(xué)研究,歷史產(chǎn)物之得以產(chǎn)生的心理根由將得到細(xì)致地闡釋。而我們關(guān)于歷史的哲學(xué)概念也將從文學(xué)史的研究中得到發(fā)展。在對(duì)生活歷史的系統(tǒng)研究中,詩(shī)學(xué)定將發(fā)揮同樣強(qiáng)大的功效。”[18]身處當(dāng)下、面向未來(lái),我們對(duì)此亦懷深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