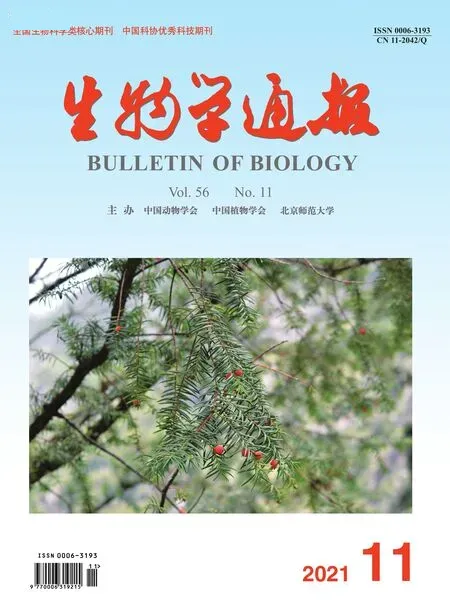華萊士:自然選擇學說的共同發現者*
劉鳳文 何風華
(華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院 廣東廣州 510631)
自然選擇學說被譽為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之一,作為以自然選擇理論為基礎的生物進化論的提出者和生物進化規律的發現者,達爾文因其《物種起源》的出版而享譽世界。然而,還有一位科學家在自然選擇學說的發現中也起到了功不可沒的作用,他就是華萊士——自然選擇規律的共同發現者。正是在華萊士的推動下,促成了達爾文《物種起源》一書的問世。華萊士和達爾文同樣都是探險家,與達爾文5年的環球旅行相比,華萊士的探險之旅長達12年,期間不僅發現了生物進化的機理,還采集了大量珍貴的標本,為當時及以后的自然科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素材。華萊士作為當時最為杰出的生物學家之一,對生物地理學的貢獻也是無與倫比的。在生物地理學中位于印度尼西亞、新幾內亞與澳洲之間,區分東洋區和澳大利亞區的分界線——華萊士線,也正是華萊士歷史功績的明證。
1 華萊士的2 次探險之旅
1.1 1848 —1862年的第1 次探險 1823年華萊士出生在英國威爾士南部的阿斯克,因父親投資失敗,家庭條件窘迫,為了謀生,華萊士被迫中途輟學。14 歲的華萊士跟著哥哥成為一名勘測員。在工作期間,華萊士對植物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后來由于勘測業不景氣,華萊士重新選擇職業,在萊斯特學院找到了教師職位。工作期間,在學校的圖書館里,華萊士閱讀了達爾文、洪堡等人的著作,并認識了一位對昆蟲學感興趣的年輕人貝茨。受錢伯斯發表的《創世自然史遺跡》的影響,華萊士萌生了尋找生物進化奧秘的念頭,于是他和貝茨一拍即合,一同踏上了探險之旅。從1848年起,華萊士在南美亞馬遜流域開始了4年的野外考察,期間收集了大量的動、植物標本,然而,這些珍貴的標本和資料在回英的船上因一場大火而所剩無幾,這對華萊士而言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但他并沒有因此氣餒,而是開始了下一次啟航。
1.2 1854 —1862年的第2 次探險 華萊士的第2次探險選擇了馬來群島,除了爪哇島外,其他島嶼還沒有人進行過透徹的調查,這對華萊士無疑是一次機會,從而彌補他因那場大火而帶來的遺憾。在長達8年的探險中,華萊士行程約22 400 km,幾乎踏遍了所有島嶼,收集了12.5 萬件標本,同時發現了許多新的物種,這批標本種類涵蓋范圍之廣,至今仍被認為是史上最重要的標本收藏,為許多科學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素材。
2 被遺忘的生物進化論發現者
1858年春,華萊士在考察中不慎患上瘧疾而發高燒。患病期間,他開始回憶在亞馬遜和馬來群島探險過程中所觀察的各種動物,思考著這些物種是如何適應環境時,突然想到了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一書中提到的疾病、災荒和戰爭等是控制人口穩定的因素,進而聯想到這些因素同樣適用于動、植物界,即優勝劣汰是物種進化的動力機制,這在本質上就是適者生存的核心觀點。于是,他將這些想法寫成了論文,并寄給了達爾文。達爾文閱后十分震驚,華萊士文章中關于生物進化的觀點與達爾文所持的主要想法存在高度的一致性[1],達爾文對生物進化理論的研究已有20年之久,如果華萊士率先發表,自己多年來的努力成果將大打折扣。達爾文經與好友賴爾和胡克爾商量后決定:將他的摘要和華萊士的論文一起送到倫敦林奈學會。1858年7月1日,在林奈學會會議上由學會秘書宣讀了達爾文和華萊士的論文,并發表在《林奈學報》上。這2 位“同時發現者”提出的以自然選擇為核心的生物進化理論開始受到學術界的關注[2]。隨后,達爾文加緊著手寫作,歷時13 個多月,于1859年完成了他的著作《物種起源》,該書發表后立即在當時的科學界引起了巨大反響,達爾文也因此作為進化論的奠基人,被后人譽為“科學進化論的奠基者”。當2 顆星星同時閃耀時,人們首先關注相對更亮的那一顆。相對于達爾文的“光環”,華萊士的名字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3 生物進化論觀點上的微妙差異
雖然達爾文和華萊士是生物進化理論的共同發現者,他們的觀點有著明顯的相似性,即以“自然選擇學說”為核心的生物進化論,但通過對二者在林奈學會上發表的論文進行分析和比較,發現他們的觀點存在一些微妙的差異。首先,在研究對象上,華萊士是對自然界的動物變異進行研究,而達爾文選擇的則是家養動物;其次,華萊士在文章中都是以動物為例,對其進化機制進行研究,而達爾文的研究對象則包括了動物和植物,比華萊士的研究范圍更廣;再次,對“生存斗爭”這一現象解釋時,華萊士更多的是與環境相聯系,而達爾文認為“生存斗爭”不僅是與環境有關,更多的是與種內斗爭相關聯。此外,達爾文還提出了“性選擇”這一第二理論,而華萊士的文章中則并未涉及。最后,2 人在文章中都提到了“變種”,但都沒有對其本質進行解釋[3]。
4 進化論和神學論的對立
達爾文和華萊士都認同物種是演化而來,但受宗教的影響,當時人們普遍認為生物是神創造的。隨著《物種起源》的問世,顛覆了人們對物種起源的認識,達爾文關于進化論的思想開始被公眾所接受。但仍有一些頑固的宗教勢力堅信物種是由上帝創造的,試圖阻撓進化論的發展。在這場進化論的保衛戰中,赫胥黎的加入成為了這場保衛戰的中堅力量。他在1863年發表的《人類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中提出了“人猿同祖論”,證明了人類并不是神創的,而是由猿進化而來的,人和猿有共同的祖先,進一步促進了進化論的傳播和發展。達爾文去世后,華萊士和赫胥黎仍然是達爾文進化論的捍衛者,在推動進化論的發展中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4]。
5 華萊士在生物地理學領域的貢獻
華萊士除了在生物進化領域作出貢獻外,在生物地理學領域也有卓越的成就。華萊士在馬來群島8年的探險與考察中注意到,在西邊印度馬來亞群系和東邊澳洲群系上棲息的動物種類存在巨大差異,代表著兩大動物區系,華萊士聯想到鳥類學家斯克萊特在全球劃分六大鳥區,這一劃分可能也適用于其他生物?于是華萊士將這2 個區域用一條假想線分隔開來,這就是影響至今的“華萊士線”。不久后,華萊士確立了六大動物地理分區,這就是現在生物8 個生態區的前身,1876年華萊士發表的《動物的地理分布》,確立了他成為現代生物地理學之父的地位[5]。
6 結論
華萊士不僅在生物進化和生物地理學領域作出了卓越貢獻,同時,他還扮演著博物學家、探險家等多種重要的角色。華萊士是一位樸實謙遜的科學家,也是達爾文的忠實支持者,雖然他們是生物進化規律的“同時發現者”,達爾文因《物種起源》而享譽世界,華萊士卻被人們淡忘了。但他并不介意,而是謙虛地將“優先權”讓給了達爾文,華萊士對達爾文非常的感激,認為如果沒有達爾文,自己的研究成果將被淹沒。同時他還大力宣揚達爾文的學說,他用“達爾文主義”作為達爾文自然選擇學說的代名詞,并在后世流傳。華萊士來自社會底層,沒有接受過正統的教育,但憑借著對科學的熱愛和自身不懈的努力奮斗,在科學界作出了卓越的成績,為人類留下了寶貴的科學財富。為紀念這2 位自然選擇規律的“共同發現者”,林奈學會設立了達爾文-華萊士獎章,同時,華萊士還獲選為對科學家而言代表著最高榮譽的皇家學會會員[6]。華萊士雖然對于大眾而言鮮為人知,但在學術界卻從來沒有被真正忘記。華萊士作為生物進化論的催生者之一,及他為科學界所作出的卓越貢獻,不應僅在學術界傳頌,而應該讓更多的人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