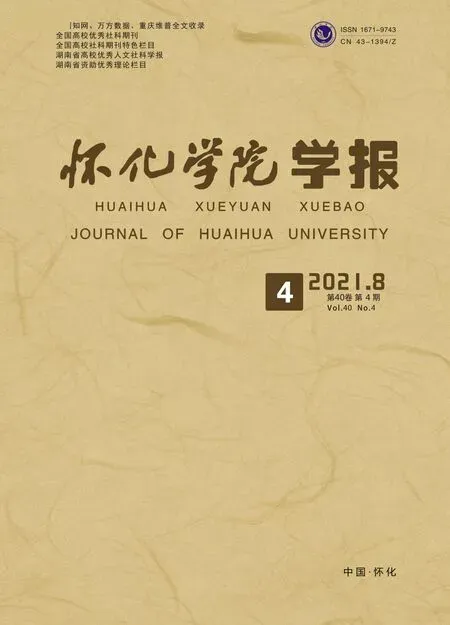“空白” 與“非空白” 的辯駁
——明代前期通俗小說批評形態分析
齊曉倩
(湖南理工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學院, 湖南岳陽414000)
引言
在通俗小說批評史上,關于明代通俗小說批評的發端有如下提法,王先霈、周偉民在《明清小說理論批評史》 中提出:“庸愚子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序》,既是小說理論批評史上第一篇通俗長篇小說的專論,也是現存最早的論述《三國演義》 的特點和意義的文章,它開長篇小說評論的先河。”[1]56陳謙豫在《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 中也提道:“他(庸愚子)弘治甲寅年寫的這篇《三國志通俗演義序》,是我國今見最早的一篇關于歷史演義小說的專論。”[2]33另外,陳洪在《中國小說理論史》 中提道:“倒是明初幾部文言小說集引發文人紛紛作序,揭開了中國小說理論史正戲的帷幕,然而,接下去又是近百年的沉寂。明中葉,由正德到嘉靖,情況稍有好轉,陸續有幾篇小說序言刊布,但理論上的進展卻并不明顯。”[3]41其中與通俗小說批評相關的 “序”,列舉到了弘治七年(1494年)蔣大器(庸愚子)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序》、正德三年(1508年)林翰的《隋唐兩朝志傳序》 和嘉靖元年(1522年)張尚德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引》。由此可見,庸愚子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序》 作為明代通俗小說批評的發端是學界共識,這一發端的表現是以“序” 為批評文體、以顯性方式存在的“理論形態”。自此,中國古代通俗小說批評形式就近似于序跋體、筆記體、評點體等,而且隨著原發資料的發現和整理,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批評形式構建了中國古代通俗小說理論批評體系的大廈。然而,中國古代通俗小說理論批評的現有格局即是古代通俗小說批評的整體嗎?如果成立,那么自洪武元年(1368年)明王朝建立到弘治七年(1494年)這126年則不得不稱為是明代前期通俗小說批評的“空白期”。
從理論上講,此種“批評空白” 是“狹義批評”范疇內的理論界定,其理論依據是源于“理論形態”批評資料的缺失。“批評往往是閱讀之后的感想的表示……這種感想的表示按照傳統當然是訴諸口頭語言或者文字的,某些超出這個范圍的表示方式,恐怕文學批評未必敢于問津。”[4]4所以受傳統批評觀念的圈囿,批評家基本上是由一些教授、學者、專職文學研究人員組成,批評表達都是如《三國志通俗演義序》 等以理論形態呈現的直言式,以諸多“批評文體” 為載體的文本形態,被稱為 “文體式”理論批評形態。然而,“理論形態” 的批評材料僅僅是批評 “形態” 系統中相對穩定的靜止資源,何況批評不同于創作,創作須以具體的顯性的姿態表現自身,但批評既可以顯性表達,也可以隱性呈現。創作可以 “空白”,但批評無 “空白”,既是 “空白”,也是一種極端化的批評表達方式,何況明代前期的 “創作空白” 仍處于爭議之中。僅僅依據 “理論形態” 批評材料的有無判定批評的 “在” 與 “非在”,勢必導致批評形態格局描述的片面。本文擬從“批評空白” 的反面,以“形態” 視域來觀照明代前期通俗小說的批評狀況,用平等的眼光、俯視的姿態和廣域的視角,探析明代前期通俗小說批評形態的多樣性。
一、“創作” 與批評
學界普遍認為,以成書于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 和《水滸傳》 為標志,通俗小說的創作手法實現了 “平話” 到 “章回體” 的轉變。只是這樣一種重大的轉變自產生后卻沒有了回響,直到一個半世紀后的嘉靖朝《三國演義》 被刊刻,才在社會上流傳較廣。因此學界定義,從元末明初《三國演義》和《水滸傳》 的產生到嘉靖之前這段時期為章回小說的 “創作空白” 期。此提法一度引來極大爭議,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兩種。其一秉持 “主觀說” 來支持“創作空白”。此觀點認為“空白” 是由文學自身形式貧困原因導致,“從文學自身來考察,明前期新舊文學樣式正處于青黃不接的交替狀態,缺乏既具有生命力又富有表現力的文學樣式,這是造成本期文壇沉寂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5]。其二是以歐陽健為代表的“客觀說”。他曾專門撰文《非“明代前期通俗小說創作空白論”》 駁斥 “創作空白” 說,明確指出這種論調的 “文獻依據是現存的長篇通俗小說都只有嘉靖之后的刊本……理論假設是歷史上產生的通俗小說,全都得到了妥善的保存,無一湮沒,無一損失”[6],并指出沒有看到不證明沒有存在過,解釋原因有三:一是自然災害;二是人為的強力禁毀;三是觀念上的鄙棄。“且不說水、火、蟲、兵等災患對古籍的嚴重損害,也不說歷代統治者對小說的瘋狂禁毀,單是對于通俗小說根深蒂固的傳統偏見,就是古代小說大量湮沒的根由。通俗小說固然受到普通讀者的歡迎,但越是暢銷的東西就越容易湮沒,因為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閑書’,誰也不會鄭重地加以收藏;官私藏書樓閣一律不收平話小說,就是最好的證明。”[6]
針對這兩種意見,筆者認為,文學由于自身發展的原因——“形式的貧困” 所造成的只能是章回小說發展的不景氣,體現的應該是數量上的多少,而不應是創作的有無。通俗小說發展到明代,其文本形態為章回小說、話本小說以及擬話本小說等。單就章回小說而言,它在宋元長篇講史平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是對 “說話” 中 “講史” 題材的記錄整理,經過若干代人的不斷累積改訂,最后成就于一位作家之手。相較于“平話”,這類作品的藝術表現力雖有所提高,但仍存在諸多局限,如題材狹窄、人物形象類型化、敘述視角單調和體制缺乏規范等。它作為新興體制,畢竟是處在生長過程中,承繼中有發展,而且這種發展和完善是有軌跡的。以回目為例,嘉靖元年(1522年)刊刻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回目是七言單句目,而且上下目之間的文字字數不一。之后出現的楊氏清白堂刊本的《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各卷回目由單句發展為了上下兩目,由于字數不等,難以形成對仗。發展到1553年楊氏清江堂刻本《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回目則對仗精工。由此觀之,章回小說體制的完善是逐步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處于生成期的章回小說體例的不完善和形式貧困阻礙不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形成全面繁榮的局面,否則《三國演義》 和《水滸傳》“發端即成經典” 的現象無從解釋。何況“文學不能歸結為若干部杰作”,“如果不是有成千上萬很快就將湮沒無聞的作品維持著一種文學生活的話,那就根本不會有文學,也就不會有大作家”[7]9。所以如今留存的元末明初的幾部通俗小說是一個時期內通俗小說存在狀態的縮影,因其 “經典” 才得以留存。而對通俗小說的批評,也正是以隱性的方式蘊藏于通俗小說體例歷史生成與演變的 “互文本” 中,潛在地詮釋了通俗小說的文體特征。“實際上,很大一部分文學批評并未和人們距離得那么遠,這些批評甚至就活躍在人們身邊,伸手可觸。我們不該僅僅盯住云端里的高聳的頂峰而遺忘了底下的平緩山坡,更不該遺忘這些平緩山坡恰恰是那些頂峰的起始。”[4]1由此看來,在某些歷史階段,一些重大轉換的完成并不是通過突變與漸進過程的中斷實現的,而主要是靠量的逐步積累才得以完成的。而這種量的積累除了分布在顯性的批評文本形態中,還分布在大量的通俗小說的文本中,通過 “互文” 方式呈現對明代通俗小說的批評,形成明代通俗小說的初始形態——“創作式” 批評形態,以作家為批評主體、以創作文本為批評表達媒介的批評形態。
此種形態的批評在醞釀期的話本小說和章回小說生發期還略顯朦朧,但隨著通俗小說民間傳播速度和廣度的加劇,在《三國演義》 《水滸傳》 等章回小說以各種形式民間流傳促成的文本形態演進中已足夠清晰。進入明代中葉,隨著《三國演義》 等小說的普遍刊行,章回小說中所呈現出來的 “創作式” 批評更是顯而易見。此種形態的批評表達不同于基于慣性的 “直言式” 批評話語,它是以內化方式將對一定時期通俗小說觀念、功用和價值的認識嵌入作品各要素的審美組合中,以踐行方式實現著對通俗小說創作的體驗式批評。尤其是文人的自覺參與,通過素材提煉和藝術編排所構建的通俗小說寫作范式,其濃縮的小說美學思想足具時代特色和批評意味。雖然 “創作式” 形態的批評深深蘊藏于作家的審美經驗中,缺少堅實的理論概括,所包含的評價與判斷還有需要進一步解釋的地方,但是“理性和審美經驗毋寧說是我們看待世界的兩種不同態度和方式,他們可以互相說明,相互驗證,但不會相互替代”[4]9。縱觀通俗小說批評的漫長發展史,雖然自明代中期以來所形成的各種批評文體對于考察范圍、研究地域都有所分工,建樹斐然。然而這些洋洋灑灑的文學批評理論并非凌空而降,它們的種子早已埋藏在通俗小說批評的初始隱性形態——“創作式” 批評之中。至此,“創作式” 批評的挖掘針對所謂“批評空白” 的意義更為突出。
二、“現象” 與批評
除了從文本和文本中的互文本比較中生產批評之外,新歷史主義開創了 “大文本” 概念。在此基礎上,“文本” 被進一步擴展,形成了“廣義文本”概念——某個包含一定意義的微型符號形式,如一個儀式、一種表情、一段音樂、一個詞語等,它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非文字的,這種意義上的文本相當于人們常說的“話語”,是人們組織現實事物的最基本的符號形式,而且廣義文本無處不在[8]99。廣義文本概念的提出和顯著特征為批評形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視角,不但作家創作的文學文本可以生產批評,就是存在于文學文本周圍的一些現象、活動也可以作為廣義文本對待去考查其呈現的批評狀況,因為它們之間具有同構性。
從通俗小說檢索目錄可見,明代前期 “話本小說” 的生產和傳播出現了和宋元時代不同的現象。現象一:“說唱詞話” 之類的通俗小說在成化年間得以復蘇,其生成方式是由明人整理加工宋元話本小說后以合集的形式開始在社會上流傳。而且在明代中期出現的最早的兩部話本小說集《六十家小說》和《熊龍峰刊小說四種》,以合集的方式表達了話本小說結束了單篇作戰的歷史,以不同于宋元時代的傳播方式展示了勃興的自信。現象二:這些整理刊刻的話本小說集子雖大部分收錄的是宋元話本小說作品,但從刊刻內容上看并非完全是宋元話本的復制,而是明顯加入了明人改編時的理解和評定,顯示了在宋元話本小說范疇下的延展態勢。現象三:盡管明人自創的話本小說數量有限,但也形成了明代話本小說的新氣象,即文人 “擬話本” 的出現。明代前期話本小說處于生產方式從整理口頭說唱內容轉向模擬寫作這一趨勢的醞釀時期,雖未成熟,但已具有話本小說進入主流文學殿堂并獲得普遍認可的前兆,作品的數量與對其態度仍然呈現出反比例關系。這些現象顯示,在通俗小說文本形態的不同歷史階段對比中,明代前期對通俗小說的批評一部分表達是蘊藏于時代 “現象文本” 中,雖仍如宋元時期以隱性方式呈現,但由于增添了時代意味,凸顯出明代對通俗小說認識的深化。而且這種 “現象文本” 的批評表達,其規模和特征足以作為一種“形態” 成為明代前期通俗小說批評形態格局中的一部分。
進一步追究,“現象式” 批評的生成與通俗小說獨特產生機制有密切關系。明代通俗小說除了話本小說之外,章回體作為明代通俗小說的主流形態,其產生擁有獨特機制———“編創” 的寫作方式。早期章回小說多屬于“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其成書方式主要有“滾雪球” 式與“聚合” 式等[9]。此種成書方式表明,早期章回小說的產生并非作者獨創,而是依據一個先行底本,在作者文學觀念的指導下,對題材、人物、情節等文學元素重新進行合意化處理。處理之后產生的新舊文本之間的差異,自然是作者對舊文本閱讀接受基礎上批評表達產生并寄藏的所在。“編創” 方式多發生在通俗小說產生的初期,后發展為改訂、重寫、續寫、評改等多種創作手法,其批評性也是顯而易見。因此,早期通俗小說批評的產生有一部分是發生在依據 “前文本” 的“新文本” 創作現象中。此現象所隱含的批評表達同樣不以理論話語現身,只是通過具體操作彰顯,但在歷史語境下,它圍繞“文學文本” 以“現象文本”形態出現,與 “文學文本” 相互交織共同傳達著對通俗小說批評的同構性效果。此類 “現象式” 批評文本雖然不是批評主體專門針對某一文學作品或文學現象做出的理論思考和書寫,但其中所滲透的批評思想仍然是批評觀念傳達的一種方式,又因其在明代具有一定的規模和影響力,因此可以成為明代前期通俗小說批評的一種形態——“現象式” 批評。
三、“禁毀” 與批評
“禁毀” 作為強權政策下的文化現象,也屬于特殊的文學現象,造成 “創作空白” 的同時卻成就了“批評” 的凸顯。正如重光《畫筌》 所言:“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空白” 之處自有妙處。所謂 “創作空白” 的形成除了文學和批評自身傳承因素外,更多的關乎客觀的文化環境。明代前期不僅通俗小說比較慘淡,就是整個文壇也蕭索一片。學者已紛紛考證出這與明代前期官方的高壓政策有很大關系,有官方的一系列律令為證,曾被學界頻繁引用。
《大明律》 規定:
“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裝扮者與同罪。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者,不在禁限。”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榜文云:
“在京軍官軍人,但有學唱的,割了舌頭。倡優演劇,除神仙、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不禁外,如有褻瀆帝王圣賢,法司拿究。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球的卸腳。”
永樂九年(1411年),朝廷頒布榜文:
“今后人民、倡優裝扮雜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瀆帝王圣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但這等詞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凈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
關于通俗文藝的是與非、存在還是禁毀處在天平的兩端,其命運就把握在判斷當中,而判斷中的強制切斷是對包括通俗小說在內的通俗文藝批評進入明代前期的另一種表現形態———“禁毀式”批評。由官方律令可見,具有震懾性的文化肅殺令限制了通俗小說的生長空間,使通俗小說的批評以顯性方式呈現更無實現可能性。但對通俗小說的批評并未因此泯滅,相反更有多方表現。一是禁毀政策本身就是官方對包括通俗小說在內的通俗文藝的批評表達,對文本、思想和傳播各個環節的控制已上升為了官方意識形態;二是反其道觀之,禁令的嚴酷程度直接折射出民眾對通俗文藝接受的踴躍。遭到“禁毀” 一方面是源于其影響力,說明通俗小說已經具有極大的社會影響力和受眾群,是通俗小說通俗性特征的凸顯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功能擴大化的極大體現。另一方面透露出通俗小說的思想具有和主流文化內容相背離的傾向,“禁毀” 政策的實施一定程度上是對通俗小說思想內容的揭示。因此,“禁毀” 所形成的“創作空白” 并不是“批評空白”,而是通俗小說的審美特征、社會功能以及讀者接受狀況等批評內容的無聲闡發和反彈性呈現,所形成的“不評之評” 雖然沒有直言性的批評話語,但這個表達的批評效果更甚于直言。
結語
綜上,明代前期被學界所確定的 “批評空白”并非概念上的真正 “空白” 狀態,只是緣于 “批評形態” 研究視域的“遺漏” 和 “缺失”,使得隱性批評方式被忽視造成的。實際上,在顯性批評形態出現之前,此時期對通俗小說的批評已在從容、平靜地進行,呈現為隱性形態,表現于立足作品中的“創作式” 批評、操作層面的“現象式” 批評以及附著于強權政策下的 “禁毀式” 批評,與顯性 “文體式” 理論批評形態形成交融互補的立體格局。這種格局的建構有利于增強文學批評活動的交互性,顯現批評話語權的博弈。通俗小說進入明代雖有所發展,仍難登大雅之堂,對其批評也迫于時代文學觀念、文化政策以及個人選擇的影響,憑借不同媒介形成了多樣批評文本,在不斷復雜化的文藝機體功能系統中,按照一定的排列方式,以交互姿態融相合或相左的理論觀念,在多維視野中形成邏輯聯系,潛在地匹配著讀者接受度。因此,進入明代中后期,隨著通俗小說的勃興,通俗小說批評也逐漸活躍起來,呈現出多角度、多層次的批評發展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