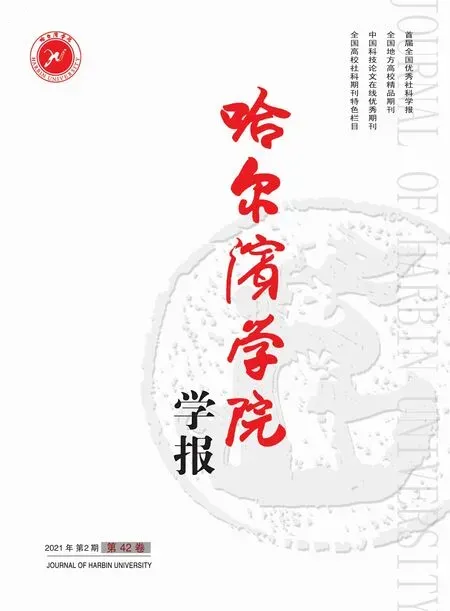論嚴歌苓小說《陸犯焉識》的悲劇意識
蘇 曼
(阜陽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基礎教學部,安徽 阜陽 236015)
美籍華人作家嚴歌苓創作的一系列文學作品中,《陸犯焉識》稱得上是她的巔峰之作。作者以一個小女孩即主人公陸焉識孫女的視角,講述了祖父經歷社會運動、牢獄之災,死里逃生,沉淀內心重新愛上他的發妻的故事。小說是在一種悲情的長河中緩緩流淌出文字來講述發生在陸焉識身上的一切。文章充斥著悲涼、苦難、煎熬卻不得不將生活繼續下去,來完成自己內心對自由、對愛的堅守。魯迅先生在《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指出:“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1](P297)《陸犯焉識》以緩慢的、平靜的、不張揚的方式將社會、時代和個體等創傷面一點點展示于人。“悲劇意識是對人類生命在世生存的悲壯性的意識,生命悲壯性是由人類既有生存發展的強烈欲望又沒有達到目的的可靠能力,只能依憑追求生存發展的意志和有局限性的能力冒險在世這一生存處境決定的。”[2](P1)在悲劇作品中,書中的主人公遭受磨難,放棄尊嚴,以求獲得生的權利。在生存成為厚重愿望的同時,理智和情感伴隨著焦慮、恐懼、不舍。嚴歌苓在小說《陸犯焉識》中,直面當時大環境下知識分子的生存遭遇,用現在和過去兩條時間線穿插敘述,展示出她對生命存在價值、愛情、親情、友情的思考,透露出一種悲涼之美。
一、悲劇意識的根源
作者嚴歌苓,1959年出生在上海,12歲進成都軍區文工團。少年時期的嚴歌苓家境衰敗,父親成為“反動作家”。在她的回憶中,父親被下放到農場,與家里失去聯系長達一年。這段經歷為作者創作提供了歷史背景素材。后來父母離異,成為她成長中最大的心靈創傷之一。她覺得在那個年代,父母的離異使她倍感恥辱,變得更加敏感,更加依靠自己的直覺去判斷人的善意和惡意,讀人的神色近乎出神入化。在《陸犯焉識》小說中,作者多次將自己的經歷感受用到對人物想象的描寫中:
“‘我必須請假去、去、去、去、去……場部禮堂。’五個‘去’字為他贏得了時間——察言觀色、見風使舵所需要的時間,容他根據‘鄧指’的反應及時編輯修正下的時間。陸焉識看見‘鄧指’的眼睛里沒有壞脾氣,無非有一點兒惡心,正派人物對于反派的正常生理反應。”[3]作者在寫作中借助主人公利用這短暫的時間去判斷對面人物的內心,倘若沒有敏銳的洞察力是無法完成想象和揣摩的。童年的遭遇是嚴歌苓形成悲劇意識的主要原因,作者將自己的經歷過往一點點滲透到人物的性格中去,將謹慎膽小刻畫的細致入微。在這種遭遇下,作者又賦予了人物內心的追求——活下去的動力,意識到自己的生存處境,正視生命中的悲劇,在意志的驅動下,完成冒險。悲劇意識自身就包含著對自由的向往。
嚴歌苓在訪談中曾經講到,她在再婚的父親和再婚的母親家里住過,有種異鄉人的感覺,那種加繆小說中的陌生人的感覺。作者在小說中講述陸焉識被平反后歸家的狀態,本是給予溫暖、給予愛的地方,卻生出了寄居者的心態。無論是自己內心的自覺,還是家人表現出的那般“施舍”,無不在敲打著“歸者”的心。客觀的身份改變不了,主觀上的心境已從“家人”的角色轉變為“客人”。沒有身份過渡,敏感的心及時的提醒自己瞬間完成角色的轉換,內心的愛與渴望頓時冷卻,反而更加平靜。作者的早期經歷成為她在小說創作中寶貴的素材,賦予作者對人物、對生活獨特的理解。嚴歌苓在采訪中也說道:“我人生的悲劇感,喜劇感,荒謬感都來自這種不夠真實的倫常關系。現在我到了這歲數,可以勇敢地誠實地來反省這樣的感情,并誠實而勇敢地把它們表現出來。虛構幫助了我面對這些感覺,正因為我的虛構本領越來越大,我才能在虛構的人物和故事里保持自我真實。虛構給了我形而上的自我真實。”
《陸犯焉識》故事原型為嚴歌苓的祖父嚴恩春先生。他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后在廈門大學教書。嚴歌苓曾經透露“她的祖父是一個神童,十六歲上大學,二十五歲讀博士,之后有著長達20年的大西北監獄生涯”,后來嚴先生在對時局的失望中自盡。盡管是在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條件下,嚴歌苓認為這本書一定要寫,是她需要完成的一件作品,是祖父的一生。同時她的父親在“文革”勞教回來后,一直處在一種逍遙或者是消極的狀態,總是在看書,這與小說中陸焉識在婉喻去世后的生活不謀而合。“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不是對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統一體,或一種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實在以及歷史理解的實在。”[4](P384)嚴歌苓的生活中存在著這種悲劇性,作者在小說中體現出來的悲劇意識是順手拈來,水到渠成的。“悲劇意識是悲劇性現實的反映,也是對悲劇性現實的把握。”[5](P3)
二、悲劇意識的體現
在整部小說中,悲劇意識貫穿前后,在每個人物形象上都有體現。有面對生死的考驗,有人性和道德的泯滅,有內心渴望自由的掙扎,有無力和無情的懦弱。唯有對人物進行深入的剖析,我們才能更好的把握小說蘊含的悲劇意識。
(一)社會悲劇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提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6](P135)人的生活受社會制約,社會的發展由人促成,人與社會互相影響。大社會歷史背景條件下,人的行為必然會受社會的影響。小說主人公陸焉識,1907年出生于上海的富貴人家,青少年時期家境富裕,生活優渥。1928年去美國留學,在美留學的五年里過著花花公子般的生活。視野開闊、興趣廣泛,且沒有耽于學業,“二十四歲的陸焉識披上了博士袍、戴上了方帽子。”[3]回國后由于種種原因開始了顛沛流離風雨漂泊的坎坷半生。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軍閥混戰,戰爭煙云籠罩著整個上海灘,學術圈也掀起了“左右”的爭論,作為某大學的教授,一名知識分子本無意加入任何陣營,但還是被裹挾其中,這也為日后埋下了隱患。戰爭的來臨,他不得已跟隨學校搬遷,前往重慶。滿腹經綸的陸教授堅持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在無教科書的情況下,用自己記憶里的教科書來授課。陸焉識的這些做法沒有錯,錯的是處在一個敏感的政治環境中,違背了“所有教員的教案必須報批,不經批準的教案是犯規教學”;錯在政治恐怖時期,本應謹慎言語、小心行事的他卻發文諷刺當時官員的做法,這為他招來了第一次牢獄之災。1945年返回上海后,此時的上海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掠奪”。陸焉識因被捕過丟失了工作,雪上加霜的是家里的房子又被政府腐敗官員勾結的青紅幫給霸占。戰爭把他“變成了這么個肯服軟、不吃眼前虧、拿熱臉去貼人冷屁股的人了”,[3]讓一個精通四國語言的留美博士變成了一個沒用場的人。社會悲劇造成個人悲劇,此時的陸焉識無力掙扎,滿腹失望。他清醒的認識到當前的形勢不可改變,唯一可以調動的是手中的筆桿,企圖掩耳盜鈴式的一吐為快,卻一次次栽在筆桿下。
50年代初,陸焉識以“反革命”的名頭被關進監獄,判了死刑,在妻子婉喻用盡尊嚴的幫助下改判為無期。在漫長的二十多年的勞改中,將一個知識分子磨去了棱角,不敢妄談一切,連尊嚴一并丟棄在西北的勞改場中。活著成了生命的動力,自由早已離去。陸焉識變得膽小甚微,生怕一點點的過失為自己招來臭罵、戴紙鐐銬、罰跪或者罰飯(在1961年的西北荒漠中,不惜去吃冒領的死人口糧,饑餓讓罰飯僅次于死刑),無論哪種懲罰對一個心高氣傲的知識分子來講都代表著屈辱,然而他卻變得麻木。
因為自己“反革命”的罪行,除了妻子,孩子都在盡量遠離他,與他劃清界限,陸焉識甚至成了孩子們口中給他們帶來一身麻煩的“老頭子”。政治環境的壓迫讓陸焉識的子女心驚膽戰,甚至羞于承認自己有父親。因為父親,小女兒一直未嫁成為大家嘲笑的“老姑娘”,兒子失去了心中的摯愛。陸焉識被釋放后,他已經不敢冒然回家。社會和時代的悲劇,剝奪了陸焉識身上的一切,他的坎坷不幸成為悲劇沖突的表現。特殊的時期和政治環境造成了陸焉識不可避免的磨難,所以他的性格注定了他不能獨善其身。作者對這些悲劇沖突的處理和環境的鋪墊,使小說讀起來更增一分悲涼意蘊。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歷史、自然環境等原因,小說人物經歷的磨難,也是當時社會的反映。60年代的“三年困難時期”,食物成為最匱乏的物質,很多人為了填飽肚子活下去,不惜丟掉自己的尊嚴,內心丑陋的一面在活著面前不值一提。在西北荒漠的草原上,文中的梁葫蘆、徐大亨、張現行等人不論是吃樹皮、冒領死人口糧還是扒老鼠洞的糧食吃,都是在當時社會環境下為了活著對生命做出的努力。
(二)愛情悲劇
陸焉識和婉喻的愛情是小說的主線。繼母恩娘想用娘家侄女婉喻在陸焉識身上打一個“如意結”,軟硬兼施的讓陸焉識娶了婉喻。這段婚姻沒有感情基礎,陸焉識對婉喻生不出任何好感,他借助出國留學來暫時逃避婚姻帶來的桎梏。在國外他自由的和意大利姑娘望達擁抱接吻,他心中有愛,但不屬于婉喻,屬于婉喻的是名份、是卑微。陸焉識回國歸來面對前來迎接的親人,他甚至忽略掉這位“期盼干了眼睛”的妻子,他對婉喻是憐憫,和愛情沒有關系。但婉喻對他充滿了敬仰,她戰戰兢兢、小心翼翼的聽從命運的安排,一邊是婆婆兼姑母對陸焉識的扭曲占有,一邊是丈夫對自己的無愛婚姻。她順從的接受,扮演好妻子的角色,傳統妻子的優良美德在婉喻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而有了女兒后的陸焉識,即便有著照相機般記憶的人,有時竟然記不得婉喻的模樣。父母之命的無愛婚姻戕害著男女雙方,本應生出的溫暖、甜蜜卻被凄涼、冷落替代。
在重慶期間,陸焉識認識了重慶女子韓念痕。陸焉識對韓念痕生出激情之愛,韓念痕也愛上了這位才子。韓念痕的愛熱烈、勇敢,兩個人在精神上契合,這種自主的戀愛讓陸焉識欲罷不能,但是又做不到拋妻棄子。敢愛敢恨的韓念痕最后退出了這份愛情。她是聰明的,為愛情心甘情愿的付出,在這無望的愛情中掙扎過后去尋求自己的生活,但也從側面說明這是愛而不得的悲劇。
在陸焉識以“反革命”為由被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后,婉喻對陸焉識的愛始終沒變,她敬仰、愛慕丈夫,按時去看望,不管多遠的路程,并且傾其所有帶上給他的補品。“婉喻的十根手指尖都被螃蟹蟄爛了,皮膚被微咸的汁水腌泡得死白而多皺,每一個蟹爪尖,無論怎樣難摳嗤的犄角旮旯,婉喻都不放過,不舍得浪費一絲一毫的蟹肉。”[3]婉喻的愛細致、體貼、勇敢、平靜,她努力地做好一個妻子,付出自己的愛。然而,陸焉識對這個以傳統的方式得來的妻子仍然沒有愛。此時的陸焉識尚且不知他的“死刑”改判為“無期”,是因為妻子對自己愛得太深沉、不惜放棄自己的尊嚴和身子換來的。婉喻的愛是在個人悲劇的鋪墊下步步迸發。
在西北荒漠,陸焉識回憶往事,想起婉喻的種種,突然發現自己已經愛上了妻子,只是愛而不知。他在自己的腦海中為婉喻寫了一封封傾訴感情的信,愛情此時成為他的信念。在沒有盡頭的改造中,陸焉識策劃了出逃。他逃跑的目的是為了去婉喻的面前,告訴她,自己是愛她的。然而終究還是沒有站到婉喻的面前說出,只是遠遠的觀望。自首后的陸焉識,為了婉喻和孩子的前途,結束了和婉喻的婚姻關系。社會悲劇造成的愛情悲劇,讓陸焉識明白此時他所能給予婉喻的愛是離婚。婉喻多年的愛等到了回應,悲劇的結局卻包含著溫暖。
當釋放后的陸焉識回到婉喻身邊時,婉喻卻失憶了,她已經認不清眼前的男人就是曾經自己深愛的丈夫,但內心還在一直等待陸焉識的歸來,即使在婉喻臨終時刻她還在固執的守著記憶等待。陸焉識歸來后所做的一切,似乎是一場愛的徒勞,任何表象已經失去了意義,陸焉識已成為婉喻內心刻骨銘心的愛。這種兩人大團圓式愛情結局,散發出一股悲涼和無奈。悲劇沖突的處理凸顯了這部小說的悲劇意識,也包含了另外一種意義,肯定了愛情的存在。
因為父親陸焉識的“反革命”罪行,兒子馮子燁的愛情被扼殺,女兒丹玨的婚姻也被耽擱。小說對這對子女的愛情沒有過多的渲染,但是依然逃脫不了悲劇的結局。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也是對當時社會歷史的反思與正視。
(三)性格悲劇
陸焉識的悲劇從其個人角度分析,主要是因為他的性格造成的。首先他心里清楚婉喻是繼母“從娘家搬來的一把大鎖,來鎖緊不安分不老實”[3]的他,他痛恨這種傳統方式對他愛情的終結,但是他接受了。他采取冷暴力、逃避的方式來驅散內心的不快。這種討好式的委曲求全恰好說明了他的內心缺乏果敢、拒絕的勇氣。“外部嘻嘻哈哈、遷就一切而內部猛烈掙扎”,[3]當不學無術、投機取巧的大衛來找他借論文時,內心明明是鄙視這種行為,但是看到“老朋友這樣潦倒、因為拖欠牛奶公司的費用,孩子斷了奶。他真覺得對不起大衛……”[3]他內心善良,他不允許自己的人品和學品有任何瑕疵,看到朋友的下場又讓他極度不安。善良用錯了地方就是一把刀,是扎向自己的刀。
不識時務、不通世故的陸焉識,被裹挾到政治斗爭中。對學術、對文字他駕輕就熟,然而對人際、對社會關系,他一塌糊涂。自小生活優越的他,缺乏憂患意識,不善生計,知識帶來的自信、清高最終敗給了當時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他身上所具有的知識分子的耿直和堅持正義,在錯誤的時局下帶來的是牢獄之災。中青年時期的陸焉識似乎看不透,最終成為恩娘口中“沒用場的人”。“有一身本事,誤以為本事可以讓他們凌駕于人,讓人們有求于他的本事……但是他們從來不懂,他們的本事孤立起來很少派得上用場,本事被榨干也沒人會繞過他們,不知如何自身陷入一堆卑瑣、已經參與了勾結和紛爭,失去了他們最看重的獨立自由。”[3]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自己缺乏足夠的認識。
在西北荒漠改造的二十年,陸焉識的性格發生了變化,有更多的時間去剖析認識自己,自我意識覺醒。他假裝啞巴,讓自己的腦子快于嘴,他學會了察言觀色,保持沉默。曾經因為去送禮請客窘到發虛的陸焉識學會了賄賂、巴結、撒謊,更學會了小心翼翼的為人處世。但善良本性卻始終未變,寧愿冒著被“鄧指”槍斃的危險,都未曾說出穎花兒媽的事兒。
三、悲劇意識中的自由意識
“悲劇意識蘊含自由意識。人在既沒有達到目的的絕對可靠能力,又沒有上帝、他人可以依傍,但又不愿意放棄生存發展權利的情況下,只能冒險地、獨立自主地承擔生存發展的責任……只有自由,才能使人超越生存恐懼,發掘生命潛能,張揚生命力量,為生存發展創造可能。”[2]在這部小說中作者傾注巨大的激情去寫自由,文章的首句就寫道:“草地上的馬群曾經是自由的,黃羊也是自由的,狼們妄想了千萬年,也沒有剝奪他們的自由。”作者借助陸焉識的形象表述著知識分子對個人精神自由的追求。陸焉識逃離婚姻實則是為了逃避那個傳統的方式,逃避別人強加給來的愛情,他追求的是自由的愛情。在陸焉識的眼中,沒有自由,不配享受戀愛,他追求婚姻自由。在國外與意大利姑娘的戀愛是自我意識下自由迸發的愛戀,不受約束和羈絆。在重慶與韓念痕的愛情,是精神上的契合,他“想的多半不是她的身子”,超越肉體上的性愛,是精神上的迷戀。
在留學歸來的游輪上,他哭泣自己即將逝去的自由。工作后,他常常流連于咖啡館和圖書館來完成自己的學術文章,他受不住夾在恩娘和婉喻之間的被動局面,此時的他追求著身體上的自由。當純粹的學術文章也會引來一派又一派的紛爭時,他發現自己竟然喪失了學術自由。失去自由的陸焉識倍感恐懼,這對他意味著自己最重要一切的失去。在重慶教學時,他向學生宣傳自由,他的內心對自由極度的渴望。陸焉識深受東西方文化的影響,游走在現實和理想之間,內心堅定的獨立自由意識,在現實中一次次遭受到碰撞。自由是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自我覺醒和追求,是追求平等、追求愛情、追求人生的自由。
在西北荒漠改造的二十年,精神文化的匱乏,政治的嚴苛,部分惡毒犯人為了獲取丁點的利益不惜傾軋揭發,喪失的不僅僅是陸焉識行動的自由,作為知識分子的體面、尊嚴一并被踐踏在泥里。第一次的出逃,看著眼前的妻子和孩子,只能偷偷地觀望,“反革命”的罪行剝奪了他的親情自由,這是他在荒漠中支撐他活下去的動力和信仰。被釋放后的陸焉識面對婉喻的失憶,重獲愛情自由的他失去了機會。在親情的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兒子的嫌棄和利用,女兒的埋怨,親情的自由似乎在形勢的逼迫下已經喪失,筑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悲劇性人生。
婉喻的失憶是她重返自由的形態,婉喻的一生悲憫又卑微,她用自己的愛來堅守愛人,堅守整個家庭,失憶在某種程度上對她是解脫,是自由的釋放。一生規矩、獨立又隱忍的女人在患病后,去除了任何他人或自己對內心的束縛,如同孩童一般。然而,無論記憶怎樣的丟失,唯一留下的是對愛人的期盼,在美好的幻想中離開。在悲劇意識形態下,為婉喻的執著和她的命運更留悲感。
自由和不自由始終是相對的,陸焉識的內心是自由的。晚年的他在沒有自己位置的家里,帶著自己的愛情一起奔向了曾經禁錮他自由、給予他心靈自由的廣闊草原。壓抑的情感讓人唏噓,小說充斥著荒誕悲劇的美學意義。
四、結語
嚴歌苓以陸焉識和婉喻的愛情為主線,以對自由的向往追求作為內涵,小說從孫女的角度來講述,平靜而悲涼的記錄著屬于他們的生活痛楚。然而,這并沒有簡單地停留在表面,而是利用細膩的筆觸,將上一代人的生活、環境、人性的變化,層層深入,挖掘每個人物的靈魂,直擊人的內心,較強的畫面感展示了那個時代生活的片斷。苦難時代下人們的悲慘遭遇,無論是社會時代,還是投射在每個個體身上的苦難,都是經過咀嚼含淚前行來追逐內心自我意識肯定的形態,這也是小說苦難凝聚而成的悲劇意識的價值所在,散發著悲劇藝術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