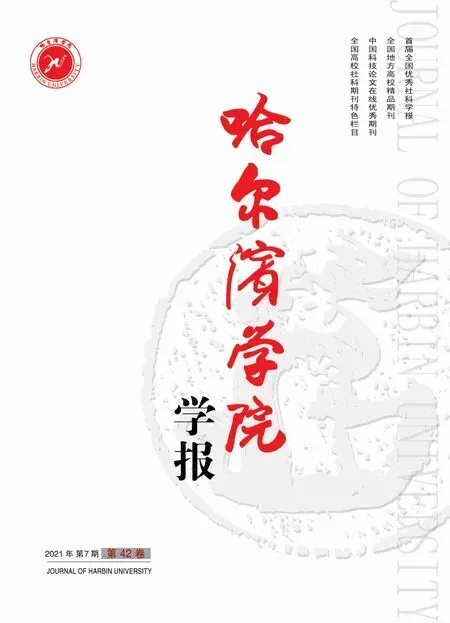時間的肌理:《愛達或愛欲》的時間論述
周漪颯,孫艷萍
(浙江大學 外國語學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時間的肌理”是《愛達或愛欲》第四部分中一篇類似論文的論述,有很強的柏格森的思想色彩。納博科夫閱讀柏格森已不是秘密。在《愛達或愛欲》尚在醞釀的一九六四年,談起柏格森,納博科夫依舊將他視作最喜愛的作家之一。而后為了完成《愛達或愛欲》①中的某個故事,柏格森的《物質與記憶》(MatterandMemory)成了他的首要參考書目。格里沙克瓦(Marina Grishakova)在其專著《論納博科夫小說中的時空及視覺模型》(TheModelsofSpace,TimeandVisioninV.Nabokov’sFiction)討論了柏格森的記憶觀對《愛達或愛欲》的部分直接影響:“納博科夫時間性的主要原理也是不同時間尺度的變化,以及這些尺度之間的相互干擾及位移。表面清晰的時間模式被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所模糊。”[1](P75)由此,納博科夫的時間似乎也出現了近似于柏格森的二元時間模型。②這好像在說明,根據衡量時間的參照物的不同,時間會出現分歧。但隨后,納博科夫表示,“就哲學而言,我完全是個一元論者”。③[2](P72)在柏格森尋求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的平衡點時,納博科夫在《愛達或愛欲》中無疑將精神世界放在了更優越的地位。“時間的肌理”展現了納博科夫對柏格森的繼承與批判。
一、時空可分
主人公凡·維恩希望能檢視“時間”的本質,而非其流逝,“因為我不相信其本質可能化約為其流逝。”[3](P510)納博科夫說:“當我們說‘時間的流逝’時,我們就會想象一條抽象的河流,它從一般的景物中流過。應用時間是時間的可測量的幻想,它對歷史學家和物理學家的目的而言是有用的,但它不能吸引我,它也不能吸引《愛達或愛欲》第四部分中我的人物凡·維恩。”[2](P182)納博科夫區分了時間的本質和流逝,指出“時間的流逝”是一種混入了空間概念的偽物。由于“太習慣于那種神話式景觀,太熱衷于將一片片的生活悉數液化,以至于說到時間,則言必稱動”,類似流逝的動態感受是由“身體對其血液流動的內察,由星辰升起所引發的、古已有之的暈眩感,當然還要歸因于我們的測量手段,例如日晷緩緩挪動的影子,沙漏的涓涓細流,秒針的滴滴答答”[3](P514)引發的。類似的時間的具體想象來自于空間內的物體、結構和框架,因此這樣的想象并不能代表時間的本質。“流逝”是虛假的,也并非納博科夫和凡所關注的目標,僅是沿著尺度流淌的隱喻。
因此在對時間進行剖析之前,“時間的肌理”首先闡述的是“時間和空間可分”。凡直敘胸臆地表明:“我們問心無愧地反對沾染或寄生了空間的、矯揉造作的時間概念,反對相對論寫作的時空。”[3](P514)空間無法脫離于時間存在,而時間卻可以獨立在空間以外。“面對‘空間’里的同一塊區域,一只蒼蠅或許會比S.亞歷山大更感到此地的闊曠,但某一時刻之于他并非‘數小時之于蒼蠅’可比擬。”[3](P516)在納博科夫和凡看來,時間是一種高等智慧生物才能產生的思辨性概念,理解時間的最低門檻就是要求有智人意識的加入。昆蟲、動物或普通的物品是不存在時間概念的。人的意識在判定時間時起到了前提性的作用。再有,跨越空間也并不需要時間。凡的空間跨越不僅是物理的,也可以是一種心理上的聯想,比如看到某符號想起了什么。這時,對于此符號的目睹者“對于一個空間單位可觸知的占有,實際上是一瞬間的事”,[3](P515)是心理上的瞬間感覺昭示了某物的位移,而并非是常識內的“經過了一段時間,物體才發生運動”。時間甚至沒有參加到運動過程中去。所謂運動,一是經過了“純一的并可分的空間”,二是“在經過空間時發生了不可分的動作,并且只對于意識才存在”。[4](P82)納博科夫的瞬間感實際上指的是柏格森筆下的第二點,這是在極短時間內發生的感覺綜合,“我們由以經過空間的動作、或先后的位置以及對于這些位置的綜合。它對于意識才是存在的。”[4](P82)
二、時之“構成”:過去、現在和未來
“時間的肌理”第二部分的內容包含了對過去、現在及未來的看法,其中,對過去的論述是“時間的肌理”的主要組成部分。唯有縱觀過去,才能“觸碰”時間。總體來看,過去是“感覺資料的積累”,[3](P518)是“影像的不斷累積”,是“一團恢弘的混沌,一個能夠回憶一切的天才”。[3](P519)即是說,意識可以存儲所有感官帶來的感覺及圖畫并隨心所欲地讓其在腦海中重現,這似是過去的萬能之處,但“對于這些意象所織就的時間之肌理,它們什么信息也不能告訴我們”。[3](P519)王安強調了意識在面對信息量龐大的過去時所表現出的“挑選”能力,“小說對時間的論述,其核心內容為個體可以以意識的武器對抗客觀時間的流逝,讓過去五彩繽紛的意象顯映在記憶的魔毯上”,[5]表示“意識可攫取綿延的時間之河的某個斷片,使之在思想中靜止”。[5]但這樣的說法并非是納博科夫所想表達的本意,先不說“時間的流逝”這樣的說法被納博科夫否定,對于人和時間的關系,納博科夫更強調一種“感官所能帶來的直感”,并通過這種感覺去感受時間,而不是有意識地對時間進行加工。同時,顯現在記憶魔毯上的過去意象以“流逝的時間”為參照物,外部時間是動態的,而人的意識在顯現回憶時進入一種封閉又靜止的狀態,反倒顯露出一種因人無法抵御客觀時間而流露出的自我安慰及盲目樂觀精神,這也是一個不準確的地方。
納博科夫和凡借“過去之恢弘”所想表達的并非是強大的意識主觀作用,同時,過去包羅萬象的特點也并不是揭露時間本質的關鍵。即使過去包含了堆積如山的信息量,但依舊無法在其中發現一種確定無疑的、用以暗示時間的事物。就算是一件使用了多年的物品,看似包含了時間的痕跡,但在不同時段相互借鑒的印象所在腦海中組成的復合圖像只是一種視覺上的效應,依舊未有脫離空間因素,因此并未暴露于“時間”運動之前。
凡說:“我們對‘過去’的認知,其標志并不在于一連串相互關聯的環鏈。”[3](P520)將過去認識為環鏈是由于三維空間概念的悄悄引入:必須要立足于“環鏈”之上,看出環鏈以外的空虛及環鏈未被剪斷的前部,才能得出線條的形狀。假如一個人未有空間概念,未有對線條及形狀的認識,那么他會將感官接收的種種感覺組合起來。就在這個組合的瞬間過程內,過去才得以產生。
為了更清楚地闡述過去,凡舉了一個例子:“……記憶意象包含了聲音余像,可以說這是耳朵對在片刻之前(那時人正集中思想使自己不碰撞到小學生)錄下之聲音的回放,于是事實上,我們在離開特森之后依然能重放教堂鐘聲的音信,以及其背后寂靜但響徹著回聲的尖塔。對于剛剛發生的‘過去’的最后幾階段的回顧,與鐘表機構的運轉比起來只花費較少的物理時間,正是這一較少才成為仍然鮮活的‘過去’的特性。‘較少’暗示出,‘過去’無須鐘表時間,而更意味著與‘時間’之真實節奏的協同。”[3](P521)這表明,過去只是歷史時間內發生過的事件性質的瞬間閃現與雜糅,并組合而成的復合體,是這意識世界以內的極短時間發生的性質變化。就算離開了教堂鐘塔,其鐘聲依舊會在腦海中縈繞。把握住腦海內的鐘聲甚至不需要刻意去回想,也能在極短的時間內把握它的總體印象。需要注意的是,當大腦重新回放這樣的鐘聲時,腦內的聲音并非像真實的鐘聲那樣一下一下響起的(除非特殊情況,我們也不會記住每一次鐘聲),而是按照自己的組織方式將其組合起來,播放著鐘聲的印象。因此把握住的只是任意復數次鐘聲所組成的一種“復合調”。該復合調的組成單位上并無明顯的分界,和數目及次序完全無關,只是一團混沌的粘合體。過去是一個由過往的無數瞬間組成的性質的組合體。
現在和未來相比過去要次要得多。現在是一個人能夠直接而實在地意識到的時段,因為現在實在太過短暫,讓人無法真正把握“當下性”,而顯得像停留于意識內的一個虛幻的點。“此時,‘現在’之風吹拂在‘過去’之巔——其下是層層我生命中,在最清晰的意識中引以為豪的路坎——厄姆布雷爾、弗盧卡、福卡!在感知的那一瞬間發生了改變,只因我自己處于持續不斷的細微蛻變之中。”[3](P522)刻意去感受現在時的心理感受發生了變化,意會“自作多情”地留下當下的內容,并將此作為現在存在的痕跡。“持續不斷的細微蛻變”即上文已提到的意識將各種接收到的信息進行組合雜糅的過程。在這樣的過程中,過去和現在不可分地連接著。凡也指出,當人刻意去感受“現在”時,需要以意識去占有“空間”的一部分以留下余跡,這是時間與空間的唯一接觸。
未來被凡稱為“虛時間”,并不能算作時間的一個單元,它充其量是一種還未到達的可能性的集合。我們通常所說的“預期”或“預計”只是對現有事項的、按照邏輯的推演或期望。“至多,‘未來’是關于一種假設的現在的理念,其基礎在于我們對事物演替的體驗,在于我們對于邏輯和習慣的忠實。”前方,是可能性的集合體,它吸納著無數個連續的瞬間。[3](P532)未來并不處于“現在”的,對無數瞬間呈現一種開放的狀態。我們平時生活中總是將未來也許發生的一種可能性認定為事件。因為可能性的瞬息萬變和無窮之多,我們無法把握未來,“未來始終游離于我們的幻覺與感覺之外。每時每刻,它都是蔓生的可能性的無窮集合。”[3](P532)正如博伊德所說的,“在經歷過先前那個標記過的‘現在’之后,盡管每個‘現在’都有這樣或那樣精確的形狀,但這并不意味著這樣的形狀是必要的,只是‘碰巧如此’。”[6]
三、“時間即節奏”
《時間的肌理》第三部分的內容為“時間即節奏”,但不僅僅是節奏。“或許唯一暗示了時間之感的東西就是節奏;并非節奏的那種周而復始的律動,而是律動之間的空隙,黑色律動之間的灰色空隙:‘溫柔的間距’。富有規律的脈動本身又令人痛苦地想起了計量,然而就在其間,便潛伏著類似真實的‘時間’的東西。”[3](P512)“節奏是音樂中重復出現的、有規律的格式。”④一段節奏的律動需要節奏點與節奏點間的空檔才能組成。或許會如下理解:如若將凡和愛達的每一次團聚作為節奏點,那么在兩人每一次分離后分別經歷了四年、四年、八年和十七年的空檔。在每一次相會的間隔里,歲月不知不覺地溜走了,由此形成了一段不均勻且急緩結合的節奏。這似乎是符合納博科夫和凡的敘述的。
但在解讀《時間的肌理》時,正如先前所說的,必不能將空間概念引入納博科夫純一的時間世界內。如若我們這樣理解“時間即節奏”這個觀點,我們就是再次在無意識內承認了時間的線形延展。雖然凡有意對事件做了普通常識內的標記(如年份),但這個人為的標記充滿了虛假,否則也不會夾雜了諸多歷史事件的顛倒和拼湊。即使凡也不可避免地使用了“間距”這個在空間內才有存在意義的詞:只有在空間以內,間距才會產生。納博科夫也說:“雖然時間與節奏相似,但它不僅僅是節奏,節奏意味著運動,而時間不移動。”[2](P82)
通常所說的節奏是一種一以貫之的固定性,最早出現在音樂及詩歌中。據說納博科夫在寫作這部分手稿時,摘錄了大量惠特羅的文字,包括十六張卡片上寫納博科夫對惠特羅的解釋:“……似是而非的呈現:可能持續幾秒鐘,很少超過五秒鐘;它被定義為在統一理解的行為中保留的一系列連續事件,就像土地中空處的水。”[1](P7)也就是說,節奏的產生依靠連貫的意識對事物的連續捕捉。本文在此做一些柏格森的節奏說的補充,為理解“時間即節奏”提供另一個視角。柏格森認為,節奏能夠降低人格的抵抗能力,使心靈呈現一種開放的、準備接受外來的影響的狀態,由此通過我們的感官連接我們的內部意識和外部事象,從而使心靈內部充滿了共鳴與感情:“節奏的抑揚頓挫麻痹了讀者的心靈,使他忘記了一切,使他如在夢里一樣跟著詩人一樣想和一樣看;但是如果沒有節奏的抑揚頓挫,則這些形象再也不會那樣強烈地呈現在讀者的心目中。”[4](P11)從廣義來說,物品上也有節奏的痕跡,比如建筑物的對稱,是一種形式上的節奏重復。在節奏出現時,由于人的注意力在指定的時刻間搖擺,日常的感覺和觀念在心靈內停止流動了,而被外界環境灌輸了他人的情緒,處于一種情感被感染的審美狀態之內。在《說吧,記憶》中,納博科夫精準地描寫了一顆雨滴在葉片上的下墜過程:
沒有任何風的吹動,一滴在一片心形樹葉上閃爍著的、享受著寄生的舒適的雨點,完全是由于本身的重量,使得葉片的尖端開始下垂,看起來像是一個小水銀球的東西突然沿著葉片的主脈表演了一曲滑奏,接著,擺脫了它晶瑩的重負的葉片又伸直了起來。葉尖,葉片,下垂,解脫——發生這一切所占的瞬間對我似乎更像時間的一道縫隙而不是時間的一個片段,心臟的一次缺跳,立刻被一陣連珠炮般的韻律償還了……[7](P293)
葉片的下墜到反彈在形象上本就和節奏很契合。在意識被葉片吸引而放下警惕,意識呈現開放狀態中,葉片弧度細微的變化向童年的納博科夫傳遞了有關時間的暗示。在注意力完全被吸引而顯得心靈中“空無一物”時,“心臟的缺跳”感也由此產生。凡的初戀“會優于他的初次傷痛或者第一次噩夢”,也是因為他被以真亂假的玫瑰震撼了,驚奇感在那個瞬間完全奪走了他的注意力:“他隨手撫摸了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他以為指尖會觸及毫無生命的質地,而沁涼的生命卻以噘起的唇吻了他的手指”,[3](P33)且玫瑰的意象在凡的回憶內反復出現。
四、結語
“時間的肌理”作為《愛達或愛欲》中論述時間觀點的重要部分,表現出柏格森給予納博科夫的靈感,包括柏格森對于混淆的“時空”概念的辨析以及對節奏部分的論述。但相比柏格森對兩種時間的同時肯定(空間內的時間、意識中的時間),納博科夫更肯定時間只能由意識把握。對于納博科夫而言,現實難以把握,未來因充滿可能性而顯得神秘而不可知,唯有過去那些給予心靈震撼的瞬間才能代表時間,并強調了心靈在進行審美時的麻痹狀態更有利于感受到時間。
注釋:
①《愛達或愛欲》在草稿階段時的命名為《時間的肌理》。
②柏格森的時間分為兩種綿延,分別涉及廣度和強度。前者外化于空間內,即是一般認知內的時間,可被鐘表測量,為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所研究,它的陸續出現就像“一根連續不斷線條或鏈環的樣子,其各部分彼此接觸而不互相滲透”。后者則屬于純意識領域,純粹而沒有空間雜物的介入,是真正的綿延。“這些變化互相滲透,互相融化,沒有清楚的輪廓,在彼此之間不傾向于發生外在關系。只是純粹的多樣性。”內心現象就是瞬息萬變且無法為人所察覺的混沌,只有發生質變后才能察覺它的存在。“在這種時間中,現在總是包含了過去并攜帶著它走進未來。過去、現在、未來不可分割地連接著。”
③出自1967年的《威斯康星研究》采訪。該采訪隨后提到了《愛達或愛欲》尚在寫作中。
④該解釋來自《牛津英漢高階詞典》。